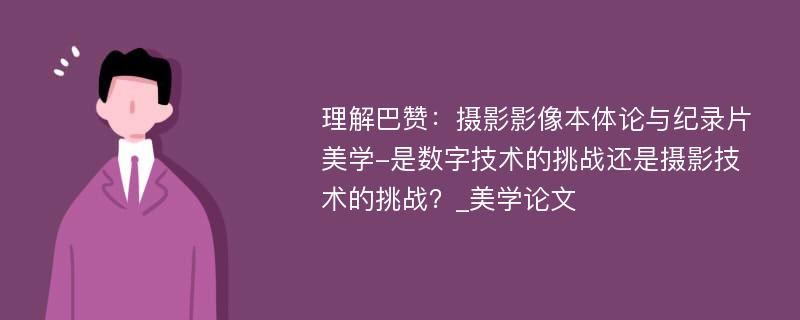
理解巴赞:摄影影像本体论与纪实美学——是数字技术的挑战还是摄影技术的挑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本体论论文,美学论文,纪实论文,影像论文,摄影技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J90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6522(2008)04-0030-05
2008年是法国电影批评理论家安德烈·巴赞(1918—1958)诞辰90周年和逝世50周年纪念。巴赞英年早逝,从事电影理论批评活动只有短短的十余年,但却为人类留下了一笔相当丰厚的电影理论批评遗产,在全世界的范围内产生了持续而深远的影响。更重要的是,他的电影理论批评对电影创作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几乎可以说是开创了一个全新的电影时代,其影响范围之广,影响时间之久,堪称电影理论批评对电影创作产生重大影响的一个几乎是绝无仅有的特例。巴赞和法国电影新浪潮的关系以及和新浪潮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的特吕弗的关系,成为世界电影史上的美谈。现在电影和电影理论都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两者却越来越不相干,在人们不断地宣称巴赞的理论受到了挑战和被超越的今天,总结和清理这笔遗产就变得十分重要了。
由于巴赞的影响和巴赞对电影的强烈热爱,今天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理解巴赞。而纪念巴赞的最好的方式就是理解巴赞。
一位美国学者曾说,“哲学始于语言放假的时候”,“哲学本身就是交战的学科”。这两句话都不错。但在我看来,后一句话中的“交战”改为“争辩”更好。人们说完了话,就给自己放了假,不再用语言追究自己的话。但哲学没有给自己放假,哲学始终有着追究语言的责任。我们就想用这样一种方式来理解巴赞。
在电影理论发展史上,巴赞以其电影理论批评活动成为经典电影理论中与蒙太奇理论相抗衡的纪实派理论的最重要的代表人物。蒙太奇理论的代表人物是爱森斯坦和普多夫金。纪实派理论的代表人物还有克拉考尔。美国学者汉德逊把蒙太奇理论称为局部与整体关系的理论,把纪实派理论称为电影与真实关系的理论。虽然他承认,前一种理论的范例是爱森斯坦和普多夫金的理论,后一种理论的范例是巴赞和克拉考尔的理论。但是,他却认为,在这四个理论家中,最好和最有影响的是爱森斯坦和巴赞。汉德逊尖锐地指出,爱森斯坦和巴赞的出发点都是真实。但是,他们实际上并没有给真实下一个定义,也没有发展任何有关真实的学说。在一定程度上,他们各自的理论都是建筑在他们自己尚未弄清楚的真实这一概念的基础之上的。他们之间的主要差别之一是,爱森斯坦超越了真实(超越了电影与真实的关系),而巴赞却没有。事实是,巴赞在理论上没有,但是在实际的批评活动中却超越了真实。这才是问题的关键。
巴赞主要是一位电影批评家,其次才是一位电影理论家。应该注意,这两者是有区别的。特别是,他作为一位活跃的批评家,成为二战后电影纪实美学的积极鼓吹者。他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对抗爱森斯坦的蒙太奇形式美学。爱森斯坦的理论活动是创作经验的总结并直接为创作服务,与爱森斯坦不同的是,巴赞的理论工作是为他的电影批评服务的,是为他通过批评大力倡导电影纪实美学服务的。巴赞大量使用的是现实主义。爱森斯坦不需要为他的蒙太奇理论的合法性操心。而巴赞却需要为他的纪实美学的合法性进行论证。这就是他提出“完整电影的神话”理论和电影影像本体论的主要目的。巴赞从1943年开始从事电影评论活动,先后担任过《法国银幕》、《精神》和《观察家》等杂志的编辑和撰稿人,1951年与人创办《电影手册》,担任主编。在《摄影影像的本体论》、《完整电影的神话》、《电影语言的演进》等论文中,相继提出了电影起源于心理学、电影影像的本体论和电影语言的进化观等理论。
我们早就应该认识到,纪实美学的合法性是不需要论证的。纪实美学天然地具有合法性。巴赞没有必要地指出电影起源的心理学背景是“完整电影的神话”,而我们却有必要指出,巴赞纪实美学起源的心理学背景是他的建立在“完整电影的神话”理论基础之上的“摄影影像的本体论”,正是这一初衷,决定了巴赞的“完整电影的神话”理论的“目的论”错误。巴赞把电影的发明创造及演进过程这样一种自然历史性进程,描绘成一种人格化的“目的论”进程。从科学的角度来说这是一个令人无法容忍的错误。这同时也决定了巴赞的电影摄影影像本体论的局限性。我们经常说,电影是科学技术进步的产物。电影自诞生以来一个多世纪,经历了四次革命——从无到有,从无声到有声,从黑白到彩色,从模拟到数字,在这一过程中,科学技术进步始终扮演了决定性的角色。但是,巴赞却说:“我认为,在这个问题上,确实应该把经济基础决定思想意识的上层建筑这种历史因果关系倒过来,把基本技术的发明看做是偶遇的巧事,与发明者的预先设想相比较,技术发明基本上是第二性的。电影是一种幻想的现象。人们的设想在他们的头脑中已经是完备的了,如同在柏拉图的天国中一样,与其说技术对研究者的想象有所启迪,莫若说物质条件对设想的实现颇有阻力,这一点是相当明显的。”巴赞把电影发明创造的第一位的原因归结为人类有史以来的一个伟大理想即“再现现实原貌神话”的实现,这个理想和神话可以追溯到远古时期造型艺术中的绘画与雕刻的“木乃伊情结”,他还指出,在古代,“这曾经是天经地义的事”,在现代又如何呢?在那些伟大的电影先驱者的想象中,“电影这个概念与完整无缺地再现现实是等同的;他们所想象的就是再现一个声音、色彩、立体感等一应俱全的外在世界的幻景”。电影是从萦绕在那些少数先驱者头脑中的一个共同的理念之中,即从一个神话中诞生出来的,这个神话就是完整电影的神话。当然这也是“天经地义的事”。巴赞以为自己已经为电影本体论奠定了一个坚实的无可置疑的理论基础。
在巴赞看来,完整电影的神话在科学技术的帮助下终于冲破重重阻碍一步一步地实现了,也就是说电影终于诞生了。当然,电影的诞生是一个过程。正如巴赞所说的那样:“因此,貌似悖理的是一切使电影臻于完美的做法都不过是使电影接近于它的起源。电影还没诞生出来呢!”[1]16 必须指出,这一点具有惊人的远见,如果说科学家正在实验中的全息电影才是真正的电影,那么,电影还真的是没有诞生出来呢。
有了这些铺垫,他就可以进行他的摄影影像的本体论描述了:“摄影与绘画不同,它的独特性在于本质上的客观性。况且,作为摄影机的眼睛的一组透镜代替了人的眼睛,而它们的名称就叫‘objectif’,在原物体与它的再现物之间只有另一个实物发生作用,这真是破天荒第一次。外部世界的影像第一次按照严格的决定论自动生成,不需人加以干预,参与创造,摄影师的个性只是在选择拍摄对象,确定拍摄角度和对现象的解释中表现出来,这种个性在最终的作品中无论表露得多么明显,它与画家表现在绘画中的个性也不能相提并论。一切艺术都是以人的参与为基础的;唯独在摄影中,我们有了不让人介入的特权。照片作为‘自然’现象作用于我们的感官,它犹如兰花,宛若雪花,而鲜花与冰雪的美离不开植物与大地的本源。”[1]16 “这种自动生成的方式彻底改变了影像的心理学。摄影的客观性赋予影像以令人信服的、任何绘画作品都无法具有的力量,不管我们用批判精神提出多少异议,我们不得不相信被摹写的原物是确实存在的。它是确确实实被重现出来,即被再现于时空之中的。摄影得天独厚,可以把客体如实地转现到它的摹本上。”“唯有摄影机镜头拍下的客体影像能够满足我们潜意识提出的再现原物的需要,它比几可乱真的仿印更真切:因为,它就是这件实物的原型。不过,它已经摆脱了时间流逝的影响。影像可能模糊不清,畸变褪色,失去纪录价值,但它毕竟产生了被拍摄物的本体,影像就是这件被摄物。相簿里一张张照片的美丽就在于此。这是些灰色的或墨色的、幽灵般的、几乎分辨不清的影子。这不再是传统的家庭画像,而是能够撩拨情思的人生的各个瞬间,它们摆脱了原来的命运,展现在我们面前,把它们记录下来不是靠艺术魔力,而是靠无动于衷的机械设备的效力。因为摄影不是像艺术那样去创造永恒,它只是给时间涂上香料,使时间免于自身的腐朽。”[1]7
巴赞所说的本质上的客观性,实际上是指电影的纪录功能,即再现功能。所说的个性就是电影的表现功能,即效果功能。巴赞的这一段涉及电影影像本体的再现功能和表现功能关系的表述,主要特点是特别突出了电影的客观性,即再现功能。或者从本体论的角度更准确地说是过高地估计了电影的再现功能,过低地估计了电影的表现功能。这是理论表述上的明显失误。这种失误不是历史性的失误,应该说,即使是在当时,也是一个时代性的错误。巴赞观点的错误在于,明显忽略了电影拍摄中色彩、光效以及摄影机的运动等手段中所包含的主观性作用。“外部世界的影像第一次按照严格的决定论自动生成,不需人加以干预,参与创造,摄影师的个性只是在选择拍摄对象,确定拍摄角度和对现象的解释中表现出来。”电影摄影“不需人加以干预,参与创造”,即使是在当时也是相当明显的错误。而在未来,当一切都可以通过计算机编程进行程序化操作,这也是有问题的。但是,他接下来说的话却是正确的:“这种个性在最终的作品中无论表露得多么明显,它与画家表现在绘画中的个性也不能相提并论。”但问题的关键却在于,后面的正确掩盖不了前面的错误。再接下来的话又是明显的错误:“一切艺术都是以人的参与为基础的;唯独在摄影中,我们有了不让人介入的特权。”正确的表述应该是:“一切艺术都是以人的参与为基础的;即使是在摄影中,我们也没有不让人介入的特权。当然介入的方式有所不同。”谷时雨非常明确地指出了巴赞的这一错误:“巴赞把摄影过程中的局部客观性极其主观武断地扩展为全局的客观性,这是非常致命的一个关键性硬伤。”有人这样批评巴赞:“如果映现在胶片上的影像永远只是通过摄影机透镜被感光材料所记载的光影,那么,巴赞的美学体系的确是难以撼动的。巴赞的确可以理直气壮地说:‘一切艺术都是以人的参与为基础的;唯独在摄影中,我们有了不让人介入的特权。’数字虚拟影像生成技术的诞生,使影像本体不再仅仅是由摄影机和感光材料‘按照严格的决定论自动生成’了,与此相反,在数字模拟影像生成的技术背景下,影像恰恰是按照人的意志,随心所欲地生成的。”[2] 这种批评低估了巴赞的错误,把一个时代的错误变成了历史的局限性。
巴赞以为,有了以“完整电影的神话”理论作铺垫后的电影摄影影像本体论描述,他就可以把他的本体论直接变成纪实美学了。我们知道,本体论是可能性,而美学却是倾向性。这个问题对巴赞来说要简单得多:“因此,新现实主义首先是本体论立场,而后才是美学倾向。”[1]321 巴赞的公式是:本体论即等于美学。我们完全可以理解,事实上,恰恰是巴赞的“完整电影的神话”理论决定了巴赞的电影摄影影像本体论的不完整性。前文提到,纪实美学的合法性是不需要论证的。纪实美学的合法性即使需要论证,也不能从电影摄影影像的本体论中寻求,而应该从社会的现实需要中去寻求。但是,巴赞纪实美学的最突出的贡献是,他在他的电影批评实践中,从一种不完整的电影本体论出发,阐发出一种相当完整的电影纪实美学。其中包括表现对象的真实、时空的真实和叙事结构的真实。为实现他的纪实美学理想,巴赞不遗余力地提倡按照长镜头和景深镜头的原则来拍摄影片,并热情洋溢地推崇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的影片。[3] 在这方面巴赞确实是功不可没。事实上,中国的电影理论界也给予了他相当合理的评价。但是,我们可以肯定地说,从一个不完整的电影本体论是绝对发展不出来一个完整的电影语言观的。将电影称为语言是一个大问题,而他的电影语言观却是一个单向度的现实主义的电影语言观。
巴赞还有一个产生很大影响并被广为引用的观点,这就是他的关于“现实的渐近线”的观点。他在《杰作:〈别了温别尔托·D〉》中说:“当然,德·西卡与柴伐梯尼力求使电影成为现实的渐近线。但是,他们最终的目的还是为了使生活本身变成有声有色的生活场景,为了使生活在电影这面明镜中最终像一首诗呈现在我们眼前。电影最终改变了生活,当然,生活毕竟还是生活。”[1]341 绝大多数的人都读不懂巴赞的这句表现得相当无奈的陈述。巴赞发现,尽管他的电影纪实美学已经相当完整了,但纪实美学这个匣子仍然不够大,仍然不能把在他看来所有好的电影全部放到这个匣子里面去。我们在他的电影批评中,还是多少能够看到“无边的现实主义”的影子。聪明的巴赞懂得,“把费里尼开除出新现实主义的企图是荒唐可笑的”,尽管如此,他还是发出了警告,他一会儿说,费里尼甚至超越了现实主义美学,步入了另一境界,一会儿又说,费里尼已经滑到了现实主义的边缘,费里尼再往前跨出一步,就走出了现实主义的边界。[1]346-347
现在我们完全有理由说,电影的纪录功能有多强,也就是说,电影的仿真功能有多强,电影的表现功能就有多强,也就是说,电影的造假功能就有多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应该说电影实际上是现实的平行线。电影是耸立在现实旁边的另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既有现实世界的逼真再现,也有创作者个人的主观表现。
《电影语言学》一书中指出:“数字化正在迅速改变传统意义上的电影,并将电影带入一个革命性的全新的时代。这场革命不仅完全可以与有声电影、彩色电影的出现相媲美,甚至还有过之而无不及。这场革命将使电影真正走出它自己的‘在创造中使用’的‘仓颉造字’阶段。即将开始一个电影的‘在使用中创造’的崭新的阶段。我们必须说,这将是一个影响全人类文明进程的伟大事件。由此,电影语言的发展对于人类的意义必将得到重新估计。就如同有了文字数千年之久,人类才对自然语言之于人类的重要意义给出了重要的估计一样,有了数字之后才可能对电影语言之于人类的重要意义给出重要的估计。在这个意义上,电影语言的意义将不亚于文字语言的意义。”[4]142-143
“在巴赞看来,映在胶片上的影像,是曾经出现在摄影机前的事物的影像,电影只是作了客观的纪录而已;人只是通过电影摄影技术把那一段已经逝去的时间永远留住而已。这种在当时就有问题的表述,在可以运用数字技术虚拟现实中并不存在的事物的影像的时候,在可以使用数字技术处理、加工已经拍成的现成电影作品的片断的时候,使用摄影机拍摄出现在其前面的对象的必要性便从根本上被动摇了。”[4]145 陈犀禾指出:“事实上,数字技术不仅导致了影像本体论的解体,同时也‘消解’了电影自身。历来非常自豪于自身特性的电影潮流现在似乎正融入更大的视听媒体的潮流。它们被称为摄影的、电子的或网络的一部分。电影正在失去它通过不懈努力获得的流行艺术之王的宝座,现在必须和电视、视频游戏、计算机和虚拟现实进行艰苦的竞争。”[5] 但是,按照前面提到的巴赞的“电影还没有诞生”的理念和电影的诞生是一个过程的观点,数字技术并没有导致电影自身的“消解”,而是在“融入更大的视听媒体的潮流”之后,变得更加多姿多彩了。
当计算机可以创作出任何能够想象得到或曾经看到过的影像之时,电影便可以不再用摄影机和胶片等介质来拍摄并通过后期制作来完成,而是可以通过计算机“做”出来,那么,至少在这个意义上,发展到数字电影阶段的电影与现实之间的关系在某种意义上便类似于文字语言与现实之间的关系了。[4]291 巴赞经常把电影同小说、戏剧和绘画的表现力进行比较,特别是小说,他说电影比小说落后了20年。“《游击队》这类影片反证了曾经比当代小说落后了20年,甚至50年。”[1]341 但是,巴赞的思想背景却限制了他把电影同语言文字进行全面比较的可能性,这才是伟大的巴赞的真正历史局限性。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如果巴赞活到大片横行的今天一定会非常生气,即使是他也许会非常喜欢的电影,他也无法把它们放到他的纪实美学的匣子里。
收稿日期:2008-05-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