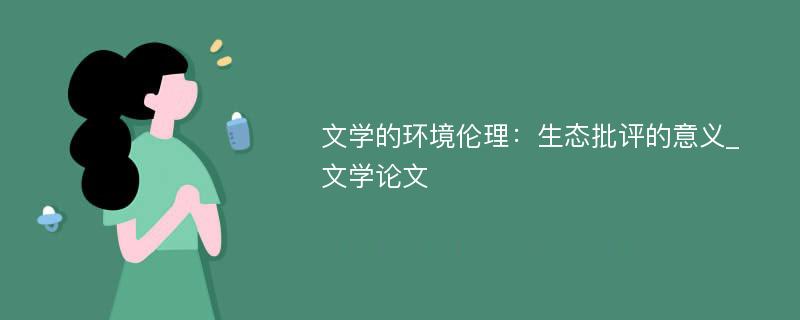
文学的环境伦理学:生态批评的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伦理学论文,批评论文,意义论文,生态论文,环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聂珍钊教授针对最近几年来文学批评理论界和外国文学研究界出现的文化环境的污染和批评伦理的沦丧,提出了一种新的文学批评伦理学(注:参见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文学批评方法论新探索”,《外国文学研究》5(2004):16—24。),他的论文发表以后已经在学术界产生了较大的反响。虽然文学批评伦理学已经是一个在文学批评史上不断被人们提及的老话题,但当今时代重提这个话题并赋予其新的解释则更为意义重大。这恐怕与我们这个全球化时代的新的生存环境和文化环境均有着密切关系。我这里仅想从另一个角度作进一步的阐发:文学的环境伦理学,这不仅是当代西方文学批评理论界十分活跃的生态批评所追求的目标,同时也是我们中国的生态文学研究者可赖以与国际学术界进行对话的一个平台。
毫无疑问,崛起于上世纪70年代后期和80年代初、目前主要活于美国文学批评理论界的生态批评对始于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时的资本主义现代性造成的种种后果是一个反拨。面对全球化时代文化环境的污染、商品经济大潮下的物欲横流和生态环境的破坏,从事人文科学研究的学者不得不对我们所生活的环境进行反思:我们的环境究竟出了什么毛病?人与自然的关系为什么会变得紧张起来?作为人文学者或文学批评家,我们将采取何种对策?对此,生态批评家均试图面对并予以回答。
生态批评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就是人与自然的关系。诚然,文学是人类对现实生活的审美化的反映,因而在不同的文学作品中表现人与自然之间的不同关系就是颇为正常的: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种关系应该是一种和谐的关系,如在华兹华斯和陶渊明的自然诗中,自然被人顶礼膜拜,生活在其中的人甚至试图与之相认同,以达到人与自然的合一。而在少数情况下,尤其是当人们的改造自然、重整环境的欲望无限制地膨胀时,呈现出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就是一种紧张的对立关系,如在麦尔维尔的小说《白鲸》和海明威的《老人与海》中,面对自然的无情和巨大力量,人是多么的微不足道!即使奋力拼搏最后也难逃失败的厄运。因此,人与自然的关系历来就是中外文学作品中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一个老的主题。人类的现实生活总是离不开自然环境,但关键的问题是我们应该如何看待我们所生存的自然环境?究竟是按照客观的自然规律来美化自然还是按照人的主观愿望来改造自然,这无疑是两种不同的自然观。应该说,生态批评家并不反对改造自然,但他们更倾向于前者。从文学的环境伦理学视角来看,文学应当讴歌前者按照客观自然规律对大自然的美化,鞭笞任意改造大自然的不切实际的做法。批评家也应当如此。
长期以来,人们总是希望按照自己的主观意愿来美化自然并改造自然,希望自然能够最大限度地服务于人类,当这种愿望不能实现时往往就以暂时牺牲自然为代价。当然这种“以人为本”的善良愿望是可以理解的。但久而久之,在不少人的心目中逐渐形成了某种人类中心主义的思维模式,认为自然毕竟是人类的附庸,因此它理所应当地服务于人类,并为人类所用。如果不能让人类如愿以偿,人类就要与之斗争,最终迫使“高山低头”,“河水让路”。总之,一定要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让自然屈服于人类的意愿。殊不知对自然资源的过分利用总有一天会使地球上的资源耗尽,导致大自然对人类的无情报复。文学家既然要写出具有理想主义倾向的作品,那就更应该关注人类生活的未来和反思当下生存的危机。生态批评的应运而生就是对这种人类中心主义思维模式的有力回应。生态批评家从德里达的解构主义理论那里挪用了反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武器,将其转化为反人类中心主义的目的。在生态批评家看来,人类中心主义的发展观把人从自然中抽取出来并把自然视为可征服的对象,人与自然对立的观念造成了割裂整体、以偏概全、用人类社会取代整个生态世界的现象,产生了目前的这种生态危机之后果。作为以关注自然和人类生存环境为己任的生态批评家试图将自己的研究视野投向一向被传统的批评忽略的自然生态环境,把在很大程度上取自自然的文学再放回到大自然的整体世界中,以便借助文学的力量来呼唤人们自然生态意识的觉醒。应该说,这在某种程度上与文学批评伦理学是不谋而合的,只是前者强调的自然环境的净化,后者则强调文化环境的净化;前者着眼于整个人类的环境道德,后者则更关注批评家自身的伦理道德。
长期以来,人类在使自己的国家现代化的过程中不惜以牺牲自然和生态环境为代价,做出了不少破坏自然环境的错事。我想我们应当从自身的环境伦理学角度来作一些反思。不可否认,现代性大计的实施使得科学技术有了迅猛的发展,人们的物质和精神文化生产也取得了巨大的成果。但是这种发展同样也催化并膨胀了人类试图战天斗地的野心,促使人们不切实际地提出了征服自然的口号,导致了人类中心主义意识的逐步形成和膨胀。但扪心自问,自然果真是人类可以任意征服的对象吗?人与自然、与周围的环境、与生存在地球上的万事万物的关系果真是可以轻易征服和控制的关系吗?这个问题的答案已经从近年来频繁出现的自然灾害中显露了出来。我们可以回顾一下最近几年内频频发生的地震、火山喷发、台风、洪水和干旱,这些无不在暗示,地球所能承受的被改造性已经达到了极限,它正在向人类进行报复,以其雷霆万钧之势毫不留情地夺去数以万计人的生命。近年来出现的全球范围内的非典的冲击便为人类生命的延续罩上了可怕的阴影,而最近出现在亚太地区的印度洋海啸更是向人类敲起了警钟:必须善待自然,否则将后患无穷!作为文学批评家和人文学者,我们更应该对之作出自己的回应。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来,生态批评在当代理论界的异军突起实际上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对这种人类中心主义思维模式的解构和挑战。但是它的终极目标并非仅在于解构,而是在解构的过程中建构一种新的文学环境伦理学。我认为这才是生态批评的更为远大的目标。
当然,生态批评,作为后现代主义大潮衰落之后崛起于北美的一种新的文学批评理论潮流,目前主要活跃于美国的文学批评界,它既从解构理论那里借用了反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武器,同时也是对现代工业文明的另一种反拨,虽然目前在欧洲大陆并没有得到广泛的响应,但仅仅在北美、北欧和澳大利亚等国家处于方兴未艾的境地,可以预见,它在今后的年月里肯定会有着相当强劲的发展势头。此外,令我们感到欣慰的是,生态批评在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也得到了热烈的响应,出现了一些可喜的发展方向,学者们几乎同时在几个层面从事生态批评理论建构和生态研究实践:一方面,在不受任何外来影响的情况下,(鲁枢元、曾繁仁等)根据中国的生态环境状况进行生态文艺学的理论建构,他们的研究成果一旦介绍到国外或通过英语这一国际性的学术语言的媒介表达出来,定能对突破生态批评界目前实际上存在的西方中心之局限起到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在北美生态批评理论的启迪下,(青年学者王诺、赵白生、宋丽丽等)不断地向国内理论界介绍西方生态批评研究的最新成果,使得国内学者的研究更具有理论的规范性和学术性,并逐步达到与国际学术界平等对话的境地;还有一些青年学者,如韦清琦等,则有意识地在一个跨越中西方文化的广阔语境下,试图从环境生态学的角度对中国当代文学进行重新书写。对此,我们可以乐观地认为,如果说,确实如有些人所断言的,中国的文学理论批评在某种程度上患了“失语症”的话,那么至少在生态批评这一层面上,我们完全可以从中国的本土实践出发,充分发掘中国古代丰富的生态学批评资源,通过与西方生态批评的比较研究,提出自己的理论建构,进而对西方的生态批评学者头脑中固有的“西方中心主义”思维模式产生一定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