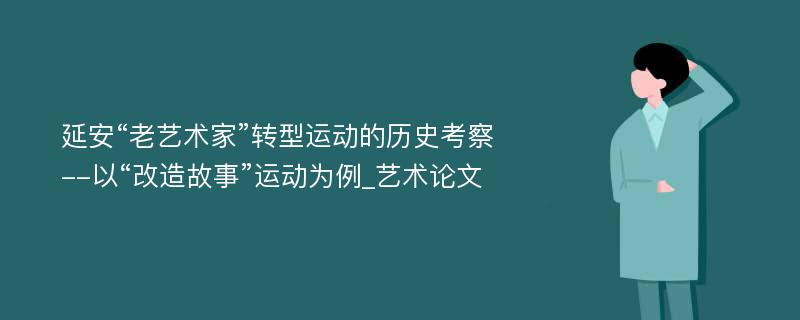
延安“旧艺人”改造运动的历史考察——以“改造说书”运动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延安论文,为例论文,艺人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3-0964(2011)01-0112-05
“旧艺人”改造运动是延安文艺的重要事件,也是中国艺术史上的重大事件,审视这场运动,一些问题是我们必须面对的,诸如为什么要对“旧艺人”进行改造?革命知识分子通过怎样的方式与途径对“旧艺人”进行改造?在此过程中,民间艺人与革命知识分子之间达成了怎样的关系?这些教育改造对民间艺人及其艺术行为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本文将以“改造说书”运动为例,对以上问题进行分析考察。
一
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指出,中国传统乡土社会基本上是一个有语言而无“文字”、甚至几乎不需要“文字”的社会[1]。真正对乡下人的世界观起架构作用的不是学校教育,而是乡间戏曲、民间故事、说唱艺术以及民谣俚曲等民间口头叙事以及民风民俗等民间行为叙事,这种民间叙事行为的主要承担者当然是民间艺人,那些游走于乡间地头“打野呵”的乡野艺人,才是农民名副其实的教育者,是农民文化的主要传承者和型塑者,他们不仅掌握着当地农村的艺术知识,熟悉本土乡人的审美好尚,而且其艺术身份也得到本土乡人的广泛认同。“民间故事每讲述一次就是一次再创作,叙事的核心是故事的讲述人,他们是村落的重要人物,有着自己独特的风格和感染力。正是通过这些讲述人,年代久远的民间故事才与听众的现实世界和历史连接起来”[2]59。同时,“民间故事通过对人事沉浮的反复验证,在人们的朴实意识里为人生提供了注脚。这些民间故事是人类潜在命运的记录”[2]1。在此意义上,民间艺人的艺术行为,不仅仅是乡民单调生活的娱乐和调节,还暗含着对乡民群体谱系的绘制,指向一个群体归宿感的历史深处。
对于民间艺人在农民文化生活中的重要作用,郭沫若在20世纪40年代初的“民族形式”论争中就有所论述,他说,在以农民为主体的解放区,民间艺人就是农民文化的载体和化身,他们最清楚农民的文化需求,最熟悉民间文艺形式。所以,中国文学的民族化、通俗化,不仅要利用民间文艺的语言、形式,其“主要契机”是“民间艺人的被利用”[3]323。不过,此观点在当时并没引起足够重视,直到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民间艺人才逐渐被重视起来。1944年10月30日,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文教工作者会议上发表了《文化工作中的统一战线》的演讲,他明确指出:“在艺术工作方面,不但要有话剧,而且要有秦腔和秧歌。不但要有新秦腔、新秧歌,而且要利用旧戏班,利用在秧歌队总数中占百分之九十的旧秧歌队,逐步加以改造。”“我们的任务是联合一切可以利用的旧知识分子、旧艺人、旧医生,去帮助、感化和改造他们。”[4]1012毛泽东将郭沫若关于“民间艺人的被利用”的观点进一步具体化、原则化,要求党的文化工作者要和民间艺人积极联合,联合的目的是利用,利用的基础或条件是改造,改造的方式与途径是帮助、教育、感化,这就是党的文化工作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每一个革命知识分子必须认真贯彻执行。在此方针政策的导引下,延安文艺工作者逐步认识到团结、改造民间艺人的必要性。
事实上,改造“旧艺人”本来就是中共在陕甘宁边区所进行的社会革命与文化革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共在陕甘宁边区实施的是乡村启蒙与乡村改革相结合,广泛的大众教育运动与农村的社会结构、经济形式的变革同步进行的策略,将农民群体的思想革命、文化革命纳入到民族解放、阶级革命的时代进程。民间艺人既是农民文化的表征与载体,又直接、间接地型塑了农民的文化心理结构,所以,改造民间艺人,不仅有利于重塑传统农民的文化心理,同时也有利于推动农村社会革命与文化革命,因此,民间艺人的改造与利用、知识分子与民间艺人的团结合作乃势之必然。“改造说书”运动就是在这种时代语境下开展起来的,由于林山等革命知识分子与韩启祥等说书艺人的倾力合作,“改造说书”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成为延安改造“旧艺人”运动的成功范例。
二
说书是陕北农村一项古老的民间说唱艺术,在下层民众的日常文化生活中非常普及。与秧歌相比,说书的流动性强,演出也更经常,而且说书所需要的人力、物力非常俭省,一个艺人、一把三弦(或琵琶),在任何地方都可以表演。说书唱书与章回小说、戏曲本子一样,是陕北农民中最流行的三种通俗文艺读物之一[5]。“简单的说书形式,是比秧歌更为适宜农民需要的”[6]140。“改造说书”因此成为延安革命文艺工作者的重大课题。1945年,边区文协正式成立“说书组”,由林山负责,着手改造旧说书。林山认为,改造旧说书的关键环节不是知识分子写新书,而是改造“旧书匠”。对于说书艺人的改造,应该从个别入手,搞出成绩后,再将“旧艺人”组织起来,办培训班集中训练,利用他们的“竞争心”和“重视法令”的胆怯心理进行“旧艺人”改造和新书普及,形成一种运动。在此过程中,知识分子要积极配合,主要从事三方面的工作:1.记录、整理、选择说书人的口头创作;2.发动知识分子与艺人合作创作新书;3.帮助改编旧说书[5]。根据这个设想,林山等人以韩起祥为对象,开始了“改造说书”的实验。
与大多数民间艺人一样,韩起祥出生贫苦,父母双亡,幼年因患天花双目失明。迫于生计,他十三岁就外出拜师学艺,十四岁即登台演出。他记忆力惊人,会说七十多部中、长篇的书,会弹五十多种民间小曲,会唱许多民间小调,还能够自己编写新书。1945年春夏之交,诗人贺敬之发现了他,并将他带到“鲁艺”,会见了音乐家吕骥、马可、安波,韩起祥的才华受到文艺工作者的赏识[7]。从1945年到1947年,韩起祥一直参与“说书组”的工作,与他合作的知识分子先后有林山、陈明、安波、柯蓝、高敏夫等。从1944年到1945年共编了二十四本书,约二十万字以上,被誉为“说书英雄”[8]300,“由一个旧书匠变成一个大家公认的名说书人,一个人民艺术家,一个民间诗人”[9]510。正是由于韩起祥的加入和带动,“新说书运动在短短的时间内(不到两年),就遍及陕甘宁边区”[9]510,全陕北有盲艺人483个,参加训练班改说新书的有273人[9]4。
那么,林山他们通过怎样的方式将“韩起祥们”由“旧书匠”改造为革命文艺工作者?他们之间的合作是如何进行的?林山说:
我们以韩起祥为对象,决心把他培养成一个典型,对他的思想、生活、创作才能、演出技巧、在群众和说书人中的影响,以致他的生活习惯、兴趣等,进行了深入的具体的研究,采用各种方式,先和他搞好关系。然后根据他可能接受的程度,从日常的接触中,从帮助他创作的过程中,一点一滴地提高他的政治文化水平和创作方法。
他的认识逐渐提高后,把改造说书看成自己的事了,我们就用他来带头,帮助我们在延安试办一次小小的说书训练班,“现身说法”……效果大多了。[10]
林山的叙述告诉我们一个事实,即在对旧说书的改造中,革命文艺工作者是从改造说书人开始的,在与“旧艺人”建立良好关系基础上,通过耐心细致的工作,逐步提高他们的政治文化水平和思想觉悟,在此过程中,“旧艺人”具有较大的自主性,革命知识分子主要起督促、帮助与引导作用。但不能因此就认为新书就是出自民间艺人自己的创作,事实上,革命知识分子对民间艺人的新书创作起到了非常重要的“监督”和“引导”作用。
这种“监督”和“引导”作用主要集中在思想观念上。旧社会穷人迫于生计才以卖艺为生,民间艺人长期生活在社会最底层,一年四季漂泊游走,因此,“大都沾染了烟、酒、嫖、赌的恶习”[11],加之他们经常表演的也是那些宣扬封建迷信、帝王将相的陈腐旧事,思想中难免会有很多腐朽落后的东西。因此,所谓“旧艺人”主要不是指他们采用的艺术形式“旧”,而是指他们的思想观念“旧”,不符合新民主主义文化的精神实质,韩起祥也不例外。林山感叹说:“旧社会对他的影响太深了,直到现在,他的思想中还存留着许多落后的东西。”[9]512在此情况下,革命知识分子自然会加强对韩起祥的思想“监管”,不过这种“监管”是春风化雨润物无声的。韩起祥回忆说:“我每一回说书,发现好句子他们就记下来,有错误,他们就告诉我哪些说错了,为什么是错误。在路上走的时候,同志们就给我读文件,给我讲解政策精神和革命道理。我是个农民,好些事情听也没听过,见也没见过,对于党的政策,有的一时解不开,想不通……同志们帮我学一些革命道理,提高了我的政治思想觉悟,我的思想才一天天开阔起来,才知道人活在世上……要为众人着想,树立起为人民服务的思想。”[12]新文艺工作者总是及时将党的时事政策传达给他,并启发他为宣传这些时事政策编写新书。他后来回忆说:“1945年到了边区文协,赶上防旱备荒,同志们说,你是不是编一个防旱备荒的材料?”于是便创作了《张家庄祈雨》。陕甘宁边区开始选举了,柯仲平对他说:“你是不是能编个选举的故事?”[13]他便创作了《张玉兰参加选举》。可见,韩起祥创作的主题选择与革命知识分子的引导是分不开的。
在韩起祥与革命知识分子的合作中,革命知识分子是中共政策的转述者、宣传者,是中共意识形态的共同建构者,同时也是旧艺人的改造者、教育者和引导者。民间艺人在革命知识分子的导引下,逐渐理解并认同了中共思想观念与价值取向,积极主动地参与了中共时事政策的宣传与意识形态的建构。韩起祥自己也说“三弦是我的机关枪”[9]512。说新书是“一段一段宣传人”,是“把新社会的好事编出来,下乡去劝善,去感化人!为老百姓工作”[9]516。连周恩来都赞扬他:“一个人身背三弦,走遍陕北的山山水水,把党的温暖送到群众的田间、炕头,这个方向很好啊!”[14]改造后的韩起祥自觉地将自己的艺术活动同革命的现实需要联系起来,韩起祥编的新书中出现了大量的诸如“科学”、“自由”、“解放”、“人民”、“选举”等主流政治话语和现代性概念,“作品政治化倾向越来越明显”[15]。但我们是否就因此判定民间艺人的创作就是艺术价值不高的“政治宣传品”如果不是或者不全是,这些作品又在多大程度上保有民间文艺和农民文化的本真趣味?
三
尽管革命知识分子在很大程度上参与了韩起祥的新书创作,韩起祥的艺术活动同革命的现实需要关系密切,但这并不能改变韩起祥说书的农民性与民间性特征。
韩起祥说书的农民性与民间性首先表现在创作与表演的方式方法上,他的创作与表演是程式化与变异性的结合。“任何一次民间文学的演说,都是依循一定的模式进行的”[16]78,具有相对稳定的模式是民间文学的本体特征之一,韩起祥的创作与表演同样具有鲜明的模式化和类型性。他说:“编书行当有一句话说得好,‘白是骨头词是肉,内容和故事好比是人身上的血脉,哪些地方应该用唱词,哪些地方应该用道白,都有一定规律的。”[17]229可见他完全是用旧说书的编书方式来进行创作的。“我当时也不懂得文艺的思想性、艺术性,只懂得把好的高尚的词句来歌颂共产党,把丑的坏的词句,骂国民党。像天空、太阳、金灿灿、银闪闪等歌颂党,表彰正气;蚊子、苍蝇等用来形容地主老财……”[17]230这种类型化的人物描述方式也是口头文学区别于书面文学的显著特征。
模式化既是民间艺人创作与表演的需要,也是接受者的心理需求,相对稳定的模式,对听众而言是一种“预期”,对演说人而言是“依据和标准”。在保持相对稳定模式的前提下,民间文艺的独特魅力在于它的变异性。“民间文学的一个被执行的创作机制,在于它不是一次性完成、一劳永逸的过程,它似乎永远没用绝对的定本。在历史的长河中,在流传过程中,它在不断更新,不断变动”[18]97。韩起祥是盲艺人,没法进行书面写作,他的创作过程往往是先想好故事,搭好架子,然后配句子,腹稿打好了,他就坐到板凳上拨动三弦,摇起甩板,随着音乐的节拍,一句一句唱出来了。在演唱的过程中,他遵照听众的意见,逐渐增删、修改。……直到听众没有多少意见了,才不大改动。但实际上,还是在不断地修改着,永远没有所谓的“定稿”,尽管你把它记录下来,发表或印成书了,他演唱时还是要改动的[9]517。林山还强调:“他的创作精神是创造的,他不受什么死规律的限制,旧的也好,新的也好。他自己认为会用的就拿来用。……音韵也不是死板的,他的原则是大体押韵能唱就行。这其实也不是他的独创,而是真正的民间诗歌的传统,韩起祥只是把这传统发扬起来。”[9]517
创作与表演方式的模式化与变异性只是韩起祥说书农民性与民间性的浅层表现,对民间审美趣味和农民伦理道德观的持守才是韩起祥说书民间性与农民性的深层体现。林山说:“他的新说书是直接为农民而创作的,语言和表现方法,都以农民能不能接受,喜不喜欢为原则。这原则他始终坚持着。”[9]516所以,尽管《时事传》是政治性极强的一部书,但是群众认为他编的书“好解下,容易记,说的老百姓话,前前后后有根据。时事说得完全”[19]。他不是生硬的宣传时事政策,而是选择群众熟悉的比喻,既通俗易懂又恰当传神。例如他将毛泽东的名言“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编成两句唱词:“它若不咬咱不招架,它若咬起戳狗牙!”[9]517他的代表作《刘巧团圆》集中反映了韩起祥说书的民间审美好尚与农民价值理念。
《刘巧团圆》(以下简称《团圆》)是根据袁静的秦腔剧本《刘巧儿告状》(以下简称《告状》)改编而成的,但是这个故事在边区乃至后来扩展到全国的影响是因为韩起祥的说书。他将题目由“告状”改为“团圆”,本身就是从文人叙事到民间叙事的转换。“有情人终成眷属”、和谐圆满是中国民间审美主要的心理取向之一,题目的巧妙转换体现了民间审美期待。题目的改变随之带来叙事重心的改变。《告状》侧重表现马专员判案的情节,以表现共产党干部精明审慎、为人民服务的工作作风为主;《团圆》则重点表现农村青年的“婚姻问题”,批判买卖婚姻。家庭婚姻始终是农民群众关心的重要问题,讲述农民熟悉并关心的内容,这就使他的说书能迅速为群众接受,因为听众也不愿意去听他们所不熟悉的内容。因此从内容上改变了袁静作为知识分子向民间灌输新政策以及新思想的导师立场。从结构上看,《团圆》紧紧围绕女主人公婚事展开,故事从退婚开始,到成婚结束,中间经历了卖婚——抢婚——判婚,情节跌宕起伏,环环相扣,结构紧凑完整,比疏于叙事重在说理的原作更能吸引观众。
从人物形象上看,《团圆》的人物形象鲜明突出,体现了民间文学的人物塑造的类型化特征。如刘巧的机智能干、心灵手巧,暗合了民间文学巧女、巧媳妇类型,也是民间所喜爱、推崇的女性形象;勤劳憨厚的赵柱(刘巧的未婚夫)是乡民称道的好后生;货郎刘彦贵(刘巧的爹)是农村典型的二流子;好色无耻的王财东则是农村地主老财的代表。韩起祥以传统道德观念为标准,将人物分为忠、奸(善、恶)两大类,忠善的一方是纺织能手刘巧、生产队长赵柱、贫农赵老汉;奸、恶的一方是货郎刘彦贵、财东王寿昌、刘媒婆,这种分类标准虽然有阶级论的影响,但又不唯阶级论。因为刘巧既是商人、二流子的女儿,又是美、善的代表,刘巧的美、善不在于她的外表如何漂亮,而在于她是劳动能手,赵柱最吸引刘巧的同样因为“他是个好劳动”,众人一致认为“刘巧、赵柱好劳动,应该立刻就成亲”。可见,韩起祥判断人物好与坏的标准是“勤劳”与“懒惰”这一农村社会最普遍的价值观念。另外,袁静在原著中没有突出抢亲事件,因为抢亲是婚姻法所不允许的,但在《团圆》中却用浓墨重彩写抢亲。“抢婚”是原始婚姻形态的一种,在西北民间尚有遗存,“延安的迎亲当中,还有一种别开生面的习俗,叫做抢亲”,名义上是“抢”,实际上,人们心里都有数,男女方早已约定时间、地点、明抢暗送,这种习俗一般只是寡妇再嫁[20]14~15。韩起祥浓墨重彩写抢亲正体现了农民的心理愿望与伦理观念。总之,“韩起祥是一个民间诗人,他的说书是直接为农民而创作的,我们只有在农村中才能看出他的真正力量”[9]519。
根据以上分析,可以得出结论:“旧艺人”改造运动使一大批民间艺人实现了思想文化观念的更新并登上了延安文艺的“大雅之堂”。民间艺人凭着自己对农村社会的深刻理解和农民文化需求的准确把握,以及自己精湛的表演技艺、丰厚的文艺知识,与革命知识分子一起,共同推动了陕甘宁边区农村的启蒙教育运动,促进了新文艺与民间文艺的有机融合。在此过程中,民间艺人与知识分子之间形成了合作互动的良性文化关系。作为主流意识形态与农民文化观念的沟通媒介,民间艺人将民族意识、阶级观念、民主自由、翻身解放、科学进步等政治观念和现代性话语,通过巧妙的转换,找到了与农民伦理道德、价值观念的结合点,从而既实现了从旧文艺到新文艺的创化,也实现了文艺所承载的政治内涵对农民日常生活的渗透,推动了农民对中共意识形态与新民主主义文化的理解和认同,但这一切并没有改变民间艺人艺术行为的农民性与民间性特征,这也是民间艺人艺术活动独具魅力的原因所在。
收稿日期:2010-12-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