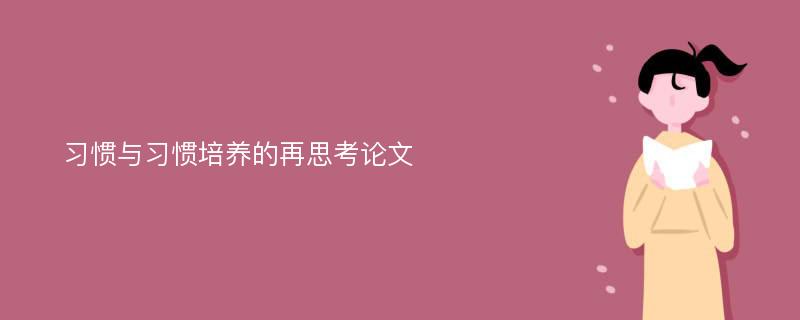
习惯与习惯培养的再思考
高德胜
(华东师范大学 课程与教学研究所,上海 200062)
摘 要: 习惯在日常话语中依然有很大的生命力,但在教育理论话语中已经没落。可以说,习惯是一个被行为主义败坏的概念。要摆脱行为主义的影响,需要对习惯概念进行再理解、再建构。自我由习惯凝成,德性也需通过习惯来成就。习惯在身心之间,既有“具身性”,又有“具心性”。习惯在发生作用的过程中,体现出“双重律”,但实际上还是“一重律”。教育在习惯的形成中起着重要作用,教育既是习惯形成的环境因素,又可通过笃行、慎思等方式进行习惯的培育,当然,教育也是改变习惯的重要方式。
关键词: 习惯;习惯形成;教育;习惯培养
一、习惯:一个被败坏的概念
“人是理性的动物”“人是政治的动物”这类说法深入人心,因此杜威之言“人既不是理性的生物,也不是本能的生物,而是一种习惯的生物”[1],就显得突兀、另类。即使有杜威鼎力加持,习惯在伦理学、教育学话语中的没落依然是显见的事实。与在学术话语中的隐身不同,在日常生活中,我们还是天天与习惯照面,天天言说习惯。这说明习惯依然是我们生活的一个重要维度,依然具有强大的生命。那么,习惯在学术空间中的隐身,如果不是习惯本身的枯萎,一定是另有原因。
“习惯”曾经是一个带有光环的词汇,习惯就是道德或德性的别称。比如亚里士多德就将习惯与道德德性等量齐观,认为“道德德性通过习惯养成”[2],鲁弗斯也说习惯是比理性更为有效的美德获得方式[3],阿奎那更是视习惯为不易消失的品质,是性情的据守[3]66。众所周知,在过去时代,教育几乎是道德教育的同义词,教育基本上就是道德教育。正是因为是道德或德性的别称,习惯在作为道德事业的教育中也处于核心的位置,或者说习惯过去一直是教育的一个“关键词”。
习惯在伦理学和教育学中的没落,与影响极大的康德哲学不无关系。康德对习惯没有好感,认为习惯只是以同样方式重复先前行为的内在身体必然性,这种必然性减损了心灵自由,也因此剥夺了善行的道德价值。[4]康德对理性与意志自由的强调,将习惯归入机械重复范畴,对思想界对待习惯的态度影响巨大。启蒙运动之后,任何与人的理性相抵牾的事物都是需要消除的对象。但即便如此,康德之后的哲学家,看重习惯的依然不少,杜威甚至公然宣称“人是习惯的生物”。
对习惯构成致命伤害的是行为主义。比如华生将习惯理解为“由刺激与反应之间所形成的稳定关系所构成的”[5]行为方式。行为主义对习惯的类似定义,从多个方面败坏了习惯。第一,习惯的行为化。在习惯的思想史上,习惯虽然总是与行动、活动、行为交织在一起,但很少有人把习惯只局限于行为,心灵习惯、灵魂习惯、感觉习惯、情感习惯的说法都不少见。行为主义则把习惯仅仅限于行为,习惯就是行为习惯,习惯从此被推向了与内在心灵无关的外在化境地。行为主义对习惯的这一窄化,绵延而至今天的教育实践领域,“行为习惯养成”之类的话语不绝于耳,就是明证。第二,行为主义对习惯的外在化不限于行为化。在行为主义之前,虽然极少有人否定习惯与环境的关系,但习惯是主体的习惯,即在习惯形成过程中,习惯主体是第一位的。行为主义将习惯理解为对外在刺激的稳定反应方式,也就是说习惯来自于外在刺激。在这里,主体与外在刺激的地位被翻转,外在刺激成了第一位的,而主体则是被动反应的第二位的存在,失去了习惯形成的主导性。第三,习惯的机械化。行为主义将习惯视为刺激与反应之间所形成的稳定关系,甚至渴望用神经回路来标示这种稳定关系,导致习惯的僵化与固化,使习惯失去了过去学术话语中的“在稳定与变化之间”的那种中道性质,进而失去了思想解释力和生命力。
值得注意的是,网络授课虽然方式新颖,方便学员,但是要保障教学效果并不容易。教师坐在屏幕后干讲,一方面难以调动大家情绪,另一方面无法与学员实时互动,了解学员掌握的情况,无法实现自由讨论式的协同学习。所以单纯的网络授课并不可取,建议采取网络授课与面授课程结合的形式,将《高等教育法规概论》《高等学校教师职业道德修养》等理论课程安排为网络授课,采取边学边考的方式,解决学员空间与时间上限制的困难;此外其余技能培训的课程依旧采用传统的面授方式。同时,观摩课堂是最快地提升教师教学认识的途径之一,也可以给学员安排观摩各专业国家级名师的精品课程网络视频。
行为主义之所以盛极一时,不在于其理论的说服力,而在于其是科学化时代科学化思维方式在心理学、教育学、伦理学等人文、社会学科中的反映。虽然诸多学术领域都对行为主义的谬误进行了清算,但行为主义的影响依然在我们的意识和无意识之中,一有适当的条件,就会现身,就会发挥其影响力。杜威对习惯的理解,带有清算行为主义的色彩,但他所处的时代依然是行为主义如日中天的时代,因此杜威的清算不可能彻底。再加上其实用主义哲学立场对行动的强调,使得他的习惯立场也没有完全摆脱行为主义的干扰。杜威之后,学术界的基本倾向是回避使用已经被败坏的习惯概念,而不是对行为主义习惯观念进行批判与清算。
行为主义对习惯的败坏,还表现在行为主义习惯观念为社会控制与教育控制提供了“灵感”。既然习惯是对外在刺激的稳定反应方式,那么通过发明、强化外在刺激就可以在目标人群那里获得期待的行为方式。福柯的研究表明,通过控制身体对人进行规训,古已有之,但规训的大规模运用,则是现代实践。在这种规训体系中,行为主义习惯思想的幽灵无处不在。虽然教育学术话语中习惯隐身不见,但在学校实践之中,通过外在刺激形成习惯以达到在学生那里获得预期行为的做法比比皆是。行为主义习惯思想在教育实践中的默然潜行,对教育事业、对成长中的人都是伤害,也使习惯背负上了更大的恶名,是对习惯概念的更为严重的败坏。
二、习惯与自我、德性
川崎机器人(天津)有限公司主要负责川崎重工生产的机器人在中国境内的销售、售后服务以及技术咨询等工作,并从顾客的角度开发和提供高性能产品。目前主要业务包括各种工业机器人的销售以及安全调试、维修、点检和紧急修理等售后服务工作,同时为客户储备了大量备品备件,并为客户提供机器人基础知识以及安全操作、维修等服务。
(一)习惯凝成自我
要拯救被行为主义败坏的习惯概念,可以从习惯与自我的关系开始。习惯不是行为主义者所限定的那样,仅仅是行为的,而是自我的标识。人是多维复杂的存在,人有身体、有思想、有情感,这是人之共性。一个人,怎么才能在芸芸众生中活成独特的个体呢?也就是说,个体怎样才能将自身变成一个可辨识的独立存在呢?我们首先想到的也许是身体,因为每个人的身体本身就是独特的。但没有纯粹的身体,所有的身体都是结合了精神的身体,否则就是“行尸走肉”。作为“行尸走肉”的身体,即使形态各异,也没有辨识的必要。每个人的感情、思想是不同的,问题在于感情、思想的内隐性、易变性、零散性,使之很难成为一个可辨识的标准。习惯处在身体、思想、感情、行动的交汇处,将人之分散的“心絮”与“活动”连接在一起,形成一个稳定而又连续的存在。正如杜威所说:“自我就是长时间形成的联合而又连续的习惯。如果没有习惯,人们所过的生活就会蜕化为松散的活动丛,无法凝成稳定、连续的自我。”[6]
由习惯凝成的自我,并不排斥身体、思想、感情,而是这些人性维度的沉淀。杜威说人不是本能的生物,也不是理性的生物,他不是在否定人的本能、人的理性,而是说这些人性维度如果不通过习惯表现出来,就不能作为人之存在的标识。人有这样那样的本能,但本能不是人、也不是个体独有的标识,本能只有通过习惯这一通道,才能成为人、成为个体独有的力量。比如,愤怒是一种本能性情感,本能性的愤怒不能作为一个人的标识,只有成为一种带有个人风格的情感习惯,才能成为一个人的标识。我们常说人是理性存在,问题是理性不是凭空而来的,而是以先前形成的习惯为基础的;另外,理性活动也会凝结而成习惯。
我们常说习惯是人的“第二自然”,那么人的“第一自然”是什么呢?显然是与生俱来的生理本能。按照惯常的思维,“第一自然”比“第二自然”原初、根本,因为“第二自然”是派生性的。但在人这里,作为“第二自然”的习惯则更为根本,才是之所以为人的标志。从个体的角度看,“第一自然”构不成自我,构成自我的只能是“第二自然”。习惯作为“第二自然”,与自我一体,就是自我本身。当然,构成自我的习惯不是单个的习惯,而是“习惯丛”(bundles of habit)。“一只燕子构不成春天”,同样,单个的习惯也构不成自我,而是由多种习惯有机组合在一起的我们的在世生活方式,才构成自我。
习惯是人在世而立的方式。如前所论,分散、易逝的“心絮”与活动凝成习惯,一个人才有了不同于他人的可以辨识的自我。别人看到的“我”,是由习惯构成的稳定存在。从这个角度看,我们是用习惯与他人建立联系的,我们是通过习惯扎根人间的。同样,我们与环境的联系也是以习惯为中介的。人在环境中生存,不可能每时每刻都去思考如何去重新理解、重新创造环境,正是在与环境互动过程中形成的习惯,成了我们与环境进行交互的方式,也成了我们的生活方式。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习惯也是我们扎根世界、与世界建立联系的方式。
作为“最伟大的习惯研究哲学家”[3]220,杜威对习惯的思考确实独到。比如,多数人只从习惯主体来思考习惯,但杜威却指出了习惯中的环境力量。他用呼吸来类比习惯,我们总是以为呼吸是机体的功能,但如果没有空气,呼吸不可能完成,因此呼吸是机体与环境相互作用的机制。习惯也是如此,我们的习惯也是结合了环境的力量。在习惯形成的开端,环境已经“介入”。人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社会性动物,我们的思与行总要顾及他人,他人也会对我们的思与行表达看法、施加影响。也就是说,一个可能成为习惯的活动,在一开始就渗入了环境与他人的力量。
(二)习惯成就德性
在被行为主义败坏之前,习惯之所以受到重视,在于习惯在品格与德性形成中的不可或缺的作用。亚里士多德关于道德德性主要来自习惯的思想影响至深。人是道德存在,千百年来,我们都在探寻德性形成之秘。在这一探寻中,很少有人能无视习惯的存在。确实,习惯与德性有太多共同的地方。首先,德性与习惯都不是客观知识,而是与人自身结合在一起的倾向(disposition)或存在状态。德性如果是客观知识,那么德性形成之路就会清晰很多,但事实是我们许许多多的关于道德的知识都与我们的真实品性无关。正是这个原因的存在,引导我们从同样不是客观知识的习惯那里去寻找德性的本质。其次,德性和习惯与实践、实行密切相关,亚里士多德说我们是通过做公正的事情而成为公正的人、做节制的事情而成为节制的人、做勇敢的事情而成为勇敢的人,同样,我们也是通过做某种事情而形成某种习惯的。再次,德性与习惯都与环境的熏陶密切相关。人是社会性动物,必须扎根人间,否则就不能在世生存。扎根人间,就意味着要接受先在群体的基本道德预设和生活习惯,这是人进入社会的前提条件。道德预设也好,生活习惯也罢,都是一种隐在的环境因素,其对新生成员的影响主要是间接的、默默的,新生成员也多是在不知不觉中受到熏陶而形成自身的品性和习惯的。最后,德性与习惯都与过去相关,又都是指向未来的。德性与习惯都不是凭空而来的,都是过去经历沉淀的结果,且在当下和未来发生作用。
MS包含了一系列促进心脑血管疾病发生发展的危险因素,而且多呈高水平、多重聚集状态,从而使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病率、患病率明显增加[11-12]。MS组分与终点事件之间存在剂量反应关系,组分数越多,其心血管疾病危险因素水平越高[13],本研究结果也表明随着MS包含组分数量增多,冠心病和脑卒中事件的发病率及相对风险呈现增加趋势。因此积极开展MS的防治干预,从降低组分数量的角度开展健康宣教和健康管理对心脑血管疾病及死亡的防治具有重大意义。
由此看来,德性中一定有习惯,虽然我们还不能确定德性中的习惯只是道德性的习惯,还是包括其他习惯,或者以其他习惯为基础。说一个人具有某种德性,也就意味着其有施行该德性的习惯。比如,某人具有诚实品质,也就意味着其在思与行中有诚实的习惯,换句话说,在面对诚实情景时,其会自动化地表现出诚实的思与行。如果没有诚实的习惯,诚实的品质显然无处存在,也无从证明。因此,我们可以说,没有习惯作支撑的德性是抽象的、虚幻的、不能兑现的德性。德性中不能没有习惯,但并不意味着德性全是习惯,德性中有习惯之外的因素,比如思考与判断。德性中有思考与判断等其他成分,并不排斥习惯在德性构成中的作用,一方面在于习惯是思考、判断的基础,我们的思考、判断能力同样不是凭空得来的,其自身也有习惯的成分;另一方面,思考、判断也有习惯性,也会成为习惯。
既然德性中一定有习惯,那么就可以通过习惯来培养德性,因此,习惯是成就德性的一个重要方式。亚里士多德说:“从小养成这样的习惯还是那样的习惯绝不是小事。正相反,它非常重要,或者说,它最重要。”[2]37从这句话可以看出,亚里士多德认识到习惯是到达德性的一个异常重要的通道。在他看来,德性不是出于自然,当然也不是反乎自然,德性体现的是人的努力与提升。在获得德性的过程中,这种努力并不那么容易,甚至需要克服痛苦。但通过习惯,德性变得可欲、自然、稳固。当然,亚里士多德这句话也指出了习惯与德性关系的另一种可能,那就是不好的习惯可以让人失去德性。一般而言的习惯是一个中性概念,可好可坏,好习惯可以成就德性,而坏习惯则会毁坏德性。而这正是教育可以着力之处:教育的使命就在于培养年轻一代的好习惯、改正他们的坏习惯。
我的画院:画院坐落在美丽的地方,有很多美丽的故事。如果想到其与宋代有着各种联系,立刻让人感到渺小,又让人振奋,力争创作出美丽的画,以不负各方。
三、习惯的身心性与“形成律”
(一)习惯的“具身性”与“具心性”
习惯居于何处?是心灵还是身体?行为主义剔除了习惯的精神成分,将习惯限定于生理甚至肌肉反应,显然,行为主义的习惯,其寓所是剔除了精神的身体。这与过去时代对习惯的认识大相径庭。亚里士多德虽然强调习惯的活动性,但依然认为习惯是灵魂持续而灵活的状态、倾向,是拥有者在特定情境下感受与行动方式的预示。[3]127-128塞涅卡也认为习惯是理性统御激情的力量,以思维方式、思维定式为形态。[3]41-43阿奎那虽然不否认习惯与身体的关联,但认为习惯的寓所只能是灵魂。在他看来,身体不能直接习惯化,因为身体的自然本性很难改变,只有与灵魂相关的身体部分才能习惯化。在阿奎那的习惯观里,理性是关键,因为只有情感、欲望服从理性,习惯才有形成的可能。表面上习惯直接与行动联系在一起,但实际上是居于灵魂的习惯在号令行动。[3]68-71现代以前的习惯理论,诸如休谟、拉韦松等,多数都认为习惯的寓所在灵魂、在心灵。
教育不是自在的环境,而是带有特定使命的改造过的环境。杜威对此有经典性的阐述,即学校不是社会环境的照搬,而是根据受教育者的能力现状和发展需要进行简化的环境;是消除无价值事物的环境;是一种社会要素平衡的环境,有利于每个人脱离自身群体的限制。[10]20-21这样的环境,对习惯的形成有特殊的意义。首先,既然是基于学生能力与发展需要的环境,那么这种环境对年轻一代形成满足自身成长需要的习惯大有裨益,或者说这种环境的建构本身就是为了帮助学生形成适合年龄与发展阶段所需习惯的。学校所建构的简化了的环境,不像自在的社会环境那样向年轻一代无意识地提出各种各样的习惯要求,而是有意识、有重点、有倾向地向学生提出在他们这个年轻阶段迫切需要且对未来发展至关重要的习惯要求。其次,作为剔除了无价值事物的环境,学校其实是对社会生活进行了一定程度的过滤。这种过滤与前面的简化一样,都体现了学校的习惯偏好。如果说简化体现的是希望在年轻一代身上形成什么习惯,那么过滤体现的则是学校不希望学生形成什么习惯。学校如果照搬社会生活,不对社会生活有所改造和过滤,那么学校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再次,这样的环境,还是年轻一代超越个人生活限制,形成适应更广阔生活,甚至是人类意义上的生活所需习惯的土壤。人在特定的地域、特定的社群中成长,不可避免地带有地域性、小群体性(即地域性、小群体性习惯),学校环境不排斥这些基础性习惯,而是通过自身过程对其进行改造与提升,以形成适应更宽广生活所需要的习惯。
环境对习惯形成的另一个作用,是环境激发习惯,或者说习惯之形成来自环境所发出的要求。人要在环境中生存,就要适应环境,就要“懂得”环境所提出的要求,就要建构与环境互动的稳定方式。比如,一个小学生升入初中,学校是新的,同学是陌生的,老师也是陌生的,学习方式也是不同的,在小学所形成的诸多习惯已经不太适用,初中生活环境向其提出了很多新的要求,他必须形成诸多新的习惯来满足环境的要求,并用这些新的习惯与环境进行稳定的互动。由此看来,环境既是形成新习惯的力量,也是改变旧习惯的力量。
与黑格尔试图联结精神与形体不同,梅洛·庞蒂直接将习惯的居所定为身体,“习惯的住所不是思想,而是身体;不是客观化的身体,而是作为世界调节者的身体”[3]200。庞蒂认为习惯首先是一种身体记忆。身体记忆不同于回忆,回忆是心理的,是朝向过去的、非连续性的图像(表象)记忆,而身体记忆是连续的、行动的(非表象的)朝向未来的记忆。心理性的回忆来自意识活动,而习惯性的身体记忆则来自过去活动的有意识和无意识沉淀。没有身体就没有习惯,过去也不可能存在,习惯就是过去通过身体对现在的绵延。庞蒂将习惯理解为“具身图式”(corporeal schema),即与身体结合在一起的“知道如何”(know-how)的实践感、一种对世界的身体理解。[7]123
庞蒂的关于习惯是“具身图式”的思想独树一帜,开创了关于习惯的现象学视域。但不是所有习惯都是“具身”的,或者说身体不是习惯的唯一寓所。庞蒂的习惯来自过去活动在身体上的沉淀,是我们理解当下、在当下做事的一个前反思性基础。他没有解决的是我们过去的思维活动,不可能消失不见,也会绵延到现在。比如胡塞尔关于归类(typification)和配对(pairing)的概念就是揭示了过去思考活动所产生的习惯在当下活动中的作用。语言就是一个归类系统,在归类的意义上,语言也就是一个习惯系统,只要我们使用语言,习惯就在发生作用。[7]131而且,思维中的习惯并不仅仅限于心智,还会在身体中得到体现。比如一旦我们形成了体积与重量比例关系的概念,在提起同样体积的物体时,身体就会不假思索地使出与该体积成比例的力,如果同样体积的物品重量却出乎意料的轻,我们就会被闪着。这说明即使是归类这样的心智习惯,也会与身体结合在一起,成为身心一致的习惯。
身心二元论是思想史上一个长久的思想裂痕,习惯寓所的争议正是这一裂痕的体现。人是整体性存在,我们在理论表达上可以将身和心分开来说,但实际上作为一个真实存在的人,身与心根本无法分离,本身就是一体的存在。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习惯的寓所既可以是心灵,也可以是身体。寓居心灵的习惯,虽然主要来自心灵活动,但不会与身体活动全无干系,也有来自身体活动的沉淀,也会在身体姿态与活动中有所体现,也具有“具身性”;寓居身体的习惯,其来源往往是身心兼具的,同样不会与心灵全无干系,同样是当下心灵活动的非反思性前提,具有“具心性”(与“具身性”对应)。也就是说,“具身性”的习惯也具有“具心性”,“具心性”的习惯也具有“具身性”。因此,习惯的寓所不是单纯的身,也不是单纯的心,而是身心的结合,在身心之间,在我们的生命中。
(二)习惯形成的“双重律”与“一重律”
拉韦松认为习惯存在双重律(double effect of habit,double law):激情的连续或重复弱化激情,行动的连续与重复提升、增强行动;延长或重复的情感一点一点儿弱化直至消失,延长或重复的行动越来越容易、敏捷、确定。[3]144为什么存在这种双重律呢?拉韦松的解释是,激情、感情是一种感觉活动(sensation),来自于身心感受到的变化。感觉活动使感觉器朝向刺激源并做好准备,慢慢地就减少了刺激物的新鲜感,进而导致感觉强度的下降,其内在机制是惰性力(the force of inertia)。而行动则相反,其重复只会使行动得到加强,变得更加熟练,直至变成“类本能”。
习惯化行动强化行动及行动所蕴含的感情、品质很好理解,比如,我们关爱他人的习惯不但使关爱自动化,变成一种“类本能”,而且这种关爱行动所蕴含的情感也会沉淀为一种品质,成为我们的品性之构成。激情与情感的重复与延长会降低激情,这一点也不难理解。比如我们第一次看到一个悲惨的事情,会在内心激起很大的波澜,但看得多了,也就习以为常了,这就是所谓的“同情疲劳”。问题是同情疲劳之后,即引发同情疲劳的悲惨事件给我们留下了什么。如前所论,习惯是沉淀的结果,对一个事物的习惯意味着该事物在我们身心上留下了痕迹。情感上对悲惨事件的习惯,同样意味着悲惨事件已经在我们身心里留下了痕迹与影响。表面上看,我们对他人的悲惨遭遇已经没有反应,但实际上反应已经在身心里了,即我们不再给予他人的悲惨遭遇以应有的同情。从这个角度看,拉韦松的双重律有值得商榷的地方,即激情的延长与重复导致激情的减弱和消失,但在减弱与消失的同时已经在我们的身心里种下了激情与情感的对立物。
那么,习惯在德性形成中到底起着什么样的作用呢?在杜威看来,品格是由习惯构成的,品格就是习惯的互渗互联(interpenetration)。[6]杜威的品格概念显然不同于个体品德或德性,更类似于一个人的性格或个性。这里的品格如果是指德性的话,显然有不合逻辑之处,因为有很多习惯与道德无关,这些与道德无关的习惯对德性的形成没有直接关系。但杜威的观念依然深富启发性,我们由此可以类推出德性是一个人与道德有关的各种习惯的互渗互联。威廉·奥克汉姆将习惯分为三种类型,一是道德习惯,二是智力习惯,三是感觉欲望习惯,我们更为熟悉的行为习惯在他那里并不能单独成类,因为行为习惯只是以上三种习惯的实行。[8]且不论这种习惯分类的说服力,德性显然与道德习惯的关系更为紧密,从杜威的角度看,就是各种道德习惯整合而形成的道德倾向与品性。当然,智力习惯,尤其是感觉欲望习惯与一个人的德性显然不是全无关联,也是一个人德性形成的基础或背景性的存在。
可以从不同的维度来深化习惯的双重律。一个维度是行动与情感的区分,再一个维度是主动与被动的区分,另一个维度是价值好坏的区分。
第一个维度,即行动与情感的区分前文已经论及。第二个维度,即行动也有主动和被动之分,主动行动(其所伴随的情感也是主动的)强化行动及其附带的情感;被动行动的持续和延长一方面是行动变得自动化,另一方面也使一开始因被动而产生的消极情感消失。被动行动的自动化,意味着这一行动及其所附带的价值已经沉淀到或建构进我们身心之中,成了我们生命的一部分,同样是表面上消失而实际上却以隐身的方式存在。比如,以分数作为刺激、衡量学生的力量与标准,个别学生一开始会有行动和心理上的抵触,久而久之,这种抵抗就消失于无形,分数则成了一种深入人心、理所当然的标准。情感也有主动和被动之分,主动情感无论好坏,都会得到强化,比如主动的关爱强化的是关爱,主动的歧视强化的是歧视。被动情感的习惯化则有两个方向,正面情感加强的是正面情感,比如别人的关爱情感给我们的关爱的暗示,在我们心中更可能种下关爱的种子;负面的情感(指负面事件本身所蕴含的情感,不是其刚一出现时我们的情感反应)比如残酷、悲惨事件的重复,给我们的是残酷与冷漠的暗示,消除的是我们对此的原初反应(比如愤怒、痛苦、同情),在我们心中种下的更可能是残酷与冷漠的种子。另一个维度则是价值好坏的维度。无论是情感还是行动,如果是好的、道德的,其重复或延长直至沉淀到我们的意识之下,加强的都是好的、道德的行动与情感;如果是坏的、恶的,其重复和延长有双重效应,一方面是坏的、恶的行动、价值得到加强,成为一种身心结构;另一方面则是减弱,即我们一开始对坏的、恶的行动与情感的反抗、抵制减弱。
从目前的情况看,把传统工艺单独视为一个学科是不合适的,它应该是不同学科的结合体。比如,冶铸类传统工艺属于冶金学,纺织类传统工艺属于纺织学,所有这些分支统称传统工艺。
行为主义对习惯的败坏如此严重,但习惯在日常生活和教育活动中依然有生命力,那我们就有拯救和保护习惯概念的必要,即恢复习惯这一概念的本来面目,就要重新厘定习惯与自我、习惯与德性、习惯的身心属性、习惯形成的规律。
由这三个维度的分析可以看出,所谓习惯的双重律其实还是“一重律”,即无论什么样的情感和行动,经过持续和延长,加强的还是其自身。这一点在主动行动、正面情感、正向价值上非常直观,根本不存在所谓的双重律或双重效应。存在双重律的是被动行动、负性情感、负面价值,即在这些维度上我们的行动、情感和价值一方面有加强,另一方面又有所减少。但从本质上看,这种双重律其实还是“一重律”,即被动行动、情感和负面价值本身得到了加强,减少、减弱的只是我们对这些东西的抵触、抵制与反抗。以“同情疲劳”为例,在一个残酷事件中,事件本身所蕴含的情感是残酷与冷漠,随着对此类事件的习惯,我们接受的正是残酷与冷漠,而抵抗这残酷与冷漠的同情则随着习惯而被消磨殆尽。被动行动、负面情感与价值在习惯化的过程中之所以存在着“双重律”,标识的是人之特性,即人是自主与道德存在。被动行动冒犯的是人的自主需要,所以会遭到抵触;负面情感和价值侵犯的则是人的道德性,自然会滋生出相反的情感与反应。但这些人性的基本力量,都抵御不了习惯的力量,都会被习惯所消解,更说明了习惯力量的强大。
四、教育在习惯形成中的作用
习惯与自我、德性有如此直接的关系,习惯培养的意义不言而喻。根据习惯身心属性和习惯形成的基本规律,我们可以探索教育在习惯培养中的作用,探索如何通过教育来培养习惯。
(一)教育:作为习惯形成之环境
我们受用终身的诸多习惯都是在教育过程中形成的,教育是中心性的习惯形成活动。在杜威看来,教育就是培养个体有效适应环境的习惯(这也是他所认为的生长)[10]。既然从事实上看我们从教育那里获得了诸多习惯,从理论上看教育又是培养习惯的活动,那么我们需要厘清的是,教育在习惯形成中所处的位置。
习惯与自我的一体性还表现在习惯的非对象化上。人是有意识和自我意识的存在,相比意识,自我意识作为“意识的意识”是更为高级的意识,发育更晚。儿童不是一出生就有自我意识的,其自我意识形成的标志是能够说“我”。在能够说“我”之前,生成中的自我已经存在。如前所论,这生成中的自我,也即动态的习惯结构。因此,从个体发育的角度看,习惯是先于自我意识的存在,也就说在个体意识到自我之前,习惯已经在建构自我。米德用“I”和“Me”来标识两种自我,主体形态的自我“I”主要来自于经历和习惯,而客体形态的“Me”则主要是以他人视角看自己的结果。在米德看来,儿童在能够以他人眼光看自身之前,已经有了一个基于习惯的主体自我。这种主体自我不是主题化、对象化的,而是一个隐在的自我。这个隐在的主体自我是儿童看世界、从他人视角看自身的基础。[7]先于自我意识的习惯,在形成之后,往往沉潜在意识之下,与自我浑然一体,“习惯就是自我,一般不会对象化而进入意识,而是与自我一体去意识其他事物,使其他事物对象化”[3]237。作为理性、感情的存在,我们会去感受、思考其他事物,将其他事物对象化。在这个对象化的过程中,都有一个主要由先在习惯构成的主体自我站在对象的对面。人是理性存在的思想影响至深,我们常常强调理性选择的重要,但习惯是我们自身一个更亲近、更基础的部分,比有意识的选择更能代表自我(后文还会论及选择与习惯的关系)。当然,沉潜在意识之下的习惯,也可以上升到意识层面成为反思的对象,但这种上升不是无条件的,而是发生在习惯受到阻碍,无法正常发挥作用的情况下,或是被他人指出、提醒而进入意识。
我说:“二丫是个姑娘家,我都人老珠黄了,东洋人不会对我么样的。再说,我是去找儿子,又不是去扯皮打架,有么事怕的呢?”
但如果说习惯纯粹是心灵的,又与我们的直观感受有落差,有太多的习惯与身体无法分离,即使是最内在的思考、情感习惯也往往会有身体显现。黑格尔解决这一难题的方案是将习惯理解为精神与形体的结合,即习惯是形体“砌入”精神,是精神对形体的直接占有,是精神在形体中的直接体现。[9]黑格尔对习惯的这一理解深有启发性,即习惯既与精神有关,又与身体有关,是将身心结合起来的一种力量。但黑格尔认为这种“砌入”是由外而内的,即从形体开始进入精神的,然后才作为精神的直接体现。这与习惯灵魂论的顺序是颠倒的,因为灵魂论者认为习惯在身体上的呈现只是灵魂习惯的外化而已。
人是有限存在,没有超能力。这就决定了即使是一个按照一定目的主动建构的环境,也不可能精细到每一个环节,也不可能完全剔除负面的因素。学校环境也是如此,一方面,虽然是主动建构的环境,但也不可能顾及一切环节;另一方面,即使是主动设计的环节,彼此间的交互作用也可能超出主动设计的控制,产生意想不到的影响。比如,学校按照一套系统规范来进行分班、指派教师,但学生之间、师生之间的互动则远远超出系统规范的控制范围。在这个意义上,杜威所说的剔除无价值事物的任务不太可能真正完成,因为在建构学校的过程中,甚至是在剔除无价值事物的过程中,也会制造出新的无价值的事物。也就是说,即使是一种改造过的、主动建构的环境,在存续期间,也会有自发、自在的因素,也不可能完全消除坏的、不道德的影响。
由此看来,即使是学校这种改造过的环境,也并不能保证所形成的习惯都是好习惯。这是客观事实,但并不能因此而否定学校在习惯养成中的意义,更不能由此导向对学校的虚无主义态度。一方面,如果学校的基本品性是正派的,学生会接受学校的基本品性所预设的各种习惯与品性要求。另一方面,学校也会“教给”学生一些不好的习惯,这并不可怕,因为学校作为改造过的环境,是一种主动活动,可以有意识的将在校内、校外所形成的不良习惯作为反思、批判的对象。一个毫无经历和习惯积累的人,我们是无法对其进行理性反思训练的。只有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和习惯的人,才有反思与理性思考的基础。
北京市丰台区南方庄社区,陈益君老人每天都往来于住所和颐养康复养老照料中心之间。陈益君的老伴患多种慢性病,长期卧床,“雇了两个保姆还不行,有时候还得把上班的儿子叫回来帮忙,真是伺候不过来。”陈益君表示,“现在住进照料中心,都是像我老伴一样不能下床的老人,比原来省心方便多了。”
(二)教育:通过笃行培养习惯
在习惯的形成中,教育不仅仅是一种环境,还是一种主动的习惯形成机制。教育是一种活动,是教育者与学生之间的相互作用。发生什么样的互动,虽然受学生成长需要的限制,但教育者还有一定的主导性。正是通过对互动活动的引导、塑造、坚持,师生共同笃行某些活动,习惯就在这一过程中形成了。通过笃行培养习惯,利用的就是活动的持续、延长就会使活动自动化、使活动本身所蕴含的价值与情感渗入身心这一基本原理。通过对一种活动的持续与坚持,该活动及其所蕴含的价值、情感就会“砌入”我们的身心之中、成为习惯这样一种直接的存在。以礼貌习惯为例,在师生互动及学生间的互动过程中,对礼貌的笃行就会使礼貌成为一种“砌入”师生生命中的习惯。正是笃行所具有的这种功效,教育,尤其是道德教育对笃行有特别的偏爱,比如通过笃行公正培养公正、笃行尊重培养尊重、笃行关爱培养仁慈等。
在教育文化中笃行是一个有正面价值判断的词汇,我们一般都会想当然地认为笃行的都是好的活动。这样的直观反应是有一定依据的,即教育是教人向善的,是让人学好的。由此出发,教育让学生笃行的应该是好的,如果是坏的,还让学生笃行,那不是教人学坏吗?但如前所论,人都是有限的,由人来办的教育也是有限的。这种有限性也会在笃行中体现出来,比如教育者主观上认为是好的,坚持让学生践行,但实际上可能对学生来说并不真的是好的。因此,从习惯形成的角度看,我们可以去除附加在笃行之上的价值判断,纯粹从方法的角度来认识笃行的作用。根据习惯形成的“一重律”,无论是主动活动与情感,还是被动活动与情感,笃行与重复的结果都是活动、情感在身心上的“砌入”。为了提高笃行的相对正确性,教育者和教育机构必须具有这样一个习惯,即“不断反思自身习惯的习惯”。一般而言,整体正派的教育,要求学生所笃行的一般也是好的,但也可能以好的用心却让学生笃行了坏的事情,这时候“反思自身习惯的习惯”就非常重要了。
笃行中的“行”可作扩展性理解,既包括行为,也包括言辞话语,更包括内在的心灵活动。将身心分开,认为身心可以单独存在与活动的身心二元论影响巨大。实际上,人是身心一体的存在,除了肌肉反射,每一个外在行为都有心理的成分;内在心理活动虽然不一定都转化为外在行为,但也与行为割断不了联系。一方面,内在心理活动以过去的活动,尤其是过去的行为和习惯为基础;另一方面,内在心理活动里往往借助生动的行为画面,是一种想象性的活动。我们总是将言辞与行为分开甚至对立起来,言辞与行为确实有可分离的一面,但言辞与行为也有不可分离的一面。在很多情况下,言辞就是行为,比如对需要的人来说一句暖心的话就是很大的关心;对脆弱的人来说,我们一句带有敌意或恶意的话就是一种巨大的伤害。在学校这种以知识和思想为主导的场域,言辞话语甚至是最为主要的活动。言辞话语往往反应一个人的内心,又总是与一个人的外在行为结合在一起,综合而成一个人的性情状态。
秦刚在《中国游记》的译者序中称该书“堪称日本大正时期文学家写作的最重要的一部中国纪行”(译者序第3页)。大正年代的时代背景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芥川游历中国的心态,使其《中国游记》的书写带有明显的殖民主义者的话语特征;反之,芥川的《中国游记》话语表现又从某种程度上迎合了大正时期部分日本人的日益膨胀的殖民者的文化心理,从而在日本产生了巨大的反响,进而影响了日本人心目中的中国江南的形象。
由此看来,所谓笃行,显然不是重复某种行为。教育中的笃行,首先应该是超越割裂观的作为整体人的活动坚持。教育所引导的重点不在于特定行为习惯,而是作为整体人的活动。通过这样的笃行,在学生那里所造就的是作为整体人的习惯,是学生的自我形成与德性建构。当然,整体习惯的培养也并不排斥从特定的行为、特定的体验、特定的言辞表达入手。比如,让学生写字工整,这是从特定的行为入手,在养成良好的写字习惯的同时,还可以由此熏陶做事认真、专心的倾向。
李红实在看不下去了:“我说齐海峰,你光给人家切二两好肉有什么用呀,你的好心好意贡献的还不知道是不是杨蓉的妈。还不如直接去找杨蓉,和她把话说清楚,成不成就不惦记了。”
教育通过笃行来培养所期望的习惯,不会一帆风顺,甚至会遭到学生的对抗。让笃行有效的方法并不复杂,但真正做到,却也不易。第一,所笃行的应该是反映学生成长需要的。诚如亚里士多德所说,德性不是自然,但也不反乎自然。学生成长的需要,就是教育的“自然”,不违背这个“自然”,是底线要求。更高的要求是顺应学生成长的需要,主动培养那些对他们的成长来说所必不可少的习惯。顺性而为,遇到阻力就小;逆性而为,遇到的阻力就大。第二,笃行是双方的,不是单方的。简单说来,教育是两代人的互动。如果教育者只是命令学生笃行以成就某些习惯,那就不是教育,而是独裁。独裁可能短时间内有效果,但也会遭到抵制,学生的抵制即使失败了、屈服了,学会的是独裁的习惯,而不是独裁所要求的习惯。教育的方式不是命令的方式,而是互动引导的方式,即用自己的笃行去引导学生的笃行。当然,教师和学生社会角色不同,笃行的内容可以有所不同,但笃行的精神是一致的。更何况,诸多与道德相关的“行”,都是超越角色的,是双方都要笃行的。第三,适当的约束很有必要。作为人,尤其是成长中的人,有各种各样的冲动,有各种各样的诱惑,单靠学生的自主与自制显然是不够的,一定程度的约束是必不可少的。这约束可以来自学校和教师,也可以来自同龄人。正是因为教育现实中的约束过多、过度、随意,我们在理论上对约束往往是过敏的,不敢主张约束的意义。在成长过程中,约束也是发展理性与自制的方式。
(三)教育:通过思考培养习惯
已经形成的习惯往往在意识之外,不需要意识的参与而自发运作。习惯的这一特征导致我们常常将习惯与思考对立起来,忽视思考在习惯形成中的作用。实际上,思考不是习惯的对立物。从思考的角度看,习惯是思考等理性活动的一个构成部分,我们的思考都有习惯的基础;从习惯的角度看,思考是形成习惯、改变习惯的一个重要环节,思考本身也可以成为习惯,即思考的习惯。如前所论,习惯既可来自有意识的笃行,也可以来自无意识的生活沉淀。从数量上来说,来自后者的习惯应该更多,我们的诸多习惯都是在无意识中形成的。在无意识中形成,在无意识中发挥作用,习惯的这一特性给我们带来了极大的方便和解放,但问题是这样形成的习惯既有好习惯,也有坏习惯。思考的作用在于一方面使已有的习惯进入意识之中,这样才能对习惯的好坏进行判断,才有坚持好习惯、改掉坏习惯的可能;另一方面,思考之后可以做出选择,从而去形成一个新的好习惯。
由此可知,育明轮在艏倾时,主机每海里的油耗量比平吃水主机每海里油耗量都有所增加,能效营运水平都比平吃水时低,在较大的艉倾即吃水差为-1.4米时,主机每海里油耗量与平吃水相比有很大的增加,能效运营水平显著降低,在比较小的艉倾下,其运营能效水平有所提高,尤其在吃水差为-0.2米时主机每海里的油耗量最小,能效营运水平最高。
亚里士多德非常重视审慎在好习惯(德性)形成中的作用。如何才能形成好习惯呢?亚里士多德的方法是命中中间、学会中道。为了命中中间、学会中道,就要避免两个极端;警惕自身容易沉溺的事物;警惕快乐,因为快乐容易让人失去理性判断。[2]56总之,在好习惯的形成过程中,审慎是关键。审慎作为一种品质(也是一种习惯),其构成并不简单,既与过去的无意识习惯有关,也与在生活中形成的思考能力与习惯有关。一个没有经验、习惯积累单薄的儿童或少年,不可能获得审慎的品质,审慎是在生活经历基础上发育出来的果实。但也不是所有经历丰富的人都能获得审慎的品质,这里的关键就在于有没有思考的能力与习惯。避免走极端,这是形成好习惯的前提,走了极端,就无法成就好习惯,问题是如何才能知道什么是过头和不及。做到这一点,经验和思考都是必须的。至于警惕自身容易沉溺的事物,警惕快乐,同样需要经验的积累,需要反思能力与习惯。
审慎在好习惯、好品质形成中的作用可以作为直接道德教育存在的依据。总体上看,习惯和道德都是在生活中自然、自发学习的,这是一种潜移默化性的非强制性学习。通过这样的学习,一个人可以形成一颗善良之心,达到一定的道德水平。但即便如此,只是自发地从社会环境中模糊地吸收养分,离受过教育的、批判性的精细道德还很远。有这样的基础,如果再加上专门道德教育引导下的主动道德学习,一个人才能达到更高的道德境界。历史上那些在道德上让后人景仰的人,没有谁只是靠自发的影响就达到了高尚的道德境界的,他们的道德成就,都有主观努力、自我修炼的成分。科尔伯格应该是了解这一规律,所以他才发明了独特的道德教育两难法,通过两难问题启发学生对道德问题进行集中思考。如果说杜威阐述了道德教育的基本样态是间接道德教育,科尔伯格则充分论述了直接道德教育作为对间接道德教育之补充的意义。在好习惯培养、道德教育中,二者缺一不可,是互补关系,不是对立排斥关系。
阿伦特将思考(Thinking)理解为从外在世界脱离出来,在内心深处自己与自己的无声对话,“从柏拉图开始,思就被定义为我与我自己之间的一种无声对话,它是与自己相伴、自足自乐的唯一方式”[11]。这种思考以记忆为基础,指向过去,是对已经发生的事情、自身作为、言行的反思、反省。杜威的思考(deliberation)更多的是未来预演,是朝向未来的,“是对各种不同的、相互冲突的、可能的行动方式的一种(在想象中的)戏剧式彩排”[1]117。两种思考,方向不同,一个指向过去,一个指向未来,但都有益于好习惯的形成。指向过去的思考,是对过去的再思与整理,是对自己生活的“反刍”,有利于无意识习惯的意识化。习惯,尤其是无意识化的习惯,是生命力量的“经济化”,带给我们的是生命力的节省,使我们以最小的能量来有效地思考、行事。且不说习惯有好有坏,习惯一旦形成,就会有习惯自身的“意志”,就要脱离主体的控制,就有可能走向习惯初始的反面。以过去为指向的思考,就是对习惯的一种预防机制,保证人享有习惯带来的益处的同时,不至于被无意识的惯性所控制,滑向一种无意识的机械生活。指向未来的思考,发生于习惯与环境、习惯与习惯、习惯与冲动的矛盾、冲突,这时已有的习惯已经不再能够适应解决问题的需要,多种选择及其效果可以借助想象在我们的头脑中进行彩排,以便我们做出理智的选择。如果说阿伦特的思考是对已有习惯的反刍的话,那么杜威的思考则是对新习惯的选择。显然,这两种思考在习惯形成与改变的作用都是至关重要的。
(四)教育:习惯改变的重要过程
人是习惯的生物,形成习惯是重要的,改变习惯同样关键。杜威说,作为集体习惯的习俗是“社会的动脉”,习俗的固化,就导致“社会动脉的硬化”,社会就会僵化、停滞。[1]64-65如果说习俗是“社会的动脉”,那么习惯则是“个人的动脉”,习惯如果固化,也会导致个人的“动脉硬化”。如前所论,人一生一直处在不断形成习惯、不断打破习惯的过程之中。如果只形成习惯,不打破、改变习惯,那么人的僵化、崩溃则是必然的。因此,社会和个人都有打破习惯、改变习惯的需要。
年轻一代从上一代那里继承、学习已有的习惯是必然的,因为每个人都诞生于一个先于自身存在的习惯世界。但只有继承、学习,显然是不够的,年轻一代也要有他们自己的习惯。每一代人新习惯的形成,对社会来说都是一个进步的机会。习惯与作为集体习惯的风俗,都有自身的延续性,一旦形成,就比较难以改变。比如利用人的好斗本性编织而成的暴力与战争倾向,利用原始占有本能而形成的自私与物欲倾向,都需要通过教育在年轻一代那里得到化育与疏解,不然随着这些不良倾向的强化,人类就会走向冲突不息、物欲横流的不归路。在人类历史上,很多类似的不良习惯,都以本能为掩护大行其道。其实,本能无罪,有罪的是对本能的利用。已经形成的恶习具有顽固性,但每一代人都有克服这些恶习的机会。教育本身就是一个专门辅助年轻一代与人类恶习斗争的活动,用以化育本能,克服旧有恶习的诱惑,形成新的属于年轻一代的习惯。正是教育活动的存在,人类才不至于被恶习引向不归路。
走进学校的学生已经是“习惯丛”。一个又一个的“习惯丛”是教育的基础和出发点,没有这些“习惯丛”,教育则无从入手。从学生的角度看,在走进学校之前形成的习惯是他们感知学校环境与教育的中介,也是他们进行体验、思考活动的基础。从教育的角度看,学生已有的习惯显然有好有坏,教育的一个入手点就是巩固学生的好习惯,矫正坏习惯。当然,教育的使命不尽于已有习惯的培养与矫正,新习惯的培养才是焦点所在。孩子都是从自身出发与世界交流的,家庭虽然重要,但在很大程度上还是自我的扩大,而教育则是站在人类的立场上与每一个人对话,教育所要培养的,就是“抬起头来凝望自身之外的世界”的各种习惯,包括超越当下、当地、个人偏好的习惯。
GPL-1主要受进食和神经内分泌等因素的调节,由回肠和结肠黏膜L细胞分泌。GPL-1作为胰高血糖原基因翻译后加工的裂解产物,其主要组成成分为氨基酸,在人的机体内以 GLP-1(7-37)和 GLP-1(7-36)NH2 两种形式存在[4]。其中,天然GLP-1的主要存在形式为GLP-1(7-36)NH2,且其生物活性最强。此外,GLP-1主要分布于胰腺管、胰岛、甲状腺细胞、肾脏、肺、胃肠道等多种组织中,具有多效性。
习惯改变不是容易的事情。如前所述,习惯就是偏好,改变习惯就是拂逆自己的偏好,往往让我们感到不舒服,甚至是痛苦,即使改变的是坏习惯。习惯是在人与环境的互动过程中形成的,习惯里有环境的因素,改变习惯的一个有效方式是从改变环境开始。学校就是一个不同于家庭和社会的环境,学生进入学校,生活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这种变化也就意味着习惯变化的开始。学龄儿童,作为社会的新成员,一进入学校,就开始改变诸多在家庭和社区生活中已经形成的习惯,并在学校环境的引导下逐步形成诸多新的习惯。在教育过程中,基于习惯改变的需要,学校和教师也可以通过改变小环境、微环境来促进学生不良习惯的改变。比如,一个竞争激烈的班级,学生之间更容易形成互相戒备、互相排斥的习惯,要想改变这类习惯,最有效的方式不是说教,而是改变竞争性环境。此外,学校作为正规教育机构有自己的习惯偏好,而这种偏好则是学生习惯形成的环境因素。学校也会因为自身偏好的固化而导致学生习惯的固化。因此,作为自觉的教育机构,学校应该具有一个基本的品质,即不断反思自身、不断改进自身。这种反思与改进即关乎学校的活力,更关乎学生习惯的改变与发展。
当前,郑州市正在全面建设创新型、服务型、国际化、现代化大都市和都市型现代农业,打造中原经济区核心增长区,努力发挥在中原经济区建设中的龙头作用、重心作用和示范带头作用,这对郑州市农田水利现代化建设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也是郑州市农田水利自身向更高水准、更新阶段发展的需要。
另一个改变习惯的方式就是帮助学生将习惯从意识之外纳入意识之内。习惯是与自我一体的存在,一般情况下我们很难将习惯意识化、对象化。未进入意识的习惯,我们的主观意志就很难对其产生作用,更谈不上改变。因此,要想改变某些习惯,首先要做的是将其纳入意识之内。教育,尤其是人文教育,其使命就在于帮助年轻一代认识自身。宏观上,教育应该从学生自身经验出发,在学生自身经验的基础上走向更深广的人类文化。在这一过程中,既有对学生自身习惯的观照,又有以人类文化为镜鉴的返照,两者都是将习惯对象化、意识化。微观上,教师作为教育引导者,可以直接把学生的某些不良习惯凸显出来,让自在的习惯进入学生的视野。对年轻一代来说,他们自己的习惯对他们具有隐藏性。而这种隐藏性正是教育的一个切入点,教育所要做的,就是通过宏观与微观的方式拨开迷雾,让学生看到自身那些隐而不彰的习惯。当然,习惯进入意识只是改变的第一步,因为习惯的改变与形成一样都是一个持续的过程,需要耐心与坚持。在改变习惯的过程中,教育一方面要给学生足够的支持和帮助,另一方面,也要在教育过程中有意识地培养学生的毅力和意志力。
参 考 文 献:
[1] 杜威.杜威全集·中期著作(第十四卷)[M].罗跃军,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78.
[2] 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M].廖申白,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35.
[3] TOM SPARROW and ADAM HUTCHINSON(eds.). A History of Habit: From Aristotle to Bourdieu[M]. Lanham: Lexington Books,2013:52.
[4] 理查得·J. 伯恩斯坦.根本恶[M].王钦,朱康,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5:19-20.
[5] 柯永河.习惯心理学[M].台北:台湾张老师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365.
[6] STEPHEN PRATTEN. Dewey on Habit,Character,Order and Reform[J]. 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2015,39(4):1031-1052.
[7] NICK CROSSLEY. The Social Body:Habit,Identity and Desire[M]. London:SAGE Publications,2001:143-149.
[8] OSWALD FUCHS,O.F.M. The Psychology of Habit According to Willian Ockham[M]. New York:The Franciscan Institute,1952:5.
[9] 高兆明.论习惯[J].哲学研究,2011(5):66-76,128-129.
[10] 杜威.民主主义与教育[M].林宝山,译.台北: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89:44.
[11] 汉娜·阿伦特.责任与判断[M].陈联营,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7.
Rethinking Habit and Habit Fostering
GAO De-sheng
(Institute of Curriculum and Instruction,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62, China)
Abstract : Habit still has great vitality in daily discourse, but it has declined in the discourse of education theory. It can be said that habit is a concept corrupted by behaviorism. To get rid of the influence of behaviorism, we need to reunderstand and reconstruct the concept of habit. The self is formed by habit and virtue also needs to be accomplished through habit. The habit is between body and mind and derived from body and mind. When it works, the habit embodies the “Double Law”, but actually it is “A Law”. Education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formation of habit. It is not only the environmental factor of habit formation, but also acts on the cultivation of habit through action and deliberation. Of course, education is also a crucial way to change habit.
Key words : habit; formation of habit; education; habit fostering
收稿日期: 2018-10-22
作者简介: 高德胜(1969—),男,河南人,华东师范大学课程与教学研究所教授,主要从事教育基本原理、德育原理、德育课程研究。E-mail:gao6403@163.com
基金项目: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生活德育的理论深化与实践推进研究”(项目编号:16JJD880027)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中图分类号: G40- 0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1298(2019)03-0017-11
DOI: 10.14082 /j.cnki.1673-1298.2019.03.003
(责任编辑 李 涛)
标签:习惯论文; 习惯形成论文; 教育论文; 习惯培养论文; 华东师范大学课程与教学研究所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