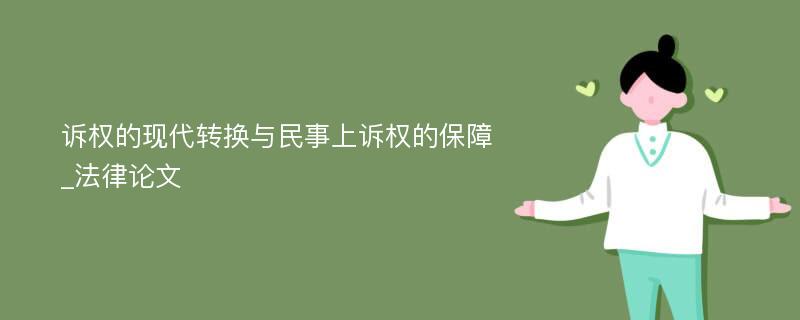
诉权的现代转型与民事上诉权之保障,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诉权论文,民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92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951(2005)06-0040-07
一、诉权的现代转型
宪法和法律赋予国民以自由权、人身权和财产权等权利,同时也相应地保障国民在这些权利受到侵害或发生争议时,平等而充分地寻求诉讼救济的途径。正如法谚所云:“救济先于权利”(Remedy precedes rights);“没有救济的权利不是真正的权利”(A right without remedy is not right)。如果某一权利在受到侵犯之后,受害者根本无法诉诸司法裁判机构,也无法获得任何有效的司法救济,那么,该权利的存在将毫无意义[1]。为此,国家有义务为国民提供司法保护,即以国家的审判权保护国民的合法权益。换言之,为实现民事诉讼的目的,必须对国民开放诉讼制度,使国民享有向国家请求利用这一制度的权能,即诉权[2]。诉权是当事人获得司法救济,实现权利的前提和基础。
“二战”以后,民事诉权逐渐超越了单纯的诉讼法意义而实现了向宪法诉权的转型。传统的诉权概念也逐渐被接受公正审判权、裁判请求权、诉诸司法权、程序保障请求权、接近正义权、接近司法权等现代话语所取代①。
诉权的现代转型首先表现为,许多国家的宪法确认接受司法裁判权是人民享有的一项由宪法保障的基本权利,诉权保障呈现宪法化的趋势。例如,在日本,1946年《宪法》第32条规定:“任何人皆享有不可剥夺的接受法院裁判的权利(No person shall be denied the right of access to the court)。”在意大利,1947年《宪法》第24条规定:“全体公民都有权向法院提起诉讼以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All are entitled to institute legal proceedings for the protection of his own rights and legitimate interests)。”
诉权的现代转型还表现为许多国际法文件对当事人的诉权保障作了明确规定,诉权因此上升为一种基本的人权,诉权保护呈现国际化的趋势。1948年《世界人权宣言》第8条规定:“任何人当宪法或法律所赋予他的基本权利遭受侵害时,有权由合格的国家法庭对此种侵害行为作有效的补救。”[3] 1966年《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将“受公正审判的权利”(right to a fair trial)作为民主法治社会中公民所享有的一项基本人权②。此外,《美洲人权公约》、《非洲人权和民族权宪章》、《欧洲人权公约》等区域性人权公约也都把裁判请求权纳入其中,作为人权保护的一项重要内容。
上诉权是诉权的体现和延伸。对上诉权的保障,是司法公正的应有之意。上诉制度是司法体制的重要构成部分,担负着多样化的司法功能③,并且需要在不同的价值目标之间进行平衡与取舍④。由于现代社会的急剧变迁,许多国家的民事上诉制度无论是在制度设计还是实际运作上均面临着种种问题,并进而影响着整个司法制度的有效运行。在我国,由于制度设计上固有的缺陷,加之司法实践中颇具中国特色的请示报告之风盛行,再审程序启动的随意性大,“终审不终”的现象普遍存在,民事上诉制度在理论与实践两个层面上均存在着比其他国家更难以克服的问题[4]。
应当指出的是,在欧洲人权公约或其他国际人权文件中,虽然都没有明确规定对民事上诉权的保障,但是,学理上认为可以间接地通过对“受公正审判的权利”的解释来解决这一问题。同时,欧洲法院以及欧洲人权委员会已在实践中发展了这方面的法理[5]。“宪法权利观念由少数国家传播为一个普遍概念,成为国际法和国际政治的重要内容,这种人权的国际化是20世纪中期的现象。”[6] 诉权保障的国际化趋势正是在这种大的背景下产生的⑤。
意大利法学家卡佩莱蒂认为,影响当事人实效性接近正义/司法的障碍主要有五个方面的因素:(1)律师费;(2)法院成本和其他经济负担;(3)诉讼的必要费用与诉讼标的金额的比例不均衡(这一障碍在小额请求案件中表现尤其突出);(4)诉讼迟延;(5)其他接近司法救济的事实上的障碍,如对专家协助日益增加的需求、当事人的愚昧无知,等等[7]。美国法学家伦斯特洛姆认为,影响对法院的诉求的因素有技术性的,也有结构性的和环境上的。技术因素确定入门的条件,它包括管辖权及可司法解决的事项;结构因素主要指法院的组织结构和承办案件的法官数量;环境因素包括积案之类的影响[8]。归结起来,影响当事人行使接近正义/司法权利的普遍性因素主要是:诉讼的成本、解决争议所需要的时间以及司法制度发现事实真相和适用法律的正确程度[9]。可以说,20世纪以来在世界范围内兴起的三次“接近正义”运动的浪潮⑥,主要是针对许多国家的民事司法制度未能向纠纷当事人提供高效、低廉、公正的纠纷解决机制而出现的。而在中国,民事司法改革所要解决的问题基本涵盖了影响当事人实效性地利用司法制度的各种机能性或结构性的问题。具体到民事上诉制度,这些问题集中体现在对当事人行使上诉权的保障方面。它涉及三个方面的内容,即上诉权的行使是否自由,上诉权形成的“法的空间”能否满足当事人的权利救济需求,上诉权行使的结果能否产生预期的制度效果。
二、基于权利行使自由的上诉权之保障
我国的民事审判方式改革发轫于20世纪80年代末,其产生的背景与国家推行市场经济和依法治国方略带来的深刻社会变革有直接的关系。市场经济的改革和发展,特别是市场经济劳动分工中隐含和要求的自由、平等、公正以及必然带来的效率为民事审判方式改革乃至整体司法改革提供了基本的动力[10]。由于整个社会正处于向市场化和法治化迈进的阶段,因此,无论是全能政府的治理模式还是超职权主义的诉讼模式都因市民社会的复活和国家与社会分际的重新界定而面临着转型。国家治理模式的转型使政府固有的部分管理权力释出,提高了公民的自主性,扩大了社会自治的空间。诉讼模式的转型则意味着法院职权的弱化和当事人处分权的强化。这是由于,我国自1949年以后实行的民事诉讼制度基本上是苏联模式的翻版,这种诉讼模式具有强烈的职权主义色彩,“法院在诉讼中居于领导的地位,它引导诉讼参加人的诉讼活动,并促使他们行使和履行自己的诉讼权利和诉讼义务”[11]。而当事人在诉讼活动中不仅没有独立的程序主体地位,而且其程序参与权也没有得到充分的保障。民事审判方式改革的推行改变了这种局面,确立了当事人在民事诉讼中的主导地位。
有学者指出,当前,强化当事人处分权可以使民事诉讼制度更加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有利于保障民事诉讼中的人权,防止法院滥用职权[12]。处分权是诉权的应有之义。在当今世界,对诉权的保障日益呈现出宪法化和国际化的发展趋向[13]。为了强化对当事人上诉权的保护,在上诉审程序中更好地贯彻处分原则,使我国的民事上诉制度适应诉权的保障水平日渐提升和强化当事人处分权的趋势,有必要在上诉审程序中确立不利益变更禁止原则⑦。
所谓不利益变更禁止原则是指上诉审法院对上诉案件的审理,不论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全部或部分地被支持,其判决既不能加重上诉人的民事责任,也不能减损上诉人应得的民事利益,其负担不得因上诉而超过原审判决[14]。日本《民事诉讼法》第304条关于“撤销或变更第一审判决,只在声明不服的范围内可以进行”的规定,以及德国《民事诉讼法》第536条关于“对于第一审的判决,只能在申请变更的范围内变更之”的规定,被认为是民事上诉审程序确立不利益变更禁止原则的典型立法例。法律赋予对立的当事人平等的上诉权,一方上诉而另一方未上诉,表明未上诉方已放弃或视为放弃部分权利,这是其行使处分权的表现。允许二审法院加重上诉人的责任的做法,既违背了处分原则,同时也有失诉讼公正[15]。从理性预期的角度看,当事人提起上诉的目的是希望得到比一审裁判结果更为有利的裁判,如果上诉审法院可以不顾当事人上诉请求的范围,在上诉请求外加重上诉人的民事责任或减少上诉人的应得利益,将上诉人置于比一审裁判更加不利的境地,那么当事人很可能会放弃上诉权的行使,接受一审裁判,这将导致上诉审制度形同虚设。因此,民事诉讼法确立不利益变更禁止原则,在保障当事人行使上诉权的同时,实际上也起到了维持上诉制度功能正常发挥的作用。但是,应当看到,不利益变更禁止原则的适用有其例外的情形:一是双方当事人不服一审裁判均提起上诉或一方当事人提起附带上诉⑧,双方当事人上诉请求重叠的部分不受不利益变更禁止原则的限制;二是一审裁判在上诉请求之外确有错误,违反了法律的强制性规定或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上诉审法院对此部分内容可进行变更而不受不利益变更禁止原则的限制。
在我国,基于上诉权行使自由的上诉权之保障的另一项重要内容是应当确实消除法院对上诉人行使撤诉权的不当干预。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一条规定:“宣判前,原告申请撤诉的,是否准许,由人民法院裁定。人民法院裁定不准许撤诉的,原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可以缺席判决。”第一百五十六条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判决宣告前,上诉人申请撤回上诉的,是否准许,由第二审人民法院裁定。”由上述规定可以看出,无论在第一审程序还是在第二审程序,法院对当事人申请撤诉都要加以审查,体现了法院对当事人自由行使诉权/上诉权的强烈的职权干预。民事诉讼解决的是私权性质的纠纷,法院在纠纷解决中处于消极的地位,实行不告不理的原则。据此,当事人撤回上诉即表明不再要求法院对纠纷进行审理和裁判,在实际效果上类似于未将某一民事纠纷提交给法院处理,因此,法院在当事人要求撤诉后仍进行积极的职权干预,与民事诉讼“不告不理”的性质不相符合。在法律对当事人以撤诉的方式规避法律或损害他人权益的行为予以规制的前提下,应当变上述“审查式”的规定为“应当准许式”的规定,从而更充分地体现上诉权行使的自由度。为防止当事人滥用上诉权,还应当规定由撤回上诉的当事人承担消灭诉讼所需的费用。
三、基于权利行使空间的上诉权之保障
大陆法系国家(如德国、日本)根据审级及裁判的形式,将上诉分为控诉、上告及抗告三类。其中,控诉相当于三审终审制中的第二审上诉,上告相当于第三审上诉,而抗告则是对判决以外的裁定、决定及命令的独立上诉方法。英美法系与大陆法系的抗告相类似的制度是中间上诉(interlocutory appeal)制度⑨。这种上诉制度适用于当事人对初审法院审理案件过程中具有战略意义的命令、裁定等程序性问题(包括具有普遍重要性的法律争议)不服所提起的上诉[16]。
判决以外的裁定、决定或命令是针对案件审理过程中的程序性问题作出的。尽管当事人可以在针对判决提出的上诉中,要求上诉审法院对一审法院作出的裁定、决定或命令进行附带审查,但是这种附带审查无法被当事人以外的其他利害关系人援用。从诉讼效益的角度看,允许当事人就一审过程中的程序性决定提起上诉至少有两方面的好处:一是可以避免在确定这些程序性决定的正确性时迟延;二是即时确定这些程序性决定的正确性可以防止初审法院漫长的诉讼[17]。因此,无论是为了保障当事人本人,还是保障当事人以外的利害关系人的权益,都有必要设立不服裁定、决定或命令的专门救济程序,并赋予该程序独立的价值。
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未设抗告程序,针对裁定提起的上诉仅限于不予受理、驳回起诉以及对管辖权异议的裁定三种。由于可上诉的裁定的范围十分狭窄,对裁定享有上诉权的主体单一,加之对于裁定的上诉审程序极为简单,这就大大限缩了上诉权行使的空间。对此,有学者指出其在实践中至少有两个弊端:一是现行的民事裁定上诉审程序是在“重实体、轻程序”的思想指导下确立的,反过来,这种程序又助长了民事诉讼中的轻程序现象,从而极大地阻碍了民事诉讼程序现代化与法治化建设的进程。二是现行的民事裁定上诉审程序不利于保护当事人等利害关系人的权利。因为可上诉的裁定的范围过于狭小及上诉主体单一化必然会直接影响到当事人等利害关系人的诉讼权利的充分享有和行使,而诉讼权利缺乏充分、有效的保障又会进而危及实体性权益的保护。[18] 决定是法院针对诉讼过程中发生的特殊程序性事项作出具有约束力的意见的另一种方式。现行民事诉讼法规定,当事人对回避、罚款或拘留决定不服的,可以申请复议一次。虽然有关规定赋予当事人申请复议的权利,但是,这种申请只能向作出该决定的法院提出,并且在复议维持原决定的情况下,当事人无权向上一级法院上诉。如果把申请复议视为不服决定的当事人与法院之间发生的一种“诉讼”,上述规定显然违反了程序中立性有关“与自身有关的人不应该是法官”[19] 的要求,因此,它对当事人相关权利的保障也必然是不充分的。笔者认为,克服上述弊端可行的办法是建立功能上相当于抗告或中间上诉的程序。在具体的程序设计上应当明确的问题有:
1.判决之外可以提起上诉的范围,应包括法律不要求法官举行言词辩论即可驳回有关程序申请的裁定或决定。因此,除不予受理、驳回起诉以及对管辖权异议的裁定外,财产保全或先予执行的裁定、中止或终止诉讼的裁定、不予执行仲裁裁决、驳回回避申请的决定、驳回执行申请的裁定、对诉讼参与人或案外人作出罚款或拘留的决定等影响当事人或利害关系人的实体或程序权益实现的裁定或决定都应允许提起上诉。
2.为防止潜在的少数人通过上诉来达到拖延诉讼的企图,对不服裁定或决定的上诉一律实行上诉许可制度,由上诉人向作出该裁定或决定的法院提出,原审法院认为上诉理由成立的,应立即自行更正;否则,应在法定期限内将当事人的上诉申请移送上级法院裁决;在紧急情况下,上诉人也可以在法定期限内向上级法院提起即时上诉,即时上诉具有停止原裁定、决定执行的效力。
3.终局判决规则(final-judgment rule)是上诉审制度的重要规则⑩。它是指一方当事人必须暂时搁置其所有反对意见,直到初审法院完全结案,才能提起上诉[20]。对一审过程中作出的裁定、决定提起上诉是这一规则的例外。由于案件审理过程中可能针对程序性问题作出裁定或决定,因此,为避免中间上诉拖延初审法院审理案件的正常进度,对不服裁定或决定提起的上诉原则上不采用言词辩论的方式进行审理。
4.除非所涉问题属于具有特别重要意义的法律争议并且法律对此作了明确规定,二审法院针对裁定或决定的上诉作出的裁判是终审裁判,不允许进行二次上诉。
四、基于权利行使实效的上诉权之保障
如果说基于权利行使自由和权利行使空间的上诉权之保障主要是民事上诉程序体制内的问题,那么基于权利行使实效的上诉权之保障则超出了民事上诉制度本身,而关涉到整个诉讼体制。权利行使的实效性是指权利的行使应当能够产生预期的制度效果。权利的行使如果不具实效性,权利就会沦为制度上的摆设。因此,上诉权行使之保障应当考虑上诉权在现实的法律世界中能否得到实现。在我国,影响上诉权行使的实效性的因素主要有两方面,一是民事司法中一度盛行的案件请示制度,二是再审程序启动的随意性问题。
(一)案件请示制度
案件请示制度是在法院系统内部历史地形成的,它是指下级法院对案件审理过程中遇到的实体或程序问题,以书面或口头的形式向上级法院请示,上级法院予以答复的一种非成文的制度[21]。我国司法活动中的案件请示做法由来已久,它虽然在法律上没有明文规定,但在审判实践中却非常普遍,并且得到司法解释的认可。最高人民法院分别于1986年3月24日和1990年8月16日下发了《关于报送请示案件应注意的问题的通知》和《补充通知》,对此加以规范,使之制度化[22]。究其根源,有学者指出,在我国,上级法院相对于下级法院而言,不仅享有全面的审查权,而且在处理下级法院的错误时享有广泛的自由裁量权,既可以发回重审,也可以自行处理(改判或调解)。而下级法院相对于上级法院而言,则不享有完全独立的审判权,所以一审法院在诉讼进行中经由请示汇报以寻求提前“指导”便成为一种具有合法性的制度或惯例[23]。考察近代中国法制史,应当承认,在立法相对滞后、各级法院法官素质参差不齐的情况下,案件请示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统一法律的适用,提高下级法院的办案质量,但是,从司法公正的角度看,它并不符合独立审判原则内生的上下级法院之间相互独立的要求,并且导致上诉权被变相剥夺,两审终审成为实质上的一审终审[24]。
法院独立审判,只服从法律。因此,与行政机关和立法机关相区别,法院上下级关系在性质上独具特色。如果说行政机关遵循下级服从上级原则的话,法院则无所谓上级。每一级法院都应当是独立的。之所以要设置不同审级的法院,并不是要建立一种上级控制下级的机制。固然,上级法院可以改变下级法院的判决,但这只是为司法判决增加一道审核程序,使得相关决策更加审慎,减少错误。实际上,在案件审理过程中,上下级法院通常有分工上的区别。在英美法系国家,第一审法院被称为“审理法院”(trial court),第二审法院则名为“上诉法院”(appellate court or court of appeal)。这样的区分意味着一审法院的主要功能在于对案件事实加以审查,并根据法律对由证据证明的事实作出裁判。二审法院原则上不再审查事实,不接受新证据,只是对审理法院的审理过程是否严格遵循了法定程序,对法律的解释和适用是否妥当加以审查;如发现不妥,上诉法院可以改判或发回重审。此外,上诉法院的任务还包括力求司法标准的统一性以及对司法过程进行不同政策导向上的调整。至于位于一国司法体系顶端的最高法院,更是协调整个司法运作的关键角色。因此,上级法院有权改变下级法院的判决,并不意味着后者成为前者的下属。正如联合国经济与社会理事会1987年8月通过的《世界司法独立宣言》所指出的:“每个法官均应自由地根据其对事实的评价和法律的理解,在不受来自任何方面或由于任何的直接或间接的限制、影响、诱导、压力、威胁或干涉的情况下,对案件秉公裁决。”(第2条)“在作出裁决的过程中,法官应对其司法界的同行和上级保持独立。司法系统的任何等级组织,以及等级和级别方面的任何差异,都不应影响法官自由地宣布其判决的权力。”(第3条)[25]
司法独立不但表现为法院整体的对外独立,还应当表现为法院系统内部的独立和法官的独立。上下级法院之间只存在相互独立的审级关系,而不存在隶属和服从关系。一个法院的司法裁判活动不受另一个法院的干预。上级法院除依上诉等程序对下级法院的审判行为予以监督外,无权就司法裁判事项主动向下级法院发布命令、指示,或进行直接的干预和监督;对下级法院裁判过的案件,只能在下级法院裁判结论产生、争议方提出新的诉讼请求后,才能受理并重新开始裁判活动[26]。
根据审级原理,上级法院有权改变下级法院的判决,这就使得请求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裁判进行审查,成为当事人所享有的一种权利。实现这种权利的前提便是上下级法院之间相互独立,作出决定的过程相互分离。否则,如果下级法院成了上级法院的下属,下级法院经常就案件的判决请示其上级,或者上级对下级进行监督(所谓“提前介入”),就如何判决作出指示,甚至直接作出具有拘束力的批复,这样的做法必然导致法院上下级的设置变得毫无意义。它所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使我国诉讼法所设置的上诉制度形同虚设[27]。
(二)再审程序启动的随意性
我国的再审程序是指法院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民事裁判、调解协议发现确有错误,依法再次进行审理所适用的程序。从一定意义上说,再审程序与上诉审程序设立的目的有某些相同之处,二者都具有消除和纠正已形成的裁判中错误的积极的作用。一般认为,再审程序是民事诉讼程序的一项补救制度,是对两审终审制的一种必要的补充。然而,由于再审程序启动的随意性,导致人民法院终审裁判的权威性受到极大的削弱,并进而影响到民事司法的整体权威性。一方面,现行法律对法院依职权决定再审无论在对象、理由与时限上均无明确的限制,“不论什么时候,不论当事人的意思如何,只要发现裁判确有错误,都可以提审或再审,这不仅有害于当事人之间权利关系的安全性、稳定性和生效裁判的权威性、稳定性,而且严重违反诉讼时效制度”[28]。另一方面,由于检察机关拥有充分的启动再审的权力,许多当事人放弃了正常上诉权的行使,把主要精力投入到不需要支付诉讼费的检察机关的抗诉监督上。有的检察机关为了完成上级下达的抗诉案件指标,甚至鼓励当事人不上诉而直接向检察机关申诉[29]。由于上述原因,近年来,再审案件逐年上升。以浙江省为例:1999年,全省法院审结民事再审案件1932件,其中检察院抗诉案件306件,占总数的15.84%;2000年,审结民事再审案件2306件,其中检察院抗诉案件528件,占22.9%;2001年审结民事再审案件2361件,其中检察院抗诉案件588件,占24.9%。仅2001年,浙江省市一级检察院就基层法院所作一审生效判决提出抗诉的案件多达461件,其中台州市就有63件[30]。再以山东省为例:1999年因检察机关抗诉进入再审程序的案件为600件,比1998年增长45.63%;2000年激增至1110件,同比增长幅度高达85%[31]。再审程序启动的随意性导致上诉制度沦为虚设,因此,它实际上也影响和阻碍了诉讼法所设计的民事上诉权的正常行使。
未来我国建立有条件的三审终审制(11),在对上诉权作审级上区分的同时,应当一并考虑法院系统内部的案件请示制度和民事案件检察监督制度的存废问题。关于案件请示制度,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指出:“各个审级的人民法院都应当依照法律独立地对案件进行审理和裁判,除适用法律问题之外,不得就证据、事实等问题向上级法院请示。”[32] 但是,从长远看,应当废除案件请示制度。至于检察机关发动再审程序的范围,应当限制在公益案件范围内;对不涉及公益的一般民事案件,检察院不应发动再审[33]。与此同时,废除人民法院依职权决定再审的规定,完善当事人申请再审的程序[34]。
注释:
①有学者提出了“诉讼权”的概念,即“公民在认为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侵犯或有纠纷需要解决时,享有的诉诸公正、理性的司法权求得救济和纠纷解决的权利。”该学者指出,在现代社会,诉讼权具有基础性和广泛性,存在于各诉讼领域。举凡民事诉讼、行政诉讼、宪法诉讼、刑事诉讼都存在着对诉讼权的保障和落实问题。在民事诉讼领域,诉讼权以起诉权、应诉权、反诉权、上诉权、再审请求权等方式得以全面体现。参见左卫民等著:《诉讼权研究》,法律出版社,2003.2~3.
②《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4条第1款:“所有的人在法庭和裁判所前一律平等。在判定对任何人提出的刑事指控或确定他在一件诉讼案中的权利和义务时,人人有资格由一个依法设立的合格的、独立的和无偏倚的法庭进行公正和公开的审讯。”参见北京大学法学院人权研究中心编:《国际人权文件选》,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20.
③一般认为,上诉审制度的功能包括吸收不满、纠正事实错误、促进法律适用的统一以及巩固司法体系的合法性等。参见[美]罗杰·科特威尔著,张文显等译:《法律社会学导论》,华夏出版社,1989.269~271.
④根据英国学者Stuart Sime的解释,这种矛盾是在鼓励判决的终局性与纠正判决的错误之间求得平衡(balance between encouraging finality and correcting mistakes)。参见Stuart Sime,A Practical Approach to Civil Procedure,Blackstone Press Limited,2000,p.489.
⑤参见《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2条第3款:“本公约每一缔约国承担:(1)保证任何一个被侵犯了本公约所承认的权利或自由的人,能得到有效的补救,尽管此种侵犯是以官方资格行事的人所为;(2)保证任何要求此种补救的人能由合格的司法、行政或立法当局或由国家法律制度规定的任何其他合格当局断定其在这方面的权利;并发展司法补救的可能性;(3)保证合格当局在准予此等补救时,确能付诸实施。”
⑥“接近正义”(Access to Justice)是20世纪90年代西方各国民事司法改革的口号。关于“接近正义”的三次浪潮的具体介绍,参见范愉主编:《ADR原理与实务》,厦门大学出版社,2002.145~147.
⑦应当指出,国内也有个别学者否定不利益变更禁止原则,见冯仁强:《评“民事上诉禁止不利益变更原则”》,载《法学》2001年第8期。
⑧附带上诉是指一方当事人提起第二审上诉后,被上诉人于已经开始的第二审程序中也提起的上诉,要求变更于己不利的部分。参见[日]我妻荣(编辑代表):《新法律学辞典》,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1.828~829.“附带抗告”、“附带控诉”、“附带上告”诸条目。
⑨参见美国《布莱克法律词典》对" interlocutory appeal" (中间上诉)的解释:An appeal that occurs before the trial court' s final ruling on the entire case.Some interlocutory appeals involve legal points necessary to the determination of the case,while others involve collateral orders that are wholly separate from the merits of the action.See Black' s Law Dictionary,West Group,1999,p.94.
⑩参见美国《布莱克法律词典》对" final-judgment rule" (终局判决规则)的解释:The principle that a party may appeal only from a district court' s final decision that ends the litigation on the merits.Under this rule,a party must raise all claims of error in a single appeal.See Black' s Law Dictionary,West Group,1999,p.644.
(11)关于我国未来建立有限三审终审制的探讨,参见杨永波、张悦:《建立一审终审与三审终审相结合的审级制度》,载《法律适用》2003年第6期;齐树洁:《构建我国三审终审制的基本思路》,载《法学家》2004年第3期;孙谦、郑成良主编:《司法改革报告——中国的检察院、法院改革》,法律出版社,2004.214~216.
标签:法律论文; 民事诉讼当事人论文; 诉讼参与人论文; 法制论文; 日本宪法论文; 上诉期限论文; 法院论文; 司法程序论文; 宪法监督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