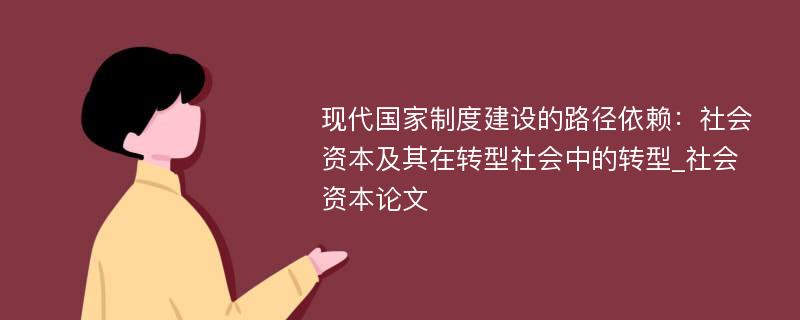
现代国家制度构建的路径依赖:变革社会中的社会资本及其转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论文,路径论文,资本论文,制度论文,国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0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8477(2007)11-0021-03
新制度主义的分析视野中,社会资本正日益成为一个重要概念。新制度主义把制度看作“包含着一套以章程和规则为形式的行为约束,一套从章程和规则出发来检测偏差的程序,最后还有一套道德、伦理的行为规范,这类规范限定了章程和规则的约束方式的轮廓。”[1] 因此,制度变迁也就不仅意味着一系列正式规则的变迁,而且还意味着那些包括传统、道德、习俗等等在内的非正式规则的变迁,意味着一整套正式规则的建立后能否与特定社会的非正式规则体系取得良性互动。而社会资本理论恰好为我们提供了在理解国家制度变迁的过程中制度与文化互动关系的整合视角。
现代国家制度构建过程中的所有制度安排都会受到一系列特定社会资本的重大影响,任何一种现代国家制度安排的成功,都最终取决于与此相关联的社会资本的发育。然而,不同社会因其历史传统、文化习惯、生存环境和发展阶段的差别,其社会资本存量和类型都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其与不同的国家制度安排的“契合度”也相应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而每一个社会的现代国家制度的构建都是在这一不同的社会资本背景下展开的,社会资本的存量和类型的差异极大地制约着现代国家制度构建的路径选择及其绩效。现代国家制度构建作为一个系统的制度变迁过程,其变迁道路的选择、艰难复杂程度以及绩效的差异,最终也就取决于当事国与这一体制相契合的社会资本存量的增长以及其传统社会资本向现代的转型。
在帕特南看来,任何社会都是由一系列人际沟通和交换网络构成的,这些网络既有正式的,也有非正式的。其中一些以“横向”为主,把具有相同地位和权力的行为者联系在一起,称之为“网状”(web-like)网络;另一些则以“垂直”为主,将不平等的行为者结合到不对称的等级和依附关系中,称之为“柱状”(maypole-like)网络。[2](p203)据此,我们可以把不同社会的社会资本划分为两种基本类型,即“公民参与网络”型社会资本和“垂直柱状网络”型社会资本。
近代以来,作为社会现代化的核心议题,现代国家制度构建的目标是实现国家制度的理性化和民主化。从历史经验来看,现代国家制度必须建立在市场经济、公民社会的基础之上,还有赖于公民文化的支撑。这些构成了现代民主国家的社会基础——“公民参与网络”型社会资本。这种社会资本以契约信任、公民文化和公民社会为基本要素,是诸如英国、北美或意大利北部地区等社会的基本特征,由一系列公民团体和公共生活参与网络所构成,即费孝通所谓“团体格局”。[3](p25)托克维尔认为,自主治理的民情使得美国人习惯于用结社治理公共事务,大量的结社节约了公共领域运作的成本,培育了公共精神,对美国的民主产生了深远影响,这正是美国民主的“灵魂”;而帕特南的研究则进一步表明这种“公民参与网络”社会资本对促进现代国家制度成功的意义,是理解“使民主运转起来”的一把钥匙。“对于民主制度的绩效来说,至关重要的要素是普通公民在公民社会中充满活力的群众性基层活动。”[2](p2)
然而,并不是所有国家的政治转型和现代国家制度构建的一开始就具备“公民参与网络”型社会资本,正如前文所述,这更多的是对西方成功经验的总结和分析。历史经验同样表明,对于今天仍在变革中的大多数非西方的转型社会而言,其社会资本的存量和特性更接近于“垂直柱状网络”型社会资本。所谓“垂直柱状网络”结构,就是指通过以血缘、地缘等为纽带而将地位和权力不平等的行为者结合到不对称的等级和依附关系之中的社会资本网络结构。这样的社会网络结构广泛存在于亚非拉的诸多欠发达国家和地区,包括意大利南部的诸多地区也是,帕特南就是以意大利南部地区作为这一垂直柱状网络结构的典型来与意大利北部地区的“公民参与网络结构”社会资本进行比较研究的。无庸讳言,传统的中国社会就接近于以庇护-附庸关系为特征的“柱状”网络,费孝通先生则称之为“差序格局”。[3](p26,30)在差序格局中,伴随着以个人为中心,从中心格局向外,成员间关系越来越疏远,个体社会资本的存量也逐级递减。而联系差序格局的纽带则是血缘与地缘,个体社会资本的运用也围绕着这种形式展开。杜赞奇则将这种差序格局社会的规范体系称之为“权力的文化网络”(cultural nexus of power),“这一文化网络包括不断相互交错影响作用的等级组织(hierachical organization)和非正式相互关联网(networks of informal relations)。诸如市场、宗族、宗教和水利控制的等级组织以及诸如庇护人与被庇护者、亲戚朋友间的相互关联,构成了施展权力和权威的基础。”杜氏将“文化”视为扎根于这些组织中、为组织成员所认同的象征和规范(symbols and norms),这些规范包括宗教信仰、内心爱憎、亲亲仇仇等,它们由文化网络中的制度与网络交织维系在一起。[4](p5)经验证明,这些对传统中国社会资本类型的特定描述,对于中国近代政治的转型和中国近代国家制度建设历程具有非凡的解释力。
一个社会的网络结构形式以何种形式为主导,主要还是受制于它基本的经济形态。实际上,以血缘、地缘为纽带的社会关系网络即使在公民参与网络为主体的社会也不是完全不存在,只是由于市场经济形态的充分发展,为非血缘关系的人际信任关系的产生和维系提供了“陌生人”之间交往互动、横向联系的机会和平台,通过长期的市场交易行为这一多次重复博弈的过程,逐步降低交易双方的信息不对称性和交易行为的不确定性,交易双方因此将逐步达成一定的互惠的默契并形成规范,从而达致一种“合作均衡”,这就使得普遍的社会信任和合作得以产生和维系。然而,在缺乏市场交换行为的传统经济形态下,封闭的小农经济形态是自给自足的,不同的经济主体之间缺乏交往互动、横向联系的机会和平台,即使有偶尔的交易行为,也多是一次性博弈的过程,这就很难使交易双方获得足够信息来降低信息的不对称性和不确定性,交易双方就不得不面对“囚徒博弈的困境”,导致不信任和机会主义的不合作行为。因此,在传统的小农经济形态下,信任很难跨越这一由血缘、地缘等“熟人”的圈子而拓展到“陌生人”领域和整个社会,进而发展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信任。而长期的传统小农经济形态使得这样一种状态不断重复,“不合作的均衡”(“霍布斯式均衡”)就难以避免。因此,身处“霍布斯式均衡”规则体系中的理性行为者,是很难在非血缘关系的“陌生人”中采取合作的行为选择的,在新制度主义看来,无论何种均衡,一旦达成,就构成了一种规则,它未必是在效率和制度绩效上是最优的,但身处其中的理性的行为者就会受到激励去按既定的规则去行事,即“一旦陷入这种境地,无论它多么具有剥削性,多么落后,任何人试图去寻找具有合作性的别样选择,都是非理性的,除非是在直系家庭里。”[2](p208)而这一行为的选择反过来又进一步强化既有的均衡,从而使得这一规范从一般的规则潜移默化成为一种特定的心理和行为习惯,演化成一种特定的文化形态,当习惯产生,我们就很难再区分这一均衡状态下的行为是理性选择还是只是完全的习惯使然了。
总之,垂直柱状的网络结构由于行为者之间信息和资源的不对称性,尽管能促进网络内部成员的合作,却难以维系整个社会的信任与合作,行为者个体的社会资本难以整合成整个社会发展所需的社会资本,成为小至社区、大至整个社会的“集体行动困境”的根源。它强化的是网络内部掌握更多信息和资源的权威,弱化的是行为者之间平等的交往互动,使得交易行为中处于相对劣势的一方屈从于这一权威,最终导致一种权威主义交往规则的形成,并塑造着行为者权威主义的人格心理习惯。因此,“垂直柱状网络”结构的社会资本形式为传统的等级制和专制主义的统治秩序提供了基本的社会结构支撑,是专制政治得以运作的社会和心理基础。马克思曾精辟地论述过这一状态:“小农人数众多,他们的生活条件相同,但是彼此间并没有发生多种多样的关系。他们的生产方式不是使他们互相交往,而是使他们互相隔离。““由于各个小农彼此间只存在有地域的联系”,所以小农之间不能“形成任何的全国性的联系”,不能“形成任何一种政治组织”。马克思还强调:缺乏组织联系的小农“便是由一些同名数相加形成的,好像一袋马铃薯是由袋中的一个个马铃薯所集成的那样”。“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头上的权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这种权力保护他们不受其他阶级侵犯,并从上面赐给他们雨水和阳光。”[5](p677-678)
在建构理性化和民主化的现代国家制度的过程中,如果忽视了不同社会资本类型的路径依赖效应,指望靠这样一个平台不经改造或直接破坏这一传统,就能完成现代国家制度构建的任务,那就很容易陷入一种幼稚的“制度浪漫主义”并导致制度变迁的失败。在“差序格局”中,规范行动者行为的是这样一种“潜规则”:它运行于传统社会的由血缘、乡缘、学缘和业缘所构成的人情网络之中,成为以利益调节与分配为核心的特殊交往方式,这一规则,合情却不合法,可做却不可说。[6](p213)这种“潜规则”是一种软化制度(正式规则)的“腐蚀剂”,其结果往往是使规则服从于“情理”而不是理性,使法律沦为权力的奴婢,从而消解正式规则的规范性作用,最终使得正式制度难以建立或者即使建立其运作也会因流于形式而失效,或者干脆发生制度的变异,更加强化原先既已存在的统治秩序。杜赞奇在研究以华北农村为典型的近代中国国家政权建设历史中,就发现20世纪前期中国的国家建设过程中,由于忽视“权力的文化网络”的作用,国家政权试图通过无视民意的“赢利型经纪”(entrepreneural brokerage)来加强对乡村社会的渗透和控制,却付出了破坏乡村社会“权力的文化网络”的代价,导致“国家政权的内卷化”,[4](p66-68)最终使得近代中国的整个现代国家制度建设的努力陷入困境,进而引发了新的革命。因此,杜赞奇指出,“直至19世纪末,不仅地方政权,而且中央政府都严重依赖文化网络,从而在华北乡村中建立自己的权威。20世纪国家政权抛开、甚至毁化文化网络以深入乡村社会的企图注定是要遭到失败的。”[4](p5)
不仅中国如此,实际上近代以来各国现代国家制度构建的历史经验都表明,由于社会资本的路径依赖作用,在“垂直柱状网络”结构为主体的社会资本上建设现代国家制度的实验,真正取得成功的案例还屈指可数,我们看到的情景,更多的是这样两种状态:要不是软弱无能的“民主”在动荡混乱的政局变动中风雨飘摇,陷入“软政权化”与分利集团化的陷阱中不能自拔;要不就是穿着现代国家制度的外衣而行传统专制政治之实,演化为专制政治的现代变体——权威政体和极权政体,“有宪法之名,无宪政之实”。这两种政治秩序的后果都是在有形无形中进一步强化原先传统的社会资本形态:低效无能的“民主”常常腐败形影相随,动荡混乱的政治秩序使“公民参与网络”型社会资本的培育和积累失去了基本的环境;① 而顽固稳定的权威政体,尤其是极权政体,较之传统的专制政治,由于技术手段和统治手段的进步,则更加强化了国家的权威,甚至使触角延伸至整个社会的几乎各个角落,其结果是国家与社会之间的界限模糊乃至消失,社会从属于国家,社会发展的空间被压缩殆尽,窒息了社会自身力量和自治能力发展壮大的机会,从而导致社会力量的弱小而无力成为一种制约国家权力的有效力量,使得以理性化和民主化为核心的现代国家制度所赖以支撑的“公民参与网络”型社会资本难以发育,而国家权力自身也常常因其大而无当的统治模式而陷入“什么都管、什么都管不好”的困境,最终导致“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以中间无数个人牺牲为战场,进行一场推移往复的道德战争,要么是前者吞没后者,要么是后者冲毁前者,几经震荡,最后两败俱伤,剩下的只是一堆道德理想国的残垣断壁。而这样的周期震荡,推移往复,既稳定不住政治国家的宪政权威,又稳定不了市民社会的自治机制……”[7](p89)这一后果,反过来又使得这些社会的现代国家制度变迁更加雪上加霜、南辕北辙,正如诺斯指出的,一旦发展被置入了一个特定的轨道,组织化的学习机制、文化习俗和社会意识形态就会强化它的轨迹,最终常常陷入一种“弱国家-弱社会”的“锁定”状态而导致制度变迁的失败。
因此,要在这样的文化土壤上建构理性化和民主化的现代国家制度,其复杂和艰难的程度就可想而知了,正如黄仁宇先生所比喻的那样:这样的制度变迁过程如同“一只走兽,除非脱胎换骨,否则不能兼任飞禽”。[8] 但面对这样一种路径依赖的困境,也并非没有摆脱的方法。正如帕特南在总结意大利南部社会政治制度变迁的经验时所指出的,“改变正式规则能够改变政治实践”,“制度变迁逐渐在认同、价值观、权力和战略上带来了变化”,“新的制度培育了一种更温和、实用和宽容的政治文化”,正式规则的改革引发了非正式规则的变迁,并具有了自我维持功能,尽管“制度历史大多发展得很缓慢”,而在建立互惠规范和公民参与网络上,历史则可能发展得更加缓慢。[2](p216-217)如在强劲的经济市场化的浪潮推动之下,许多传统“差序格局”的“乡土社会”就出现了一种“差序格局理性化”或“工具化的差序格局”的趋势。[9] 但政治和文化系统的变迁仍存在着它自身演变的独立性,因此,要在“垂直柱状网络”结构的社会成功建构理性化和民主化的现代国家制度,就必须在经济发展和由此带来的社会结构变迁和文化结构的变化的基础上不断推进国家制度体系的创新,避免因“作茧自缚”而陷入路径依赖的“锁定”状态,尽量控制正式制度变迁中的“外部效应”对社会资本的负强化作用,从而建立起良性循环的机制。因此,这样的制度创新,就不仅仅是正式制度的创新,同时也是非正式制度的创新过程,即从传统的“垂直柱状网络”结构社会资本向“公民参与网络”结构社会资本转化和变迁的过程,是一种“创造性的转化”。[10] 这一过程比起正式制度的创新,需要创新主体花费更多的时间、耐心和成本,拥有更多的智慧和更好的把握制度创新的技术和艺术的能力,然而没有这一漫长的过程,要取得制度创新的成功是难以想象的,这是任何一个向现代化转型的缺乏“公民参与网络”型社会资本的社会建构现代国家制度都必须面对并必须予以解决的问题。而在这样的传统社会真正的实现在正式规则与非正式规则的良性互动基础上,成功地完成现代国家制度构建与社会资本的现代化转型,也将无疑是对于整个人类文明多样性的全新贡献。
注释:
①社会环境的长期稳定是公民团体发育和成长的重要条件,参见:曼库尔·奥尔森.国家兴衰探源:经济增长、滞胀与社会僵化[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