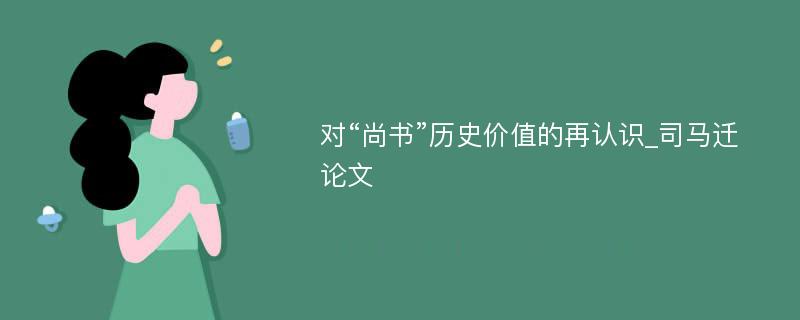
《尚书》史学价值再认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再认论文,史学论文,尚书论文,价值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尚书》是对传统文化影响深远的一部典籍,在整个封建时代,除少数几个人从史学角度审视过它外,人们一直把它作为六经之一来看待,影响了对它思想内涵的正确揭示与把握。近代以来,人们对《尚书》所具有的珍贵史料价值、所蕴含的政治思想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为正确把握《尚书》的价值提供了依据。今天,当我们从史学思想的角度再来审视这部典籍时,我们对它在史学上的价值,会有更进一步的认识。本文拟就从三个方面探讨这一问题。另外,本文不涉及《尚书》的今古文真伪问题,只以学者们考定的、现今流行的今文《尚书》二十八篇作为论述依据。
一、从刘知几到章学诚:对《尚书》史学价值认识的逐步深化
刘知几在《史通·六家》中对随、唐以前史书体裁做总结,把《尚书》作为一种重要的史书著述形式来看待,与《春秋》《左传》《国语》《史记》《汉书》并提。其中心论点有三:
其一,认为《尚书》为记言体史书。所谓“《书》之所主,本于号令,所以宣王道之正义,发话言于臣下”。①此言盖有所本,《汉书·艺文志》六艺略《书》序:“《书》者,古之号令”,《春秋》序:“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只是班固时史部尚不能脱离经部而独立,班固所谓《尚书》,依然是从经的角度审视它,刘知几则明确将其列诸史书之列,不能不说是一个发展。
其二,作为记言体史书,《尚书》的体例是不纯的。刘知几认为《尚书》作为记言体史书,所载应是“典、谟、训、浩、誓、命之文”,但其中“《尧》、《舜》二典,直序人事,《禹贡》一篇,唯言地理,《洪范》总述灾祥,《顾命》都陈丧礼,兹亦为例不纯者也”。②记言记事兼而有之,在刘知几看来是不合史法的。
其三,指出《尚书》这种记言体史书本身存在不可克服的缺点,随着历史的发展,这种体裁也就消失了。所谓“宗周既陨,书体遂废”。后虽有续作者,但终因“理涉守株”,“受嗤当代”,③没能继续存在下来。
刘知几虽拘泥于体例来谈《尚书》,但他在中国第一部史学理论专著《史通》中把《尚书》这部封建时代的经书看做是史书的一种,扭转了人们长期从经学的角度研究《尚书》的局面,无疑是有进步意义的。正如张舜徽所言:“《书》与《春秋》,自来列诸六艺,视为垂世立教之书。昔人纵然目为史之大原,抑未有取与《史》、《汉》并论者。下侪汉人诸作,等量齐观,则自知几始。俾学不囿于经史之分部,而有以窥见著作之本,推廊治史之规,刘氏之功,又不可泯矣”。④
和刘知几相比,章学诚对《尚书》史学价值的认识更深入了一步。他提出“六经皆史”说,“六经皆史也。古人不著书,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⑤把包括《尚书》在内的六经当作史书看待。他在《文史通义》中,以《书教》为名,写了三篇文章阐述自己对《尚书》以及古代史书体裁变革的看法,中心论点如下:
其一,《尚书》作为一种史书撰述形式,体现的重要思想是“因事命篇”,“体圆用神”。章学诚指出,史书的撰述形式要取决于内容,而《尚书》正是这方面的代表。“夫史为纪事之书。事万变而不齐,史文屈曲而适如其事,则必因事命篇,不为常例所拘,而后能起讫自如,无一言或遗而或溢也。此《尚书》之所以神明变化,不可方物”。⑥他批评了刘知几拘泥于史例来谈《尚书》的做法,认为《尚书》并非体例不纯。他说:“《尚书》典谟之篇,记事而言亦具焉。训诰之篇,记言而事亦见焉。古人事见于言,言以为事,未尝分事言为二物也。刘知几以二典,贡、范诸篇之错书,转讥《尚书》义例之不纯,毋乃因后世之空言,而疑古人之实事乎”。⑦指出刘知几以后代史法来衡量《尚书》,是不对的。
其二,《尚书》蕴含了古代帝王的经世思想,而这种经世思想是通过灵活的著述形式体现出来的。“典、谟、训、浩、贡、范、官、刑之属,详略去取,惟意所命,不必著为一定之例焉,斯《尚书》之所以经世也”。⑧孔子删定《尚书》“取其疏通知远,足以垂教也”,来教育学生。
其三,《尚书》这种著述形式并未消亡,随着历史的发展,它的优点被后人吸收,融合到其它史书体裁中。司马迁作《史记》,“体圆用神,犹有《尚书》之遗”,⑨袁枢作《通鉴纪事本末》,“文省于纪传,事豁于编年,决断去取,体圆用神,斯真《尚书》之遗也”。⑩《尚书》“圆而神”的撰述形式,对后世影响是很大的。针对史书为体例所拘,“斤斤如守科举之程式”的弊端,章学诚提出“师《尚书》之意”,(11)效法《尚书》因事命篇,不为常例所拘的撰述形式,变革史体,使之更好地表现丰富多彩的历史内容。
可以看出,章学诚对《尚书》的看法与刘知几所取的角度是不同的,刘知几纯粹从“史法”的角度认识《尚书》,章学诚则从“史义”的角度认识《尚书》,他探讨《尚书》体例,主要从它是否正确表现了历史内容出发,并指出《尚书》具有经世的内容,这些,都使得人们对《尚书》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
二、《尚书》史学思想的精华:思考历史变动总结历史盛衰
从史学思想的角度看,在先秦文献中,《尚书》最突出的思想是思考历史变动,总结历史盛衰。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殷鉴”思想。殷周之际是一个剧烈变动的时代,发生过巨大的社会变革,王国维指出:“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12)正因为此,取代“大国殷”的“小邦周”,怀着强烈的忧患意识,思考夏殷由盛而衰直至灭亡的历史过程以及周的历史前途,明确提出“殷鉴”思想。这在《尚书》中《周书》各篇表现特别明显,“我不可不监于有夏,亦不可不监于有殷”,(13)“人,无亍水监,当于民监,今惟殷坠厥命,我其可不大监,抚于时”。(14)非常强大的夏殷为什么“坠厥命”,周怎样才能避免这一命运,成为《尚书》殷鉴思想的核心。
《尚书》在总结历史经验,考察历史盛衰时,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综览的眼光,从历史发展的长时段来观察历史盛衰,超越了就一事一物孤立地进行总结。二是能够从盛与衰、兴与亡两方面进行思考,全面分析历史盛衰的原因。
从《尚书》我们可以看出,殷商自成汤至帝乙,是兴盛的时期,从帝乙开始便走向衰落,直至灭亡。《尚书》用综览的眼光总结了导致这种盛衰局面的原因,一是由教化敬天到欺天,最终被天所弃。“自成汤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变惟天丕建,保义有殷。殷王亦罔敢失帝,罔不配天其泽。在今后嗣王,诞罔显于天,矧曰其有听念。于先王勤家诞淫厥佚,罔顾于天显民祗。惟时上帝不保,降若兹大丧。”(15)从成汤到帝乙,努力施行教化,谨慎祭祀上天,因此兴盛,而此后诸王,欺骗侮慢上天,奢侈腐化,因此受到上天遗弃,招致灭亡。二是由勤于政事,体恤民情到耽于朝政、忽视民间疾苦。殷中宗(大戊)“治民祗惧,不敢荒宁”,享国七十五年,高宗(武丁)“嘉靖殷邦,至于小大,无时或怨”,享国五十九年,祖甲“能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鳏寡”,享国三十三年,以后的殷王,“生则逸,不知稼穑之艰难,不闻小人之劳,惟耽乐之从”,而享国也只有十年、七、八年、五、六年、三、四年了。周文王创业之时,“康功田功,徽柔懿恭,怀保小民,惠鲜鳏寡。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万民”,(16)享国达五十年。勤于政事、怀保小民而盛,享乐腐化、不恤民情而衰,通过这种兴衰原因的比较,警醒统治者“鉴于兹”。三是由任用贤人治国到任用小人治国。夏朝先王任用贤人,国力大盛,夏桀登基后,“惟乃弗作往任,是惟暴德,罔后”。(17)殷代夏而立,“成汤既受命,时则有若伊尹,格于皇天。在太甲时,则有若保衡。在太戊时,则有若伊陟、臣扈,格于上帝。……在祖乙时,则有若巫贤。在武丁时,则有若甘盘。率惟兹有陈保×有殷,故殷礼陟配天,多历年所。”(18)殷之所以“多历年所”,正是由于任用了伊尹、保衡、伊陟、臣扈、巫贤、甘盘等有贤能的大臣。但商纣“愍惟羞刑暴德之人,同于厥邦;乃惟庶习逸德之人,同于厥政”。(19)不任贤人,残暴无情,招致亡国。《尚书》把用人当作关系历史盛衰的大事,这在神意史观笼罩的殷周,是非常了不起的见解。
其二,对天人关系的看法。在古代,不少思想家都用天人关系来解释历史的盛衰,并试图利用这一关系找出历史演进的原因。《尚书》对天人关系的看法,可以说是中国古代人问题的滥觞。殷商以前的人们在历史意识上一直是信奉上帝神的,认为王朝的更替、历史的盛衰,都是上帝的安排。但是,自命为遵天行事的夏、商、周的更迭,使得人们不得不深入思考天人关系,并开始认识到天命不是永远不变的,天命是会转移的。“惟命不于常”,(20)“天命不易”,(21)“天不可信”(22)等等。这样,从商到周,“敬天”思想就逐步发展到“敬德保民”,人们虽然还没有完全摆脱上帝神的束缚,但已注意到人的重要,指出国家存亡、历史盛衰,更重要的是人事的作用。“越我民罔尤违,惟人”,“天难谌,乃其坠命,弗克经历嗣前人恭明德”,(23)“天畏斐忱,民情大可见。小人难保,往乃尽心,无康好逸豫,乃其义民”。(24)表明了历史意识已开始摆脱神意的束缚,从人神混杂的状态逐步走出,“敬德保民”则说明了《尚书》对历史变动的思考开始从上天向人世间转移。《尚书》中“敬德”的内容是很广泛的,但中心内容是“用康保民”(25)“子子孙孙永保民”。(26)要体恤民情,爱护百姓,除掉奢侈行为,安抚边境之民,“协和万邦”。这样才能使国家长盛不衰。国家统治要以民心为据,“天斐忱辞,其考我民”,(27)看看民心就知道天命的动向了,把现实的人间的政治当作天命转移的根据。《尚书》认识到民心在历史盛衰,王朝更替中的作用,把天人关系的认识向前推进了一步,并一直影响着以后历史家、思想家对这一关系的认识。
其三,肯定社会变革的合理。《尚书》中记载了两种类型的变革,一种是尧舜时的“禅让”,一种是夏殷、殷周间的“革命”,这两种变革形式都是顺应天意与人意的,反映了先秦时期人们对历史变动的思考。汤革夏命,是因为“夏王率遏众力,率割夏邑,有众率怠弗协”,沉重的剥削与压迫激起了人民的极大愤怒,“时日曷丧,予及汝皆亡”,人民决心要与夏王同归于尽,“有夏多罪,天命殛之”,(28)商汤代夏,正是顺应了民心与天意。“乃惟成汤克以尔多方简,代夏作民主。慎厥丽,乃劝。”(29)受到四方诸侯拥戴,把人民从灾难中解救出来。武王克商,也是因为殷代后王残酷暴虐,淫乱腐化,任用小人,“俾暴虐于百姓”,(30)周取而代之,同样合乎天命与人意。《尚书》在解说社会变革时,还没有彻底摆脱天命观的束缚,但它认识到社会到民不聊生时,就要进行变革,这是顺应天意与人意的,无疑就肯定了变革的合理。这一点是应该引起我们充分注意的。
总之,从史学思想的角度看,《尚书》反映了当时人们历史总结意识的发展,它把夏殷周三代的兴替联系起来考察,不把它们看作是彼此不相联系的偶然现象,力图从中找出三代更替的某种因果联系,并试图通过历史盛衰的考察,来构想未来社会的发展方向。这种思想在先秦史学中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三、《尚书》对司马迁史学思想的影响
司马迁对《尚书》进行过深入研究,他曾随孔安国学习《尚书》,据《汉书·儒林传》载:“孔氏有古文《尚书》,孔安国以今文读之,因以起其家。……而司马迁亦从孔安国问故。”司马迁作《史记》,“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31)“考信必于六艺”(32),对《尚书》下过深厚的功夫。他还指出《尚书》,曾经过孔子整理:“孔子之时,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追迹三代之礼,序《书》传。…故《书》传、《礼记》自孔氏。”(33)不仅如此,司马迁还吸收与发展了前代思想家对《尚书》的认识。《庄子·天下篇》说:“《书》以道事。”《荀子·观学篇》说:“《书》者,政事之纪也。”都把《尚书》看成是对先王政事的记载。司马迁进一步指出:“《书》记先王之事,故长于政。”(34)这就包含了两层意思,其一,《尚书》记载的是先王事迹;其二,《尚书》与政治治理密切相关。因此,他既把《尚书》看作上古史料,又吸收了《尚书》史学思想的精华,融入自己的史著之中。
据分析,《史记》中的《五帝本纪》《夏本纪》《殷本纪》《周本纪》《三代世表》《鲁世家》《宋世家》《卫世家》《燕世家》等篇中,均大量引用了《尚书》中的材料。这里有一个司马迁引《尚书》是今文还是古文的问题,自汉至清,对此争论不已,见解不一。我们分析过《史记》所引《尚书》各篇,有今文也有古文,司马迁是兼采今古文的,这不难理解,司马迁不是经师,他要根据自己撰史的要求来采摘可信的史料,正如刘家和所指出的:“与当时株守一经及一家之说而拒斥他说的陋儒不同,司马迁对儒家诸经之间的态度是开放的。”(35)当着司马迁叙述史事时,《尚书》只不过是他所要利用的上古史料,他冲破经学师法,本着实录的原则来选择资料,是不足为怪的。
司马迁在利用《尚书》时,也吸收了《尚书》史学思想的精华,并加以发展,形成自己的风格。
其一,《尚书》在思考历史变动时,注意到人心向背,用贤与否对王朝盛衰的作用,司马迁吸收并发展了这一思想,《夏本纪》表扬“维禹之功,九州牧同,光唐虞际,德流苗裔”。《殷本纪》表扬伊尹助汤,殷以兴,傅说相武丁,“殷国太治”。《周本经》表扬周公辅成王,周朝得以巩固,共和二相行政,宣王从此中兴。相反,夏桀不务德义,诸侯多畔。殷纣“淫乱不止,微子数谏不听”,遂亡。司马迁在《楚元王世家》中引用《逸周书》中的话说:“安危在出今,存亡在所任”,指出任用贤人的重要。不仅如此,司马迁还发展了《尚书》中“保民”的思想,对人民群众的力量又有了更充分的认识。《夏本纪》记禹治水说:“禹乃遂与益、后稷奉帝命,命诸侯百姓兴人徒以傅土,行山表木,定高山大川”,指出禹治水成功,是依靠了百姓的力量。因此司马迁说:“三代之际,非一士之智也”。(36)认为夏商周三代的兴亡,不是那一个人所能决定的,而是老百姓的力量在起作用。
其二,司马迁继承与发展了《尚书》用综览的眼光看待历史盛衰的方法,提出“原始察终,见盛观衰”(37)的思想”《尚书》指出殷商自成汤至帝乙,国力强盛,帝乙之后,势力衰落。司马迁更进一步深入考察了殷商盛衰的过程,自成汤至太甲,殷兴盛;帝雍已时,由盛转衰;太戊时,“殷复兴,诸侯归之”;河颤甲时,“殷复衰”;祖乙时,“殷复兴”;阳甲时,“殷衰”;盘庚时,“殷道复兴”;小辛时,“殷复衰”;武丁时,“殷国大治”;帝甲时,“殷复衰”;帝乙时,“殷益衰”;商纣时,国家一片混乱,终于灭亡。司马迁对整个殷王朝盛衰的考察,与《尚书》试图用综览的眼光看问题是密切相连的。而且,司马迁把这一思想扩大到考察自黄帝至汉武帝时三千年历史的盛衰,并试图“稽其成败兴坏之理”,更是达到了一个新境界。刘咸忻曾说:“《记》曰:疏通知远,《书》教也。疏通知远即察势观风也。孟子之论世,太史公之‘通古今之变’,即此道也。”(38)洵非虚语。
其三,《记》中书体的体裁形式,借鉴了《尚书》。司马迁就:“礼乐损益,历律改易,兵权山川鬼神,天人之际,承敝通变,作八书。”(39)赵翼《廿二史札记》“各史例目异同”条说:“八书,史迁所创,以纪朝章国典。“礼、乐、律、历、兵权、山川、鬼神、天人之际等均为国家大政的重要内容,司马迁所以设书体是为了记载国家大政的发展史。《史记》八书采取了《尚书》的内容和对象,因为《尚书》的主要内容也正是国家大政,梁启超指出:“其八书详记政制,蜕形于《尚书》。”(40)范文澜也指出:“《史记》八书,实取则《尚书》,故名曰书。《尚书》尧典、禹贡,后世史官所记,略去小事,综括大典,追述而成。故如‘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以闰月定四时成岁’即《律书》《历书》《天官书》所由昉也。‘岁二月东巡狩……车股以庸’,《封禅书》所由昉也。‘帝曰:弃,黎民阻饥,汝后稷,播时百谷’,《平准书》所由昉也。《禹贡》一篇,《河渠书》所由昉也”,(41)肯定了书体的名称和内容、对象基本上是借鉴于《尚书》的。《史记》八书借鉴《尚书》,把它与先秦典籍中有关国家大政的论载及纪事本末体的方法和体裁相结合,并将书体融于《史记》整体中,赋以新的更有系统的对象和内容,也是基于司马迁对《尚书》的深入研究而完成的。
四、结语
从以上论述我们可以看出,在先秦史学中,《尚书》是不容忽视的一部著作,它不但记载了上古若干重大历史事件,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更重要的是它具有思考历史的变动、总结历史盛衰的史学思想。《尚书》对历史盛衰的考察已达到相当高的程度,反映出三代以至春秋时期人们历史总结意识的发展。《尚书》记言、记事的体裁形式引起后世史家的注意,被后世史家改造发展。认真总结《尚书》的史学思想,对我们正确认识先秦史学的历史地位,都是具有启发意义的。
注释:
①②③《史通·六家》
④《史学三书平议·史通平议卷一》
⑤《文史通义·易教上》
⑥⑨⑩(11)《文史通义·书教下》
⑦⑧《文史通义·书教上》
(12)《观堂集林·殷周制度论》
(13)《尚书·召浩》
(14)《尚书·酒浩》
(15)《尚书·多士》
(16)《尚书·无逸》
(17)(19)《尚书·立政》
(18)(22)(23)《尚书·君爽》
(20)(24)(25)《尚书·康诰》
(21)(27)《尚书·大诰》
(26)《尚书·梓材》
(28)《尚书·汤誓》
(29)《尚书·多方》
(30)《尚书·牧誓》
(31)(34)(37)(39)《史记·太史公自序》
(32)《史记·伯夷列传》
(33)《史记·孔子世家》
(35)《史记与汉代经学》《史学史研究》1991年第2期
(36)《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
(38)《治史绪论》中篇
(40)《饮冰室合集·专集》第十六册之七十三,第16页
(41)《文心雕龙注》卷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