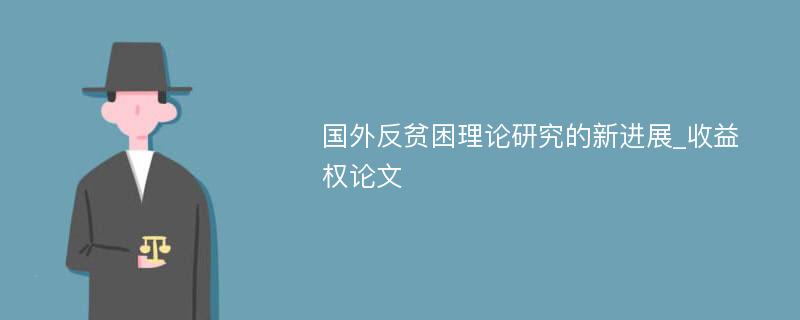
国外反贫困理论研究的新进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理论研究论文,新进展论文,贫困论文,国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07)05—0027—03
一、农民家庭收入增长与反贫困
增加农民家庭的货币收入可以有效减少他们的贫苦程度的观点,已经得到包括世界银行在内的学者和政策决策者的认同。这是因为世界上绝大多数穷人是农民,农业是他们主要的就业机会和生活来源,而土地是农业生产的根本,自然的想法是,在市场化发展滞后的条件下增加和改善农民的生存状态必然从“地根”上做文章。具体而言,包括土地产权的调整和土地生产力的增加。因为通过土地再分配政策的实施,可以使耕者有其田,耕者用其田,不但可以使贫困者获取最重要的生产资料,解决他们的就业问题,而且家庭组织的内部协调可以有效解决农业生产过程中的委托代理问题,进而增加农业生产的劳动投入,提升其家庭福利。另外,通过诸如绿色革命在内的土地生产力的增加,可以加速农业产出的增长速度,进一步提高他们的家庭收入。从理论上,发达国家先进的农业技术和充沛的资金通过全球化途径扩散到发展中国家,有可能提高农村生产力,进一步提高农村家庭的收入水平。但是,Blaikie等人(1980)根据他们在尼泊尔的实践研究, 认为发达国家驱动的市场趋同和一体化过程,一时难以瓦解市场发育不完善的以土地为基础的发展中国家的农村生产分配体系,逆转传统农业的产出和农民家庭的资源配置方向,起到提高农民收入的作用。
到了2002年,还是Blaikie等人,还是在尼泊尔的研究,使他们对自己20 年前对全球化进程中农民收入的判断产生怀疑。他们认为原来的模型低估了全球化进程中资本和劳动力市场对农民收入的影响,因为农民的非农收入以及全球化过程中的非农就业机会的增加对农民收入发生了显著性的影响。Afsar 进一步分析了在全球化过程中有五种力量使农民收入的重心从农业转向非农产业:(1)土地生产的收入减少,比如工农价格差和政府的产业政策的工业倾向;(2)非农产业的就业机会增加,特别是外资、外贸所带动的就业机会增加;(3)环境退化, 土地的过度使用和工业污染加重使农村环境难以保持高的生产能力;(4)土地短缺, 因为人口增长和城市扩容,土地使用非农化;(5)文化和社会变革, 城乡人口流动和消费倾向的媒体宣传,改变了农民对农业的投资偏好等。五种力量的作用使农民家庭在农业中得到的收入比例逐渐降低,而从非农部门得到的收入却逐渐加大,收入来源越来越多元化。在印度,从1971年到1999年,非农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从19%上升到48%。在坦桑尼亚等非洲六国,非农收入也已经达到60~80%。在菲律宾的East Laguna村,从1974年到2000年,农民的农业收入已经从90%下降到36%。在1998年泰国农民中至少三分之二的家庭中,有一个家庭成员全职或者兼职于非农部门。Krishna(2006)基于印度一个农村地区连续25年贫困变化数据研究发现, 农民家庭收入的多样化使得51%的原本贫困的家庭摆脱了贫困,其扶贫效果比增加工作可得性大7倍多,后者只有7%,具体的收入多元化的方法有:组建家庭微型企业;家庭成员在非农业部门就业;增加市场附加值高的产出品种,优化农业产出结构等。从这个角度出发,如何尽可能融入全球化进程,充分利用经济一体化过程所提供的新发展机会,改善农民的收入结构,才是提高农民收入的根本途径,才是适宜的扶贫政策。
二、农民家庭生产与反贫困
从目前全球横截面的数据看,家庭规模似乎与贫困程度成反比,即家庭规模越大,家庭贫困的概率就越大。但是很少有人考虑到,在不少发展中国家,贫困家庭生产更多的子女是避免他们极度贫困的一项基本生产活动。在大家庭中,家庭生产具有明显的规模经济,例如照明用具,无论家庭成员的多寡,都需要购买,而大家庭中通过共享能够使平均支出下降,具有明显的消费规模经济;家庭内部成员之间同舟共济和相互扶持以抵抗不利的人生变故,可以减少总的保险支出,具有保险规模经济;在生病时可以相互照顾,不必积累大量的资财已备医疗费用,而且可以相互发现病情并及时帮忙解决,增加了健康程度和延长了预期寿命,具有健康规模经济;共享知识和生活技巧,还具有知识生产的规模经济等等。面临日益恶化的环境条件,缺衣少药、营养不良的贫困家庭,子女的死亡风险大,家庭成员的疾病发生率高,劳动生产率低下。在这种情况下,没有一定的子女数量,难以得到家庭生产所需要的充足劳动供给,确实难以将家庭运作维持在规模经济范围内。
因为具有人力资本的子女从事家庭生产的生产率比不具有人力资本的子女为高,增加子女的人力资本积累可以显著的提高家庭生产的产出水平,因此,提高家庭福利的另一条途径是积聚更多的人力资本。从整个家庭生命周期看,追求跨时效用最大化的贫困家庭,就需要将家庭时间和资源在目前消费和未来消费(人力资本储备)之间进行重新配置。从子女的角度看,就是如何分配他们的上学时间与劳动时间,即家庭安排子女在学习的同时,还需要参加多少家务劳动、市场劳动和家庭集体劳动,以得到家庭效用最大化。子女上学的机会成本是其劳动收入,劳动收入提高,增加了子女上学的机会成本,减少了家庭配置给他们的学习时间,如果劳动收入再有所提高,势必会提高了子女的辍学率。由此得到的助学扶贫政策的思路是降低子女求学的机会成本(参加劳动的收益)或者提高其学习的实际收益,以提高子女的入学时间,提升贫困家庭的人力资本水平。在世界银行的倡导下,一些国家相继出台了一些资助子女入学的助学扶贫政策,即为上学的子女提供粮食补贴或货币补贴,结果提高了入学率,降低了辍学率。另外,助学扶贫政策还可以提高家庭生产的技术水平,因为受过基本教育的家庭成员,可以形成一个相对完善的学习和知识结构,熟悉一些全球化背景下的生存和生活方式,可以更好的适应全球化中资本市场和劳动力市场的需求,增强其家庭的非农收入能力。
与城市生活相比,影响农村家庭生产多少和生产什么的营养与健康因素是非常复杂的。一些小的偶然事件就可能诱发贫困家庭产生一场大的灾难,一些粗糙的扶贫行动有时候反而成为致贫因素。在饮用水问题上,表现得最为突出。随着全球化和工业化的推进,工业用水加剧、城市污染、水质变差、水源枯竭等使家庭安全饮用水日益短缺的同时,一些随水和空气传播的疾病也开始死灰复燃。为了避免巨额的医疗支出,农村贫困者为获取安全饮水,需要支付更高的成本。Hope(2006)研究发现,提高水的可得性是增加农村贫困家庭福利的最重要的因素,世界上,最穷、最渴、最弱势的群体往往缺水。在非洲南部,最穷的群体业就是获取水量最少的群体。在印度的一些地区,家庭主妇平均一天仍需要花费近一个小时的时间获取可饮用水,而每个家庭平均需要1.7个担水人。WHO(2003)则直接断言,大部分(穷人的)健康福利最终来源于水的服务和水的正常使用、良好的卫生习惯。不少国家为了提高农村地区水的可得数量和质量,增加农村地区的健康和营养水平,在加大对环境污染的控制力度的同时,曾经使用了三种方法。第一是掘井;第二是供水至农村社区,比如规定200米必须存在一个水龙头;第三是水的供应市场化。Bauer (1997)对智利进行了长达20年的水市场化试验,他认为,建立水的私有产权市场化交易,虽然可以克服政府失败和减少政府支出,提高水资源的配置效率,但是由于水的非排他性和高额的交易成本,易造成污染等外部性,市场价格并不能有效地传递反映供求的信息,要达到高效的水资源(公共资源)的市场化配置难且复杂,水的市场化并不能提高穷人获取饮用水的数量。而供水到社区和街道,也并不能有效提高穷人的可饮用水的数量和质量,因为生产饮用水的另一个投入——燃料(农村用柴)并不容易得到。
罕有经济学者对地位产品进行研究,因为某人消费地位产品后的效用水平需要依赖其他人的偏好和认同,该消费者在消费前后的偏好不能保持一致性,致使经济学方法难以直接使用①。但是,随着经济一体化的加快,在相对封闭和保守的农村地区,家庭生产他们的地位和尊严具有极其重要的经济价值。诚实、信用、乐善好施和尊严是他们能否取得社会资源的最重要的担保物和竞争优势,家族和地缘关系是他们非农就业的主要渠道。一般认为,家庭通过其定位标准和价值观的对比来确定自己的地位,进而决定如何生产和怎样生产地位产品,对于符合自己标准的就接受,否则就摒弃。贫困家庭为了能够得到周围的认同,往往需要花费很长时间来积累物质财富,以便在关键时刻,比如婚丧嫁娶,生产“最恰当”的地位产品。但是又因为地位产品是相对的,某个家庭能否获得设计的地位产品并不完全取决于他的支付水平,而部分取决于与他争夺地位产品的对手的支付,该家庭只有比对手多支付一个可辨识的增量,地位产品才能形成,才能够获得相应的认同,否则其支付就成为沉没成本而失去了。如果贫困家庭被迫生产与其收入不相互匹配的地位产品,则可能直接增加贫困程度。在Krishna的研究中,在原来25年前非贫困的家庭因为结婚而致贫占新增贫困的69%,而办丧事占28%②。
生产地位产品的另一个可怕后果是,如果农村存在相当比例家庭动员其时间和财富参与这种沉没成本竞赛,增加扶贫资源仅仅可能增加的是他们参加竞赛的动力,扶贫结果可能反而加速农村家庭财富的耗损和破坏,使贫困家庭更难跳出贫困陷阱。相应的扶贫政策如何固化地位产品生产于生产性活动之中,具体方法有:第一,地位产品固定在城乡迁徙上,使农村家庭在生产城市地位产品的同时,增加了其人力资本存量;第二,固定在创业竞争上,引导地位竞争于扶贫创业上;第三是增加农民家庭的互助合作组织和组建正式的劳动力就业市场,构建农民的社会资本网络,增加社会资源对贫困家庭的滴注管道,减少对地位产品的需求。
三、家庭内部的产权安排与反贫困
第一,家庭内部受教育权的重新配置:母亲是否应该被优先赋予?在美国《经济评论》2005年第10期上,刊登了对这个问题的一个争论。作为正方的Behrman和Rosenzweig依据母亲比父亲更偏爱子女的假设,认为如果优先赋予母亲的受教育权,就可以提高家庭产品——子女的质量。因为接受到较高教育的母亲更有能力帮助子女,这就为子女提供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势必产生巨大的非市场效益,他们的结论得到计量经济学的验证。事实上,这个观点一直是包括世界银行在内的国际机构的主流观点,为了实现联合国的千年发展目标,他们常常督促不少发展中国家推行类似的政策。作为反方的Antonovics和Coldberger使用正方的同一套数据,得出了与正方截然相反的结论。他们的研究结果是,提供父亲的教育水平对子女的教育具有明显的正效应,而母亲的效应几乎为零,甚至为负,母亲教育这种无效率在子女入学前阶段更为明显。原因是,提高了母亲的教育水平,显著提高了母亲的市场参与率,减少了母亲的家务时间和陪伴子女的时间,势必降低了家庭产出水平,影响后代的教育水平的提高。双方的争论其实在讨论母亲在家庭生产函数中的父母的边际技术替代率弹性的大小问题,由于家庭关系千差万别,仅仅基于性别分工进行教育权配置似乎过于简单,难以符合日益多元化的家庭实际。
第二,家庭控制权及其争夺。Chen和Wooley(1999)根据博弈理论研究认为,家庭控制权是由家庭成员的谈判地位决定的,谈判地位高的一方,拥有更多的控制权。其中,市场收入是谈判地位的一个重要因素,较高的市场收入提高了他/她的选择范围,减少了对其它家庭成员的依赖性。平均起来,男性的就业率高于女性,因此,相应的政策含义是增加女性的就业水平,以减少家庭内部的不平等程度。市场的供给态势是另一个重要因素。因为在婚姻市场、子女市场上供不应求的一方,将拥有更多的发言权,占据更多的控制权,瓜分更多的家庭利润。贫困家庭的实际状况是否如此呢?Paponek和Laurel(1988)调查了印度尼西亚的家庭控制权状况后发现,在该国母亲拥有70.5%家庭控制权。这与Pahl(1983)调查的发达国家的低收入群体的数据惊人的相似,后者正好为70%。但是Pahl还发现在中高收入群体中,这个比例下降到25%,即父亲拥有了75%的家庭控制权。因此推论,如果母亲更偏好化妆,父亲更偏好饮酒,那么,在低收入群体中,母亲执政必然导致化妆支出比例高于饮酒支出,反之,在中高收入人群体中,父亲施政又使饮酒支出比例超过化妆支出。这个结论对扶贫开放的政策含义是,由于女性掌握着实际的家庭控制权,符合女性特点的扶贫政策才可能有效③。
第三,家庭收益权的界定。在家庭组织中,具有经济理性的家庭成员在家庭未破裂时,自然会为家庭破产后的生活未雨绸缪,即调节当前家庭生产中的资源配置重点和方向,包括家务劳动的投入数量质量、子女的投资水平,以及家庭固定资产的变更等,甚至不惜将家庭资源转移更富的家庭,形成扶贫资金的逆向流动,因此扶贫必须首先界定家庭收益权。目前,法律判定的家庭收益权,基本上依据的是社会的一般生活水平,而没有同家庭成员的家庭贡献相对应。Hersch(1999)建议用机会成本来界定收益权。根据经济理性假设,理性的经济人在众多方案中选择最佳的一个而丢弃其它次优选项,以此推论,家务劳动的价格至少与次优选择(市场工作)的时间一样有价值,这样,选择其市场工资作为机会成本就可以来计算家务劳动的价值。比如界定子女看护的价格,由于子女看护是家庭生产的主要方面,而子女看护的内容既要包括子女远离危险的需要,被爱、呵护、喂养的需要,又要包括有利于子女正常发育的环境、教育等各种因素, 子女的监护权收益就相当可观。Bartfeld和Meyer利用美国1995年的数据研究表明, 平均起来子女抚养费是拥有子女监护权一方的家庭总收入的17%,赡养费是2%,合计19%。 但如果没有得到监护权收益(子女抚养费)的家庭,由于没钱支付市场便利和子女拖累,有31%的母亲无法参与市场工作,相比之下,得到子女监护权收益的家庭,母亲的市场参与率为82%。但从实际效果看,30%的监护人仍然处在贫困线以下,若使他们摆脱贫困,子女抚养费至少还需要提高56%④。美国的政策已从贫困家庭的支持计划转向就业补贴,迫使母亲参加工作,同时增加对子女看护的补贴。这显然没有找到问题的根本,因为不理顺家庭内部的收益权,家庭不仅享受不到规模经济的好处,还会被无边无际的交易成本所折磨,势必增加贫困家庭的痛苦程度。
利用家庭经济来展开反贫困问题研究,必然涉及到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人类学、女性学,甚至自然科学,需要各个学科的相互借鉴和相互融合。但是,家庭组织本质上是一个经济组织,随着经济发展阶段和经济条件的变化而各具特色,而且,使用经济学的基本工具,确实可以增加家庭外部资源的扶贫效果,因此研究影响家庭脱贫的制约因素和行为变量,构建涵盖家庭收入、生产方式以及家庭内部产权安排的家庭扶贫路径,进而形成一个政府、企业和家庭组成的三维分析框架,可以有效拓展反贫困的作用空间。
注释:
① Becker等是少数几个例外之一。他们假定了地位产品与市场品是消费的互补品,得到的结论是地位产品的消费均衡低于效用计划者分配均衡数。参加Becker,G.S.Murphy,K.M.and Werning,I.,2005,pp.282—310.
② 当然,作者还分析了农村金融对婚丧嫁娶致贫的影响,其中主要影响因素还有高利贷。参加Anirudh Krishna,2006,pp.271—288.
③ 比如,结婚女性大都是风险规避型,这就要求扶贫开放的投资项目应该具有低风险和短期回报率高等特点。
④ 转引自苏姗娜·格罗斯巴德·舍特曼主编《婚姻与经济》,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14—25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