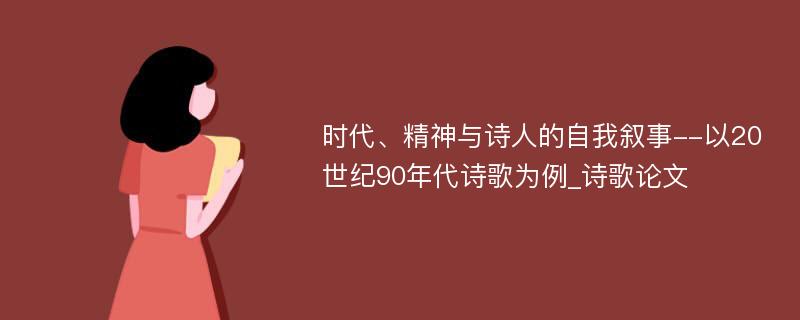
时代、精神与诗人的自我叙述——90年代诗歌个案研究之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个案论文,诗人论文,诗歌论文,年代论文,自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04(2001)04-0084-05
诗与时代的关系是近年来有关90年代诗歌争论中的一个重要话题。其中核心的问题并不是诗要不要与时代发生关系,而是诗怎样与时代发生关系。一些批评90年代诗歌脱离时代的论者显然仍保持着对“朦胧诗”的忠诚,这当然有其自身的合理性。如果说“朦胧诗”业已构成了当代诗歌的一种传统,这种传统显然没有被后来的写作者予以足够的重视。但优势本身也是一种局限,“朦胧诗”为未来的诗歌写作呈现了某种重要的可能性,但并没有、也不可能呈现所有的可能性。即便是这种重要的可能性,其所具有的动力和动态特征,也不是由“朦胧诗”派的主要诗人来完成的。我指的是在时间的流逝中始终与时代发生有效关系的那种精神原质。
“朦胧诗”的重要作品之与时代的独特关系是通过引入某些意义模式而建立的。由于这些作品大多写于20世纪70年代早期和中期,诗人与时代发生着直接的对抗。诗人通过引入光明与黑暗、历史的罪恶与一代人的雕像这样的二元对立模式,从而为自己争得了独立的精神空间,为自己的痛苦、抗争和梦想注入了新的意义。正如那首著名的《结局或开始》开篇所写的那样:“我,站在这里/代替另一个被杀害的人/为了每当太阳升起/让沉重的影子像道路/穿过整个国土”。仿佛整个民族的苦难都集中在诗人的肩头,他痛苦地醒着,孤独地站着,艰难地背负着。所以,当一个新时代醒来时,人们从这些诗中突然发现了从未发现的苦难,也经历了以往未来得及经历的痛苦。但“朦胧诗”也在接受时代的考验,这正好发生在“从残留的夜色中/人们领走了各自的影子”(北岛)之际。显然,诗人在追寻光明的同时,也存在着被光明无限圣化的倾向;在那为对抗历史的罪恶而塑造的一代人的雕像中,也同时演化着自我的膨胀。黑暗并不只存在于历史的空间,它也同时存在于人们包括诗人的内心深处。正如诗人王家新说的那样:“只有今天派诗人(包括受他们影响的)不再只从社会而从他们自己内心的黑暗中寻找创作的动力时,他们才有了新的发展。”
但在大陆写作语境中完成这一转变过程的却不是“朦胧诗”的主要诗人们,而是另一些诗人,其中就包括王家新。尽管王本人曾否认他今天的写作与当年的“朦胧诗”之间的关系,但我仍然认为他与“朦胧诗”之间有一种扯不断的精神渊源关系。“朦胧诗”中的那种可贵的精神原质仍然保留在他90年代的诗歌中,但已有了富有逻辑性的变异和发展。诗集《游动悬崖》[1]中收入的《再也不会有人来了》,在我看来正是对北岛《回答》的最初的回应。
群体的苦难赋予个体以使命感,使个人得以成为大写的“人”。但苦难过后呢?当苦难不再成为个人需要承担、同时也向其索取意义的对象,当大写的“人”还原为小写的“人”,还原为日常的、再也无法使自己崇高的个体,他将面临着什么呢?
再也不会有人来了/打开窗户,风声向弦音一样飞过/风声绷紧了黄昏的天空/我收拾好自己,将残茶泼掉/然后坐下来/我已经没有什么可做/天空中已响起死亡的脚步
时代的变迁使承担者从伟大的孤独变为渺小的孤独,由沉重而显现的苦难所赋予的生命的外部光环和内在擢升感一点点消失。“几万只死亡的脚步踩在一个人头上”,而不是几万双眼睛盯着他看。不管诗人本人是否有过北岛们的经历,但他可以想象和“借代”,这其实是那一代读诗的人在遭遇“朦胧诗”时都可能有过的经历。诗人只能以“多么辉煌”四个字反讽自己的即时状态,但此刻的反讽依然不是入骨入髓的。“生,或者死”的抉择摆在他面前,而抉择根本不是能由个人所安排的,仿佛命运使然。这是一个挣扎着的过程:“城市远离我们/岸远离我们,鸟群在风中/寻找它最后的家/而我守在这里/哪里也不去/我在下沉……”诗人仍然定位于“上”与“下”的空间:“如果没有天使下凡/我就等着一个人的到来。”这不禁使人想到北岛的句子“在一个没有英雄的时代里/我只愿作一个人”,但方向却是相反的:一个明显的“向上”的冲动和一个明显的“向下”的不甘。诗中“风”的摇撼感始终对应着这种“不甘”,即使在下沉,即使遭遇着外部光环的剥落和内在擢升感的抑制,诗人仍然不肯把自己处理得渺小和琐细,他依然写着这样的句子:“我的苦痛像弯弓一样饱满/这是积蓄已久的冲动/创伤一触即发”,这使人联想到“最后的审判”。不过,这也的确是一个关于审判的故事,只是审判不再指向世界,而是指向自身。于是,我们业已象征性地看到,那个通过“宣读那被判决了的声音”而宣判世界的人,如今已转向对自我的宣判——“风中已响彻死亡的脚步/一个骄傲的头颅/垂下”。一代人的雕像就这样在风声中“下沉”。
新的故事已经发生,新的写作也已开始。也许,自我圣化、自我放大正源于人的深刻的本性,所以诗人才将自己的笔触指向人内心的暴力和黑暗。即便是在与另一个世界的对话中,他仍然不忘追问:“那一声凄厉的哀鸣/是来自屋外的雪野,还是/来自我们的内心……”《瓦雷金诺叙事曲》是诗人“再生”的第一个标志。时代已使他由与一个孤独的群体的苦难的关系,伸展为与普遍的人类的苦难之关系。他开始从最根本处思考这一关系:
静静的夜
谁在此刻醒着
谁都会惊讶于这苦难世界的美丽
和它片刻的安宁……
一个显形的有限者,还有一个匿名的无限者,对应着,浮现出来。苦难已经成为中介,而不再是单一的抗拒的对象。于是,他认可并欣悦于这样一个事实:“命运夺去一切,却把一张/松木桌子留了下来,/这就够了。”“何况还有一份沉重的生活/熟睡的妻子/这个宁静冬夜的忧伤……”被剥夺者不是抗拒,并发出对抗的嘶喊,而是接受,默默地“把苦难转变为音乐”。这是一个关键性的“转变”,是一个人面对(或丧失)无限者时向有限者的还原。诗人一定是在某个时刻经历着两个时代的循环,一个是帕斯捷尔纳克式的,冬夜,蜡烛,户外的暴风雪和切身的苦难;一个是日常的,琐细的,恼人的,此刻并未出场、但却无处不在的,也是路德对他的门徒说过的:“留在人群中和你的行业里——在那里魔鬼和世界将赋予你足够的苦难。”诗人也折磨于他都认可的两种境况,一种是美的,从存在中提纯的,拒绝外部世界、拒绝时代和社会介入的:“怎忍心在这首诗中/混入狼群的鼻息?”怎能让死亡/冒犯这晶莹发蓝的一切?”;一种则是还原了的,包含着存在的全部复杂性:“纯洁的诗人!你在诗中省略的/会在生存中/更为狰狞地显露。”诗人开始偏离日瓦格医生的背景,他所提出的问题,也许适用于在某一时刻同时交叉于我们的两个时代,这就是:“我们怎样写作?/当语言无法分担事物的沉重,/当我们永远也说不清/那一声凄厉的哀鸣/是来自屋外的雪野,还是/来自我们的内心……”
这是一个逐渐深入的过程。无论是作为中国诗人,还是作为中国人,其成长的过程也是伴随着理解和觉醒的过程。尽管“认识你自己”刻在古雅典的廊柱上,并作为西方哲学的古老命题,但对于上个世纪和这个世纪的我们,似乎有着双重的意义。“理解来得迟了”,《埃兹拉·庞德》开首的这突兀的一句,几乎道出了中国几代知识者的精神命运。“所有的道路都通向他/我们却没有上路/我们比一个犯有过失的人更不可饶恕/现在,是他向我们走来/埃兹拉·庞德向我们走来……”但走来的并不是这个人的声名和艺术,而是一个来自深渊的启示:“从错到错,从一个虚幻的顶峰/跌回到更大的盲目”。这是对历史中的群体和个体的双重总结,尽管二者可能并不在同一个层面上。此刻,我觉得王家新仍在暗中回应着“朦胧诗”的一以贯之的“光明与黑暗”的主题,只是在相反的方向上回应着。诗人的反思已经深骨入髓了:“光明弄瞎了双眼/血,混入毒瘴;对至善的追求/并不能使人幸免于恶/被许诺给伟大,却一再演错了角色/只有痛苦,只有傲慢(这上帝也无法抑止的)/痛彻着我们的一生。”从《再也不会有人来了》到《埃兹拉·庞德》,诗人为什么一再追究着人的“傲慢”的本性?他显然已经了悟了个人的苦痛、民族的不幸和人类的灾难与之的内在关联。他看到人的普遍的命运:“人类需要自欺”,也明白了作为诗人的任务:“让我看到真实”。这种对“真实”的追索已非源于智慧的冲动和这种冲动背后的人的无限性感觉,而是源于某种煎熬中的宗教情绪和人的有限性意识。诗人追索的是:什么能“帮助我们,在时间的打击下/最终站稳脚跟”?于是,精神拯救的话题,死亡与再生的话题,便频繁地出现在他的诗中:
想到那里一张被死亡所照亮的脸——一种从疼痛中到来的光芒,就开始为我诞生……
在忧伤与无助中我感到如此无望,于是另一面山坡从我对面大幅度升起:我达到了赞美。
(《词语》)
有一种现象已被注意到:王家新90年代初期的几首重要篇章,似乎都是在与异国诗人的遭遇中并在其震撼下写出的。诗人本人似乎也受到来自这方面的困扰,所以他在某篇诗学文章中写道:“文学的存在会一再地要求再生、对应与改写,以成就它自身。”“一部文学史,无非就是文学自身的这种不断重写、变通与自我调节。而一个诗人如果脱离了文学的这种‘重写’或者说‘被写’,他就不对文学构成意义。因此,我从不认为我的写作就是一种‘创新’,我只能视它为一种对文学的敬礼,一种‘还愿’——为了它的养育之恩。“[2]我在此不想对诗人的理论主张做出评价,只想追问被诗人“改写”、“重写”、“对应”和“再生”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文学。就此,我想扯开谈一谈。
当北岛写下“我,站在这里/代替另一个被杀害的人”时,他实际上也在讲述着一个有关“代替”的故事。而“代替”的故事早在两千年前就已发生过:耶酥被钉死,代替他传播福音的先是保罗,继而是教会。由教会(主要是中世纪)传播福音是对那个为福音而死的人的嘲讽,但根子已扎在耶酥的时代,因为耶稣的主要门徒不是犹太复国主义者(通过融入并复兴整体而放大自己),就是争坐耶酥左右的彼得们(通过等级制而提升自己)。福音被充耳不闻,道成肉身被撇在一边。代替的初衷被代替者无法克服的人性弱点所窒息。福音,这个传到人间的好消息,其哲学和文化精髓就在于,人的敞开了的内在精神是人存在的惟一根据:“天国就在你心中。”它取消了任何由外部事物或“自我”充当人之存在根据的资格。它针对的正是人的无所不在的死亡恐惧,和为对付这种恐惧而匆忙向外伸出的求援的手。它当然不会无视虚无和荒谬,而是将其吸收进自身。这是从苦难中吸取的光明和被蒙上的喜悦。当剥去由教会和基督教神学所赋予的僵硬的外壳后,我们就会看到西方文学中的一种至关重要的内在精神。如果说新诗所隶属的中国新文学是在外来文化主要是西方文学的摧生下诞生的,那么这种脱胎换骨式的吸收,在整体上从一开始就过滤掉了西方文学中的这种深邃的内在精神。接受即选择,中国新文学何以在整体上过滤掉这种文学精神,是一个非常值得探讨的问题。其结果我们已经看得很清楚了:当作家们内在的生存意义发生危机时,便在种种历史的具体性中,纷纷向外部世界寻找自己的生存根据。作家们的两极化——“左翼”化和布尔乔亚化,正是未经真正分析和吐纳者对自身的生存焦虑和存在的虚无之匆忙的、传统式的反应。我并不是主张作家应外在于时代和自身的实践,恰恰相反,我是在强调作家以什么样的“自我”介入时代和自身的实践。中国艺术家内在生存的虚弱正好被外部强大的实践性掩盖了。所以,新文学中种种已有的可贵精神后来为一种毁灭性的力量所毁灭,几乎是自然而然的事。当我们今天回过头来感叹中国作家与前苏联、东欧作家之不同时,我们常常忽略掉一个重要因素,即当初在对西方文学接受时一种被过滤掉的文学精神。
作为新时期诗歌开端的“朦胧诗”的弱点,正如大家后来所看到的:从承受民族苦难的英雄,到按奈不住生存焦虑而充任个人英雄。他们中也有人对此有所意识并努力改变,如北岛就曾从庄严走向反讽,但这种转变更像是形式的、来自理性而非心灵的转变。“代替”角色的流产也就在所难免。于是,当我们谈论王家新之与大师的“遭遇”,还有王家新本人谈他的文学“再生”和“重写”的诗学主张时,我们都不能不注意到,他所遭遇的正是西方文学的那种曾被我们过滤掉的内在精神。
这就是你,从一次次劫难里你找到我
检验我,使我的生命骤然疼痛
从雪到雪,我在北京的轰响泥泞的
公共汽车上读你的诗,我在心中
呼唤那些高贵的名字
那些放逐、牺牲、见证,那些
在弥散曲的震颤中相逢的灵魂
那些死亡中的闪耀,和我的
自己的土地……
(《帕斯捷尔纳克》)
他的“把苦难转变为音乐”(超越)和“诗中省略的/会在存在中/更为狰狞地显露”(拒不超越),他对人的傲慢和内心黑暗的持续追究,他的不假外力又清洗自恋的敞开的自我,无不显示着那种精神在新的时代和别一区域的“再生”和“复活”。也许不是他一个人这样做,也许他这样做时也同时困惑于自己的民族身份和时代的精神风尚,但就文学的接受和移植而言,却是极富有价值的。因为这种“重写”和“再生”之“写”与“生”,必须是经过血肉化的,是从自己的存在中升起,并对自己的存在说话的。而在我们这个时代,某种超验价值的保留,哪怕是其“空位”的保留都是困难的,但对于困顿中的人们,对于拒绝做当代英雄而迎面承受虚无感、无价值感和时代焦虑感的人们,也是需要的,只要不把它理念化,只要让它向存在始终开放着。正如诗人所言:“在这个时代,如果我不能至死和某种东西守在一起,我就会漂浮起来。漂在大街上,或一首诗与另一首之间。”(《反向》)
于是,在时代与个人之间,已有某种精神出现,但这已不再是对“类”的强加和规范,而是于个人的保留,并明显地具有一种单数的性质。这使诗人在这个奔驰而又停滞、充满着各种喧嚷和复杂性的时代中,得以保持一种相对稳定(而不是绝对稳定)的自我感。这应该是一种健康的标志,当我们都身处时代神经症的包围之中时。这也使前述“朦胧诗”中的那种精神原质通过注入新的精神质素,得以延续、变异和发展,并与时代发生着最为密切的关系。发表于1998年的长诗《回答》[3]可被看作王家新对自己过去写作的一个总结。诗人近十年来重要作品中的主题,几乎都在这首诗里奏响。其中给我以突出印象的是诗人对变化着的时代的那种痛切感。如果说“朦胧诗”的一些主要作品曾对历史的罪恶做出了一种对抗式的反应,那么王的《回答》则是对时代神经症所做出的另一种对峙而又包容式的反应。黑沉沉的夜已经退居幕后,“我们就这样/失去了阳光和土地/也失去了我们自己”(北岛)的强力式的剥夺,转换成了弥散性的剥夺:“我也几乎不再关心/自己是谁,而只是想说:这就是我们的时代/——你的痛苦,你的生活,你的真实/只是这部伟大传奇中的一个细节。”时代的变迁使人们更换了一套语码重新叙述生活,这是以“真实”而非“太阳”的名义所实施的另一种宏大叙事,并被“假定人人都懂得它的意义”(荣格语)。你依然被其编织着,不是通过“血淋淋的太阳”(北岛)和“那枚灰色的变质的月亮”(多多),而是通过另一种并不触目的“修辞”,通过“时代的滔滔宏论”,通过各种当代英雄和被抽象了的大众快乐的示范。发出质疑甚至抗议的诗人也不再像当年的“代替者”那样,孤独而受难般地站立着,他已有了某种内在的破碎和抽空感,使对抗性的自我叙事成为不可能:“长久以来我想写一本书,但我所构想的/一切正受到生活的嘲弄;/长久以来我与一些从不存在的女人为伴,/现在我明白了:这些假天使肢解了我的生活,/毒害了我的灵魂/却不能成为这部书的主人公。”于是,一个在他诗中隐约起伏了近十年的主题在这里再次奏响:“我看到控诉暴力的人,其实在/渴望着暴力;那些从不正视自己的人/也一个个在革命的广场找到了借口;/……从当年的红小兵到女权主义者,/从‘解放全人类’到‘中国可以说不’,/人们一个个被送往理论的前线,并在那里牺牲”。他再次看到了人性中的黑暗,不是从罪恶的制造者那里,而是从当年的受害者、从自己周围或最亲近的人、甚至从自己身上:“我们从不认识的苦难,/使我们走到了一起:它在一开始使我们/不与生活妥协,现在则互不妥协;/它使我们彼此相像,虽然又如此不同。/它带来的夜,我们至今仍未走出。/它书写着我们,爱我们,威协着我们——/它是暴戾的,我们却像狗一样对它忠实。”
当然,诗人是打算写“一部书”的,用以完成自我的叙述,而我们恐怕都得写一本自己的“书”,如果我们还不想被那种宏大叙事完全编织,不想被时代神经症全然吞没的话。于是,下述追问便不是多余的了:“谁能拿出真实的勇气/讲出一个真实的故事?谁能正视自己/而不是把他留给另一个鲁迅或陀斯妥耶夫斯基/去审判?”一组对立的形象由此而浮现:时代英雄和当代白痴。后者踉跄于混合着狂笑的风雪中,“在一个疯狂的世界要求着理解”。一个真实的故事也许就是高叫着或默默地走向毁灭的故事,一个拒绝时代神经症、拒绝虚幻的自我的故事,当然也就是一个关于白痴的故事。诗人在其他地方曾经涉及到的一个主题——对失败的认可,在这里又一次得到体现。这不禁使人联想到福音书中的耶酥的形象,一个拒绝尘世的权力(“瞧,那个以色列王!”)、拒绝宗教的权力(“魔鬼叫他……站在殿顶上”)、拒绝把无用换作有用(“你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的形象[4]。这种全然放弃突兀的并不是英雄,而是一个失败者,一个连弟子都要背叛和忘却的被遗弃者。如果说在文学中一直悄然流淌着这种认可失败的主题的话,那么福音节应该是它的源头。如今诗人在汉语语境中重写着这一主题,并看到了它与“真实”、与自我的虚幻之剥落的关系:“让我感激我的失败;因为在我的失败中,/我开始认识苦难;在我的无可挽回的失败中,/我在朝向一种更高的不可动摇的肯定……”这种在认可失败中获得的肯定,大概就是另一种非神学意义上的“复活”。它排斥了人惯有的绝然的态度,在推掌拒绝时也伸手接受,对峙着也包容着。“是到了再见的时候了——/平静下来,你仍是我亲爱的人,/平静下来,愤怒会化为怜悯,而挽歌/也应当作赞美出现”。这是超越了“关系”后的和解,仿佛不仅是对诗人生活中的具体人,也是对世界本身,虽然和解只是单方面的。的确,世上没有被仇恨的对象,当你有足够的自由和强大的心灵力量时,当世界转换为“我与你”时,当一种更高的存在出现时……
王家新的《回答》在抗拒时代神经症和宏大叙事时,多少也完成了对自我的叙述,虽然这种自我叙述仍是急促的。这表现在诗中过分的散文化和说理化,也表现为诗人内心的冲突在某些字句间的隐秘体现,如那种折磨于出众者和普通人、对失败的认可和对光荣的渴望之间的心绪,那种在普遍的人性和民族的宿命之间的滑动和游移,但诗人许诺“我会让一本书来总结我们、回忆我们”。那是一本我们都应该写的“书”,诗人当然会给它以诗的形式。
从王家新十年来的写作已经看出,时代对于他从来没有丧失过强烈的吸引力,但他自己仿佛越来越被时代“驱除”,以至于他不得不表白自己实际上只是在为他这一代人中的几个人写作,是属于“个别的、私人性质的”。这暗合了今天派诗歌当初的命运,但后者是一种历史的限定。对于王家新而言,他既折磨于“理解来得太晚了”,也折磨于“饥饿仍是我的命运”。他是把写作当作逼退虚无的方式,以期完成精神的拯救、也即达到另一种“赞美”的。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充溢着对苦难中的欢呼的回应,但也同时是一个自我戕害的过程。
我的写作摧毁了我
我知道它的用心,而生活正摹仿它
更多的人在读到它时会变成甲虫
在亲人的注视下痛苦移动——
我写出了流放地,有人就永无归宿
(《卡夫卡》)
也许,更复杂的命运正等待着人们。问题依然是:认同荒谬,还是在荒谬中与之拉开一点距离?是我们摹仿生活,还是让“生活摹仿它”?
收稿日期:2001-01-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