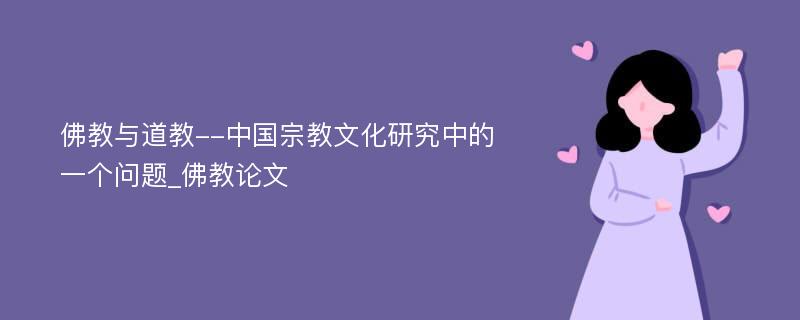
哪一个佛教哪一个道教——谈中国宗教与文化研究中的一个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道教论文,佛教论文,一个问题论文,中国论文,宗教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文化差异还是宗教差异
近来在讨论东西方文化比较时,有人开始注意到更精细的分别,所以一句颇为尖刻的追问就流行开来:“你说西方?是哪一个西方?英国?法国?还是美国?”“你说东方?是哪一个东方?印度?日本?还是中国?”这倒让我们学到了一招,也就是说要追问一下问者的思路,所以,近来有人向我询问中国的佛教、道教时,我也先来确定一下他所说的是“哪一个佛教?哪一个道教?”这使得有人不太理解,其实这一追问的起因很简单,只不过是几年来我对一种批评的思考,这一说法的意思也很简单,只不过是对一个有关中国宗教与文化的特点的表达。
一九八六年我写《道教与中国文化》一书时,曾比较突出地区分了中国思想史上特别是唐宋以后,中国士大夫与中国民众在宗教思想上的差异和生活情趣上的差异〔1〕,我觉得, 中国士大夫阶层与民众阶层之间的文化差异比起不同宗教信仰者之间的教派差异更深刻。比如说,信仰佛教的士大夫与信仰道教的、信仰儒家的士大夫在思想上、情趣上的相同点可能很多,而信仰佛教的士大夫与同样信仰佛教的普通民众在思想上、情趣上的相同点反而很少。这一观点引起了一些批评包括海外的批评〔2〕,这些批评集中起来就是一个问题, 即同一个中国宗教的各个信仰者所信仰的难道是不同的宗教内容吗?换句话说,在中国古代,是否文化差异竟然比宗教差异更深刻更重要,以至于同一宗教的内容会被信仰者的文化差异在理解时分裂为二,而不同宗教的思想却会在同一文化层次的人中间被理解为同一的东西?
说实在的,只要不是只执著于《弘明集》、《广弘明集》或《集古今佛道论衡》之类宗教著述的记载和渲染,而较多地留心中国一般文献记载中的宗教信仰者和社会实际生活中的宗教信仰者,就可能同意我的看法。因为这种看法并不是我一个人独有的,许多研究中国的学者对中国宗教都有类似的感觉。 美国学者本杰明·史华慈(Benjamin I Schwartz)在《古代中国思想世界》一书的后记里谈到,很多人把中国文化看成是一个,即包括上层与下层文化的统一体,他举出弗里德曼《论中国宗教的社会学研究》为例,弗氏认为中国的精英宗教和农民宗教都建立在共同基础上,它们是一种宗教的两种版本,这两种宗教“只是习惯用语式的互译”,但是史华慈认为这种说法过于强调了二者之同而忽略了彼此之异,因为这两种文化在中国思想的历史上“产生了决定性的分离”,所以,二者之间“并非同一种文化的两个版本间不成问题的平行并列,而是一种既包括相互影响又包括至少部分分离的两个领域之间相互紧张的经常性动态互动关系”。这是很正确的。因为名称相同的“精英宗教”与“农民宗教”的“异”似乎比“同”还多,比如说佛教中那种以机锋、警句、偈语为启悟契机的禅宗,就绝不为民众所理解而只是受到文人的喜爱,而普通民众信仰的禅宗,不过就是文人所批评的一个戒律相对松懈、行为相对自由的佛教门派,至于更多的民众信仰的,是道理简单的净土宗,念南无阿弥陀佛只是为了“菩萨保佑”,而净土宗里的深奥理论,他们并不去理会,而文人士大夫却对其中的哲理颇有兴趣,对“有求必应”的念诵效应则普遍怀疑。不止是佛教,看似深入中国人心的儒学也如此,一个研究儒家思想的美国学者萧洛克(John ·K·Shryock )特别反对那种对学术思想与大众思想不加区分而笼统地讨论文化的方式,在他看来,孔子的影响一直局限在学者即儒士圈子之中,对大众的影响并不大,“尽管孔子在中国拥有巨大的影响,但他是否曾经获得广大民众真正的崇拜,这仍然是值得怀疑的”〔3〕, 这种看法虽然有些偏执但也不无道理,其实,学者们通常用来作为研究儒家思想的最重要资料的五经及其数量巨大的注疏,在平民中间并不一定有多少影响。傅斯年在《论学校读经》中就说过,“六经之内,都是十分之九以上但为装点之用,文章之资的”,它们的民间影响,未必就比《水浒》、《三国》来得大,就是作为上层思想意识的孔子思想,即使渗透到了民众那里,它也必须经过祭祀仪式、通俗讲唱、家规族规等等形式的演绎、解释,完成了它的世俗化,所以尽管同样信奉儒家思想,那种理解其中不言自明的价值与意义,于是将它作为自觉意识的上层文化人,与在传统的影响和社会的规范下习惯性地遵从道德律令和伦理规定的普通民众,当然是不相同的,五经四书里的道理和乡规家训里的条款虽然相通但不一样。
信仰分层的现象
可能最为明显的例子是关于道教的,到中国农村中去过的人,都可以明白民众信奉的道教其实和文人所向往的道教全然不同,和从《道藏》里归纳与描述出来的道教也不一样。如果有人拿着一本道教史去按图索骥,恐怕看到的都与书中所说的不同。近来读到李养正先生所写的《当代中国道教》,尽管十分有用,但总觉得这是在道协、道观、道教书本和官方文件里所看到的道教,并不全是根植于中国社会生活中的道教,而日本蜂屋邦夫教授新出的《中国の道教》虽然调查翔实而广泛,但是依然是道观与道士的道教。只有当人们在农村的庙会、祭祖、节日和各种临时性仪式上真正看到那种深入民众的、与日常生活相关的宗教活动时,人们才能理解道教的意义和影响。
由于被古代中国含糊地称为“道教”和西方汉学笼统地称为“Taoism”的道教,本身就有道家与道教的差异以及士大夫信仰者与非士大夫信仰者的差异,冯友兰、顾立雅(H G Creel )都主张把后世“道”的信仰者分开,把道教中比较重视思想信仰的部分与比较重视仪式操作的部分分开,顾立雅说道家可以分为“哲学性的道家”和“神仙性的道家”(Hsien Taoism),前者讨论的是思想学说,后者追求的是长生不老,后者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中国上古的方术、仪式与不死信仰〔4 〕。他还认为,在西汉中叶,方述崇拜与道家思想还是泾渭分明的,直到方术家接受了“道”的名称和黄老道家的术语名词,才与道家混融,但二者的关联依然很少。这个说法可能太粗率,但大体并不错。也许只有荷兰学者徐理和(E·Zurcher)反对把道教分为“哲学性道教”和“民众性道教”,他说这将会导致误解,但他所担心的误解其实是指把“玄学”算成道教,在中国,一般的研究者中并没有人把“玄学”说成是道教,他的担心至少在中国并没有意义,因而也还是没有说明为什么不能把道教分为两类〔5〕。其实直到后来,道教信仰者也还是两种, 热衷于谈玄论道的一类和热衷于设斋打醮的一类,道教对世俗社会的策略也还是两种,即所谓“遇上等人谈性理,逢下等人谈因果”,性理是哲理的,因果是具体的,上等和下等人之间毕竟不同。“晓钟历历,晚磬冷冷,细参个里机关,凡处境无非梦境。岚气重重,云峰乙乙,饱看天然图画,不学仙也是真仙”,四川青城山建福宫的这幅对联是给文人看的,精神的超越和自然的享受,体验在山水之间,不是那些整日为生计奔波的民众的生活,我们问几个来进香的老乡,都说不懂,倒是“有求必应”、“心诚则灵”、“祸福无门,惟人自招”却是大多数人都挂在口边,毕竟这是实际生活中最要紧的信条和宗教信仰中最落实的地方,也是宗教最能抓住人心的地方。
“信仰分层”——我们姑妄这样称呼这一现象——的确是中国宗教世界的事实,其实,这就是所谓的“大传统”和“小传统”的分别,在中国士大夫尤其是唐宋以后的文化人那里,儒家的至善、佛教的超越、道教的永恒,作为一种人生境界和生活情趣、人格修养常常很接近,而在民众那里,儒家的敬祖重祭、佛教的水陆道场、道教的斋醮法事,作为一些出于实用目的的生存的技术,则往往可以互补。我们在历史资料里总是看到,文化人的人生情趣里,三教是一致的,我们在社会调查中总是发现,民众的宗教活动中,三教是混融的。也许正是因为如此,更早一点的陈荣捷氏在《近代中国宗教的走向》中就指出,“将中国人们信仰的宗教区分为儒道佛三教,不如改为大众阶层和知识分子阶层两个层面的划分,W·E·Hocking教授曾把东方宗教性信徒分为僧侣、 在家的神秘论者、学者和一般平民四类,但在中国,第二类基本不存在,其余三者则可分为大众阶层与知识阶层,这里所说的大众,即占中国百分之八十五的有迷信而无教养的人,而知识阶层则包括文化人及有一定学识的农民渔民或不多用语言却常常发挥伟大智慧的同样卑贱地位的人”〔6〕。 最近出版的日本渡边欣雄《汉民族の宗教——社会人类学の考察》一书也表达了类似的意见,他在跋语中就指出,“正是混淆宗教作为汉民族的宗教”,而他所说的“混淆宗教”是儒道佛混融后包括仪式、义理、行为在内,在民间广泛流行的宗教,而与上层文化人心目中界限很分明的儒家、佛教、道教,内容并不一样〔7〕。
其实,无论是上层文化人还是下层民众,思想的深处都需要宗教,问题是上层文化人如果说可以在宗教经典的阅读和宗教哲理的思辨中得到理智的安慰,在宗教所指出的生活境界中得到人生的情趣,在宗教的仪式里感受到天理与人心的沟通,那么,下层民众却无法从这里感受到宗教的意义,于是思想世界就出现了一个空白地带,这一地带就需要佛教、道教的仪式、方法和伦理规范来填充,中国民间的佛教道教就是承担了这样的责任,在宗教的一般性伦理中民众对情感和欲望有了一种评判标准,在宗教的生活规范中百姓对行为和现象有了一种认同或反对的尺度,在宗教的仪式中民众对人与神之间的沟通有了一种信心,当然,最重要的是宗教的方法与技术使民众的具体问题得到了心理上的解决。
也许人们会问,为什么中国宗教会有如此的现象?这的确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至今还没有特别明确的解释,不过,如果可以粗略地概括,我以为可能有以下三方面的因素:
第一,正如韦伯(Max Weber)等人早已说到的那样,亚洲的宗教从未有一个能发展成长期单一性、支配性的宗教组织,也不曾拥有世俗的权力,因此并不能要求信仰者对宗教思想有绝对的信仰,也不能在身份上对信仰者进行约束,因此它并没有神圣的权威。
第二,中国的儒释道三家在思想上的逐渐合流,和意识形态对这种合流的默认与鼓励,使得宗教思想不太有排他性,彼此之间的差异并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于是中国的信仰者也无须固执地坚守某一宗教,而可以出入于三教。
第三,中国宗教信仰的实用性特征是十分强烈的,信仰对于信徒没有特别的心理震摄与精神约束,信仰者可以根据自己的理解、兴趣和需要对宗教进行取舍,这样,文化素养、人生情趣和知识构成就成了宗教信仰者选择信仰内容和表现的分类,用所信仰的宗教为基准还不如以信仰者的文化层次为基准。中国上层知识阶级对于宗教的态度、理解、使用与下层民众阶级差异实在太大,他们的宗教信仰与其说是信仰还不如说是一种兴趣,对于他们来说,佛教也罢、道教也罢,都是一种知识、一种情趣、一种生活的消闲雅事,而对于一般的民众来说,宗教也不完全是一种信仰,而更多的是一种依靠,一种技术,一种在生活中解困脱厄祈福得佑的对象,有时候,宗教组织还是一个互相依赖以对付外在世界各种压力的弱小者的团体,普通民众可以在这里找到生存下去的信心与意义〔8〕。
注释:
〔1〕这里所说的士大夫阶层和民众阶层, 主要是依据其受教育程度、文化素养与生活态度来区分的,因此与通常意义上以身份划阶层不太一样,比如那些依靠祖荫或血缘而获得上层身份的人,在宗教信仰上可能属于后一阶层,尽管他在政治地位、经济条件上与后一阶层并不一样。
〔2 〕如日本学者中野美代子《卜一キョ一チかダォィケムガ》(《东方》154期,东京1994 )及坂出祥伸在《道教与中国文化》日译本后附的《译者后记》(东方书店,东京,1994)。
〔3 〕萧洛克《对孔子的国家崇拜的起源和发展:一个初步研究》224页,世纪出版社,纽约,1966。此处采用程钢先生的译文, 见《国际汉学著作提要》,江西教育出版社,1996。
〔4〕顾立雅《什么是道教?及中国文化史的其他研究论文》24 页,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70。
〔5 〕徐理和《佛教征服中国》第六章《化胡——佛道初期论争史》,英文本,莱顿,1959。《佛教の中国传来》,田中纯男等日本译本,328页,クガ书房,东京,1994。
〔6〕陈荣捷氏《近代中国宗教的走向》,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53,日译本题为《近代中国ゴサる宗教の足迹》,福井重雅译, 144页,金花舍,1974。
〔7 〕渡边欣雄《汉民族の宗教——社会人类学の考察》一书跋语《要约と结论》,336页,第一书房,1991。
〔8〕这种看法对还是错?从理念上我以为是对的,不过, 这种人文学科式的考证、推理、判断,往往是文献加上思想加上感觉,若要真正得到证实,却需要社会科学的调查与统计作为依据,这就是我近几年来一直策划“中国民间信仰调查”的原因之一,但是由于经费等缘故,这一计划至今未能实施。
标签:佛教论文; 中国宗教论文; 文化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道教论文; 宗教论文; 日本道教论文; 道教起源论文; 读书论文; 国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