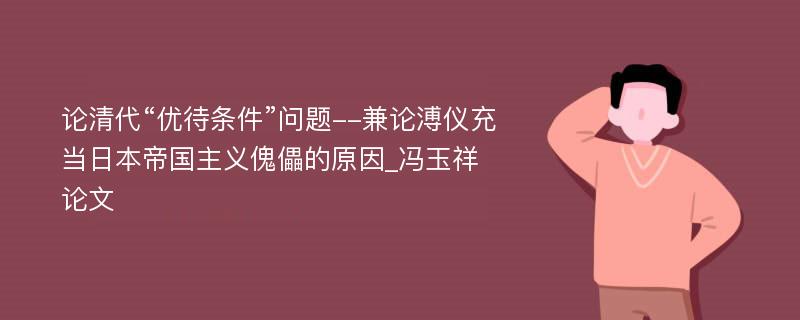
也谈《清室优待条件》问题——兼评溥仪充当日本帝国主义傀儡的原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优待论文,帝国主义论文,日本论文,傀儡论文,也谈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代史研究》1994年第1 期刊载了喻大华先生《〈清室优待条件〉新论——兼探溥仪潜往东北的一个原因》(以下简称《新论》)的文章。该文对《清室优待条件》、冯玉祥驱逐溥仪出宫和溥仪叛国原因等问题发表了一些看法。拜读之后,笔者认为该文不仅观点陈旧,而且在一些问题的论述上、尤其是关于溥仪充当日本帝国主义工具原因的看法,涉及到一个十分严肃的历史和现实问题,即如何评价某些对国家、民族犯有严重罪行历史人物的犯罪原因。为此笔者也试就该文所涉及的上述三个问题略陈管见,与喻先生商榷并就教于方家。
一
关于《优待条件》的产生,《新论》否定了学术界对此的传统观点。学术界普遍认为《优待条件》是由袁世凯等炮制,是中国资产阶级对封建反动势力的又一次妥协,清王朝结束统治后其皇室受到优待是极端荒谬的。而《新论》则认为首先提出《优待条件》的是革命政府代表,并对其做出了高度评价。他称《优待条件》的产生“具有历史必然性”,“不是个人意志的产物,而且有其积极作用”;“正是《优待条件》的提出,使清皇室发生了分化,并使之尽快退出历史舞台。中华民族在保持了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和尊严的同时,迅速地进入了共和时代。”(注:喻大华:《〈清室优待条件〉新论》,《近代史研究》1994年第1期,以下凡引本文时不再注明出处。)在此, 做为辛亥革命副产品的《优待条件》,被拔高成为加速建立民主共和国的原因。对此,笔者不敢苟同。
实际上,此论实为旧说,决非喻先生首创。1924年11月,在冯玉祥驱逐溥仪出宫后不久,唐绍仪就对上海《字林西报》的记者发表讲话说:“当时清帝逊位,缩短革命时间,保全人民,颇与民国以建设机会,故民国亦承认此优待条件以报之”(注:长沙《大公报》1924年11月13日。)。唐是辛亥革命时期代表袁世凯参加南北和谈的首要人物,也参与了与清室商谈《优待条件》。从肯定自己的历史出发,他替《优待条件》唱赞歌是可以理解的,其观点与《新论》大同小异。所不同的是,《新论》把《优待条件》产生的作用拔得更高。
《优待条件》的产生确有一定的社会原因。辛亥革命是在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经济政治发展还不成熟、中外反动势力相对强大的背景下发生的。革命并没有改变中国的社会性质,也没有给予封建的政治势力及经济基础以致命的打击。资产阶级革命派最终向反动势力妥协,从而将政权交给了袁世凯并最终保留了清室。这是由中国社会发展的特殊性所决定的,也就是“历史必然性”。
但是,《新论》所说的“历史必然性”并不是上述的经济政治原因。喻先生认为产生《优待条件》的原因有两点:(一)“险恶的国际环境迫使南北双方优待清室,以尽快地完成政权更替,避免招致列强干涉。”(二)“国内秩序混乱、财政危机的局面迫使南北双方必须优待清室,以尽快建立民国,早日拨乱反正。”
为了给上述原因寻找根据,《新论》极力夸大帝国主义干涉中国革命的危险及清室的力量,认为:“假若革命进一步拖长并发生较大的混乱,则难免为俄、日干涉提供机会。”这个观点倒可名副其实地称为“新论”了。到目前为止,所有研究辛亥革命、且有一定权威性的学术专著,都否认帝国主义干涉中国革命的可能性,帝国主义列强在华矛盾重重,并对腐朽的清王朝已不抱希望,故以扶植袁世凯来干涉中国内政。这已是不争的事实。固然,日、俄帝国主义最初确曾有干涉、分裂中国的阴谋,但由于害怕中国的革命力量,并碍于和英、美、德等帝国主义的勾心斗角等原因,被迫中断了其罪恶企图。英、美、德等帝国主义出于在华利益的考虑,没有如庚子年间结伙武装干涉中国革命的打算。这是中国革命大势及帝国主义矛盾斗争的结果,与《清室优待条件》何干?
《新论》还特别强调指出:清室“接受《优待条件》,留在北京,就使得日本军阀的满蒙独立计划失去了借口,潜往东北的肃亲王善耆也难以打着清室的旗号进行活动。……日本政府不得不命令川岛等人暂时停止满蒙独立活动。可见《优待条件》对保障国家统一起了多么大的作用”。这里,喻先生为极力美化、拔高《优待条件》的作用,已全然不顾历史事实了。
《新论》所谓的满蒙独立活动(史称第一次满蒙独立运动),分满洲独立(即让清东三省总督赵尔巽、统领张作霖拥立肃亲王善耆在满洲“独立”)和蒙古举兵(即唆使、资助内蒙古喀喇沁王、巴林王等蒙古族王公在内蒙举兵起事)两部分。清室接受《优待条件》后,日本并没有停止满蒙独立活动的策划与实施,2月22日, 日本政府也仅是决定中止满洲独立的策划。其原因也并非清室接受《优待条件》,而是赵尔巽、张作霖在袁世凯极力笼络下,一反以前效忠清室、依靠日本的立场,表示拥护共和,使日本策划的满洲独立失去了基础;再加之英国政府于2月16日照会日本政府,要求立即停止策划满洲独立。在这种情况下, 日本政府碍于英日同盟关系,决定中止满洲独立的策划与实施,也就在所必然了。可是,对于蒙古举兵,日本政府非但没有因清室接受《优待条件》而停止,反而更加紧锣密鼓地进行。一直到3月下旬, 日本参谋本部才训令暂时中止举兵,改为在内蒙训练军队、贮存武器弹药,以待时机。5月下旬,日本提供的武器弹药经大连运至公主岭, 由日军大尉松井清助负责运往喀喇沁和巴林,6月8日在途中被中国军方截获,武器弹药全部被烧毁。至此,蒙古举兵的策划才宣告破产。(注:详见王树才《日本帝国主义分裂中国的首次尝试——第一次满蒙独立运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85年第4期。)上述史实说明, 《新论》的观点是毫无根据的。假若《新论》的观点成立,那么,又该如何解释日本帝国主义于1916年(其时《优待条件》依旧,溥仪仍居宫中)策划、实施的第二次满蒙独立运动呢?显然,喻先生不能自圆其说。
更为离奇的是,《新论》还把垂死的清王朝的力量说得十分强大。在作者看来,不仅革命的力量,甚至连袁世凯的北洋武装都抵挡不住清王朝的垂死挣扎。《新论》声称:“清室一旦决定撤回东北,袁世凯根本无力阻挡。当时北京警察中满人居多,数量达1.2 万人的禁卫军虽改为由冯国璋统领,但多数士兵和下级军官仍为满人。而北洋军则已开往前线,与革命军对峙。所以,清室一旦孤注一掷,南北双方想极力避免的国家分裂就可能出现,那无疑是中国历史上的一大悲剧。”
《新论》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即通篇的结论都是建立在假设的前提下。我们姑且不论历史能否假设,即以事实论,武昌起义爆发后,清室已经丧胆。1912年2月26日, 京津同盟会员彭加珍的一个炸弹更使得皇族作鸟兽散,最顽固的宗社党连吹大话的胆量都已丧失,还谈得上什么组织反抗!须知,清皇室没有一个敢于“孤注一掷”的挑大梁的人物;其在北京的军事力量,实际上根本不值一提。军警算不上正规的武装力量,历来也不是野战军的对手,这是起码的常识。《新论》所说北京“汉人害怕满人报复而出走,满人害怕将来的下场而出走,两个月内避离北京的人数达40万”,这已经表明,北京军警连起码的社会秩序都维护不了,怎么还会成为清皇室的救命军?清廷的“禁卫军”虽然是一支正规的军队,但其组成人员八旗纨绔子弟居多,贪污腐败惊人,战斗力极差。连清朝重臣世续都承认“兵无斗志”。可见,“禁卫军”怎么可能成为与革命及北洋军对抗的“王牌”呢?实际上,“禁卫军”已为袁世凯的心腹冯国璋所掌握,清廷已失去了对其的控制。《新论》以此来宣染清皇室的“实力”,实在让人感到不可思议。
必须指出,在革命爆发后,京畿各界人民对于民主共和无不向往。“即满人中亦居多数赞成”(注:“何宗莲致孙中山电”,《南京临时政府公报》第8号,南京大总统府印铸局1912年编印,第309页。),清王公宗室及顽固派官僚虽然想勾结陕甘总督长庚和署理陕西巡抚升允反对革命,一些蒙古封建王公也图谋回归本部武装顽抗,但兵饷俱无,故只是虚张声势,空言塞责而已。
袁世凯的北洋军并非如《新论》所说,已全部派往南方与革命军对峙。当时,北洋第六镇在石家庄,第二十镇在滦州,北洋第二混成协、第三十五混成协在东北,北洋第五镇在山东,第三镇、第一镇就在北京。此时,完全听命于袁世凯的姜桂题的“毅军”也驻扎在京郊。我们不把由旗人组成的北洋第一镇算做袁世凯的力量,仅就其它诸部而言,京畿和东北也完全在北洋武力控制之下,清皇室哪里有什么反抗力量!
实际上,武昌起义后革命者的真正对手是袁世凯,清王朝能否存活下去也取决于袁世凯。袁一石双鸟,他成功地借革命力量震慑清皇室,又以北洋军事实力向革命党人施压。革命派所担心的不是清皇室,而是袁控制的北洋武装。1912年1月上旬, 革命党人与袁世凯的南北和谈达成了秘密协议:袁世凯逼使清帝在优待条件下退位,同意建立“共和政体”,然后孙中山把临时大总统的职务让给袁世凯。(注:章开源、林增平:《辛亥革命史》,人民出版社1981年7月版,第382页。)《优待条件》就是在这种条件下出笼的,南方代表伍廷芳也是在与张謇及袁世凯集团秘密商谈之后提出的。《新论》首先强调伍是始作俑者,继而又承认袁世凯方面提出的对清室优待条件高于革命党人的事实,已说明了历史的真相。袁世凯之所以如此,是为了避免招致“欺侮孤儿寡母”的“逼宫”之嫌,并不是心怀对清室的仁慈。1915年袁世凯帝制自为,还假惺惺地在《优待条件》上亲笔题道:“先朝政权未能保全,仅留尊号,至今耿耿,所有优待各节,无论何时断乎不能变更,容当列入宪法”(注:《民国人物小传》,传记文学社第74卷第1期。)。《优待条件》的提出, 只不过是袁世凯实现个人野心的手段与结果而已。
值得提出的是,《新论》绝口不提资产阶级革命派曾反对优待清室这一事实。黄兴在1912年1月19 日特致电伍廷芳说:“和议愈出愈奇,殊为可笑。第一条仍保存大清皇帝名称及世世相承字样,可谓无耻之极!”(注:观渡庐(伍廷芳):《共和关键录》第一编,著易堂书局民国元年本,第77页。)据当时外电报道,“南方革命党之激烈派于保存太后及皇上名称极不满意。然平和派势力甚大,足以抵抗之也”(注:《欧报对于中国革命之舆论》,丛刊本《辛亥革命》(八),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510页。)。 革命党人是在妥协倾向占上风的情况下才接受《优待条件》的。这其中,起主导作用的是伍廷芳、汪精卫等人。他们认为对清室优待是“枝节”,“共和目的已达,其它枝节似可从宽”(注:观渡庐(伍廷芳):《共和关键录》第一编,第80页。)。革命党人之所以接受优待条件,是为了换取袁世凯逼清帝退位,建立共和国。此时,革命党人与袁世凯方面都没有对外国干涉的恐惧,更没有对清室“孤注一掷”的担心及为避免民族分裂等策略的考虑。所以,《优待条件》的产生主要是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封建势力及封建伦理意识强大所决定的。其中,袁世凯个人的意志占了相当大的成分。
所以,《清室优待条件》是辛亥革命的副产品,并不是什么使中国“迅速地进入了共和时代”的动力之一,更没有、也不会在保障国家统一方面起重大作用。革命后,民国的首都保留了一个封建小朝廷,不仅散发腐朽臭气,还日夜图谋复辟,使其成为引起民国政治动乱的一个根源。基于此,《优待条件》实无什么“积极作用”可言。
二
《新论》不同意学术界的一般看法,即《优待条件》为国内外的野心家留下一个制造中国变乱的傀儡工具,认为此论“说服力不强”,“因为即使不给清室以优待,只要不把清皇族斩尽杀绝,他们就会有成为野心家制造动乱工具的可能性,这和是否优待关系并不大……”。然而,喻先生接着又说:“小朝廷的合法存在的确会对复辟势力产生一定的鼓励作用。”既然如此,怎么又肯定使小朝廷合法存在的《优待条件》呢?又怎么能说清室成为野心家制造动乱的工具与《优待条件》关系不大呢?喻先生承认小朝廷存在的反动作用,同意其为复辟势力“精神中心”的提法,但又称其与《优待条件》无关,显然是矛盾的。
为了美化《优待条件》,喻先生说:“世界上很少存在有百利而无一害的事物,关键在于执政者懂得并会运用趋利避害这个道理。《优待条件》会使复辟势力受到一定的鼓舞,但也会使其在活动时有投鼠忌器的顾虑。”所以,他得出结论说:“民国政府可以利用该条件的存废来影响和制约复辟派,同时借优待条件来控制清室。”接着,《新论》不惜笔墨论述了民国政府对封建势力的姑息纵容,从而得出结论说:“主要是民国政府而不是《优待条件》鼓励了复辟。”
这就太离奇了。就好像盗贼偷盗的原因并不是由于其有贼性,而主要是警察缉捕不力。这种逻辑恐怕不会为人所接受吧。《优待条件》是革命力量向封建势力妥协的产物,北洋头目与清统治者在阶级实质上又没有大的区别,且全系清朝旧臣,故民国政府对清室的非法活动及对复辟势力的包庇、纵容是必然的,也是客观存在的。但是,喻先生仅仅问罪于民国政府,而对清室的阴谋活动只字不提,显然有失偏颇。大量史实证明,清室的复辟活动一天也没停止过。
张勋复辟就证明了由《优待条件》而存在的逊清小朝廷对共和制的威胁。对此,《新论》仅仅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逊清皇室接受了复辟这也是事实”,而绝口不谈清室的责任。张勋复辟被平息后,以段祺瑞为首的北洋军阀头目为清室开脱罪责,认为是被胁迫。这早已被证明是谎言。当时一些有识之士就认为,清室既便是被胁迫参与复辟,也是对民国的犯罪。冯玉祥在“主张处分清室通电”中说:“此次张逆叛乱,国本动摇,固张逆之不法,然非清廷之酝酿,何以至此,是倡乱虽在张逆,而祸本实在清廷……。”(注:“主张处分清室通电”,《冯玉祥政治要电汇编》,北平东方学社1933年11版,(政)第6页。 )可谓一针见血。
溥仪被驱逐出宫后,清室善后委员会在故宫养心殿溥仪居室发现了大批证明清室阴谋复辟的文件。其中最重要的材料有:康有为述游说复辟经过函;金梁二事折;金梁条陈四事折;江亢虎请觐溥仪函;金梁为江亢虎请觐折;升允等谏阻移居颐和园折;陈夔龙谏阻出洋折等。(注:《民国日报》1925年8月7日。)
这些文件,以金梁的密折最具代表性。金在密折中为溥仪制定复辟计划,要他以“密图恢复为第一,恢复大计,旋转乾坤,经纬万端,当先保护宫廷”;并建议清理皇产,保护宫殿文物等。其中在图恢复条目下,提出“恢复方法,务从机密”;“求贤才,收人心,联友邦,以不动声色为主……”;“至于恢复大计,心腹大臣运筹于内,忠贞之士则命于外,成则国家蒙其利,不成则一二人任其害……。”康有为在其致庄士敦函中说:“所致游说,天佑中兴,望以所历代奏,先慰圣怀。”(注:《民国日报》1925年8月8日、《晨报》1925年8月23日。)
上述文件是图谋制造国家内乱的罪证。溥仪将其密藏,业已充分表明了自己的政治态度。他与金梁、康有为等均是图谋颠覆民国的罪犯。
清室善后委员会公布了上述文件后,溥仪还全然否认,称其:“多属捏词伪造而来,令人至可哂可鄙。”其于此, 清室善后委员会于1925年8月14日将复抄的上述材料函送京师地方检查厅,要求立案起诉。(注:《晨报》1925年8月20日、1925年8月15日。)但是,在段政府的包庇下,国务院会议决定令地方检查厅不予受理,其理由是该文件所涉及虽属犯罪行为,但因段政府上台后已宣布大赦,故让司法总长杨庶堪以私人名义出面,与善后委员会代表李石曾面商调和办法。因此,此案不了了之。尽管如此,清室图谋复辟的阴谋大白于天下后,为溥仪出宫叫屈的声音也立渐平息。
喻先生既然对清室的罪责视而不见,但却又说,在张勋复辟后“如果民国政府修正《优待条件》,加强对清室控制的话,不但能顺应一般的民意,而且中外旧势力都没有干涉的理由”。这就奇怪了。假如清室仅仅是“被胁迫接受复辟”,又有什么理由修正《优待条件》呢? 1917年修正《优待条件》既然可行,那么冯玉祥在1924 年修正《优待条件》又有什么值得非议的呢?
更让人不可理解的是,《新论》一面肯定及美化《优待条件》,一面又指责民国对逊清皇室的“无原则的优待”。既然《优待条件》能维护国家统一与民族的团结,又能限制复辟势力的活动,那民国政府为保证该条件的执行,对清室一些违法的行为视而不见,采取“宽大”态度又有什么不对呢?那不是对国家的根本利益更有利吗?《新论》不能自圆其说。
三
《新论》第三部分全面否定冯玉祥驱逐溥仪出宫及黄郛内阁修正《清室优待条件》。喻先生首先否认此举的合法性,认为:“此前民国政府一直把该条件视为‘缔结条约性质’的法律文件,只有国会有权决定其存废。摄政内阁的这一举措是明显的越权违宪行为。”
此说更是陈辞。最先跳出来持此说的是逊清皇室。北京政变后,孙中山先生应冯玉祥之邀北上,到京便接清室于宝熙函,称冯之此举违法,清室不能认为有效,请他“主持公道”(注:刘汝明:《刘汝明回忆录》,台北传记文学社1973年8月版,第55—56页。)。 康有为此时致电段祺瑞,大骂冯玉祥,并诘问“条约可随意而废?”(注:长沙《大公报》1924年12月5日。 )唐绍仪也喋喋不休地说:“前既曾同清帝订立庄严条件,则惟有遵守之”;“在未商订新办法前,决不能有所变更也”;“中国人民若因政治上及他项理由,认为此项条件有更改之必要,亦当以合法之程序表示其意。一个人之横暴恣肆行为总不可视作全国人之意愿”;“张勋复辟之时,民国曾有取消清优待条件之动机,当时民国未尝要求更改,今日尚有更改之理由?……”;“此破约背信之举亦为军阀专制之一例”(注:长沙《大公报》1924年11月13日。);胡适在致王正廷(时任外交总长)的信中也说:“我是不赞成保有帝号的。但清室优待乃是一种国际信义条约的关系,条约可以修改,可以废止,但堂堂民国,欺人之弱,弃人之丧……强暴行之,这真是民国史上一件最不名誉的事。”(注:《晨报》1925年11月9日。)
与此同时,社会上掀起了一阵反对冯玉祥、替清室叫屈的鼓噪。段祺瑞执政府召开“善后”会议时,有所谓正谊书社者,集刻了一本要求保障清帝“权利”的通电,向“邪氛民国”的执政府、善后会议会场如雪片般的分发,对执政府施加压力。该书所辑通电列名者有所谓“满蒙协进会”、“满族同进会”、“旗族互助同进会”、“京师总商会”等名目及逊清遗老、复辟分子骨干等,其余不具名而标出人数有433人。 该书称“凡属血气之伦,均抱不平之感”,“民情惶惑,舆论沸腾”,“中外震骇,大动公愤”(注:《民国日报》1924年2月25日。)。 其主要论调就是攻击冯驱逐溥仪出宫之举为不合法。
相反,进步力量则对冯玉祥的举措给予坚决支持和高度评价,北京各界还成立了“反对优待清室大同盟”。1924年11月11日,孙中山致电冯玉祥,嘉奖他废除清室帝号,称此举大快人心,并高度评价说:“复辟祸根既除,共和基础自固,可为民国前途贺”。章太炎也致电冯玉祥、胡景翼称:“念自六年复辟以后,优待条件,当然消灭。”叶楚伧在《民国日报》上发表评论说:“鹿钟麟勒兵隆宗门,唤令溥仪出宫,将一片中华民国领土还给中华民国,这一阵功烈实不在回师倒曹之下。(注:《民国日报》1924年11月14日、1925年11月13日、1925年3月4日。)
就攻击冯玉祥此举不合法的论调,进步人士也给予了有力的批驳。《优待条件》确是在1912年2月10日得到南京临时参议院的通过, 但此后已被清室破坏。孙中山先生在1925年1月6日嘱秘书处给清室的复函中已明确指出这一点:“自建国以来,清室始终未践移宫约,而于文书契券,仍沿用宣统年号,对於官吏之颁,给荣典赐谥,亦复用弗改,是以民国元年优待条件及民国三年优待条件善后办法中,清室应废行之各款,已悉行破弃。逮民国六年之举,乃破坏国体之大毒。优待条件之效用,更是完全毁弃无余。虽清室於复辟失败以后,自承斯举为张勋胁迫而成,斯言若信,则张勋乃清室之罪人,然张勋既死,又予‘忠武’之谥。实为奖乱崇叛,明示国人以张勋之有大造于清室,而复辟之举实为清室所乐观。事实俱在,俱可复按。则民国政府对于优等条件势难再继续履行。吾所以认11月间摄政内阁之条件,及促清室移宫之举,按之情理、法律皆无可议……。”(注:《民国日报》1925年8月10日。)
当时,《现代评论》杂志还发表了署名周鲠生的一篇文章,专门论述冯玉祥修改《优待条件》的法理问题。文章指出:“《优待条件》不是一件国际条约。清室不是一个国家,它和民国没有对等之地位。《优待条件》也不是与外国政府订立的,也没有受外国列强保护。虽然这条件曾由中华民国政府照会各国驻北京公使,然此不过是片面公告的形式,并非构成国际保障。所以,民国关于该项条件之履行,毫无国际义务可言”。文章进一步阐述《优待条件》的性质,认为该文件也不是私法契约。因为“契约必是双方或多方的协议。《优待条件》如属契约,应是经民国政府和清室双方签订的文件”。“民国政府虽然在事前曾就条件内容与清室磋商,然而最后还是经民国单方面名义,以一般法令形式公布的,并未与清室构成私法契约的关系。实则《优待条件》不过是民国政府在新旧交替情况下,为政治善后的权宜办法,对于国中一姓人给予一种特典。这是片面的恩惠,而不是双方的协议。这项特典之法令,既不能超出法令之上,而其永久性又没有特殊的国际的或宪法的保障。民国以主权之资格在法律上自有修改或取消之权利。”(注:《民国日报》1925年8月10日。)
所以,根本就不存在关于修改《优待条件》的法理问题,段祺瑞是反对驱逐溥仪出宫及修改《优待条件》的,他闻此事后,曾气得将身边的痰盂踢翻,大骂摄政内阁,并打电报给冯玉祥,说如此“何以昭信天下乎?”(注:那志良:《宣统皇帝出宫前后》,台北《传记文学》36卷第1期(1980年1月),第95页。)但是,他上台执政后,并没敢利用手中权力贸然恢复《优待条件》。这固然与惧怕冯玉祥有一定关系。但主要也是深知冯之此举有理可依,并深得广大人民与进步力量的支持,故也只得承认既成的事实。帝国主义各国对冯玉祥的行动也深为不满。事发后,列强驻京公使曾由荷兰公使欧登科出面,召集紧急会议,一致认为冯玉祥对清室的处理“殊反人道主义,遂决定向中国外交部予以警告”(注:《晨报》1924年11月7日。)。但是,各国也仅此而已, 也没有提出法理方面的指责。之所以如此,是冯玉祥此举并无违法之处。
所以,《优待条件》和民国政府颂布的一般政令一样,其废止并不一定需要国会讨论通过。事实上,冯玉祥回师北京,猪仔国会已被解散。其后一直到1947年蒋记国大召开,中国就没有所谓的国会,民国一直就没有真正的法治。喻先生在此指责冯玉祥的行动没通过国会,似有强人所难之嫌。
实际上,《新论》肯定《优待条件》、否定冯玉祥驱逐溥仪出宫的根本用意恐不在于上述事件本身。因为文章十分明确地说:冯玉祥驱逐溥仪出宫“产生的危害实际上比以前还大”,“客观上使日本帝国主义有机可乘,去笼络控制溥仪”。他虽然抽象地承认:“溥仪成为日本侵略中国的工具有其本质上的主观决定因素,并且也可以说这是主要的”;但具体又说:“中华民国的失误是导致溥仪决心孤注一掷的一个原因”。这句话是此篇文章的点睛之笔。
上述说法也绝非喻先生首创。早在60年代,台湾学者沈云龙就曾指责冯玉祥为“不识大体之辈,群相造作,使溥仪走向极端,供人利用,无形都负对不起国家的责任”(注:颜惠庆:《颜惠庆自传》,台北传记文学社1973年版,第13页。)。喻先生只不过是重复这个论调而已。
修正后的《优待条件》规定:“大清宣统皇帝从即日起永远废除皇帝尊号,与中华民国国民在法律上享有同等一切之权力。”这已经给溥仪指出了光明的前途。当时的进步人士也对溥仪等人的前途命运发出警告。1925年3月,徐谦等253个著名人士,联合发表一意见书,反对恢复一姓尊荣,扰乱民国,并就一些复辟卖国分子与日本勾结,指出:“若辈怂恿溥仪,逃入日使馆,反陷溥仪於不能为民国人民之绝境,若再有其它举动,更予溥仪以莫大之危险……”(注:《民国日报》1925 年3月9日。)。但是,溥仪顽冥不化,一心想恢复“大清江山”, 这是他最终走上卖国道路的思想基础。而喻先生通篇想说的只有一个意思,既溥仪卖身投靠乃事出有因。喻先生的结论看似是历史逻辑推理,但实际上是建立在假设(溥仪如果不被驱逐出宫就不会“孤注一掷”)基础上来立论的,是站不住脚的。在此,我们也不妨假设一下,如果不修改《优待条件》,溥仪仍当小朝廷的皇帝,谁又能保证他在“七·七事变”之后不当日本人的工具呢?
历史上的任何大是大非的事件都可以找出一些互为因果的因素。若依照喻先生的逻辑,吴三桂引清兵入关是由于刘宗敏掠去了其爱妾陈园园;而国民党内的派系斗争则成为汪精卫“孤注一掷”的重要原因……。这样,历史还有什么真理与正义可言呢?
日本帝国主义侵华后,不少民族败类就是在政治失意的情况下,抱着东山再起的罪恶目的而卖身的,如王克敏、殷汝耕、齐燮元、梁鸿志之流。但是,我们不能以其政治失意的前因而为其当汉奸的后果辩护。同样的一些北洋失意要人,在日本帝国主义百般威逼利诱下,却能保持了晚节。清室的成员也没有悉数潜往东北。任何人,不论其身份地位如何特殊(《新论》强调溥仪地位的特殊性),个人前途的抉择与国家民族的利益不应是相悖的。做为中华民族的一分子,在任何时候首先考虑的应该是国家与民族利益这一大节。所以,我们不能以任何理由为出卖国家与民族利益的失节行为辩解。
总之,《清室优待条件》没有什么积极意义可言,冯玉祥将其修正并驱逐溥仪出宫也是无可非议的。笔者所述绝非“新论”,愿以此就教于喻先生及学界同仁。
标签:冯玉祥论文; 袁世凯复辟帝制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历史论文; 日本皇室论文; 日本中国论文; 民国日报论文; 袁世凯论文; 民国论文; 大公报论文; 溥仪论文; 辛亥革命论文; 北洋军阀论文; 清朝历史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