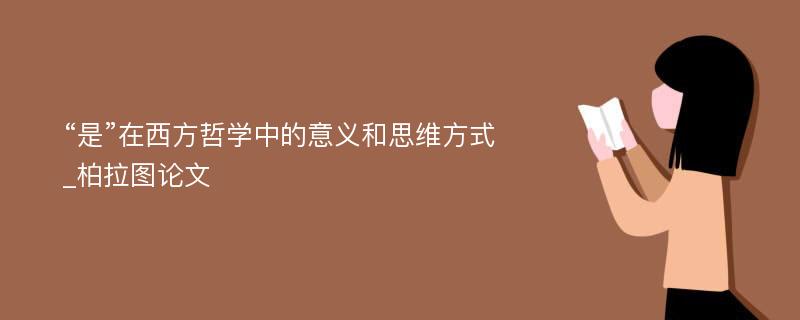
西方哲学中“是”的意义及其思想方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意义论文,思想论文,方式论文,西方哲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汪子嵩和王太庆两位老师合写的《关于“存在”和“是”》一文(注:此文载于《复旦大学学报》2000 年第1 期。 )讨论了西方哲学中Being这个概念的翻译, 认为已经“约定俗成”的“存在”这个译名不足以准确表达Being,主张改译为“是”,至少对于理解亚里士多德、 巴门尼德哲学应当如此。从表面看,这只是一个术语翻译问题,然而研究西方哲学的人当知道,Being对于西方哲学这座大厦来说, 具有奠基石的功效,对于我们追溯西方哲学的思想方式来说,又有行经走纬的作用。
这篇文章从几个方面论述了Being当译为“是”的理由, 其中包括追溯其印欧语系的词根并作词源和词义的考释;阐述了作为系词的“是”与西方哲学中逻辑表达式的关系;还结合巴门尼德和亚里士多德哲学,说明以“是”这个译名去释读他们的思想,在一些向来疑难的关节点上所获得的新见解。对于此文得出的结论,我是完全赞成的。
其实早在20世纪40年代,陈康先生在他译注的柏拉图的《巴门尼德篇》中就把相应于Being的希腊文on译作“是”和“是的”了。1959 年初版的吴寿彭译的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也作了同样的处理。然而,长期流行于学术界的却是“存在”这个译名。据信其主要的理由中有:人们的思想不习惯于把“是”当做一个概念来思考,同时也因为汉语没有词性的转换,不便在行文中把它当做名词来谈论。这两点理由是互为表里的,缺少这样的思想,也没有表达这种思想的语言。的确,西方人把“是”用作哲学概念时,同时伴随着一种思想方式,而且,随着在不同哲学中“是”的意义的不同,思想方式也不同。如果我们想进入西方哲学的堂奥,也许不得不用“是”这个词。为此,本文试以“是”去述说西方以论说“是”为主题的两种不同的哲学:传统的是论(ontology)和海德格尔的哲学,以期揭示其思想方式。 兹从作为最普遍概念的“是”谈起。
一、作为“最普遍”概念的“是”
大家都承认,“是”是西方哲学中广泛使用的核心概念,读西方哲学书总是碰到它。早在巴门尼德那里,“是”就作为哲学术语了。柏拉图以相的方式讨论过“是”、“不是”、“所是”或“是者”。亚里士多德提出,哲学就是关于“是者之为是者”的学问。中世纪神学甚至以“是”指称万能的上帝。黑格尔声称他的《逻辑学》是一个严密的演绎体系,其中的范畴无不有其来历,这个范畴体系的开端就是“是”。海德格尔革新传统哲学时,也围绕着对于“是”的阐述,其最著名的著作即称为《是与时》(注:Heidegger,Being and Time,tr.by John Macquarrie and Edward Robinson,Harper and Row, Publishers,1962;参见陈嘉映、王庆节译《存在与时间》,三联书店1987年版。)。
在各位哲学家那里,“是”的用法及意义是不尽相同的,但是有一点恐怕是人们都会承认的:在西方哲学史上,“是”被认为是“最普遍”的哲学概念,即,“是”的意义在于它是那个具有最普遍性质的范畴。至少,这是“是”的多种用法和意义中最重要的一种用法和意义。
什么是“最普遍”呢?通常人们把它理解为包容一切的意思。可是什么是“一切”呢?事实上,由于人们的阅历不同,尤其是思想方式的不同,所谓的“一切”是不一致的。囿于日常生活的人把凡是他亲身经历和感受到的东西称作一切。有科学常识的人把一切扩大到细胞、分子、原子、基本粒子以及这些物质的运动规律。我们也没有理由把那些非物质的东西排除在“一切”之外,例如数学对象、符号组成的信息世界,甚至宗教信仰和哲学思想表达的对象。用什么词语才能使这一切得到表述呢?
在中国历史上,人们曾经把“物”作为泛指一切的名称。墨子称“物”为达名(注:《墨子·经上》。),荀子则称之为大共名,他说:“故万物虽众,有时而欲徧举之,故谓之物。物也者,大共名也。”(注:《荀子·正名》。)这种观念及其表述方法影响深远,直至今日人们还用“万物”、“世间万物”的说法泛指一切。“万物”在英文里作“all things”,显然,哲学的对象并不限于all things,“万物”不足以成为哲学的最普遍的概念。
西方哲学把“是”当做最普遍的哲学概念。那么,在什么意义上“是”能成为最普遍的概念呢?为了搞清这一点,我们须追溯到柏拉图。柏拉图是第一个将“是”作为最普遍的相的人。事由起于他的后期著作《巴门尼德篇》,在那里,柏拉图为补救其前期有关相的理论的不足,发展出一种关于相之间相互分有或结合的理论。他提出,单一的相是不能成立的,相只能成立于它们的相互结合关系中。所谓相的相互结合,在形式上就表达为通过系词“是”把分别代表两个相的词组合成的句子。如“一是数”,这个句子就表示“一”和“数”这两个相的结合。“一”这个相的意义是通过“一是某者”这样的句式得到述说的。换句话说,“一”成立于与其他相的相互结合关系中。反之,如果“一”不与任何相结合,那么它除了自身就得不到任何规定,甚至连它自身也不能成立。因为,表示“一”成立的句子写作“一是”,这是希腊文里最简单的句子,它须是“一”和“是”的结合,可是,“是”也是一个相。由此可见,“是”这个相由于它还具有系词的身份,在柏拉图关于相的相互结合的理论中发挥着突出的作用。它不仅是相之间相互结合的纽带,还是每个相成立的起码的条件。“是”的这种性质使它成为最普遍地与其他相结合在一起的一个相。柏拉图论及“是”与“数”的结合时说:
如果一切数皆分有“是”,数的每一部分亦将分有“是”。这样,“是”就分配于许多是者中的每一个,不论其为最大的还是最小的,都无缺漏。认为所是者(anything that is)竟缺少“是”,简直是胡说了。(注:Plato,Parmenides,144A,tr.by Jowett;参见陈康译《巴曼尼德斯篇》,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79—180页。)
这里透露出,凡是分有“是”的相都被称为是者,由于一切相均须与“是”结合方能成立,所以凡是相都能以是者相称。而“是”本身则因遍及一切相而成为相的统领。
柏拉图以上说的都是在相论的范围内。严格地说,由于相并不就是今人所说的概念,我们还不能肯定“是”在他这里已经成了最普遍的概念,但是,他至少为后人指示了通向最普遍的哲学概念的方向。亚里士多德也根据对语言中作为系词“是”的表语成分的分析,划分是者的类型,追溯“是”和是者的意义。他指出,被称为“是”的东西有四类:(1)作为事物的属性;(2)作为表语的那些词的类,即范畴;(3 )作为被判断为真和假的东西; ( 4 )作为现实的和潜在的东西(注:Aristotle,Metaphysics,1017 a8—b9,1003 a20,tr.by W.Ross;参见吴寿彭译《形而上学》,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93—94页。)。也许系词“是”后面所示的东西不止这四类,然而不论有多少类,只要表示为由“是”引导的东西,无不是“是者”。仅据以上四类,是者的范围就很广泛:它可以指实际存在的东西(事物的属性、现实的东西),也可以指并非实际存在的东西(潜在的东西),可以指作为真的判断和假的判断的东西,甚至还可以指语词的类。这里已经透露出:是者是依“是”才是为所是的,而“是”的意义则是在是者方面得到显现的。
事实上,凡是我们感受得到、想像得到并能形诸语言的东西,都可以表达为“这是某者”的句子,因而都是是者,都落在“是”的范围内。西方人因此可以用是者指称一切可以指称的东西。例如, 称人类为human being,哪怕“无”这个概念也是一个是者, 只要它是一个概念;而又因为“是”包容一切,也以“最完满的是”指称全能的上帝。
虽然在西方语言中,是者被用来指称一切可以指称的东西,但是当亚里士多德说,哲学是研究“是者之为是者”的学问时,作为哲学研究对象的是者只限于那些一般的是者,那些特殊的是者则是各门专科学问研究的范围(注:Aristotle,Metaphysics,1017 a8—b9,1003 a20,tr.by W.Ross;参见吴寿彭译《形而上学》,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56页。)。亚里士多德根据语词类型概括得出的十个范畴,可以作为一般的是者的例子来了解,他说:
指实体的,如“人”或“马”;指数量的,如“两丘比特长”、“三丘比特长”等;指性质的,如“白的”、“语法的”等性质;“两倍”、“一半”、“大于”等属于关系的范畴;“在市场”、“在吕克昂”是地点范畴;“昨天”、“去年”是时间范畴;“躺着”、“坐着”是指姿势的名辞;“穿了鞋的”、“武装的”属状态范畴;“施手术”、“进行针灸”是主动范畴;“接受手术”、“接受针灸”是被动范畴。(注:Aristotle,Categories,1 b25 tr.by E.Edghill;参见李匡武译《工具论》,广东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2页。)
当我们循着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思路,从关于事物的名到达一般的是者时,我们已经不知不觉地在思想上跨出了两大步。首先是从名到是者。名是用来指示实际事物的,我们有“名符其实”的说法。不指示任何实际事物及过程的名被认为是无意义的,是应当予以遗弃的。而当我们的思想切换到是者的层面,一切都被称为是者时,那些“徒有其名”的名,因其转换成了是者,也获得了置身之地。因为,名的根据在于它所指的实,而是者的成立仅须依其在语言中成为系词“是”的表语。其次,当从个别的是者中概括出一般的是者时,思想又跨越了一步。这时,是者离开实际事物更远了,运用这些是者进行的思考也更具有纯粹概念性思考的特点。
既然哲学研究一般的是者,那么哲学中的“是”必定是在与这些一般的是者的相互关系中得到规定的“是”。一般的是者总是某种特殊规定性的是者(如亚里士多德所列十范畴),“是”使得者是其所是,但“是”本身却不是任何特殊规定的是者。西方哲学沿着这条思路,终于在黑格尔这里得出了有关“是”的如下结论:
有、纯有(按即Sein/Being,“是”,下同)——没有任何更进一步的规定。……有假如由于任何规定或内容而使它在自身有了区别,或者由于任何规定或内容而被建立为与一个他物有了区别,那么,有就不再保持纯粹了。……有、这个无规定的直接的东西,实际上就是无,比无恰恰不多也不少。(注:黑格尔:《逻辑学》,杨一之译,商务印书馆1974年版,第69页。)
黑格尔的这番话是对西方哲学史上最普遍的概念“是”的最严密的表述。根据这个表述,我们可以理解“是”有如下三个特征:(1 )“是”这个概念是最普遍的概念,这是从逻辑方面规定的,是逻辑的规定性。逻辑的领域是超越时空的,因而我们不能指望“是”指示什么实际可经验的对象,也不能从对象方面去理解“是”的意义。最普遍的“是”的逻辑规定性在于“是”与同样是从逻辑上加以规定的诸是者的相互关系中。(2)对于最普遍的概念“是”, 不能有任何进一步的意义方面的说明,除非把它说成无。因为任何进一步的说明都是把一种特殊的规定性加给“是”,从而会使它失去最普遍的性质。(3 )“是”是不能被定义的。定义的方法是种加属差。“是”既然作为最普遍的概念,不可能有比它还普遍、还高的种概念。
虽然对于作为最普遍概念的“是”的意义说不明、道不清,有的只是否定性的意见,然而“是”却是西方理性主义从事哲学演绎时不可缺少的逻辑开端。
我们已经说明了“是”是西方传统哲学中最普遍的概念,以及这个概念从系词“是”演化而来的过程。或许有人会因为汉语中的系词“是”离开上下文便意义不确定、也因为没有把系词“是”当做一个概念的习惯,于是就不赞成把它用作being的译名。那么试问,在现代汉语中,还有哪一个词可以充作最普遍的概念呢?离开了系词“是”,又怎么说明这个最普遍的概念的形成过程呢?有一点则是可以确定的,即任何有确定意义的概念肯定不是最普遍的概念。
二、“存在”不是最普遍的概念
我国学界流行以“存在”译being,几乎已经根深蒂固。 然而这个译名对于我们理解西方传统哲学及其思想方式却造成了很大的障碍。
人们喜欢取“存在”这个译名,可能是由于“存在”比“是”容易理解,同时也可以找到词义上的根据。因为“to be ”作为实义动词使用时,可以是“存在”的意思。我们确实在恩格斯写于1886年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里,读到了应当理解为“存在”的being:“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 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思维对存在、精神对自然界的关系问题……”(注: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4页。)。不过我们也应该注意,早在出版于1878年的单行本《反杜林论》中,恩格斯有过一个说明:“当我们说到‘是’,并且仅仅说到‘是’的时候,统一性只能在于,我们所说的一切对象都是着(are)、存在着(exist)。”(注:恩格斯:《反杜林论》,人民出版社1970年版,第40页。)这表明恩格斯在使用being 这个词的时候肯定是指“存在”的意思。然而问题在于,为什么恩格斯要特别加以说明,如果being一向约定俗成为“存在”的意思,这一说明就是多余的。恩格斯有必要在此作一说明,这一事实恰恰说明,至少恩格斯所批判的杜林并没有这样认为。而杜林又是摹仿黑格尔的,这点是明确的。恩格斯指出:“杜林先生的世界的确是从这样一种‘是’(being)开始的,这种‘是’没有任何内在的差别、任何运动和变化,所以事实上只是思想虚无的对偶语,所以是真正的虚无。”(注:恩格斯:《反杜林论》,人民出版社1970年版,第41页。)显然,我们是不能把杜林理解的那个being当做存在的。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存在”是一个标志世界的客观实在性的概念,它与“物质性”、“自然界”是同义的。所以哲学的基本问题即“思维对存在的关系问题”,也可表述为“精神对自然界的关系问题”(注: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第15页。)。事实上,当马克思主义把being解释成上述意义的“存在”时, 其中已经包含着对西方传统哲学的革新。如果我们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解的“存在”加到传统哲学的being上去, 这不仅抹杀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传统哲学实行的变革意义,而且会把那些在传统哲学框架里围绕“是”这个范畴的纯粹思辨的哲学当做表述存在问题的哲学,从而使我们面对西方哲学陷入一个又一个的困惑。
例如,恩格斯主张“世界的真正统一性在于它的物质性”,批判杜林主张世界的统一性在于它的“being”。如果我们以为杜林的being就是“存在”,并且与物质性同义,那么,恩格斯岂不是在自相矛盾?
又如,西方哲学史上曾经以上帝是完满的being为大前提, 推论上帝存在(exist)。如果以为being就是“存在”,那么这个推论译成中文后形式上就是错误的,根本就没有必要作进一步讨论和批判。
这些都是由于不加分析地把being统译成“存在”造成的后果。
事实上,大家都知道,英文中另有一个表示“存在”的词, 写作existence。“是”与“存在”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存在”作为一个是者,是从“是”中分化出来的。
“存在”从“是”分化出来,这是一种逻辑的思想,它表示“存在”这个范畴逻辑地蕴含在最普遍的范畴“是”之中。这种观念的产生有其语言学的踪迹可寻。在古希腊的时候,语言中还没有分别表述“有什么”(thereness)和“是什么”(whatness)的词, 也即没有“存在”和“本质”这两个词。而“是”这个词则被认为既表示了“存在”,又表示了“本质”。所以,当柏拉图说“一是”这个句子时,可以认为是同时表达了“有一”和“这是一”这两重意思。这在表述现实事物的日常语言中是常见的现象,现实的事物必须既是一个什么,又必须是存在着的。两者缺一就不成其为现实的事物。例如,当说“这是一座金山”时,我们明白了它的“是什么”,然而由于它并不存在,它就不是现实的事物。
正因为当时希腊文只有“是”而没有分别表示“有什么”和“是什么”的词,当亚里士多德想加以分别表述时,就显得十分麻烦。例如,当他想表达“有什么”,即“存在”的意思,是这样说的:“我说的‘是’或‘不是’,是没有进一步限定的,不是指‘是或不是白的’。”(注:Aristotle,Posterior Analytics,89 b33,tr.by G. Mure;参见李匡武译《工具论》,第222页。 )下面一段话是亚里士多德对“有什么”和“是什么”的分别表述:“一个事物是的原因——(此‘是’)不是指是这或是那,即有这种或那种属性,而是没有限定的‘是’;以及它是其所是的原因——(此‘是’)不是指没有限定的‘是’,而是有某种本质属性或偶性的‘是这’或‘是那’。”(注:Aristotle,Posterior Analytics,90[a10],tr.by G.Mure;参见李匡武译《工具论》,第223页。)
从“是”中区分出“存在”和“本质”的过程是颇具戏剧性的。原来,亚里士多德的著作曾被译成阿拉伯文,“在阿拉伯文里不存在一个将这两种意义结合在一起的适当的词”(注:A.C.Graham, Unreason within Reason,Openg Court,1992,pp.87.),即阿拉伯文里没有一个相当于希腊文系词“是”的词,所以,“亚里士多德著作的阿拉伯文版是直译的,然而由于语言结构的原因,它们径直将亚里士多德译成一位有时谈论存在,有时谈论本质,却从不谈及‘是’的哲学家”(注:A.C.Graham,Unreason within Reason,Openg Court,1992,pp.88.)。大约在公元12世纪至13世纪,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又经阿拉伯文转译为拉丁文,从这时起,拉丁文中才逐渐形成了明确区分存在和本质的词。
上述语词演变的历史告诉我们:“是”这个词原来就包含“存在”的意思,但它比“存在”的含义要广;“是”有时也表达“存在”的意思,但“存在”却不能取代“是”。尤其是,当“是”作为西方哲学中最普遍的概念时,更不是“存在”所能取代的。
三、关于“是”的理论——是论
前文一再坚持,要把“是”当做西方哲学中最普遍的概念来理解,因为这直接关系到对西方哲学中一门最核心的学问——ontology的理解。仅从字面上说,ontology就是关于on/being即“是”的学问,照惯例也应译作“是论”(注:王太庆先生在《柏拉图关于“是”的学说》(载台湾的《哲学杂志》1997年8月第21期)中,已经使用“是论”一词。)。西方哲学史上重要的大哲学家的学说,如果不是直接建设“是论”的,多少也是围绕着“是论”、或针对“是论”暴露的问题而发的各种议论。因此可以说,只有进入“是论”的门庭,才能得着西方哲学的精神。然而长期以来,我国学界关于这门学问流行的译名是“本体论”,近些年也有的译为“存在论”。这些译名使人觉得这是一门关于本体或存在问题的学问,种种误译,大抵都同一开始就没有把“是”理解为最普遍的概念有关。
究竟什么是“是论”?为什么单用“是”这个名称标志这门学问?详述起来等于是展示一部西方哲学史,本文只能作单刀直入、抽取筋骨的叙述(注:参见拙著《本体论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虽然“是论”这个名称出现在17世纪末,这门学问的奠基者却是柏拉图。柏拉图建立了一种关于相的理论,这种理论认为,我们能感知的事物总有生灭变化,因而是相对的,从它们我们得不到关于它们真正所是的组织,能说明它们真正所是的是相。相不在可感的事物中,它们存在于可感世界之外的另一个世界,即相的世界里。这种理论的积极作用是,使人认识到从感觉得到的知识的局限,从而力图透过现象去发现真理。但这种理论也带来许多难题。首当其冲的一个是,既然相不是我们直接感知的东西,是否真的有相以及一个相的世界的存在?这个问题是无法从正面回答的。柏拉图巧妙地把问题转化成相是如何才有其“自在的是”(ousia)的,或者说,相在怎样的情况下才能成立? 以《巴门尼德篇》等为代表的柏拉图后期相论试图解决这个问题。他的结论是,单独一个相是不能成立的,相只能成立于它们相互结合的关系里。本文第一节曾提及,语言中有广泛连系作用的系词“是”,到了相的世界里,被柏拉图用作一个起纽带作用的相,一切相只有通过和“是”的结合,才是其所是,并与其他相结合在一起。柏拉图关于相的结合的理论,就是西方哲学史上最初的“是论”。
相的结合的理论被称为真理,然而它却不是我们可感世界里的真理。人们完全有理由问,这样的真理对我们来说又有什么用处呢?适逢历史进入了基督教发展的时期,柏拉图那套非人间的真理恰好被基督教神学吸纳,用来论证天国的真理。这套理论在其漫长的进程中,后来又采纳了亚里士多德的形式逻辑。于是,相的结合就发展为范畴间的逻辑演绎体系。范畴逻辑体系的出现,是“是论”成熟的标志。
对于日常思维方式中的人来说,“是论”是很难理解的,更何况对于不同语言习惯和文化背景的我们。对于一种理论,人们习惯上首先要问,它是以什么为对象的理论?然而“是论”从其奠基起,就不涉及任何对象,更不是从经验中概括出来的关于世界或宇宙的一般规律的学说。甚至,当它被表述出来的时候,也不能把它看成是人的主观思想的产物,而应视为是范畴自身中的逻辑必然性的展现。从肯定的方面说,“是论”所表达的是绝对理念自身的运动,是纯粹理性自身的展现。
所以,从18世纪初德国哲学家沃尔夫最早为“是论”所下的定义起,我们就发现,这种纯粹的哲学理论除了摆弄范畴本身,并不是关于任何我们所熟悉的对象的。这个定义说:
是论,论述各种抽象的、完全普遍的哲学范畴,如“是”以及“是”之成为一和善,在这个抽象的形而上学中进一步产生出偶性、实体、因果、现象等范畴。(注:转引自Hegel,Leture on the History of Philosophy,Vol.Ⅲ.London,1924,p.353;参见贺麟、王太庆译《哲学史讲演录》第四卷,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189页。)
这一定义中提到的在形而上学中进一步“产生”出偶性等范畴的“产生”,指的是逻辑地演绎出来。这在《不列颠百科全书》(第15版)“是论”条中明确地说出来:“依他(按指沃尔夫)的看法,是论是走向关于诸是者之本质的必然真理的演绎的学说。”而《美国大百科全书》则尤其侧重于指出“是论”不以任何经验事物为对象、超经验的性质:“是论,形而上学的一个分支,它研究实在本身,这种实在既是与经验着它的人相分离的,又是与它的思想观念相分离的。”
现在我们再回过头来谈与是论密切相关的这个“是”的意义问题。我们已经交代过了,在柏拉图那里,“是”这个相倚仗其在语言中的系词的身份,成为相之间相互结合的纽带,因此我们对“是”这个相的理解离不开对作为系词的“是”的理解。自从是论引进逻辑方法以后,“是”就成了一个严格逻辑规定的范畴。而且,它不是一般的范畴,而是作为全部演绎体系开端的范畴。形式逻辑的三段论,用康德的话来说,本质上是一个先天分析判断,结论中的东西事实上只是将逻辑地包含在前提中的内容展开。因此,是论作为演绎体系,要逻辑地推出各种范畴,其最初的大前提,即作为全部逻辑体系开端的范畴,必定是一个无所不包、最普遍的范畴。这个范畴就是“是”。作为最普遍的范畴的“是”,其意义只是相对于各种特殊规定性的范畴即是者而言的,此外,“是”并无其他所指(注:牟宗三先生在《五十自述·架构的思辨》中曾谈到西方哲学中的“存有领域(realm of being),关于这个领域的理论,他的体会是:“一个表达逻辑自己的纯形式的推演系统,自始即不牵涉对象,全系统一无所说,与外界根本无关。然而它表示什么呢?这须慎审体会。我步步审识的结果,遂断定它只是‘纯理之自己展现’,它不表示任何东西,它只表示‘纯理自己。’”(见《牟宗三集》,群言出版社1993年版,第58页)这个“存有领域”实际上就是西方哲学的“是论”。)。
是论曾经被认为是纯粹的哲学原理。作为纯粹的原理,它并不指示任何对象,而只是从概念到概念的纯粹思辨。甚至,当我们说它是纯粹概念的思辨时,还得指出,这不是人在思维,而是假定为绝对精神自己的展开。在这个意义上说,是论是完全脱离实际的、空洞的理论。对于这种理论形式及思想方式,日常思想方式的人们是十分陌生的;在中国古代,也从来不曾出现过这种形态的哲学。人们习惯于与对象相联系的思想,即关于某个对象的思想,哪怕是虚构的对象,却不习惯不与对象相关的空洞思想。也许正因如此,人们就容易接受“本体论”、“存在论”这样的译名,以满足有其对象才踏实的思想的需要。但是这一脚却踏到是论之外去了。
我们且不要因为是论有脱离实际的明显缺点而怀疑它在西方哲学史上的存在和地位。事实上,这种理论的存在有其历史渊源,并且正因为有这种理论,才使哲学家们在批评和克服其缺陷的过程中,推动了西方哲学的发展。例如,笛卡尔以“我思,故我是”这个命题,把“是”等同于思维。考虑到“是”原来是另一个世界里的纯粹原理的逻辑开端,笛卡尔的这一转语所起的作用,正在于把这套原理体系纳入人的思维,逻辑演绎从此被肯定为人所具有的理性能力。这一转折使西方哲学的重心从是论移到了认识论,从而开启了西方近代哲学的序幕。
四、海德格尔的“是”的意义
西方哲学中谈到的“是”的意义是多种多样的。本文前面所谈的作为逻辑意义上最普遍的范畴的“是”,主要见于是论中。由于是论在西方哲学中的重要地位,这种意义的“是”是我们首先需要了解的。同样,如果有一种哲学针锋相对,根本反对把“是”当做一个逻辑范畴看待,便是对以是论为核心的西方哲学传统的挑战,它也是本文尤其应当关心的。海德格尔哲学正是这样一种哲学。
照海德格尔的说法,传统哲学看似在讨论“是”(Sein/Being)的问题,实质上却停留在是者(das Seiende/being,即that it is )的水平上。因为在传统哲学里,“是”是一个范畴。海德格尔要讨论的“是”,是指“天是蓝的”、“我是快活的”这样的句子中的“是”,所以,从西方的语法来说,传统哲学的“是”是动名词Sein,海德格尔的“是”则是不定式sein,只是屈从于文法,在行文中也写作Sein。照海德格尔的看法,由于从柏拉图以来,西方哲学实际上只停留在是者的水平上而没有真正深入到“是”的意义问题,所以整个西方哲学史只是一部忘“是”的历史。“是”的问题的重要性在于,大家都承认,是者是依据“是”的方式是其所是的,阐明了“是”的意义也就说明了是者的来历。号称西方第一哲学的是论既然只停留在是者的水平上,就称不上是最深的哲学,因为它的来历也可从“是”的方面得到说明。
那么“是”的意义究竟是什么呢?对“是”的意义应该从何处着手去寻问呢?前面我们曾引“天是蓝的”、“我是快活的”,海德格尔要寻问的是这种表述中作为系词的“是”的意义。可是我们不要以为海德格尔是一位研究词义的语言学家。他在这些表述中看出,天、蓝的、我、快活的,这些是者得到了首肯。在我们的首肯中,是者得到了显现,“是”的基本意义就是显现。使是者得以显现的“是”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判断、解释、说明、表述、领悟等等都是“是”的方式。在许多情况下,我们并不必使用到“是”这个词,甚至是在没有去想一下的情况中把握着是者的。例如,在一场激烈的乒乓球比赛中,运动员须全神贯注回击飞来的球,他打得越顺手,就越不及去想一下手中握着的拍子,拍子与他是浑然一体的;只是当拍子影响了他正常发挥的时候,才会特别留意拍子出了什么毛病。在这两种情况里,运动员对待他的拍子的方式是不同的,在前一种情况里, 运动员对拍子取环顾(circumspection)的方式,后一种取看(seeing)的方式。相对于这两种方式, 球拍分别成为应手状态(readiness-at-hand )的是者和显在状态(present-at-hand)的是者。这个例子说明,是者之为是者, 在于人与之打交道的方式,这种打交道的方式既是事物那样的是者的“是”的方式,也是人自己这个是者“是”的方式。所以,“是”的方式应当在人与周围事物打交道的方式中去寻求。
人自己也是是者。人是在与周围的他人和事物打交道的关系中是为所是的,这种打交道正是人自己的“是”的方式,所以海德格尔用“本是”(Dasein)称呼人,它表示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在与周围的交道中(即“是”中)是为所是的是者。这里所谓打交道的现象,是人主动介入到自己所在的世界的过程, 描述为“是于世中”(Being- in- the-world),“本是”就是以这个结构去“是”、去展开的。世间是者之为是者,取决于人与之打交道的方式,而人则是打交道现象中主动的方面。因此,追寻“是”的意义,归根结底在于揭示人自己的“是”的方式。
这里还要交代一点:虽然一切都在“是”中是为所是,只有人这个是者才在自己“是”的过程中同时领悟着“是”,海德格尔称人的这种与众不同的“是”的方式为生存(existence)。因此之故, 海德格尔称本是为“澄明之所”,意味各种是者在其中得到显现的场所。也由于这个特点,关于“是”的意义问题可以从本是依“是于世中”的结构展开出来的生存状态(existentiality)的分析中去寻问。
以上的初步介绍已经透露出,海德格尔哲学所谈的“是”的问题,与传统哲学的“是”的问题,其间存在着如此巨大的差别,以致于我们只有从哲学的不同方向和形态方面才能讲清两者的差别。
从古希腊哲学起,西方人就开始把哲学定位在追求真理的方向上。在其发展的过程中,西方人认为真理应当具有普遍性和必然性的特征。这就是说,真理不应因人而异,而应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结果就产生了是论这样的理论。是论运用范畴进行逻辑演绎,被认为是普遍性和必然性的保证,并因而被称为是具有客观性的。“是”和是者就是这样一些从逻辑上加以规定的范畴,其中,作为全部逻辑体系开端的“是”是最具普遍性的范畴。然而,当海德格尔主张,是者之“是”的意义应当在本是的生存状态中去寻求,于是,哲学便转向深究人自己的“是”的方式的方向上去了。又因为人自己作为是者也是在自己的“是”的过程中成其所是的,所以追究人自己的“是”的意义等于深挖人之为人的来历。海德格尔得出的最终结论是,能够刻画本是之“是”的特征的是时间性。“是”的时间性特征,使“是”必定要从自身冒出来,介入或沉沦于它所在的世界,从而是为所是。死亡也是本是自身所“是”的方式,它使本是不可能再去“是”了。据此,人们认为海德格尔哲学是以探究人生意义为其方向的。本是的“是”的过程就是我们每个人自己生命展开的过程,“是”的时间性特征不但说明生命总是要展开出来,而且说明生命是有限的。明白这一切的真正目的,在于实现自己本真的生存,也就是要达到人生的自觉性。
不过,要是让海德格尔自己来说的话,他不会同意把他的哲学看做是哲学所可能取的多种方向中的一种。对他来说,如果哲学研究的问题应该是最深刻的问题,那么,通过对本是的生存状态的分析而追寻“是”的意义问题,当是一切哲学中最深的问题,因而应当是哲学最基本的方向。其他方向的哲学中所谈及的问题,可以从他的哲学里得到说明。由于是论一向被传统哲学认为是纯粹的原理,所以海德格尔要使是论在他的理论框架内得到解释。他批评是论中作为最普遍的范畴的“是”既然不能被定义,也不能用任何特殊的规定性去解说它,说明在是论的框架内,“是”的意义是得不到阐释的。他又指出,是论里的“是”既然是一个范畴,它实际上只是一个是者。是者的本质或来历可以从它“是”的方面去说明。作为例证,他谈到过“无”的问题。在是论中,最普遍的“是”因没有任何进一步的规定性而被等同于“无”。可是海德格尔指出,这样的“无”其实仍然是一个是者,因为它是一个范畴。真正的“无”是人自己的一种生存状态,在这种状态里,无思无虑,物我浑然一体,甚至连“无”这个词也说不上。只是当从这种状态醒过来,擦亮眼睛回想起来,才说出了:原来刚才的状态就是“无”(注:Heidegger.What Is Metaphysics,tr.by R. Hull and Alan Crick,见Existence and Being,Vision Press Ltd,1967,p.367;参见熊伟译《形而上学是什么》,载《海德格尔选集》上,孙周兴选编,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144页。)。海德格尔认为, 这种“无”的境界是我们每个人可能亲身体验的,是作为概念的“无”的出处,概念的“无”则是对生存状态的“无”反思的结果。依此类推,是论中的每一个范畴应当都能通过生存状态的分析,说明它们的出处和来历。事实上,是论中的范畴只具有逻辑规定性而不涉及对象,这是是论号称绝对真理却与现实世界隔一道鸿沟而存在于彼岸世界的原因。绝对真理既然是普遍必然的真理,它也不是从经验事实的概括中得出的。它倚仗逻辑演绎,声称是自己说明自己的。现在,海德格尔对其中的范畴的来历从生存状态的分析中作了说明。于是海德格尔认为,对本是的生存状态的分析是比是论还要基本的学说,
因而称之为“基本是论”(fundamentalontology):“基本是论——所有各种是论只有据此才得以得出——必须在对本是的生存状态的分析中去寻求。”(注:Heidegger, Being and Time,p.34;参见陈嘉映、王庆节译《存在与时间》,第17页。)
海德格尔哲学与传统哲学的差别还体现在二者的方法上。以是论为核心的西方哲学重逻辑的方法,这是不必多说的。海德格尔则称自己的方法为现象学的。一切是者是其所是的过程是现象,或者反过来说,在现象中,一切是者是其所是。前面说过,本是是使一切是者得到显现的一块澄明的场地。于是,所谓现象就是本是自身的展开。本是是依“是于世中”的结构展开的,这意味着,一切世内的是者显现出来时,总伴随着人与之打交道的一种方式,即本是自己的生存方式,或曰“是”的方式。而我们每个人自己就是本是。因此,当采用现象学的方法去描述本是的“是”的方式时,我们不必到别的地方去找一个本是,而是直接把自己这个本是“是”的方式描述出来。海德格尔又称这种方法为释义学的。显然,无论是现象学的还是释义学的,都是引导人们去体验自己生存的方式,并将这种体验描述出来。
同传统哲学比较,海德格尔哲学不仅在方向和方法上与之不同,就是在哲学形态方面也是不同的。哲学的灵魂在于形而上学。哲学的形态指的是形而上学的形态。以黑格尔哲学为代表的西方以是论为核心的形而上学解体以后,人们一再惊呼,哲学终结了。但是并没有人否认海德格尔哲学中仍然有形而上学这个灵魂(注:卡尔那普的著名论文《通过语言的逻辑分析清除形而上学》(载洪谦主编《逻辑经验主义》上卷,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就是将海德格尔哲学作为形而上学的典型的。)。但是仔细分析起来,海德格尔的形而上学与西方传统的形而上学是不同的。传统哲学把形而上学看做是对经验的超越,是走向经验之外的东西(注:康德在《未来形而上学导论》中说:“形而上学知识这一概念本身就说明它不能是经验的。”(庞景仁译本,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7页))。如果我们承认海德格尔哲学也是一种形而上学,那么它不仅不脱离经验,而且需要个人自己当下的体验。这种体验里有对日常经验的超越。日常经验总是拘执于是者的,为要体验本己的“是”,就需要剥离是者,从而赤裸裸地显出使是者是其所是的“是”来。剥离是者的过程是一种超越的体验,但这种超越不是超出经验,而是超越日常经验、去深入把捉形成这种经验的自己的生存方式。因此,我们看到两种不同的形而上学:一种是从经验向外超越、直到用概念的逻辑演绎表示的传统形而上学,另一种是从经验向内超越、直到显露出使这种经验成为可能的自己的生存方式的海德格尔的形而上学。
值得我们惊讶的是,这两种有重大区别的形而上学,都是借助于“是”这个词做文章的。这岂不是说明哲学思想的革新也只能在传统文化的背景中展开么?
五、思想方式始于词的运用
本文的出发点是要说明西方哲学中的Being译为存在之不妥, 而当译为“是”。但是本文不采取逐条辨证的办法,而是径直采用“是”这个译名,去述说西方哲学。结果,我们发现,这样表述中的西方哲学,与采用“存在”这个译名表述的西方哲学相比较,不仅面貌上有了不同,而且以是论为核心的西方哲学的形态、方法及其特有的思想方法也更清楚地呈现在我们面前。如果这种述说是符合西方哲学的真实本义、是成功的话,那么就是对“是”这个译名的一个检验。在词的运用中,就有了思想方式。
人们容易接受“存在”和“本体论”这样的译名,其中一个主要的原因,可能是因为人们一见“存在”和“本体论”,就对这两个词的意义有一种理解。而离开了上下文,“是”这个词的意义就不明白了。其实这还是拘执于日常思想方式而没有进入西方是论所特有的那种思想方式。是论中的范畴区别于日常语言中的概念:日常概念的意义在于这个概念所指的实际情况或对象,而是论中的范畴既然是超时空的,它就不指示什么实际情况和对象。正如冯友兰先生关于理论思维中的概念所说的那样:“如果能了解‘红的’概念或共相并不红,‘动’的概念或共相并不动,‘变’的概念或共相并不变,这才算是懂得概念和事物、共相和殊相的分别”(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一册,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2页。)。冯先生是从否定方面说的。从肯定的方面说,逻辑范畴(即冯先生所说的理论思维的概念或共相)的意义在于它们的相互关系的规定中。比如说,作为逻辑范畴,整体和部分是相互规定的,其中有整体是部分之和、部分必定包容在整体中等等必然的关系。如果用在日常语言中,情况就可能不一样,如蟒蛇的胃(部分)容得下一头牛(整体)。是论中的范畴是摆脱了经验事物的绝对的概念,只有这样才留下了纯粹概念间的关系。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说,“存在”并不是实际的存在,“本质”也并不是事物的本质,“存在”与“本质”是在其相互关系中而有其各自意义的。是论中其余的范畴也都如此。所有的范畴都通过化为是者而与“是”建立逻辑关系,如此而已。因此,如果是为了迎合日常思维方式,为概念确定其对象而取“存在”和“本体论”这样的译名,那完全是多余的。事实上,“本体论”这种名称立即使人想到关于“本体”的学问,字面上的可理解性反而封闭了通向理解是论的道路。
海德格尔明确他所谈的是“我是快活的”、“天是蓝的”这类句子里的系词的“是”。大概没有人会把这些句子里的“是”读成“存在”。如果我们能容忍以“是”谈论海德格尔哲学,却坚持以“存在”去读西方传统哲学,那么,海德格尔哲学问题的提出就没由来了,西方哲学的文化背景也就断裂了。作为系词的“是”看似只起联络主词和宾词的作用,实际上当某些东西通过系词表达出来时,其中包含着人对它们认可的态度。这种态度不只是纯粹意识性质的,它首先存在于人与之打交道的实际活动中,是人自己的生存方式。用汉语的“是”述说海德格尔哲学,既表达出了与西方传统哲学不同的一种哲学,又在其中保持了西方文化背景的一致性。
最后一点关于语法问题。有人担心汉语中没有动词转换成动名词的语法规则,所以觉得“是”不能作为名词被谈论。本文自始就在谈论“是”的问题,而没有顾及它的词性,行文想也没有什么不便。既然只有西方语言中有动词名化的规则,就让西方语言去遵守。汉语本来就“词无定品”,为什么要遵守西方语法呢?
标签:柏拉图论文; 哲学研究论文; 世界语言论文; 西方哲学论文; 形而上学论文; 关系逻辑论文; 读书论文; 哲学家论文; 反杜林论论文; 巴门尼德篇论文; 工具论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