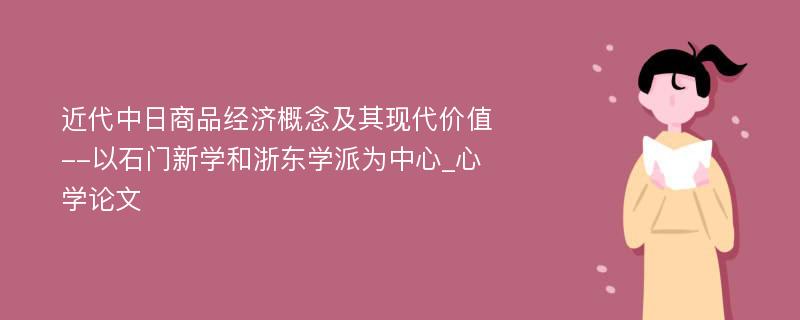
中日近世商品经济观及其现代价值——以石门心学和浙东学派为中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浙东论文,石门论文,近世论文,商品经济论文,学派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2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511-4721(2007)04-0083-13
本研究以“历史发展阶段的相似性”而非“实存时间”作为比较研究的基准,选择中日近世商品经济观中最具代表性的两个学派——江户时代石门心学与宋代浙东学派进行分析考察。主要基于两者都处于商品经济迅速发展的“近世”(pre-modern)阶段,均蕴积着社会经济形态转化的重要因素,突出地表现为商品经济观的变迁。传统社会以产品经济为主,而近代社会商品经济成为主导形态,市场逐步成为资源有效配置的主要方式。因此,从“近世”向“近代”的转化过程中,商品经济是一个关键性要素;而如何认识与对待商品经济及其发展,成为商品经济观的核心。中日两国近世的商品经济观,对后世直至今天都有着很大影响。
江户时代(1603-1867)是日本社会重要的转型时期,商人思想家石田梅岩(1685-1744)创立的“石门心学”即是商品经济发达的产物,在日本思想史和经济思想史上有着重要地位。其阐释商人的职业伦理与赢利的合理性等,并赋予经济伦理以宗教意义,类似于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提出的“新教伦理”,对日本步入近代化历程及其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①。由于石门心学与中国儒学尤其是“朱子学”有关,因此比较研究宋人的学说很有意义。
在中国历史重要的转折时期——宋代的思想流派中,以叶适(1150-1223)等为代表的浙东学派作为儒学在宋代的新发展,与朱熹、陆九渊之学鼎足而三,其商品经济观颇具新的时代特色,并对后世影响较大。从宋人陈亮、叶适直到清初黄宗羲等人,勾勒出了浙东学派的演进轨迹。比较中日商品经济观,宋代无疑相当重要,这不仅有利于开拓东亚经济思想史这一新领域的研究,还可以提供观察传统经济观之现代价值的一个新视角。
为何可以将中日两个间隔数百年的学派进行比较研究?这首先必须考察两者所处的时代背景和学理关联。笔者曾在《中日近世商品经济观略论——东亚现代化基础研究之一》、《中日近世经济思想比较研究与现代》等论文中作过阐述②,参考了日本东洋史学大家内藤湖南、宫崎市定等提出的“宋代近世说”,并结合笔者对宋代社会经济的研究③,提出江户时代与宋代在两国历史发展进程中具有若干历史发展阶段的相似性。众所周知,中国传统时代经历了数千年的漫长岁月,这与日本不同,划分历史阶段无疑不能只依据具体的“时间”。宋代被国际学界公认是中国的“商业革命”和“文化高峰”时期,当时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发生了许多前所未有的时代变迁,如贵族的衰微、庶民的抬头、新文化的产生、商品经济的发展等等,内藤先生甚至将这些与江户末期进行比较,明确指出两者“有类似的情形”[1](P52)。江户时代同样是日本社会重要的转型时期,同样发生着许多前所未有的时代变迁,关于江户时代是日本的“近世”,应属学者的共识,包括经济思想史学者大抵无歧义。
笔者认为两个学派所处的具体历史环境具有“近世”特征,主要是:两者均系结束中世分裂战乱后武人建立的集权政体;两者的统一都是相对的,实际上各类危机四伏,迫使政府多次变法改革;两者都在政治集权的同时采取经济、文化上较为宽松的政策,制度方面也进行了一些创新变革;两者的社会结构都呈现出若干转型时期的相似性,主要是商品经济高度发展,社会职业的等级身份制也逐渐变化;两者都是思想文化的高潮时期,宋君主张“重文兴运”与幕府提倡“文治主义”很相近,文化的世俗化、庶民化时代特征都较明显;两国的经济思想均呈现出一定的学理谱系,并对后世产生很大影响。同时,必须看到两国也存在若干差别,如皇帝的易姓改朝与万世一系不同,身份制变化与等级制稳固相左,中央集权制的统一性与幕藩体制的独立性有别,士大夫与武士在“四民”中名同实异等等。另外,日本近世接受宋学的过程本身就是扬弃汲取多种学术思想交融整合的过程。石田梅岩虽受宋学影响却又有许多不同,石门心学是日本学术思想和社会经济发展的集中体现④。
为什么说商品经济是近代化转型的关键?其实,以“传统时代”同“现代社会”的空间对峙为基点的现代化理论与研究很值得推敲。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翰·希克斯(J.Hicks)的《经济史理论》,揭示了市场经济起源及其发展的本质,成为经典。笔者视经济形态的演进即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为社会转型的关键,除受前人启迪之外,也基于个人长期的学术研究与思考——商品经济观不仅按到了经济形态演进的主脉,而且抓住了历史更迭进程的枢机。
主要依据是:
第一,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促进了交流、联系与交换,打破了分散、隔绝的传统经济形态,奠定了市场经济的结构基础。
第二,商业利润的获取,有利于资本的原始积累和商人或市民阶级经济实力的增强,商业的专门化和商业组织以及专业商人的出现,动摇了传统体制的社会基础。
第三,随着产品经济向商品经济的过渡,指令或习俗经济让位于市场经济,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和统一市场的形成,瓦解了传统社会的经济基础。
第四,随着商品货币关系的深入,促进了财产权利、法制观念的变迁,最终导致政治制度的创新。
第五,市场促进分工,而分工拓展市场,商业活动的频繁,促进了人身依附或固着地域关系的松解;从业者身份地位的改变,不仅有利于自由劳动力的产生,而且改变着人们的职业伦理观念。行业规范与职业伦理以及从业者的自律,成为市场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
第六,市场经济作为法制经济类型,其“看不见的手”需要健全的法制制约和普适的伦理约束,经济利益与道德伦理相辅相成,突出地反映在商品经济观中。
或许还可以列举出一些内容,但关键在于如何认识商品经济及其发展,以及与之相应的社会行业及其从业者,这些在传统时代与步入近代是有很大差异的,成为经济思想尤其是社会历史转型时期经济观念变迁的重要标识。
宋代浙东学派如何能够成为比较研究的基点?宋学是伴随宋代经济发展、社会变迁和思想文化整合而形成的儒学新发展,中国商品经济观的重大变化就发生在宋代,开启了此后经济思想发展的新趋向。笔者长年致力于宋代经济思想的研究,认为传统的“重本抑末”观念至宋受到深入批判,如欧阳修力主“使商贾有利而通行”,李觏要求“一切通商,官勿买卖,听其自为”,吕陶建议“许令通商”,苏轼反对“与商贾争利”,主张“农末皆利”⑤。如此等等都是商品经济观发展的标识,许多观点是前所未有的,在经济思想发展史上颇具价值。这些思想对南宋浙东学派很有影响,而浙东特殊的区域文化催生着这一学派鲜明的地域特色。
浙东是南宋经济文化的高峰区域,奠定了中国此后发展的基本格局。这里商贸繁荣、经济发达、人文荟萃,“东南财赋地,江浙人文薮”,“两浙之富,国之所恃”[2](卷32)。叶适的老家温州不仅是造船基地,还是商贸口岸,绍兴二年(1132)开始置市舶司;浙东也是纺织业发达区,有“千室夜鸣机”的记载,还出现了“机户”、富工、富贾等,促进了商品经济观念的发展。这样的变化是以文化昌盛为基础的,如洪迈《容斋随笔·四笔》卷5载:“七闽、二浙与江之西、东,冠带诗书,翕然大肆,人才之盛,遂甲于天下。”晁说之《景迂生集》卷13《南北之学》则提出:“主新说者,南方之学也。”《宋史·地理志》说这里的人“善进取,急图利,而奇技之巧出焉”。总之,这里与中原内陆农耕区域人们的安土重迁、贵本贱末、黜奢崇俭、重义轻利等传统不同,人多兼营副业或外出经商打工,直到今天,浙人善做生意还是很有名的。这样的区域经济文化特征体现为浙东学派“经世致用”的实学特色。
再来看石门心学产生的时代背景与心学创立者石田梅岩的思想渊源。石田梅岩1685年9月15日生于日本丹波国桑田郡东悬村(今龟冈市东别院町东挂),名兴长,通称勘平,号梅岩。1692年他到京都商家当“奉公”(伙计),1699年辞归乡里。1707年再度上京,在吴服商黑柳家当学徒,后升小掌柜。1727年辞去,1729年在京都初开讲席,这就是心学发端之时。1739年他刊行《都鄙问答》,1742年在大阪开讲席,1744年《齐家论》(亦称《儉约齐家论》)刊行,是年9月24日去世。主要著作即《都鄙问答》和《齐家论》,及其后学所编《石田先生语录》(以下简称《语录》)、《石田先生事迹》(以下简称《事迹》)等。
一般认为江户时代是日本町人(即商人)勃兴的时代,石田梅岩创立的石门心学,是关西地区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为倡言“町人之道”而创立。时值德川幕府第八代将军德川吉宗统治时期,许多著作如奈良本辰也《町人的实力》等专有研究。梅岩初开讲席时,恰是“商业社会”逐渐建立并确立了全国性规模的商品供需原则的时期⑥。但当时的商品货币经济植基于武家为中心的社会,呈现出一定的畸形性,这同宋代的政治集权与商品经济发展并存相似,承前启后、新旧交汇是社会转型期的重要标志。生活在实物经济中的武士与工商业者建立的商品货币经济之间产生矛盾,同时出现了幕府和诸藩的财政危机。德川吉宗推行“享保改革”,以奖励武艺、禁止奢侈、提倡俭约为宗旨,振兴产业以增加收入。然而,紧缩政策造成了商业不振和经济不景气,与町人利益及商品经济的发展相抵触。经济思想领域也存在明显的分歧,关键就是如何看待新兴的商品经济。
总的说来,当时的思想家传统意识还较浓厚,一些人依旧从武士本位的立场出发,秉持农本主义经济观,强调“町人无用论”,主张抑制其利润追求,“农本商末”观念还根深蒂固。如熊泽蕃山说:“农者,本也;工商,助农者也。”贝原益轩《君子训》提出:“古之明王重农抑工商,贵五谷而贱金玉,行俭约而禁华美,此重本抑末之道,成治国安民之政也。”荻生徂徕的《政谈》强调:“重本抑末者,古圣人之法也。本,农也;末,工商也。”⑦“贵谷贱金”、“尊士抑商”等传统思想仍有市场,如高野昌硕《富强六略》也倡言“商业无用论”。与此相对,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町人势力的加强,基于町人立场的主张也多了起来,集中出现了代表町人利益的前所未有的许多文献,如西川如见《町人囊》、三井高房《町人考见录》等,而在深刻性、系统性等方面最具代表性的就是石田梅岩的论著。精神自觉与町人发展相伴随,大阪批发商以“本商人”自勉,逐步确立起“町人之道”。井原西鹤描绘了强调重信用的“正直之道”的町人风姿。从“本商人”意识产生出强劲的道德性能量,通过梅岩而得到反省、自觉和体系化。寻求在封建秩序中町人的生存正道,并对之进行教化是梅岩的强烈意愿,“这可以说是由新兴町人的转变所产生的精神的自觉,因此是石门心学创立的意义之所在”⑧。
梅岩的学问形成与经历分不开。梅岩在黑柳家时最初热衷神道,但接触儒学典籍后逐渐转化,其学问是从自身的内在要求出发的,重视“知心”、“知性”,对佛教尤其是禅宗的关心也逐渐形成。《事迹》记载他三十五六岁时已知“性”,其《都鄙问答》卷之一中多处论及孟子的“尽心知性”,“知性乃学问之纲领”等。他谈“见性”的体验,并论及朱子《大学补传》中的“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日本思想史家源了圆《石田梅岩论》提出,梅岩的体验与那些“仅以文字之迹理解朱子学的半吊子朱子学者是不同的”⑨。梅岩主张抑制利己心和求利欲望并与日常生活中奉行俭约相合,进而达成献身自己的义务与职业,具有“世俗内”禁欲主义意味,成为町人及大众伦理的特征。
研究者一般都注意梅岩的学术师承,心学经济思想研究者竹中靖一指出:“石门心学的思想核心无疑出自儒教。”说他接受朱子学“性”“理”之说,但并非把朱子学当金科玉律,竹中认为石田梅岩的思想特征是“三教止扬”⑩,即对儒、佛、神道三教的扬弃与汲取,神道的“正直”、儒教的“诚”和佛教的“慈悲心”在梅岩看来是相通的。心学研究专家柴田实的《〈都鄙问答〉的成立》,深入考证梅岩的思想源流,指出其主要思想倾向是儒学。柴田提出梅岩的代表作《都鄙问答》引用汉籍共38种389次,其中《论语》引用133次、《孟子》引用达116次,其余为《大学》、《中庸》等,儒经共引18种362次,含程朱理学之书。再就是引用诸子之书9种11次,史书4种8次,其他为佛典及日本书籍,陆王心学的著作完全没有引用(11)。因此,不能仅凭“心学”之概念就将陆王心学与石门心学相联系。
美国学者贝拉(R.N.Bellah)提出梅岩是“最具独创性的思想家”,其师小栗了云“具有宋代的自然哲学(性理)的学识,还精通佛教和道教”。至于梅岩的学术渊源,“儒教给他的思想最大的影响。心与自然(性)的概念是其体系的基础。这是从孟子那里直接取来的,而有关这些的说明,则大部分得之于宋代朱子学”(12)。从梅岩言论中可见其与儒学的直接关联。《孟子·滕文公下》有“入则孝,出则悌,守先王之道,以待后学者”。他《都鄙问答》卷之一则强调:“尧舜之道,孝悌而已。鱼跃水里,鸟翔空中。《诗》云:‘鸢飞戾天,鱼跃于渊。’道者,察上下也,何疑哉!”又说:“学问之道,首要谨敬自身,以义尊崇君主,以仁爱事父母,以信义交朋友,广爱人而悯恤贫穷之人。有功不自夸,衣类诸物,守俭约而戒华丽。不荒疏家业,财宝知量入为出,守法治家,学问之道大抵如此。”《事迹》记述“先生曰:‘吾天生好究道理,自幼时为友所嫌,亦调皮作恶。十四五岁时顿悟,以是为悲;及三十岁时,大抵明理,犹显于言端;四十岁时,觉如梅之烤焦仍少有酸;至五十岁时,大抵不为恶事”。到六十岁,则曰“我今为乐矣”。这样的表述乃至表述的方式,使我们立即想起《论语·为政》的名句:“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通过文献考究,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石田梅岩的言论著述,确可称为“言必称孔孟”,必以“圣人之道”为教,却也包涵其特有的思想内容。
浙东学派同样言孔孟而解之以己意,这也是儒学至宋的新发展特征。宋代浙东学派主要包括以吕祖谦为代表的金华学派、以陈亮为代表的永康学派和以叶适为代表的永嘉学派,共同特点是倡言事功,主张经世致用,谙悉掌故和经济。有关浙东学派的研究取得了可观的成果,但对于其经济思想尤其自宋至清及与后世近代化的联系的研究还少见。朱熹曾指出此学派的特点“专是功利”[3](卷123)。所谓功利,经济活动是主要内容。金华、永康两派在经济思想方面或有独到之处,但不突出,也不很系统,不足以代表浙东学派经济思想的最高成就。其中较有价值的如陈亮反对传统的“重本抑末”思想主张农商并重,“农商一事也,上下相恤,有无相通……商藉农而立,农赖商而行,求以相补,而非求以相病”[4](卷11《四弊》)。他与朱熹进行著名的“王霸义利之辩”长达数年,一般被认为是事功之学与理学的“义利观”争辩。不过理学家并非如一般人认为的那样全然否定人欲功利,如程颐讲:“人无利,直是成不得,安得无利?”[5]((《河南程氏遗书》卷18)朱熹说:“义利之说,乃儒者第一义。”[6](卷24)但朱熹又说过:“圣人岂不言利?”只是不大为人注意而已。他并不否定从“义”出发的“利”,而反对从“欲”出发的“利”,认为“万物各得其分便是利”[3](卷68),以往的一些成论需要重新考察(13)。理学与浙学有别但也并非完全不相通,在学术渊源方面也有关系,名家何柄松曾指出:“所谓浙东的学派实在就是程氏学说的主流,在南宋时代和朱、陆两家成一个鼎足三分的局面。”[7](P204)叶适本人则与二程、朱熹都有一些直接关联。
叶适,字正则,温州永嘉(今温州)人。晚年在永嘉城外水心村著书讲学,世称水心先生。淳熙五年(1178)进士,史称其“志意慷慨,雅以经济自负”。他有实践经验,倡导“务实而不务虚”,曾治边郡、措屯田、安流民、建堡坞、守江北,修实政、行实德。主要著作有《水心文集》、《水心别集》、《习学记言序目》等。一般认为永嘉学宗二程,由先辈周行己、许景衡等,经薛季宣、陈傅良发展“实事实理”学风,到叶适而蔚为大观。黄百家说:“永嘉之学,薛、郑俱出自程子。”[8](卷56)但全祖望提出:“世知永嘉诸子之传洛学,不知其兼传关学。”[8](卷32)他认为:“浙学于南宋为极盛……,叶、蔡宗止斋以绍薛、郑之学为一家,遂与同甫之学鼎立,皆左袒非朱、右袒非陆,而自为门庭者。”[8](卷53)为叶适立学案,论“水心较止斋又稍晚出,其学始同而终异,永嘉功利之说,至水心始一洗之。……乾淳诸老既殁,学术之会,总为朱、陆二派,而水心齗齗其间,遂称鼎足”[8](卷54)。叶适的思想同样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他早年在朝中为朱熹理学说话,《进卷·管子》指陈管仲“以利为实,以义为名”[9](卷6)。还主张“谈谊而不谈利,计德而不计功”[9](卷9)。晚年的代表作《习学记言序目》则明显不同,反对空谈,倡言功利。总之,叶适远承伊、洛,近师周、郑,光大薛、陈而集永嘉学术之大成;是有宋以来反传统思想与务实精神的集中体现,也是儒学发展流变与东南地域社会经济结合的产物。
永嘉学派的经济思想在宋代浙东学派中最具系统性,叶适的商品经济观是为典型。首先,如何看待获利?这是道德伦理与经济利益关系的“永恒话题”。叶适说:“‘仁人正谊不谋利,明道不计功’,此语初看极好,细看全疏阔。古人以利与人而不自居其功,故道义光明。后世儒者行仲舒之论,既无功利,则道义者乃无用之虚语尔。”[10](卷23)批大儒董仲舒名言“全疏阔”,无功利的道义被认为是无用的“虚语”,这是对传统义利观的深刻修正。叶适说:“古人以利和义,不以义抑利。”[10](卷27)“昔之圣人,未尝吝天下之利。”[9](卷3)他主张“成其利,致其义”[10](卷22),即“利”与“义”不仅不矛盾,而且是“义”的基础,别于将“义”置于首位或要求以符合“义”的规范取“利”。他并非不言“义”,而是主张利义统一,强调致富获利的合理性;认为功利是义理的外化,“崇义以养利”[9](卷3),“义”成为养“利”的手段。
获利的合理性或正当性问题,不仅在中国而且在日本都是商品经济观的主题之一,而“重本抑末”则同样是传统经济思想的主要倾向。叶适却提出“以国家之力扶持商贾,流通货币”,反对抑商政策,认为:“夫四民交致其用而后治化兴,抑末厚本,非正论也。”[10](卷19)在他之先反对“重本抑末”者并不罕见,但对论点本身进行公然否定、从学理上指为“非正论”的则自叶适始。工商业与农业在叶适看来都是社会经济中必要的行业,商品经济应得到扶持而不是抑制。尽管他还未能从根本上改变“农本工商末”的基本理念,但其“非正论”说,标志宋人的商品经济观进入一个新时期。叶适还主张“商贾往来,道路无禁”[9](卷1),严批政府专利,“坐盐茶、榷酤及它比、巧法、田役、税赋之不齐以陷于罪者,十分之居其六七矣。故曰比三代之刑为重”[9](卷2《国本上》),要求改变政策。
叶适对工商业的重视,不仅表现在反对重本抑末和夺商专利方面,而且提高到欲使工商业者参政议事、进入统治集团的程度,“其要欲使四民世为之,其理固当然,而四民古今未有不以事。至于烝进髦士,则古人盖曰无类,虽工商不敢绝也”[10](卷12),否定不许工商子弟为官的旧规,主张入仕无身份限制。当时已初步出现“乃至工商之子亦登仕进之途”,“如工商杂类人内有奇才异行卓然不群者,亦许解送”[11](选举14)。苏辙说过:“凡今农工商贾之家,未有不舍其旧而为士者也。”[12](卷21)这与唐代“工商之家不得预于士”[13](卷3)不同了。叶适的观点很有价值,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商人经济地位的提高,其政治要求也提上日程;但古代中国谈不上有商人思想家,因此士大夫中代表商人利益、为他们讲话的意见就很难得。从北宋范仲淹以“吾商”自喻,到叶适要求许可工商业者入仕途,证实社会经济发展促进思想观念变迁。但这还有较大局限性,是建议朝廷或教化百姓的主张,并非工商业者自觉自律的论点,不同于石门心学的町人主体性认知,也不同于西方市民阶级的自治权益要求。
值得注意的是,永嘉学派对“农本工商末”基本概念的否定和突破,叶适的学生陈耆卿在叶适死后继续光大其学,所修《嘉定赤城志》卷37《风俗门·重本业》,即采用绍圣三年(1096)当地地方官郑至道《谕俗七篇》的内容,明确提出士农工商“此四者皆百姓之本业,自生民以来,未有能易之者也”,肯定工商业均是“本”,而且是生民以来天经地义的。此为迄今所见最早的“四业皆本”史料,较认为此论最早由黄宗羲(1610-1695)提出早约五百余年(14),这是经济思想史上的重要贡献。
经济思想的主旨是强化国家的经济实力,还是考虑百姓的生存疾苦,历来也是争议的论题。商品经济的发展很大程度上有赖于民间经济实力的强盛,“藏富于民”尽管是儒家传统主张,却是从富民是富国的基础出发的。叶适发展了这样的主张,强调许民求富、保民之富,反对政府抑制,还公然为富人辩护,反对政府“抑兼并”。他说:“今俗吏欲抑兼并,破富人以扶贫弱者,意则善矣。”但不能实行,因为“小民之无田者,假田于富人;得田而无以为耕,借资于富人;岁时有急,求于富人;其甚者,庸作奴婢,归于富人;游手末作,俳优伎艺、传食于富人;而又上当官输,杂出无数,吏常有非时之责无以应上命,常取具于富人。然则富人者,州县之本,上下之所赖也。富人为天子养小民,又供上用,虽厚取赢以自封殖,计其勤劳亦略相当矣”[9](卷2《民事下》)。在叶适看来,富人的社会功能几乎达到无所不包的程度,作为国家的根基,富人理当受到保护,这也包括工商业者,他反对政府“山泽之所产,无不尽取”,要求:“因时施智,观世立法。诚使制度定于上,十年之后,无甚富甚贫之民,兼并不抑而自已,使天下速得生养之利。”[9](《水心别集》,卷2)他还多次要求除苛捐杂税,使“小民蒙自活之利,疲俗有宽息之实”[9](《水心文集》,卷1)。这种保护求富的主张,与儒家“不富不贫”的传统已大相径庭。
余英时的《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很有影响,主要讲明清时代,后也谈到“富民论”,提出苏辙《诗病五事》中的“使富民安其富”,指出:“这在儒家经济思想史上是一个比较新颖的观点。当时除了其(指苏辙)兄苏轼以外,司马光也持论相近,南宋叶适则发挥得更多。但这一新观点的广泛流行却在明代中叶以下。”(15) 实际上,宋代为富人辩护思想已经不少,这与商品经济发展和经济对政治的反抗过程相一致,成为前近代经济观的重要特征。明代丘浚说:“富家巨室,小民所赖,国家所以藏富于民者也。”[14](卷13)反对抑制富人,“乃欲夺富以与贫以为天下,焉有是理哉”[14](卷25)!并发展了“安富”的思想;王夫之则说:“故大贾富民者,国之司命也。”[15](《大正》)“国无富人,民不足以殖。”[16](卷2)类似论点更普遍,是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必然反映。
与商品经济密不可分的是货币问题。宋代的货币思想不仅在中国而且在世界经济思想史上都应有其独特地位。由于商品流通扩大形成货币供应不足被称为“钱荒”,是宋代货币问题的焦点。南宋时纸币已较为广泛地流通,“钱荒”不单纯指流通中必要货币量不足,还涉及几种货币并行的关系,南宋人的货币思想在商品经济观中有特殊价值。叶适的货币思想主要集中在《财计中》、《淮西论铁钱五事状》以及《文献通考·钱币二》等中,其反传统倾向在货币思想中也有突出表现,他说:“今之所谓钱乏者,岂诚乏耶?上无以为用耶?下无以为市耶?是不然也。”[9](卷2)对几乎众口一辞的“钱荒”提出质疑。他认为并非真的“钱荒”,从物价变化考察铜币购买力来看,不是“钱重物轻”,反倒是“钱轻物重”,他说:“今日之患钱多而物少,钱贱而物贵也明矣。”他考察历代米价变化来证明“天下百物皆贵而钱贱”,认为这是“方今之事,比于前世,则钱既已多矣,而犹患其少者”的原因。即物价上涨的普遍要求,使不断扩大的铸币量依然不能满足需求,铜币购买力下降,钱多物少,必然形成钱贱物贵,钱多反而物贵。这完全不同于传统认识,转而辩证地观察货币量与物价变动的关系,比单纯从货币绝对量看问题要深刻得多。他进一步提出,尽管钱的绝对数量并不少,而实际流通量却不足,主要原因是纸币的发行排斥了铜币,使之退出流通所致。他指出由于钱币不足“造楮以权之”,形成“凡今之所谓钱者反听命于楮,楮行而钱益少”,所以“大都市肆,四方所集,不复有金钱之用,尽以楮相贸易”;结果是“皆轻出他货以售楮,天下阴相折阅,不可胜计。故今日之弊,岂惟使钱益少,而他货亦并乏矣”。他认为纸币的流通,加速了本来就不能满足流通需要的铜币退出流通领域;他不仅认识到铜币为纸币所驱,而且指出这是一种必然规律,“虽然,壅天下之钱,非上下之所欲也,用楮之势至于此也。赉行者有千倍之轻,兑鬻者有什一之获,则楮在而钱亡,楮尊而钱贱者,固其势也”[17](卷54)。——这就是“劣币驱除良币”规律!货币理论史上的“格雷欣法则”,被认为是16世纪英国人格雷欣(Thomas Gresham,1519-1579)首先发现的,实际上,叶适早于西方人三百余年就阐述了这一规律!这是中国人相当重要的贡献。比他稍晚的袁燮(1144-1224)也认识到此规律,他说:“臣窃观当今州郡,大抵兼行楮币,所在填委,而钱常不足。间有纯用铜钱不杂他币者,而钱每有余。以是知楮惟能害铜,非能济铜之所不及也。”[17](卷273)并行几种不同货币,就会呈现上述规律。中国历史上很早就有人接近对上述规律的认识,如汉代贾谊《新书》卷4:“奸钱日繁,正钱日亡。”南北朝时颜竣也指出:“若细物必行,而不从公铸……五钱半两之属,不盈一年,必至于尽。”[18](《颜竣传》)但都不及叶适“不知夫造楮之弊,驱天下之钱”、“楮在而钱亡,楮尊而钱贱”、“楮行而钱益少”等更明确。
总的来说,以叶适为首的浙东学派的商品经济观具有顺应历史发展和顺乎经济自身发展规律的趋向,开启了经济思想发展的新时期。浙东学派的“经世致用”之学为后世继承发展,明代泰州学派创始人王艮的学问被称为“百姓日用之学”,其主张“百姓日用即道”;明末清初南方的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即所谓“三大启蒙思想家”,在商品经济观方面也都提出了各自的主张或见解;清初北方的颜李学派也力倡实学,讲求“习行经济”之学,传统中被轻视的“工艺之术”得到重视,并作为漳南书院研习的“四科”内容之一。明末清初的实学思想家的商品经济观明显有承继宋代浙东学派的倾向,姑且不论黄宗羲“工商皆本”说与宋人学说的关系,像叶适要求容许工商业者入仕途一样,颜李学派的王源也主张改变“商贾之不齿于士大夫”状况,“使其可附于缙绅也”。他还提出:“本宜重,末亦不可轻。假令天下有农而无商,尚可以为国乎?”要求:“使商无所亏其本者,便商也。”[19](卷11)笔者认为这些主张对于中国社会步入近代奠定了一定的思想基础,但却难于彻底冲出传统罗网。
石田梅岩的经济观具有明显的伦理倾向,他提倡勤勉敬业、恪尽职守,主张节欲与赢利统一,将商人的思想学术化、伦理化,并上升到宗教观念的高度,以阐释士农工商各行业平等与商人获取利润的正当性、合理性,与市民社会的要求相适应。日本经济思想研究者指出其“倡导正直、俭约为中心的经济合理主义”(16)。“商人之道”、“正直”、“俭约”、“职分”、“义利”等等都是石田梅岩商品经济观的基本概念,要弄清其具体含义,不能仅分析这些“抽”出来的概念本身,而必须重点考察其《都鄙问答》、《齐家论》等原典。结合文献与其他材料来理解和研究,才能较为准确地把握其实质内涵和思想特征。
“商人之道”是梅岩商品经济观的核心,《都鄙问答》卷之一《问商人之道之段》,集中阐述其“商人之道”的基本论点。他说:“若言商人其始,自古以其有余易彼不足,以互通有无为本也。商人精于计算,若致今日之渡世者,一钱不可谓之轻。以此为重而致富,乃商人之道也。”商人不可太贪心,这样就可化作“为善”,因为“通用天下之财宝,若万民之心得安,则与天地四时流行、万物长育相合。如此而虽至积富如山,不可谓之为欲心也。”无“欲心”“则达天下至公之俭约,合乎天命而得福。……且当守御法敬谨自身,虽为商人,徜不知圣人之道,虽同是赚钱,却赚得不义之财,当至断子绝孙也。如诚爱子孙,当学道而致荣。”所谓“商人之道”的关键是一个“道”字,即“圣人之道”,要赢利也要守道,这就将商人获商利的合理性与遵循“圣人之道”有机结合起来。“道”的要求,在儒家学说中是被屡屡强调的,如《论语·卫灵公》:“君子谋道不谋食。”《论语·里仁》:“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而行之,不处也。”《孟子·滕文公下》:“非其道,则一箪食不可受于人。”那么,“道”与“利”又是怎样的关系呢?来看梅岩一段问答:
曰:“商人多贪欲,每每为贪欲之事。夫对之施以无欲之教,犹如令猫守鱼。劝彼进学,亦属无用。欲施之以无用之教,汝非持歪理而可疑者乎?”
答:“不知商人之道者,专意于贪欲而至家亡;若知商人之道,则离欲心勉以仁心合道为荣,以之成学问之德也。”
曰:“若如此,教其卖物不取利,仅以本钱出售乎?习者外则以不取利为学,内则实教其取利,此乃反教其为诈者也。……商人无利欲,终所未闻也。”
答:“非诈也。请详听非诈之由。有仕君者,不受俸禄而为仕者乎?”
曰:“断无此事!孔孟尚言不受禄为非礼,是乃因受道而受,此者,不可谓之欲心。”
答:“卖货得利,商人之道也。未闻以本金出售而称之为道者。……商人之取卖货之利,与士之食禄相同。商无利得,如士之无禄。……商人当思正直,与人为善,和睦相处,此味无学问之力而不可知也。然商人却常嫌学问无用,当如之何?……凡鬻货曰商,如此则当知卖货之中有禄。故而,商人将左之物过手于右,亦为直取其利,非曲取也。……商人由直取利而立,直取利者,商人之正直也。不取利,非商人之道也。’……”
以上出自《都鄙问答》卷之二。梅岩肯定“不取利非商人之道”,又要求按照“正直”的伦理标准取利,即儒家主张的“以义取利”,这与中国许多思想家的主张是一致的。针对商人有欲心而且做欺诈得利之事的质疑,梅岩提出应当教导商人求学以达正直取利,这就是“商人之道”。正如《论语·述而》中孔子所说的:“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梅岩强调町人社会中学问之必要性。在肯定商人合理取利的同时,他还将此同武士获得俸禄置于同样天经地义的地位,并举孔门弟子子贡经商并非无道之例,佐证自己的观点合于圣人之道。
“正直”是梅岩经济伦理的基点,也是商人获利的准则,“以义取利”就是他的“商人之正直”。要实现“正直”,不仅在取利方式上而且在利润率上都要“合理”。这个“理”不仅具有伦理性质,而且还有认识市场规律的内涵。来看以下问答——
曰:“本金若干其利几何,当天下定一,为何伪称亏本以高价出售?”
答:“卖货必依时价行情,以百钱所进之货物,若只得九十钱必不出卖,是乃亏本也。因之百钱之货物,有时亦以百二三十之价出售。行情上涨生意兴隆,行情下跌则买卖萧条,此乃天之所为,非商人之私也。天下定物之外时有失常,失常,常也。……本金如是取利多少乃难知之事,此非伪也。……士农工商者,助成天下之治也。四民有缺,则无以为助。治理四民,乃君之职也;佐助君主,则四民之职分。士者,乃原本有位之臣也;农人,乃草莽之臣也;工商,乃市井之臣也。为臣者侍佐君主,乃为臣之道;商人买卖者,乃佐助天下也。工匠得工钱,乃工之禄也;农人耕作收获,亦同士之俸禄。天下万民若无产业,以何而立?商人卖货之取利,亦是世间公认之禄也。夫何独以买卖之利为欲心而云无道,厌恶商人而与之断绝哉!何以贱商人之生计而嫌之耶?……买卖得利是为定规,若得定利而尽其职分,则自成天下之用。商人不受利,则其家业难以精勉。吾之禄乃买卖之利,故有买者入乃得受之。……吾所教,乃教商人有商人之道,非全教士农工之事也。……”
曰:“如是,则商人如何得心致善?”
答:“为武士者,侍其君而不肯用命,难称其为士;商人若亦知此,吾道明矣。若对养吾身之买主以诚相待不怠慢,十之八九得合买主之心。合买主之心,再精勤于其业,何必担心度世艰难?且首要恪守俭约,……想得不义之钱,不知子孙将绝。当今之世何事亦当照光洁之镜,以士为法。……为世人之镜者,士也。……商人取二重之利与暗钱,知对先祖不孝不忠,心想士亦为劣,言商人之道何如?有以士农工之道为替。孟子亦云:道,一也。士农工商共为天之一物。天,岂有二道哉!”
此亦出自《都鄙问答》卷之二。商利不是“规定”的,而要依时价行情即市场规律而定,此“乃天之所为,非商人之私”。《孟子·滕文公上》说:“夫物之不齐,物之情也;……巨屦小屦同贾,人岂为之哉?”此“物之不齐,物之情也”,与彼“失常,常也”,有异曲同工之妙,都是对市场调节物价的功能的认识。梅岩强调不应“取二重之利”,认为这就是“非”,就是“不义”,违背“商人之道”必须杜绝,否则要断子绝孙。他认为“不义之禄”和“非道之欲”都是应当“去”的,分析“商人多不闻道,故有此类事”,是“不知天罚者”,要教之以“五常五伦之道”,可见其经济伦理明显脱胎于儒学。
梅岩对市场功能和商业价值都予以了阐释,并从社会结构功能来阐释“四民”存在的理由,肯定工商业的社会作用。此前也有人从“通有无”角度肯定商业作用,但对商人的鄙视并未改变;而梅岩认为士农工商的“职分”均受于天,都是社会中不可或缺的,商人获利如武士得俸禄一样都是天经地义的,“这在近世经济思想史上,确实是很伟大的业绩”(17)。不过,“士”在梅岩看来依然是尊贵的,是“世人之镜”,其他行业应效法。各种职业的人都要“精勉其业”,恪守其“道”,抑制“欲心”。梅岩改变了“尊士抑商”、“贵谷贱金”等传统观念,这与中国唐宋以来主张“四民”并存、反对“抑末”的思想变迁颇为相似。“重本抑末”是中国经济思想史的重要范畴,从商鞅“能事本而禁末者,富”,韩非“使其商工游食之民少而名卑,以趋本务而外末作”,发展到唐代崔融“不欲扰其末”、白居易“别四人之业,使各利其利焉”(18),直到前述宋人提出“与商贾共利”、“一切通商”、“农末皆利”、浙东学派“抑末厚本非正论”、“四业皆本”等论点,商品经济观的确发生着与商品经济兴盛相应的变化。这一变化,在宋代与江户时代凸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成为两国近世社会的共有现象。
在“正直”之外,“俭约”同样是梅岩经济观的重要概念。《齐家论》(即《俭约齐家论》)是其阐述“俭约”的核心文献,名称即透出浓厚的儒学特色,也是将修、齐、治、平之说与其经济合理主义有机结合的产物,《齐家论》有云:“吾之所愿者,一人亦能知五伦之教。若为事君者,当以克己奉公不辞劳苦勤勉其职为先,所得之事为后,以尽其志。”他论“俭约”,源自儒学“子曰:礼,与其奢,宁俭”。“俭约”在他看来是与身份相应的:“若知身份之相应,俭约为常也。”即各行业均当依其“等”而“不逾等”,否则“过分,皆奢也”。上述均出自《齐家论》上篇,与孔孟学说可谓一脉相承。《论语·述而》有:“奢则不逊,俭则固。与其不逊也,宁固。”《孟子·尽心下》记:“养心莫善于寡欲。”梅岩强调俭约时注重与职业身份相应,要求人们知足安分。《语录》卷10记载其:“不越贵贱尊卑之品,有财宝而守法,实则俭约也。”他的经济观等级性特征鲜明,与“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等级制要求很近似,而等级制的分配与消费是封建制度的重要特征。
《齐家论》下篇论述“齐家治国,俭约为本”,梅岩专作《俭约序》:“俭约乃节用财宝,应我之分,无过与不及,舍物费之谓也。因时合法,用之事成,天下治理,安稳太平。……士农工商,各应尽心于己业,……勤于职守,日夜不怠,是为治世也。”梅岩在论俭约的同时,仍然屡屡强调“士农工商,各得尽心于己业”,职业的分工是“天命”,“不知己分”就有可能“难逃天罚”。《都鄙问答》卷之一有“合天命乃得福”之说,《语录·补遗》记述其说“为商人者,乃天命之所为”。他将职业与“天命”相联系,赋予勤勉和俭约以宗教意义,有类似于“新教伦理”的涵义,蕴含韦伯提出的建立在“天职”观念上的合理性经济行为导致资本主义产生的价值。R.N.Bellah在《日本现代化与宗教伦理》的“结论”中指出,梅岩有很强的宗教性动机,与西欧新教伦理相似,“日本的宗教,强调勤勉与节约,要求对神圣者履行义务,对邪恶的冲动或欲望秉持自我净化,由此赋予勤勉和节约以宗教性意义。这样的伦理,对经济的合理化极有利,它是韦伯有关新教伦理研究的主要点,我们应当说在日本也同样有利”。
“俭约”作为梅岩“商人之道”的重要内涵,与“正直”密不可分,都是士农工商的“共通之理”,并具有宗教伦理色彩。他于《齐家论》下篇说:“或言,町家之事琐细,难用大道言之。吾以为不然。自上至下,职分虽异,其理则一。得心而行节俭时,则家齐、国治、天下平。此焉非大道乎?……《大学》所谓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以修身为本。修身何有士农工商之别!”“故士农工商虽职分各异,会得一理,则言士之道与农工商通,言农工商之道与士通,何必四民之俭约要分论耶?言俭约无它,乃天生之正直也。天降生民,万民皆天之子也。故人乃一小天地,本无私欲,故我物即我物,人之物乃人之物,贷物收领,借物返还,丝毫不为我私,此乃正直也。若行此正直,世间一同和睦,四海之中皆兄弟也。”“私欲虽害世,不知此之味而成俭约,皆至吝,为害甚也。吾所言由正直至俭约,则至助人。”这些话的关键在于阐明“俭约”与“正直”的关系,并说明“由正直至俭约”,区分了俭约与吝啬,要求去除私心私欲。他不止一次讲“随法”就是俭约,这个“法”既是“物”之所具有的,也含幕府“实定法”之意,反映了梅岩思想的多重性与过渡性质。
中日近世的商品经济观不仅影响两国步入近代化,而且作为深层的民族文化积淀,对今天都有影响。如果说,“儒家文化与现代化”或“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成为研究热点,那么直接支配人们经济行为的经济思想尤其是与市场经济机制的建立和发展相伴随的商品经济观,无疑值得下大气力进行研究。
我们知道,石门心学同浙东学派一样都是伴随商品经济发展和社会变革而产生的,而且同样具有区域经济文化的鲜明特色。心学兴起于关西并非偶然,江户商人与幕府及奢侈商业联系紧密;京都、大阪则不然,京都是手工业大都市,大阪是商业贸易中心,商业发展的自由度与商人精神的活跃性与江户都有差别,比较适应心学的产生。石田梅岩个人的素质、经历、学识、热情等等,为心学的创始提供了条件;新兴町人阶级在理论与学问上的渴望,构成心学问世的特有需要。贝拉认为心学“对明治维新而言,在民众的心理准备这一点上是重要的。但是,通过商人阶级的运动,心学并未为商人求得直接的政治权利,而接受武士为政治的指导者,使商人在经济领域中与武士的角色同化”。不过他也指出中日两国存在许多不同,心学的宗教伦理适应商人需要而广为传布,中国则不然;两国的一些用语或概念可能相同,但强调点甚至基本价值有重大差异,而且认为梅岩“决非典型的町人”,不应将其视为封建主义之敌和对市民阶级政治自由的拥护者(19)。梅岩确实很少批评幕府,也明显尊崇武士,其经济观中保有维护等级制的特色,其对获取商业利润合理性的论证,并不妨碍其忠君尽孝,其思想特色是修、齐、治、平理念与经济合理主义合一。其实,诸学并存而又返本开新的思想倾向反映了社会转型时期的特征,从上述叶适的思想轨迹中也可略见一斑。
浙东学派和石门心学在两个方面的贡献颇值得重视,即类似马克斯·韦伯阐述资本主义兴起的要因——新教的“天职观念”和“世俗内禁欲主义”。韦伯认为正因为儒教缺乏这些,故而不能促进资本主义的产生,而中日近世的商品经济观足以提供反证。关于“世俗内禁欲主义”,中国历朝历代几乎无不强调节俭制欲,“黜奢崇俭”是几千年的主流观念,叶适则不仅仅反对奢侈,而且重在反对政府聚敛,指责“盖财以多而遂至于乏”[9](卷15)。但赋予“俭约”从经济伦理到治国方略的内涵,并促进后世社会形态演化和经济高度增长的则是石田梅岩。他表述为“天下至公之俭约”,在《语录》卷一说:“俭约者,为天下之利也。”这样的“利”,大概就体现为近代以来日本经济的高速发展得益于高储蓄。而中国要求有利于民间财富增加和积聚的主张,表现为浙东学派以来的“求富”、“保富”、“安富”等论点和发展商品经济的思想。不过,中国历史上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商人思想家”,也很少有工商业者记载的思想文献,即使到明清时代有了一些,也多以商路里程等技术层面的内容为多;中国的商品经济再发达,也有与自然经济相适应、相补充的一面;中国的工商业受到政府的严格控制,民营经济发展有限;中国的经济伦理更多的是具有社会性而非宗教性。如此等等,都是与日本不同的。
对于“天职观念”,梅岩强调“职分”是“天之所命”,天经地义,人必知己之职分,并要谨敬地“守”、勤勉地“行”,以求尽职。《都鄙问答》卷之二:“不知职分劣于禽兽。犬守门、鸡报时。”《语录》卷九:“侍则侍、农人则农人、商卖则商卖人。职分之外若另有所望,则是违天,若违则背天命。”恪谨天命知足安分的职分观,既是发展家业、维系社会的条件,又是尽忠国家的基础,即《都鄙问答》卷之一所述的:“使知天所命之职分而力行时,身修、家齐、国治而天下平也。”柴田实认为梅岩“总是举出世袭职业阶级(士农工商)的原理是无疑的,他极力倡导的是正直之德,否定不正当的利益,强调正直与俭约是紧密相连的”(20)。心学的商品经济观是对町人自觉自律的要求;而“天职”在浙东学派那里则是以“本业”来表述的,要求朝廷将士农工商都视为“本”即天经地义的正当职业,尤其主张工商业者不应再受歧视和抑制,这对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和社会形态的演进无疑是有益的,但并非是工商业者主体性认知的结果。
赢利是商人的天职,梅岩也指出商人会从欲心出发赢利,这就需要“道”来约束,即“商人之道”。反对从利欲出发谋利,而要求“以义取利”,这也正是儒学尤其是宋人较为普遍的意识,叶适则表述为:“成其利,致其义。”[10](卷22)梅岩的“取之有道”,还与他对社会结构和“天下人心”的整体认识分不开,石门心学作为“町人的哲学”,具有“道德性实践之实学”的普遍意义,梅岩多次讲:“士农工商,其道一也。”因此,商业利润的获取,需要兼顾各方利益,商人得利万民心安,“顾客与商人共立的经济伦理,或共心一同的商人伦理,能够表现为今天‘共生’的经济伦理”(21)。Tessa Morris-Suzuki著《日本的经济思想》认为,梅岩的理论“显示出与欧洲的古典派经济学者的著作中所见的启蒙性的私益概念,有着某种意味深长的相似性”。还说:“‘商人之道’也包含着培育对于人类本性的深刻洞察力。得以洞察时,商人能够理解何为真正的利益。所谓真正的利益,不是贪欲得以一时性满足,而是勤勉、俭约或所有经商赢利中提供和需求最大限度的价值之存在。”(22) 要求取利非一时性、非一行业的观念,可称为“普遍性经济合理主义”。
在日本历史上,石门心学的经济观、怀德堂的道德论以及涩泽荣一的“论语加算盘”,成为促进经济成长和近代化发展的思想动力。石田梅岩逝世后其高足手岛堵庵(1718-1786)继承并发展了梅岩的学说,中泽道二则将心学传播到江户,传播对象也从町人发展到武士和农民,一些藩的统治者也受其影响。心学基本属于都市运动,而都市容易受到西欧化和产业革命的影响,传播也很快,18世纪末各地的心学讲舍逐年增加,到19世纪30年代已近两百所。心学不仅通过公开讲释,也通过大量印制小册子扩展影响。许多商家店铺的“家训”“店则”都与心学思想有关,可证心学的普及及其对商品经济与商业伦理的作用。一般认为明治维新以后作为运动的心学逐渐衰弱,但据明伦舍编辑的《石田先生门人谱》,迄1880年心学门人有三万六千余人,心学商品经济观至今对日本的商业理念和市场经营都还有影响。
山本七平的《日本资本主义精神》以很大篇幅讲述石门心学及其影响,并联系昭和时代的现实提出“昭和享保与江户享保”之论;稻盛和夫与梅原猛也著书充分肯定梅岩的“商人之道”,并呼唤回归这样的资本主义精神(23)。梅原是名教授,而稻盛是著名企业家,其京瓷集团的经营哲学和企业文化都非常重视传承这种精神。日本中小企业对石门心学更是尊崇,从江户商家到今天京都的零售商,多把“商人之道”视为律己的准则。2000年10月15日,国立京都国际会馆举办了有一千三百多人参加的“石田梅岩心学开讲270年纪念研讨会”,R.N.贝拉教授作了题为“心学与21世纪的日本”的讲演,可见心学影响之深远。由于“平成不况”和“泡沫经济”,日本社会中以不正当方式牟利的企业行为时有发生,一些有识之士呼吁企业经营者重新学习“商人之道”,这能够从一个方面证实心学的现代价值。
浙东学派的商品经济观,同样对后世产生积极影响。笔者在以往论文中考察清代浙东学派代表人物黄宗羲,指出其不仅与宋学有学术渊源,而且有赴日经历;浙学从宋代叶适、经明代王阳明直到清初黄宗羲,对商品经济都有独到的见解。浙人无安土重迁观念,却有出外经商打工或漂洋出海谋生的传统,如19世纪的“宁波商帮”被认为是继徽、晋两大商帮之后势力最强的地缘性商人群体。笔者注意到他们不同于徽商、晋商等与官府有着紧密联系,而是重在拼经济实力和经营智慧。他们不仅经商,还兴办产业,而且积极投资于教育或公益事业,同时也注重自身的文化修养。直至今天这样的传统对于促进当地市场经济的发展还起着作用,前些年声名很大的“温州模式”就是其体现;温州人还敢于利用法律武器在国际贸易中捍卫自己的权益,都是其商品经济观与国际“接轨”的体现。
然而,不应回避日本经“明治维新”而成功步入近代化历程,中国历“戊戌变法”却未能跻身近代世界强国的史实。自甲午海战“学生打败先生”震惊大清朝野,一代代国人就不断深思、探求、寻觅两者的同异缘由。毋庸讳言,影响两国近代化历程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但经济无疑是基础性要因;而经济思想既源基于现实经济状况,又直接引导和制约经济政策的制定和经济活动的开展,其作用远非其他文化、宗教因素可比,可惜的是从经济思想史的学科界域进行的系统性比较研究还十分薄弱。由于两国社会制度、文化心理、民族特性诸方面的差异,经济思想对两国近代化的历史转型与社会发展产生的实际作用是不同的,这不仅影响了两国后来的发展道路,而且积淀为两国国民不同的思维习惯与经济观念。因此,比较研究两国的经济思想具有特别意义。
例如,浙东学派能够促进地方经济发展不等于能够完成社会形态的演进。自宋至清,浙东学派的商品经济观,无论是主张“四业皆本”还是要求“许民自利”,以及对安富、理欲、货币等的思想诠释,确有发展却谈不上实质性突破,原因就是社会经济形态未发生根本性变迁。笔者反复申明,中国反映商品经济发展要求的主要是官员或学者,多是建议朝廷或教化百姓,从而局限性较大,无法成为商人主体意识的自觉,因此不同于石门心学那种町人自律的内在需求。差异源于两国基本的社会结构、制度基础与思想文化差异,中日商品经济观尽管有许多类似论点,但针对性与内涵实质却是有差别的,对两国近代化转型的影响也不同。
从历史条件来看,中国直至推翻帝制为止专制政体的力量始终强大,商人没有发展成为类似西方市民阶级那样的独立阶级,不足以同封建政权抗衡,这是由中国的政治体制和经济结构决定的。仅以人们津津乐道的徽商所在地歙县为例,清代就有进士296人,状元5人,榜眼2人,探花8人,一些商人在致富之后弃贾业儒仕进,买官置地或奢侈消费而不是扩大再生产,这些往往成为商业资本的主要投向;地主、官员、商贾角色互换,三位一体,与日本强调俭约、积蓄的原始积累不同。中国的大商帮多与官府有关系,并不是像石田梅岩所言把经商视为一种“天职”,而主要是作为赚钱手段。出现的商书如《商贾便览》、《士商类要》等,也多是技术性而非思想理论性读物,很难产生商人的独立精神。经济思想中强调发展工商业或主张百姓求富等论点,主要是为统治者进言献策,以缓解贫富矛盾和社会危机,难以像心学的“商人之道”那样成为步入近代社会的思想基础。有学者认为中国古代没有代表“市民阶级”的启蒙思想,“中国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启蒙思想只能产生于鸦片战争以后”[20]。
在中国,商品经济与自然经济的兼容互补,和政府严格控制工商业,使之成为国家财政的重要来源的政策,必然限制民营经济的规模与发展,加上帝国主义列强的入侵掠夺,经济困顿,民不聊生,近代化步履维艰。另外,与宋代较为宽松的文化氛围不同,清廷实行思想文化专制政策,经世实学让位于乾嘉朴学,使得自宋以来的经世致用之学渐趋变质,考据训诂之学与今古文之争占据学术文化的很大板块。日本则不同,商品经济和文化主导权逐步掌握在町人手中,心学普及成为走向近代化的社会思潮,通过下级武士的倒幕运动,日本走上了近代强国之路,尽管埋下了诸如军国主义等等隐患。中国的儒生至多如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在抵御外侮和拯救民族危亡中依靠光绪皇帝变法维新,终归于失败。
限于篇幅应当终结了。需要补充的是有关石门心学经济思想的研究,最全面系统的还是竹中靖一的《石门心学的经济思想》,可惜书中没有研究中日经济思想的联系,笔者曾撰文进行专门考察[21]。竹中是田岛锦治的高足本庄荣治郎的学生,而田岛先生在京都大学首开中国经济思想讲席,其著作《东洋经济学史——支那上古的经济思想》(1935)就是本庄根据他的讲义等编辑而成的。本庄在日本经济史、经济思想史研究上很有成就,可惜也没有研究中国,只有竹中的学兄出口勇藏1946年出版《孙文的经济思想》。简言之,无论是石门心学本身还是其研究者,其实都与中国不无关系,可惜有关中日经济思想渊源流脉及其演进以及东亚经济学术史等重要课题,迄今尚未得到足够的重视,而世界经济学说史至今基本都还只是西方的内容!笔者近期在东京大学、一桥大学诸处的讲演中提出上述问题,并引起震动,企盼更多学者的共同努力。
注释:
①“近代化”与“现代化”在英文中都是" modernization" 。本文依据所研究的时代与内容并参考中文和日文的表述特征,主要采用前者,但谈到诸如“现代化理论”等专用概念时不另改动,特此说明。
②分见《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第1卷,1993年2月;高崎经济大学学会:《NOVITAS》第3号《特集:东洋思想与现代》,1994。
③叶坦:《宋代社会经济结构的变迁》,《江海学刊》1990年第5期;《宋代工商业发展的历史特征》,《上海社科院学术季刊》1991年第2期等。
④两者的异同,参见笔者合作研究的、川口浩主编的《日本の經濟思想世界》,日本经济评论社2005年版,第450-454页。
⑤分见《欧阳修全集·居士集》卷45,《李觏集》卷16,《净德集》卷3,《苏轼文集》卷35。
⑥古田绍钦等编:《石田梅岩の思想—“心”と“儉约”の哲学》,べりかん社1979年版,第12页。
⑦分见《集义和书》卷8、《益轩全集》卷3、《政谈》卷1。
⑧古田绍钦等编:《石田梅岩の思想—“心”と“儉约”の哲学》,べりかん社1979年版,第39页。
⑨古田绍钦等编:《石田梅岩の思想—“心”と“儉约”の哲学》,べりかん社1979年版,第82页。
⑩竹中靖一:《石門心学の經濟思想》,ミネルゥ”ア書房1962年版,第95、109页。
(11)参见柴田实《梅岩とその門流——石門心学史研究》,ミネルゥ”ア書房1977年版,第3-23页。
(12)R.N.Bellah著,堀一郎等译《日本近代化と宗教倫理》,未来社1962年版,第199、202、211页。
(13)参见叶坦《论“利”》,《中国经济史研究》1998年第4期。
(14)叶坦:《富国富民论——立足于宋代的考察》,北京出版社1991年版,第183-185页。
(15)余英时:《现代儒学的回顾与展望》,中文版载《中国文化》第11期,1995年7月。他注释说明:“关于这一问题,可看叶坦《富国富民论》,北京出版社1991年,第二章第四节《为富人辩护的新观点》85-92页。”还说1994年4月他在东京大学讲演,笔者送他拙著“有助于此文的修订,特此致谢”。
(16)岛崎隆夫编:《近世日本經濟思想文選》,敬文堂1971年版,第90页。
(17)竹中靖一:《石門心学の經濟思想》,第308页。
(18)分见《商君书·壹言》、《韩非子·五蠹》、《全唐文》卷219、《白香山集》卷47。
(19)参见《日本近代化と宗教倫理》,第250、225、210等页。
(20)柴田实:《梅岩とその門流——石門心学史研究》,第53页。
(21)芹川博通:《經濟の倫理——宗教にみる比较文化论》,大修馆书店1994年版,第323-324页。
(22)Tessa Morris-Suzuki著,藤井隆至译《日本の經濟思想》,岩波书店1991年版,第47、48页。
(23)稻盛和夫、梅原猛:《回归哲学——探求资本主义的新精神》,学林出版社1996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