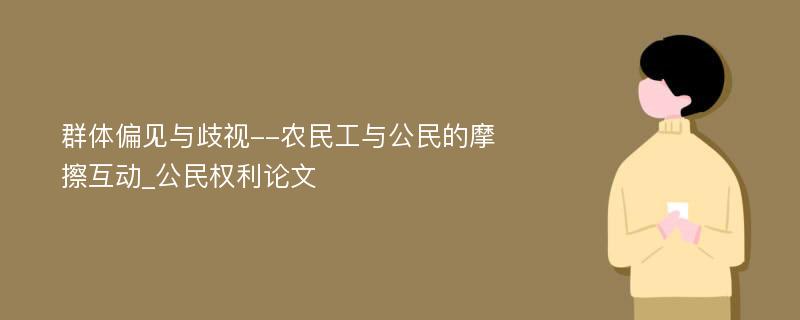
群体性偏见与歧视——农民工与市民的磨擦性互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互动论文,磨擦论文,农民工论文,偏见论文,群体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国外历史上,通常大规模的移民会引起移民与移入地国家和地区居民的磨擦、冲突。我国的民工潮引发了与国外移民遇到的类似问题,即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的磨擦性互动问题。
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的摩擦性互动实录
农民工进城后与城市居民的融合,是城市秩序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也是城市化的一项重要内容。1997年零点调查集团对京沪穗汉4城市各255户居民入户面访,发现城市居民对外来务工经商人员正负感受之比为4.1:2.4,正面感受居于优势。有16.5%的人有“讨厌、看不起的感觉”。该集团在持续3年对京沪汉等地外来人口的调查,发现有18%的外来务工经商人员感受到当地居民的强烈歧视,45%的外来务工经商人员感到有时会受到歧视或会受到某些城里人的歧视,有2/3的外来务工经商人员表示他们不敢也不愿与城里人交朋友。[1]对农民工在城市的适应问题,南京大学社会学系分别于1998年暑假、1999年寒假和暑假作了专题调查,采取标准化访谈的形式,总共收集到农民工个案资料315个。这些个案说明了农民工在与市民的互动中,依然存在着许多障碍。有67%的农民工谈到了在与城市人交往过程中,存在着令农民工感到疏离的社会气氛——对农民工的偏见与歧视。
[个案1]陈明亮,男,20岁,湖南人,现在苏州郊区某木料加工厂打工。
大城市里的人特别瞧不起外地来的打工人员,在他们看来,我们生来就跟做坏事联系在一起。我们很想同这里的居民保持良好关系,谁也不想总在一个被别人瞧不起的环境中生活。就像苏州人,有些叫法真是令人哭笑不得,不管是北方来的民工,还是南方来的民工,都管叫“江北人”,而湖南不是在苏州南边吗?这个称呼就代表着一种低下的社会地位吧!只要我们一开口,外地口音一出来,这里人就会露出不屑的神情,为这,我们有些人就学当地口音,想做个真正的当地人。我现在有一个朋友,他能讲很标准的苏州话,为此也自豪过。但有时一些知道他原籍的苏州人就会讥讽他,说“现在倒真的快成为苏州人了嘛?”每次他听到这些都会非常的痛苦。他现在已经不愿再学苏州话了,这对他是一种耻辱。从这些原因,你就可以看出来,为什么我们与当地人的关系这么差。(调查员 张静波)
[个案2]王建民,男,安徽巢县人,34岁,在上海打工。
我在上海差不多已呆了4年,其它大城市也去过几个。凭良心讲,我还是想回老家,大城市的日子我总觉得不自在。其实,上海人挺排外的,北京也是,大城市都有那么一点,对外地来的,尤其是像我们这样的民工特别瞧不起。城里人总觉得外地民工脏、傻,没见过世面,好骗,好欺负。我说件事儿吧:我有一个远房表姐在上海给人做保姆,她干得很好,做人又老实。一年前她做的那家人是一家知识分子,有一次家里少了几百块钱,主人就怀疑我表姐,话里带刺。我表姐忍了几天,实在耐不住,就让主人去报警查个清楚。第二天,主人却把我表姐给莫名其妙地辞了。表姐气不过,找到里弄讨个公道。后来总算搞清楚了,是那家的儿子偷偷拿了钱去打电子游戏,一听要报警就跟家里说了。他妈却怕丢人,就把我表姐辞退遮丑。事后那家人竟连一句道歉的话也不讲,女主人还丢下一句话说:乡下人素质总是差的,谁知道手脚干不干净,还叫冤枉?多气人的话,也不知谁的素质差,亏他们还是读书人呢!我们因地位低下而遭到人格上的侮辱几乎是司空见惯的。(调查员 陈舒)
偏见与歧视的理论
从上述案例中我们见到的是一种群体性的偏见与歧视。偏见(prejudice)包含两个成份:信念和态度。偏见的信念成份叫刻板印象,即关于一个类型中所有人、物或环境的简单化的或未加证实的概括;态度部分由对于偏见对象的评价性判断构成。“因此,也许可以把偏见正式定义为以刻板印象的方式对人、物或环境作出判断。一种偏见既可能是肯定的,也可能是否定的”[2]。偏见是在缺乏足够证据的基础上,根据某个人的群体身份而下的定论。在日常生活中对农民有着身份偏见的人认为,城市居民比农村居民在素质上要高出一等。他们将对农民的偏见投射到农民工身上:农民工进城抢了城市人的工作;农民工素质低、愚昧无知,破坏了城市的秩序;农民工是一个犯罪率较高的群体;等等。偏见本质上是一种不符合事实的态度与看法,可以是袒护的(如对城市居民),也可以是敌视的(如对农民工),但总是固执的,即这种先入为主的观念总是难以改变的。
偏见形式上针对个人,实质上针对群体。针对个人,也总是将他当作某一群体或类别的一分子。偏见是一种归类过程,是一种“错误而僵死的概括”。偏见对于持有它的群体有特殊的作用:首先是“替代”,即把愤怒的情绪发泄在另一并不相干的群体身上。如失业下岗工人自己不能顺利就业时,就会将农民工作为“替罪羊”,认为是农民工抢了自己的饭碗。其次,持偏见的人把自己的错误推到别人身上,这种“投射”是偏见的真实内容的来源。人们由于害怕承认自己的内心感情,于是把这些情感归于那些与自己完全不同的人们身上的方法来否认这些情感在自己身上的存在。[3]如有些市民对自己不适应社会竞争、文化素质差感到心理恐惧,他们就将这些弱点投射到农民工身上。再次,是提高自己的地位。通过对偏见对象的贬低、打击,给自己找一个更低的参照群体,以满足自己的心理平衡。
歧视(discrimination)是指某人以优越群体成员的身份,不平等地对待另一群体的人的行为。“歧视是指由于某些人是某一群体或类属的成员而对他们施以不公平或不平等的待遇”[4]。偏见是一种基于某种信念上的认识态度,歧视则是一种基于偏见上的外显的行为。不能说有偏见的人必定有歧视行为,但一般情况下两者相连。默顿在研究美国的种族主义偏见时曾指出,偏见态度与歧视行为有四种可能结合:(1)非偏见非歧视者,称全天候无偏见者。(2)非偏见歧视者,或称良好气候下的无偏见者。虽然他们自己并无偏见,但由于社会尊严、选举、生意等原因而支持歧视。(3)偏见非歧视者,或称良好气候下的持偏见者。他们勉强执行非歧视政策。(4)偏见歧视者,称全天候的偏见者。大多数人属于第二或第三类型,即属于那些行为受到社会压力约束的人。[5]这一观点可以为研究我国的群体性歧视作参考。在对待农民工的态度上,具有偏见的城市人可能较多,但具有歧视行为的人要相对地少一些。具体来说,日常生活中我们见到的市民对农民工的歧视行为主要有:
(1)语言轻蔑。对所谓“低等”的人出言不逊,表现出反感和敌意。城市中不了解农村和农民的人,常常以自己城市居民的优越身份来蔑视农民工,讲一些刺伤农民工的话。城市居民对农民经常有“农二”、“乡下人”之称,明显含有轻蔑的意思。例如,南京市民对农民工的“二哥、二姐”的称呼(由工人老大哥、农民老二哥演化而来,这里突出了农民的身份,有蔑视的含义),上海地区对“江北人”的称呼(江北意味着贫困、愚昧、野蛮、落后),都是在生活中常见的歧视性语言。而有些农民工为了模仿城市人,学说当地话,以期通过语言来掩饰自己的身份。
(2)有意回避。不惜麻烦千方百计地回避躲藏他们所讨厌的人。我们经常见到这样的景象,在公共汽车上,并不拥挤,有的衣着时髦的青年人见到衣着打扮像农民工的人,有意地绕过去躲开,以显示自己身份的不同。在公共场合,有些人见到农民打扮的人,作出掩鼻的状态,嫌对方不整洁、有气味、肮脏。无知导致偏见,有些持有偏见的城市人将穿着打扮、口音举此等行为特征或生活方式都作为傲视农民工的资本,把欺负农民工当作一种安全的游戏,通过对农民工的歧视以显示自己的“高贵”地位。
(3)职业排斥。有的城市或单位,制定和奉行保护城市居民,排斥农民工的政策,明确规定农民工不得进入福利待遇较高的职业。在工作中,农民工的工资待遇、福利保障要比城市职工的低,干同样的活,享受不同的待遇。农民工只能进入城市居民不愿意从事的职业岗位。将农民工限制在低级的劳动力市场。城市居民在内心深处,担心的是农民工以其特有的素质所带来的竞争压力。从城市民意调查来看,“农民工抢了城里人的饭碗”,这种观点在城市里也有相当的社会基础。据零点公司1994~1997年连续四年在北京、上海等地的调查,“农村人进城工作,城里人有何担心”?前三年,城里人占据首位的担心是“影响城市治安”;1997年7月的调查,城里人占第一位的担忧是“冲击本地劳动力市场”达59%,对于治安的担心退居其次。[6]国外社会学者发现,有些群体的成员比另外一些群体的成员更有可能对少数民族群体产生偏见。如工人阶级中的白人往往与黑人在职业上形成竞争,所以他们往往比社会地位较高的白人对黑人更有偏见。[7]我国的群体性歧视中还没有这方面的实证研究,但这一规律是值得重视的,城市下层劳动者确实与农民工存在着某些就业竞争的状况,摩擦性互动的频率更高。现实的利益冲突是产生偏见的温床。
(4)人格侮辱。在日常生活中,城市执法人员或市民对农民工的人格不尊重。同样是骑自行车违章,警察对城市居民态度比较和蔼,但对农民工模样的人却较恶劣。农民工从内心感受到有的城市居民从心眼里瞧不起农民,在社会上身份是较低的“二等公民”。李强教授的研究表明,[8]在进城农民工所遭受的各种歧视中,虽然就业岗位和劳动报酬方面的歧视,是最具实质性的,但引起受歧视者的心理反应,却并不如他们在日常生活及社会交往中所遭受的歧视那么强。究其原因,进城农民工日常生活和社会交往中所受到的歧视,直接地伤害了进城农民工的人格和尊严,因而印象极为深刻,感受极为强烈。歧视到一定程度,被歧视者就无法容忍,会以各种形式表示反抗。
我国进城农民工由于角色转换与身份转换的脱节,他们在城市只能以准市民的身份,而不是以市民的身份存在,他们在与城市居民的互动中处于劣势地位。“一等公民”与“二等公民”的社会意识,还没有稀释。
制度性歧视的根源
群体性歧视在形式上虽然没有种族歧视那么严重,但在性质上无多大区别。它是一种建立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基础上的全方位的群体性不平等;而我国特有的“一等公民”与“二等公民”的问题,正是这种基于制度性要素支撑着的群体性不平等。我国存在的这种群体性歧视是非法律性的(政治上、法律上我国公民无论是干部、工人还是农民身份,都是平等的),在我国的主流文化中,无论是民族之间,群体之间,倡导的都是平等,是反对偏见与歧视的。但群体性歧视本质上是制度性的,在制度因素中干部、工人、农民的身份客观上是不平等的。对不同群体存在着不同的政策与制度,这是制度性歧视产生的矛盾根源。虽然我国社会改革已经20余年,在城市管理体制方面的改革也有一些进步,以户籍制度为核心的城乡隔离政策也有所松动。但对进城的农民工来说,一个根本性的事实就是:户籍制度、教育制度、保障制度、人事制度、医疗制度依旧,传统的城市管理制度仍然只承认稳定的居民,而不承认流动的农民工,依然将进入城市的农民工排斥在外。城市对农民工经济制度上的接纳和社会制度上的不接纳这一矛盾依然存在。政策与制度对具有城市户口的人与农村户口的人仍然持有双重的标准;对前者是保护,对后者是限制。农民工在城市可以“立业”,但不能“安家”。城市不能够给他一个“户口”,意味着农民工没有城市居民的身份,没有城市居民可以天然获得的一切福利待遇。哪怕农民工在这个城市已经工作和生活了数年、数十年,永远是一位无根的漂泊者,与城市居民相比仍然是“二等公民”。这是对“二等公民”的偏见与歧视存在的客观基础。
社会学家注意到了在不平等群体之间的这种摩擦与矛盾。美国社会学家萨姆纳提出,根据群体成员对待群体的立场和态度,可把群体划分为内群体与外群体。凡是成员感到自己与群体关系密切,对群体的归属感强的群体,就是内群体。内群体中的人可以产生一种同类意识,在群体内成员表现为合作、友善、互助、尊重。外群体,也称他群体,是与内群体相对应的一个概念,指凡是自己没有加入的、由他人组成的,或这群人与自己无关的群体。人们对外群体常常表现为冷漠、轻视或有偏见,尤其当内群体与外群体对立时。[9]城市居民与农民工有着鲜明的内群体与外群体的意识,分别站在各自的立场上,将对方视为一个与自己群体完全不同类的群体。市民与农民工这两大群体生存在同一空间中,表面上是有所交往的,但在心理意识上,农民工存在着高度疏离感,成为游离于城市的、既缺乏保护也缺乏约束的社会群体。
群体性偏见不是天生的,是后天形成的。在城市体制没有根本改革的情况下,长期生活在城市“福利城堡”中的市民,在天然的而不是通过努力获得的社会资源与竞争方面占据着优势,使得某些市民形成“一等公民”的身份优势意识。“一等公民”心态实际上已内化为一种城市的市民性格,许多有偏见或歧视行为的市民,他们可能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对待农民工的偏见与歧视,他们只是按照几十年来演化的“刻板印象”来判断事物。一部分市民将农民工视作“外来人”,认为他们没有权利享受城市的优越条件,在心理上将“他们群”视作异类,在认识上表现出偏见,在行为上表现出歧视。尽管这部分市民的人数不多,但是对这类歧视所造成的负面影响却不能低估。因为它容易使农民工将这种态度误解为广大市民的一般态度,容易引起农民工的反感,导致群体性摩擦与冲突。而与之对应的农民工群体则用“我们群”来使处于不利地位的自身能够团结起来,保护自身利益。“我们群”会产生“我们感”的群体意识。尽管农民工在心理上是竭力地反抗“二等公民”的地位,但在长期的二元结构现实面前,低下的经济、社会地位迫使他们屈服于“二等公民”的意识。他们对“一等公民”夹杂着羡慕,更多的是相对剥夺感的不平衡心态。这种不平衡心态有可能会发展成为对抗城市与居民的破坏心理。
农民工自身局限性
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的摩擦性互动,制度性歧视是主要的原因,但也有因农民工的活动条件与自身素质的限制而引起的对城市生活的不适应。
社会交往的局限性。进城农民工的社会交往与他们的职业和居住相关。居住地是进城农民工除劳动场所以外最主要的活动场所,居住的地点及其所在社区环境,对进城农民工的社会交往影响很大。由于绝大多数的进城农民工所从事的工作具有行业性特点,农民工的生活圈子相对较为封闭,与城市居民的沟通较少。同时,职业的类型决定了劳动时间和劳动强度,进而影响到他们的闲暇时间和精力。农民工与城市居民在互动中以业缘关系为主,情感性的互动则较少发生。
文化适应力强。互动中农民工总是处于被动的地位,这种被动性来自于他们经济、社会地位的劣势引起的“二等公民”的自卑心理和过度的心理敏感,使他们处处抱着谨慎的态度,自觉或不自觉地回避与城市人交往。一是囿于“都市里的老乡”。农民工愿意与自己的同乡交往是因为具有相似性,如相同的工作环境、相同的经历、相同的生活条件和生活方式,在老乡、亲属、朋友等初级群体中,他们可以获得信息与共享社会资源,共渡闲暇时间。我们在调查中发现,许多农民工提到在城市生活中,“我最快乐的是星期天和老乡聚会。”二是囿于文化的同质性。城市的生活方式、待人接物方式、看待事物的观念、人际关系、风俗习惯,使农民工感到不适应;但同类中的乡土文化习俗,使他们感受到熟悉的家乡文化环境。这种文化同质性给他们的交往带来安全感和人格的平等感。农民工文化适应力弱,这使他们囿于习惯性的同乡交往而不愿意主动地突破这一交往圈,客观上形成了自我隔离状况,与城市主流社会、主流文化相疏离。
“过客”心态。只有具有社区意识的人才会热爱所生活的社区;只有具有家园意识的人,才会有主人翁的意识,关心与参与家园的建设。由于土地牵制和户籍限制,大多数农民工将自己的未来定位在农村,[10]加上城市中偏见与歧视的客观存在,促使农民工对城市形成“过客”心态,对城市没有“我们群”的归属感和“主人翁”意识,只有“陌生人”的感觉:城市再美丽,建筑再雄伟,环境再干净,那也是城市人的城市,与我们农民工没有关系。
少数农民工素质低。许多研究已经表明,进入城市的农民工群体相对于滞留在农村的农民而言,群体的素质较高。但其中有部分人的文化水平、道德素质、法律意识相对落后。他们在城市中的越轨行为,给城市秩序与居民生活带来消极影响,并产生“晕轮效应”。
纠正偏见,化解歧视
中国社会的进步不仅仅是经济的发展、物质的丰裕,也需要人文精神的提升,特别是社会公平观念的普及,对人格的普遍尊重。而某些基于计划经济体制而建立的政策与制度,也要进行改革。逐步地消弱制度性歧视的政策是我们努力的目标。
偏见和其他态度一样,也是来自于周围的文化环境。城市中的舆论导向一度较为片面,仅仅把农民工看作是劳动力的重要源泉,而没有看到他们也是有多方面需要的社会活动群体;长期以来对农民进城带来的负面效应报道得多,对他们为城市所作的贡献宣传得少,对城市居民存在的偏见消除不够。自然化解偏见与歧视时间过于缓慢,我们需要主动地采取某些人为措施,加速偏见的瓦解。行之有效的人工化解就是传播媒介的正确宣传。例如职业偏见,仅凭感觉就简单地认为农民工“抢了城里人的饭碗”,在职业上对农民工持排斥态度是不正确的。据笔者对城市农民工就业岗位的调查,农民工在城市主要从事的是“拾遗补缺”的职业,除了少数职业与市民就业有所冲突外,大多数职业具有填补城市职业空白的性质。通常这些职业在支付性要素中具有劳动强度大、工作环境恶劣、劳动条件差、有危险性等特点,在获得性要素方面,则是收入低、没有福利、缺少保障、不稳定等。通常市民放弃了对这些职业的选择,并鄙视这类职业。农民工在从事这类职业时,不仅要承受物质上的低收入,还要承受精神上的失落。这些职业的意义,只有在春节期间,大批农民工撤离岗位时才能直观地反映出来。
城市居民间接地从宏观的层面了解到农民工对城市发展所作的贡献,而直接地从微观的层面看到民工的某些负面的行为。他们在日常社会生活中的直觉经验感受是农民工素质较差,没有教养。但如果我们站在农民工的立场,从他们的角度来考虑,就可以发现,有些东西不是什么了不起的问题。在农村田野走路,根本就不需要什么交通规则;随地吐痰、乱扔废纸是十分正常的,因为农村根本没有专门垃圾箱与吐痰的地方。这对农民工来说不是什么不良的道德品质,只是与城市不适应的行为方式而已。长期受城市文明熏陶的城市居民,没有理由因为这些而歧视他们。绝大多数农民工,进入城市不久,就学会了城市的各种各样的规矩。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农民工在政治权利上、人格上与城市居民是完全平等的。农民工对城市也享有权利。传播媒介的舆论宣传中要增加尊重、重视农民工的内容,引导市民以平等的态度对待农民工。传播媒介要特别强调:“一等公民”的意识是一种类似于种族中心主义的偏见,它将长期以来政府对城市的倾斜和保护政策视为理所当然,没有看到城市居民得以享受的各种福利保障和较高的社会地位,有许多正是通过广大农民默默地奉献而来的。
二元社会结构导致的城市居民与农民工的社会地位不同,归根结底不是农民工的素质问题,而是机会不同所致。尽管这些限制农民工的政策、制度有其存在的历史性和合理性,但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它的局限性,即这是一种以牺牲农民利益为前提的不平等做法。如果经济制度与社会制度的歧视性政策不改变,歧视农民工的客观因素存在,那么,在人们的思想观念中的偏见就不容易改变。我们要从城市化与现代化的高度,看待农民工的城市适应问题,通过户籍制度、就业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等的社会改革,将进城农民工纳入正式的城市社会管理和服务体系之中,使他们成为一个既有保护又有约束的社会群体,化解城市发展中这一潜伏的矛盾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