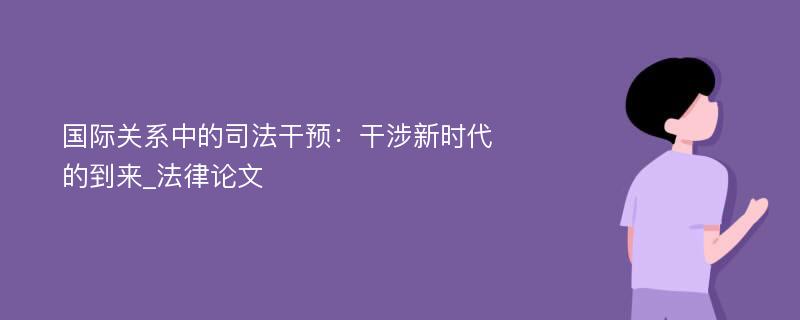
国际关系中的司法干涉:新干涉时代来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际关系论文,司法论文,时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8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9550(2011)07-0111-17
自冷战终结以来,人道干涉① 曾经在20世纪90年代风靡一时,并随科索沃战争而发展至高潮。在进入21世纪后的这十年中,司法干涉(judicial intervention)则大有取代人道干涉之势,在国际关系中产生了重要影响。
最先关注司法干涉现象的学者是美国常驻联合国高级法律顾问戴维·谢弗(David J.Scheffer)。② 此后,尽管有学者继续跟进关注和研究司法干涉现象,③ 但由于其关注对象主要为国际刑事司法机构,因而在进入21世纪之前尚未引起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司法干涉现象真正引起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主要源于国家针对发生在他国的严重国际犯罪行使普遍管辖权的实践,相应实践肇始于皮诺切特案。此后,基于普遍管辖权行使的司法干涉为部分国家所重视和实践,从而涌现了一些经典案件,如“逮捕令案”、④ 以色列前总理沙龙被诉案等。⑤ 随着澳大利亚于2010年5月31日就日本在南极的捕鲸行为在国际法院提起诉讼,一国基于所享有的普遍性法律利益来对他国进行的司法干涉作为一种新司法干涉形式开始“登场”,这不仅发展了通过国际司法机构所进行的司法干涉,还标志着司法干涉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
司法干涉一方面在促进国际司法正义、实现“有罪必罚”及维护国际社会整体利益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另一方面也给现存国际秩序带来了挑战,给国际关系中的主权平等原则和不干涉内政原则带来了强力冲击。因此,如何准确认识和评价司法干涉,无论是对于未来国际秩序的构建还是对于中国来说均具有重要意义。
一 司法干涉的概念及其特征
所谓司法干涉,主要是指一国或多国通过本国司法机构或国际刑事司法机构的方式来对发生在他国的严重国际犯罪行使管辖权。⑥ 对于一国基于所享有的普遍性法律利益并通过非刑事性国际司法机构如国际法院来援引不法行为国国家责任所进行的司法干涉,由于此种干涉所涉事项并非针对严重国际犯罪,而是针对国家违背其所承担的对于国际社会整体的义务即“对一切”义务,其在性质和方式上均有别于针对严重国际犯罪所进行的司法干涉,并且,此种干涉形式尚处于发展之中,其很难被包括在前述定义之中,因而放在后文单独讨论。
由于在犯罪管辖问题上历来实行属地和属人管辖优先原则,而无论是属地管辖还是属人管辖,传统上均被视为“本质上属于国内管辖事项”即内政范畴,因此,一旦国家通过本国司法机构或国际刑事司法机构来对发生在他国的犯罪行使管辖的时候,特别是国家通过本国司法机构来实施管辖的时候,由于相应犯罪并没有发生在该国,犯罪者和受害人也不具有该国国籍,国家同该犯罪不存在直接的、实质性的紧密联系,在此背景下,国家对该犯罪的管辖已经构成了对其他国家属地管辖权或属人管辖权的“侵犯”,因而当然体现为一种干涉。此即司法干涉的本质含义。
司法干涉分为国家层面的司法干涉和国际刑事司法机构层面的司法干涉。国家层面的司法干涉主要是指一国或多国通过本国司法机构来针对发生在他国的严重国际犯罪行使普遍管辖权,包括普遍刑事管辖权和普遍民事管辖权;国际刑事司法机构层面的司法干涉则主要是指国家通过国际刑事司法机构来对发生在特定国家的严重国际犯罪行使管辖。
无论是国家层面的司法干涉还是国际刑事司法机构层面的司法干涉,其共同特点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司法干涉是通过行使司法管辖权来进行的,是在规范的层面上进行的,与使用武力无关,因而有别于人道干涉。
第二,无论是国家层面的司法干涉还是国际刑事司法机构层面的司法干涉,均与普遍管辖权密切相关。国家层面的司法干涉实质是通过普遍管辖权的行使来进行的,国际刑事司法机构在促进普遍管辖权的行使方面同样有积极作用。关于此点,下文将展开论述。
第三,无论是国家层面的司法干涉还是国际刑事司法机构层面的司法干涉,其行使均建立在有效规范基础之上,具有实在国际法依据。例如,很多条约中都有“或引渡或起诉”条款。⑦ 条约当事国对于在其境内发现的犯有该公约规定罪行的人,即使其为外国人,所犯罪行发生在外国,如不同意引渡,就有义务起诉。此时,无论是引渡还是起诉,对于该国而言均具义务性质。就习惯国际法而言,习惯国际法确认每个国家均有权对某些特定罪行如海盗犯罪行使普遍管辖权。而在临时性国际刑事法庭如前南斯拉夫国际刑事法庭和常设性国际刑事法庭即国际刑事法院成立之后,当国家基于履行义务的要求而在本国法律中确立了对法庭所管辖罪行的普遍管辖权并在实践中行使此管辖权的时候,此时的司法干涉,要么是基于执行联合国安理会决议即“宪章义务”的要求,⑧ 要么是基于履行《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所规定的条约义务,其规范基础是非常确切的。司法干涉存在相应的规范基础是其有别于人道干涉的最根本特征。
二 司法干涉的出现和存在原因
司法干涉现象在21世纪“异军突起”的首要原因在于:20世纪90年代“风靡一时”的人道干涉饱受质疑,而对于这些质疑,倡导者和实行者很难有效反驳。
人道干涉⑨ 是指当一国境内发生或即将发生大规模严重侵犯基本人权的事件或情势时,为预防或制止此种灾难,一国或多国未经该国同意而对该国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的干涉行为。⑩ 从此定义可以看出,人道干涉的基础在于相应国家存在严重人道危机。真正的人道干涉应该是完全非利己性的,干涉者在所干涉事项上没有或者不追求自己的利益。但遗憾的是,在人道干涉的已有案例中,完全符合这一条件的案例寥寥无几。在很多情形下,人道干涉往往被滥用。(11) 这是人道干涉饱受诟病的首要原因。另一重要原因还在于,当使用武力来进行人道干涉时,人道干涉的规范依据在实在国际法中很难找到。由于在实在国际法中对武力的使用有着严格限制,仅适用于自卫和安理会的授权这两种情形,仅仅以人道关切为由就针对一国使用武力进行干涉,干涉者无法在国际法上为自己有效辩护。(12) 总体而言,人道干涉虽然具有“正当性(legitimacy)”,但由于缺乏“合法性(legality)”基础,因而既不可避免地影响到其“正当性”,也影响到国际社会成员对其的影响与评价。
正因为人道干涉遭受到基于上述两点的责难,针对严重国际犯罪,国际社会需要找到其他既能体现“正当性”又能体现“合法性”的新干涉形式,司法干涉便“应运而生”。
司法干涉存在的另一原因在于终结“有罪不罚(impunity)”现象。正如有国家在联合国大会讨论和审议“普遍管辖权原则的范围和适用”议题时所指出的,“近几十年来,国际法取得的重大成果之一,就是各国理解到,就严重罪行而言,不应存在有罪不罚现象”。(13) 犯有严重国际罪行者应该得到相应惩罚,所谓“法网恢恢,疏而不漏”即为此意。但由于如下种种原因,“有罪”却“不受惩罚”的现象依然“屡见不鲜”:(1)相应犯罪是相关国家政策的一部分,从而使相关犯罪呈现出“国家犯罪”或系统性犯罪的特征,在此情况下,该犯罪发生地国家本身缺乏管辖意愿或根本不可能管辖,其他国家基于政策考量等因素一般也不愿管辖;(2)国际法中的豁免规则会使对特定犯罪的追诉变得困难,由于在传统国际法中,国家行为在他国享有国家豁免,从而使得某些犯有严重国际犯罪者可以借助“国家行为”理论来逃脱他国对其进行的审判;(3)部分转型国家为了以更小代价实现成功转型,往往会给予特定的犯罪以豁免或赦免;(4)特定国家所设立的“真相与和解委员会”为实现种族和解等目的,也会对特定犯罪放弃追究责任,如大屠杀后的卢旺达和消除种族隔离政策后的南非等。(14) 在此背景下,司法干涉便有了存在的必要性。
三 司法干涉的具体形式
国家层面的司法干涉主要体现在普遍管辖权的行使上,包括普遍刑事管辖与普遍民事管辖两方面。通过国际刑事司法机构所进行的司法干涉则既包括通过临时性的国际刑事司法机构所进行的司法干涉,也包括通过常设性的国际刑事司法机构所进行的司法干涉。
(一)通过普遍刑事管辖所进行的司法干涉
普遍刑事管辖是指一国对发生在他国的严重国际犯罪行为行使刑事管辖权。当国家在行使普遍刑事管辖的时候,既不问犯罪发生地,也不问犯罪者和受害者国籍。针对发生在他国的犯罪行使普遍刑事管辖权是司法干涉的最主要形式,也是积极主张和推行司法干涉国家的常用形式。目前在此领域最热衷者主要是欧洲国家,如英国、比利时、西班牙、德国、法国和荷兰等。(15) 而在这些国家中,尤其以比利时和西班牙曾经最为积极。(16) 因此,这里仅以此两国为例略做介绍。
1993年6月,比利时制定了《关于惩治严重践踏国际人道法行为的法律》。基于此法规定,比利时对非发生在本国的战争罪、反人道罪和灭种罪拥有管辖权。此法案颁布后,一些人权组织和他国的受害者均来到比利时法院指控他国犯有这些罪行的高官,包括以色列前总理沙龙、美国在任总统小布什等。(17)
西班牙普遍刑事管辖权则肇始于其宪法法院于2005年9月26日对《司法组织法》第23.4条的解释。(18) 宪法法院通过解释指出,西班牙法院基于该条在行使普遍管辖权的时候,不需要“直接联系”。即使相关犯罪没有发生在西班牙境内,犯罪者不具有西班牙国籍,受害人也非西班牙国民,西班牙仍然有权行使普遍管辖权。(19) 基于此解释,西班牙国家高等刑事法院在行使普遍管辖权上进入了“狂飙突进”阶段。西班牙法院不仅启动了对危地马拉政府高级领导人的调查、指控程序,甚至向危地马拉提出了引渡请求;与此同时,西班牙法院还将视线投向了美国关塔那摩监狱所使用的“水刑”犯罪以及以色列在加沙地带所犯下的罪行等。(20)
(二)通过普遍民事管辖所进行的司法干涉
普遍民事管辖是指当严重国际犯罪行为受害者在他国通过侵权民事诉讼方式寻求救济时,该国有权行使司法管辖。同普遍刑事管辖一样,一国在向严重国际犯罪行为受害者提供侵权民事救济的时候,同样不问犯罪行为发生地,也不问受害者和加害者的国籍。此概念肇始于美国法院对其1789年制定的《外国人侵权索赔法案》(Alien Tort Claims Act,下称“1789年法案”)的解释与适用。
美国1789年法案规定,如果外国人遭受到以违反国际法或美国为当事国的条约的方式的侵权,对于该外国人因此而在美国提起的民事诉讼,美国联邦地方法院应有权管辖。此法案自制定后,在近两个世纪内一直处于“休眠”状态,直到1980年菲拉蒂加案,(21) 美国联邦第二巡回上诉法院首次适用之。在该案中,法院指出,法案是针对违反“广泛确立的、普遍公认的”或“具体、普遍、义务性的国际法律规范”的行为;法案并不要求相应的侵权行为发生在美国领土之内,或是由美国人所实行。因此,该法可以适用于与美国没有“联系”的行为与人。(22)
美国于1988年4月18日签署了《禁止酷刑公约》,为履行公约义务,为批准公约做好国内法上的准备,(23) 美国国会于1991年制定了《酷刑受害者保护法案》(Torture Victim Protection Act)。与《外国人侵权保护法案》类似,《酷刑受害者保护法案》同样允许酷刑、即刻处决受害者在本国用尽当地救济的基础上,有权在美国提起侵权诉讼。在实践中,此法案与《外国人侵权索赔法案》一起,有时单独适用,有时合并适用,共同推进了美国在普遍民事管辖领域的实践。而此种实践,已经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24)
相较于普遍刑事管辖,普遍民事管辖具有自身优点:
首先,普遍刑事管辖实践不易。由于侵犯人权的犯罪大多具有制度性犯罪的特点,是大规模的、国家主导或受到国家纵容,犯罪地国一般缺少管辖和惩治动力。而当另一国针对该犯罪行使普遍刑事管辖的时候,特别是在通过检察机关启动刑事指控程序的时候,一方面容易激起相应国家的强烈反对和抗议,另一方面也不易获得本国理解和接受。(25)
其次,普遍刑事管辖机制在启动和行使过程中还会遇到很多“技术性”障碍,如在一些国家,普遍刑事管辖的启动须得到总检察长的批准,允许私人启动普遍刑事管辖的国家并不多,跨国刑事犯罪调查取证难度过大等,往往会导致普遍刑事管辖“开花而不结果”。普遍民事管辖则很少碰到这些技术性障碍。
最后,从缺席审判和证据证明标准角度看,普遍民事救济更容易。由于刑事诉讼采用“排除合理怀疑”证据标准,在犯罪嫌疑人缺席时启动普遍刑事管辖,将既不符合程序正义,也不利于犯罪嫌疑人权利保障,因而一般不允许缺席审判。但普遍民事管辖不同。由于民事诉讼主要采取“盖然性”证据证明标准,被告人缺席不妨碍民事审理程序的继续。(26)
(三)通过国际刑事司法机构所进行的司法干涉
通过国际刑事司法机构所进行的干涉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基于联合国安理会决议所设立的特别国际刑事法庭,如前南斯拉夫国际刑事法庭和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能够有效地对发生在特定国家境内的特定犯罪行使管辖,实现“定向”正义;而就国际刑事法院而言,则能针对缔约国境内所发生的罪行进行管辖,特定情形下还能针对发生在非缔约国境内的罪行进行管辖,如针对苏丹达尔富尔情势。(27)
第二,无论是特别国际刑事法庭还是常设国际刑事法院,都能促进国家针对特定犯罪的普遍管辖实践。例如,联合国安理会在设立前南刑庭的决议中明确要求,“决定所有国家应按照本决议和《国际法庭规约》同国际法庭及其机关充分合作,因此所有国家应根据国内法,采取任何必要的措施来执行本决议和《规约》的规定,包括各国遵从初审法庭依照《规约》第29条提出的协助要求或发布的命令”。(28) 为此,德国、法国等纷纷制定了本国与前南刑庭合作的法律,规定本国有权针对前南刑庭所管辖的犯罪行使临时性的普遍管辖权。(29) 国际刑事法院更是如此。很多国家在批准《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之后,都专门制定了与法院合作的相关法律,如英国2001年所制定的《与国际刑事法院合作法》。(30) 这些国家为了同临时性法庭及常设性法庭有效合作,就必须并且有义务在本国国内法中确立对法庭/法院所管辖罪行的普遍管辖权并在实践中行使之。
第三,就国际刑事法院而言,其管辖权特质会刺激并有助于国家有效行使普遍管辖权。根据《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序言第十段规定,“强调根据本规约设立的国际刑事法院对国内刑事管辖权起补充作用”,国际刑事法院的管辖权具有“补充性”特点,换言之,国家的管辖权相应地就具有“优先性”。相对于国家行使普遍管辖权而言,“补充性”有两重含义:(1)对于国际刑事法院所管辖的四类犯罪而言,国家应居于主导地位。只有在国家“不能”或“不愿”的情形下,国际刑事法院才能介入。(2)“补充性”反过来又有利于刺激国家针对相应罪行行使“充分而有效”的管辖权,特别是普遍管辖权。原因很简单:一旦国家给国际刑事法院留下“不能”或“不愿”行使管辖权的印象,国际刑事法院就有权直接介入,国家显然不期望如此。国际刑事法院管辖权的“补充性”实质上把调查和指控国际犯罪的首要责任赋予给了国家。就此意义而言,《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关于管辖权“补充性”的相关规定实际上创设了一个规范性环境,在此环境内,国家被期望积极行使普遍管辖权。
四 司法干涉的积极意义与消极影响
从国际法律规范形成的“三部曲”理论来看,(31) 国家热衷于推行司法干涉的主要目的在于,试图通过自身的行为来影响国际社会的其他成员,促使其他国家认可和接受相应规范与实践,进而实现司法干涉的国际化,在全球范围内真正实现“有罪必罚”。同时,司法干涉还能向犯有严重国际罪行者发出一个明确的“信号”:罪行实施者都会受到相应的惩罚,而不存在庇护犯罪者的真正“天堂”。就此意义而言,司法干涉是有其积极意义的。
但是,司法干涉的消极影响同样不应忽视与低估。司法干涉会对国家主权平等原则和不干涉内政原则带来严重挑战。由于事关国家主权,管辖权的行使一直是国家间关系中的重要和敏感内容。相对于属地和属人管辖权而言,作为司法干涉主要形式和内容的普遍管辖权是一种补充性质的管辖权。正因如此,当一国针对另一国行使普遍管辖权的时候,由于其与该另一国的属地和属人管辖权相冲突,即使该国是所谓的大国或强国,即使该国“不能”或“不愿”行使属地或属人管辖权,依然会激起相应国家的强烈反对和抵制。例如,以色列前总理沙龙被指控后不久,按照预定计划,他要前往欧盟布鲁塞尔总部参加一次会议。考虑到针对他的刑事指控在比利时已经启动,他被建议不要前往,其最终听从了此建议;在小布什和其他一些美国高官被指控后,国务卿科林·鲍威尔(Colin Powell)认为,这些指控事关北约总部,因为其妨碍了相关人士前往比利时。如果比利时不修改自身法律,甚至考虑将北约总部迁出比利时。(32) 因此,普遍管辖权的行使一方面会构成对他国主权平等的侵犯,构成对他国内政的干涉;另一方面,作为一种结果,往往会因此而导致国家间冲突的产生。
普遍管辖权的行使还会给国际法中的国家豁免规则带来重大挑战。
根据国际法中的豁免理论,基于国家主权平等原则,国家行为是不受外国法院管辖的。可是,在皮诺切特案中,当皮诺切特提出,自己是智利前总统,相应行为是国家行为,因而应享有豁免的辩护主张时,英国上议院并没有接受他的这一主张,而是指出,国家元首如果犯下了酷刑罪行,他就不能主张豁免,因为酷刑不能被认为是官方行为。(33) 美国联邦法院在行使普遍民事管辖的实践中也曾发表过类似论点。在菲律宾前总统马科斯被诉案中,美国法院驳回了马科斯女儿“政府雇员”的身份主张,强调外国官员超越权限的行为并非政府行为,而是个人行为,因而不能享受国家豁免。(34) 国家在行使普遍管辖权的过程中对豁免理论的限制性解释无疑会对传统的国家豁免理论带来严重冲击。而对于此种冲击,相当多的国家并不认可。例如,智利对于英国罔顾皮诺切特豁免的行为即表示强烈反对和抗议;当比利时针对刚果在任外交部长签发逮捕令后,刚果通过在国际法院提起诉讼来解决彼此间的争议。特别是在2004年《联合国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公约》通过之后,由于上述解释与实践并未被纳入公约规定之中,因此,一旦国家基于上述对豁免理论的限制性解释再行相关实践,必然会在相关国家间激起强烈反弹。这将对国家间关系的稳定带来严重挑战。
司法干涉给国家间关系带来的另一挑战就是,部分国家在通过行使普遍管辖权进行司法干涉的时候,往往具有选择性,会为特定的政治目的所操纵。特别是有部分国家在行使普遍管辖权的时候,往往只针对特定国家的特定人物,特别是重要的政治人物,对于其他国家发生的类似罪行,则往往“视而不见”。司法干涉中的此种“厚此薄彼”现象不仅达不到防止“有罪不罚”现象出现的目的,相反,还会制造更多的不公正。
而就国际刑事司法机构而言,特别是就国际刑事法院而言,如果考虑到了巴希尔案这个因素,其对国际关系所带来的不确定影响无疑特别明显。
自联合国安理会于2005年将苏丹达尔富尔情势移交国际刑事法院之后,针对该情势,国际刑事法院已经针对苏丹启动了包括针对在任总统奥马尔·哈桑·艾哈迈德·巴希尔(Omer Hassam Ahmed Elbashir)在内的三起刑事指控。(35) 其中,针对巴希尔所签发的国际逮捕令尤为引人瞩目。自2008年启动相应程序以来,国际刑事法院先后于2009年3月4日、2010年7月12日针对巴希尔签发了两份逮捕令,指控其涉嫌犯有战争罪、反人道罪和灭种罪。达尔富尔情势是国际刑事法院第一次针对非缔约国行使管辖权。尽管由于存在安理会授权,国际刑事法院对此案的管辖权不存在“合法性”质疑,但是,由于其针对一国在任元首接连签发逮捕令,此种行径必然会激起那些依然对国际刑事法院持观望甚至反对立场国家的警惕甚至怀疑,认为其有被作为政治工具使用的嫌疑。由于在国际刑事法院设立过程中,即有部分国家高度质疑国际刑事法院在特定条件下有权对非缔约国行使管辖权,并质疑检察官权力过大,(36) 认为国际刑事法院的建立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司法干涉时代的来临,(37) 巴希尔案实质上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此种质疑。这实质上是不利于国际刑事法院在实现全球法治进程中进一步发挥重要作用的。
五 基于普遍性法律利益所进行的司法干涉:司法干涉的新发展
一国在自身具体利益没有遭受到任何直接侵害的情形下,因基于所享有的普遍性法律利益而在国际性法庭“援引”(38) 另一不法行为国的国家责任,此种“援引”同样构成一种司法干涉,是司法干涉近几年正在发展的形式。
国家在国际关系体系中所承担的义务主要是契约性义务,此种义务具有对等和互惠特征。与此同时,国家在国际关系体系中也承担了对国际社会整体的义务即“对一切”义务。(39) 当一国承担的义务具有“对一切”性质时,所有其他国家在监督该义务的履行上都享有权利,享有法律利益。一旦一国违背了其所承担的“对一切”义务,根据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2001年二读通过的《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条款草案》第48条(40) 和第54条(41) 的规定,其他国家有权通过在国际性法庭起诉或采取反措施(42) 的方式来援引其应该承担的国家责任。
当一国基于另一国违背其所承担的“对一切”义务而援引其国家责任的时候,特别是通过在国际法庭诉讼的方式来援引其责任的时候,原告国自身具体的、直接的、物质性的法律利益并没有遭受到任何损害,但是,其基于“对一切”权利所享有的抽象的、间接的、非物质性法律利益遭受到了侵害,因而有权通过诉讼的方式来援引不法行为国的国家责任。此时,原告国所享有的这种法律利益,被称为普遍性法律利益。无论是在“温布尔登案”(43) 中,还是在“梅梅尔地区规章解释案”(44) 中,常设国际法院都认可和支持了国家基于普遍性法律利益所享有的诉讼权利和资格。
而在国际法院成立之后,在澳大利亚诉日本“在南极捕鲸行为的非法性案”之前,国际法院对于一国基于普遍性法律利益所提起的诉讼,在实践中曾持有别于常设国际法院的立场。这方面最明显的例证是,在埃塞俄比亚和利比里亚诉南非“西南非洲案”中,国际法院驳回了两原告国基于普遍性法律利益的诉讼。(45) 因此,当澳大利亚于2010年5月31日在国际法院提起针对日本的诉讼之后,由于澳大利亚在相应事项上所享有的利益同样是一种间接的普遍性法律利益,一旦国际法院在此案中持支持立场的话,则表明国际法院改变了此前在类似事项上所坚持的法理。而从国际法院在波黑诉塞尔维亚“《灭种罪公约》适用案”判决中的相关论述看,有理由相信国际法院会采取支持澳大利亚行为的立场。
在2007年2月26日做出的“《灭种罪公约》适用案”判决中,当论及国家基于该公约第1条(46) 所承担的预防灭种义务的含义与范围时,国际法院指出,公约第1条中所称的预防义务,应是一种直接义务。在承担预防义务上,公约要求国家采取一切合理措施进行预防,而不管灭种发生在何国。当国家在其权力范围内没有采取一切有效的措施去预防灭种行为的发生时,就应承担相应责任。在承担预防义务上,国家应做到“尽职尽责(due diligence)”。而在判断是否“尽职尽责”上,除了考虑地理因素外,还特别需考虑特定国家对灭种者的有效影响。(47) 此论述表明,公约当事国在他国灭种即将发生或已经发生之后,应承担积极预防义务而无消极“旁观”之权利。一旦国家不履行自己应承担的预防义务,即被视为违反了基于公约所承担的义务,因而应承担相应的国家责任。在此情势下,其他国家有权通过采取适当的行动如到国际法院起诉,或采取单独或集体反措施的方式来援引其国家责任。(48) 国际法院的上述论述实际上肯定了国家基于公约所享有的普遍性法律利益的可诉性。国际法院通过此论述所表明的立场,完全迥异于在“西南非洲案”中所持立场。如果说国际法院在此案中的上述论述为国家基于普遍性法律利益的诉讼提供了理论基础的话,那么澳大利亚诉日本“在南极捕鲸行为的非法性案”则可视为是国家实践国际法院上述论述的一块“试金石”。一旦国际法院支持了澳大利亚的诉讼,则不仅表明国际法院无论是在理论方面还是在实践方面均改变了自身在“西南非洲案”中所持的相关法理,还表明通过国际司法机构的司法干涉出现了新形式,有了新发展。
六 司法干涉与中国:机遇、挑战与应对
司法干涉概念自1996年首次被提出以来,西方学者围绕此法律现象的研究已有十余年,尽管相关研究也存有一定不足,(49) 但围绕司法干涉的研究也取得了若干重要成果。(50) 遗憾的是,到目前为止,中国学者尽管对作为司法干涉现象之一的普遍管辖有一定研究,(51) 但是,现有研究没有从“司法干涉”角度切入,而且对通过普遍民事管辖所进行的司法干涉和基于普遍性法律利益并通过国际法院所进行的司法干涉的研究则几近空白。
笔者认为,作为一种法律现象的司法干涉,其重要性和作用日益凸显,已发展成为与人道干涉并行的另一种重要干涉形式。由于此种干涉形式在规范依据方面有较人道干涉更坚实的基础,其对于传统国际法的冲击力更大,对于热衷于干涉的国家的诱惑力也更大。在此背景下,司法干涉对于当前中国而言,无论是在国家利益的维护方面,还是在法律制度的创新方面,可能既意味着挑战,也意味着机遇。
就国家利益维护上的挑战而言,由于中国一直倡导和遵循国家平等原则、不干涉内政原则等国际关系基本准则,而无论是基于普遍管辖权所进行的司法干涉,还是基于普遍性法律利益所进行的司法干涉,都表现为对他国国内管辖事务行使管辖权,是对他国国内管辖事务的一种干涉,因而会对这些准则构成挑战。
就法律制度创新上的挑战而言,无论是就普遍管辖而言,还是就国际法中普遍性法律利益的保护而言,中国均欠缺充分有效的国内法机制。在此背景下,一方面,针对其他国家对中国采取的司法干涉行动,中国没有相应的法制应对基础和应对手段,从而无法基于对等原则对相关国家构成一种对抗和牵制;另一方面,一旦中国在本国法律体系内提供了相应机制,特别是提供了普遍管辖的机制,实质上意味着要求中国针对发生在他国的犯罪进行管辖。此种管辖实践,即使存在条约义务基础与适当的国内法基础,(52) 但也面临两方面问题:其一,相应的基础并不完备。例如,尽管根据《灭种罪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9条的规定,中国对发生在他国的灭种犯罪拥有理论上的管辖权,但在刑法缺乏“灭种罪”规定的情形下,根据“罪刑法定”原则的要求,中国是无法完全基于公约的规定来对“灭种罪”行使管辖权的。其二,对于他国基于普遍管辖权而对发生在异国的犯罪行使管辖的实践,特别是在缺乏条约规定基础上的类似实践,中国此前一直认为该类实践构成了对一国国内管辖事务的干涉,在此背景下,要求并主张中国在本国法律体系中确立普遍刑事管辖机制,可能很难在短时间内获得决策层和实务部门的支持。
就国家利益维护上的机遇而言,司法干涉是一种正在形成和发展中的国际法律现象,从国际法律规范形成过程角度看,其是否会被更多国际社会成员所接受并实践,是否会最终发展成约束国际社会所有成员的行为规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各国立场与实践。在此背景下,如果中国恪守传统准则,不建设性地参与此类实践,不试图寻求通过自身实践来影响国际社会在此领域的行为规则,则意味着中国将既丧失促进相应行为准则形成的机会,也将丧失更好地保护自身利益的机会。
就法律制度创新上的机遇而言,一方面,中国目前正处于人权快速发展的阶段,但在人权保护的方式方法特别是法律方法上,中国还存在着很多制度性空白。司法干涉的诸多表现形式对于填补中国的诸多制度性空白无疑具有很好的借鉴和启示意义。另一方面,基于普遍性法律利益所进行的司法干涉对于发展中国国内的公益诉讼,完善国内有关法律保护的法律利益的规则体系,无疑也具有很好的启示意义。
既然司法干涉既给中国带来了挑战,也带来了相应的机遇,那么中国该如何确定自身对于司法干涉的立场?
笔者认为,由于不同形式的司法干涉的规范依据各有不同,其“合法性”特质也有很大差别,因此,对于不同形式的司法干涉,中国有必要分开考虑并确定相应的立场。例如,对于基于联合国安理会决议所建立的两个临时性国际刑事法庭即前南刑庭和卢旺达刑庭,考虑到中国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所应负的责任,对于通过这两个法庭所进行的司法干涉以及其他国家基于同这两个法庭合作而在国内法中所确立的普遍管辖权,中国应予以支持,并在可能的情形下考虑自身基于安理会相应决议所承担的义务,在国内法中确立对法庭所管辖罪行的普遍管辖权;而对于《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当事国基于同国际刑事法院合作目的而在各自国内法中所确立的对于法院所管辖罪行的普遍管辖权,中国也不应表示反对。但对于国际刑事法院在针对非缔约国情势的管辖方面的实践,则应持相对谨慎的立场。在安理会表决是否将相应情势移交国际刑事法院管辖方面,中国应在衡量本国国家利益等方面因素之后做出投何种票的决定。
对于国家基于普遍刑事管辖所进行的司法干涉,从中国当前利益考量看,中国原则上应持相对反对的立场。但考虑到国际社会在此方面的实践已较为丰富,中国一概的反对立场可能不太现实。在此背景下,中国可考虑从强化其行使的条件与范围入手,强调普遍刑事管辖应仅针对特定犯罪,国家行使此类管辖应遵循一定限制,如应遵循“在场原则”、“不能或不愿原则”等。(53) 因为从实践看,普遍刑事管辖所带来的消极影响主要源于国家实际行使过程中对此权利的滥用。由于相对于属地管辖和属人管辖而言,普遍管辖权具补充性质,因此,每一国家尽管有权在本国法律体系中确立对某些罪行的普遍管辖权,但是,当国家基于立法性普遍管辖权而实际行使普遍管辖的时候,由于往往会同其他国家所享有的属地与属人管辖相冲突,因此,国家需遵循一定的自我限制,否则,普遍管辖权就非常容易演变为一种干涉工具,导致国家间冲突的产生。(54)
而对于普遍民事管辖,考虑到国家在此方面的实践还未普遍化,相当多的国家都处于观望之中,中国应特别警惕其进一步扩展的问题。对于美国试图通过国际条约来“国际化”其国内实践的“企图”,(54) 中国应及时洞察并采取有效的制止措施。
而对于国家基于普遍性法律利益并通过国际法院所进行的司法干涉,在国际法院已经显示出初步支持的立场的情形下,中国应对相关领域的国际实践进行综合性的深入研究,在研究基础上确定应对立场。
总之,面对司法干涉所带来的挑战与机遇,中国如何在维护自身利益的同时进行制度性创新,在维护自身利益的同时尝试将自身利益融入进相应国际行为规范之中,这恐怕是目前中国最需要解决的课题。就此意义而言,司法干涉对中国带来的挑战不仅是实践性的,同时也是理论性的。中国一方面有必要加深对司法干涉现象的理论研究,另一方面,在实践层面则应积极关注他国实践,并谨慎确定自身的应对立场。
[收稿日期:2011-01-20]
[修回日期:2011-05-07]
注释:
① 本文中所称的“干涉(intervention)”,在不同的中文语境中曾有不同的翻译,如“干涉”、“干预”等。本文没有对干涉和干预进行区分,而是在中性意义上使用“干涉”这一表述。
② 1996年,戴维·谢弗在《外交政策》上发表了题为《国际司法干涉》的文章,对根据联合国安理会决议设立的两个临时性国际刑事法庭的作用和意义进行了评论。参见David J.Scheffer,“International Judicial Intervention,”Foreign Policy,No.102,1996,pp.34-51。
③ 例如,Rachel Kerr,“International Judicial Intervention: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Tribunal for the Former Yugoslavia,”International Relations,Vol.15,No.2,2000,pp.17-26; Kristofor J.Hammond,“Judicial Intervention in a Twenty-First Century Republic:Shuffling Deck Chairs on the Titanic?”Indiana Law Journal,Vol.74,No.2,1999,pp.653-710。
④ 2000年4月11日,比利时签发了针对刚果在任外交部长的国际逮捕令。刚果认为此行为侵犯了在任外交部长的特权与豁免,于是在国际法院提起了针对比利时的诉讼。
⑤ 巴勒斯坦的一些人权组织和受害者认为沙龙在1982年的萨布拉和沙提拉难民营屠杀平民一事上负有责任,因而在比利时提起了针对他的刑事指控。
⑥ Andrea Birdsall,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s of Judicial Intervention,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09,p.3.
⑦ 如《禁止酷刑公约》第7条第1款规定,“缔约国如在其管辖的领土内发现有被指控犯有第四条所述任何罪行的人,属于第5条提到的情况,倘不进行引渡,则应把该案件交由主管当局进行起诉”。
⑧ 根据《联合国宪章》第24条和第25条的规定,安理会基于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目的所做决议,应当被视为是联合国会员国所承担的“宪章义务”。
⑨ 国内也译做“人道主义干涉”,但由于“人道主义”的英文表述主要为“humanitarianism”,因此,本文采用的表述是“人道干涉”。
⑩ J.L.Holzgrefe,“The Humanitarian Intervention Debate,”in J.L.Holzgrefe and Robert O.Keohane,eds.,Humanitarian Intervention:Ethical,Legal,and Politics Dilemmas,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p.18.必须申明的是,对于人道干涉,不同学者的定义也存在一定区别,区别最大的方面主要体现在是否应将基于安理会授权的联合国集体行动也纳入人道干涉的含义之中。例如,武汉大学的杨泽伟教授就认为,“(人道主义干涉)包括两类行为:一类是为了人道主义目的而实施的强制行动,它是在出现大规模侵犯人权的情况下,根据《联合国宪章》第7章,由全球性或区域性国际组织实施的或者由其授权而进行的集体干涉;另一类是没有授权的单方面的或由多国进行的干涉”。参见杨泽伟:《人道主义干涉在国际法中的地位》,载《法学研究》,2000年第4期,第127-128页。由于国际社会围绕人道干涉的分歧与争议主要集中于没有获得授权的人道干涉,而基于联合国授权的集体行动则没有分歧,因此,本文所采用的“人道干涉”的定义主要是指后者。
(11) 实际上,在《人道干预——伦理、法律和政治困境》(Humanitarian Intervention:Ethical,Legal,and Politics Dilemmas)论文集中,很多作者对人道干涉会被滥用这一点毫不质疑。参见J.L.Holzgrefe and Robert O.Keohane,eds.,Humanitarian Intervention:Ethical,Legal,and Politics Dilemmas,pp.1-2。
(12) Allen Buchanan,“Reforming the International Law of Humanitarian Intervention,” in J.L.Holzgrefe and Robert O.Keohane,eds.,Humanitarian Intervention:Ethical,Legal,and Politics Dilemmas,pp.130-173.
(13) 参见联合国文件:《普遍管辖权原则的范围和适用:秘书长根据各国政府评论和意见编写的报告》(文件号:A/65/181,2010年7月29日散发),第7段。
(14) Peter Burns and Sean McBurney,“Impunity and the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against Torture:A Shadow Play without an Ending,” in Craig Scott,ed.,Torture as Tort: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on Development of Transnational Human Rights Litigation,Toronto and Ontario:Oxford-Portland Oregon,2001,pp.277-278.
(15) 有关各国普遍管辖权实践的描述,参见 Human Rights Watch,“Universal Jurisdiction in Europe:The State of the Art,” Vol.18,No.5(D),2006,pp.38-100; Wolfgang Kaleck,“From Pinochet to Rumsfeld:Universal Jurisdiction in Europe 1998-2008,” Michig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Vol.30,No.3,2009,pp.927-980。
(16) 之所以称其为“曾经最为积极”,是因为后来这两个国家都修改了自身的相关法律,实践上与其他国家基本保持了一致。
(17) 由于被指控者很多都是各国在任高官,这些国家尤其是美国给比利时施加了巨大的外交压力。在此背景下,比利时先后两次对法案进行了修改,对指控进行了诸多限制。关于此点,参见Wolfgang Kaleck,“From Pinochet to Rumsfeld:Universal Jurisdiction in Europe 1998-2008,” Michig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Vol.30,No.3,2009,pp.932-936; Malvina Halberstam,“Belgium's Universal Jurisdiction Law:Vindiction of International Justice or Pursuit of Politics,” Cardozo Law Review,Vol.25,2003,pp.247-266。
(18) 西班牙《司法组织法》第23.4条和西班牙刑法的规定,西班牙国家高等刑事法院(Audiencia Nacional)有权针对西班牙公民或外国人在西班牙境外所犯的诸如灭种罪、恐怖主义犯罪、海盗罪、非法劫持航空器罪等罪行行使管辖权。
(19) Angel Sánchez Legido,“Spanish Practice in the Area of Universal Jurisdiction,” Spanish Yearbook of International Law,Vol.8,2001-2002,pp.21-22; Naomi Roht-Arriaza,“Guatemala Genocide Case,Judgment No.STC 237/2005,” America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Vol.100,No.1,2006,p.207.
(20) 与比利时类似,西班牙在行使普遍管辖权过程中同样遭受到了巨大的国际压力。基于此压力,西班牙于2009年对法案进行了修改,对普遍管辖权的启动进行了限制。
(21) 基本案情是:一位叫菲拉蒂加(Joel Filártiga)的巴拉圭青年因遭受巴拉圭警长酷刑致死。为平息因其死亡所致的骚乱,巴拉圭决定让该警长以旅游名义溜到美国。菲拉蒂加的姐姐和父亲到美国后知悉了该警长的行踪,遂以法案为依据提起侵权索赔诉讼。参见630 F.2d 876,2d Cir.1980。
(22) 参见630 F.2d 876,2d Cir.1980,pp.884-885。
(23) 美国正式批准此公约的时间是:1994年10月21日。
(24) 有关普遍民事管辖的详细分析以及国际社会对其的关注,参见宋杰:《普遍民事管辖的发展与挑战》,载《法学研究》,2011年第1期,第182-184页。
(25) 例如,西班牙针对皮诺切特案的逮捕令签发之后,负责此案的加尔松法官在本国受到很大抵制。参见John Terry,“Taking Filártiga on the Road:Why Courts Outside the United States Should Accept Jurisdiction over Actions Involving Torture Committed Abroad,” in Craig Scott,ed.,Torture as Tort: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on Development of Transnational Human Rights Litigation,pp.544-545。
(26) 当然,就美国而言,在某些特殊情形下,如在某些涉及宪法规定的公民的某些权利的民事案件中,此类民事诉讼所适用的证据证明标准,有别于一般民事案件所采用的证据证明标准。此类案件所采用的证据证明标准,主要是“清楚的、明确的、令人信服的标准”。
(27) 2005年3月31日,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了第1593号决议,决议“认定苏丹局势继续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因此,“决定把2002年7月1日以来达尔富尔情势问题移交给国际刑事法院检察官”。
(28) 参见联合国安理会1993年5月25日通过的关于设立前南刑庭的第827号决议第4段。
(29) 例如,为执行联合国安理会第827号决议,法国于1995年1月2日和1996年5月22日分别通过了第95-1号法律和第96-432号法律。参见Human Rights Watch,Universal Jurisdiction in Europe:The State of The Art,Vol.18,No.5(D),2006,pp.55-56。
(30) http://www.legislation.gov.uk/ukpga/2001/17/.
(31) 这一理论认为,国际法律规范的形成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规范的出现,第二阶段是规范的被接受,第三阶段是规范的国际化,即被国际社会成员所接受。参见Andrea Birdsall,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s of Judicial Intervention,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09,p.2。
(32) Malvina Halberstam,Belgium's Universal Jurisdiction Law:Vindiction of International Justice or Pursuit of Politics,Cardozo Law Review,Vol.25,2003,pp.251-261.
(33) Christine M.Chinkin,“United House of Lords:Regina v.Bow Street Stipendiary Magistrate,ex parte Pinochet Ugarte (No.3),”America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Vol.93,1999,p.708.
(34) Estate I,978 F.2d at 497; in Chuidian v.Philippine Nat'l Bank,912 F.2d 1095 (9th Cir.1990); 25 F.3d 1467 at 1470 (9th Cir.1994).
(35) 关于这三起指控,参见国际刑事法院网站,http://www.icc-cpi.int/Menus/ICC/Situations+and+Cases/Situations/Situation+ICC+0205。
(36) Andrea Birdsall,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s of Judicial Intervention,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09,pp.113-139.
(37) Andrea Birdsall,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s of Judicial Intervention,p.113.
(38) 此处所使用的“援引”,是在正式的法律意义上使用的。关于其含义,国际法委员会在关于国家责任条款草案第42条的评注中进行了较详细的阐释。国际法委员会认为,法律意义上的“援引”主要是指通过一定的法律形式,如通过在国际法庭提起针对一国的诉讼,一国向另一国提出一项正式的权利要求等,都意味着“援引”对方的责任。单纯的外交抗议,或声称保留采取行动的权利等,都不叫“援引”。关于国际法委员会对“援引”的界定,参见James Crawford,The International Law Commission's Articles on State Responsibility:Introduction,Text and Commentaries,Cambridge and 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2,p.256。
(39) “对一切”概念是国际法院在巴塞罗那电力、电车和电灯公司案中首次提出来的。在该案中,国际法院指出,“有必要在国家对国际社会整体所负的义务和在外交领域对另一国所负的义务之间划一条界线。在本质上,前者涉及所有国家的利害关系。鉴于与此等义务有关的权利的重要性,可以认为所有国家都对保护这些权利具有法律上的利益,这些权利同时也是(国家)对一切(erga omnes)所负的义务”。参见ICJ Reports 1970,paras.33-34,p.32。
(40) 第48条是有关“受害国以外的国家援引不法行为国国家责任”的规定。关于此条规定的评论,参见宋杰:《“保护的责任”:国际法院相关司法实践研究》,载《法律科学》,2009年第5期,第61-62页。
(41) 第54条是有关“受害国以外的国家采取的反措施”的规定。关于此规定的评论,参见Jie Song and Qingjiang Kong,“A Generalization of the Obligation to Prevent:From Genocide Convention to Racial Discrimination Convention,”Frontiers of Law in China,Vol.6,No.1,2011,pp.13-15。
(42) 由于本文关注的是通过司法行动所进行的干涉行动,因此,对于反措施的问题就不予展开。
(43) 关于温布尔登案的判决,参见http://www.icj-cij.org/pcij/serie_A/A_01/03_Wimbledon_Arret_08_1923.pdf。
(44) 关于“梅梅尔地区规章解释案”的判决,参见http://www.icj-cij.org/pcij/serie_AB/AB_47/01_Memel_Arret.pdf。
(45) 关于此案的详细分析与评论,参见宋杰:《“保护的责任”:国际法院相关司法实践研究》,载《法律科学》,2009年第5期,第57-59页。
(46) 第1条规定,“缔约国确认灭绝种族行为,不论发生于平时或战时,均系国际法上的一种罪行,承允防止并惩治之”。
(47) 参见ICJ Judgment of 26 February 2007,paras.428-438。
(48) 关于此点,参见国际法委员会2001年二读通过的《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条款草案》第42条、第48条以及第54条的规定及相应评注。
(49) 此种不足主要体现在两方面:(1)没有学者整体性地对司法干涉的四种形式进行研究;(2)对基于普遍性法律利益并通过国际法院所进行的司法干涉的研究较少见。
(50) 国外学者的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1)从普遍刑事管辖角度对司法干涉进行研究,如 Stephen Macedo,ed.,Universal Jurisdiction:National Courts and the Prosecution of Serious Crimes under International Law,Philadelphia: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2004; Mitsue Inazumi,Universal Jurisdiction in Modern International Law:Expansion of National Jurisdiction for Prosecuting Serious Crimes under International Law,Utrecht:Intersentia,20050 (2)从普遍民事管辖角度对司法干涉进行研究,如 Donald Francis and Anthea Roberts,“The Emerging Recognition of Universal Civil Jurisdiction,” America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Vol.100,No.1,2006 ,pp.142-163; Kate Parlett,“Universal Civil Jurisdiction for Torture,” European Human Rights Law Review,Vol.12,No.4,2007,pp.385-403; (3)从国际刑事司法机构或国际政治角度对司法干涉进行研究,如 Andrea Birdsall,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s of Judicial Intervention,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09。
(51) 中国在此方面的部分研究成果主要参见高秀东:《论普遍管辖原则》,载《法学研究》,2008年第3期,第126-139页;赵秉志、黄俊平:《论普遍管辖原则的确立依据》,载《社会科学战线》,2005年第3期,第207-216页;黄俊平:《普遍管辖原则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朱利江:《对国内战争罪的普遍管辖与国际法》,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朱利江:《普遍管辖国内立法近期发展态势》,载《环球法律评论》,2010年第1期,第144-151页。
(52) 条约基础的含义是:中国加入的某一条约中如果规定了“或引渡或起诉义务”的话,中国是有权在本国国内法中确立并行使“起诉义务”的管辖权的;国内法基础是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9条的规定,“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所规定的罪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所承担条约义务的范围内行使刑事管辖权的,适用本法”。
(53) 普遍刑事管辖应针对哪些特定犯罪行使,其行使的条件或限制应有哪些,限于研究主题、所涉问题的复杂性及篇幅原因,本文不拟展开,而考虑另行撰文予以专门讨论。
(54) 国际社会显然已经意识到了此问题的严重性。非洲联盟国家早在第63届联合国大会上就主张将“滥用普遍管辖权原则”列入大会议程。在非洲联盟国家的推动下,联合国大会于2009年将“普遍管辖原则的范围与适用”列入联合国大会第64届会议的议程,并请联合国秘书长根据联合国会员国提交的资料和意见编写一份关于普遍管辖权原则的范围和适用的报告。联合国秘书长于2010年7月25日递交的报告认为,各国“结束有罪不罚现象的目标本身不能产生滥用或导致与国际法其他规则的冲突”,“因此,应本着谨慎、司法独立、公正和公平的精神来行使普遍管辖权”。参见联合国文件:A/65/181,第7段、第5段。
(55) 美国“国际化”其国内实践的“企图”主要表现在两方面:(1)在《禁止酷刑公约》第14条意义上推进其实践,此种推进获得了禁止酷刑委员会的大力支持;(2)在《民商事管辖权和外国判决海牙公约(草案)》拟定谈判的过程中,美国试图将自身实践“融入”公约草案之中并获得了一定成功。关于上述两点,参见宋杰:《普遍民事管辖的发展与挑战》,载《法学研究》,2011年第1期,第185-19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