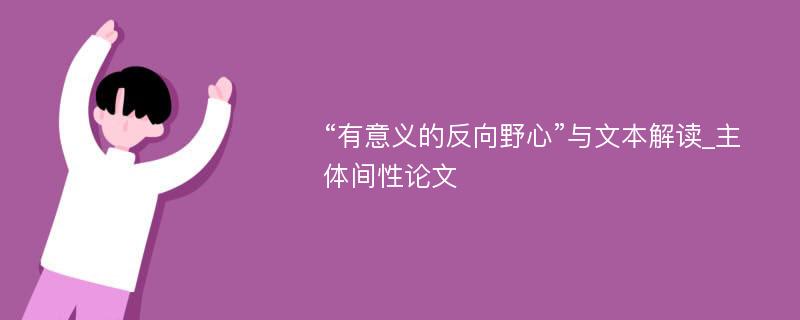
“以意逆志”与文本阐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以意逆志论文,文本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2146(2006)02—0010—05
“以意逆志”的命题,是孟子在和弟子讨论如何正确理解《诗经》文本意义时提出来的。《孟子·万章上》云:“故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强调诗歌的意义并不完全等同于诗句的言词含义,从而不能因为个别文字而妨碍一句诗的意思(“不以文害辞”),也不能因为个别诗句妨碍作者之旨趣(“不以辞害志”),而应从自己的体会出发,以人之常情、事之常理来揣摩领会诗人的创作用心(“以意逆志”),庶几才不至于误解诗义。这里,孟子的观点非常明确:其一,阐释者领会诗篇意义时,不能断章取义,不能割裂诗句的具体语境。这无疑是针对春秋时代蔚然成风的赋诗言志行为来说的。其二,鉴于诗人以诗言志,诗篇借文、辞而载志,所以阐释者当以意而逆志。诗歌的意义只能通过阐释者与诗人的互“逆”方式才能生成(“是为得之”)。
汉人赵岐在《孟子注疏》中说,“以意逆志”理论,“斯言殆欲使后人深求其意以解其文,不但施于说《诗》也”,指出它不仅仅是一种理解和解释《诗经》意义的方法,而且对于解读其他文本都具有普遍的指导价值。确实,经过后世诸多文学理论家、批评家的实践和总结,“以意逆志”已经上升为中国古代一种具有普遍价值的解释方法论,一种诗歌意义生成的基本方式。究其原因,是因为孟子的“以意逆志”说不仅深富哲理基础,其本身亦包含了丰富、深刻的理论内涵,从而能有效地指导诗文的阐释实践。我们试从解释学的角度梳理如下。
一 意:阐释者主体意识的确立
所谓阐释者主体意识,包含两个方面,其一,是指阐释者对自我作为能动主体的意识,即认识到自己是积极参与文本意义建构的组成要素;其二,是指阐释者对自我作为历史主体的意识,即认识到自己是历史性的具体存在,具有为特定历史文化语境所制约的前理解结构和阐释立场。本文认为,孟子通过对“意”的强调,完成了阐释者主体意识的确立。
首先,从“意”的主体归属来看阐释者能动主体意识的确立。
“以意逆志”之“意”究竟是诗人之意还是读诗人(阐释者)之意?对此历来多有诉讼,有的归为作者之“意”,有的归为阐释者之“意”。学界多认同后一种看法。笔者认为,把“意”理解为阐释者之意,是最为妥当的。因为从引文的文气脉络来看,“说诗者”一气贯下,统摄诸句,所以“以意逆志”当是“说诗者”之所为,是其以自己的心意、体会、测度去探求作品的意义。
将“意”界定为阐释者之意,在解释学上的价值是重大的。它从理论上把阐释者划入了文本解释的活动过程,肯定了阐释者参与文本意义建构的权力和能动性,高度弘扬了阐释者在理解活动中的主体能动地位。当代西方本体论解释学超越传统方法论解释学所取得的一个积极成果就是,阐释者的主体能动性得到了充分尊重。在传统的方法论解释学中,理解和解释被设定为对内在于文本中的作者意图或客观旨意的认识,阐释者的主体性成了科学认识所极力排除的消极因素。而对于伽达默尔而言,艺术的经验需要读者参与才能完成,文本意义的生成依赖于阐释者的理解:“艺术作品的存在就是那种需要被观赏者接受才能完成的游戏。所以对于所有文本来说,只有在理解过程中才能实现由无生气的意义痕迹向有生气的意义转换。”历史流传物的意义生成同样离不开阐释者的参与:“理解必须被视为意义事件的一部分,正是在理解中,一切陈述的意义——包括艺术陈述的意义和所有其他流传物陈述的意义——才得以形成和完成。”[1](P215—216) 据此,当代文学解释学认为,文学的意义及意义的阐释是文学实现自身的根本方式,而文学意义的生成则是作者、文本与阐释者相互之间的对话、交流与重构。[2](P263) 在对话交流中,作品的空白与未定性因读者而得到充实、丰富,阐释者的期待视野因文本而得到调整、提高,文学意义作为作品与阐释者两个世界之对立中介的第三生成物被建构出来。
孟子虽没有当代文学解释学这样明确的阐述,但他将阐释者之意视为理解活动的起始点,表明他已经深刻认识到了阐释者的主体能动性。综观《孟子》一书,《万章上》记载孟子对《小雅·北山》和《大雅·云汉》诗篇的意义阐释,《告子下》中对《小雅·小弁》和《邶风·凯风》诗篇的意义阐释,这些案例鲜明地启示我们,孟子正是从自己主体之“意”出发来深入到诗文阐释之实践的。孟子通过“以意逆志”命题所确立的阐释者能动主体意识,也绵延不绝地贯穿在中国古代文本阐释的思想中,如刘勰《文心雕龙·知音》篇所谓“缀文者情动而辞发,观文者批文而入情”,朱熹“读书须是以自家之心体验圣人之心”[3](P2887),王夫之“作者用一致之思,读者各以其情而自得”[4](P139—140) 等等,都是将读者的体验与理解纳入到了文本意义生成的整个过程,从而凸现了阐释者的主观能动性。
其次,从“意”的性质来看阐释者历史主体意识的确立。
史上对“意”的学术诉讼主要集中在主体归属的层面,而对于“意”的内涵与性质少有涉及。在论争者那里,后者似乎是个附加性的问题,“意”之主体归属既明,其内涵与性质自然相与跟随而明:诗人之意就是诗人之志,表现为诗篇的主旨;阐释者的“己意”就是读诗之意,表现为对诗篇内容的把握。但是,读诗之意的“意”,仍然是将“意”的根源归为客观的诗歌文本,不免陷入孟子所反对的“以辞害志”之困窘。如何才能将“意”真正落实在阐释者自己身上呢?笔者认为,联系孟子的“心性”论来分析阐释者之“意”的性质,也许不失为一条好的途径。
阐释者以自己的主体之“意”进入阐释过程,也就是以段玉裁所说的“心之所识”来建构文本意义。而作为阐释主体的“心”,在孟子那里一方面具有功能层面上的意义,如《孟子·告子上》所谓“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另一方面则是价值层面上的意义,表现为仁义礼智等道德规范的内化,此即所谓心性“四端”:“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孟子·公孙丑上》)心是人性之本、道德之源,是仁义礼智的安身处、发端处。所以,面对传世的儒家经籍文本,阐释者应该涵养、培育一颗无障无蔽、不偏不执、激荡张扬、澄澈通明的仁义之心,这可视为孟子理想中的阐释者之“己意”。就内涵而言,它“养明”“去蔽”、“以仁存心”、“以义存心”,是充塞着仁义礼智的“恒心”;就性质而言,它刚健中正、澎湃活泼,是洋溢着“浩然之气”的道德精神。阐释者秉持这样的主体“心意”进入经籍文本,自然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所得文本意义不出仁义礼智四端。即以《诗经》阐释为例,便可看得相当分明。《诗经》的作者不一,产地不一,形成时间不一,大部分都是民间百姓“率性而作”的“里巷歌谣”,所表达的内容与情感倾向本来极其复杂,但秦汉儒家却几乎能从每一首诗篇中寻绎出道德教化意义来,这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恐怕就是他们在进入诗文阐释之前,就已经预设了一个“以仁存心”的主体立场。
对阐释者之“意”做出理想性的规范,也就是对阐释者主体意识的内涵与性质予以界定。在标扬阐释者主体能动性的同时,又规范着这种能动性的价值指向。尽管在孟子那里,人之初,性本善,仁义礼智的价值指向似乎先验而绝对,但在我们今天看来,这种先验而绝对的伦理显然只是儒家特定文化理念的反映,只能被视为一种历史性的主体意识,即一定历史阶段、一定历史语境下对主体意识的某种规定。
在西方解释学中,阐释者的主体意识可以说到了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那里才真正建立起来。他们一方面强调只有在文本与读者的对话、交流中才能生成意义,赋予了阐释者参与意义建构的主体能动地位;另一方面又强调阐释者作为主体存在必然是一种历史主体的存在,有着历史的规定性和局限性,即他不可避免地带有前理解结构或曰偏见,并不能以清明无染的绝对“贞洁”去忠实地复现文本的原意,只能从自己的当下视域中进入文本阐释。而孟子对阐释者主体意识的标扬,在肯定阐释者主体能动地位的同时,同样也包含了某种类似于前理解结构的规定性。区别在于,海德格尔的“前理解结构”与伽达默尔的合法“成见”,强调的是历史和文化传统的先在性对阐释主体的浸淫与影响,而孟子激荡张扬、澄澈通明的仁义之心,强调的则是儒家伦理诉求对阐释主体价值观念的规范与塑造。
二 逆:意义在心理会通中生成
在理解活动中,如果说阐释者之“意”是预在的起始点,那么,作为阐释目标的作者之“志”便是至高追求的末端点,意义生成于两者之间的融通。孟子把这一融通的心理过程命名为“逆”。
何谓“逆”?许慎《说文解字》注云:“逆,迎也。”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云:“逆、迎二字通用。”郑玄注云:“逆,逆受而钩考之。”综上所述,“逆”大体上有三个义项:一是迎纳、接受;二是钩考、测度;三是追溯、反求。这三个义项,在“以意逆志”中,作为主体之间的心理与精神交流活动均可成立,分别为:以己意迎纳(或接受)作者之志;以己意钩考(或推究)作者之志;以己意反求(或追溯)作者之志。
何以要“逆”?因为阐释者之意与作者之志两者之间存在距离。其一是语言的阻隔。语言在历史中漂移,可能产生了能指与所指的变化,使得作者之志模糊了。所以必须字求其训,句索其旨,钩考沉浮,出入文辞,辨字句于毫发之间,析义理于微言之中。其二是文化的间距。阐释者与作者之间总有一段由历史所形成的文化上和时间上的距离,这种主体之间的“断裂”往往导致沟通不易。因此阐释者必须“披文以入情,沿波讨源”,追溯推究,体察品味。在反求中努力克服历史间距和文化间距,与古代作者会千年于一堂,虽“世远莫见其面”,但“觇文辄见其心”,此心与彼心相与契合,成为刘勰笔下的“知音”。
进一步,何以能够“逆”呢?当下的阐释者为什么能够跨越茫茫历史时空所带来的文化间距,实现与古代诗人心理之间的会通?笔者认为,孟子的“以意逆志”说,虽然是在和弟子讨论《诗经》意义的具体语境中提出的命题,但深入考察,这一理念实际上与孟子的整个“心性”论思想有着深刻的关联。正是因为秉有深刻的哲学思想作为理论基础,这个命题才得以成为后世儒家经籍阐释中尊奉不已的纲领。概略言之,孟子的“心性”论在两个方面支持了“以意逆志”说:其一,人性本趋同,是故不同主体之精神与心理有融通之基础;其二,人之初性本善,是故不同主体之精神与心理交流主要在道德伦理层面上展开。
首先,在孟子那里,人性趋同是人的精神心理世界得以互相沟通的终极根源。《孟子·告子上》说:“故凡同类者举相似也,何独至于人而疑之?圣人与我同类者,……口之于味也有同嗜焉,耳之于声也有同听焉,目之于色也有同类焉。至于心,独无所同然乎?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谓理也,义也。圣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孟子认为同类相似,人的生理感觉与审美知觉有相通的一面,人心亦然,这是对先圣孔子“性相近”(《阳货》)说的继承与逻辑证明。其次,孟子进一步明确把趋同相近的人性归为仁义礼智等道德规范的内化:“仁,人心也。”(《孟子·告子上》)孟子由同类相似而推及人性趋同,再进一步推及人之初性本善,这一理论推导为“以意逆志”提供的支持或规范是:第一,不同生命主体之间内在相同的人性,使得精神与心理有了共同的基础,有了化合、融通的可能性。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己之所欲即他人之所欲,己之所不欲即他人之所不欲。一个“万物皆备于我”的我心,可以体察、感应、融通一个与之类同的彼心。如《韩诗外传》卷三所谓:“圣人以己度人。以心度心,以情度情,以类度类,古今一也。类不悖,虽久同理。”第二,孟子进一步把共同人性设定为“仁义礼智”四端,赋予生命主体之精神与心理交流以鲜明的道德伦理导向,这就深刻影响了后世儒家对传统典籍的阐释,使得他们总是习惯于去从传统典籍中爬梳古圣先贤的昭昭仁德,寻觅纲纪人伦的谆谆教化,在很大程度上规范了意义生成的单一方向。对于儒家来说,解释从来不是为了获取某种客观的认识,也不是如何准确把握作品主旨,而在于体认、追慕、神会甚至践履作者(往往被神化为“圣人”)刚健活泼的志意。以意逆志,可谓恰切地表达了人伦心理与人伦心理、道德精神与道德精神之间复杂的会通、渗透、熏染关系。
由此看来,阐释者之意之所以能逆通古诗人之志,是因为二者本质相同,同为心性“四端”。在具体的诗歌理解活动中,阐释者以人之常情去体察,以义之常理去推究,实现诗人与读诗人之间道德精神与人伦心理的融通,最终破解诗人的美刺意图。由于诗的文辞可能运用了夸张的修辞手法或比兴的表达方式,所以阐释者一方面只有借助语言文辞才能逆志,另一方面又不能完全拘泥于文辞,必须辅之以“意”的测度,通过心理体验来准确领会诗人意图。
经由阐释者与诗作者的心理会通来追问诗歌意义的生成,这是一个具有重大价值的理论发现。因为文学阐释作为一种意义领悟的主体行为,归根到底是一种精神—心理的活动。在此活动中,作者、文本与读者一起进入到意义生成的本体世界。文本架起理解和解释的桥梁,缺席的作者通过文本而在场,在场的读者通过文本实现与作者的会通。这样,作者的精神心理世界与读者的精神心理世界就以文本为中介形成了交流和对话关系,理解和解释必然在更深的层面上体现为精神与精神的碰撞、心理与心理的融通。
回顾西方解释学的发展历程,我们可以发现,从18世纪语文学方法论到19世纪普遍解释学的飞跃,就鲜明昭示出,理解和解释不仅仅是一种语言训诂、语法分析和内容考释的技巧,而更应该是一种对主体生命精神和心理的把握。早在阿斯特对理解方法的三种区分中,就已强调“精神的理解”(即对作者和古代精神的理解),相对于对文本的“语言理解”(即文本语言形式的理解)和“历史理解”(即文本内容的理解)来说,是“真正的和更高的理解”。[5](P6) 施莱尔马赫在此基础上提出,文本的意义就是作者的意向或思想,而理解与解释就是重构作者的意向或思想。通过语言解释完成客观的重构;通过心理解释,即努力从思想上、心理上去设身处地地体验作者的原意或原思想,则可以实现主观的重构。[6](P61,71) 狄尔泰进一步拓展了这种精神—心理的解释。在他看来,人文科学的对象是过去精神或生命的客观化物,而理解就意味着通过这个客观化物去把握过去的精神或生命之表现,“我们把我们由感性上所给予的符号而认识一种心理状态——符号就是心理状态的表现——的过程称之为理解。”[7](P76) 因而最有效的解释方法就是生命的“体验”和“再体验”,获得精神的“共鸣”。
在中国源远流长的经籍阐释传统中,孔子可以说是对历史流传物进行心理解释的先驱。他不仅在理论上提出“诗可以兴”“兴于诗”,认为《诗经》能感发人的心理志意,而且在教育弟子的实践中,尤为注意引导他们对诗篇作“举一反三”“触类旁通”“告诸往而知来者”的心理体验与联想。而孟子首创的“以意逆志”说,则可以视为中国古代诗学心理解释理论的纲领性命题。后世陆九渊称读书当“沉涵熟复,切己致思”[8](P40),朱熹称读书当“虚心涵咏,切己省察”[3](P179),以及中国诗学接受理论中悠远的“以味品诗”的传统,都是强调文本意义的解读与阐释应该超越“文”“辞”的具体语境层面,力求通过阐释者微妙复杂的心理体验,来会通、迎合作者的情思,这无疑是对“以意逆志”命题的继承与弘扬。
三 “以意逆志”的当代启示
孟子的“以意逆志”命题,不仅在后世的经籍阐释特别是文学阐释中产生了重要影响,而且在多个层面上具有和当代理论链接、对话的可能性,对我们今天深入认识文学理解活动仍然有着深刻的启示意义与价值。
(一)与“主体间性”理论的对话 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是西方20世纪以胡塞尔、海德格尔、伽达默尔为代表的现象学和解释学哲学所凸现的一个范畴。胡塞尔在肯定先验主体性(先验自我)的同时,提出了主体间性概念,以求摆脱唯我论的困境。而海德格尔则开始由历史主体性向主体间性(共在)转化。伽达默尔的解释学把解释活动看作一种主体间的对话和“视域融合”;哈贝马斯的交往理论把原子式的孤立个体转换成为交互主体。哲学领域中这种主体间性的转向同时也深刻地影响了各门现代人文学科,形成了人文学科的一个新的研究焦点,即关注主体与主体的关系,把对象世界,特别是精神现象不是看作客体,而是看作主体,研究或规范一个主体怎样与完全作为主体的另一个主体的相互作用,并确认自我主体与对象主体间的同在性、平等性和交流关系。
金元浦是国内最早将主体间性问题引入文学研究语境的学者之一。在他看来,文学研究领域中,主体间性的涵义及本质规定性主要表现为:“1.主体间性在社会生活和文学实践中所表现的主体间的相互交流、相互作用、相互否定、相互协同,即社会性的交互主体性的涵义;2.主体间本位在交流实践及其验证中达到的客观性、协同性、解释的普遍有效性和理解的合理性;3.主体间性在语言和传统中运作的历史性内涵。”[9](P240) 这里第一点强调了文学主体间性的社会意义,指出文学在本然形态上是由“作者—文本—接受者”等诸多元素组成的一种主体间的存在。第二点指出,文学阐释的普遍有效性和文学意义的相对确定性,表现为文学解释共同体之间在文学交流中达到的一定程度的一致性。第三点强调,对于历史流传的文学史作品的接受与阐释,不仅在共时的维度上进行,而且在历时的维度上展开。因之,历时性的对话与交流必然展现出主体之间的丰富的历史性内涵。
孟子的“以意逆志”说,认为对文本底蕴的把握,既无法做到完全屏弃自我,以“涤除玄览”“心斋”“虚静”的方式去复原作者之志,也不宜过度膨胀“己意”,将作者之志简单地纳入自己的“己意”,而主张经由“逆”的方式,以己度人,以心度心,以情度情,在人之常情中,在义之常理中,实现作者之志与阐释者之意的融通。可以说,这个沟通作者与阐释者的常情、常理,客观上体现了一种朴素的“主体间性”思想。当然,客观上的相通与暗合,并不意味着主观上的理论自觉。孟子所“自觉”认识到的,其实只是伦理学层面上相近趋同的人性,也就是他强调的“心性”四端。我们今天所谓的“文学主体间性”,在他那里,顶多只有“伦理学主体间性”的意义。
(二)与“视域融合”理论的对话 “视域融合”(Horizont verschmelzung),是伽达默尔哲学解释学的一个重要理论。“视域”概念原本出自尼采和胡塞尔,表示看法、观点或见识。伽达默尔把它移用于自己的解释学领域,认为“视域(Horizont)概念本质上就属于处境概念。视域就是看视的区域(Gesichtskreis),这个区域囊括和包容了从某个立足点出发所能看到的一切。把这运用于思维着的意识,……以此来标示思想与其有限规定性的联系以及扩展看视范围的步骤规则。”[1](P388) 通俗地说,“视域”就是主体受限于特定处境,从某一立足点所能看到的一切内容。一个主体的立足点越高,他的历史视野、文化视野就越是开阔,越能够按照大和小、远和近去正确评价视野所及的范围内一切事物的意义。“获得一个视域,这总是意味着,我们学会了超出近在咫尺的东西去观看,但这不是为了避而不见这种东西,而是为了在一个更大的整体中按照一个更正确的尺度去更好地观看这种东西。”[1](P392)
美国学者霍埃指出,在解释学中,“视域这个术语是用来描述解释的处境特征或受语境制约的特征的。”在解释活动中,阐释者和他要理解的文本具有各自的视域:文本包含作者的视域,称为“原初视域”(the past horizon);阐释者具有在当下具体时代和环境中形成的视域,称为“当下视域”(the present horizon)。[10](P96—97) 历史的代际传递运动,把原初视域与当下视域分向历史之纵向坐标系的两端,从而在两者之间构成了一种时空距离,这就意味着原初视域与当下视域不可避免地存在差异与冲突。因之,“每一种与流传物的接触,本身都经验着本文与现在之间的紧张关系。”[1](P393) 从某种意义上讲,理解与阐释就是“暴露”并缓解这种紧张关系,最终归向两方视域的融合,即各自超越自身视域范围的局限性,生成一方新的意义视域。
孟子的“以意逆志”说,朴素地暗合了这种“视域融合”的理论。他将阐释者之“意”与作者之“志”分而别论,客观上体现了两者之间的差异和区分,指明它们分属各自独立的两种状态;又以“逆”的心理活动架起“意”与“志”的桥梁,使得两者可以往来融通,这与伽达默尔“视域融合”的理论观点在精神实质上无疑有相通之处。但是,孟子更多强调阐释者之意与作者之志在仁义层面上的相同性,而对于它们各自的历史规定性,即由其自身历史文化语境所决定的当下特殊性,并没有深刻的理论自觉。而后者,恰恰是伽达默尔所强调的“理解的历史性”。
收稿日期:2006—02—18
标签:主体间性论文; 解释学论文; 孟子思想论文; 阐释者论文; 文本分析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读书论文; 诗经论文; 国学论文; 孟子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