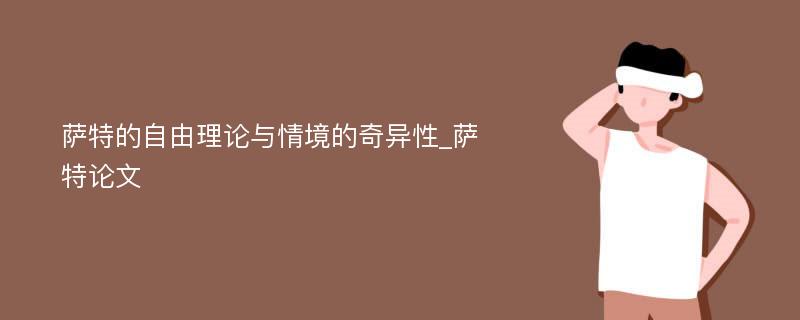
萨特论自由与处境的吊诡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萨特论文,处境论文,自由论文,吊诡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565.5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3060(2006)01-0026-08
一、决定论与自由意志的传统讨论
就行动的层次而言,人与世界的关系究竟为何?这向来是哲学所关心的重要问题之一,传统的决定论与自由意志(determinism and free will)之争论便是表达了人与世界之关系的不同看法;主张自由意志者认为人的行动可以不受任何原因所决定,主张决定论者则主张世界的客观结构不仅支配自然现象也支配着人的行动。但传统上有关自由意志与决定论的讨论所导致的两难是:无论赞成人有自由意志或无自由意志皆无法充分说明“为何人必须为自己的行为负责”这个问题。主张自由意志者,即一般所谓非决定论者(indeterminist),认为人的行为没有任何原因,它只是这样发生了,没有为什么,所以也无法被解释。既然行为是无缘无故发生的,我们无法知道为何这件行为会发生在行为者的身上,我们也就不能去追究行为者的责任。主张决定论者,认为人的行为如同自然现象都是有原因的,是可加以解释的,而且它主要受制于外在的种种现实条件、行为者的性格以及从小自环境所受的影响,所以表面上看起来人有自由的选择,实际上却不然,在受到这些内在外在因素决定的情况下,他没有自由,所以不须为自己的行为负任何责任。
我们是否可能跳出这个两难?传统上试图回避这个两难的方式有底下几种:首先,所谓“软的决定论”(soft determinism)接受“决定论”的前提,承认人的行为是有原因的,因而是可加以解释的,特别是透过人的性格或意念等主观因素来解释,但这却不表示人在某些时刻不能表现出与他的一般习性不同或正好相反的行为,只要这个可能性存在着,我们就不能说人不必为他的行为负责。其次,这个立场所理解的自由并非“非决定论”中所谓的“无缘无故”,而是指“不受外在人为束缚和不受内在精神恍惚影响而能实现自己的欲望意念”。它不再追问这些内在的欲望意念等等是否还有其它更为深层的原因。当一个人的行为是自由时,他自然必须为自己的行为负责。这个立场可说藉由重新厘清自由的涵义调和了决定论与自由意志,也回答了人是否该为自己行为负责的问题,尽管它对于“人的欲望意念是否还受更深层的原因所影响”这个问题却是有所保留。
如果我们坚持要清楚说明“人的欲望意念是否还受更深层的原因所影响”这个问题,则难免会走上“硬的决定论”(hard determinism)这条路,这个自从神学思想出现以来就普遍受到讨论,而在近代科学发达以后更广受支持的立场认为人的行为实际上就是受各种条件所支配,人根本不能自由决定自己的行为,自然也不必为它负起任何的责任。
如果上述几种立场都不能提供我们令人满意的答案,则所谓的“自由论”(libertarianism)也许可以提供我们新的思考方向,这个立场并不接受“决定论”的前提,它不认为人的行为可以像自然现象一般被客观的观察和解释,人的行为之所以独特就在于它不同于自然现象。但这是否意味着人的行为——如“非决定论”所言——是没有原因的呢?主张“自由论”者认为人的行为还是有原因的,只不过这个原因是在行为者身上,所谓主观上的原因,也就是所谓的理由(reason)。人的行为之所以不同于其它的自然现象还在于它是经由斟酌考虑(deliberation)之后而发生。亦即,人的行为在还没有发生之前它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可能选项让他去作选择,而他之所以会这么做一定有他的理由在。如果我们想要了解一个人的行为,便不能不将行为者主观上所赋于行为的意义纳入考虑。基本上“自由论”否定“决定论”的前提,它也否定“非决定论”的想法,它可说是以另起炉灶的方式回答了“为何人该为他的行为负责”这个问题。①
基本上本文认为传统有关决定论与自由意志的讨论都略过了“处境”(situation)的概念,忽略了它与行动之间的密切关连性。当我们探讨人该或不该为他的行为负责时,为何不去问他究竟是处在什么样的处境底下而有此行为呢?所谓的“处境”是不是因为它变化万千而不可能去加以说明呢?当我们说人的行动都离不开处境,都是在面对处境中的问题并试着加以解决时,它的涵义究竟是如何呢?本文将试着在萨特(Jean-Paul Sartre,1905—1980)的思想脉络中探讨这个问题。
二、行动、原因与动机
萨特探讨自由的问题是从厘清行动的概念入手。一开始,萨特就指出:“在人们尚未事先去解释行动这个概念本身内含的结构之前,居然就能对决定论和自由意志论进行无止境的论述,为了其中一个或另一个论点举出一些例子来加以印证,这真是奇怪的事。”② 萨特一语道破传统有关决定论与自由意志问题的形上学思考性格,人们急着争辩究竟自由意志存不存在,究竟人该不该为自己的行为或行动负起责任,却对行动概念本身视若无睹,更不用说要对行动的脉络也就是处境加以重视了。萨特究竟是如何解释行动的涵义呢?首先他说:
行动(act)这个概念包含着许多我们将进行组织并分等的从属概念:行动就是改变世界的面貌;就是为着某种目的而使用某些手段;就是造成一个工具性的、有机的复合体,以造成预定的结果,并且在这之中由于个个环节彼此紧密相连,以至于其中一个环节的改变会导致整个系列的改变。③
行动是人们藉以改变世界的一种方式,它不会单独发生,而是总处在特定的环节之中,而这些环节又是紧密地关联在一起。但是除此之外,更为要紧的是,萨特接着补充说:
一个行动原则上是具有意向性的。一位笨手笨脚的抽烟者不留神引爆了火药库,他不算采取了行动;相反地,当一个人受命炸开一处采石场,当他受命引燃了预定的爆炸时,他是采取行动了:他实际上知道他所做的事,或者可以说他有意识地实现了一项策划。④
行动必然带有特定的意向,是人基于某项特定目的而支使身体去从事一些动作,如果人的动作不是有意识发生的,则纵使在他身上发生了某些事件,也不能算是他的行动所产生的后果。萨特问,为什么人会采取行动?为什么会产生特定的意向呢?答案在于:无非是感受到有某一些欠缺,采取行动者意识到他缺少些什么,想要藉由行动来加以弥补。萨特举了古代罗马帝国的例子:
引起君士坦丁大帝要找一个城市来和罗马抗衡的意向在于他感受到实质上的欠缺:罗马太缺乏基督教的气氛,应当有一座城市来与它抗衡。⑤
君士坦丁大帝藉由建造一座全新的城市来弥补心中的某种缺憾,他希望加速整个罗马帝国的基督教化,而这个愿望在旧的城市——罗马,是不容易实现的。君士坦丁大帝的意图很明显,意向十分明确,因此他的行动不难被理解。现在的问题是,君士坦丁大帝之所以会有这个行动,是他对于整个当时的客观情势有所体认的必然结果吗?也就是换成另一个人当罗马帝国的皇帝也会选择同样的行动吗?或者是,这是君士坦丁大帝的特殊选择,换成另一个人就会有着全然不同的结果。前者被萨特称为原因(cause),后者则被他称为动机(motive)。萨特解释说:“原因的特征……在于对处境的客观领会。”⑥ 一个人的行动假如是理性的,那就是基于对整体客观情势的充分体会与把握,则任何人在相同情境底下都会表现出同样的行为来。原因是客观的,它是当下事物的状态向意识所揭示的模样。任何人只要不受情绪等主观因素的影响,总是会接受它作为行动的原因。相对而言,“动机通常被看作一种主观的事实。它是欲望、情感和激情的总体。”⑦ 萨特认为,当历史学家解释某些历史人物的行动,却找不到充分的原因时,不得已往往藉由动机来作说明。比如说,当历史学家不明白,为什么君士坦丁大帝明明在皈依基督教并不能带来任何利益的情况之下还坚持这么做,只好假设他有某种心理状态,某种动机,是只有他自己最清楚的。这种基于主观心态对于行动所作的解释往往会使得事件的发生成了偶然,因为换成另一个人,只要他有着不同的激情和欲望,他就会有不同的行动。虽然如此,萨特仍然在原因与动机之间看到了关联性,他指出:
于是,原因和动机是相关联的,正如自我的非显题意识(non-thetic self-consciousness)是与对象的显题意识有本体论关联(ontological correlate)一般。又好比对某事物的意识是自我的意识一样,动机同样只是对原因的把握,而不能是别的,因为这种把握是自我的意识。⑧
萨特举了一个实例作说明:
例如,我能加入社会党,因为我认为这个党是为正义和人类的利益服务的,或者因为我相信在我入党后它将会成为主要的历史力量:这就是原因。而我同时又能说我的入党是出于动机:对某些领域的被压迫者的怜悯或慈善之心,像纪德(Gide)所说的为站在“优越的一边”(" good side of the barricade" )而感到耻辱,或者甚至是复杂的自卑感,想惹恼周围的人的欲望等等。当人们肯定我是由于这些原因和这些动机而加入社会党时,人们能说些什么呢?很明显,这里涉及到两个完全不同的意义层次。如何将它们加以比较呢?如何确认它们在上述的决定中各自所占的部分呢?毫无疑问地,这是在通常情况下对原因和动机进行区分时所遇到的最大困难……。⑨
萨特认为原因与动机之间往往不能作明确的区分,它们总是有可能被放在天平的同一端被衡量,例如传统的决定论者就认为原因与动机无所不在,人类的行动背后无论如何总是有些密密麻麻大小不等的原因与动机,只要我们充分地认识它们,我们就会了解某个特定行动的发生不是没有理由的。萨特指出:
决定论深刻的意义在于在我们之中确立了一种在自己的不间断连续性。……动机引起了行动,就像原因导致结果那样,一切都是实在的,一切都是充实的。⑩
萨特能够认同决定论者将原因与动机看成一体,但是显然不能赞同决定论者所主张的,原因与动机本身会“引起”行动。萨特问,一群工人之所以会起来闹革命是“因为”他们的贫穷,或是“因为”他们所承受的痛苦吗?贫穷与痛苦本身是引发他们采取行动的动机吗?如果工人们向来将他们的贫穷状态视为平常,如果他们对于别人眼中的“痛苦”生活向来甘之如饴,则他们是不可能寻求任何改变的,他们甚至于会把那一种生活形态看成“工人的条件”,工人自然而然地就是该过着这种生活,不是吗?在此情况之下,这种痛苦本身便不能是他们行动的动机?那么,什么时候工人才会“动起来”呢?
正如前面所提到的,行动者必须感觉到有所欠缺,他必须克服并被否定“认为他的痛苦是很自然的”这回事。但是这如何可能呢?首先他必须跟他当下的状态保持一段距离,省思考察他的苦难是怎么一回事,他必须思索痛苦之为何物。萨特生动地描述了这个省思的状态。
从人们能够设想事物的另一状态的那天起,一束新的光线就照在了我们的艰难和痛苦之上,我们就决定这些艰难和痛苦是不堪忍受的。(11)
如果我们从来不去思考自身的痛苦是怎么一回事,而只是习惯它,则痛苦本身是不会引发任何行动的,在此萨特颠覆了一般的看法。而引出两个重要结论:“(1)任何事实的状态,不管是什么样的(社会政治、经济结构、心理‘状态’,等等)本身都不可能引起任何一个行动。因为,一个行动就是为自己(for itself)向着不存有的东西的投射,而存有的东西自己完全不能规定不存有的东西;(2)任何事实的状态都不能规定意识把它当作否定性或欠缺。”(12)
任何的事实状态本身是不可能被看成是否定的状态,唯有当事人经由反省并预期另一种状态的出现,我们才可能回过头来否定当前的状态,在对于期待中的状态感到有所欠缺的情形之下,行动乃可能发生,这时,工人的“痛苦”才可能成为行动的动机。用萨特自己的话来说:
仅仅因为我透过将自己虚无化以走向我的诸多可能性而脱离了在自己(in-itself),这在自己才能取得作为原因或动机的价值。原因和动机只能在一个恰恰是非存有物的整体(an ensemble of non-existents)即被谋画的整体内部才是有意义的。而这个整体,最终就是作为超越性的我本身;就是应该在我以外成为我自身的那个我。(13)
换言之,“一切行动的必要和基本的条件就是行动着的存有的自由。”(14) 自由基于自由的谋画复活过去的动机,重新评价它们,因此“过去的动机,过去的原因,现在的原因和动机,将来的目的透过存在于原因、动机和目的之外的自由的涌现本身而组成一个不可分割的统一体。”(15) 既然行动的基本条件是自由,那么我们就必须对萨特的自由概念作一番说明。
三、自由与处境
萨特的自由概念是所谓的“绝对自由”(absolute freedom)或“存有学的自由”(ontological freedom),这是人作为“为自己的存有”(being-for-itself)所具有的根本特质,人必须勇于面对自由选择并为之负起绝对的责任。他的意思是,人是自由的,而且不得不自由。这里的自由不是指不受外在束缚之谓,也不是作为道德必要预设的意志自由,萨特说人的本质是自由的,只因他责无旁贷地必须选择自己的未来。放弃选择也是一种选择,虽然人们往往不愿意加以承认。就这个意义而言,人的自由乃是绝对的。
萨特的自由概念与他对意识的看法极为相关,在他看来人的意识之基本特性乃是“超越”(transcendence),人总是朝向未来,设定意向对象作为自己努力追求的目标,周遭事物则因我的意向性而获得特定的意义。萨特将人的意识称为“为自己”(for-itself),它不同于作为“在自己”(in-itself)的其它事物。“在自己”之物本身不会有任何的变化,它不会意欲自己的任何改变,但是“为自己”之存在者(就是人)就不一样,他会透过构想自己的未来改变现状。人的生命总是处在一个未完成的状态,不断在追求下一个理想,也不断在作选择,虽然他终究是想完成“为自己”和“在自己”的统一状态,只不过这是一个永远达不到的理想,只要人还活着,他就永远在追求着些什么,永远必须作选择,这是人不可抗拒的命运。如果有人想要放弃或排斥这种状态,萨特认为他就会处于一种自欺(bad faith)的状态。自欺是不道德的,也是对自己不负责任的做法。
我命定是为着永远超出我的本质,超出我的行动的动机和原因而存在:我命定是自由的,这意味着除了自由本身以外,人们不可能在我的自由中找到别的限制,或者可以说,我们没有停止我们自由的自由。就为自己想掩盖自己的虚无,并试图以在自己的存有模式作为他真正的存在方式而言,他正是在企图掩盖他的自由。(16)
“虚无”(nothingness)是人的意识作为“为自己”之根本特质,人在向未来投射之中,他不再是他原来的自己,他从理想的状态回头看自己,而否定眼前的自己。否定自己就是将眼前的自己虚无化,但是人们藉以否定眼前自己的理想既然还不是已实现状态,所以也是虚无。换言之,人生彻头彻尾都被虚无所贯穿。然而虚无不表示否定生命的意义,反而才能真正肯定人之为人的意义,如果人是固定不变之物,则它只能任人摆布,不能改变现状,是对人的最大否定。虚无或许用“缺如”来解释比较恰当,当人心中有个理想,因而对照出现状的种种缺失时,他就是处于一种缺如的状态。
我们已经看到,对人的实在来说,存在就是自我选择:他所能容纳和接受的任何东西都不是从外部,也不是从内部而来的,人的实在完全孤立无援,他被完全地抛置于这难以忍受的必须自我造就的必然性中——即使连最琐碎的部分都是如此。于是,自由不是一个存有:它是人的存有,也就是说人的存有的虚无。如果人们首先想象人是充实的,那么按着要在人身上寻找人在其中是自由的时刻或者心理范围就将是荒谬的:也可以说就像在一个预先就装得满满的容器中去寻找虚空一样。人不能时而自由时而受奴役:人或者完全并且永远是自由的,或者他根本就不自由。(17)
人由于体认到自由,必须为自己的选择负起全部的责任,感到无比沉重的负担,莫不想逃避之。因此他一方面意识到自己的责任,另方面却又想逃避之,而时时处于焦虑不安(anguish)的状态。人必须为他的选择负责,这是萨特存在主义(Existentialism)的核心思想。至于在萨特的自由理论中,为何会出现“处境”的问题呢?这跟自由的吊诡性有关,萨特指出:“只有在处境中才有自由,而且只有透过自由才有处境”(18)。这里意味着,人的自由虽是绝对的,他不得不自由,但是他的自由却是受到限制的,限制来自于人先天具有“现实性”(facticity),它是人生而在世不可改变的事实,例如,我某时生于某地,由不得我随意改变,又人终究必须一死,这是人所必须接受的事实,这些事实都使人意识到他的自由有其限度,不能为所欲为,爱怎样就怎样。但这些事实并不就等于处境,在萨特的眼中,任何处境的形成都是自由选择的结果,它在特定目的的光照之下自我呈现,相对而言,现实性则是混沌未明的,它尚未形成特定的形貌。换个说法,任何处境都是具体的(concrete),而现实性由于混沌未明而停留在抽象的层次。处境简单的说就是人对周遭事物之为利或为弊之体认,它是在“越过给定物而朝向一个目的”(19) 中展现,所以本身既非主观亦非客观,而是两者之间的关系。萨特说:
处境是为自己与在自己的关系,在此关系中在自己被为自己所虚无化。处境是全部的主体(他无非就是他的处境)以及全部的事物(除了事物别无他物)。处境是主体在他的越过(surpassing)中照亮了事物,如果你愿意如此说的话,它就是事物在与主体的关连性中表现自己。它就是完全的现实性,世界的绝对不确定性,我的出生,我的地方,我的过去,我的周遭世界,我的邻人,然后是我无所限制的自由使得我的现实性呈为现实性。(20)
总之,任何具体处境的意义都依赖于人所设定的目的和计画。没有一个处境是中立而与人无关的,处境一定是相对于某个人的某个构想才呈现出来,所以处境一定是有益或有害于达到这个目的。至于一个处境是具有帮助性或具有阻碍性,人有着绝对的自主权,这是他的自由。
萨特用五方面详细地说明处境的涵义,分别是我的地方,我的过去,我的周遭事物,我的邻人和我的死亡。萨特指出,在每个人的生命中具有一些如前提及的现实性,但这些现实性就像有待挖掘的矿产,在它们未显露之前,我不能确定它们究竟是什么模样,它们浑沌未明,等待着我去确定它们的意义。而此意义是完全依赖于我的意识我的自由和我的选择。但自由是不是可以跟这些现实性全然无关呢?萨特强调,如果缺乏现实性作为它可超越的对象,自由亦不是自由,这就是上面所说的自由的吊诡性。萨特说:
自由就是对我的现实性之体认。(21)
现实性一旦被自由给赋于意义,它就是可明了的,可明了的现实性也就是处境。底下分别以萨特自己所举的例子来加以说明。萨特说,为何有人会将留在Mont-de-Marson当作是不利的处境呢?这明显的跟他对自己的期望有关,如果他一心一意想在家乡发展事业,则他应当会将他的地方当作是有利的因素;只有当他想离开家乡却又备受阻挠无法如愿时,他才会抱怨他所处的地方对它是不利的。那“单纯的在家乡”不是一件客观的事实吗?萨特说,这种“客观的”描述是显不出“我的地方”之意义的。这里的重点在于,什么叫作“我的地方”?每个人对于他自己所处的地方不会没有一些感受,一些想法,而这些感受和想法究竟是怎么来的呢?无非就是我对自己未来的一些期望和构想,在我的目的之“光照”下,我的地方不会是平淡无味的几何平面或点,它总是透显出某些意义来。同样,我的过去也总是透显出某些意义来,不会只是时间之流的某些段落或点而已。而它们的意义正是来自于我对自己未来的选择。萨特举老兵是否接受新政府安排为例,如果他接受政府的安排,那他等于是对自己过去所参与之战役的意义加以否定,如果不接受,那他就是对这段过去予以肯定。一般人也许会认为,一个人会不会作某个决定,受过去的影响很大,因为过去如何如何,所以现在才会如何如何。但萨特强调,“我的过去”本身不会发号施令,除非我赋于它力量,也就是使它具有某些特定的意义。然而这些意义是如何构成的呢?无非又回到我对自己的未来之构想上。当人们说,我的过去所造成的处境就是如此,我没有别的办法,萨特会说,这是一种逃避责任的说法,过去本身不会塑造现前的处境,是我对未来的选择让“我的过去”塑造了我的处境。萨特用非常简短的句子表达:
确切的说,当我出生时,我来到一个地方,但对此一地方我却是负有责任。(22)
我不能决定生于何处,但是要为我的出生地负起责任来,因为出生地对我所具有的意义决定于我对未来的选择,而此一选择完全操之在我。
就周遭事物而言,萨特举的例子是,如果有一块大石头摆在我眼前,则我所遭遇到的是帮助性的还是阻碍性的处境呢?萨特认为这完全决定于我的计划和目的,如果我的目的在于赶路,则这块大石头是阻碍,我所遭遇到的是阻碍性的处境。但如果我的目的不在于赶路,而在于看风景,则眼前的这块大石头却是可以被我当作垫脚石,有利于用来欣赏风景。
在我的处境面向中,“他人”和“我的死亡”比较特殊。首先萨特指出,每个人总是会碰到和使用不是他所建构出来的意义结构,例如他所使用的语言,他所接触的种种器具。人好象是被动的非承受这些由他人所创造出来的意义结构不可,但是萨特提醒我们,语言本身不会发言,他说:
为了要让它显现,为了要让不同的字彼此关连起来,为了让它们彼此拴住……于是有必要将它们综合起来,而此综合的力量并不来自于它们本身……所以说只有在说话者的自由勾画当中语言的法则才被组织起来,藉由说话我塑造了文法。自由乃是语言法则的唯一可能基础。(23)
由此看来,关于他人的问题和“我的地方”等等面向似乎没什么大的差别,但重点是他人之为他人还在于他也是自由的,而此一自由的主体会将我视为客体,结果是我体认到在这个世界上我不是唯一的主体,这个体认可以说是对我的自由的最大限制,因为此一限制的缘故,我最能认清我原来一直都在处境中这个事实,我的自由原本就必须和它的限制打交道。
不过话说回来,他人再如何地限制我,首先还是得经过我的自由的认可,如果我不让他限制我,不把他当一回事,他人对我也是莫可奈何,萨特的例子是,只有当我先把自己当作犹太人别人才有可能把我当犹太人排斥我,也唯有如此才能感受到“身为犹太人”的处境。总而言之,我自己对他人是一个什么样的存有(being-for-Others)最后还是决定于我自己所设定的目的。(24)
在“我的死亡”这个问题上,萨特也强调它跟“他人”问题息息相关。首先萨特反对人可以等待死亡这样的说法,他认为除非一个人被判了死刑或是得了癌症之类的绝症我们才可说人是在等待死亡,否则人何时会死变量太多让人无法确定。他用一个俏皮的比喻来说明这个情况,他说死亡对人来讲就像是一个被判死刑的人在就刑前却突然死于流行性感冒,萨特想说明的乃是,死亡可能无缘无故地突然降临,但也可能无缘无故地无限延后。总之,“我的死亡”之降临本身就已经充满了变量,所以不可能被等待,更不可能是我计画或投射的对象。萨特在此一再提到海德格的死亡概念,他不认同海德格强调死亡对人体认生命有限的意义,除了生命的有限性因为死期的不确定而不能确定之外,他还强调,人的有限性其实不必然必须透过“我的死亡”来说明,因为纵使人不会死他还是有限的(能力有限,知识也有限等等)。萨特将死亡的问题转移到别处,他所关心的是,一个人一旦死亡,他就不再能建构自己的生命意义,失去了主体性,变成他人眼中百分之百的客体。死亡把自己带向了客体的存有,就如同当我还活着的时候,也会被他人视为客体一般,问题是,只要我还活着,我就有机会抗拒别人将我客体化,可是一旦死了,这个抗拒也就跟着消失了,我只具有“客体的意义”,任人摆布。由此可知,“我的死亡”作为处境与他人是离不开关系的。萨特说:
何谓死亡?无非就是现实性和为他人之存有(being-for-others)的某个面向,亦即,无非是给定物(the given)(25)
人作何种选择,完全操之在己。所以萨特主张人必须为他所处的环境之意义负起全部之责任。这种想法可说非常肯定人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但是推到极端却不免产生有些令人不解的结论。例如萨特宣称如果我参加了战争,那战争就成为了我的战争,意思是说,我不能说我被迫参战,因为我大可选择逃兵或者自杀来抗拒参战,既然我没有这么做,我就等于是作了选择,而且是自由地作了选择。同样,萨特强调,一个囚犯仍然是有绝对自由的,因为他可下定决心逃狱,它不能因为门禁森严而自哀自怨,说自己没有自由。在萨特眼中并没有所谓“受环境所迫,无奈的去做一些自己并不想做的事”的情况。换言之,人不会受环境所迫,有的只是人选择了环境对他的支配。
萨特对人的自由之高度肯定造就了它的存在主义思想,人并不具有事先给定的本质,人的处境犹如他的本质都是人自由选择的结果,所以萨特一方面注意到人生而在世有不可逃避的现实,但此一现实本身不能决定我一定会如何行动,它的意义毕竟是经过我的自由选择才确立的。在自由与处境的关系上自由还是有着优先的地位。
注释:
①Feinberg,Joel( ed.) ,Reason and Responsibility:Readings in some basic problems of philosophy( 4[th] edition) [C],Encino( Cal.) :Dickenson Publishing Company,1978.
②、③、④Sartre,Jean-Paul,Being and Nothingness( tr.by Hazel Barnes) [M],London:Methuen & Co.LTD( 简称BN) ,1957,p.433.
⑤、⑥、⑦、⑧、⑨、⑩Sartre,Jean-Paul,Being and Nothingness( tr.by Hazel Barnes) [M],London:Methuen & Co.LTD( 简称BN) ,1957,p.434,p.446,p.446,p.449,p.447,p.440.
(11)、(12)、(13)、(14)、(15)Sartre,Jean-Paul,Being and Nothingness( tr.by Hazel Barnes) [M],London:Methuen & Co.LTD( 简称BN) ,1957,p.435,p.435,p.437,p.436,p.450.
(16)、(17)、(18)、(19)、(20)Sartre,Jean-Paul,Being and Nothingness( tr.by Hazel Barnes) [M],London:Methuen & Co.LTD( 简称BN) ,1957,p.439,p.411,p.439,p.548,p.549.
(21)、(22)、(23)Sartre,Jean-Paul,Being and Nothingness( tr.by Hazel Barnes) [M],London:Methuen & Co.LTD( 简称BN) ,1957,p.494,p.495,p.518.
(24)Sartre,Jean-Paul,Being and Nothingness( tr.by Hazel Barnes) [M],London:Methuen & Co.LTD( 简称BN) ,1957,p.526.
(25)Sartre,Jean-Paul,Being and Nothingness( tr.by Hazel Barnes) [M],London:Methuen & Co.LTD( 简称BN) ,1957,p.54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