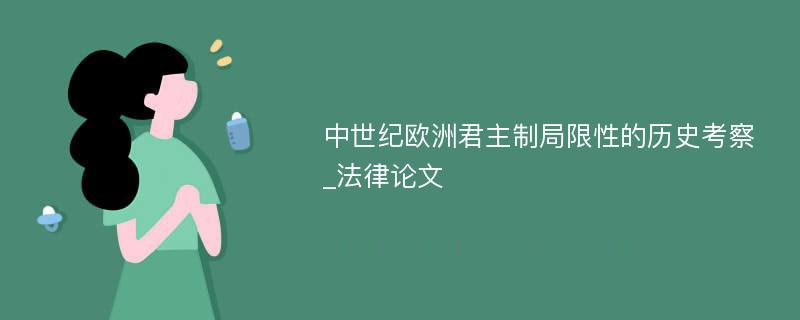
中世纪欧洲王权有限性的历史检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王权论文,欧洲论文,中世纪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9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1505(2006)02—0022—05
中世纪的欧洲同时并存有多种政治实体,对应地存在多种法律体系。其中,一个有趣而影响深远的历史及法律现象是:各王国的君主理所当然地要服从法律。这既不是口耳相传或文献中记载的轶闻花絮,也不是有赖乎个别明主贤君个人自觉的偶尔的现象,而是一种普遍的政治与法律实践,也是一种牢固的理念。剖析这一重要的制度现象及其原因,有利于加深对西方法治传统的理解,也有助于我们树立法律至上的观念。
一、王权有限性的制度举要
自11世纪末开始,无论是北欧还是南欧,从欧陆腹地到不列颠岛,有许多独立王国的法律都明确规范着王权的运作,强调王权是有限的权力,并不是国王个人可以为所欲为的,王权并非至高无上,而是受到法律制约。
在北欧,1241年出现的斯堪的纳维亚的第一部官方法律汇编《日德兰法书》是这样开头的:“国家应根据法律建立”;在欧陆腹地,13世纪早期写成的《萨克森明镜》规定道:“如果一个人的国王和法官做不正当行为,那么他必须加以抵制,而且他必须对国王和法官的每次不当行为加以阻止,即使后者是他的亲戚或封建领主也一样。因而他并不违背他的忠诚。”西南欧的阿拉贡的有一项著名的法律准则,即只要国王履行其职责,臣民就要服从他,“否则的话就不然。[1](P357)”
东南欧的匈牙利,1222年国王安德鲁二世(AndrewⅡ)被迫签署了《金玺诏书》,其中有各种有利于“高层低级贵族”(即自由民)而限制王权的规定。《金玺诏书》规定国王及其继承者承担以下义务:每年在一个固定的时间和地方召开议会:“任何贵族非经依法传唤和判罪,不得因任何强权者的意愿而被捕,或受伤害”;“不得征税、颁发货币或未经邀请而去巡视贵族的地产、房屋或村庄”;“未经议会同意”,“不得把官职授予进入王国的任何外国人”。进一步的义务还有,不得授予世袭官职;不得在短于12个月的间隔内发行新的货币;如果任何一个人依法被宣判有罪,那么任何强权者的袒护都不能使他不受惩罚。《金玺诏书》最后说:“我们还规定,如果我们或我们的任何一位继承者在任何时候违反了这项法规的条款,那么,我们王国中的所有主教和高层低级贵族,现在和将来的每一个人,都将因此拥有不受控制的、通过言语和行动的反抗权利。这种权利是永恒的,它并不招致叛国的指控。[1](P358)”由此可见,《金玺诏书》更大程度上强调的是对王权的限制,对应地则是保护自由民的权利。
最著名的限制王权的事件和法律,出现在不列颠岛的英格兰。1215年英格兰国王在贵族和教会的迫使下签署了《自由大宪章》[2](P144—154),据此,国王在法律上必须承担的义务包括:不经“我们王国的地方全体会议”的同意,不得征收任何兵役免除税或贡金(第14条);“民事诉讼……应当在指定地点受理”(第17条);“不得凭借某种没有确凿可信证据的指控使任何人受审”(第38条);“任何自由民都不受逮捕、监禁、没收财产、褫夺公权、放逐或任何方式的伤害……除非那么做是按照与他地位相等的人的合法判决或按照国家法律”(第39条);“在权利或审判上,不得偏袒任何人,也不得拒绝或拖延任何人”(第40条);“所有的人都可以自由的离开和进入英格兰,但战时除外,国内被褫夺公权的那些人和与我们交战的人除外”(第41条);“只有通晓法律的人才能任命为法官、治安长官、郡长或执行吏”(第45条)等等[1](P357—358)。并且,《自由大宪章》的第61条还极为详细地规定了在国王没有履行上述义务时,制裁国王的程序。凡此种种的规定,不但于具体事项和可操作性的程序上明确地限制着王权的运作,而且,这些也为后世的“法治”原则的形成提供了精神内核。因此,有学者分析该法律文件后指出,“在宪政的意义上,国王如今处于法律之下”[3](P125)。
当然,这种法律的统治在实践中并不总是得到不折不扣地落实。当时的一些强势的国王,如西西里的罗杰二世(RogerⅡ,1112—1154)、西西里和德意志的弗雷德里克二世(FrederickⅡ,1217—1223)都在一定程度上实行中央集权政策,或多或少地追求君主绝对化的倾向,但他们也无不利用法律来实现其统治,把制定法律看作国王职责的一部分,声称应当受到自己制定的法律的约束,在合法地改变法律之前,他们必须服从法律,必须在法律之下统治(rule under law)。与前述匈牙利、英格兰不同的是,他们的强势在多元权威的对垒中还是有所显现的,即以法律明确地确立了王权对教会、封建贵族、城市公社和普通民众的最高权威。
二、王权有限性的理论阐述
法在王上的上述制度性规定得到了12—14世纪诸多理论家和法学论著的阐发与支持:
首先,以契约论作为王权有限性的理论依据。14世纪初,有思想家指出,国家起源于人对自己境遇的理性认知,这使得他们选择一人充当他们的统治者,并以契约的方式使自己受制于国王。他们把国家的起源归因于理性、说服以及人民的同意[3](P121)。更有甚者,1324年出版的《和平的捍卫者》一书坚持共和主义的立场,认为国家的统治者是人民,人民设立统治者并不是不可撤回的。人民可以监督或废黜统治者,统治者不过是“辅助性的、工具性的、起执行作用的。[3](P120)”在“所有的世俗法学家都认可统治权力的行使来自人民”、人民从未终局性地放弃其权利的同时,教会哲学家也无一例外的反对世俗的专制主义。13世纪的圣托马斯·阿奎那(St.Thomas.Aquinas,1227—1274)认为王权起源于人民,并把它解释为与人民之间的协议。
其次,初步述及了限制王权的现实途径。阿奎那从《罗马法典》和上帝的权威出发,指出:“‘甚至我们的权威都以法律的权威为依据。事实上,权力服从法律的支配,乃是政治管理上最重要的事情。’……按照上帝的判断,一个君王不能不受法律的指导力量的约束,应当自愿地、毫不勉强的满足法律的要求。[4](P123)”对于国王应当受法律制约,英格兰的法学家布拉克顿(H.D.Bracton,约1216—1268)1259年在其所著的《论英格兰的法律和习惯》中,也有重要的论述。虽然身为王室法学家,布拉克顿仍坚持认为:国王处于“上帝和法律之下”;国王有义务服从法律;不是国王创制法律,而是法律造就国王。“英格兰的法律和习惯……既然都已经人们同意或认可,并经国王誓言的确定,那么便永远不得修改和破坏,除非经过相同程序。”布拉克顿还逐字引述了古罗马法学家帕皮尼安的格言:“法律是共和国的共通答问。”而在解释古罗马另一位法学家乌尔比安的格言“国王所好即具法律效力”时,布拉克顿指出,这“并非国王意志的鲁莽胡来,而是依据权贵同伴的建议,在慎重考虑和讨论后,由国王授权正当确立的事情。[5](P58—59)”它表明了非经权贵们的同意,国王的意志不是法律,国王并不是凭单个人的意志就可以为所欲为的。正当程序和平等贵族的同意是限制王权的现实途径。
再者,肯定了反抗暴政、诛杀暴君的合法性。
1159年轰动欧洲的《论政府原理》一书中这样写着:
“诛杀一个暴君不仅是合法的,而且也是正确和正义的……对于践踏法律的人,法律应当拿起武器反对他,对于努力使公共权力形同虚设的人,公共权力将狂猛地反对他。……暴政不止是对公众的犯罪,而且还是一种更有甚于此的犯罪——假如能有这样一种犯罪的话。……在践踏甚至应该统治皇帝的法律的犯罪中,……谁试图使他不受到惩罚,谁就是对自己和整个人类共同体的犯罪。”
此外,作者索尔兹伯里的约翰(John of Salisbury)还引用了查士丁尼《学说汇纂》中一段有关罗马人民把权力移交给皇帝的著名的话,并论证说,君王只是人民的“代表”或“代理人”[1](P343)。这里明白无误地传达了这样一种观念, 即王权来自于人民的授权,是法律统治皇帝而不是相反,践踏法律的国君是暴君,践踏法律也是对整个人类共同体的犯罪,对于暴君,人人有诛杀的权利和义务。在这里,依暴力统治是没有理论上的合理性的,而依法治理既是得到神意嘉许的,也是与西方传统的对自然正义的信仰相一致的。
圣托马斯则从王权源自与人民间的协议这一契约论的角度,证成反抗暴君的合法性:
“特别是在一个社会有权为自身推选统治者的情况下,如果那个社会废黜它所选出的国王,或因他滥用权力行使暴政而限制他的权力,那就不能算是违反正义。这个社会也不应为了这样地废黜一个暴君而被指责为不忠不义,即使以前对他有过誓效忠诚的表示也是如此;因为,这个暴君既然不能尽到社会统治者的职责,那就是咎由自取,因而他的臣民就不再受他们对他所作的誓约的拘束。[5](P59—60)”
除了理论家系统美妙的阐释,12—14世纪盛行于整个欧洲的法律意识泛化也强化了法在王上的观念。人们普遍地相信,法律不仅具有维护秩序的功能,而且根本上具有维护正义的功能;法律不仅是当下的一时性的设计,法律还应被理解为一种连续发展的制度,后续的统治者都有义务在原有法律的基础上进行建设,不断颁布新法律,同时维护整个制度的基本原则不变。
三、王权有限性的原因简探
中世纪的欧洲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法在王上或者说王权有限性的史实和信念,与以下因素紧密相关:
其一,日耳曼民族传统的价值观念是限制王权的历史根源。中世纪欧洲的历史是以日耳曼人征服了西罗马帝国而拉开序幕的。与罗马帝国后期强调的“国王的决定具有法律效力”这一带有集权专制色彩的观念所不同的是,日耳曼的原初观念是“国王的权力并不是无限的,他不能一意孤行。[6](P59)”古老的日耳曼传统还主张:国王的意见受制于强有力的部落意见且不能逾越祖先的法律,并且,在制定新法前要征询公众意见,这就约束了现实政治中的专制主义的统治[3](P121)。 人民对国王不是唯命是从,日耳曼民族的国王从没有像罗马皇帝那样主张自己的优越地位,而是信奉权力最终来源于人民,统治者是人民的代表:这一统治者不是绝对的,而必须与其权力的渊源一致,他要尊重地位在他之上的人民的法律。王国的公共生活中,一切决定取决于人民,如果提议得不到人民的同意,就会遭到否决[3](P87—88)。日耳曼人的统治和日耳曼民族传统的价值观念在欧洲中世纪早期持续了五、六百年之久,对当时及其后的王权政治有不可忽视的历史影响。
其二,灵俗二元化权威是限制王权的根本保证。到了11世纪晚期,欧洲确立起了教会和国王双重权威。正如《萨克森明镜》所说的:上帝把两把剑留给世间,给教皇以精神之剑,给皇帝以世俗之剑,罗马教会的强大足以对君主的权力和权威构成实质性的限制。二元权威的存在与竞争也导致多重法律制度的存在,当一种权威施以不公正时,人们会设法寻求另一种权威的保护。在此,唯有依法而治才能获取更大范围的治理权和管辖权;二元权威的存在与竞争也使得体制外的批判有了自由存在的空间,持批判话语的法学家——无论是世俗法法学家还是教会法法学家,都致力于系统地提出这样一种政府和法律理论:即一方面与时代的灵俗二元权威的现实相符合,另一方面又将对统治者专横地行使权力予以限制。
其三,世俗社会多元化治理方式和民主因素是对王权的重要牵制。伯尔曼在描述和分析11世纪晚期——13世纪世俗领地王国的特点时指出:在政治和法律理论上,国王的权力受宪法的限制,包括对他的管辖权及在管辖权内如何行使权力的限制;在政治和法律实践中,国王的权力受王国内各种各样社会共同体的限制。当时的个人除了臣民身份外,同时还可能隶属不同的社会阶层或社会团体,诸如属封建贵族阶层、城市市民阶层、商人阶层、神职人员阶层以及地方、区域和氏族社会团体等等。这些社会阶层或社会团体要求其成员尽职或对之都有相应地义务性约束,这便在一定程度上分散和消解了世俗国王的权威。其次,这一时期,无论是宗教团体还是各种世俗的社会共同体,都有着强烈的民主色彩,如对重要问题能作出决定的是全体会议而非某个个人权威者;一些重要的职位由选举产生或予以罢免,“与此相似,中世纪中期的世俗生活中,也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集体行动,其中自治而非服从君主式的领导是常规的形态:在新近出现的大学中,在遍布城镇的行会和互助会中,在城镇的管理中,莫不如此。[3](P122) ”民主自治的治理方式不可避免会地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专制统治。如果说灵俗二元化权威的政治结构是从权力的外部对“王权”的“分权”和制度上的制约的话,那么多元化的社会治理方式则可视作是从权力的内部对世俗“王权”的制衡。
上述王权有限性的制度、理论及生成原因的各方面,即便到了欧洲中世纪的后期仍在发挥着影响与作用。典型的,可以英国为例加以说明。历史行进到了17世纪,英国君主制开始走向极端,拼命扩张国王特权的詹姆斯一世(JamesⅠ,1603—1625)曾傲慢地声称:“要我受制于法律,说这话就是叛逆。[7](P5)”但在1609年他对议会演说时依然要说:“国王以双重的誓言来约束自己遵守他的王国的根本法律:一方面是默契的,即既然作为一个国王,就必须保护他的王国的人民和法律;另一方面是在加冕时用誓言明白地表明的。因此在一个安定的王国内,每一个有道的国王都必须遵守他根据他的法律与人民所订立的契约……一旦不依照他的法律来进行统治,就不再是一个国王,而堕落成为一个暴君了。……所以,一切既不是暴君又不是背誓者的国王,都将欣然束身于他们的法律范围以内。”詹姆斯一世对议会的演说,不免有惺惺作态之嫌,但至少说明了,即便到了君主专治时期,欧洲的这些国王还是在权力上有所收敛的,不敢胡作非为。对此,洛克评价说,詹姆斯一世明白“国王与暴君的区别只在于这一点上:国王以法律为他的权力的范围,以公众福利为他的政府的目的,而暴君则使一切都服从于他自己的意志和欲望。[8](P122—123)”
四、结论与启示
检视上述史实,我们可以说,王权受法律制约是中世纪欧洲一项重要的制度和政治现象。王权的有限性和人民反抗暴政的合法性等观念、依法而治(rule by law)及法治(rule of law)理论、契约论原理等,都不是全然地发端于古典自然法理论盛行的时代,中世纪的政治实践为所有上述理论铺展了制度上的雏形,同时,也为此后这类理论的系统发展奠定了基础。中世纪后期,古典自然法学说、启蒙运动以及资产阶级革命或改良对专制主义的摧枯拉朽的痛击,仔细考量起来,实非一日之功,“限权”、“法律至上”等制度与观念在欧洲其实是有着漫长的历史渊源的。
以上述史实反观中国历史,两千多年的传统社会中,历代君王集立法、行政、司法大权于一身,皇权高高在上,毫无限制。君主帝王既是国家的最高权力,又是社会的单一权威,而法律不过是帝王之具,① 皇权从未被法律所规制和支配,相反,皇权却在根本上支配着法律。“法律在根本上不是社会(统治与秩序)和权力的基础,而是国家最高权力的工具,权终究大于法。[9](P279)”由此, 存在的是专横的权力和刑罚恫吓色彩强烈的暴虐的法律。士大夫阶层由于没有体制外可资保护的力量,也不敢象同期的西方法学家思想家那样畅所欲言,不敢对君主专制体制的正当性、合法性提出质疑和批判,最多只能在体制之内发出作用有限的民贵君轻、以民为本这样的劝谏,“士大夫阶层为了整个王朝利益,虽然想方设法,包括说服教育君主本人,对王权进行了某些有效果的限制,但因为在中国社会条件下,士大夫阶层的力量主要来自王权,并未形成一支独立的、强大的社会力量,因而直到明清,这种限制还是很不稳定的。君主如果不愿意接受某一限制,按制度他可以随时摆脱。[10](P300)”传统社会制度思想方面的流弊在今天仍然没能得到彻底的根治,人们的观念中也还不同程度地残留着“权大于法”的影响。
以上述史实反思中国现实,经过近三十年的改革开放,我们制定了以宪法为核心的各种法律,规范政府权力,保障公民权利,法律成为对权力进行制约的重要手段。但实践中,法律对公权力的制约效果不尽如人意,法律对社会的支配程度也还很有限。特别是在树立法律至上的观念方面,对比欧洲自12世纪以来深厚悠久的历史渊源,可以说,我们还需要不断地启蒙,付出更多的努力。
收稿日期:2006—02—06
注释:
① 如《韩非子·定法》中把法和术视为君主统驭臣下的“大柄”,主张“君无术则弊于上;臣无法则乱于下。此不可一无,皆帝王之具也。”又如《潜夫论·衰制》中称:“夫法令者,人君之衔辔策也,而民者,君之舆马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