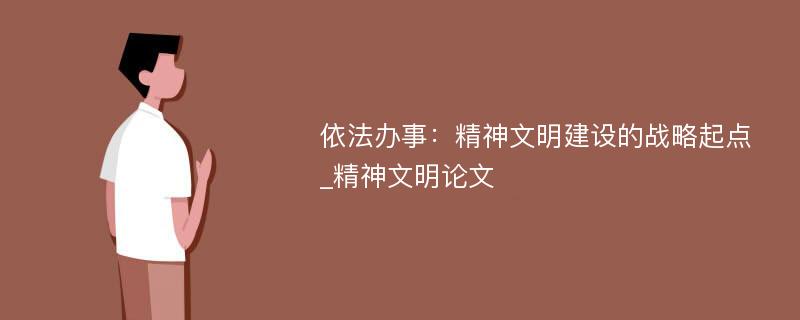
依法办事:精神文明建设的战略起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精神文明建设论文,依法办事论文,起点论文,战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取得物质文明建设的巨大成功的同时,也面临着精神文明建设的急速“滑坡”,并且这种状况仍在继续。察其原因:传统精神文明建设模式遇到市场经济的撞击和瓦解,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精神文明新体系还没有生成。我们在构建精神文明的新体系时,还没有找到将社会主义精神与市场机理融为一体的恰当切入点,以至我们仍处在迷惘和徘徊之中。我们认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精神文明新体系建设的切入点就是“依法办事”。
一、行为文明:精神文明建设的出发点
精神文明是人类群体在社会生产和生活过程中在精神世界取得的一种进步。这种进步表现为行为和动机两个方面。从主观愿望上讲,人们总希望动机进步能成为精神文明的主旋律,“善行”和“善德”吻合一致。这就产生了以动机文明为修建起点的精神文明建设模式。我国传统精神文明建设把重点设置在动机的文明上,不重视人的行为的塑造,或者也重视人们行为的塑造,但却把实现的途径仅仅归结在文明动机的培养上,忽视以规范约束行为,以行为整塑动机,最终实现行为和动机的双向文明。因此,当我们的动机文明为中心的传统精神文明体系遇到以行为文明为中心的市场文明的冲击时,显得局促无措。精神文明建设基点的错位,导致精神文明建设绩效的极大虚衍性和对形势变迁的缺乏适应性。这种定位无论从理论逻辑,还是从实践情势,从计划理论,还是从市场观念,它都充分显示了自己的错误。
精神文明建设是人的建设。人作为社会活动的主体,既是精神文明的建设者,又是精神文明的被建设者,既是精神文明建设的主体,又是精神文明建设的客体。人的精神文明建设的落脚点,要么是动机文明,要么是行为文明。动机文明非常重要:只有文明的动机,才会产生自觉文明的行为,只有人类都存有文明的心灵,世界才会文明普照。然而动机却是主观的、难以测度的,它的建设也是十分困难的。同时,行为和动机也并不总能同一律动,行为并不能充分表现其动机的性质。人们不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善行必然寓含着善德。相反也不能有这样的结语:善德必须带来善行。动机和行为的不一致性,要求我们只能把文明评判的基点放在行为上,因为只要是善行,总是有益的。不能因为动机不纯的善行而否定它,也不能因善良动机下的恶行去肯定它。“一种行为无论心愿多么纯正,但其趋向是有害或者无益的,这种行为就不是善行”。(注:〔英〕葛德文:《政治正义论》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01页, 转引自《世界法律思想宝库》第372页。)所以,以行为的优劣、 善恶作为文明的评判标准是唯一可行的选择。我们绝不是贬低动机文明,也不否认动机文明对行为文明的意义。但是我们认为只有以行为文明为起点,重视文明行为的塑造和它对动机文明的生成作用,才能最终达到动机和行为的共同文明。
党的十四大以来,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已成为我国经济改革的主要实践。市场在给我国带来经济发展的同时,也给我国精神文明建设带来了新的问题和挑战。我国传统精神文明对市场的陌生和不适应性,被要求必须重新定位和安排。
市场经济的最大特点和成功机理,在于它遵循人性规律,利用人的自利心理和自我奋斗的动力,建立起以竞争为基础、以供求调节为杠杆的自利肇始、利他终局的经济运行机制。它从关心个人经济行为的成功和个体资本的扩张,达到提高社会整体经济效率和增加社会财富总量的目的,最终实现“共富”目标。与此相适应,市场道德价值体系的评价基点是人的行为。市场文明观认为,人们的行为只要合乎法律,合乎公序良俗,不必计较其利已动机。因为动机文明并不是这种体制预设容纳的内容,同时这种以催动物质文明建设为己任的文明修建模式,也不具备关注的心力。市场文明的实现方式是以利已为起点,以利他为终点。只要人的行为具备道德性(合乎法律、合乎社会公共利益),即使他的动机并不具有道德先进性,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仍然能为人类整体幸福作出贡献,最终达到行为文明。
社会主义传统精神文明的评价基点不仅是人的行为,更重要的是人的动机。它不仅强调善行,而且要求善德,强调善德对善行的决定作用,它不接纳不具善德的善行。传统精神文明的实现方式也不同于市场文明观。它以利他为起点,以利已为终点。它要求每个人的社会行为必须明白无误地表现出它的道德先进性,它要求个人为国家、社会和他人利益而奋斗,通过全人类幸福的实现,最终实现个人幸福。
应该说,市场精神文明和我国传统精神文明在终极关怀上是一致的,都是致力于人类思想和行为的至善至美,致力于人类的整体幸福,不同的是二者选择的起点和实现方式存在差别。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精神文明新体系,必须把市场精神文明以“行为文明”为实现起点的科学性同社会主义传统精神文明关注“动机文明”的理想先进性结合起来,以“行为文明”为起点,把行为和动机的共同文明作为我们奋斗的目标,实现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
有人说我国传统精神文明的建设是行之有效的,它之所以需要重新定位和安排,是由于体制和环境的变迁。实际不然,由于起点的误差,导致传统精神文明建设模式也存有诸多缺陷。把“行为文明”作为建设的出发点,不仅是构建新模式的要求,同时也是修缮旧体制的需要。
首先它可以改变传统精神文明内容的泛、大、空,使之更加重视具体行为规范的建设。过去我们比较重视精神文明原则的确立,但不重视其具体化和实践化,导致这些原则长期停留在理论宣言和号召倡导的层次上。因此只有以行为文明作为修建起点,踏踏实实走重(zhòng)建之路,把精神文明的原则宣言化为群众的行为信条,才能使它真正植根于群众行为的沃土之中,开花结果、发扬光大。
其次,它可以使精神文明的内容更具群众性和普遍性。传统精神建设重视英雄人物的示范效应。它希望通过树立典型、宣传先进,强制推广文明理想,实现社会整体文明。被树立的典型人物往往又被宣传行为文明的英雄,同时还是动机文明的完人。而对基本群众的行为规范建设却重视不够。这种重英雄、轻群众的理想化建设模式只能是“阳春白雪”。伦理学家罗国杰指出:“道德作为一种价值体系,它本身就象一座山一样,蕴含着从低到高的无数阶梯,包涵着先进性的最高要求和群众性的基本要求的统一。”(注:1997年4月26日《人民日报》)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的道德现实是:无私奉献、一心为公,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在我们的社会应该说是较小的部分,顾全大局、遵纪守法、热爱国家、诚实劳动的人则属绝大部分。因此,我们不能丢掉绝大多数的道德教育和建设,只抓少数“精英”的道德建设,更不能把对少数人的道德要求作为整个社会的道德准则。以“行为文明”为起点,抓基本群众的精神文明建设,并使之普及化,是我们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精神文明建设的务实之举,是通向共产主义精神文明终极目标的必经之路。
二、依法办事:行为文明建设的战略起点
自古以来,法律和道德就是两个互相联系、彼此渗透但又范畴迥异的社会控制模式。法律对道德的养育与道德对法律的浇灌,铸就了法律的道德性和道德的法律性,因此,古有“德主刑辅”“出礼入刑”的史载,今有精神文明建设“一靠教育、二靠法制”的宏论。把“依法办事”作为行为文明的建设起点,是一个无需论证的明理。但在市场条件下,探讨这个命题,会有很多新的意蕴。
法律是人类文明的“储存器”和“调节器”。法律文明是人类文明的重要内容和组成部分,法律文明的历史始终紧伴着人类文明的步伐。法律不仅熏陶于人类文明的“烟火”,折射人类文明的光华,同时又以自己的方式“凝聚”、“升华”这种文明,并促其发挥光大。马克思主义认为,法律必然反映占统治地位的精神文明。因此自有法律史以来,精神文明就深植于法律的土壤之中,法律以其严谨的逻辑性、内容的公开性和适用的强制性,有力地推动着精神文明的进步和发展。任何时期,统治者都不会忽视利用法律对社会意识形态进行控制,不会忘记运用法律建设精神文明。我国社会主义法就全面记载了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我国宪法肯定了“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国际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政治道德文明,规定了“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的公共道德文明,《民法通则》确认了“自愿公平、等价有偿、诚实信用”、“尊重社会公德,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商德文明。婚姻法确定了“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平等”、“父母抚养教育未成年子女,成年子女赡养扶助父母”的家庭道德文明。这些规定反映了社会主义社会各方面的道德要求,构筑了我国精神文明体系的基础,成为国家进行精神文明教育和公民进行精神文明修养的基本依据。从这个意义上说,国家的精神文明发展战略,公民的道德修养,其起点应该是“依法办事”。
法律不仅是精神文明的“储存器”和“调节器”,同时它还以自身文明的光辉闪耀在精神文明的殿堂之中,因此,依法办事就是在实践一种文明。
首先,法律凝聚了人类的理性文明。人性弱点的表现是“损人利己”,这是一种非理性。有史以来,人类发生的无数次征战和浩劫无不源始于这种非理性。因而,探索矫正人性弱点的途径和方法成为人类世代的梦想。法律的诞生,正是人类纠抑非理性的尝试。法律的主题就是约束人类的非理性行为并使之理性化。虽然经过数千年的自我陶冶和群体磨合,但人类初始的非理性并没有绝迹。因此法律仍然担负着人类理性化的沉重使命。当代法律作为理性工具同人类的非理性进行坚韧不拔的抗争:法律要求人们在享有权利和自由时,必须接受义务的限制,进行交换时必须进行协商,法律还认可建立公共机构对人类关系进行调节,对损人利已行为加以抑制和制裁。法律的理性是人类理性的重要内容,属于人类文明系统。因此,合法的行为应是理性的行为,而理性行为则必然是文明的行为。
其次,法律汇萃了人类的科学文明。法律不仅是政治御用工具,具有强烈的阶级性,同时也是一部科学“大典”,具有显著的科学性。法律的科学性就是它对社会规律和自然规律的忠实记录,是对时情、地情的透彻认识和彻底尊重。当代法律已注入科学的基因,集聚了科学的智慧,具备了科学文明。行为的科学化是文明的基本要求,比如,孝敬父母是中华民族几千年的传统美德,但“割股疗亲”只能叫“愚昧”,对爱情忠贞不渝和“好女不嫁二男”也是绝然不能相提并论的。因此,从依法办事到行为科学化,从行为科学化到行为文明,这就是法律、科学与文明的交换公式。
最后,法律吸纳了人类的伦理文明。伦理文明的核心就是尊重人、尊重人性、尊重人情。法律的伦理性处在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中世纪法律尊崇神权、君权,鄙视人、压制人性、禁锢人情,伦理性稀薄。资本主义法律,倡导民权、分权,尊重人性人情,弘扬个人人格、自由和权利,伦理性得到了充分展示。社会主义法宣布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当家作主,这是一种新型的法律伦理。法的伦理性正是法的文明性,因此合法就意味着文明。
邓小平同志说过,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一靠教育,二靠纪律,这里的纪律就包括法制。教育是经常性的,纪律则是特殊时期的特殊手段。当前我国的精神文明建设正处于一个“滑坡”的特殊时期:政治道德领域中存在着“自由化”倾向;公共道德领域中存在着“秩序虚无”主义;职业道德中存在着“拜金主义”;家庭道德中出现了“性解放”现象等等。除此以外,黄、赌、毒等早已绝迹的丑恶现象又死灰复燃、沉滓泛起。此诸种反文明现象的共同特征是,它们不仅极大地败坏了社会主义道德,而且也严重践踏了社会主义法律,具有违背道德和破坏法制的双重危害。在我国精神文明建设处在历史的低谷,突破了最低警戒线——法律的特殊关头,拯救精神文明建设大局,不仅是颂扬少数模范人物、高唱精神文明理想的赞歌,更重要的是要肃整法纪,贯彻依法办事,以法制约束人们的行为,从而达到法律所要求的最基础的精神文明,抑制精神文明的滑坡趋势。所以,加强依法办事是当前精神文明建设的当务之急。虽然法律所确认的精神文明属于较低层次文明,依法办事所实现的也仅是初级精神文明,但是只有做到了依法办事,实现这些基础文明,我们才能迈入高级文明阶段。
三、加强依法办事,推动精神文明建设
90年代以来,我国的立法工作进入了加速冲刺的“快车道”,从缺“法”少“律”的“无法可依”,发展到拥有比较完备的法律体系,做到“有法可依”,立法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然而执法形势却令人担忧,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现象普遍存在,执法滞后的情势同市场经济对法制质量的高要求形成巨大反差,以致出现“泡沫法制”的危言。(注:徐向华:《论法律和道德的作用关系》,载《政治与法律》1997年第5期第19页。)执法的腐败败坏着法律的威信,损害着精神文明建设的根基,因此,强调依法办事,事关重大,刻不容缓。
加强依法办事,首先必须坚持依法治国的基本方针。法治在国家治理战略中的位置,直接影响着依法办事的前途和命运。法治,还是人治;权大,还是法大,这是关系治国方略抉择,是决定法律有无至高无上的权威,是决定能否容忍任何组织和个人凌驾于法律之上的千秋大计。江泽民同志明确指出:“实行和坚持依法治国,就是使国家各项工作逐步走上法制化和规范化。”这就概括了我国党和政府治理国家的基本方针,明确了“法治”在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方向。确立依法治国的战略,为依法办事奠定了基础。江泽民同志还指出:“依法治国是社会进步、社会文明的一个重要标志,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必然要求。”这就指明了依法治国的文明性质,也寓含了依法治国对精神文明建设的意义。因此,坚持依法治国是依法办事的源泉和运作基础,是精神文明建设的政策环境。
加强依法办事,必须强化依法行政。行政机关是国家机关中影响最大、与公民联系最密切、同时也是权力最大、机构最多、人数最众的一个部门。国家所颁布的绝大多数的法律法规需要由行政机关执行。因此,行政执法的好坏直接关系到我国法制建设的质量和前途,也是直接影响着我国精神文明建设的进程。目前社会中出现的有法不依、权钱交易等行政领域中的腐败现象,不仅破坏了我国的法治建设,败坏了社会风气,同时也极大地污染了群众的精神文明建设情绪。因此,依法行政是加强依法办事的核心和关键。
加强依法办事,必须要求在经济活动中遵守法律。由于市场法则的作用,经济领域中弥漫着“个人主义”、“利已主义”和“拜金主义”的毒雾,见利忘义、唯利是图、尔虞我诈、坑蒙拐骗肆意横行。虽然我们建立了一套较为完整的市场法律体系,但有法不依、肆意践踏法律的现象屡见不鲜,不守合同、随意毁约、制假贩假、毁损竞争对手的商业信誉和商品声誉、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金融和证券欺诈、侵犯他人知识产权、偷税漏税抗税,市场道德严重衰落,“道德风险”急剧攀升。这是由于坏法而导致的坏德,由于破坏经济法律法规而导致的经济精神文明衰落。经济领域中的最低道德“警戒线”——经济法律被打破了。建设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精神文明新体系,必须振奋经济法制纲性,加大执法力度,坚决贯彻依法办事,严惩经济违法和犯罪行为,这是经济精神文明建设的现实出路。
加强依法办事,必须要求公民恪守法律。首先必须培养公民的守法道德观,使他们明确依法办事是一种道德要求,是精神文明的基本规则,增强守法的自觉性。其次,使公民树立正确的权利观。权利不是绝对的、没有限制的,享受权利的同时必须承担义务,杜绝只享受权利、逃避义务的违法行为。再次,应使公民树立正确的义务观,改变法律是治民工具的认识,树立社会主义法律的人民性、民主性观念,作到自觉守法。公民是最基本的社会主体,是法治的主体和基础,公民是否依法办事,关乎法治的实现,关乎精神文明建设的成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