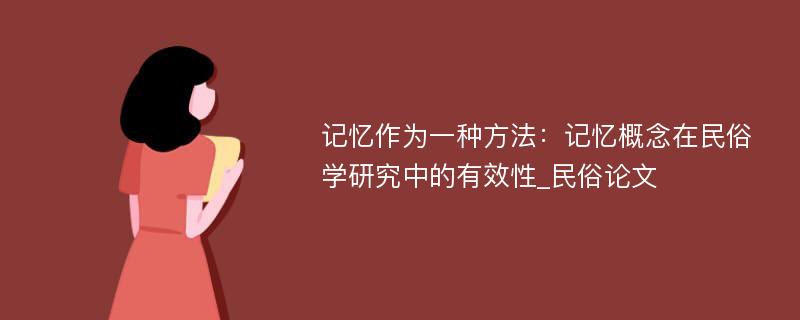
作为方法的记忆——民俗学研究中“记忆”概念的有效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记忆论文,民俗学论文,有效性论文,概念论文,方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89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890(2010)04-109-07
一、记忆论与民俗学
近年来有关记忆研究日益活跃。其起因是,电脑的发明,产生了人工智能的信息处理模型,对人的研究也开始由关注外在的活动转到内部机理。随着认知科学、脑科学的进展,新的记忆的认识开始逐渐成型。过去把记忆仅仅当作盛信息的储藏室,而新的研究完全改变了这个看法。新的对记忆的理解是,记忆在形成过程中,被称为自传式的记忆,即过去发生的事情和经验,是在和他者发生关系的过程中,被唤起、生成的,记忆是一个带有可塑性的动态系统。①记忆的本质是可塑性,这个观点不但在大脑生理学领域,也在分析社会、政治现象时得到广泛运用。在人类学和社会学中,记忆不是作为个人的现象,而是一种集团的现象而发挥作用。莫里斯·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的这个集体记忆论重新受到瞩目,进而推动了共同体和记忆的关系,即社会记忆论的研究。这个倾向致力于把握技艺、技能的习得、即传承过程本身的合法的边缘性参与(Legitimate Peripheral Participation)有相通之处。讨论风景、景观、建筑等所谓空间的物象化的地理学,最近出现了向人文主义、现象学倾斜的动向,这个动向也可以作为记忆论的一个支派。而历史学更是积极地导入了记忆论。有关战争受害者的证言的可信度和正当性的讨论,促进了对历史叙事理论(narrative theory of history)和口述史的再认识。这些动向一方面引起了历史修正主义论争,另一方面,还引发了诺拉(Pierre Nora)等提出了“记忆之场”等相关的追忆、纪念、彰显等共同记忆化(commemoration)的问题,以及强调其公共性的公共记忆论等。在此,历史和记忆的关系从多方面得到论述。进而发展到对叙述过去这一行为的本质是什么,近代历史学的基础实证主义是什么等根本问题的再认识。②
而民俗学领域的情况又如何呢?近几年来,民俗学研究中冠以“记忆”一词的研究著作也频频出现,书籍如小松和彦的《记忆民俗社会》③,赤坂宪雄《别册东北学》的总特辑《迈向记忆之海》④,2002年出版的香月洋一郎《记忆与纪录》⑤一书对宫本常一式的田野调查方法进行了详尽的分析。这些著作对民俗学到底有什么意义呢。是否仅仅是一种跟风式的行为呢?我的答案是否定的。因为记忆、作为一种现象和方法,即使是无意识的,无目的的,和其关系最为密切的不是别的学科,而是民俗学。而且依靠记忆、从记忆中获得恩惠最多的,也是我们民俗学。
如果我们不使用民俗、传承、常民这些惯用的词汇给民俗学下个定义的话,它可以这样表述。民俗学就是不借助记录,而是以“记忆”为对象,通过“访谈记录”的技法,通过人们的“叙述”、“对话”来研究人们的生活和意识的学问。按照这个定义,对民俗来说,记忆成了最本质性的存在。但是,长期以来,记忆研究一直没有得到体系化。其原因并不仅仅因为其意义是不言自明的。从学术史来看,妨碍记忆研究在民俗学中展开的最大障碍是民俗学和历史学、文献记录的关系。
民俗学领域记忆唯一被作为研究对象加以讨论的、是社会经济史家古岛敏雄的民俗学批判而引发的和记录相对比的讨论。古岛比较了在研究伊那的下层武士农民是如何成为地主的附属时,通过记忆和通过记录两种不同研究方法的差异。通过记忆研究得出的下层武士制度的特点是,以红白喜事时向地主无偿提供劳务为双方关系的基本点。这种关系的产生虽然和租赁土地的分割有关,但是,文献记录中被忽略的赋役劳动的存在则是通过记忆的角度挖掘出来的。对此,古岛指出,人的记忆“是传承者的人生经验最为旺盛的时期由自身的经验为基础加以整理、合理化的产物。(下线为引用者所加)不能简单地把他的记忆当作过去的事实。”⑥对此,民俗学家几乎没有人提出反驳,而且把这个意见当作“忠告”而接受。由此更是助长了民俗学界因记忆的不确定性而加以排斥的倾向。把记忆放在文字记录之下,不去“访谈记录”,而是使用文献资料进行研究的民俗学家逐渐增加。同时,通过在数量上的限定,对资料的科学化、精确性的探讨日益增加。比如要从三个访谈对象得到的材料中找到共同部分才能确定其为可靠的资料,经过三代传承的事象才能确定为“民俗”等。这种力图排除记忆的模糊、不确定性的努力,特别在1970年代的方法论讨论中,上述古岛对记忆的观点再一次得到重视。从地域和传承母体的关联性来把握民俗的地域民俗学开始兴起,则更促进了对民俗资料可靠性的追求。将生活中不易变化的事象当作“民俗”、或者“基层文化”,并把这些事象看作是固定不变的。这种倾向逐渐导致了甚至有人把民俗学作为历史学的辅助学科,“补充历史中无文字记录的部分”、“丰富历史世界”。柳田国男曾说,“印刷使社会文化产生了惊人的变革”,其结果“具体个别的口耳相传的传承,和记录相对,其资料价值逐渐消失”⑦(下线为引用者所加)。对记忆作为证据的怀疑,柳田国男的这个论点在民俗学界也逐渐得到接受。
柳田去世以后的战后民俗学,致力于提高资料的可靠性,即通过对民俗资料这个研究对象来确立民俗学的科学性。但是,民俗学并非是以民俗为对象就是民俗学⑧。把“民俗”作为研究对象,并以揭示民俗为目的,这种学术指向是将民俗认定为相对固定不变的地域传统,并试图揭示具体民俗事象的发生与起源,而对其发展变化并不关心。由此产生了仅仅使用文献的“民俗学”。古岛的批判,是针对这个现象的发生而起的。本来完全是针对民俗事象的发生而言,虽然他对民俗学的批判可以说并没有找对目标。但是,民俗学者接受了他的意见,这是因为他的意见和民俗学的上述变化有关。对民俗学来说有效的记忆,不适合于作为经济史学研究的资料,这本来是天经地义的。倒不如说古岛批判中加了下线的部分,才是记忆的本质,也是民俗学的本质。
这样看待记忆的作用的话,那么记忆研究能否成为民俗学有效的方法呢?柳田在他的《口承文艺史考》中写到,“人们重视口头传承,大体是没有文字资料保存下来的时候,抑或是为了消除材料缺乏而引起的误解,需要用来举证的时候。而很多人都相信,同样的事象,只要文字资料记录,口头的东西其寿命就像太阳底下的霜一样短暂”。⑨(下线为引用者所加)针对这种倾向,柳田提出了相反的见解。柳田强调了口头传承的重要性。他虽然说“现在来证明这一点,看起来好像很荒唐”,文字记录虽然有“将某个时代的传承”固定化,以“保存其正确的形态”的作用,但是另一方面,文字记录“带有抑制其自由进化的力量”。而与此相对,口头传承并不是“错误记忆的结果”,而是“新创造的产物”。我们的民俗学,就是从这个变化的过程中发现意义,并以此为起点而成立的。最近的民俗学研究中的记忆论,也提出应该放弃将消失的记忆记录化的主张,同时还应该改变把作为唤起共同记忆之场的民俗当作记忆装置的这种静态的把握方式。而要更能动地,探索本质性的民俗学研究的记忆论。
二、记忆的定位和访谈记录之法
我们首先参照一下心理学中记忆的定义。记忆是铭记、保持过去的事件和经验,并以某种方式重新想起的技能(作为过程的记忆),这个精神活动的结果得到了过去认识方式和其整体(作为存在的记忆)。在上述的定义的基础上,我们提出如下几条,作为民俗学中记忆研究的要点。
①民俗学不是以文献记录,而是以记忆为素材的学问。它主要以没有被文献记录下来的事项作为研究对象。
②在研究中,它的基本方法是对直接性的口述、对话进行访谈记录。
③通过以言语为媒介的记忆提取信息,原生态地把握当地人们的生活世界。
④同时,把非言语的如身体行为、感觉、思维方式、价值观、感情、身体技能作为研究对象。
⑤这些知识系统以身体作为媒介,在不同的个体、群体之间发生的保持、传承、传播。力图去把握这个传承的过程和特征。
⑥将使这样的记忆可视化、有形化的行为,通过访谈记录、民俗语汇化、民俗志等方法加以记录(主要是文字化)。
具体来说,①的记忆,是作为结果的记忆的利用,而更具民俗学意味的方法上的独特之处,是②以后的部分。和人类学的参与观察法不同,民俗学虽然受其影响,但是是以访谈记录法为主。这种方法强调倾听当地人们的声音。这是因为民俗学希望通过和采访对象的交流、从他们的叙述中把握埋藏在他们的生活世界中的生活智慧、技能、思维方式、价值观。和文字资料这样的有目的的记录相比,对很少有记录的、非文字的、日常的、平民的、被认为理所当然的、被忘却的事物的关注,并为这些被忘却的生活做出记录,才使民俗学有了存在的理由。但是,访谈记录绝非仅仅是一种如挖掘一些稗史传说之类的对文献史学的补充作业。千叶德尔、手冢惠子指出,访谈记录能够揭示他者的心意世界,在方法论上具有独特的优势。
千叶德尔的基本论点是,访谈记录,是在人们的日常生活的场所对其生活进行调查,它不仅通过叙述者的叙述和实际状态的相互关系来把握事实和事象。还关注叙述人的视线、态度和对事物的看法以及“真实的心理反映”。
访谈记录在实际操作时,对各个事象的相互关系,调查者往往要反复提问,直到得到满意的答复。通过这个过程,将已经忘却的事象、关联性,将有意识、无意识的记忆重新唤起叙述者的记忆,将事象更明确、升华为详细的高质量的资料,并赋予过去、现在的生活以意义。这个超出了调查者提出的问题本身的答案,将以前隐而不露的新事象、课题在认识的过程成型。而对于沉潜在模糊状态下的事象以及对其的评价和感情等,在访谈记录的过程中,对话成为一个交流的媒介,在互动中形成一个整体的认识。受访者常常会说“听你这么一说,还真是这样”。也就是说,通过互动产生某些契机,出乎受访者的意外,而又得到他认可的效果。这就是访谈记录法的本领。⑩
在访谈记录时,处在“现在、这里”的叙述人叙述“那时候、那里”,手塚(11)从这个模式出发,指出所谓访谈记录是一个叙事的创造过程。这个和最近的历史叙事化论相通。所谓历史叙事化论,是指过去的事件通过叙述行为,把被唤起的各种事件,按照一定的时间序列排列起来,放到一定的“叙事”的文脉中重新配置,所谓历史事实由此建构完成。(12)历史叙事化论的基本主张是,所谓历史是叙述话语的产物,不存在所谓客观的历史事实和历史的必然性。这种结构主义的逻辑、逐渐发展成为对过去历史学的存在前提,即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存在的怀疑。而人类叙述过去的、现在的事象和经验这个行为,到底意味着什么?没有史料那样的实物,直接以人为对象,采用访谈对话的形式,这个形式会达到什么作用?对这些问题,民俗学必须对此做出回答,并找出成熟的解决方法来。
但是,把访谈记录,以及民俗学的方法,仅仅归结于叙事与对话,是不全面的。千叶也注意到这一点,他说,访谈记录在对话时除了语言以外还伴随着“动作”,“眼神”、“表情”等其他的心理活动的表现。(13)正是这些“非文字”的部分,民俗学称为心意现象,把这个作为追求的终极对象。柳田国男提出的“眼睛能够观察到的、耳朵可以听取到的、和必须直接接触感受到的”(14)这三分类,民俗学的目的在于揭示第三部分即心意现象。具体来说指好恶、爱憎、兴趣、喜怒哀乐这些感情、风气、信仰、思维方式、宇宙观、人生观、道德观、以及生活之理想、幸福与不幸的标准、以及选择上述事象的内在的技术(15)。柳田一边强调上述的研究目标,又说,“无法描写的内部生活”(16),“只有直接接触感受”。就像柳田国男笔下的清光馆的细君“我们无论问什么,她都莞尔一笑,不作声响”、“对于偶然路过的旅人,即使说了也无法理解她的内心世界吧”(17)。无声的身体记忆应该如何把握,如何将其对象化,在方法论上是一个巨大的难题。
柳田国男是如何处理这个难题的呢?他把口承文艺放到第二部,故事也放入这一部分。比如在《民间传承论》中,他认为,灵魂、幻觉等这些“只要有词汇,其意义的异同、内容还是可以明白的”。对柳田来说,⑥的“赋予无形的东西以名称”的行为,大概就是民俗语汇化(18)。但是,柳田的方法并没得到继承,很难说是成功的。(问题是,除此之外还有别的方法吗?)柏格森把习惯当作是过去固定下来的运动机制得以保持、再生,从仪礼和惯习中把它们找出来,加以分析,自然而然会找到心意的所在。这种黑箱式的理解,带有逻辑上的问题,无法推进问题的研究。从④、⑤的角度来看,近年人类学、民俗艺能研究尝试了从行为者的实践中来探求身体性知识身体性习惯如何传承、再生产。而合法的边缘性参与论的皮埃尔·布鲁迪(Pierre Bourdieu)的手法也是一个选择。民俗学可以以这个方法为参考,并从②、③、④的角度来探讨别的方法。
前述香月洋一郎从很多一直保持沉默的战争体验者的话语构造从某个时期开始发生变化这一事实进行了分析。这个变化简单说来,就是他们的叙述变得娴熟老练了。以前的“没有经历过战争的人根本没法理解”的姿态和生硬的部分消失,那些在无法言喻的世界中深深地苦恼的体验者,随着时间的流逝,开始象反刍一样重新排列组合,说出自己的体验。这是作为一种生活的信念,不断重新把握的内部形成的话语。这个叙事归结于“民俗学成立的场所酿成的”事象(19)。近十多年来,大量战争受害者开始讲述自己的“历史”。这种现象不应仅仅归结于冷战构造这一时代背景。而是一种向记忆外化的转换。借用岩崎的说法,不是说出记忆,而是记忆本身涌现出来(20)。从精神科学的记忆论来看,“无法说出”、“不愿想起”这类的外伤性记忆(traumatic memories)、通常象成人的记忆一样、带有无法由语言加工成一个线性叙事结构的特点(21)。要摆脱这种心灵创伤,必须将记忆升华为一种叙事,想说而无法说出的心灵的呼声,以及沉默都是一种无法忘却的历史,将被压抑的记忆言语化的作业,今后恐怕是民俗学的一个重要工作(22)。访谈记录就是将还没有用语言表述的记忆,通过对话,在短时间内叙事化的技法。
香月所说,叙述就是“本人没有明确的意识的内心的涌动以明确的形式表现出来(23)。手塚也说,说出的东西,既不是客观的事实,也不是虚构。仅仅是叙述者真实的体验。(24)”按照这个说法,记忆就如藤原归一所述,记忆是人们为了给“现在”的生活赋予意义,而对“过去”重新评价的行为。(25)过去如何被铭记,如何被赋予意义(保持),又是如何被叙述(唤起),无论是个人还是集团,对这个记忆化的过程,我们民俗学家必须从原点开始进行探讨。并迫切需要对其方法进行精确化。
三、民俗主义和记忆的政治学
关于记忆,我们目前面临的时代,现代可以说进入了一个“记忆、纪念、保存的时代”(26)。各地掀起的申报世界遗产的热潮,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纪念碑、纪念日、纪念活动等的大量出现。不仅如此,上述的1中,迎来了大众开始大量通过修史、自传等方式记录自身的时代。现代更是有意识地创造值得记忆的东西。同时,世界遗产有大量的观光者来访,世界遗产似乎真正变成了人类共有的遗产。人们对文化遗产、历史的意识的提高,用诺拉的话来说,是记忆能力弱化的反动,起因于记忆方式的根本性改变。在这样的形式下,固有的民俗学的格局,已经无法真实地把握现实世界。有两点需要加以考虑。
1.历史和记忆的关系的变化,民俗主义和再记忆化的问题。
2.在上述的社会状况下,记忆的多层性(复数性)及其政治问题。
对于现代特有的记忆的质的转换,诺拉用“历史在加速”来表现。他提出“和记忆一体化的历史的终结”的同时开始了“记忆之场”的研究。所谓“和记忆一体化的历史的终结”,是指在不断反复的时间中,和过去(记忆)共生的农民集团中,那些被认为是典型的被身体化的过去(历史)消失了。这不仅限于农村,家庭、学校、国家等确保价值的保持、传达的“与记忆一体化的共同体都趋向消亡”。由此造成的“从遥远过去开始的事象终于走向消亡”的历史的断裂感。相反地将记忆具象化了。空间、纪念碑、制度、象征、做法、纪念活动、还有著作等、记忆都被固化了。诺拉的“记忆之场”就是如此。和过去保持连续性的这种情感,在这些“场”物质化,并逃避。就是因为记忆的集团已经不存在了(27)。
同样的问题意识,也可以从柳田的论述中找到。他从文字的普及和印刷术的发达看到“故事的衰退”。而民俗学界更积极地论述这个问题的,是德国民俗学界对于民俗主义的讨论。下面我们使用英语的(folklorism)来表述,但是确立其方法的是德国的赫尔曼·鲍辛格(Hermann Bausinger)。他认为这个现代民俗文化的存在方式和其问题显现出来的“与其说严密,不如说是含蓄的概念(28)”。例如外面是稻草屋顶,门口坐着身穿民俗服装的老人,而屋里看不见的地方则安装着卫星天线,人们过着非常现代化的生活。民俗主义就是人们利用民俗文化的要素,仅仅保存表面的部分,一种布景演出式的传统文化表演,来满足从都市来观光的人们一种乡愁和欲望。同时,民俗主义还对下列问题提供了思考的格局,即都市的人们为什么会被这种朴素所吸引。
同样的光景在日本也比比皆是。比如世界遗产白川乡等文化厅认定的重要传统建造物群保护地区。那些表面上看起来带有传统气息的东西在日本各地涌现,日本的战后民俗学就是把这些当作“民俗”的。草屋顶、民俗服装并非单纯作为传统而保护,为什么人们要以某种“传统”的方式来自我展现。把握这个行为的本质,需要一个涵盖其外部的鸟瞰整体的视角。历史学也对诸如纪念碑的创立、各种纪念活动的创造等题目,通过再记忆化(rememoration)这种当下的、结构的宏观视野来进行探讨。
无论民俗学还是人类学,都以文化是无意识地传承为前提。但是,现代传承开始变成一种有意识的行为,一种有意识地创造记忆的时代。将这个现象用“文化的客体化”作为命题来探讨,由此诞生了观光人类学。在观光人类学从当地人在观光这个文脉下主动积极的作为,挖掘出“当地人的主体性”、“创造过程”,但是,对强调主体性的表象化,受到了结构主义的批判(29)。为了回应这个批判,唯一的选择就是努力去记录记忆的复数性和多样化的住民的声音。小关隆指出,通常,共同体内部存在着复数的记忆,在不同层级的主导权争夺中,不断地被建构(30)。通过记述这样的记忆化过程的复数性,传承母体论之后,作为统合共同体的集合表象的一个整体的“民俗”和共同体,回复到其真实的状况便成为可能。通过“民俗”所作的村落共同体的描写,忽视了向外部开放的文化的整体性,鲍辛格指出,“作为完整的组织的古村落”,被重新象现实存在一样被描绘出来(31)。这里,“存在着不同的传统,依据的是不同的历史”。米歇尔·赛尔特(Michel de Certeau)批判说,这个民俗主义,仅仅停留在文化要素上的话,“肯定会被回收到体制内部”。而创造出一种为经济、政治的商业主义的民俗学的产物”(32)。他的批判虽然带有否定民俗学本身的意味,但是对我们来说,重要的是如何建立不受政治体制影响的民俗学。这是一个困难的但无法回避的问题。
民俗主义表述出来的对“传统”形式的强调,以连续性为根据,为了追求更古老的、更历史性的事物、否定昨天、捏造过去。晚近的过去和变化过程或被无视,或被起源性或古老性修正,最终表现为一幅图画般的景致。和“作为完整的组织的古村落”也描述一样,它还起到了掩盖共同体内部的对立和紧张的作用(33)。这种隐含其中的保存思想,如过去家永三郎所批判的,“评定为文化遗产,与其说促进了历史的进展,不如说起到了相反的作用”(34)。作为阻碍变革的传统回归的理据,妨碍了共同体本来具备的依照自身规律的发展。特别是最近的日本文化政策,通过民俗主义来建构民族主义(35),作为文化论,通过大众传媒,被那些期望共同体的团结一心的地方议员、希望促进地方经济的观光业者和一部分掌握地方权力者所利用。中央权威也利用它,使之对共同体成员的义务产生强制力。特别是这个过激的保存优先主义(36),是以都市人的视线来进行价值判断,而不是当地人的感受。历史学对口述史的关注,是源自对被压制的那部分人的声音的意义的关注。而民俗学的出发点也是对非中心、非文字、被支配等社会边缘的人们的关心。因此,民俗学内部隐含了使共同体内部被压制的记忆表象化的原始动力。作为最接近生活底层的记忆观察者,民俗学不应该为了都市人,为了掩盖战后农业政策的失败和现实的矛盾而推波助澜。而应该去积极寻找解决的方法。这才是民俗学应该寻找的方向。
*此文是岩本通弥为他主编的《现代民俗志的地平3记忆》一书写的总论。经作者同意,由译者作了若干文字的删减,以论文的形式译出发表。——译注
注释:
①太田信夫、多鹿秀継編:《記憶研究の最前綠》,北大路書房2000年。
②岩崎稔:《歴史学にとつての記憶と忘却の問題系》、《歴史学における方法的転回》,歴史学研究会編,青木書店2002年。
③原名:《記憶する民俗社会》——译注
④原名:《記憶の海ヘ》——译注
⑤原名:《記憶すること·記録すること》——译注
⑥古島敏雄:《民俗学と歴史学》,《歴史学研究》142号1949年,野口武徳、宮田登、福田アジオ編《現代日本民俗Ⅰ》102页三一書房1974年重新收录。以我的阅读范围来看,唯一对古岛的论点提出反驳、批判的只有千葉徳爾《記録と記録》《民間伝承》16卷9号,1952年。
⑦柳田国男:《口承文芸史考》,《定本柳田国男集》6卷,第10页,筑摩書房1968年。
⑧拙稿《“民俗”を対象とするから民俗学なのか》,《日本民俗学》215号1998年。(中文译文:《以“民俗”为研究对象即为民俗学吗?》,载《文化遗产》2008年第2期——译注)
⑨柳田国男:《口承文芸史考》,《定本柳田国男集》第6卷,第20页,筑摩書房1968年。
⑩千葉徳爾:《“聞き取り"という調查法について》,《狩猟伝承研究再考編》,風間書房1997年,第320-327页。
(11)手塚恵子:《心象と民俗》,小松和彦、香月洋一郎編《身体と心性の民俗》,雄山閣1998年,第191页。
(12)野家啓一:《物语の哲学》,岩波書店1996年,第17-18页。
(13)千葉徳爾:《“聞き取り”という調查法について》,《狩猟伝承研究再考編》,風間書房1997年,第320-321页。
(14)柳田国男:《口承文芸史考》,《定本柳田国男集》,筑摩書房1968年,第6卷,第149页。
(15)柳田国男:《民間伝承論》,伝統と現代社会社1980年,第216-227页。(中文译本《民间传承论与乡土生活研究法》,王晓葵、王京、何彬译,北京:学苑出版社2010年版——译注)
(16)柳田国男:《民間伝承論》,伝統と現代社会社,第238页。
(17)柳田国男:《清光館哀史》,《定本柳田国男集》,筑摩書房1962年,第2卷,第111页。
(18)柳田国男:《民間伝承論》,伝統と現代社会社,第227页。
(19)原名:《記憶すること·記録すること》——译注,吉川弘文館2001年,第29页。
(20)岩崎稔:《歴史学にとつての記憶と忘却の問題系》、《歴史学における方法的転回》,歴史学研究会編,青木書店2002年,第275页。
(21)ジヨデイス·L·ハ一マン(中井久夫訳):《心的外傷と回復》,みすず書房1999年,第53页。
(22)爱知县师胜町历史民俗资料馆为防治老年性痴呆而开设了“回想法中心”并取得了成效。这个尝试具有创新意
义。《DOME》67号,2003年
(23)原名:《記憶すること·記録すること》——译注,吉川弘文館2001年,第144页。
(24)手塚恵子:《心象と民俗》,小松和彦、香月洋一郎編《身体と心性の民俗》,雄山閣1998年,第199页。
(25)藤原帰一:《戦争を記憶する》,講談社2001年,第45页。
(26)ピエ一ル·ノラ(诺拉):《記憶と歴史のはざまに》,《記憶の場》1巻ピエ一ル·ノラ編2002年(这个论点和说法在荻野昌弘編《文化遗產の社会学》新曜社2002年一书中亦有采用。)
(27)ピエ一ル·ノラ(诺拉):《記憶と歴史のはざまに》,《記憶の場》1卷,ピエ一ル·ノラ編2002年(这个论点和说法在荻野昌弘編《文化遗產の社会学》新曜社2002年一书中亦有采用),第29-30页。
(28)河野真:《解说民俗学の研究課題としてのフオ一クロリズムス》,《愛知大学国際問題研究所紀要》91号,第79页,1990年。
(29)足立重和:《伝統文化の管理人》,《社会構築主義のスベクトラム》,中河伸俊ほか編,世界思想社2001年。
(30)小関隆:《コメモレイシヨンの文化史のために》,《記憶のかたち》,阿部安成ほか編,柏書房1999年,第8页。
(31)ヘルマン:バウジンガ一(河野真訳)《科学技術世界のなかの民俗文化》,愛知大学国際コミユニケ一シヨン学会,2001年,第83页。
(32)メシエル·ド·セルト一(山田登世子訳):《文化の政治学》,岩波書店1999年,第62、166页。
(33)ヘルマン:バウジンガ一(河野真訳)《科学技術世界のなかの民俗文化》,愛知大学国際コミユニケ一シヨン学会,2001年,第86页。
(34)家永三郎:《文化史と文化遺産の問題》,文化財保存在國協議会編《文化遺産の危機と保存運動》,青木書店1972年,第82页。
(35)拙著《“文化立國”論の憂鬱》,《神奈川大評論》,第 42号,2002年。
(36)指过度强调保护优先的观点。这个表述在鳥越皓之《柳田民俗学のフイ口フイ一》東京大学出版会 2002年亦有使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