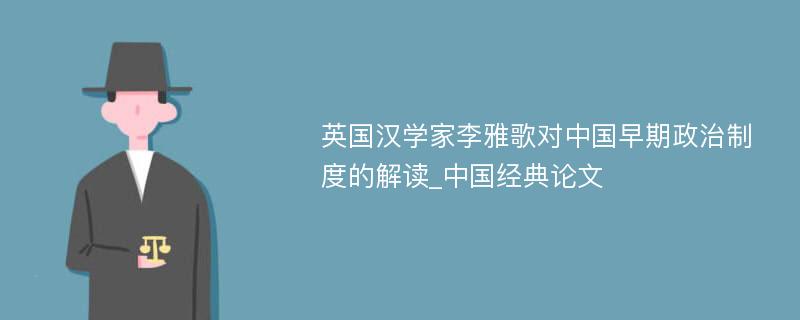
英国汉学家理雅各对中国早期政治制度的阐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雅各论文,汉学家论文,英国论文,中国论文,政治制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 B512.4;B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627(2009)02-0102-10
英国汉学家理雅各(James Legge,1815—1897)被誉为十九世纪西方汉学界最重要和最有影响力的儒学专家,其代表译著《中国经典》一直作为儒家典籍标准译本受到西方汉学界的推重。《中国经典》将汉语原文同步置于译文上方醒目位置,并配以长篇序文和详尽注释,体现了译著的权威地位。研读《中国经典》,不仅可以从中领略儒家文本之美,感受儒学思想意蕴,也可以了解和认识其负载的中国古代政治、文化、宗教和社会等图景。但是,透过译者个性鲜明的译文、注释,尤其是那些充分蕴涵译者思想的序言,我们发现译文展现的中国早期政治制度其实是注入了太多的译者主观意象和基于西方学术背景的个人理解。对于这一现象,研究理雅各的学者,无论视译者为中西文化的使者,还是视之为文化殖民者,大多认为理雅各早年所受教育、尤其是宗教信仰和传教经历决定了他的翻译理念,从而使他的翻译及其对中国早期政治制度的描述具有浓厚的基督教色彩。然而,除宗教之外,我们还分明感受到另一种力量的存在和牵制,其强度和韧性甚至时时超越宗教信仰而支配翻译思想,以致使译者常常身不由己地同原著所代表的源语文化进行激烈的抗争。正是这种力量最终决定了译者对中国文化的认识和评价,并导致了其翻译理念中的矛盾现象。本文拟将译者及其《中国经典》置于具体的文化和历史语境,解读译者对中国早期政治制度的描述及其阐释,以揭示真正决定理雅各中国文化视角的无形力量。这种无形力量当然不是来自上帝或宗教,而是以民族利益为旨归的现世政治控制力量,但恰恰是这种政治控制力量,在关于理雅各的研究和著述中被忽略了。
一、对夏商周制度的讽喻
西欧封建社会,公权衰微,私权林立,兵连祸结,社会动荡。封建主以土地关系为纽带层层分封,形成了森严有致的金字塔般的等级体系。英国虽孤悬于大海之上,其制度建构与西欧相比,却未曾有明显差异。这些,构成了理雅各自童年以来的基本知识背景。带着这一既定背景,理雅各审视了中国夏商周三代的历史,他发现中英两国虽在空间上分处亚欧大陆两端,在时间上相隔千数百年,但中国三代的政治建构与英国历史并无不同,贵族同样从君主那里获取封地,“并可继续分封土地,只须获得君王允准”①。既然如此,理雅各认为,此时的中国社会被称为封建社会当无疑义,而中国最早的国家自然为封建帝国。也正因为中央政府软弱无能,割据势力强大无羁,中国封建社会才经历了夏商周三代迁延近两千年的漫长历史。在《尚书》译序中理雅各写道:“当首领的尊严发展至王权,部落成长为国家,中国采用的是封建帝国(a feudal empire)的形式”②。《尚书·夏书·禹贡》中,禹“锡土姓”,将九州的土地分封给诸侯,并分别赐以姓氏。理雅各认为禹此举必已获得舜的准许,分封土地恰似征服者将新占领的领地分给属下,而禹大规模封赐姓氏的时代则必定是中华帝国的真正起始③。理雅各将夏朝作为中国封建制度的开端,并认为直到周王朝,这种制度才得到充分发展和巩固④。
正如封建制度下的西欧动荡不安一样,在理雅各看来,封建制度带给夏商周的也远不只是和平与繁盛。理雅各虽不否认中国封建时期曾有过繁荣,但他认为那种繁荣过于短暂,无异于阴郁天气中的阳光一现。对于《中庸》中所描绘的“今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理雅各不屑一顾,并讽刺当年罗马天主教士译介儒家经典时对这一制度的赞扬,认为“这种一统的价值极小”⑤。理雅各此处对罗马天主教士的讽刺并非只是由于宗教派别之争,因为虽然新教传教士“出于宗派原因,在很多场合对同时代天主教传教士加以攻讦,然而对早期来华的天主教传教士,他们却很少妄议”⑥。因此,理雅各的讽刺更多是在针对周代封建制度,而他对封建制度的否定则旨在诋毁孔子。
在《中国经典》中,理雅各从儒家经典的逻辑性、孔子学说对后世的影响等方面对孔子进行了尖锐抨击。比如,他认为《大学》的论证“前提与结论之间缺乏充分的联系”,“与其说是逻辑思维的结果不如说是语言修辞的游戏”,“论证过程和其初衷不相协调”;《中庸》“是凭知觉而不是凭逻辑说理”;《春秋》“有许多不实之处”,他认为孔子的这部著作没有价值,对该书受到中国人如此崇拜表示不解,并指出中国的道德和政治状况正是盲目崇拜孔子的结果。误导中国人的不是别人,正是孔子。由于孔子的影响,中国人无法正视现实。他指出,如果他对《春秋》的研究可以使中国人信服,把视线从孔子身上移开,那么,他一生的重大目标也就完成了⑦。另外,他坚信,随着历史的进步,“孔子必将让位于耶稣”⑧。
正如吉拉多特所言,“理雅各对孔子的讨论表明他对中国及欧洲的历史和哲学做了慎重的比较研究,而他对孔子与基督及基督教文明之间的比较进一步揭示了这位传教士汉学家的内心世界”⑨。理雅各承认孔子是一个令人尊敬的老师,有着众多弟子,但当孔子被后人提升到圣人的至尊地位时,理雅各就无法容忍了。理雅各批判孔子是为了打击孔子在中国人心目中的圣人地位,而对中国古代封建制度的讽刺和批判则意在进一步颠覆孔子的权威。
孔子学说被后世许多朝代的统治者奉为治国安邦的权威理论,因此从政治制度方面论证孔子学说的缺陷和错误,显然对孔子的权威更具颠覆性。对于孔子所竭力颂扬的周王朝,理雅各认为,虽然周文王统治时期为“宁静时期”,但整个周王朝的统治却显得“过于柔弱”,以致“社会政治混乱无序,各诸侯国战乱频仍,冲突不断”。并且理雅各还特别指出,“古老的封建帝国并没有因孔圣人对周王朝的颂扬而变得强大”,恰恰相反,“在一片血腥的无政府状态中逝去了”⑩。
尽管对三代的政治制度竭力讽刺,但理雅各还是昭示了古代中国的希望,那是因为他在最古老的儒家经典中发现了早期中国一神教的线索,而这种发现又是对孔子的进一步批判。
理雅各与同时代那些“在中国文化中横冲直撞的传教士有本质的不同”(11),他秉承了明末清初耶稣会士索隐式研究中国儒家经典的传统,“是最早在古代中国找到基督教上帝的现代西方学者之一”(12)。在儒家典籍中,理雅各发现中国“只有天,而没有地狱,暴君死后也和圣明君主一样在庙堂中接受后人供奉”(13),并且他反对“昊天上帝,则不我遗,父母先祖,胡宁忍予”的宣王拜祖,认为“宣王之父厉王如此人格败坏又怎能给他佑助”(14)。尽管如此,理雅各还是认为古代中国的部落首领和统治者对上帝知之甚多,君王是接受并依据上帝的旨意进行统治的,各诸侯也要遵从上帝的旨意恪守正义(15)。但理雅各发现孔子却是“非宗教的”。
理雅各认为孔子“并非反宗教而是非宗教的”(16)。在《诗经》和《书经》里,“帝”和“上帝”(理译为God)的概念多次出现。在理雅各看来,这一概念具有人格神的特点,能够统治天地,决定人的道德本性,统领各个民族。通过奉行上帝的意志,国君得以统治国家,诸侯得以秉行正义,善恶各有所报。而孔子却更乐于使用“天”(理译Hearen)的概念,整部《论语》,没有一处提及具有人格特点的“帝”或“上帝”。理雅各认为,“天”只具备自然属性但没有人格特点,因此,孔子“缺少对古代圣贤们的虔诚”,因为从宗教观念的继承性来看,孔子改变了古代圣贤们对宗教的理解,对其极力颂扬的先代圣人缺乏尊重。而孔子对宗教的这种态度又直接影响了后世中国人的宗教观,以致形成了中国人的无神论,“使中世纪和现代的中国人很难接受基督教的上帝”(17)。
理雅各对三代制度的批判,意在击碎孔子在中国人心目中的圣人形象。而他对古老的儒家经典中“上帝”概念的寻踪及阐释,又进一步从根本上否定了孔子的地位和学说。但是,在他看来,中国并非没有希望,这种希望在于封建帝国虽然混乱无序破烂不堪,却存有基督教的“上帝”观念。依靠这一观念,中国有希望走出三代的阴霾,奔向光明的前程。
二、对秦“革命性”的赞颂
理雅各认为秦王朝推翻周代封建制度是一场真正的革命,而他对此的界定是:以持久的力量,推翻旧的国家制度,建立自己的新制度。与多数史学家侧重抨击秦始皇苛政不同,理雅各给予秦王朝的创立者以极高的评价。他指责周代各诸侯国没有仁慈和正义,却对秦国大加赞赏,称其为“年轻、有活力、充满阳刚之气的国家”(18),赞扬秦始皇“摧毁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制度,建立了现代专制帝国”(19),并认为史学家对秦始皇的评价太低、不够公正。
理雅各赞扬秦是由于它的革命性,并且也期待中国出现另一场革命。他认为“自古老的封建帝国消亡,秦建立专制国家始,中国就再没有出现过革命,而只是统治者和朝代的更替”(20)。他期待着对专制制度的革命,并期望这场革命的结果是建立基督教国家。正如同时代美国基督教传教士卫三畏所言:“我确信汉人的子孙有着伟大的未来;但是惟有基督教的发展才是适当的手段,足以拯救在这一进步中的各个冲突因素免于互相摧残”(21)。卫三畏对于中国的未来及基督教在中国发展的表述还比较委婉,而理雅各的态度则不仅直截了当而且极为苛刻,他指出“无论未来中国是否能成为独立国家,这个国家获得繁荣昌盛的首要条件是学者和统治者要谦卑,否则将永无希望”(22)。当然,理雅各所要强调的是中国人必须谦虚而客观地认识自己的历史。然而当十九世纪西方基督教国家开始和中国频繁接触时,理雅各的这种说法就很容易让人联想到英国为维护国家利益而采取的殖民政策:如果可能就用非正式手段,如果必要就正式吞并。
作为一名传教士汉学家,我们并不否认理雅各有着虔诚的宗教信仰和孜孜以求的治学态度,但同时又身负作为英国公民的民族责任。他背井离乡远涉重洋,最初在马六甲极其恶劣的环境中履行他的传教使命,后又在香港教区践履他的传教领导职责。他三十年如一日,潜心于中国传统典籍的翻译,译著几乎涵盖了十三经的全部、道家及佛教的部分著作,另还有大量有关中国文化的研究著述。虽然理雅各有时试图平衡作为英国公民和作为传教士以及汉学家的责任,然而由于这三种角色之间本来就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和冲突,他的努力在大多数情况下实际上失败了。特别是在关键时刻,他的汉学研究和宗教信仰无不是服务于大英帝国的政治需要。
事实上,理雅各译著中对秦朝革命性的颂扬为西方发动鸦片战争提供了理论支持。卜拉特曾指出:理雅各强调禹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性是没有根据的(23)。然而,理雅各强调禹的重要性同赞扬秦始皇的革命性的思想逻辑却是一致的,他们都是帝国的缔造者,都开创了新的国家制度。沿着这一逻辑推进,对于中华帝国的发展,英国的侵略也具有革命性,因而也是值得颂扬的。“在西方人看来,第一次鸦片战争是从已经存在了大约2000多年的旧事物向将会变革国计民生的方方面面的更新的西方思想转变的出发点”(24),因此,按照理雅各对秦革命性的界定,第一次鸦片战争显然也是一场革命,一场帮助中国改革旧制、摆脱落后愚昧、走向新生活的革命。这就顺理成章地为鸦片战争找到了必然和正义的理由。
当英国利益需要维护时,理雅各的民族主义便“高于他的宗教信仰,以致于不加批评地支持大英帝国”(25)。出于虔诚的基督教信仰,理雅各认为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这在《中国经典》中多有涉及。但事实上,这种平等仅限于宗教理论范围,在实践中,他仍然主张将世界上的国家依据文明的程度划分为文明、半文明和野蛮国家(26)。文明国家(欧美国家)之所以文明是因为有知识的人懂科学和艺术,尽管文明国家的很多人对此也是知之甚少。半文明国家(亚非国家)之所以半文明是因为他们有很多习俗是野蛮的,尽管这些国家也有少量的艺术、法律和书籍。中国的愚昧落后是为西方人所不齿的,他们“对于中国充满了既愤怒又轻蔑的优越感”(27)。理雅各选择这种有悖基督教教义的内容并非投西方人所好,而是意在支持英国的殖民活动。
虽然理雅各有着正直的品格,和许多有良知的西方人士和大多数基督教传教士一样,从人类道德和基督教伦理的立场出发抨击鸦片贸易,但对于鸦片商的资助,理雅各却欣然接受;他虽并不主张西方国家用炮火来改变中国现状,但对于鸦片战争以及炮火下达成的不平等条约却毫不掩饰地表示赞赏。他将第一次鸦片战争描述为“上帝的意志正在中国进行着伟大的事业”(28)。第一次鸦片战争后,英华书院从马六甲迁至香港之际,身为书院负责人的理雅各把这一迁移描述为“前进中的一个伟大步骤:一次向撒旦统治之地靠近的漫长进军”(29)。中国官员和百姓认为传教是一种变相侵略,甚至担心传教士是英军间谍,但像其他传教士一样,理雅各认为传教是对中国的救赎,理应享有合法权利。既然外国人到中国是对中国人的救赎,那么作为回报,中国理应敞开大门贡献自己的各种资源,否则,用炮火将这扇大门打开就理所当然。由此,鸦片战争似乎不再是侵略战争,而鸦片战争的结果,则是上帝带给中国人民的福音。
三、以政治制度解释三代更替
理雅各以政治制度解释夏商周三代更替的结果,必然使清王朝和专制制度在中国的消亡成为必然结论,从而为英国侵略者在中国内地的殖民扩张进一步找到借口。
理雅各以封建制度解释三代的更替,将朝代覆灭的统治者因素,转化为制度因素。对于《尚书》中把夏商的灭亡归结为统治者的荒淫残暴一说,理雅各不以为然。他认为正如汤、武并不是道德英明一样,桀、纣也不是万恶不赦。夏商周的灭亡都是由于国力耗尽,末代君主也只是过于软弱无能,而不是过于残暴(30),而国力衰微和国君软弱都是封建制度的必然结果。春秋时期“中国大地实际上没有国君,各诸侯国家都以自己的是非标准来行事,没有仁慈和正义,也不以繁盛为原则,而是大国、强国欺凌吞并小国、弱国”(31)。的确,封建制度“带来了中央权力的削弱与地方权力的强大,也带来了所谓的‘封建无政府’状态”(32),在诸侯与中央政权之间争斗加剧的朝代末期,国君的统治便显得更为软弱无力。
除此以外,理雅各还认为封建制度下的一夫多妻制也会导致社会持续混乱。理雅各对一夫多妻制可谓深恶痛绝,他在《尚书》译序中对尧将两个女儿嫁给舜的举动极为惊讶,在《诗经》译本中对周文王及其王后倡导和发扬一夫多妻制大加批判。他指出“在封建社会,这种婚姻制度更具灾难性”:“受宠的妃子在夏商的最终亡覆中是显见的祸水,另一个宠妃则代表了周代末世的灾难”(33)。在理雅各看来,一夫多妻制还可以导致诸侯间的嫉妒、猜疑以至战争的爆发。他相信,既然存在堕落和无序,这个古老国度的道德就是再糟糕也不为过。并断言“只要一夫多妻制存在,中国得到西方国家的礼遇简直就是空想”(34)。从这种断言可以透视理雅各以古喻今的政治视角。
的确,在论及中国早期政治制度下的朝代更替时,理雅各真正关注的既不是上古中国封建制度,也不是后来的秦王朝专制帝国,而是中国当前政治制度和它的未来,因为这与大英帝国的利益息息相关。事实上,理雅各不仅早已在理论上把西方文化的植入视为消除中国专制制度的重要手段,而且身体力行,力主将这一理论付诸实践。1854年,他任职于香港殖民政府教育委员会,当时即已提出要在香港最大限度地推广英语学习。1860年,他又提出一项教育改革计划,并刻意论证这一计划的优越性:政府将会拥有一名积极参与教育工作的官员,同时许多在中国受过良好教育、与香港华人有联系的青年就会进入欧籍教师的英语班。理雅各的教育主张和改革计划的实施,使中国传统文化在殖民地香港进一步边缘化,同时也为内地培养了一支具有西方现代政治思想的革命力量,为中国专制制度的消亡创造了条件。
“耶稣不是西方人的耶稣,是天下人的耶稣”(35)。然而,理雅各却是西方、更确切地说是英国的传教士汉学家。在殖民地的教育改革中,他甚至再次将民族利益置于宗教信仰之上,把香港教育由教会统治转为世俗管理,使政府控制教育得以实现,并使香港教育开始注意对内地的作用和影响。在改革实践中,理雅各以民族利益为根本原则,这在其译著中得到了充分体现,而这种根本原则,与英国在中国内地的殖民扩张实有异曲同工之妙。
理雅各认为“古老的封建帝国业已消逝,专制帝国不久也会同样消亡”(36)。理雅各对中国早期政治制度的描述似乎在遵循英国历史发展的轨迹,但十九世纪中国的状况显然不同于十七世纪的英国。但无论如何,理雅各在以自己的方式为大英帝国的利益而尽职尽责。正如鸦片商人颠地所言:“我知道,在中国的西方商人都很慷慨大方,他们中的许多会帮助你完成这项工作,你不必为了拉赞助而东奔西跑。如果你在出版方面有什么难处的话,我会承担这部分费用。我们在中国赚钱,很乐意帮助任何对我们赚钱有利的事情”(37)。《中国经典》引用这番话是感谢鸦片商人对理雅各翻译事业的资助,同时也表明,理雅各的翻译工作代表了英国的民族利益。
理雅各《中国经典》的翻译工作始于英国殖民势力深入中国内陆的1856年,此时,英国已是世界上占有殖民地最多的国家,但英国国内工商业对海外原料和市场的巨大需求,再加上维多利亚女王(1830—1901)对帝国扩张的积极倡导和支持,使英国殖民扩张的步伐在整个十九世纪都未曾停息。
当然,诚如费乐仁所言,第二次鸦片战争导致传教活动极大受阻,理雅各才因此正式开始他的翻译事业,但从其主观言论来看,这位传教士汉学家的翻译活动的确是在配合大英帝国的殖民扩张。因具有保护中国内地自由传教的条款,理雅各将第二次鸦片战争签署的条约视为“天国福音”,“为福音进入中国切实有效地打开了大门”。英国的军事侵略无不以本国的商业利益为出发点,这类批评言论在香港也是经常见于报端,理雅各却对此视而不见。他谴责中国人“热衷于报复”,认为中国人虽有浓厚的忠君思想,爱好和平,但对于血腥的复仇,他们甚至会置官府的命令于不顾。在政府统治无力时,就像当前的清政府,个人及团伙就将法律控制在自己手中,以致整个国家陷于无休止的复仇和战事之中(38)。
理雅各对中国人好报复的看法,部分地出于中国基督徒车金光的被害,但对于中国的战乱,理雅各丝毫没考虑外国人的责任,而是归于中国人好报复的人格缺陷。并且认为,中国人的仁慈和互惠只限于“五伦关系组成的社会,却把外国人排除在外”(39)。这里所谓外国人,显然包括外国传教士、商人和军队(40)。另外,他还暗示了清政府的软弱无能,无法有效地统治民众。在此,理雅各又一次证明中国的专制政府的确应该消亡了。但是专制帝国怎样消亡?消亡之后又以怎样的政治制度来替代?理雅各指出:“中国的未来要取决于派遣代表进京的外国政府”(41)。显然,在理雅各看来,不谦卑、爱报复的中国人无法把握自己的未来,中国的未来只能靠外国人来帮助筹划和实现。于是,英国在中国内陆的军事扩张就具有了充分的合理性。
作为传教士汉学家,理雅各并没将中国的前途寄希望于他所信仰的救世主,也没有寄予基督教,而是寄于外国政府。这充分说明他的翻译工作和学术研究是以民族利益为旨归,以宗教信仰和学术研究服务于本国政治。在此基础上,理雅各实现了学术研究、基督信仰与民族主义的共荣共生,并使学术和宗教成为民族利益得以实现的工具。
翻译工作作为一种跨文化交际行为和学术活动,很难与政治绝缘,这在特殊的历史和文化语境中表现尤为显著。当“西方文化对中国的输入已成为政治控制的一部分”(42),理雅各从事汉学研究和典籍翻译的目的,即是“帮助西方人理解中国的宗教、道德、社会和政治状况,并找到最适合中国的改革方法”(43)。因此,西方汉学家对中国文化的译介也自然具有了政治性。
《中国经典》的编辑出版是面向特定的读者群体的。这个群体包括:传教士、汉学研究人员、中国事务研究人员、中国事务管理人员以及与中国打交道的西方商人。和普通读者相比,他们具有更加强烈的政治观念。因此,理雅各在《中国经典》译文和注释中,特别是在序言中充分表明了他的政治倾向。在《中国经典》译著中,翻译的客观忠实,基督教义的宽容仁慈,无不在以民族主义为表现形式的政治倾向面前黯然失色。译者一方面贬损中国封建社会的混乱无序、赞赏秦朝建立现代专制帝国的丰功伟绩,一方面又将关注的目光投向现实的中国和英国。在这种目光中,有自觉迎合政治形势、将国家和民族利益置于学术和宗教信仰之上的个性,有对赞助商的感恩之情,更有与民族利益发生冲突时,源语文化和目的语文化的激烈碰撞与妥协。
分析理雅各对中国早期政治制度的描述,从而揭示潜藏在文本背后的政治因素,无疑对全面理解理雅各的译著及翻译思想具有极大的帮助。我们不会因为这种渗透其作品的政治控制而否定译者为翻译中国传统典籍付出的艰辛劳动,也不会因此抹煞译著在汉学界以及汉籍英译史上的地位,但也不能因译著和译者的地位而忽略其中的政治倾向。虽然那个民族隔阂的时代渐行渐远,人们耳熟能详的已经是全球化进程中的经济和文化,然而全球化并不意味着民族差异的消除,更不意味着民族和国家利益之争的结束。承载着不同民族文化的交流中介——翻译事业及其成果,仍会在一定背景下被当作政治控制的工具去混淆读者的视听,造成读者对原著理解的偏差。
注释:
① James Legge,The Chinese Classics,Vol.Ⅲ,“Prolegomena”,Taipei:SMC Publishing Inc.,2000,p.198.
②④ I bid,p.197.
③ James Legge,The Chinese Classics,Vol.Ⅲ,Taipei:SMC Publishing Inc.,2000,pp.142-143.
⑤ James Legge,The Chinese Classics,Vol.Ⅰ,Taipei:SMC Publishing Inc.2001,p.424.
⑥ 吴义雄:《在宗教与世俗之间: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在华南沿海的早期活动研究》,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26页。
⑦ 岳峰:《架设东西方的桥梁:英国汉学家理雅各研究》,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76—180页。
⑧ Lauren F.Pfister,Striving for‘The Whole Duty Of Man’-James Legge and the Scottish Protestant Encounter with China,Vol.Ⅱ ,New York:Peter Lang,2004,p.88.
⑨ Norman J.Girardot,The Victorian Translation of China :James Legge' s Oriental Pilgrimage,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2,p.58.
⑩ James Legge,The Chinese Classics,Vol.Ⅲ,“Prolegomena”,Taipei:SMC Publishing Inc.,2000,p.199.
(11) 岳峰:《架设东西方的桥梁:英国汉学家理雅各研究》,第181页。
(12) D.E.Mungello,“A Confucian Voice Crying in the Victorian Wilderness”,The Journal Of Religion,Oct.2003.
(13) James Legge,The Chinese Classics,Vol.Ⅳ,“Prolegomena”,Taipei:SMC Publishing Ine.,1994,p.134.
(14) James Legge,The Chinese Classics,Vol.Ⅳ,Taipei:SMC Publishing Inc.,1994,p.531.
(15) James Legge,The Chinese Classics,Vol.Ⅲ,“Prolegomena”,Taipei:SMC Publishing Inc.,2000,pp.192-193.
(16) James Legge,The Chinese Classics,Vol.Ⅰ ,“Prolegomena”,Taipei:SMC Publishing Inc.2001,p.99.
(17) Ibid,p.101.
(18) James Legge,The Chinese Classics,Vol.IV,Taipei:SMC Publishing Inc.,1994,p.204.
(19)(20)(22) James Legge,The Chinese Classics,Vol.Ⅲ,“Prolegomena”,Taipei:SMC Publishing Inc.,2000,pp.199-200.
(21) [美]卫三畏著,陈俱译:《中国总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修订版序第4页。
(23)(24) [美]M.G.马森著,杨德山等译:《西方的中华帝国观》,北京,时事出版社,1999年版,第288、110页。
(25) Lauren F.Pfister,Striving for‘The Whole Duty Of Man’-James Legge and the Scottish Protestant Encounter with China,Vol.Ⅱ,New York:Peter Lang,2004,p.51.
(26) Ibid,p.46,p.51.
(27) Kenneth Scott Latourette,The Chinese-Their History and Culture,New York:Macmillan,1946,p.274.
(28) Brian Harrison,Waiting for China,The Anglo-Chinese College at Malacca,1818-1843,Hong Kong: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kong Press,1979,p.107.
(29) Helen Edith Legge,James Legge:Missionary and Scholar,London:Religious Tract Society,1905,pp.24-25.
(30) James Legge,The Chinese Classics,Vol.Ⅲ,“Prolegomena”,Taipei:SMC Publishing Inc.,2000,pp.198-199.
(31) James Legge,The Chinese Classics,Vol.Ⅴ,“Prolegomena”,Taipei:SMC Publishing Inc.,2000,pp.113-114.
(32) 黄春高:《西欧封建社会》,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版,第51页。
(33) James Legge,The Chinese Classics,Vol.Ⅲ,“Prolegomena”,Taipei.SMC Publishing Inc.,2000,p.199.
(34) James Legge,The Chinese Classics,Vol.Ⅳ,“Prolegomena”,Taipei:SMC Publishing Inc.,1994,p.140.
(35) Lauren F.Pfister:Striving for‘The Whole Duty Of Man’-James Legge and the Scottish Protestant Encounter with China,Vol.Ⅱ,New York :Peter Lang,2004,p.30.
(36) James Legge,The Chinese Classics,Vol.Ⅲ,“Prolegomena,”Taipei:SMC Publishing Inc.,2000,p.200.
(37) James Legge,The Chinese Classics,Vol.I ,“ Biographical Note”,Taipei:SMC Publishing Inc.2001,p.10.
(38) James Legge,The Chinese Classics,Vol.Ⅰ,“Prolegomena”,Taipei :SMC Publishing Inc.2001,p.111.
(39) Ibid,p.102.
(40) Lauren F.Pfister,Striving for‘The Whole Duty Of Man’- James Legge and the Scottish Protestant Encounter with China,Vol.Ⅱ,New York:Peter Lang,2004,p.105.
(41) Ibid,p.69.
(42) Kenneth Scott Latourette,The Chinese - Their History and Culture,New York:Macmillan,1946,p.274.
(43) James Legge,The Chinese Classics,Vol.V,“Prolegomena”,Taipei:SMC Publishing Inc.,2000,p.51.
标签:中国经典论文; 基督教教义论文; 理雅各论文; 中国宗教论文; 语言翻译论文; 国学论文; 尚书论文; 孔子论文; 传教士论文; 封建制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