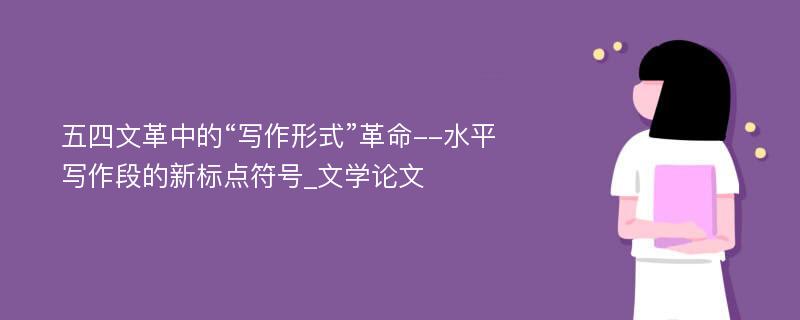
“五四”文学革命中的“书写形式”革命——横行书写 分段 新式标点符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学革命论文,标点符号论文,形式论文,五四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492(2010)03-0166-07
早在清末的白话文运动和域外文学的翻译过程中,像卢戆章、严复、黄遵宪、周氏兄弟等,就已初步探讨或使用过分段、横行书写和新式标点符号,但由于时代的局限,这些初步的尝试并未对文学变革产生很大影响。到了五四时期,文学革命的先驱们,在思想革命、语言变革和书写形式变革方面“三管齐下”,最终取得了文学革命的胜利。讨论文学革命及其现代文学的形式特点,“书写形式”的变革,也是一个无法绕开的话题。
一、留美时期胡适对变革“书写形式”的尝试
对于清末语言变革中新式标点、分行分段等书写形式的提倡和应用,胡适并不陌生,显然对他倡导文学革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他说,“林译小说都用圈断句,故能读者较多”。谭嗣同、梁启超等的“新文体”,“靠着圈点和分段的帮助,这种解放的新文体居然能做长篇的议论文章了;每一个抽象的题目,往往列举譬喻,或列举事例,每一譬喻或事例各自成一段,其体势颇像分段写的八股文的长比,而不受骈四俪六的拘束,所以气势汪洋奔放,而条理浅显,容易使读者受感动。”[1]
胡适在发起文学革命之前的1915年,东美中国学生会新成立了一个“文学① 科学研究部”(Institute of Arts and Sciences),胡适是文学股的委员,他与赵元任商量把“中国文字问题”作为本年文学股的论题。胡适这年8月为会议作了英文论文《如何可使吾国文言易于教授》,其中提出使用新式标点符号的建议,他说:“吾国向不用文字符号,致文字不易普及;而文法之不讲,亦未始不由于此(说见所著《文字符号论》)。今当力求采用一种规定之符号,以求文法之明显易解,及意义之确定不易。”[2]胡适说他这里讲标点符号的重要是学外国文得来的教训。事实上,胡适早在这一年的6月,为当年创刊的《科学》杂志作了一篇长约万字的论文《论句读及文字符号》,这篇长文发表于1916年1月《科学》杂志第二卷第一期。他在日记里记此事道:“吾之有意于句读及符号之学也久矣。此文乃数年来关于此问题之思想结晶而成者,初非一时兴到之作也。后此文中,当用此制。”[3]胡适为《科学》创作此文并非偶然,由中国科学社于1915年创刊的《科学》杂志,此时已经采用横行书写和新式标点符号。《科学》杂志对于横排和新式标点的采用曾做过这样的说明:“本杂志印法,旁行上止,并用西文句读点之,以便插写算术及物理化学程序,非故好新奇,读者谅之。”② 可见横行书写及新式标点的提倡,首先是受西洋拼音文字和科学文章的影响而提出的。这从大的方面说,文学革命本身的用意,在于以西洋的科学思想和精神改造中国文学。用西洋文学描写的准确性和逻辑性来衡量中国文学,中国文学的含糊笼统以及由此而养成的国民笼统含糊的思想,都有悖于科学精神;③ 若从小的、技术的层面来看,在这一愈趋于世界化的时代,中文原有的书写形式即不合于印刷术的要求,也有碍于文化交流和文化融合。所以,我们说,书写形式和标点符号的使用,看起来是一个小的枝节问题,但究其实,它与白话文的采用一样,都是使语言朝着通俗化、精确化方向变革的一个很重要的措施。
但这些在科学文章等应用性的文章中早已使用的书写形式和标点符号,为什么也要在文学革命时再经多次讨论而应用到文学中来。汪晖认为,这是由于白话文在近代经历了以西方为榜样的技术化、科学化的改造过程。科学语言成了新的日常语言和文学语言的创新源泉。尽管汉字及其书写是一个古老传统的产物,但中国的现代语言,特别是中国现代语言的书写形式是以科学语言为元形式的。他说:“我所以如此强调现代白话文经历了技术化的过程,是因为白话文本身并不是全新的创制。唐代口语文学的存在由于敦煌发现的古写本而得到确认。宋代的评话、元代的杂剧,以及宋代以后的儒者、僧侣的语录,元代由蒙语译出的皇帝敕语、圣旨和颁布的法律,以及明代的小说都是白话口语的见证。正由于此,不是白话,而是对白话的科学化和技术化的洗礼,才是现代白话文运动的更为鲜明的特征。白话文和文学语言的特殊关系的形成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胡适等人有关新文学的历史叙事注重于为白话寻找历史合法性,而忽略了这种现代语言与科学语言的关系。其实,1916年就在《新青年》杂志孕育白话文运动之前,胡适在《科学》月刊第二卷第二期(应为“第二卷第一期”,笔者注)发表了他写于1916年6月的长文《论句读及文字符号》及两篇附录《论无引语符号之害》和《论第十一种符号(破号)》,这些文章不仅发表于首用横排、标点的《科学》月刊,而且在某种是意义上也是对于《科学》月刊的一种说明。《论句读及文字符号》分三个部分,分别是‘文字符号概念(无符号之害)’、‘句读论’和‘文字符号及其用法’。文中规定了符号十种,在引论部分,他讨论没有文字符号的三大弊病:一为意义不能确定,容易误解,二为无以表示文法上的关系,三为教育不能普及,实际说明了语言变革的基本方向。”[4]
二、《新青年》对“书写形式”的讨论和实践
以科学语言的精密、准确及其书写形式的规范来革新文学,不仅仅是我们今天的后见之明,证诸当时的言论,也可见文学革命确实具有科学化的取向。
1917年4月1日《新青年》三卷二号李濂镗致胡适的信中说:“盖今日吾国欲臻富强之域,非昌明科学普及教育不可。欲昌明科学普及教育,则改良文学,实入手第一着也。”这非常清楚地说文学革命的目标和取向是“昌明科学”、“普及教育”,而文学革命只不过是其手段。既然要昌明科学,那么文学改良就得以科学的精神和规范来进行。这是文学革命要将科学语言的形式规范变成文学的形式规范的根本所在。
横行书写、新式标点虽早在文学革命之前的清末的应用性文字中已经使用了,但自1917年1月1日《新青年》二卷五号揭起文学革命大旗以来,它们能否应用到文学领域中来,还得经过许多争论。
与《科学》月刊从一开始使用横排和新式标点不同,《新青年》从一开始就是横排竖行杂用。1915年9月15日《青年杂志》一卷一号中陈独秀译《妇人观》(Thought on Women)译文和英文均为横行;但同期中署名“中国一青年”译美国马克威博士与斯密士学士著《青年论》则译文用竖行,英文用横行。《新青年》虽从四卷一号开始用新式标点符号,但这种横排、竖排并置的情况在《新青年》中一直延续到1922年7月。但有一点是明确的,《新青年》中最早使用横排的文章都是英汉对照的翻译文。这说明横排的使用,是为了与西洋拼音文字在书写形式上保持一致。
文学革命发动以来,对横行书写和新式标点符号讨论最多、最积极的当数钱玄同,1917年5月1日他在《新青年》三卷三号中与陈独秀通信讨论西文译名时说:
……或曰,高等书籍写原文,固为便利。然中文直下,西文横迤,若一行之中有二三西文,譬如有句曰:
“十九世纪初年,France有Napoleon其人。”如此一句,写时,须将本子直过来,横过去,搬到四次之多,未免又生一种不便利,当以何法济之?曰,我固绝时主张汉文须改用左行横迤,如西文写法也。人目系左右相并,而非上下相重,试立室中,横视左右,甚为省力,若纵视上下,则一仰一俯,颇为费力。以此例彼,知看横行较易于直行。且右手写字,必自左至右,均无论汉文西文,一字笔势,罕有自右至左者,然则汉文右行,其法实拙。若从西文写法,自左至右横迤而出,则无一不便。我极希望今后教科书从小学起,一律改用横写,不必专限于算学、理化、唱歌教本也。既用横写,则直过来横过去之病可免矣。此弟对于译言之意见,足下以为何如?
……
我们既然绝对主张用白话体文章,则自己在《新青年》里面做的,便应该渐渐的改用白话。我从这书通信起,以后或撰文,或通信,一概用白话,就和胡适之先生做《尝试集》一样的意思。此外别位在《新青年》里面撰文的先生,和国中赞成做白话文章的先生们,若是大家都肯“尝试”,那么必定成功。
同期《新青年》陈独秀答钱玄同道:“仆于汉文改用左行横迤,及高等书籍中人名地名直用原文不取译音之说,极以为然。”
在钱玄同提出改用横行书写的同期《新青年》中,刘半农详细地提出分段、标点符号等“形式上的事项”,他说:
此等事项,较精神上的事项为轻。然文学既为一种完全独立之科学,即无论何事,当有一定之标准,不可随随便便含混过去。其事有三:(一)分段中国旧书,往往全卷不分段落。致阅看之时,则眉目不清。阅看之后,欲检查某事,亦茫无头绪。今宜力矫其弊,无论长篇短章,一一于必要之处划分段落。惟西文二人谈话,每有一句,即另起一行。华文似可不必。
(二)句逗与符号余前此颇反对句逗。谓西文有一种毛病,即去其句逗与大写之下,即令人不懂。汉文之不加句逗者,却仍可照常读去。若在此不必加句逗之文字上而强加之,恐用之日久,反妨害其原有之能事,而与西文同病。不知古书之不加句逗而费解者,已令吾人耗却无数心力于无用之地。吾人方力求文字之简明适用,固不宜沿有此种懒惰性质也。然西文,;:.四种句逗法,倘不将文字改为横行,亦未能借用。今本篇所用.、。三种,唯、之一种,尚觉不敷应用,日后研究有得,当更增一种以补助之。至于符号,则?一种,似可不用,以吾国文言中有“欤哉乎耶”等,白话中有“么呢”等问语助词,无须借助于记号也。然在必要之处,亦可用之。!一种,文言中可从省,白话中决不可少。“”‘’之代表引证或谈话,——之代表语气未完,……之代表简略,()之代表注解或标目,亦不可少。*及字旁所注123等小字可以不用,以汉文可用双行小注,无须foot-note也。又人名地名,既无大写之字以别之,亦宜标以一定之记号。先业师刘步洲先生尝定单线在右指人名,在左指官名及特别物名,双线在右指地名,在左指国名朝名种族名,颇合实用。惜形式不甚美观,难于通用。
(三)圈点此本为科场恶习,无采用之必要。然用之适当,可醒眉目,今暂定为三种,精彩用。,提要用·,两事相合则用⊙。惟滥用圈点,当悬为厉禁。[5]
时隔两月,钱玄同在《新青年》三卷五号里提出应用文“改革大纲十三事”,其中再次谈到标点符号和横行书写问题:
8无论何种文章(除无句读文,如门牌、名刺之类),必施句读及符号。(句读,如.,:;之类,或用。、△亦可。符号,如()“”|[用于人名之旁]‖[用于地名之旁]之类。此事看似无关弘旨,其实关系极大。古书之难读误解,大半由此。符号尤不可少。)惟浓圈密点,则全行废除。
……
12改右行直下为左行横迤。[6]
紧接着在1917年8月1日《新青年》三卷六号,钱玄同再次致信陈独秀,讨论横行书写和标点符号问题。他说:“我以前所说要把右行直下的汉文改用左行横迤,先生回答道,‘极以为然’。现在我想,这个意思,先生既然赞成,何妨把《新青年》从四卷第一号起,就改用横式?”他进而提出,以后不仅像《科学》《现象从报》这些讲科学的杂志,采用横式,“即不纯粹讲科学,或完全和科学不相干的(小说诗歌之类),也是用横式比用直式来得便利。”“又像文章中间所用的符号和句读,要他清楚完全,总是全用西洋的好(《科学》的符号和句读,全西式,看下去很明白。《现象从报》仍用中式,便不醒目),这又是宜于横式的。”
钱玄同在这里明确提出,要将此前已在科学文章等应用文中使用的横写与新式标点用到诗歌、小说等文学之中去,并催促以除旧布新为宗旨的《新青年》赶紧将之付诸实践,以为社会先导。
陈独秀在同期《新青年》答复钱玄同说:“《新青年》改用左行横迤,弟个人的意思,十分赞成,待同发行部和其他社友商量同意即可实行。”
不知陈独秀商量的结果如何,《新青年》在接下来的1918年1月15日四卷一号并未采用横排方式,倒是从这一期开始采用新式标点符号。黎锦熙在讲到《新青年》四卷一号的变化时说:“到民国七年(1918)《新青年》第四卷出版时,新式标点符号方才与直行的汉文合作,当时看起来还觉得怪不合式的。”[7]
1918年2月15日《新青年》四卷二号中,钱玄同针对有人嫌西文新式标点符号太多、记起来麻烦,他建议暂时可采用繁、简二式:繁式用西文,;:.或。!六种符号,简式用、。两种符号。同期《新青年》中,钱玄同为刘半农翻译的《天明》所写的附志里再次强调标点符号之于文学的特殊意义。他说:“文字里的符号是最不可少的,在小说和戏剧里,符号之用尤大;有些地方,用了符号,很能传神;改为文字,便索然寡味:像本篇中‘什么东西?’如改为‘汝试观之此为何物耶’;‘迪克’如改为‘汝殆迪克乎’……如其这样做法,岂非全失说话的神气吗?”
1918年8月15日《新青年》五卷二号通信栏里,朱我农质问“《新青年》何以不用横行?用横行既可免墨水污袖,又可以安放句读符号。我所见的三四本《新青年》每一页中句读符号错误的地方至少有二三处。这就是直行不使用句读符号的证据。”同期《新青年》中胡适与钱玄同都对朱我农的来信作了答复。胡适虽在文学革命前就提倡使用新式标点符号,但对横行书写问题并不热心,他说:
《新青年》用横行,从前钱玄同先生也提议过。现在所以不能实行者,因为这个究竟还是一个小节的问题。即如先生所说直行的两种不便:第一“可免墨水污袖”,自是小节;第二“可以安放句读符号”;固是重要,但直行也并不是绝对的不便用符号。先生所见《新青年》里的符号错误,乃是排印的人没有句读知识之故。《科学》杂志是用横排的,也有无数符号的错误。我个人的意思,以为我们似乎应该练习直行文字的符号句读,以便句读直行的旧书。除了科学书与西洋历史地理等书不能不用横行,其余的中文书报尽可用直行。先生以为如何?
钱玄同答复朱我农说:
中国字改用横行书写之说,我以为朱我农先生所举的两个理由,甚为重要。还有一层,即今后之书籍,必有百分之九十九,其中须嵌入西洋文字。科学及西洋文学书籍,自不待言。即讲中国学问,亦免不了要用西洋的方法。既用西洋的方法,自然要嵌入西洋的名词文句:如适之先生新近在北京大学中编纂之《中国哲学史大纲》内中嵌入的西洋字就颇不少。若汉文用直行,则遇到此等地方,写者看者均须将书本横搬直搬,多少麻烦,多少不便啊!至于适之先生所谓“应该练习直行文字的句读符号,以便句读直行的旧书”:这一层,我觉得与改不改横行是没有关系的。适之先生所说的“句读符号”,不知还是重刻旧书要加句读的呢?还是自己看没有句读旧书时用笔去句读他呢?若是重刻旧书,则旧书既可加句读,何以不可改横行?如其自己看旧书时要去句读他,此实为个人之事,以此为不改横行的理由,似乎不甚充足。同人中如适之半农两先生,如玄同都能用新式句读符号句读古书,却并没有怎样的练习过。总而言之,会不会用“句读符号”,全在懂不懂文中的句读:如其懂的,横行直行都会用;如其不懂,横行直行都不会用。这句话未知适之先生以为然否。
惟《新青年》尚未改用横行的缘故,实因同人意见对于这个问题尚未能一致。将来或者有一日改用,亦未可知。朱先生之提议,在玄同个人,则绝对赞同此说也。
1918年9月15日《新青年》五卷三号中,胡适对慕楼和黄觉僧讨论句读符号的意见作了答复。慕楼、觉僧认为中文可用其他新式标点符号,但中文中有么、呢、乎、哉等表疑问和感叹的词,若与?!并用,似乎重叠。胡适说他原来也持此意见,但后来认为钱玄同的看法更为合理。钱玄同认为?!这两种符号都不可废,因为中国文字的疑问、感叹句,往往并不用上举诸字;并且这些字有各种用法,不是都拿来表疑问、感叹的意思。胡适还解释了他对使用标点符号的基本看法,认为“文字的第一个作用便是达意。种种符号都是帮助文字达意的。意越达得出越好,文字越明白越好,符号越完备越好。这是本社全用各种符号的主意。”
对于《新青年》在使用横行书写方面的迟疑和使用标点方面的混乱状况,陈望道在1919年1月15日《新青年》六卷一号中作了尖锐的批评,他说:“……我对于诸子,还要说诸子缺‘诚恳的精神’,尚不足以讲‘撤销他们的天经地义’。譬如文字当横行,这已有实验心理学明明白白的诏告我们,诸子却仍纵书中文,使与横书西文错开;圈点与标点杂用,这是东人尾奇红叶的遗毒,诸子却有人仿他,而且前后互异,使浅识者莫名其妙——这不是缺‘诚恳’的佐证么?”
钱玄同在回答陈望道的批评时说:“《新青年》杂志本以荡涤旧污,输入新知为目的。依同人心理,自然最好是今日提倡,明日即有人实行。但理想与事实,往往不能符合,这是没法想的。同人心中,决无‘待其时而后行’之一念。像那横行问题,我个人的意见,以为横行必较直行为好,在嵌入西文字句的文章里,尤以改写横行为宜,曾于本杂志三卷三号、六号、五卷二号通信栏中屡论此事。独秀先生极以为然,原拟从本册(六卷一号)起改为横行。只因为印刷方面发生许多困难的交涉,所以一时尚改不成,将来总是要想法的。至于标识句读,全用西文符号固然很好;然用尖点标逗,圆圈标句,仅分句读二种,亦颇适用。我以为并不妨并存。《新青年》本是自由发表思想的杂志,各人的言论,不必尽同;各人的文笔,亦不能完全一致;则各人所用的句读符号,亦不必定须统一,只要相差不远,大致相同,便得。”
新式标点符号的使用中虽有新、旧二式混用的情况令人不满,但总归是已经采用了,而横排问题在《新青年》中的使用则充满了曲折。
1919年11月1日的《新青年》六卷三号,钱玄同还在和陈大齐(百年)讨论横行问题。钱玄同基本上是老调重弹,认为横行书写便于嵌进西文,以免墨水污袖,印刷时便于加标点符号。而陈大齐则从生理学的方面,说明横行书写更符合人在阅读和书写时眼球运动的生理需要。
1921年8月1日《新青年》九卷四号中,张东民《华文横行的商榷》一文是《新青年》最后一篇讨论横行问题的文章。作者认为横行书写的好处,“一,合眼睛的卫生,可以延长目力的寿命。二,减少眼睛的运动,读者可少头痛之虑。三,新圈点法和横行法须相联取用,不可去此用彼。四,可添白话诗的美观,并且增他的自由活泼精神。”张东民在此提倡横行的理由,除了和前举诸人相同的以外,是他将横行这一书写形式上升到现代文学的审美层面来加以认识。他说:“现在新式的自由诗词,是渐渐的盛行了。但是倘若吾们能将那些诗词,横写起来,那么更觉得美观,而且诗中的精神,也愈活泼易见了。”
讨论虽然一直在进行,但《新青年》直到1922年7月1日最后一期,不曾全面实行横行书写。
新式标点符号经过清末至文学革命时期二十多年的讨论和实践,像白话文的使用一样,最终也以得到国家权力机关的认可而得以确定其合法性。1919年11月,马裕藻、朱希祖、钱玄同、周作人、刘复、胡适等六人向教育部提出《请颁行新式标点符号议案(修正案)》,规定了十二种新式标点符号的写法和用法,以及空格分段等;认为没有标点符号不能断句、不能明白表示意思、不能教授文法,所以他们“请教育部把这几种标点符号颁行全国,使全国的学校都用符号帮助教授;使全国的报馆渐渐采用符号,以便读者;使全国的印刷所和书店早日造就出一班能排符号的工人,渐渐地把一切书籍都用符号排印,以省读书人的脑力,以谋教育的普及。”[8]
在胡适等人向教育部提请使用新式标点符号议案的同时,《新青年》也于1920年1月1日七卷二号中对其日后所用的标点符号和行款首次作了详细而明确的规定:“本志从第四卷起,采用新标点符号,并且改良行款,到了现在,将近有两年了。但是以前所用标点符号和行款,不能篇篇一律,这是还须改良的。现在从七卷一号起,划一标点符号和行款……本志今后所用标点符号和行款,都照上面所说办理,请投稿和通信诸君,把大稿和来信也照此办理”。[9]
胡适等人的提议,很快得到了教育部的通过。1920年2月,教育部以第五三号训令通令全国采用新式标点符号。训令说:“据国语统一筹备会函送新式标点符号全案请予颁行等因前来查原案内容远仿古昔之成规近采世界之通则足资文字上辨析义蕴辅助理解之用合亟检同印刷原案一册令行该厅查照酌量分配转发所属学校俾备采用此令。”[10]教育部虽通令采用新式标点,但自己的公文仍没有标点,显示了过渡时代的特点。
三、“书写形式”的变革对于现代文学的意义
新式标点符号的使用,对于现代文学的意义极大。它与白话的使用一样,把文字从古典的押韵、对仗、平仄等形式束缚中解放了出来,使它能够更加生动活泼而又精密准确地表情达意。现引几位新文学运动的当事人及古典文学研究者论及新式标点符号的言论,以说明新式标点符号之于现代文学的意义。
1920年,周作人写了《圣书与中国文学》一文,认为《圣书》的中国语译本,“在中国语及文学的改造上也必然可以得到许多帮助与便利”,这既有精神上的灵肉一致的融合、人道主义的思想等,也有形式方面“欧化的白话”,其中包括标点符号的应用:“人地名的单复线,句读的尖点圆点及小圈,在中国总算是原有的东西;引证话前后的双钩的引号,申明话前后的括号解号,都是新加入的记号。于字旁小点的用法,那便更可佩服;他的用处据《圣书》的凡例上说,‘是指原文没有此字,必须加上才清楚,这都是要叫原文的意思更明显’……《马太福音》的确是中国最早的欧化的文学的国语,我又豫计他与中国新文学的前途有极大极深的关系。”[11]
1921年,胡适回顾他1904年在上海梅溪学堂读书时《时报》的文体对他的影响时说:“……用简短的词句,用冷隽明利的口吻,几乎逐句分段,使读者一目了然,不消费功夫去点句分段,不消费功夫去寻思考虑。当日看报人的程度还在幼稚时代,这种明快冷刻的短评正合当时的需要。”[12]胡适后来成为文学革命的发起人,而且从语言形式入手来革新文学,不能说与清末语言变革运动中分行分段、新式标点的采用对他的影响没有关系。
1934年,胡适在天津《大公报》撰文指出,报纸文字的标点分段与白话文的使用一样,对于新文学运动起了极大的促进作用。他说:“古书的难懂,不全在文字的难认;识了几千字的人,往往还不能读没有句读的书。所以古时凡要人容易懂得的文字,必须加上句读。所以童蒙读本有句读,告示有朱笔句读,佛经刻本有句读,诉状公牍必须点句,科举考卷也要作者自己点句……新式句读符号的采用,起于留美学生办的《科学》杂志。民国七年以后,《新青年》杂志开始用新式句读符号。后来北大教授们提出的‘标点符号案’经教育部颁布之后,‘标点符号’的名称就正式成立了,标点的采用也更广了。”[13]
对于新文学何以要采用标点符号以及它对中国文学的深远影响作出最为精彩分析的当属郭绍虞。作为新文学早期的作家和古代文学研究专家,他能从整个文学史的高度洞察新、旧文学之别,尤其是他认为只有从语言形式方面才能说明文学本身的演变,所以他往往从中国语言的特性出发来分析中国文学的演变。他在《中国语词之弹性作用》一文指出,现代文学之语体文所以会走上欧化的路,关键在于标点符号的采用,他说:“有人以为那是近人不满于以往文辞只重平面的铺排,而欲求其意义之复杂包孕,始创此类特殊的句法。但是此种要求亦不自今日始。以前翻译佛经的时候,也早已创造出这种包孕的句子,何以这种句法不会影响到其它文体,又何以佛经必须以四字为句,这个关键实在全在于标点符号。盖昔人作文先要注意到断句。骈文无论矣,即在散文也是如此。一般古文家所研练揣摩者,大都不外句法的问题。句调可以成诵者,古文即能够成功。否则句读且不易确定,教人如何懂得。一般古文家的作品,凡句涩言艰者,往往不传,即传亦不易普遍。”在他看来,古人的讲求文句的匀整、对偶、叶韵,都是因为没有标点符号,而利用汉字本身的特点,使其充当断句的标识。现在的语体文因为有了标点符号的辅助,才能表达古文无法表达的曲折的情致、复杂的意思。[14]
1939年,郭绍虞在《新文艺运动应走的新途径》一文中详细论述了新文学在“写文方式”与“造句方式”上的创新所给予中国文学的解放作用。他认为,旧文学之弊在于重词藻、有定格而没有内容,师古而不师心,陈陈相因,展转相师,说话形成了一定的套式,而生趣索然。旧文学之所以会走上这样一条道路,是因为文字本身还要充当句读符号,不能曲折变化。“明代文人如袁中郎等辈也很想独创一格,何以不会成功?旧文艺中如白话小说应当变化自如了,何以亦束缚于章回体之下而不能自拔?乃至何以白话的语录体会变成骈俪的语录体?何以戏剧中自话的说白,会变成骈俪的说白?”在他看来,新文学与旧文学的区别,新白话与旧白话的区别,或者说白话文的提倡在历史上早已有之,而唯独这次能够取得成功的原因,即在于分行分段、新式标点符号的采用。他解释新文学运动之所以是创格而有别于历史上的白话文时说:
此种关系,由于旧文艺是准语言体,离口语远,新文艺是纯语言体,与口语合,所以袁中郎辈虽也不避俗字俗语,而终不脱文言化的白话,遂也终不能为创格。这般说,固然不失为原因之一,但是我觉得更重要者,仍在于上文所说的欧化。欧化所给予新文艺的帮助有二:一是写文的方式,又一是造句的方式。写文的方式利用了标点符号,利用了分段写法,这是一个崭新的姿态,所以称为创格。造句的方式,变更了向来的语法,这也是一种新姿态,所以也足以为创格的帮助。这即是新文艺所以成功的原因……由写文方式言,旧文艺正因为不用标点符号,所以不能不注意断句;一注意断句,不是句法匀整,成为骈文韵文,绝不类语言的姿态;便是词意过求完整,很少能写出语言特殊的神情。
……
再有,旧文艺正因为不分行写,所以不能不注意段落,注意照应,注意顺序,但是一注意这些问题以后,自然成为:“某生,某处人,生有异禀,下笔千言……一日于某地遇一女郎……好事多磨……遂为情死,”等刻板文章。由小说言不成其为小说,由传记言也不成其为传记,写得不生动,写得不经济,但在旧文艺中却最多这一类的文章。梁启超译《十五小豪杰》称其书:“一起之突兀,使人堕五里雾中,茫不知其来由,此亦可见泰西文字气魄雄厚处”。实则这类气魄雄厚的文字在先秦古籍中倒可以遇到,在唐宋以后的古文中倒不易遇到。此其故,恐怕与写文不分行的方式,多少有一些关系。所以我说秦汉人的文辞,一分行写,一加标点,则精神更出,现在人的文辞,假使不分行写,不加标点符号,可以使人没法断句。从前文人,不曾悟到标点符号的方法,于是只有平铺直叙的写,只有依照顺序的写;不曾悟到分行的写法,于是只有讲究起伏照应诸法,只有创为起承转合诸名。这样一来,不敢有变化,也无从有创格,平稳有余,奇警不足,这是旧文艺所以日趋贫乏的原因。即有一二奇特之士,欲革除这种陈腐闒茸的文风,而不得其法,只知删除语助辞,只知故意使上下文不相衔接,方且自以为得古人属词造句之法以自矜高古,而不知违了文从字顺的戒条,文辞虽奇,其奈人之看不懂何!明代文人所谓“秦汉”与“唐宋”二派的争峙,实在即是这些关系。平易者流为浅俗,奇险者成为艰涩,一则贫乏而无生气,一则摹拟而无新意,二者皆讥。
新文艺便不然。有时一字可成一句,可以占一行。如:
“夜。”
只此一字,便令人想到下述故事的背景,是在夜间。便令人想到夜幕开展的各种景象,便令人感到夜神降临时的各种心理,便令人从这种景象这种心理中体会到与下述故事的调和。这即是新文艺的创格之一。这种情形,在旧文艺中是绝对看不到的。
……
我们要晓得,分行一写,则于看的时候可以领略文中分段的精神;连续着写则必须于诵读时才能体会得出。这才是昔人所以需要诵读而现在人不甚需要诵读的理由。所以我说新文艺的成功在于创格,而所以能创格则在标点符号。[15]
他认为新式标点符号、分行分段,“这些都是新文艺之所长,而旧文艺之所短。新文艺有了这种工具,有了这个方便法门,所以一方面格式尽多变化而不虑其单调,内容尽可丰富自不患其贫乏;而在另一方面则即使有些佶屈聱牙的句子,也不致令人不能句读,无从索解。”[16]
尽管我们说,将新文艺运动的成功归于分行分段和标点符号的采用等形式方面的革新,可能显得有些夸张。但我们也不容抹杀这样一个事实,即新文学运动的成功、新文学特质的形成,确实离不开这些形式要素。横行书写、分行分段,特别是新式标点符号的使用,对于中国文学的意义在于,它把文字在古典文学中所承担的句读作用,下放给了分行分段和标点符号,从而使现代文学的语言能够在形式上更加灵活自由而又曲折多变,在内容上能够更加复杂包孕而又层次清晰,这都是中国古代文学所不能具备的。论者一般讲现代文学与古代文学的区别,只注意白话取代文言这一语言形式的变化,孰知没有这些写文方式的新变,白话文学很有可能由文言的“滥调套语”和“对仗”转到白话的“滥调套语”和“对仗”中去。
[收稿日期]2009-12-08
注释:
① 这里的文学与今天的“文学”概念不同。
② 《科学》创刊号例言,1915年。
③ 周作人在《思想革命》中说:“我们反对古文,大半原因为它晦涩难解,养成国民笼统的心思,使得表现力和理解力都不发达。”1916年1月10日《东方杂志》中黄远庸的《国人之公毒》将“笼统主义”视为国民性的痼疾而痛加针砭:“余因含茹深痛,深觉中国今日之输入外国制度与学术也,一切皆以笼统主义笼统之,故为此论。盖国人之公毒既瀚漫不可救,故如德儒李般之言,凡国民有其一定之性质。其性质未易,则任取何种新制度新文物以贯输之。而此等新有者,皆随旧质而同化,一一皆发出其固有之形式而后止,此前所谓毒未拔而补剂适以滋毒之说也。然今日世界,何谓文明,曰科学之分科,曰社会之分业,曰个性之解放,曰人格之独立。重论理,重界限,重分划,重独立自尊,一言以蔽之,皆与笼统主义为公敌而已。”1918年6月15日,张厚载在《新青年》四卷六号通信栏中说,文学改良后,文学上有三大益处,其一为:“使文学有明确之意思,真正之观念。旧文学之弊,在笼统含糊;黄远生以‘笼统为国人之公毒,不仅文字一事’,新文学则绝无此种弊病,一字有一字之意思,一句有一句之意思,一节有一节之意思,文字浅显,而意思明确;多作此种文字,可使吾人头脑清楚,知识明白。”
标签:文学论文; 标点符号论文; 胡适论文; 钱玄同论文; 新青年论文; 文化论文; 读书论文; 白话文论文; 五四运动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