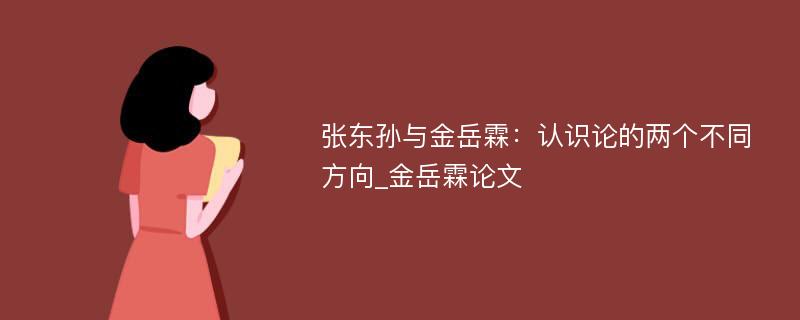
张东荪与金岳霖:两条不同的知识论路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两条论文,知识论文,金岳霖论文,张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 张东荪和金岳霖是20世纪中国哲学知识论的巨擘,但他们各自所建构的知识论系统却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并表现在人类知识的诸多根本问题上,从而呈现出两条不同的知识论路向。就其中的内在与外在的关系、间接呈现与直接呈现、写真与非写真的问题而言,二人的差异表现在:张东荪坚持“内在关系说”、“间接呈现说”和“非写真说”,而金岳霖则坚持“外在关系说”、“直接呈现说”或“直知对象论”和“写真说”。二者的差异并非表明孰优孰劣,但说明了在金岳霖之外,张东荪对于20世纪中国哲学知识论也是作出了重要贡献的。
在20世纪中国哲学知识论领域中,存在着两个重要的知识论系统,其一是张东荪的知识论系统,其二是金岳霖的知识论系统。这两个知识论系统,在人类知识的诸多根本问题上,都有着相异或相反的观点,其所走的,显然是两条不同的知识论路向。
两条路向之观点的差异,在知识与真实性之关系、知识论与形上学之关系、归纳原则之地位、感觉与外物之关系、概念与经验之关系、经验之本性、综合命题与分析命题之关系、知识之标准、唯理论和经验论之关系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上,都有明显的表现。限于篇幅,本文只谈三个主要的方面,一是内在与外在关系问题,二是间接与直接呈现问题,三是写真与非写真问题。在金岳霖之外,提出或坚持内在关系说、间接呈现说与非写真说,可以说是张东荪对于20世纪中国哲学之知识论的三项主要贡献。
⑴张东荪坚持“内在关系说”,金岳霖则坚持“外在关系说”。
“内在关系说”(theory of internal relation)的提出者是布拉德雷(F.H.Bradley,1846—1924), “外在关系说”(theory ofexternal relation)的提出者是罗素(B.Russell,1872—1970), 他们都是英国哲学家。前者是自立的,后者是为反对前者而提出来的。
张东荪并没有提出“内在关系说”概念,为什么本文又认为倡导“内在关系说”是张东荪对中国哲学的一项贡献呢?本文谓是贡献,主要是出于这样两方面的考虑:张东荪第一个将“内在关系说”引进到中国哲学中,让它成为中国哲学的一部分,这是贡献;张东荪第一个用内在关系解释知识关系,确系中国哲学史上从来未有之壮举,这是贡献。
用一句通俗的话来表达,“内在关系说”是这样一种学说,它认为关系可以改变关系者的性质,换言之,它认为关系者一旦进入关系,便失去其原有面貌与性质。张东荪认为知识关系就是这样的一种内在关系,知识是内外和合的产物,进入知识关系的“外物”不可能再是本来意义上的外物,进入知识关系的世界不可能再是“纯粹自然”的世界。
其实张东荪并不同意布拉德雷“一切关系都是内在关系”的说法,他觉得这一说法有点过于武断。他认为“外在关系”还是存在的,如弓和箭的关系、书与桌的关系等等。他只是反对用“外在关系”去解释知识关系。你可以说这种关系是外在的,那种关系是外在的,但你决不可以说“我知道这个东西”是一种在外的关系。用“外在关系”解释别的关系,张东荪可以接受;但若用“外在关系”来解释知识关系,张东荪决不让步,“有一点则我持之甚坚,就是唯有在知识的关系上决不能用关系在外说来解释”。〔1〕
金岳霖相反,他不仅否定知识关系是内在关系,而且根本否定“内在关系”的存在。金岳霖完全地、毫无保留地接受了罗素“一切关系都是外在关系”的主张,可以说是一种极端的“在外论”。张东荪还很谦虚地向“外在关系”作了很大程度的让步,金岳霖对“内在关系”却可谓寸步不让、毫不留情。他不仅主张知识关系是外在关系,而且坚持认为一切关系都是外在关系。
“外在关系说”主张关系不改变关系者的性质和面貌,进入关系的关系者与未进入关系前保持同一。金岳霖认为知识关系正是这样的“外在关系”,知识的对象在知识中与不在知识中,是一样的,“这本书”虽有被知与未被知的关系不同,但没有性质上的分别。进入知识的“外物”就是本来的外物,我所知道的“外物”的样子,就是外物本身本来的样子。唯其如此,我们才能认识“外物”。
金岳霖似乎没有证明知识关系为什么只能是“外在关系”,而不能是“内在关系”。关于前一方面,他仅仅停留在:“官能活动不必有外在关系”、“但是有外在关系”、“假如它是外在的”等等一类模棱两可的说法上。关于后一方面,他认为“如果我们坚持内在关系论,我们所知道的决不是事物底本来面目。……如此说来,如果我们坚持内在关系论,知识根本就不可能”。〔2〕
这话未免太绝对了。只能说对于金岳霖本人不可能,对于别人也许是可能的。张东荪曾嘲笑新实在论的关系在外说“非常浅薄”、“不合理”,是“速断”、“误会”、“实不能成立”,看来“内在关系”对张东荪的知识论而言,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需的。上面金岳霖所说的话,在张东荪这儿也许应改为“如果我们不坚持内在关系论,知识根本就不可能”。
⑵张东荪坚持“间接呈现说”,金岳霖则坚持“直接呈现说”或“直知对象论”。
“直知对象论”(theory of immediate object )是英哲摩尔(G.E.Moore,1873—1958)提出来的, 其基本含义是认为对象可以在能知中“直接呈现”,而无需“中间媒介”。换言之,此主张认为,能知可以直接和所知打交道,达到一个客观内容,同时却又不损害对象的客观性。此一见解与摩尔“捍卫常识”的立场有密切的关联。
“间接呈现说”一词并不是张东荪本人提出来的,而是本文作者研究概括后加给张东荪的。张东荪反对上述摩尔的“直接呈现”理论,针锋相对地提出了自己的认知主张,给其理论冠以“间接呈现说”一名称,是恰当的。张东荪的此一主张有几层基本的意思:(a)能知不是白板、明镜或静水,而是具有各种复杂之结构的,同样所知亦不能独立;(b)在能知与所知、内我与“外物”间,隔着感相、知觉、概念、 设准等中介,由于这些中介相互间无法还元、无法同一,能无法直达所,内亦无法直达外;(c)“外物”或所知的“本来面目”只是一种设定,承认此设定,就需承认它达于能知时肯定已被“扭曲”,不承认此设定,便可直认透入能知之内的世界就是“本来”的世界。简言之,对张东荪而言,所知是有呈现,但绝不是“直接呈现”,而只能是“间接呈现”。〔3〕
本文之所以认定张东荪之“间接呈现说”是他对中国哲学的大贡献,是因为中国哲学知识论领域,一直是直观说和直知对象说的天下,从来没有人打破这一格局。张东荪可说是打破这一格局的第一人,他几乎是反叛了中国哲学知识论之全部传统。这需要有很大的勇气。
中国哲学之直观说和直知对象说,走的都是“直接呈现”的路子,都是一种直接认识。前者直认本体,后者直认对象;前者是能所合一,后者是能所的性质相似或关系一致。总之都无需“中间媒介”。
金岳霖接受了摩尔的主张,同时却也暗中接续了中国哲学的传统。他认为认识就是引用所得意念于所与而得到的符合感,我们可以分析这一认识的历程,以明其构成成份是怎样的。但这是认识论的工作,而不是认识的工作,“认识是顿现的,不是推论的,甲认识X, 他一下子就认识,他不是根据种种理由,而得到一结论,说X是某某, 然后才认识它。这一点非常之重要”。〔4〕
认识是顿现的而不是渐成的,是直接的而不是推论的,表明能所、内外之间并没有“中间媒介”,所知的本性是直接呈现的。金岳霖说:“在认识经验中,没有问题的时候,官觉者直接认识个体。”〔5〕如张某认识X,他是直接地认识X的,而不是推论出X的;X直接呈现在张某的印象中,张某无需思考使X意念接受了这一呈现。如果不出现问题, 这一认识便算成立了。如果出现了问题呢?出现了问题,张某必然要引进“推论”,一般来说,认识便变成为间接认识。但金岳霖认为这种说法是不对的,张某引进“推论”,依然不妨碍认识之为直接认识,无论在怎样的条件下,张某的认识都是直接的。
所知的性质和关系,在达于能知时并没有改变其原貌,不管问题发生与否,能知心目中的性质与关系与所知本有的性质与关系,总是一一对应的,总是符合的。认知者虽然引进了“推论”,但却并没有引进别的条件和中介,所以此种“推论”其实并不间接。能知心中的性质和所知之性质相似、能知心中的关系与所知之关系一致,依然是直接的相似、直接的一致。所以对金岳霖而言,不管出现什么情况,认识总是顿现的直接的,官觉者总是直接认识个体,而“不是由官觉到性质相似与关系一致而推论到个体”。他其实没有必要加上“除非问题发生”、“在没有发生问题底时候”之类的状语。
⑶张东荪坚持“非写真说”,金岳霖则坚持“写真说”。
“非写真说”(non—opprehensional theory)是张东荪从批判实在论那里借来的一词,他认为这个词能很好地表达他自己的知识论观点。他提出“非写真说”显然是受到了批判实在论的影响,但他之此说,却远远超出了批判实在论。批判实在论只谈到知觉(perception)的“非写真性”问题,张东荪则证明了全部知识的“非写真性”。
张东荪的“非写真说”认为,(a)感觉与其背后的刺激在性质上大不相同,感觉上所现的都不是真有其物,所以感觉决不是“所与”,感觉不是解释的材料,而就是解释本身;(b)知觉亦不是简单地“摹写”感觉,知觉在把感觉配入全境中时,把意义(meaning)亦插入了进去,所以知觉也是对感觉的解释;(c)概念亦不是对知觉的摹写, 它由知觉而来,却又明显地超出了知觉,添加了知觉中没有的内容;(d)外在者或“外物”是什么,完全取决于物理学或形而上学的解释, 它根本上只是一个解释的结果,而并非实有其物。
感觉、知觉、概念、外在者与设准,乃是张东荪所认定的知识的五元,这五元的关系是这样的:设准不是概念的写真,它是工具,是为解释而设的;感觉、知觉、概念与外在者各各独立、不可归并、不可还元;感觉不是外在者的写真、知觉不是感觉的写真、概念不是知觉的写真,简言之,知识不是世界的写真。——这些便是张东荪“非写真说”的根本所在。〔6〕
张东荪给中国哲学补进一个“非写真说”,真乃是一桩了不起的事情。他从哲学的高度、从知识论的层面,对中国哲学中曾有的“言不尽意”思想,作了合理的说明,并从一方面指出了释道两家立“无言”之教的理论根据。
与张东荪相反,金岳霖是主张“写真说”的。“正觉”是外物的写真,知识是世界的写真;知识之成为知识,正在其“临摹”了或者“拓写”了我们周围的世界。正觉的呈现是“客观的呈现”,客观的呈现是“所与”,所与是“外物或外物底一部分”。金岳霖说:“所与有两方面的位置,它是内容,同时也是对象;就内容来说,它是呈现,就对象说,它是具有对象性的外物或外物底一部分。内容和对象在正觉底所与上合一……”〔7〕在这里, 金岳霖终于把“直接呈现说”与“写真说”结合起来,实现了此两种主张的“合一”。
总而言之,张东荪以“内在关系说”、“间接呈现说”和“非写真说”这样三个根本观念为主干,在金岳霖的知识论之外,构筑起另一个知识论系统。尽管这个系统还免不了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但这个系统确实是存在的。金岳霖的知识论系统不是唯一的,更不是唯一好的。有了张东荪的工作,20世纪前半期的中国哲学才有了另一种风采,于中国哲学的发展言,张东荪是功不可没的。
(本文是作者博士论文的一部分。感谢导师汤一介先生的指导)
收稿日期:1995—10—18
注释:
〔1〕张东荪:《认识论》,上海世界书局1934年版,第80页。
〔2〕〔4〕〔5〕〔7〕金岳霖:《知识论》,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150、269、276、130页。
〔3〕参见张东荪:《认识论》之“帘幕”喻。
〔6〕参见张东荪:《新哲学论》,上海商务印书馆1929年版, 第261页;《知识与文化》,上海商务印书馆1946年版,第11页; 《思想与社会》,上海商务印书馆1946年版,第4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