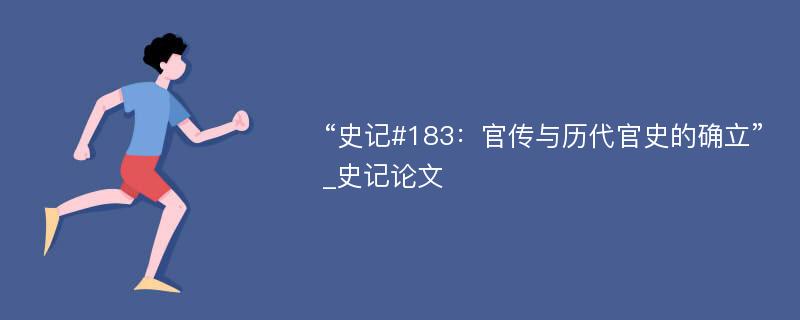
《史记#183;循吏列传》与历代正史《循(良)吏传》的设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记论文,正史论文,列传论文,历代论文,吏传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0139(2013)08-0117-11
西汉史学家司马迁撰《史记·循吏列传》,以合传的形式为春秋时期的五位“循吏”立传。何谓“循吏”?司马迁如何记载“循吏”事迹和表述他们的为政特点?由此体现了司马迁怎样的吏治思想?后代正史沿用《史记》体例而设置《循吏传》(或变言为“良吏”、“良政”、“能吏”),历代史家的吏治思想与司马迁又有何关系?凡此,还未见有学者做过专门的深入讨论,今不避翦陋,草成此文,以向学术界同行请教。
一、《史记》“循吏”含义、事迹及其为政特点
司马迁对“循吏”一词的含义、对“循吏”事迹和他们的为政特点,有具体的记载和表述。
《史记·太史公自序》有云:
奉法循理之吏,不伐功矜能,百姓无称,亦无过行。作《循吏列传》第五十九。[1]
又,《史记·循吏列传》开篇即有“太史公曰”:
法令所以导民也,刑罚所以禁奸也。文武不备,良民惧然身修者,官未曾乱也。奉职循理,亦可以为治,何必威严哉?[2]
日本学者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引赵恒曰:“法令为文,刑罚为武。‘奉职循理’四字,乃太史公‘循吏’之本旨。”[3]按此言甚确。又,《循吏列传》中记述“循吏”公仪休的事迹,亦言其“奉法循理”云云(详后)[4]。司马迁的提法,无论是说“奉法循理”,还是说“奉职循理”,意思应该是一致的,乃言“循吏”为政,能遵循法理、恪奉本职。又,唐代学者司马贞《史记索隐》解“循吏”之义曰:“谓本法循理之吏也。”[5]传末《索隐述赞》又云:“奉职循理,为政之先。恤人体国,良史述焉。”[6]所言“本法循理”,与“奉法循理”、“奉职循理”,意思相同。当然,还需联系司马迁所说的“官未曾乱”和“亦可以为治,何必威严哉”等语来理解“奉职循理”的含义。“官未曾乱”是说吏治未遭败坏;“威严”乃严厉而使人惮畏之义,如《管子·八观》所言“禁罚威严,则简慢之人整齐”云云[7]。司马迁主张以宽厚仁德为政,反对以“威严”治民,故言“亦可以为治,何必威严哉”?由此而知其言“奉法(职)循理”决非泛泛而言,而是有所指的。这涉及他对先秦以来吏治的总结,尤其是对汉武帝时期吏治败坏、苛酷为恶的批评,本文后面有详论。
《史记·循吏列传》记载了春秋时期五位“循吏”,他们是孙叔敖、子产、公仪休、石奢、李离。司马迁对相关史料做了选择取舍,对各位“循吏”为政的特点也做了具体的表述。
其一,孙叔敖。
《循吏列传》云:
孙叔敖者,楚之处士也。虞丘相进之于楚庄王以自代也。三月为楚相,施教导民,上下和合,世俗盛美,政缓禁止,吏无奸邪,盗贼不起。秋冬则劝民山采,春夏以水,各得其所便,民皆乐其生。[8]
按:此述孙叔敖事迹,自“施教导民”至“盗贼不起”数语至关重要,因为这正是“循吏”为政的显著特点。“秋冬”以下云云,是一个劝民利民的具体事例,说秋冬时节劝导百姓进山采伐木竹,春夏时节则“乘多水时而出材竹”(裴骃《史记集解》引徐广注语)[9],所以言“各得其所便,民皆乐其生”。
孙叔敖还有两个便民、导民的故事,颇为典型。一是楚庄王以为现行流通的货币轻了,想改为大的,这让百姓觉得不方便,“皆去其业”。孙叔敖顺乎民意,说服了楚庄王。二是楚人风俗车乘较为低矮,不便于驾马。楚庄王想下令改为高的。孙叔敖叫庄王不要下令,而是让有身份的“君子”乘坐这种高车,以作示范,结果半年以内,百姓也都自觉地将车乘改为高的了。司马迁评说曰:“此不教而民从其化,近者视而效之,远者四面望而法之。故三得相而不喜,知其材自得之也;三去相而不侮,知非己之罪也。”[10]
其实,孙叔敖本是楚庄王时杰出的政治家。如据《左传·宣王十二年》记载,晋楚邲之战,他始谏楚王毋轻率进兵,后又辅佐其指挥楚军大败晋兵[11]。汉初学者韩婴所撰《韩诗外传》亦载其有谏诤楚王之事[12]。又,《荀子·尧曰》记缯丘之封人说孙叔敖,言不得罪楚之士民之事[13],《韩诗外传》亦载此事(文互有详略殊异)[14],还见于《淮南子·道应》[15]和《说苑·敬慎》[16]。《后汉书·循吏列传·王景传》又记其率民“起芍陂稻田”之事[17]。凡此,《史记》皆不见载录。由此而知,司马迁只在《循吏列传》中记载其施教政缓、便民导民的事迹,以突现其“循吏”特点,对有关史料是有所选择取舍的。
其二,子产。《循吏列传》云:
子产者,郑之列大夫也。郑昭君之时,以所爱徐挚为相,国乱,上下不亲,父子不和。大宫子期言之君,以子产为相。为相一年,竖子不戏狎,斑白不提絜,僮子不犁畔。二年,市不豫贾。三年,门不夜关,道不拾遗。四年,田器不归。五年,士无尺籍,丧期不令而治。治郑二十六年而死,丁壮号哭,老人儿啼,曰:“子产去我死乎!民将安归?”[18]
此述子产事迹非常简略,突出的是他作为“循吏”的政绩和去世后百姓的哀悼之意,却并未具体记载其为政事迹。按,《左传·襄公三十年》记载子产为郑相,“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恤,庐井有伍”云云[19];又《左传·襄公三十一年》记其内政、外交均有佳绩,并善择贤才、不毁乡校等等,以及孔子所言“人谓子产不仁,吾不信也”[20];又《左传·昭公六年》记“郑人铸刑书”,杜预注“铸刑书于鼎,以为国之常法”[21];又《左传·昭公二十年》记子产谓子大叔言为政“唯有德者能以宽服民,其次莫如猛”云云[22]。至于《史记·郑世家》记子产事迹,亦突出其仁德言行,如其谓韩宣子曰:“为政必以德,毋忘所以立。”[23]又,定公六年,郑国失火,“公欲禳之。子产曰:‘不如修德。’”[24]就百姓而言,对子产之为政也有一个认识和态度转变的过程。据《左传·襄公三十年》记载:“从政一年,舆人诵之曰:‘取我衣冠而褚之,取我田畴而伍之。孰杀子产,吾其与之!’及三年,又诵之曰:‘我有子弟,子产诲之。我有田畴,子产殖之。子产而死,谁其嗣之!’”[25]《史记·郑世家》又记载子产卒,“郑人皆哭泣,悲之如亡亲戚”[26]。《韩诗外传》也记子贡对人言子产之治郑,“一年而负罚之过省,二年而刑杀之罪亡,三年而库无拘人。故民归之如水就下,爱之如孝子敬父母。子产病将死,国人皆吁嗟曰:‘谁可使代子产死者乎?’及其不免死也,士大夫哭之于朝,商贾哭之于市,农夫哭之于野。哭子产者,皆如丧父母。”①凡此,皆可与《循吏列传》所载子产事迹互参。
其三,公仪休。《循吏列传》云:
公仪休者,鲁博士也。以高弟为鲁相。奉法循理,无所变更,百官自正。使食禄者不得与下民争利,受大者不得取小。客有遗相鱼者,相不受。客曰:“闻君嗜鱼,遗君鱼,何故不受也?”相曰:“以嗜鱼,故不受也。今为相,能自给鱼;今受鱼而免,谁复给我鱼者?吾故不受也。”食茹而美,拔其园葵而弃之。见其家织布好,而疾出其家妇,燔其机,云:“欲令农士工女安所雠其货乎?”[27]
可以看出,公仪休做到了“奉法循理”:一是不收受礼物,其拒绝馈遗的理由亦合乎情理;二是拔葵出妇之事却做得有点绝,而且似乎不合情理然却是“不得与下民争利”。无论合否,在司马迁看来,皆“奉法循理”之所为也。
就史料来源而言,检《韩非子·外储说右下》始记公仪休拒收遗鱼之事,文字则稍异,而且讲了“受鱼,必有下人之色;有下人之色,将枉于法;枉于法,则免于相”的一番话[28]。这是典型的“法术”言论。而《韩诗外传》记此事(文字亦稍异),则用以证明《老子》“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无私乎,故能成其私”(按今本第七章文)和《诗经》“思无邪”(按今本《鲁颂·駉》文)之意[29]。《淮南子·道应》记此事,也是用以证明《老子》语[30]。可见司马迁记此事,用意已有不同,是着眼于“奉法循理”。又,《新序·节士》记此事,作“郑相”某某(未具名)所为[31],可参。
其四,石奢。《循吏列传》云:
石奢者,楚昭王相也。坚直廉正,无所阿避。行县,道有杀人者,相追之,乃其父也。纵其父而还自系焉。使人言之王曰:“杀人者,臣之父也。夫以父立政,不孝也;废法纵罪,非忠也。臣罪当死。”王曰:“追而不及,不当伏罪,子其治事矣。”石奢曰:“不私其父,非孝子也;不奉主法,非忠臣也。王赦其罪,上惠也;伏诛而死,臣职也。”遂不受命,自刎而死。[32]
石奢“坚直廉正,无所阿避”,事例很典型,可谓忠孝两全。此事最早见于《吕氏春秋·高义》,略有异文,人名作“石渚”(“渚”、“奢”字异而古音同,当为传写异文),言其为人“公直无私”,“为人臣也可谓忠且孝矣”[33]。《韩诗外传》略同,说他“公正而好直”,且记“君子曰”称其“贞夫法哉”,又用以证孔子“子为父隐,父为子隐,直在其中矣”(今本《论语·子路》)和《诗经》“彼己之子,邦之司直”(今本《郑风·羔裘》)之意[34]。《新序·节士》则说他“公正而好义”[35],余则几全同于《韩诗外传》。
其五,李离。《循吏列传》云:
李离者,晋文公之理也。过听杀人,自拘当死。文公曰:“官有贵贱,罚有轻重。下吏有过,非子之罪也。”李离曰:“臣居官为长,不与吏让位;受禄为多,不与下分利。今过听杀人,傅其罪下吏,非所闻也。”辞不受令。文公曰:“子则自以为有罪,寡人亦有罪邪?”李离曰:“理有法,失刑则刑,失死则死。公以臣能听微决疑,故使为理。今过听杀人,罪当死。”遂不受令,伏剑而死。[36]
此记李离之事称许其法不阿私,甚至以身伏法。最早见于《韩诗外传》,而文字加详,还引“君子”言称许其“忠矣仁矣”[37],又知司马迁录此事有所删节,用意也不在忠与仁,而在“理有法”。“理有法”,也就是“奉法循理”之义。又,《新序·节士》所载此事又比《韩诗外传》为详,只是没有“君子”的评语[38]。
综上,概括司马迁所记各位“循吏”的事迹及其为政特点,实际上表现在施教政缓、导民便民,为政仁德、民之所望,遵奉法理、不与民争利,忠孝仁义、坚直廉正,法不阿私、甚至以身伏法等诸多方面,此即“奉法(职)循理”的具体内涵。
但是,古代有学者提出了一个问题。据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引陈仁锡曰:“汉之循吏,若吴公、文翁,不为作传,亦一缺事。奢、离二人得事,未见为循吏。”②意思是说,司马迁之作《循吏列传》,本该列入汉初的“循吏”吴公、文翁,而石奢、李离二位,依其事迹则不当视为“循吏”。今谓:对这一问题的理解,需结合司马迁的吏治思想来讨论。
二、“循吏”与司马迁的吏治思想
司马迁之称许“循吏”,为他们立传,是基于其为政应当宽厚仁德、反对威严苛酷的吏治思想。而这一思想的形成,既以孔子、老子等儒、道先贤的吏治思想为依据,又是其对先秦以来吏治的经验教训的总结,尤其是对汉武帝时期“酷吏”横行、吏治败坏的批评,还有他本人遭祸受刑不幸遭遇的影响。所以,其为“循吏”立传,现实针对性很强,既是为了以史为鉴,也是结合自身遭遇的有感而发。前面引司马迁“奉职循理,亦可以为治,何必威严哉”之语,正是无限感慨之言,主要针对的正是汉武帝时期的苛酷吏治。其记述春秋时期各位“循吏”的事迹,亦重在他们的宽厚仁德和遵奉法理(参前引述)。
他的这一思想,在《酷吏列传》中有更为明确地表述,《酷吏列传》开篇有云:
孔子曰:“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老氏称:“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法令滋章,盗贼多有。”太史公曰:信哉是言也!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浊之源也。昔天下之网尝密矣,然奸伪萌起,其极也,上下相遁,至于不振。当是之时,吏治若救火扬沸,非武健严酷,恶能胜其任而愉快乎!言道德者,溺其职矣。故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下士闻道大笑之”。非虚言也。汉兴,破觚而为圜,斫雕而为朴,网漏于吞舟之鱼,而吏治烝烝,不至于奸,黎民艾安。由是观之,在彼不在此。[39]
以上所言,全面地体现了司马迁的吏治思想,可做如下三方面分析。
其一,开篇所引孔子和老子语录,是其吏治思想的理论依据。司马迁所引孔子语录,见于《论语·为政》[40];所引老子语录,分别见于《老子》三十八章和五十七章[41]。孔子的意思是说,用法制教令引导百姓,用刑罚律令规整百姓,他们只能暂时地免于罪过,却没有廉耻之心;用道德来引导百姓,用礼教来整顿百姓,他们就不但有了廉耻之心,而且人心归服。《论语·为政》记载孔子主张“为政以德”[42],《里仁》又记载孔子言“以礼让为国”[43],故有如此说。又,《礼记·缁衣》录孔子言又云:“夫民,教之以德,齐之以礼,则民有格心;教之以政,齐之以刑,则民有遁心。”[44]仍是强调要用道德礼教教化百姓,使人心归服而不是离心离德,此可与上录《为政》言互参。至于《老子》语录,三十八章四句,盖言得“道”的人并不在乎“德”(王弼注“德者,得也”[45]),因此有德;而未得“道”的人不失“德”,因此而无德。这几句话语义深奥,今不细绎可也。重点是五十七章“法令滋章,盗贼多有”之语,言法令规章制定得越多越详明,盗贼反而越多。通读《老子》五十七章全文,其治世思想愈明,曰:“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吾何以知其然哉?以此。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民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盗贼多有。故圣人云: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46]参王弼注可知,老子强调的是要“以道治国”,而“圣人”云云四者则能“崇本以息末也”[47]。先秦儒、道思想代表人物孔子、老子的这些主张,为司马迁所膺服和推崇,故曰“信哉是言也”。
其二,法令的得失尤其是秦政之失。司马迁言“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浊之源也”,亦为《汉书·酷吏传》所引用(参后),颜师古注云:“言为治之体,亦须法令,而法令非治之本。”[48]这一解释甚为准确。所以其言“昔天下之网尝密矣”至“非虚言也”一段,指出秦时法令严密(参司马贞和颜师古注[49]),但奸伪萌生,以至于丧败,不可拯救。而吏治虽“武健严酷”,但是就好像救火扬沸一样,乃治标不治本,用司马贞《索隐》之言就是“本弊不除,则其末难止”①。所以治本应当言道德,但是那个时候没人这样做,故曰“言道德者,溺其职矣”。司马迁又引孔子言“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今见于《论语·颜渊》[50],意思是说审理诉讼,我和别人差不多,一定要使诉讼之事消灭才好。何晏集解引王肃注云“化之在前”[51],说先要对百姓进行教化;而朱熹《四书集注》引范氏曰“听讼者治其末、塞其流也,正其本、清其源,则无讼矣”[52],这一解释从本末源流的角度立论,说到根本上了,完全符合司马迁引述孔子语录之宗旨(前引司马迁有言曰“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浊之源也”,就是这个意思)。至于“下士闻道大笑之”一语,今见于《老子》四十一章,文略云:“上士闻道,勤而行之;中士闻道,若存若亡;下士闻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为道,故建言有之。……”[53]寻其大意,就是颜师古所言“大道玄深,非所能及,故致笑也”[54],司马迁显然是借老子之语讽刺当时的在位者根本不懂“道德”之本意。他两引孔子、老子语录,反复其辞,前后呼应,用以阐明己之吏治思想,有深意存焉。
其三,对汉初吏治的肯定。司马迁所言“汉兴”以下数语,是对汉初吏治的肯定,言:汉初吏治,反秦之政,除其严法峻刑,律法政令甚为疏阔,就好像渔网的网眼很大,足以漏掉吞舟的大鱼,但是吏治状况甚好,无有奸伪,百姓治安。结论是:“在彼不在此”。裴骃《史记集解》引韦昭曰:“在道德,不在严酷。”[55]言之甚确。
总之,由以上讨论可知,司马迁以孔子、老子的“为政以德”、“以道治国”思想为本,对历代吏治做了深刻的论述和总结,并明确地表达了为政应该宽厚仁爱、法制宽缓,注重以德教民的吏治思想。
至于“酷吏”,他们的所作所为则与“循吏”判若水火。而对“酷吏”和苛酷吏治的批判和谴责,是司马迁吏治思想的另一重要方面。
《酷吏列传》列举了郅都至杜周十人,言汉高后时开始出现,且愈见酷烈;武帝时的“酷吏”,至于暴虐。诚如梁代史学家姚思廉《梁书·良吏传》录其父姚察所言:“汉武役繁奸起,循平不能,故有苛酷诛戮以胜之,亦多怨滥矣。”[56](又参后所引述)清代学者王鸣盛《十七史商榷》亦言:“酷吏多而吏治坏,在武帝世也。”[57]
司马迁言,郅都至杜周十人,“其廉者足以为仪表,其污者足以为戒”[58]。这一见解很深刻,因为“酷吏”的出现及其所作所为,是人主之所好,人主以为能,是严刑峻法的制度安排使然。“酷吏”中有尽职尽责的,甚至也有廉洁不贪的。如:张汤死后,“家产直不过五百金,皆所得奉赐,无他业”[59];尹齐病死,“家直不满五十金”[60]。但他们为政苛酷,仍为司马迁所谴责。至若王温舒、杜周等人,逢君之恶而“以恶为治”[61],滥用刑狱,以致构陷,并为巨贪,非惟“酷吏”恶吏,也是贪官污吏。此外,司马迁还列举了冯当、李贞、弥仆、骆璧、褚广、无忌、殷周、阎奉等人,他们或暴挫妄杀,或分尸锯项,或椎击成狱,毒若蛇蝎,无恶不作,以至司马迁无限悲叹而曰:“何足数哉!何足数哉!”[62]清代学者赵翼《廿二史札记》亦有《武帝时刑罚之滥》一条,引杜周之事为例,而感叹曰:“是可见当时刑狱之滥也。民之生于是时,何不幸哉!”[63]
考察司马迁对“酷吏”和苛酷吏治的谴责和批判,还需联系到他本人遭祸受刑的悲惨遭遇。生活在吏治败坏、滥用刑狱的武帝之世,他也是大大的不幸。
据《史记·太史公自序》,汉武帝天汉三年,“太史公遭李陵之祸,幽于缧绁”[64]。《汉书·司马迁传》记载其报故人仁安书,述说己遭祸入狱、无由求援、受刑蒙辱(最终受腐刑)之事,其言也哀。文略云:“因为诬上,卒从吏议。家贫,财赂不足以自赎,交游莫救,左右亲近不为一言。身非木石,独与法吏为伍,深幽囹圄之中,谁可告诉者!……今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肤,受榜箠,幽于圜墙之中,当此之时,见狱吏则头枪地,视徒隶则心惕息。……”[65]《文选·报任少卿书》同④。此言“卒从吏议”的“吏”,以及“法吏”、“狱吏”,定是“酷吏”、恶吏、污吏。他们构陷重判的暴虐,苛烈残民的酷刑,也用在了司马迁的身上。
这样悲惨的不幸遭遇,也必然激发了作为史家的司马迁从历史与现实相结合的角度思索历代吏治。他肯定和推崇春秋时期的“循吏”为政以德、以礼教民、法制宽缓、体恤民情等等,批判和谴责汉代尤其是武帝时期的“酷吏”“以恶为治”,对民对吏(包括对士大夫)苛酷暴虐、构陷“黑打”、重刑严判,这既是对儒、道“为政以德”、“以道治国”吏治思想的继承,又是对先秦以来吏治实践的反思,包括了对汉初以来吏治实践的经验教训的总结,尤其是对武帝之世吏治败坏的批判,以及他自己遭陷受害的惨痛经历。所以,他对春秋时期五位“循吏”事迹及其为政特点的记述,对汉世尤其是武帝时期作恶多端的“酷吏”的揭露,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是他为了以史为鉴,并结合自身不幸遭遇的有感而发。因此,司马迁的所作所为,也就决非单凭个人之好恶、发泄一己之私怨,而是秉承“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精神⑤,彰显的是史家良知和历史正义。
现在可以解释前面所引陈仁锡提出的问题了。
将西汉初期的吴公、文翁列为“循吏”,是班固之所为,见《汉书·循吏传》,本文后面将有引述。二人的事迹,司马迁不会不知道。但他所记述的“循吏”,却只是春秋时期的五位,是何故也?今按: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引陈子龙曰:“太史公传循吏,无汉以下者;传酷吏,无周以前者,寄慨深矣。”[66]又,清代学者方苞《史记评语》亦言“《循吏》独举五人,伤汉事也”,“史公盖欲传酷吏而先列古循吏以为标准”[67]。他们都结合《史记》中《循吏》、《酷吏》二传来探索司马迁著史立传之用心,给人很大启发,可惜话未说透。我的理解是,司马迁为“循吏”(包括“酷吏”)立传及其寄托感慨,是基于对春秋以来历代吏治的经验教训的深刻反思,是表达对汉高后以后特别是对武帝时期“酷吏”“以恶为治”的深恶痛绝,也是对自身不幸遭遇的凄然长叹。如前所论,他对汉初吏治本来是肯定的,却不愿在《循吏列传》中为汉初“循吏”立传,可见其痛切之深、愤激之至,庶几可谓“洪洞县(衙)里无好人”了。另一方面,汉世尤其是武帝时期的那些“酷吏”、恶吏、污吏,从根本上违背了“奉法(职)循理”的为官之道,以恶法残民害民,又何曾受到良法的规范、制约或惩处呢?他们往往不得好死,也只是因为失宠于君,或贪恶太甚,大抵属于“恶有恶报”,并不是良法对他们进行了清算和公正的判决。所以,司马迁将石奢、李离与孙叔敖、子产、公仪休一起列为“循吏”,称许他们能“奉法(职)循理”,依法行事,“坚直廉正,无所阿避”,甚至甘愿以身伏法,从而无论在道义上还是行为上,都与“酷吏”形成了高尚与卑劣的鲜明对照。司马迁的用心,不可谓不深矣。
我们这样解读《史记·循吏列传》,洵足体会和认识到,司马迁所肯定和推崇的“循吏”,正是体现其吏治思想或曰吏治理想的典范。
三、历代正史《循(良)吏传》的设置
司马迁撰《史记》而设置《循吏列传》,意义重大,影响深远,历代正史,多效其体。除《三国志》、《周书》、《旧五代史》、《新五代史》而外,自《汉书》而至《清史稿》,或直接沿用《史记》体例而作《循吏传》,或变言而曰“良吏”、“良政”、“能吏”。司马迁的吏治思想,也深刻地影响了历代史家。而各代史家所述所论,对我们理解“循吏”、“良吏”、“良政”、“能吏”的含义,了解他们如何继承、发挥司马迁的吏治思想,甚有助益。故略作引述,以见其义。
东汉史学家班固撰《汉书》,继承了《史记》体例,亦立《循吏传》。《循吏传》开篇有云:
汉兴之初,反秦之敝,与民休息,凡事简易,禁罔疏阔,而相国萧、曹以宽厚清静为天下帅,民作“画一”之歌。……至于文、景,遂移风易俗。是时循吏如河南守吴公、蜀守文翁之属,皆谨身帅先,居以廉平,不至于严,而民从化。[68]
上引一段,大意甚明。尤其是“凡事简易,禁罔疏阔”,“宽厚清静”以及言“循吏”吴公、文翁“谨身帅先,居以廉平,不至于严,而民从化”诸语,实际上还解释了何谓“循吏”。而“不至于严,而民从化”一语,又可以说是对前引司马迁所说“何必威严哉”,以及称许孙叔敖“不教而民从其化”等语的照应。又,唐代学者颜师古为《汉书》作注,而曰:“循,顺也。上顺公法,下顺人情也。”[69]此言“循吏”所为,上顺国家法理,下顺民情民意⑥,这为“循吏”的含义提供了一个较新的解释,可参。
又,班固效司马迁,亦作《酷吏传》,并于开篇全录《史记·酷吏列传》“孔子曰”至“在彼不在此”一段(小有异文)[70],可见他对司马迁吏治思想(包括对“酷吏”的批评)的认同和接受。
尚需注意的是,班固又以“良吏”言“循吏”,这对后代一些正史中《良吏传》的设置,产生了很大影响。
《汉书·循吏传》曰:
及至孝宣……常称曰:“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亡叹息愁恨之心者,政平讼理也。与我共此者,其唯良二千石乎!”以为太守,吏民之本也,数变易则下不安,民知其将久,不可欺罔,乃服从其教化。故二千石有治理效,辄以玺书勉厉,增秩赐金,或爵至关内侯,公卿缺则选诸所表以次用之。是故汉世良吏,于是为盛,称中兴焉。[71]
按:依班氏所录汉宣帝语观之,作为郡守和郡国相的“二千石”为政,“政平讼理”者可称之为“良”。“讼理”,据颜师古注,则“言所讼见理而无冤滞也”[72]。
《汉书·叙传》又云:
谁毁谁誉,誉其有试。泯泯群黎,化成良吏。淑人君子,时同功异。没世遗爱,民有馀思。述《循吏传》第五十九。[73]
按:颜师古对上引三、四句注云:“黎,众也。言群众无知,从吏之化而成俗也。”[74]即言百姓化成于良吏。而从上引几条资料看,班固两言“良吏”,显然是因为汉宣帝将能“政平讼理”、“有治理效”的郡守、郡国相等“二千石”称为“良”;但他并未以“良吏”之名作传,而仍作《循吏传》,则是直接继承了司马迁。又,从班固所言中对“循吏”、“良吏”的混用来看,“良吏”与“循吏”的含义,是没有什么区别的。
“循吏”之名,后来为《后汉书》、《北齐书》、《南史》、《北史》、《隋书》、《新唐书》、《宋史》、《金史》、《明史》、《清史稿》所沿用;“良吏”之名,后来为《晋书》、《宋书》、《梁书》、《魏书》、《旧唐书》、《元史》所用。《南齐书》又易名为“良政”,《辽史》复变言曰“能吏”。然寻其旨意,与“循吏”为政特点大致无差,但又有所引申发挥,而且明显地受到司马迁和班固立传设论的影响。
下面,对“循吏”以及“良吏”、“良政”、“能吏”再略作讨论,以进一步探讨历代史家的吏治思想及其与司马迁的关系。
刘宋史家范晔所撰《后汉书》,不但设置了《循吏列传》,还有《酷吏列传》。《循吏列传》卷末“赞曰”有云:
政畏张急,理善亨鲜。推忠以及,众瘼自蠲。一夫得情,千室鸣弦。怀我风爱,永载遗贤。[75]
按《韩诗外传》有云:“治国者譬若乎张琴然,大弦急则小弦绝矣。”[76]此正范氏言“政畏张急”之所本,言治国不应峭刑峻法(上引《韩诗外传》前有云“令苛见民乱”,“吴起峭刑而车裂,商鞅峻法而支解”等语[77]),而应宽缓为治。又,《老子》六十章有云:“治大国若烹小鲜。”[78]谓不扰民(王弼注“不扰也”)、不折腾。由此,则能推忠恕于万民,守长得化下之情,而黎民百姓则鸣弦而安乐(参李贤注[79])。范氏对“循吏”为政特征的表述,可知矣。又《后汉书·酷吏列传》“论曰”批评“严刑痛杀”、“以暴理奸”,“以为严辟既用,而苟免之行兴;仁信道孚,故感被之情著”。所以,应当以“德义”、“化导”治民,认为这才是“崇本”[80]。
唐初史家魏征等人奉旨所撰《隋书》,不但设置了《循吏传》,还有《酷吏传》。《循吏传》云:
古之善牧人者,养之以仁,使之以义,教之以礼,随其所便而处之,因其所欲而与之,从其所好而劝之。如父母之爱子,如兄之爱弟,闻其饥寒为之哀,见其劳苦为之悲,故人敬而悦之,爱而亲之。若子产之理郑国,子贱之居单父,贾琮之牧冀州,文翁之为蜀郡,皆可以恤其灾患,导以忠厚,因而利之,惠而不费。……[81]
按此言善治民者当以仁、义、礼为本,要爱民亲民,民亦“敬而悦之,爱而亲之”,揭示了“循吏”为政的基本特点。所举子产,司马迁将其列入“循吏”,其治理郑国,孔子称其“仁”,可参前所引述。又,孔子弟子子贱治单父之事,略见于《吕氏春秋·察贤》,谓其任人而治,而不是任力而治[82];《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亦载其事[83];又略参《说苑·政理》,言乃君子之治而众人欣悦,并受到孔子的称许[84]。贾琮之事,见于《后汉书》本传,言其赴任车不垂帷以“远视广听,纠察美恶”,“州界翕然”[85]。文翁治蜀,注重教化,则见于《汉书·循吏传》的记载[86]。无疑,他们都是“循吏”的典型代表。
《隋书·酷吏传》卷末“史臣曰”又云:
御之良者,不在于烦策,政之善者,无取于严刑。故虽宽猛相资,德刑互设,然不严而化,前哲所重。[87]
这番话讲得很精辟,是对历代吏治的最好总结。“政之善者,无取于严刑”一语,既是对“循吏”为政以德的肯定,也是对“酷吏”苛烦严刑的批评。又,“不严而化,前哲所重”一语,当是指前引班固所言“不至于严,而民从化”,而班固本是继承、发挥司马迁的吏治思想(参前所引述)。
从时间上看,正史中最早设置《良吏传》(也是最早未设置《酷吏传》)的,是梁代史学家沈约所撰《宋书》。传末“史臣曰”:
夫善政之于民,犹良工之于埴也,用功寡而成器多。汉世户口殷盛,刑务简阔,郡县治民,无所横扰,勤赏威刑,事多专断,尺一诏书,希经邦邑,龚、黄之化,易以有成。……今吏之良,抚前代之俗,则武城弦歌,将有未暇,淮阳卧治,如或可勉。……[88]
今按:“尺一诏书”指汉宣帝对“二千石”诏书勉励之事,见前引《汉书·循吏传》;又言“龚、黄之化”,也是用的《汉书·循吏传》所载汉宣帝任用著名“循吏”黄霸、龚遂的故事[89]。“武城弦歌”说的是子游作为武城县令,其为政奉行君子爱人之道,能以礼乐教民,见《论语·阳货》[90],亦见于《史记·仲尼弟子列传》的记载[91];“淮阳卧治”则用西汉武帝时淮阳太守汲黯无为而治、“淮阳政清”的故事,见《史记》、《汉书》汲黯本传的记载[92]。沈约称许“良吏”善政、政简无扰,用了子游、汲黯的故事为例,还特意标举汉宣帝时期的“龚、黄之化”,并有“今吏之良”云云,其为“良吏”立传,而不使用“循吏”之名的大旨可知。
又,唐代史学家姚思廉所撰《梁书》,亦设《良吏传》(亦未设置《酷吏传》),开篇即引汉宣帝“政平讼理,其惟良二千石乎”之语以立说[93],而卷末又录乃父姚察之论曰:
前史有循吏,何哉?世使然也。汉武役繁奸起,循平不能,故有苛酷诛戮以胜之,亦多怨滥矣。梁兴,破觚为圆,斫雕为朴,教民以孝悌,劝之以农桑,于是桀黠化为由余,轻薄变为忠厚。淳风已洽,民自知禁。尧舜之民,比屋可封,信矣。若夫酷吏,于梁无取焉。[94]
按:此言“前史”,自然说的是《史记》,故姚氏接言“汉武”云云;而汉武帝时“役繁奸起”,政令“苛酷”,恰为司马迁所深恶痛绝(前有论)。姚氏所言“梁兴,破觚为圆,斫雕为朴”云云,也是套用的司马迁《史记·酷吏列传》“汉兴,破觚而为圜,斫雕而为朴”之语(前有引),用以称许梁初宽厚仁德、教民劝民,“淳风已洽,民自知禁”之吏治。这说明,司马迁之定“循吏”之名、为“循吏”立传,对姚氏父子著史有直接的影响。姚氏又言“若夫酷吏,于梁无取焉”,似不是说梁代无“酷吏”,而是说《梁书》不传“酷吏”。这是将“酷吏”与“良吏”对举,称许“循吏”,不齿“酷吏”,这一点也值得注意(参前所论)。
梁代史学家萧子显撰《南齐书》,则作《良政传》。略云:“齐世善政著名表绩无几焉,位次迁升,非直止乎城邑,今取其清察有迹者……”[95]卷末“赞曰”又云:“蒸蒸小民,吏职长亲。棼乱须理,恤隐归仁。枉直交瞀,宽猛代陈。伊何导物,贵在清身。”[96]这是强调“善政”、“清察有迹”、亲民爱仁、洁身清正等等,这与司马迁和班固等史家所称许的“循吏”事迹没有什么区别(参前引述)。
元代史学家脱脱等撰《辽史》,有《能吏传》,开篇即云:
汉以玺书赐二千石,唐疏刺史、县令于屏。以示奖率,故二史有《循吏》、《良吏》之传。辽自太祖创业,太宗抚有燕、蓟,任贤使能之道亦略备矣。然惟朝廷参置国官,吏州县者多遵唐制。历世既久,选举愈严。时又分遣重臣巡行境内,察贤否而进退之。是以治民、理财、决狱、弭盗,各有其人。考其德政,虽未足以与诸循、良之列,抑亦可谓能吏矣。作《能吏传》。[97]
按:《循吏传》之设置,本始于司马迁;而两《唐书》则《旧唐书》作《良吏传》,《新唐书》仍作《循吏传》。元脱脱等人所言,似为疏略。其又言辽代这一批地方官员的“德政”“未足以与诸循、良之列”,所以只能称为“能吏”,这似乎有些贬低。但史传称“循吏”、“良吏”为“能吏”,此前已有唐初房玄龄等人所撰《晋书》,其《良吏传》开篇亦引汉宣帝之语以立言,又有“良能之绩”、“晋代良能”诸语[98]。可见《辽史》之传“能吏”,似不为无据。又,《宋史》、《金史》亦由脱脱主持修撰,而二书并作《循吏传》,看来还是继承的《史》、《汉》传统。
至于明、清二史,仍旧设置《循吏传》(二史皆未设置《酷吏传》)。《明史·循吏传》卷前对明代吏治有一综述,内有“廉者能约己而爱人”,太祖时“守令畏法,洁己爱民,以当上指,吏治焕然丕变矣”;“下逮仁、宣,抚循休息,民人安乐,吏治澄清”等语,还有“循良之选”的提法[99]。而曰“循良之选”,当是兼及“循吏”和“良吏”;但仍以“循吏”之名立传,可见是继续沿用《史》、《汉》的做法。又言“自守令超擢至公卿有勋德者,事皆别见。故采其终于庶僚、政绩可纪者,作《循吏传》”[100]。凡此,可以看出史臣们对“循吏”含义的理解和界定,以及他们的吏治思想。《清史稿·循吏传》卷前对清代吏治亦有一综述,内有康熙“平定三藩之后,与民休息,拔擢廉吏”,乾隆时“吏治修明”等语,并云沿用《明史》之例,只为“由令守起家者”立传,而“尤以亲民为重”[101]。凡此,也可以看出史家对“循吏”含义的理解以及他们的吏治思想。
综上所论,可做如下几点总结。
其一,“循吏”含义,质言之,就是司马迁所概括的“奉法(职)循理”;析言之,则是施教政缓、导民便民、遵奉法理、不与民争利、坚直廉正、法不阿私等等,并体现了主张为政宽厚仁德、反对威严苛酷的吏治思想。而历代史家将其表述为善政无扰、亲民导民、清正廉洁、办事公直且有政声等等,在基本内容和精神实质上与司马迁是一致的。
其二,“循吏”为政的要旨是仁德亲民、廉洁公直,“酷吏”则苛酷残民、以恶为治。这是中国古代鲜明对立的两种吏治,自先秦两汉而下,历代皆然。而自司马迁始,历代史家基于他们的历史良知,从为官行政的角度肯定前者、批评后者,态度是一贯的,他们的吏治思想也是一脉相承的。
其三,司马迁所记述的“循吏”,皆为春秋时期各国中央政府的官员,且官至卿相,而后代诸正史的《循吏传》、《良吏传》、《良政传》、《能吏传》所记载的,则主要是各代县级以上的地方官员,尤其是地方行政长官,即所谓的县令、郡守之属。虽然他们中间也有人后来或中途供职于中央政府,但其为政且有政绩则主要是在地方州县,即前引《明史》所谓的“终于庶僚、政绩可纪者”,或《清史稿》所谓的“由令守起家者”,所以史家述其为政,也就突出了他们在地方州县宽厚仁德、善政无扰、清正廉洁、办事公直等内容,而“尤以亲民为重”。可见,由于时代的演进和官制的变迁,历代史家对司马迁是有因有革的,他们对“循吏”含义的解说,也就当然有所侧重,有所引申和发挥,他们的吏治思想也就有了一些新的提法和新的时代特点。
其四,司马迁撰《史记》而设置《循吏列传》,意义重大,影响深远。历代因之,而又逐步定位于主要为中下级地方行政长官中的“循吏”立传。这些官员或因地位相对而言不高,事迹相对而言不显,未可单独立传,故以合传的形式(地位、事迹再次者甚至以附传的形式)集中载录和彰显他们为政以德、廉正亲民等政绩,让他们青史留名,并成为后世官吏们取效的典范。与此同时,历代史家又依凭他们的史德、史才、史识,从中总结历代吏治的经验与教训,阐发他们的吏治思想,为后人探讨古代吏治和官德文明,从而知古以鉴今,提供了丰富而宝贵的文献史料和思想资源。司马迁和历代史家的所作所为,功莫大焉。
注释:
①许维遹《韩诗外传集释》卷第三,中华书局1980年版,109页。按:《史记·循吏列传》记子产死事,司马贞《索隐》曰“《韩诗》称子产卒,郑人耕者辍耒,妇人捐其佩玦”(《史记》卷一百一十九,中华书局1959年版,3101页),当为《韩诗外传》佚文。
②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卷一百十九,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1937页。按:原文“得事”疑有误,当作“行事”,待查。
③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二十二,中华书局1959年版,3132页。按:《汉书·酷吏传》师古注云“本弊不除,则其末难正”。见《汉书》卷九十,中华书局1962年版,3646页。“止”、“正”二字孰是孰非,也可能都讲得通,待考。
④萧统《文选》卷第四十一,中华书局1977年版,578-579页。按:文字小异。
⑤参班固《汉书》卷六十一《司马迁传》“赞曰”所言,中华书局1962年版,2738页。
⑥按:师古曰“人情”,“人”盖本作“民”,为避唐太宗李世民之讳而改也。参陈垣先生《史讳举例》所论,中华书局2004年新1版,119-120页。
标签:史记论文; 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论文; 循吏论文; 中国历史论文; 汉朝论文; 历史论文; 司马迁论文; 老子论文; 孙叔敖论文; 读书论文; 孔子论文; 酷吏列传论文; 历史学家论文; 汉书论文; 后汉书论文; 离骚论文; 西汉论文; 二十四史论文; 唐朝论文; 周朝论文; 历史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