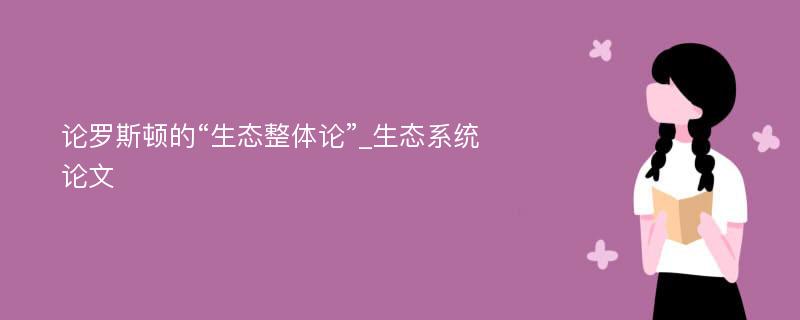
论罗尔斯顿的“生态整体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生态论文,罗尔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罗尔斯顿“生态整体论”主旨
罗尔斯顿(Holmes RolstonⅢ,1933-),美国科罗拉多州立大学哲学系终身荣誉教授,国际著名环境伦理学家。其治学道路从物理学转向神学而后定位于哲学,专攻环境伦理学。他的理论与“大地伦理”(Land Ethics)、深层生态论(Deep Ecology)一同被称为“生态整体主义”的环境伦理学。
罗尔斯顿认为:环境伦理学是“一种恰当地遵循大自然的伦理”[1],因为“自然最有智慧”[2],借助现代生态学,罗尔斯顿用一种整体的方法去解释自然和评价自然,并且重新审视了人在自然中的位置和作用。
首先,生态学揭示的“自然”是一个完美、稳定的生态共同体,一个进化发展的生态系统,一切价值之源。价值产生于自然界一切事物的相互联系、需要、利用、合作、竞争关系之中。内在价值(生命)、工具价值通过生态系统的连接机制整合于最高价值——生态系统的系统价值。这种最高价值的表现之一就是创造出人这种最高内在价值。生态系统的价值结构如下:
在机体个体层面:罗尔斯顿接受了康德主义(Kantianism),把每一个有生命的个体看成是内在价值。内在价值表现在个体的利用环境生存、发展、抵抗死亡、实现其形态的过程中,又只能这样而存在;自然中个体的死亡或牺牲只是转化成别的个体的工具价值。个体的生和死都融入系统的价值之流,这是生态系统运转和进化之途。
在物种层面:生命个体顺应环境而自我更新演变成新的物种,物种由携带同一基因的个体生命之流保持下来,作为一种同一性而具有价值。环境中的物种是一个具有选择性的复合体,通过自然选择、生存竞争淘汰不适应的个体,促进了物种质量的提高和进化。这是生态系统进步的表现。
在生态系统层面:个体和物种都只是更大的进化伟业(自然本身的进化)中的一个过程、产物和工具。[3]进化事实表明,生态系统通过竞争、协调、加于个体的自然选择来选择适应的性能、选择生命的质量和数量,促进物种的分化,淘汰不适应的物种,以完美的资源能量运转模式支持越来越多的物种,在系统底部的无机物、植物的工具价值(支撑生态系统)的基础上,产生越来越有主体性的物种直至人类。生态系统这种创造性的进化过程就是系统价值。个体和种的价值只有处在生态系统的网状结构中并参与进化才有意义。
生态金字塔就是在内在价值与工具价值的转换之中,限制与维持物种的平衡之中保证所有物种的欣欣向荣,促进生态系统保持动态的和谐与稳定,向着更有序、更高自然价值的方向进化。评判自然中的事物要放在这个大的、进化的整体中联系起来看。
其次,人生活的真实状态是:人、文化与自然密不可分又有一定距离。
一方面,人是进化的产物,是生态系统食物链的上层,人的生存发展、内在价值的实现必须依赖于支持系统的下层无机物、植物等层次,自然非为人类而创造。人受制于自然环境,无法脱离环境建造文化、求得发展,人类若在进化中失败,会有更高级的物种代替人类。
另一方面,人是不与动物完全等同的物种,在进化的过程中,人形成了思考、语言和推理能力,人带着认识和评判意识思考并存在于一个开放的整体世界中,人出类拔萃的形而上能力使人区别于动物而具有责任心去关怀其他事物;人依靠具有道德色彩的文化生活在自然中而不是仅仅适应自然;人拥有影响自然使之趋向稳态的能力。
最后,人的卓越能力不应成为人傲慢统治其他事物的理由:因为从生态学的角度出发,生态系统中没有两个毫无差别的生命,在功能的角度,人类同样不是世界的中心,所有事物不是同等的,不同的事物合成一个整体才发生作用,所以人们不可能单独为自己需要和利益而将其他事物置于控制之下(反过来影响人类自身);毁灭自然最终将毁灭人类;人们不可能脱离其环境而自由,而只能在其环境中获得自由,人类应当整体的考虑问题。而实现这一目标在于人性的提升,只有当人培养出“真正的利他主义精神”时,人的自我完善才能完成,才能使用人独特的能力,在地球上“既做为生态系统的一个‘公民’又做为其‘国王’……对生态系统进行治理。”[4]在地球上建造适应人生存,也适应环境的人类文化,从而达到人与自然的整合。
二、“生态整体论”与“大地伦理”的渊源
罗尔斯顿的理论体系从某种程度上可以看做是全面吸收了大地伦理的进一步的阐释和系统化的辩护。
由美国环境运动先驱利奥波德(Aldo leopold)创立的大地伦理,是生态整体主义的环境伦理学的最早形态,它的核心是:“一个事物,当它有助于保护生物共同体的和谐、稳定、美丽的时候,它就是正确的,反之必错”。[5]
利奥波德与罗尔斯顿有着并不相似的经历,前者是从事实践环境保护工作的专家型学者,后者却是从事理论研究的大学学者;相似的是二人对大自然之美、之神奇、之厚载万物的由衷赞叹。利奥波德的代表作《沙乡年鉴》中有三分之二的篇幅描述自然因各种生命争奇斗艳而展现出的令人惊叹的美和活力。罗尔斯顿更把孕育着无数生命的自然称为终极的存在,因而他走向研究环境伦理学的道路时,就为大地伦理深深感动。“在利奥波德那里,‘……作为生态系统的自然……是一个呈现着美丽、稳定与完整的生命共同体。’”[6]利奥波德的“大地情结”贯穿于《沙乡年鉴》中的诗意的、感性的描述出来的沙乡景色当中,罗尔斯顿的生态系统由更科学化、更客观的语言表达成一个生命之网,一个繁荣昌盛的生态金字塔。两人都认识到,把自然当作死的资源或者任人类索取的农场都不是人类和自然相处的长久之道。用相同的热爱,罗尔斯顿和利奥波德呼吁人们依靠生态学理解这个在千万年中创造了无数生命奇迹的自然:“发现内在隐藏在大自然表面的冷漠、凶残和邪恶背后的美丽、完整和稳定”,[7]理解自然选择下物种的创生、繁荣,从而热爱“那些使得大地,以及生存于大地之上的生物获得其独特的形式(进化)并维持着它们的生存的自然过程”[8],结合了爱和理解,人才能采取尊敬它的完美、和谐和完整的态度,有效参与维持自然运转和进化过程的生生不息。罗尔斯顿还将利奥波德未阐述完整的“自然价值”加以系统化,归纳出自然的生命支撑价值、经济价值、消遣价值、历史价值等12种价值,并指出:作为一个进化的、走向更有序的、创生万物的系统而言,它本身的价值是最高的。
同样立足于“整体的和谐”,罗尔斯顿为利奥波德所作的辩护要比其他人令人信服。利奥波德的观点曾被雷根(Regan)攻击为“生态法西斯主义”:如果生命共同体的美丽、和谐、稳定为唯一标准的话,人也被看成是大地的一个普通成员,为了这个整体的好,是否可以像捕杀鹿那样牺牲一些人呢[9](特别是人的所作所为已经破坏了大地的时候)?玛汀纳尔(Marti knell)和艾瑞克·凯茨(Eric Katz)质问:有何理由可以为了整体而牺牲个体的权利?[10]虽然有大地伦理的传人卡利科特(Callicott),以及玛瑞塔(Don Maietta)和莫兰(Jo Moline)从准则/行为、直接/间接整体主义角度去辩护,[11]但并不令人信服;而罗尔斯顿的辩护就简单明了:“利奥波德并没有提出严格意义上的人际伦理学观点”。[12]“当人们获得某种关于生态系统如何运作的描述时,利奥波德相信,我们就能提出某种关于尊敬这个系统美丽完整和稳定的义务……对待人的义务依然一如既往的存在着”[13]。罗尔斯顿认为攻击利奥波德为“生态法西斯”是没有完整的理解利奥波德,因为生态系统与人类文化是两个截然不同的共同体(虽然文化受制于自然,但文化不同于自然,就像人不同于动物一样),利奥波德研究的是生态系统中的秩序,并由此提出对生态系统的“应该”如何做,把它用于文化(对待人的“应该”)是那些人犯了范畴倒置的错误。正如我们遵循自然整体的智慧让自然中挨饿的鹿直面自然的选择,但我们出于人类社会的道德不会拒绝救助非洲的难民。并且,利奥波德并不仅仅把人认为是“普通的公民”,罗尔斯顿认为完整的理解应当是既是公民,又是“王”,这种优越性表现在一种责任意识之上;“失去侯鸽的我们为这种损失而哀痛,如果葬礼是为我们举行的,鸽子几乎不为我们哀痛。这一事实……就是我们比动物优越的证据”。[14]这种优越感要求我们用爱来治理这个“共和国”,关怀其余物种的福利而不是相反。
三、“生态整体论”与“深层生态论”的分歧
深层生态论是经奈斯(Naess)、德韦尔(Devall)、塞申斯(Sessions)、福克斯(Fox)等人的努力而发展起来的激进的与环境保护实践结合的整体主义环境哲学。它以现代生态学为基础,倡导将“自我”(人)与自然融于一体的“自我实现”,与自然中的一切平等相处、共同发展。深层生态论与罗尔斯顿的生态整体论重大区别在于:
对生态学的定位上:虽然罗尔斯顿也曾借他人之口承认;“……能建立起概念与自然规律的结构体系,使人类认识到自己在自然中的位置,这样的认识,必定是道德价值的一个根基……对这个目的来说,生态学是核心的。”[15]但在罗尔斯顿看来,生态学使人类认识到自己的狂妄自大的一面,但并非为深层生态论所号召的人必须退到与万物平等共处的状态之中,生态学揭示的自然的智慧是一面,罗尔斯顿把人类的智慧、人类文明的成就看成是与之互补的另一面,他同样称赞:“人类文明发展过程……使生态系统有着间断式的不平衡,有意识地替代和改变”。[16]在这个意义上说,生态学帮助人类意识到自己生命的本源,作为自然中有最高内在价值之生命的责任和义务,为一个人类和自然和谐相处的地球而努力,而不是像深层生态论那样消极地完全把自我消融到环境中去。
深层生态论对生态学的应用,是为自己的理论需要而服务,带有片面性。比如,在奈斯的生态智慧T中,最大的多样性和最大的共生是“自我实现”理论的出发点,[17]将生态学说中自然界的生物多样性、共生关系推及人类社会,逻辑上是合理的,但是“共生”并不是自然界的全部,它是生态学可以认同的普遍原则,但并不具有普遍的意义。物种之间的主要关系是竞争和捕食,用罗尔斯顿的话来说:“生态学模型中,说自然界中不仅存在着互惠也存在着对立,这已成为公理性的。生态系统对它自己所支撑的生命也加以阻挠;事实上,生态系统对生命的阻力能刺激生命向前发展,在这一点上它不亚于生命的助力所起的作用。一个物种或一个个体生物的完整是依赖于一个场的函数。在这个场中,完整在于捕食和共生、建构与毁灭、升成与降解的交织之中,这个生命的系统包括了人类……尽管人类有许多选择,他们还是处于此系统之中的,从而不免于环境的压力,是这些压力促成了人类的独特性,并确定了人类的完整性。”[18]通过罗尔斯顿,我们可以看出奈斯理解的狭隘片面,貌似残酷的竞争和捕食牺牲了许多个体,却促进了整个物种乃至生态系统的欣欣向荣。罗尔斯顿不仅仅“认为大自然中会出现蓄意而为的合作行为是错误的”,[19]赞赏生态系统中看不见的手的调整,更强调在人类社会中“……一个完全充满敌意的环境会扼杀我们,一个完全顺从的环境会使我们迟钝退化”[20],两种都不能对生命完全的好,在人类社会中同样不能也不应该消除竞争。
深层生态论的生态中心平等论声称,“存在的领域中没有严格的本体论划分。换而言之,世界根本不是分为各种独立存在的主体与客体,人类与非人类世界之间也不存在任何分界线,……只要我们看到了分界线,我们就没有深层生态意识。”[21]这一说法是从生态学揭示的整体性出发,为“自我实现”的扩大认同做准备,因为既然人与非人自然物之间并无实质界限,那么“自我”(人)必然可以认同一切存在物融为一体,从而对一切非人的事物、与我们利益无关事物的保护也就是必然的了。范帕姆伍德(Valplumwood)曾批评过这实质是一种扩展的利己主义、人类中心主义,以扩展“自我”(人)至大自然来保护大自然,牺牲他者的独特性和独立性,借融入“自我”(人)来获取道德地位和保护。[22]罗尔斯顿则坚决主张人与动物的区别,这种区别在于人除了智力、语言、形而上的能力,还有“大自然同时为我们装备了良心,而没有把良心赋于那些非人类存在物”,这种良知指导人类活动适宜并适应(不管它在多大程度上发展了)大自然中一直存在着的那种前道德性质的调节机制。因而人不但利己(人类)也可以利它,高贵的人性因对其他形式的存在采取了尊敬态度而成了完美的人,因赋有反思其栖息地的高贵能力而成为万物之灵,[23]人类利他(生存于共同体中其他物种)精神恰恰使人区别于动物,区别于仅仅是“存在物”,这个意义上说,整体主义应当是承认寓多样性(利益)和内在价值于一体的整体,而不是人类扩张的自我利益整体。罗尔斯顿的境界如此高于深层生态论提倡的境界,他的“整体”因而也更具现实性、可操作性。
四、罗尔斯顿对生物中心论和动物权力/解放论的批评
如果说罗尔斯顿试图纠正深层生态论的激进和不合实际,他也试图避免动物权利/解放论的过于保守。
动物权利/解放论从道义论出发,反对给动物个体带来痛苦的一切饲养、使用、科研、商业、狞猎等活动。生物中心论秉承施韦兹(Albert Schweitzer)的主张,将这一关怀的对象范围扩大到所有生命之物,认为所有有生命个体都有价值和值得平等的尊重。罗尔斯顿的观点与他们有不少相同之处,如都主张把道德对象扩大到除人类以外的动物,承认生命的价值和权利,但罗尔斯顿毫不留情地对动物权利/解放论和生物中心论的观点提出批评,而且从整体的角度出发,这些批评比国内的一些观点更具说服力。
罗尔斯顿则主张:“动物个体的愉快、幸福只是环境伦理学所关心的也仅仅是其中的一个问题……它还要考虑,我们究竟在多大程度上依照生态系统的模型来调节我们的行为”。[24]自然并非道德代理者,而只是一个生物的“最佳适应地”,当人类观察自发性的大自然时,要求人们“把这个世界(人类没有创造也没有义务去改变的这个世界)所发生的一切当做理所当然的东西接受下来”。[25]对荒野自然中受伤的动物,人类没有救助的义务,当人类干预自然侵害野生动物的栖息地,造成了植物和动物的濒危时,人类才有责任和义务去保护它们,但对有感觉生命的任何义务都不能超越对生态系统(系统价值)的义务,因而,适当的野生动物贸易和猎杀繁殖过多、影响到生态系统中工具价值最大的植物利益的鹿都是许可的,是尊重这个生态系统本身的最高价值。而保护野生动物的栖息地比保护野生动物更有效,也更符合自然之道。
环境伦理学“并不要求我们去否认生态规律,而只要肯定它,即使我们饲养动物或重建我们的生存环境时也是如此”。[26]在文化中,对动物的任何使用必须有一个生态模型——生存、较严肃的目的(科研)、琐碎的目的——当生态模型逐渐退隐时,使用动物的合理性也不存在了,因而饲养家禽家畜并以之为食,是遵循大自然,因为生态系统中一个物种必须以另一种物种为食,接受自己生存的生态系统的逻辑规律和生物规律并非任何不道德的问题。狩猎,则“我们完全可以根据生态系统的生命金字塔规律——在那里,具有优势的动物悄悄追踪它的猎物——来理解打猎所曾经具有的受人尊重的古老内涵。”[27]人类的打猎因而具有神圣的价值。但只为了显示身份而不是为生存必须穿动物皮毛,则是不道德和不合理的。
罗尔斯顿还批评说,以感觉或痛苦来论证对动物的义务不过是地道的人类中心论,这样做是把权利给于那些我们能在其身上看到我们影子的高等动物或与人类较亲近的动物,在实践中我们往往就会忽略掉那些我们不甚了解的或者说“无用的”动物和生物。
生物中心论的两大缺陷是:1)把濒危动、植物与普通动、植物的价值看成是同等的,因而在人类选择两者之间的保护时无所适从。2)对生物平等的论证是不充分甚至是不可信的,罗尔斯顿正是从这两点批评生物中心主义的可操作性。在他看来,虽然也承认有机物的内在价值大过无机物,但他认为从保护生态系统的多样性出发,濒危动/植物对生态系统的价值要高于普通动/植物,判断它们之间的利益冲突不是根据生物中心主义提倡的心理复杂程度,而是看它们在生态系统中发挥作用大小,看它们在整体价值流中的作用。亦且有机体“价值异彩纷呈和多元化的……对它们的尊重不可能兑现成同等的权利或对其幸福的同等关心”,[28]这一点还间接来自罗尔斯顿对“生物平等”的批评,从物种层而言,不同的物种(细菌、植物、动物)其生态系统功能不同,内在的价值和工具价值也是不同的;从人与动物的比较而言,主张“把人视为与狼、猴子、驯鹿平等的事物来加以对待的观点,似乎是把人‘降低’到纯粹动物的价值水平……似乎又是人为地拔高动物的地位,这类判断缺乏必要的判断力,从坏的方面说,这是一种物种盲视,看不到物种之间的真正差别,以及那些具有道德意义评价上的差别。一个真正的伦理学家将坚持保护人们所发现的那些具有不同价值的复杂事物的多姿多彩的丰富性”。[29]动物之善,也必须放在其小生境内体现,并不意味着小生境中不同生命的价值和善是同等的,更不能认为人与动物之间不存在有任何决定性意义差别。因为动物仅仅生存于这个世界,人却能了解这个世界的存在物,人有智力、语言、思想和研究形而上学的能力,这种优越性也是一种以进化为基础的优越性,值得人感激的优越性,人是大自然最精致的作品,具有最重要的价值。“生态系统既是一个生物系统也是一个人类处于其顶端的系统”,[30]那些边缘人(胎儿、婴儿、智力障碍者、精神病人)的存在并不能消解人格的存在,不能用来证明人与动物的同一性,罗尔斯顿把生物中心论所谓的“平等”称之为“愚蠢”。他相信,人的优越性带来人的责任感,人有能力并且有义务保护其余的物种,包括区别地对待不同的物种。
五、三点启示
系统地分析、比较罗尔斯顿的生态整体论,至少给予我们三点启示:
1.罗尔斯顿试图在激进的自然中心主义和根深蒂固的人类中心主义之间找一个折衷点,因而在他的体系中表现出一种调和:他反对人类中心主义在自然面前的那种不可一世的主宰方式,同时又认为只有人才能担当地球守护者和国王的职责;他用生态学的事实证明了地球并非为人类而存在,人类作为地球生态系统的一分子,有最高的内在价值但不可能超越地球系统本身的价值,但他仍然反对深层生态论那种激进的、认为人应该关心自己一样关心自然、动物和植物甚至是号召为了自然的健康将地球人口减少到10亿的观点。他用系统价值这一观点调和这两种倾向——自然生态系统才是最高的价值之源,它创造了人这一万物之灵就是为了让人来维护这一整体的利益,只有整体的好才会有其中个体的好和价值的实现,人必须按照自然的智慧来从事自己的活动,这要求人了解自然的伟力,爱自然的神奇。最后罗尔斯顿寄希望于人类的明智和美德。虽有不足,但这确实是一个比较合乎实际的体系。
2.非人类中心主义/人类中心主义的分法是否妥当:当前这仍然是伦理学界争论的焦点,所依据的标准却是混乱的。如某些学者认为:非人类中心生态伦理观就是“完全抛开人类生存利益尺度,把保护自然系统的完整、稳定、美丽作为人类行为的终极目的和对人对自然道德行为的终极尺度”。[31]“夸大了人与自然的同一性,把人与其他物种置于同一进化层面”。[33]这种将观点极端化、依据对方片言只字来攻击对方观点的做法,并不利于我们吸收当代生态伦理理论的精华,也容易引起思想的混乱。这也说明我们对待西方生态伦理研究不足,进一步的深入探讨是必要的。
3.我们要建立一种怎样的生态伦理才是完全合理的?有没有提出一种统一的生态伦理的可能?罗尔斯顿在1999年访华时的回答也许对我们有所启发:他认为环境生态伦理流派众多,分歧颇大的根据在于人与环境的生态多样性,因而将其纳入伦理道德考虑的方式必然不是一个模式,具体环境伦理理论是有针对性、个性和镶嵌互补性的。人与自然界冲突和矛盾的解决,实质上是确立在多种环境伦理基础上统一的生态文明。[34]也许生态文明是统一的,但环境伦理学理论还无法做到独尊一家,如何整合,还有待于进一步吸取各派伦理学的精华,而不是单停留在批判的层面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