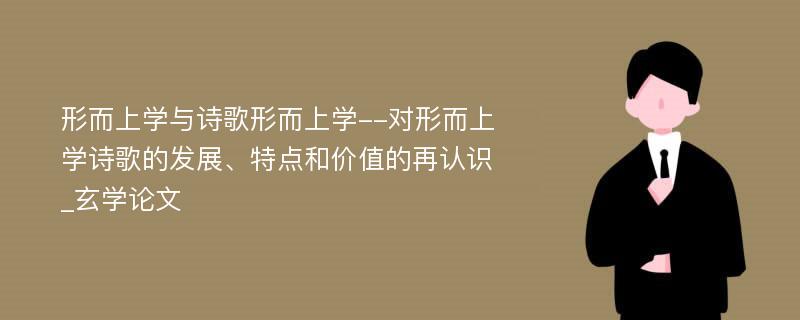
玄学的诗化与诗的玄学化——关于玄言诗的发展、特征和价值的再认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玄学论文,再认论文,的诗论文,化与论文,特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哲学与诗歌相互转化的双向运动
魏晋玄言诗的产生,是哲学与诗歌相互激荡的结晶。这种现象形成的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究其根本,乃是由于玄学和玄学活动本身的某些特点所决定的。
(一)魏晋玄学思辨的内容高度贴近诗歌表现的对象
众所周知,中国哲学是一种高度关注人本身的人生哲学。因此,中国哲学家思考的问题往往也是诗人所关注的焦点。在以追求个体人格自由为出发点的庄子哲学中,这种重叠已经有明显的体现;而在以庄子哲学为核心的魏晋玄学时代,这种重叠更臻于极致。从竹林七贤到金谷园诗会诸友,再到兰亭会众贤,魏晋名士莫不是集哲学家与诗人双重身份于一身。说魏晋浪漫主义的玄学是“一种诗化的本体论”(注:刘小枫:《诗化哲学》,76页,山东文艺出版社,1987。),是极为中肯的卓识。在这种背景下,面对共同的人生问题,魏晋士人是用抽象的哲思还是用形象的诗文去阐发,实质上变成了选择表达形式的问题。因此,玄学与诗的相互转化就显得很自然了。比如,由于时代政治的原因,理想人格一直是贯穿魏晋玄学思潮的中心问题,其他如圣人有情无情论、逍遥论、“将无同”论,等等,都是围绕着这个中心而展开的著名命题。同样,这些命题也不断再现于诗人的笔下。嵇康所向往的那种“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的生活,“绝智弃学,游心于玄默”的人物,正是作者对“逍遥”现实意义的心解。又阮籍《咏怀诗》其四十六咏道:
鸴鸠飞桑榆,海鸟运天池。岂不识宏大,羽翼不相宜。招摇安可翔,不若栖树枝。下集蓬艾间,上游园圃篱。但尔亦自足,用子为追随。
诗中“自足”于蓬艾间、园圃篱的鸴鸠,与向、郭《庄子注》所倡导的“任性自足”的逍遥论同一腔调。这种逍遥论在阮诗以前未见正式出现,或许,向、郭之逍遥论肇源于阮诗?
同样,玄学中的“才性论”、“养生论”,也是诗人时常吟咏的题材。显而易见,理论上的“才性论”与带有玄意的赠答诗,是通过清谈中人物品藻这一中介而相互联系起来的。导源于汉末清议和清论的清谈,是玄学思潮兴起的先声。因此,其中的人物品藻早在建安时期就已影响到诗歌创作了,刘桢《赠从弟》其二(“亭亭山上松”)已着先鞭。正始以降,赠答诗中的这类人物品藻俯拾皆是,嵇康《答二郭诗三首》其一、程晓《赠傅休奕诗》、欧阳建《答石崇赠诗》,等等,都是具有玄味的人物品藻。道家向来注重养生之道。从现存材料看,玄学论养生盖始于竹林名士。阮籍游苏门山时,就曾向真人叙说“栖神道气之术”(《栖逸》篇)。至于嵇康与向秀关于养生的往返辩难,更成如王导之流谈士乐此不疲的话题。在这样的一些论调影响下,游仙诗和隐逸诗的出现和带有玄味,就不足为怪了。嵇康《游仙诗》则与其养生论同一机杼:“王乔弃我去,乘云驾六龙。飘飖戏玄圃,黄老路相逢。授我自然道,旷若发童蒙。采药钟山嵎,服食改姿容。蝉蜕弃秽累,结交家梧桐。”阮籍《咏怀诗》其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八等,虽咏游仙,但也与《清思赋》、《大人先生传》一样,是“皆以道言”的(参见黄节《阮步兵咏怀诗注》)。
降及东晋,当诗已经普遍成为一种体玄认道的工具和对象时,诗的玄学化也就超过了玄学的诗化。《世说新语·文学》对此屡有记载:
郭景纯诗云:“林无静树,川无停流。”阮孚云:“泓峥萧瑟,实不可言。每读此文,辄觉神超形越。”
简文称许掾云:“玄度五言诗,可谓妙绝时人。”
谢镇西经船行,其夜清风朗月,闻江渚间估客船上有咏诗声,甚有情致。所诵五言,又其所未尝闻,叹美不能巳,即遣委曲讯问,乃是袁自咏其所作《咏史诗》。因此相要,大相赏得。
在这样的赏会中,诗的意义和价值显然已经超越了文学的阈限,从而进入了形超神越的玄境。过去论者讨论两者关系时,多注意到了玄学向文学的转化,却相对忽视了文学向玄学的浸透,(注:袁峰的《魏晋六朝文学与玄学思想》(三秦出版社,1995),已经注意到“建安文学对魏晋玄学的影响”,惜其论仅限于建安时期的文体、文论。)因此往往采用“玄学——士人心态——文学”这样的模式。这是有偏颇的。
(二)玄学理论提供了玄学与诗相互转化的理论依据
对这一问题,海内学者的论述主要集中在“言意之辨”上。汤用彤先生宏论先发,指出“得意忘言”是具有广泛影响的魏晋时代新方法,故魏晋六朝之音乐、绘画、文字等,都是玄学家“尽意”、“得意”的表达媒介。(注:《魏晋玄学和文学理论》,载《理学·玄学·佛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王葆玹先生则认为:玄学在“正始期间至少出现了五个认识论的派别”,其中“‘微言尽意’说与清谈及玄言诗的关系密切,‘微言妙象尽意’说曾是山水诗的理论基础,‘妙象尽意’说对书法、绘画、音乐等等广有影响”(注:王葆玹:《正始玄学》,317页,齐鲁书社,1987。)。此说颇为精确地揭示了玄学与各种艺术之间的微妙关系。
值得进一步指出的是,魏晋名士不仅把精妙的清谈视为“微言”,而且也常常将带有玄味的诗也当作“微言”玩味。《三国志·王粲传》裴注引《文章叙录》说:应贞“少以才闻,能谈论。正始中,夏侯玄盛有名势,贞尝在玄坐作五言诗,玄嘉玩之”。“能谈论”、“在玄坐”暗示,夏侯氏所玩味的,不在于诗情,而在于理趣,就如阮孚、简文帝和谢尚之醉心诗中玄味。竹林名士嵇康是以琴和诗为“尽意”手段的。他说:“弹琴咏诗,聊以忘忧”(《赠兄秀才入军》其十六)、“琴诗可乐,远游可珍”(同上十七)、“操缦清商,游心大象”(《四言诗十四》其三)……在这里,琴和诗成了嵇康借以忘忧、守道、逍遥和游心大象(道)的最佳工具。东晋高僧康僧渊的一段话较为明白地揭示了诗与“言意之辨”的关系:
省赠法頵诗,经通妙远,亹亹清绮,虽云言不尽意,殆亦几矣。夫诗者,志之所之,意迹之所寄也。志妙玄解,神无不畅。夫未能冥达玄通者,恶得不有仰钻之咏哉。(《代答张頵祖诗序》)
所谓“几”,是说赠诗极为接近尽意的境界。说诗为“意迹之所寄”,则已突破“诗言志”、“诗缘情”的传统樊篱,而臻“诗寄意”的哲学妙境了。当然,并非所有的好诗都是“微言”,只有那些能够充分体现出自然大道玄冥的诗,才算是“寄意”之作。
(三)玄学活动为玄学与诗歌互相转化的双向运动提供了直接的驱动力
这主要体现在清谈与赠答诗的彼此激扬中。出于拯救“微言绝”的使命感,魏晋名士选择了口头性的清谈作为玄学活动的主要内容和方式。而正是这种口头性决定了清谈以及整个玄学发展的两大方向:一是愈来愈抽象而趋于学理化;二是愈来愈具体而生活化(或曰泛化)、艺术化。前者多凝定为各种玄学理论著作,后者则关系到玄言诗(也包括其他艺术)的生成。因本文论旨的关系,这里主要讨论后者。
就玄学发展总体而言,如果说正始时期是“思辨的玄学”,那么,竹林时期是“性情的玄学”,中朝时期是“生活情调的玄学”(注:参见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第3章第3节。),江左时期则是艺术的玄学。这种划分可以以各阶段清谈的主要特征为标识。正始清谈,重在义理,思辨性强,内容纯正,故正始清谈多转化为玄学著作,而疏于文学之创作。竹林名士迫于政治的血腥,似乎在躲避那种大场面的清谈,他们的玄学活动更多地寄意于弹琴、咏诗、长啸,甚至借助于饮酒、裸体、服食等怪诞之举去“越名教而任自然”。正因为如此,竹林玄学才“以《庄子》为主,并由思辨而落实于生活之上”,从而变成了“性情的玄学”(徐复观语)。这种生活化、性情化的玄学正是诗歌诞生的温床。阮籍聆苏门先生长啸而作《大人先生传》、《大人先生歌》,嵇康以赠答诗与嵇喜、阮侃、郭氏兄弟清谈,阮籍、嵇康因倾心养生而发游仙之咏等创作过程,都表明了这一趋向。
中朝玄学的“生活情调”主要体现于清谈。孔繁先生精辟地指出:“西晋清谈上承正始、竹林,下启东晋,谈风盛炽深入社会生活,虽以谈理为主,而涉及生活之多方面和学术之各领域。”(注:孔繁:《魏晋玄谈》,137页,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降及东晋,这种生活情调的清谈更加泛滥。大凡日常生活的事物,都可以运用玄学的立场、态度和方法去清谈、品题一番。清谈的泛滥对玄学来说,是学术性、思辨性的衰落,但对文学而言,却是有力的促进。清谈的泛化直接地波及到对文学的讨论。除上文已引阮孚、简文帝、谢尚对诗的叹美外,《世说新语》的记载又有:
庾子嵩作《意赋》成,从子文康见,问曰:“若有意邪,非赋之所尽;若无意邪,复何所赋?”答曰:“正在有意无意之间。”(《文学》篇)
孙兴公作《天台赋》成,以示范荣期,云:“卿试掷地,要作金石声。”范曰:“恐子之金石,非宫商中声!”然每至佳句,辄云:“应是我辈语。”(同上)
如果说这些记载还没有脱尽清谈之玄意的话,那么,谢氏家族的许多谈论便已蜕变成纯文学的讨论了。谢安雪夜内集子弟“讲论文义”,问“白雪纷纷何所拟”(《言语》篇),因子弟集聚问“《毛诗》何句最佳”(《文学》篇),都成为文坛佳话。谢家诗风经久不衰,当与这种对诗文经常性的清谈有关。其实,时尚也如此。王孝伯问其弟王睹“古诗中何句为最”(《文学》篇),庾亮以亲族之怀名庾仲初《扬都赋》“可三《二京》,四《三都》”(同上)等,都表明谈诗论文之风不独盛于陈郡谢氏家族。
玄学的清谈既生于名流,亦长于名流。这使清谈始终带有浓郁的清雅之气,亦使清谈的形式极易趋向于艺术化,甚至成为“名士身份之装饰品”(注:陈寅恪:《金明馆丛稿初编》,18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这一趋向可以从两晋名士对于清谈这清韵奇藻、优雅氛围等方面的追求中体味出来。清谈尚辞藻之杰出者,当推郭象、胡毋彦国、裴遐和支道林等。《世说新语·文学》记载颗众,谈及者已多,自可不论。两晋清谈的艺术化除了讲求音辞外,更体现在对优雅环境、氛围的追求。西晋元康末年的洛水之游与晋永和九年的兰亭高会,实质上都是盛大的清谈活动(或广义的玄学活动)。值得品味的是,洛水之游的兴趣中心在谈名理、论史汉、说人物,而兰亭会的兴趣重心则在“游目骋怀”、“一觞一咏”;兰亭会的艺术兴味显然浓于洛水之游,清雅气氛逾于金谷园之聚。所以,数十首《兰亭诗》的产生绝非偶然。对东晋名士来说,清谈同样需要一种能激发诗兴的外境。对此,《世说新语》屡有记载:
刘尹云:“清风朗月,辄思玄度。”(《言语》)
许掾尝诣简文,而夜风恬月朗,乃共作曲室中语。襟怀之咏,偏是许之所长。辞寄清婉,有逾平日。(《赏誉》)
庾太尉在武昌,秋夜气佳景清,使吏殷浩、王胡之徒登南楼理咏。(《容止》)
诗人面对清风朗月、气佳景清而愈兴理思。此可与《文心雕龙·物色》所谓“春日迟迟,秋风飒飒。情往似增,兴来如答”云云同读。
这样,我们从内容的生活化和形式的艺术化两方面,清晰地看到了魏晋清谈向诗歌艺术、感性审美靠拢乃至融合的迹象。这一趋向正是促使玄言诗在东晋达到鼎盛的重要原因。
二、玄言诗的发展阶段及主要特征
关于玄言诗的发展过程,目前学术界一般认为:东晋是玄言诗阶段,此前上至正始或建安只是玄言诗的孕育阶段。但在与此相关的起源、分期、定义和特征问题上,各论者的意见却存在较大的分歧。(注:详见葛晓音《汉唐文学的嬗变》、王锺陵《中国中古诗歌史》、钱志熙《魏晋诗歌艺术原论》、卢盛江《魏晋玄学与文学思想》等。)笔者认为:以理性向感性转化和感性向理性转化为标志,玄言诗的发展过程,大体上可以分为玄学的诗化、诗的玄学化和玄学的自觉诗化三个阶段。与之相对应,玄言诗呈现出情理并茂、理过其辞和淡思浓采的不同特征。
南朝文学批评家对玄言诗发展过程的看法并不一致。檀道鸾从诗骚传统出发,以为玄言诗兴起于东晋初而终结于东晋义熙,他说:
正始中,王弼、何晏好《庄》、《老》玄胜之谈,而世遂贵焉。至江左李充(它本均作“至过江,佛理”)尤盛。故郭璞五言始会合道家之言而韵之。询及太原孙绰转相祖尚,又加以三世之辞,而《诗》、《骚》之体尽。询、绰并为一时文宗,自此作者悉体之。至义熙中,谢混始改。(《世说新语·文学》注引《续晋阳秋》,余嘉锡笺注本)
沈约、刘勰、萧子显、钟嵘等诸家意见大抵源于檀氏。沈约、萧子显同于檀氏,都明确地将东晋建武至义熙的百年划为玄言诗阶段(《宋书·谢灵运传论》、《南齐书》);刘勰则以正始为玄言诗起点(《文心雕龙》之《明诗》、《时序》);钟嵘则以为玄言诗肇始并鼎盛于西晋,流行并衰变于东晋(《诗品序》)。这些批评都是在看到比今天多得多作品的基础上提出的,所以值得特别注意。
(一)根据刘勰的意见和今存的作品看,正始、竹林时期应是玄言诗发展的正式起点,即“玄学的诗化”阶段
刘勰所说“正始明道,诗杂仙心”、“正始馀风,篇体轻淡”,都是指此而言。在这一阶段,玄学与诗的关系主要呈现理性向感性摆动,即玄学的抽象哲思被戴上了诗的形象花环;又由于司马氏血腥的屠刀,这些花环也变得异常哀艳。因此,玄言诗具有了情理交融的特征。
尽管岁月已经湮灭了正始、竹林时期的大量诗篇,但阮籍、嵇康的诗章足以使我们看透历史的风尘。“逍遥放意志,何为怵惕惊”(《言志诗》),何晏残存的诗作及夏侯玄对应贞诗的玩味(上已引),都依稀流露出正始玄学家并不乏诗人情怀的信息。“阮旨遥深”、“归趣难求”,难道不是玄风使之然?阮籍的近百首《咏怀诗》则充满着时代的悲哀和老庄的超脱精神,“下集蓬艾间,上游园圃篱。但尔亦自足,用子为追随”(其四十六),政局的险恶逼迫诗人只能学燕雀在蓬蒿间逍遥自足!“嵇志清峻”、“托喻清远”,正是诗人以老庄为师而形成的傲岸人格折射。嵇康既以诗、琴为“得意”的寄托,则赠答诗也未尝不可作为清谈。其《赠兄秀才入军诗》云:
流俗难悟,逐物不还。至人远鉴,归之自然。万物为一,四海同宅。与彼共之,予何所惜。生若浮寄,暂见忽终。世故纷然,弃之八戎。泽雉虽饥,不愿园林。安能服御,劳形苦心。身贵名贱,荣辱何在?贵得肆志,纵心无悔。(其十八章)
诗中密集地化用了庄子《天下》、《逍遥游》、《齐物论》、《刻意》、《养生主》等篇哲理,充分显出以诗谈玄的趣向。嵇喜当然也听出了其中的玄味,故其《答嵇康诗四首》也作针锋相对的辩解,如其二云:
君子体变通,否泰非常理。当流则蚁行,时逝则鹊起。达者鉴通机,盛衰为表里。列仙徇生命,松乔安足齿。纵躯任世度,至人不私己。
像这样以赠答诗谈玄的例子在嵇康集并非仅见,其《答二郭诗三首》其二、《与阮得如诗》也如此。如果像有些论者那样,把阮、嵇这样的诗仅仅看成是玄言色彩的加浓,并由此推论正始时期是玄言诗的孕育阶段,显然是有违于诗中事实的。应当看到:阮、嵇诗是有意识地谈玄,是时代玄学思潮深刻浸润的结果,他们的诗在总体上洋溢着老庄的超迈精神,绝非只是偶尔的用典。玄言诗的孕育阶段应该上推到正始以前的汉末,如刘桢的《赠从弟诗》其二、繁饮的《杂诗》。正如刘师培先生所说:建安文学“渐藻玄思”。从这两方面考虑,正始、竹林时期应是玄言诗的正式起点,阮、嵇是其代表。
(二)玄言诗发展的“诗的玄学化”阶段,主要包括西晋后期至东晋中期
此时期的诗人们纷纷主动地去迎合玄学的思潮,诗的绮丽花环被玄学的抽象思辨拆毁了,诗与思之间呈现出感性向理性日益靠拢的趋势,玄言诗变得“理过其辞”了。
钟嵘力主将西晋末作为玄言诗的起点和繁荣时期,东晋只是“微波尚传”的衰变时代。其《诗品序》已说得很清楚:“永嘉时贵黄老,稍尚虚谈。于时篇什,理过其辞,淡乎寡味。爰及江表,微波尚传……”刘勰也曾概括地说:“自中朝贵玄,江左称盛,因谈馀气,流成文体。”(《文心雕龙·时序》)其间差别在于刘勰是以东晋为盛。但现代不少论者却以西晋玄言诗过于散逸,或语焉不详,或干脆抹掉了西晋的这一环。这是不公允的。
从现存作品看,西晋元康(291-299)前后的玄言诗较为集中。清谈家孙楚(元康三年卒)《征西官属送于陟阳候作诗》,即是以玄理消释别情的完整玄言诗。与孙楚同时的隐士董京,其诗则以玄理美化隐逸(《诗》、《答孙楚诗》)。值得注意的是,当时的文坛领袖张华与友人之间的赠答诗也充满玄意:“奚用遗形骸,忘筌在得鱼”(何劭《赠张华诗》);“属耳听莺鸣,流目玩倏鱼”(张华《答何劭诗三首》其一);“恬淡养玄虚,沈精研圣猷”(张华《赠挚仲治诗》)。以张华在文坛举足轻重的地位而言,这种与其儿女情长诗风格迥然不同的诗作,理应会影响当时诗风的趣向,例如“三张”的一些诗就染有较浓的玄言色彩。同样,金谷园主人石崇(永康元年卒)及其周围诗人,如石崇《答曹嘉诗》、欧阳建《答石崇赠诗》、嵇绍《赠石季伦诗》、曹摅《赠王弘远诗》和孙拯《赠陆世龙诗》等人的赠答诗也洋溢着玄理。尤可注意的是,西晋某些赠答诗也流露出对清谈的推崇,体现了诗与清谈的关系。“文藻譬春华,谈话如芳兰”(石崇《赠欧阳建诗》);“精义测神奥,清机发妙理。自我别旬朔,微言绝于耳”(曹摅《思友人诗》);“赠物虽陋薄,识意在忘言”(潘尼《送大将军掾卢晏诗》)。在创作上,受西晋尚缘情、贵绮靡诗风的影响,玄言诗人在援理时,主观上并没有放弃对情、辞的追求,但客观上的确也存在着“理过其辞”的倾向。从上述围绕在张华、石崇周围某些诗人的作品看,西晋玄言诗实在是玄言诗发展过程中不可缺少的重要一环。
如果说西晋玄言诗主要是从感物走向缘情、理思的话,那么,东晋玄言诗则是从“理感”而趋于寄兴、释情。清谈既有“襟怀之咏”、“理咏”(上已引),则诗也有“理感”。“理感则一,冥然玄会”(庾友《兰亭诗》);“超兴非本有,理感兴自生”(庐山诸道人《游石门诗》);“奇趣感心,虚飚流芳”(郗超《答傅郎诗》)。从玄理出发,精彩纷呈的现象界,被诗人抽象成了单一的概念,“森森群像,妙归玄同”、“器乖吹万,理贯则一”(郗超《答傅郎诗》),“寥朗无涯观,寓目理自陈”(王羲之《兰亭诗》其一);诗人的情感被玄理淡释了,“亹亹玄思得,濯濯情累除”(许询《农里诗》),“理苟皆是,何累于情”(孙绰《答许询诗》)。由此,东晋玄言诗呈现出了“理过其辞”的一面。
(三)玄言诗发展的第三个阶段是“玄学的自觉诗化”
这一阶段肇始于东晋初,而形成于晋宋之际,与第二阶段在时间上有部分交叉。从表面上看,这段时期玄学与诗的关系类似于“玄学的诗化”时期,但实质上两者有很大的差别。如前所说,江左之玄学是艺术化的玄学,西晋以来的诗论是追求华美的诗学,东晋以降的玄言诗乃是名士自觉谈玄的工具。因此,清谈中的“名理奇藻”才能转变成诗作上的“淡思浓采”。这一结果是诗玄双向运动的必然阶段和最高境界。晋宋之际的陶、谢得时代风气之厚助而成为该阶段的突出代表。
晋室东渡之际,伴随着对清谈误国的沉痛反省(如刘琨《答卢谌诗序》),对“理过其辞,淡乎寡味”的玄言诗的反动也开启了。郭璞首唱,谢灵运殿后,几代诗人先后用了一百年的时间,才比较彻底地扭转了玄言诗一味言理、抛弃感性的颓势。对这一过程,钟嵘概括说:
先是郭景纯用隽上之才,变创其体;刘越石仗清刚之气,赞成厥美。然彼众我寡,未能动俗。逮义熙中,谢益寿斐然继作。元嘉中,有谢灵运,才高词盛,富艳难踪,固巳跨刘、郭,陵轹潘、左。(《诗品序》)
按照钟嵘的意见,郭璞是变创玄言诗的第一人。但在檀道鸾看来,郭璞却是玄言诗人的始作俑者。现代学者余嘉锡先生认为郭璞是玄言诗人,但不是始作俑者。他追源溯流说:
刘勰尝言:正始明道,诗杂仙心。则景纯此体,亦滥觞于王、何,而加以变化。与王济、孙楚辈,同源异流。特其文采独高,彪炳可玩,不似平叔之浮浅,永嘉之平淡耳。(《世说新语笺疏》文学篇笺疏)
余说甚是。王、何之仙心已不可见,但阮、嵇游仙之作仍在。比较而言,郭璞的游仙诗确有竹林之遗韵,故笔者上文说嵇康的游仙诗下启了郭璞等诗人的神仙之咏。郭璞虽然开始改造玄言诗,但他并没有跳出玄言诗的樊篱。这样看来,郭璞诗是否是玄言诗、是否为东晋玄言诗之起点等问题,也都涣然冰释了。
对谢灵运的山水诗和陶渊明的田园诗、饮酒诗也当如是看。与钟嵘一样,南朝论家是持否定态度的,现代论者也只谈陶、谢诗的理趣,极少将之放在玄言诗的范畴里讨论。笔者认为,陶、谢诗是诗与玄共同孕育的最完美的结晶,也是玄言诗发展的终结。
从背景上说,当诗歌在东晋成为谈玄论道的工具以后,诗人们也在不断地寻求把玄言诗写得像诗。如孙绰对许询诗、潘岳文章的评价(《答许询诗》、《世说新语·文学》),自诩“一吟一咏,许(询)将北面”(《品藻》),等等,都显示出东晋玄言诗人对诗歌艺术的一种自觉追求。更值得注意的是,从东晋中期以来,随着玄学自然观的改变,清谈和玄言诗都在趋向于对山水的“会心”、“玄览”和“理感”:
简文入华林园,顾谓左右曰:“会心处不必在远。翳然林水,便自有濠、璞间想也。觉鸟兽禽鱼,自来亲人。”(《世说新语·言语》)
而方寸湛然,固以玄对山水。(孙绰《庾亮碑文》)
乃悟幽人之玄览,达恒物之大情。其为神趣,岂山水而已哉。(庐山诸道人《游石门诗序》)
驰心域表,寥寥远迈。理感则一,冥然玄会。(庾友《兰亭诗》)
所以,孙绰把山水与文学紧密地联系起来:“此子神情都不关山水,而能作文?”(《世说·赏誉》)在王羲之的眼里,则是“寥朗无涯观,寓目理自陈”(《兰亭诗》其一)。这些都体现出东晋玄言诗由表现玄理的抽象化转变为以山水为表达媒介的具象化趋向。
如果说郭璞是以游仙之言,孙绰和许询是以佛家之辞来改造“理过其辞”的玄言诗的话,那么,谢灵运则是以美妙的山水成功地改装了“淡乎寡味”的玄言诗。他的山水诗正是使玄言诗具象化这种趋向,再进一步向客观世界对象化的结晶。首先,谢灵运是把山水当作体玄的具象看待的。所谓“山水性分之所适”(《游名山志》),即是他“以玄对山水”理性审美态度的说明,所以其山水始终割不掉悟理的尾巴。其次,谢灵运又把山水这一具象当作欣赏的对象看待。所谓“研精静虑,贞观厥美”、“此皆湖中之美,但患言不尽意,万不写一也”(《山居赋》及自注),即是他对山水常常保持着感性审美态度的流露。所以,其山水诗才能把大自然写得那么精彩纷呈。谢灵运对山水的这种双重审美态度,正是他能超越东晋诗人,成功地改装“淡乎寡味”玄言诗的关键所在。
与谢灵运相似,陶渊明是以田园、美酒来改装“理过其辞”的玄言诗的。从《形影神诗》、《归去来兮辞》序等诗文思想倾向看,他未尝不是以田园、美酒作为体玄之具象的。所谓“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归园田居》)、“酒能祛百虑,菊解制颓龄”(《九日闲居》)、“悠悠迷所留,酒中有深味”(《饮酒》),都流露着陶靖节归心自然的意趣。陶集里有相当一部分诗作都浸透着玄意,即使是最为人称道的名篇,也时常露出玄理的尾巴,“人生似幻化,终当归空无”(《归园田居》其二)、“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饮酒》其五)……至于《形影神诗》、《连雨独饮》和《饮酒》其三、其六等诗,更是整篇玄气,浓得化不开。因此,从总体上说,陶诗也没有跳出玄言诗的樊篱。
如果说“玄览”是玄言诗创作中感性与理性思维的分水岭,那么,郭璞、谢朓,特别是陶渊明、谢灵运就是通过一个个充满玄味的具象,把玄言诗从一味抽象的泥潭里拯救出来。他们用感性将玄言诗的演进推向了情、景、理交融的高境,即所谓“淡思浓采”。否认郭璞、陶渊明和谢灵运的诗是玄言诗,貌似拔高了其思想与艺术的价值,其实是泯灭了他们在诗歌史上的地位,同时也湮灭了玄言诗生存与发展的原始生态!
三、多重价值的多元评价
文学作品的价值是多重的。对生成于特定文化思潮中的玄言诗来说,尤其如此。玄言诗的多重价值既源于其自身构成因素的复杂性,也缘于其演变过程的历时性。因此,对其公允的评价也应当是多元的。
(一)从诗歌史和诗歌审美本身来说,玄言诗有许多值得肯定的东西,并非是一无是处的坏诗
在中国诗歌史上,玄言诗既改造、拓宽了诗歌表现的题材,又丰富了诗歌表现的方法。在嵇康、郭璞的笔下,传统的游仙诗不再是对生命无奈的哀叹和虚幻的企盼,而是超越现实而任自然的抒情诗;在玄学名士那里,赠答诗不仅仅是表现风雅的篇什,而是人物品藻的诗意化;庾阐、王羲之、陶渊明和谢灵运等诗人对大自然的“玄览”,则有意无意地开拓出了节候(如三月三日诗)、兰亭、隐逸、田园和山水等崭新的诗苑。无视玄言诗对中国诗歌史这些积极的贡献,无疑是不公允的。
在诗史上,玄言诗久负“恶名”的原因是被认为导致了诗歌的抽象化,剥落了诗歌的情感与辞采。不可否认,玄言诗在其发展过程中,的确存在着这么一个严重的抽象化时期,但同样不可否认的是,就玄言诗发展的总体而言,它又丰富了诗歌对情感和辞采的表现力。一方面,大量的诗例表明:言理与抒情并非是截然对立的,哲理往往有助于诗情的升华。“泽雉虽饥,不愿华林”、“泽雉穷野草,灵龟乐泥蟠”,嵇康正是借助于庄子的逍遥精神来抒发其任自然情怀的;“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陶潜正是凭借其“新自然观”来消解对社会、生命的忧虑的……玄言诗中类似的抒情方式都是利用哲理来加强抒情的,只是它与传统的叙事抒情、借景抒情等方式都有所不同而已。我们不但不能因此而否定其抒情性,相反,还应当充分肯定它对诗歌抒情新方法的创立。玄言诗的抒情是有渐“淡”的趋势,但在那些“采菊东篱下”悠然诗境的深层,却是对“道丧向千载”的深深忧患;在那些“池塘生春草”清丽诗语的背后,却是“心迹双寂寞”的无尽悲哀。玄言诗之“淡”,往往是抒情深沉的结晶,而非“以理祛情”的结果!
另一方面,大量的诗例还表明:言理与修辞并非是截然对立的,哲理往往有助于辞采的提炼和精确。有学者注意到,玄言诗尚简约的语言风格与清谈好“微言尽意”的方式直接有关。这种风格不仅体现在赠答诗里,也表现在一些景物描写上。如王胡之《答谢安诗》中的“自然挺彻,易达外畅,聪鉴内察”,即是人物品评语言;谢安《答王胡之诗》第五章“兰栖湛露,竹带素霜。蕊点朱的,薰流清芳。触地舞雩,遇流濠梁”云云,即充分表现了简约语言的概括力和准确性。(注:傅刚:《魏晋南北朝诗歌史论》,181页,吉林教育出版社,1995。)
(二)玄言诗以其哲学的品格促成了“寄兴”这一新诗学观的诞生
诗学观的兴替与哲学思想的消长向来密切相关:在经学家的苦心经营下,“言志”的诗学观传统得以建立;汉魏士人的激扬,导致了“言志”诗教的轰毁和“缘情”骚韵的复兴;魏晋玄学的勃起,则引发了“寄兴”诗学观的绽放。汤用彤先生曾透辟地说:
盖于文有两种不同之观点:一言“文以载道”,一言文以寄兴……此种“文以载道”实以人与天地自然为对立,而外于天地自然,征服天地自然也。后者为美学的,此盖以“文”为感受生命和宇宙之价值,鉴赏和享受自然……故文章当表现人与自然合为一体。(注:汤用彤:《理学·佛学·玄学》,327页。)
在创作实践上,这一诗学观既体现为魏晋大量赠答诗对个体价值、个人人格理想的肯定和颂扬,也体现为山水诗对大自然的鉴赏和感悟(即玄览、理感)。所谓“仪凤厉天,腾龙陵云。昂昂猗人,逸足绝群。温风既畅,玉润兰芬。如彼春零,流津烟煴”(王胡之《赠庾翼诗》第一章),并非仅仅以物喻人,而是在人与自然合一中品藻人物;所谓“取欢仁智乐,寄畅山水阴”(王羲之《答许询诗》),正是在鉴赏和享受自然中来感受生命和宇宙之价值的。有论者说“畅神思想,早在东晋就已普遍存在于文人游览山水的诗作中”(注:詹福瑞:《走向世俗——南朝诗歌思潮》,66页,百花文艺出版社,1995。),也可以说是“寄兴”诗学观的另一种表述。
“寄兴”的诗学观借助于理性,使诗更加走向诗人的内心,在终极层次体现了对生命和宇宙的关怀。“诗言志”主要体现为诗人对社会的责任,“诗缘情”主要表现为诗人对自我情感的抒发,两者对外部世界多采用“感物”表达方式;(注:张伯伟认为,“自魏晋至南朝,诗人的主观感受和客观物象的关系还处在‘感物’型的阶段”;“在谢灵运诗中,‘感物’也是一个基本的写作方式”,但又不限于此。参见《禅与诗学》,179~183页。)而“诗寄兴”则注重诗人自我内心世界的揭示,它多运用“理感”、“玄览”的创作原则。对此,谢灵运《归途赋序》曾说:
昔文章之士,多作行旅赋。或欣在观国,或怵在斥徒,或述职邦邑,或羁役戎阵,事由于外,兴不由己,虽才高可推,求怀未惬。
在他看来,只有发自内心的情思才可以惬怀,才可以“会性通神”(《山居赋》)。这种“兴”虽说是主观意识,但它既得江山之助,又借理思之悟,是“感物”与“理感”交融的产物。上引康僧渊《代答张頵祖诗序》,庐山诸道人《游石门诗序》,即指此而言。其中冥达玄通之神、所悟之大情,正是对生命和宇宙的终极关怀。玄言诗的哲学化,归根到底是在这层意义成立的,而并不在于它对哲学命题、活动和方法的一般表现。
(三)从文化学的层面上来审视,玄言诗有着比在诗史、诗学层面上更为深广的价值和意义
这主要体现在其思维的独特性和诗哲相融的本体论两方面。由于华夏民族成熟的思维之根深植于《周易》和《诗经》,所以易象与诗象的异同格外引人注目。宋人陈骙说:“《易》之有象,以尽其意;《诗》之有比,以达其情。文之作,可无喻乎?”(《文则》卷上丙)这是说《周易》之象与《诗经》之比,都是一种象喻,但在功能上却有尽意与达情的差别。清人章学诚也讨论过两者的异同,得出了中国古代学术“未尝离事而言理”和“《易》象通于《诗》之比兴”的结论(《文史通义·易教》下)。钱钟书先生据陈、章之说,辨曰:《易》之象主义理,《诗》之喻主文情。“哲人得意而欲忘之言、得言而欲忘之象,适供词人之寻章摘句、含英咀华,正若此矣”(注:钱钟书:《管锥编》,14、15页,中华书局,1986。)。三位学者的讨论表明,在中华民族思维之树生长的初期,抽象思维与形象思维之间有言理与抒情表达手段上的差别,但无根本目的上的不同,两者是可以相通兼容的。这一点正是以“三玄”为核心内容的魏晋玄学得以从理性向感性摆动、从哲学认知向审美体验转变的关键。所以,“得意忘言”、“微言妙象尽意”的手段,可以有诗歌、音乐、书法、绘画等多种艺术形式。因此,具有“淡思浓采”特征的玄言诗的诞生,有着中华民族思维“未尝离事而言理”、“神与物游”这种特性历史发展的必然逻辑。
与庄子哲学一样,魏晋玄学与玄言诗也是用人格本体来概括、表现宇宙的。一方面,“尽管玄学讲了许多有无、本末、言意、形神……但问题的核心仍然是如何才能成统治万方的‘圣人’”(注: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即理想人格的实现。另一方面,尽管玄言诗有赠答、游仙、隐逸、节候和山水等形式变化,但所咏之核心仍然辐凑于畅神、寄兴和理想人格。嵇康之泽雉、郭璞之仙境、王羲之之兰亭、陶渊明之田园和谢灵运之山水,莫不是玄学的形象翻版。因此,魏晋玄学人格本体论的审美精神与玄言诗注重寄兴和理想人格的审美态度,才能在比思维方式更高的层次上重叠、融合起来。
把玄言诗置于世界的诗坛上来审视,其价值与意义更耐人寻味。当一千六百多年前的魏晋士人以哲学家和诗人的双重身份把人性从汉代经学的枷锁中解放出来的时候,西方的哲学家、诗人还匍匐在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耶稣(形而上学、宗教)的脚下。当他们意识到自己被社会物欲追求、神学思想深深异化了的时候,省悟到自己与本性、自然之间已经深刻分裂了的时候,才纷纷惊呼:诗人应当与哲学家交换位置,人应当“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荷尔德林诗句)。于是,诗歌与哲学才开始在人的本体意义上交流起来。法国的象征主义诗人声称:
如果一个诗人永远只是诗人,没有丝毫进行抽象思维和逻辑思维的愿望,那么就不会在自己身后留下任何诗的痕迹。(瓦雷里语)(注:参见、转引胡经之等编《文艺学美学方法论》第3章,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
在德国,浪漫美学作为一种诗化哲学,曾伴随着欧洲近现代浪漫主义思潮而勃然兴起。从叔本华、尼采、狄尔泰到海德格尔形成一种思想传统,即把诗不只是看作一种艺术现象,而更多地看作是解决人生的价值和意义问题的重要手段,把美学视为人的哲学的归宿和目的地。正如卡西尔所说:“把哲学诗化,把诗哲学化——这就是一切浪漫主义思想家的最高目标。”(注:参见、转引刘小枫《诗化哲学》,山东文艺出版社,1987。)这种把哲学诗化和把诗哲学化的现象,尽管在其具体的形成过程上与魏晋之际玄学的诗化与诗的玄学化有所不同,但在本质上却是相同的——都指向人的生命本体论。“目送归鸿,手挥五弦”、“朝乐朗日,啸歌丘林”、“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清晖能娱人,游子澹忘归”……这样的人生难道不是一种诗意化的栖居?
在玄言诗这颗由哲学与诗共同孕育的结晶里,集中地折射着中国哲学诗意化和中国诗歌哲学化的迷人光彩。这才是玄言诗最根本的价值和意义!
标签:玄学论文; 玄言诗论文; 谢灵运论文; 诗歌论文; 世说新语·文学论文; 嵇康论文; 读书论文; 魏晋论文; 东晋论文; 竹林七贤论文; 咏怀诗论文; 名士论文; 魏晋时代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