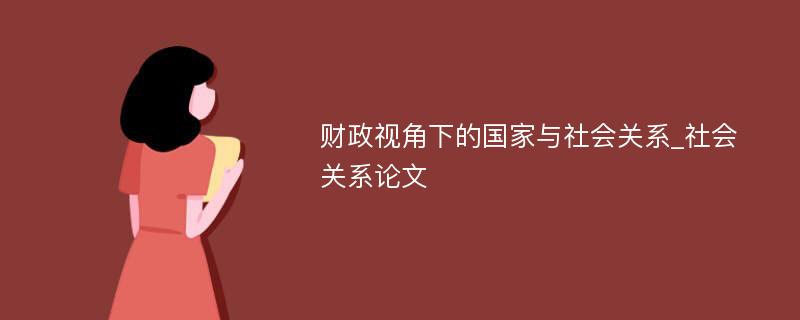
财政视野下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关系论文,视野论文,财政论文,国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政治体系和经济体系的互动,它起始于对国家财政的研究。随着发展,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主题、对象、范围和方法越来越多元化。①即便如此,财政仍然是政治经济学中的一个重要课题,因为它是国家进行治理的基本保障,最直接地牵涉了政治和经济的互动,也最为典型地展现了国家和社会的关系。无论是横向地观察世界各国,还是纵向地追溯各国的历史,都可以发现不同国家或同一国家在不同时段在财政征收和支出的对象、方式和规模等方面存在着明显的差别,而这些差别对国家和社会关系有着重要的影响。
就一般的国家和社会的关系研究而言,往往分两个层面来考察,一是国家影响社会的层面,二是社会影响国家的层面。在国家影响社会的方面,主要从两个角度来看,即国家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以及国家对社会实行的保护程度。在社会影响国家的方面,也可以分为两个视角来考察,即社会对国家权力施加的限制以及社会对现有政治秩序的接受程度。换个方式来说,国家和社会关系可以被简化成以下四个问题:为什么有些国家的经济发展更为快速,而有些国家经济发展困难重重?为什么有些国家更倾向于去保护社会从而减轻市场经济的负面效应,而有些国家却不倾向于这么做?为什么有些国家的权力受到了社会的更多限制,而有些国家的权力所受社会的限制更少?为什么有些国家的社会秩序更为稳定,而有些国家的社会秩序更加动荡?它们是所有现代国家在发展过程中都不同程度所面临和需解决的重要问题。
对这些国家和社会关系问题的探讨,对中国有着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在西方国家的侵略和威胁下就开始从古代帝国向现代国家转变。今日的中国和其他现代国家一样,需要去发展经济、保护社会,同时国家的权力也必须受到社会的制约和遵循。在今日中国,国家和社会呈现出怎样的关系?在市场经济的快速推进中,受损的社会力量如何才能得到保护?在促进经济、保护社会的过程中,国家日益扩大的权力如何才能得到限制以至于不被滥用?这些都是中国持续发展首先需要探讨和回答的问题。
通过财政视角考察国家和社会关系,无疑能更加清晰地展示两者之间的究竟是如何交互作用,同时也会给中国政治经济持续发展带来新的更为深入的启示与思考。
财政视野下国家对社会的影响,即国家促进经济和国家保护社会两个方面。在现有文献看来,国家对财政的需求是其推动经济的重要动力和条件,而援助或者资源收入等非挣得型收入不利于国家对经济的推动。同时,财政丰富与否以及财政收入的性质是决定国家是否能有效保护社会的关键因素。而财政视野下社会对国家的影响,一方面体现为社会凭借着自身的资源能够对国家权力有所限制,另一方面体现为社会对国家财政行为的不满会导致对政治秩序的挑战。这些理论对中国的现实政治经济发展而言有着深刻的启迪作用。
二、财政视野下国家对社会的双重影响
(一)财政视野下的国家促进经济
经济发展历来是社会科学的讨论热点。对于第三国家的发展,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持依附论的学者是悲观的,在他们看来第三世界的欠发展是因为核心国家将之锁定在边缘位置。然而,这派理论面临的挑战是东亚新兴工业经济体的经济奇迹:为什么有的边缘国家能够兴起,而有些国家继续被边缘化?
要回答这个问题,一个途径是回到国家本身,即考察国家对于经济的关系。国家对经济的促进作用早为许多学者指出。20世纪40年代波兰尼(Polanyi)就在《大转型》中指出:通往自由市场之路,需要在中央集权和不断干预下得到持续地增强。根据张夏准在《富国陷阱》对西方市场制度的介绍中所言,即使是市场主体也是国家的创造。格申克龙(Gerschenkron)进一步认为后发展国家面临的发展问题不同于已经发展起来的国家,后发展国家首先需要发展的产业资本需求量很高,需要强组织的推动,比如德国就通过银行来提供资本,而俄国由国家来承担资本供给。赫希曼(Hirschman)观察了后发展国家后认为,国家的作用不仅仅局限于提供资本这一职能,它还需要承担企业家的职能,需要创造最大化投资的动机。日本和韩国的经济发展正是与其国家的这些作用密不可分。
如果说有些边缘世界国家能够发展起来,是因为国家发挥了作用,但是没有回答的问题是,为什么其他第三世界的国家没有发挥类似的作用呢?为什么有的国家有动机促进经济发展,而有的国家更多的是在掠夺国内社会?追着这个问题,很多学者提出了自己的解释,比如殖民地遗产论,威胁感知论等。而从财政收入视角出发的这派学者提出了一个简洁的也颇具普遍性的解释。
这派观点建立在对经济学中“荷兰病”现象的反思之上。之前经济学家认为自然资源能够帮助后进国家,因为资源可以帮助这些国家获得资本,政府也可以便利地获得财政收入和提供公共物品。但到了20世纪80年代后,这种观点被证伪了,即很多第三世界国家虽有着丰富的自然资源,但是并没有发展起来。经济学家提出的解释可以概括成一种现象,被冠名为“荷兰病”,指的是发现石油资源后,导致了相关的服务业、交通业等急剧发展,使得资本从工业和农业中撤出,从而有害一国的长期发展。不过“荷兰病”解释的问题在于:它假设劳动力和资本是固定的,并充分就业。但实际上这两者的供给并非固定,而且发展中国家往往存在劳动力过剩的情况。同时,这种观点也抽象掉了国内政治因素的作用。
政治学学者正是从这个基础上进行思考。在他们看来,丰富的自然资源会扩大那些推行不利于经济发展政策的行为者的权力。这个观点常常用来解释拉丁美洲和亚洲经济发展的不同。由于拉丁美洲有着丰富的自然资源,国家凭此就可以获得大量的财政收入,所以能推行不利于经济发展的进口替代战略时间比较长。但是,如果国家凭借自然资源就可以获得大量的财政收入,而不需要向社会团体征收财政收入,那么国家应该有更强的自主性,能够更加自主地决定政策的走向。那么为什么国家被锁定在既定的发展策略中呢?这是因为在拥有资源租金(rent)的情况下,国家变成了租金分配型国家或是石油国家(petro-state),即这个国家和社会的制度在租金的作用下变得不利于生产性活动,并具有锁定作用。也就是说,资源和发展的逻辑链条中,需要加入“制度”这个变量:即容易获得的财政收入,塑造了不利于生产的制度,最后导致了国家的不发展。这便是“富饶困境”的症结所在。②同样,这个逻辑也适用于对外援助对国家的影响上。在这派观点看来,只要国家不依赖于国内生产性部门来获得财政收入,它就不会关心国内的生产状况。租金使得国家可以少收税,从而不需要对社会负责,不需要促进经济发展,也不需要了解国内的经济状况。
如果说财政收入性质通过影响制度来解释不发展的话,那么反过来它是否能够解释发展呢?财政因素是否可以解释发展型国家的兴起呢?在一些学者看来,发展型国家的崛起有两个条件,一是国家面临着严重的外部威胁,二是统治者希望借助经济发展来构建联盟和维持统治。但是这两个条件的存在并不能直接推导出国家是发展型的,因为如果一个国家拥有大量的援助或者自然资源收入时,统治者可以依赖这些容易获得的财政收入来抗击危机和构建联盟。只有一国的财政收入紧缺时,国家才会努力推进经济发展,在发展过程中获得应对危机和构建联盟的资源。③所以说,财政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发展型国家的兴起。
上述逻辑不仅适用于全国层面,也适用于地方政府对经济的推动。尤其是在解释中国经济奇迹时,这个财政逻辑为很多学者所强调。相比于俄罗斯的经济发展,中国经济在改革开放之后的迅猛发展变得更加突出。有学者指出,这是因为中国保持了政党国家,它进行了分权改革后,一方面地方的财政收入可以根据经济发展来获得,另一方面也无法向中央要钱,所以只能专心搞建设和积累上。而俄罗斯因为政党国家瓦解了,所以中央就集中经济资源以图控制地方政府。结果是导致地方向中央要钱,更注重中央财政的分配,而不是谋求发展俄罗斯的地方经济。④换句话说,中国财政分权体制使得地方政府的财政硬化,为地方政府提供了从经济增长中获得额外财政收入的激励。因此改革开放以来,地方政府官员为了增加财政收入,采取了很多有利于经济发挥的措施,比如加大对基础设施的投资、扩大规模招商引资。⑤不过,中国地方政府的行为也并非完全一致,不同的地方政府由于财政征收的对象差异有着不同的行为。在一些以农业为基础的不发达地区,地方政府更倾向于扮演掠夺型而非发展型政府的角色。
(二)财政视野下的国家保护社会
国家的作用不仅在于推动国内经济和社会财富的发展,也在于国家为了社会免于市场风险而提供的保护,福利保障的供给就是具体的政策表现。充足福利提供的前提就是国家有着较为充裕的财政收入。“二战”后,国家的急剧膨胀成为20世纪非常明显的一个现象。学者卡梅隆(Cameron)曾这样形象地描绘国家的扩张:“随着‘福利国家’的成熟,政府日益增加社会服务的供给以及对失业者、病人、老人和穷人的收入转移。而且,政府也变成商品的重要生产者,在一些欧洲国家中石油、汽车和交通产业受到国有企业的主导。此外,通过使用各种财政和货币工具,比如公共支出项目、税收以及贴现率,政府试着调节失业和通货膨胀水平以及弱化商业周期的影响。它们也会通过计划性的制度来指导经济的长期发展……的确,国家的汲取角色得到了如此之大的扩张,以至于熊彼特根据欧洲历史发展、写在半个世纪之前的话到了今天似乎更有道理:‘国家手持着税收议案,渗透并主导了私人经济。’”⑥
不过这种保护型的福利国家并不是没有受到挑战: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它便面临着全球化的挑战。全球化的基本理念是自由市场,反对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另外,各种要素跨国流动的加快,也限制了国家向这些主体征收财政收入的意愿和能力,于是一个直接的结果就是政府开支面临着被削减的极大压力。如果各国政府竞争性地削减福利开支,那最终的可能是各国福利冲向谷底(race to the bottom)。但与此同时,全球化也带来了社会民众对福利国家的新要求。一方面由于全球化带来的经济波动,受到波动影响的社会民众需要政府提供保障;另一方面也由于工作性质发生了变化,越来越强调对特殊技术的需求,所以雇员希望国家可以通过福利的方式来加大对技术学习的投资。从这个方面说,全球化进一步要求国家向社会征收财政资源并提供公共服务。那么全球化到底塑造了更为竞争型的国家,还是更为保护型的国家呢?
在一些学者看来,这取决于国内的政治力量,比如福利制度创造的新利益集团倾向、政治家的理性计算、中间选民的偏好等。正是这些利益集团在不同国家的不同分布,导致了各国在压力下对福利提供的选择。但这些政治解释基本上都强调的是社会需求的影响,而忽略了国家何以能够维持高昂的福利支出这个问题,也就是忽略了国家财政这个角度。
从这个角度出发,学者考特(Kato)指出,在更为保护社会的国家中,是国家征收财政收入的方式发生了改变,使得民众对国家汲取不是那么敏感,这样国家就可以继续从社会征收更多的财政收入来维持福利国家。其中最明显的一个变化就是间接税的兴起和传播。通过对增值环节征税而不是对所得收入征税,国家减少了和人们的直接接触,在这种“财政幻觉”之下,获得了大量的财政资源。⑦因此,顺利实行间接税的国家仍然能够维持以及扩大保护型国家,而在一些无法顺利实行间接税的国家,福利供给面临着全球化的更大压力。
其次,财政征收方式的不同对于福利国家的变革也会产生不同的影响。比如20世纪90年代德国和美国在长期福利保护方面出现了差异:德国制定了新的长期福利保护项目,而美国在这个方面没有进展,尽管两国之前在这个政策领域的经历和面临的社会利益集团压力都是类似的。有学者指出这是因为两国的财政制度不同。在德国,其财政收入的征收权集中在中央政府,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获得主要是通过联邦政府的转移支付来满足,而美国的地方政府更加能够财政自给。当地方政府感知到社会的福利需求并面临财政压力时,德国的中央政府会立马感知到,并最终形成全国层面的政策。而美国则缺乏这种地方政府的传导机制。⑧因此,国家财政收入的征收方式的不同,也会影响一国福利制度的发展和变革。
同样,对于提供福利的地方政府而言,不同的财政收入来源直接决定了面对资本要素加快流动的不同反应。有学者指出,如果一个省份大部分的财政收入来自中央政府的话,那么该地政府与地方商业联系不那么紧密。相反,如果一个省份的财政收入主要是来自对商业力量和工人的税收,那么该政府对私人经济更加负责。由于这种差别,拥有不同财政来源的地方政府面对要素流动的压力有着不同的反应:如果地方政府依赖于自己的税收,那么分权化会促进地方政府的缩小。如果地方政府依赖于上级政府的转移支付,那么分权化会扩大政府。⑨
以上这些观点对中国社会保障的发展带来很多思考。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是一个非常碎片化的权威体系。⑩在社会保障支出方面,同其他财政支出一样,也存在着“碎片化”、“分散化”的倾向。(11)目前,中国大部分社会保障项目以地市级,甚至县级为单位建立。(12)地方政府不仅直接面临着全球化带来的资本流动问题,而且由于政府官员的晋升和财政激励,也导致了中国内部区域间对资本的竞争和抢夺。另一方面,中国的财政体制虽然在20世纪90年代初有所变更,但是转移支付的份额依然比较小,而且政治性的考虑更多。这也进一步使得地区对资本需求更为敏感。那么中国地区之间对资本的竞争是否会使得由地方政府提供的社会保障“冲向谷底”?如果中国希望社会保障发挥“安全网”、“社会稳定器”作用,实现保证社会成员底线公平、稳定社会、缓和社会矛盾的效果,那么这些问题必须是值得认真思考的。
三、财政视野下社会对国家的双重作用
(一)财政视野下的社会限制国家权力
现代国家的典型特征是对暴力的合法垄断,在当代武器的技术和资本含量日益提高的状况下,国家似乎是越来越难以被社会撼动。为了避免绝对的权力必然带来绝对的腐败,除了国家各部分之间横向的制衡之外,社会也需要对国家权力进行一定的控制。有意思的是,现代国家在形成过程之中,即合法垄断暴力的过程中,社会对国家权力的控制在若干国家中已经开始了。这是如何发生的?
现在大多数学者都承认,现代国家源于激烈的国际竞争:从1480年到1550年70年间,欧洲发生了48次主要战争,1550年至1600年50年间就有48次,而从1600年到1650年50年间则增加到116次。(13)尽管激烈的国际竞争环境使得各种类型的政治实体都朝着现代国家的方向聚合,但是各国内部的政治制度安排却是不同的。其中,有的国家形成了宪政制度,有的国家变成了绝对主义国家。为什么在类似的国际竞争环境中,有的国家权力受到了更多的限制,而有的国家却没有?财政视角出发的研究给出了很有意思的回答。
蒂利(Tilly)在探讨战争和国家形式间关系时认为:收税的难度、特定军队所需的花费、发动战争抵御竞争者的费用等决定了欧洲国家形式的差异。那么,又是什么决定了“收税的难度”呢?蒂利指出:“在汲取方面,在其他情况一样的条件下,资源总量越小、经济商品化程度越低,汲取资源来维持战争和其他政府活动的工作越是困难,于是财政机关延伸地越是宽泛……总体而言,对土地征税成本更高,而相对而言,对贸易征税成本较低,特别当大笔贸易能够被轻易地监督时。”(14)英国和普鲁士的历史发展较好地印证了其观点。普鲁士更加依赖对土地征税,所以它征税的成本更为高昂。普鲁士努力塑造一个与其周边更大国家相当的军队,所以其汲取资源机构非常庞大。而英国有着大量丰富和商业化的资源,所以它的汲取机关比较小。蒂利的理论贡献是在战争和国家形式之间加入了一个变量,即财政征收对象的特点。根据他的推论,英国避免成为绝对主义国家,是因为其财政资源的丰富和商业化。这个观点受到了其他学者的认同。比如曼(Mann)就明确将不同资源的汲取方式与国家的政权形式联系起来。他认为绝对主义国家采取了集权化的官僚制度来强制动员国内的货币和人力资源,而像英国这种商业发达的国家,不需要建立这种集权化的官僚制度,从而维持宪政制度。(15)
上述的观点暗含有两个假设,后来的学者便通过修改这些假设对该理论进行了调整和转变。首先,在上述观点中,唯一的行为者是国家,看不到社会和市场利益的力量,这些都被简化成了征收对象的特点,即资源是否丰裕或者是否商业化。但是在面对着战争威胁的情况下,为什么国家对社会商业化资源的汲取会有所节制?为什么不通过绝对主义的制度建设向这些商业化资源征收最大化的财政收入?很显然,资源是否充裕本身不能够解释制度的不同。贝茨(Bates)从财政征收对象的流动性来解释为什么有的国家能够形成宪政制度。在贝茨看来,由于战争期间政府需要财政支持,但是资本家具有规避税收的途径,比如资本流出,所以政府给予他们决策的一定权力,两者可以进行谈判,社会力量也在这个过程中对国家的权力施以限制。(16)
其次,上述观点把国家简化成是单一的行为体,却忽视了国家内部的结构,比如地方政府的不同种类。在珥特曼(Ertman)看来,地方政府相对于中央政府而言可以分为参与型(participatory)和管理型(administrative)。参与型的地方政府体现为以地域为基础组建起来的议会制度,而管理型地方政府表现为以身份为基础组建的议会制度。当中央政府需要财政收入时,参与型的地方政府可以以地方性共同体身份为基础,一方面组织财政收入给中央政府,一方面能够避免受到绝对主义王权的控制,从而能够保证宪政。而管理型的地方政府却无法为身份导向的议员来提供共同体的身份和资源,从而无法克服绝对主义王权的控制。(17)
以上两点思考对考察中国现实有着较强的启示意义。首先是对于中国政治发展的分析。在一些现代化理论的学者看来,随着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商业力量的兴起,那么这个国家会走向西方式民主。(18)暂且不论商业力量是不是民主化的充分还是必要条件,中国的经济发展是否造就了独立的商业力量诉求就已经成为问题。首先,中国的改革是渐进式的改革,资本的来源极为多元,造成了中国商业所有者背景不同、企业大小不一样、政治联系不一样,因此商业力量有着不同的社会和政治身份,很难形成一个一致的阶级,他们对政策的偏好也是不同的。(19)同时,中国对商业力量有着统合的制度安排,通过吸收企业家入党、建立组织关系等手段对这些新的商业利益集团进行统合。(20)换句话说,中国的国家和社会关系是交织的,国家不会为了财政需求而向商业力量妥协。相反,社会对国家权力的控制反而是来自国家内部的促动,因此中国的民主化呈现了一条和西方很不相同的道路,即由民政部推动、从基层政府为起点的民主化。(21)
还有一部分学者寄希望于中国的分权能使地方政府约束中央政府的权力。如财政联邦主义的学者就认为在中国财政分权的背景下,地方政府可以避免国家层面的政治干扰。(22)但财政联邦主义忽略的是国家的权力常常是多维度的,财政分权不代表政治分权。政治权力往往更为关键,中国通过党管干部等机制牢牢地控制着地方政府。很明显,中国的地方政府的性质更多的是管理型的,而非参与型的。因此,目前中国国家权力的约束机制仍然需要回到国家内部去寻找,机构内部的权力制衡以及基于合法性的考虑是国家自我限制权力的动机来源。
(二)财政视野下的社会挑战国家秩序
发展中国家除了发展问题外,还面临着随发展而来的社会挑战国家秩序的问题。起初,学者们对经济发展和秩序稳定之间的关系比较乐观,认为发展就会带来秩序。但是很快这种乐观情绪就被替代成学者们口中的“政治衰败”。亨廷顿精辟地指出,快速的现代化并不一定会带来政治发展,相反可能会造成政治衰败,因为动员与参与的快速增长会削弱政治制度的基础。不过,不是所有的第三世界国家都经历了政治衰败。那么,为什么有的发展中国家内部冲突不断,而有的国家的秩序相对稳定?
在一些学者看来,发展中国家内部冲突不断是由结构性因素导致的。第三世界国家都是被强力纳入现代国际体系中的,采取“国家”为国际社会中的基本政治制度单位也是国际竞争的结果。不同于西欧国家建设过程已经成熟、开始针对民族国家的潜在威胁而组建区域共同体的现状,第三世界国家正处在国家缔造的过程之中。国家缔造过程是一个国家针对反对性地方集团的不断的集权化过程,在此过程中国家需要持续地向社会征收财政收入。只要政府能够设计出控制资源攫取、获得财政收入的制度安排,那么国内政治就会趋向于稳定;相反,如果由国内社会秩序的挑战者来掌握资源,那么社会就比较混乱。(23)但是,如果在国家缔造过程中国家过分地向社会征收财政收入,这会引起社会反弹和内乱不断。(24)这个观点和斯考切波研究社会革命的逻辑相一致。她提出革命的条件之一便是在外部威胁的压力之下国家向社会过分扩大对财政收入的征收力度。
除了财政收入的规模之外,财政收入的性质也是解释国内冲突的一个因素。有学者曾探讨过土耳其和伊朗社会秩序差异的财政原因。土耳其的财政来源主要来自国内剩余,国家要征收财政收入,就需要满足社会主体的需求,在这个过程中建立了统合主义结构。因此,国家和社会之间的相互沟通比较流畅,社会秩序倾向于稳定。相反,伊朗的财政收入主要来自石油,伊朗政府与国内社会联系淡薄,国家没有通过经济合法性来建构自己的政治合法性,从而使得国内社会逐渐不满,借助于宗教来挑战国家。(25)但需要指出的是,拥有自然资源的租金并不必然导致国家不回应社会需求,造成社会秩序的不稳定。从逻辑上来说,政府有了大量的租金作为财政收入,就不那么需要直接向公民收税,同时还可以提供很多公共产品,这样就不会引起社会的反弹。所以说,对于国内秩序而言,光是探讨财政收入维度是不足够的,同样需要考察的是财政收入的使用方式。当财政支出的分配是根据人际型的一些关系,比如家庭关系、友谊关系进行分配时,会引起社会的不满,从而导致国内秩序的不稳定。像中东地区一些国家国内秩序混乱,就是因为人际型的财政分配方式。(26)
综上所述,财政的征收规模、征收方式、收入性质、收入使用方式等都会影响到国家和社会的关系,最终影响到一个政权的合法性和社会稳定程度。社会秩序的财政解释无疑也给理解中国现实带来了很多的洞见。改革开放后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中国局部地区也出现了一些影响社会秩序的群体性事件,其中一部分事件就是由地方政府的不当财政行为导致的。从财政收入的角度来看,政府财政收入最大化的一些行为造成了国内社会的不满和反弹。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土地作为一种生产要素不断彰显出市场价值,土地逐渐成为地方政府收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地方政府为了更快的经济发展和获得更多的财政收入,加快了土地的流转工作。它们常常低价征收土地,高价转出,失地农民往往对土地补偿不满意,有些农民就不愿意拆迁。于是,一些地方出现了强拆等现象,直接造就了社会的极大不满。据有些学者指出,土地相关的问题是农民不满和抗争的首要原因,在2006年的头9个月全国就发生了“大规模农村事件”17900件。(27)
从财政支出的角度来看,中国的财政使用往往缺乏透明度。中国农村税费改革之前出现的社会不稳定,部分原因也正是财政支出方面的问题。因为政府对社会的回应性(accountability)不足,财政收入往往没有用在农民所需要的用途之上,农民也往往不清楚自己所缴纳收入的最终用途。农民的公平观念建立在支出和回报的比较上,当他们觉得付出没有得到合理回报时,就产生了对纳税的反感。地方政府官员的征收成本提高,只能通过骗、吼和吓来征得收入,这是税费改革之前农村社会不稳定的原因之一。(28)因此,中国财政的规模、征收方式和使用方向都与国家稳定和社会秩序密切相关。
四、结论
财政的收入和支出是国家的基本功能,也是国家维持存在的必要手段。正如上文展示的那样,其征收和使用的对象、规模和方式等方面的不同会对国家—社会关系带来一系列的重大后果。和其他理论视角一样,它提供了系统理解社会世界的一条途径。财政视角下的研究对我们理解和思考中国的现实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目前,中国的国家财政汲取能力非常强大,很大一部分社会财富集中在政府手中,这在相当大程度上影响和塑造了中国的国家和社会关系。一方面,国家可以利用财政收入来集中支持一些关键产业来推进中国经济的腾飞,另一方面,却使得社会更多地依附于国家,对政治权力监督的动力只能更多地指望于来自国家内部。一方面,国家集中了大量财政收入可以对社会进行有效的治理和提供更多的保障,另一方面,却使得社会对国家征收规模和支出方式有所不满和反弹。因此,要有效地调节中国的国家和社会关系,实现“和谐社会”的目标,财政将是一个“牵一发、动全身”的关键改革领域。
同时,中国的现实以及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比较也为财政研究带来了大量的研究素材,有利于理论突破和概念创新。比如,财政的制度安排与一国政府治理水平、政体选择、政党体系等有着何种关系?将财政和中国独特的国家缔造和形成过程相联系,在历史中考察财政和国家制度和政治的互动,将是一个极有生命力的领域。其次,财政本身安排的跨国和跨时差异,还需要进一步系统的研究。比如,就税收而言,为什么经济水平相似的中国和印度在税收结构存在着差异,中国的直接税比例要远低于印度?对于大多数国家而言,分权往往意味着支出的分权,而财政征收权几乎是持续地集中在中央政府手中。为什么中国在计划经济时代的历次分权都伴随着财政征收权的下放?为什么会存在跨时代的变化?无疑,这些都将成为比较政治经济学进一步深入研究的广阔领域。
注释:
①朱天飚:《比较政治经济学与比较历史研究》,《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1年第2期,第67—68页。
②Terry Lynn Karl,The Paradox of Plenty:Oil Booms and Petro-States,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7.
③Bryan K.Ritchie and Richard F.Doner,"Systemic Vulnerability and the Origins of Developmental States:Northeast and Southeast Asia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59,2005,pp.327—361.
④Michael Burawoy,"The State and Economic Involution:Russia through a China Lens",World Development,Vol.24,No.6,1996,pp.1105—117.
⑤Montinola Gabriella,Yingyi Qian and Barry R.Weingast,"Federalism,Chinese Style:The Political Basis for Economic Success in China",World Politics,Vol.48,No.1,1995,pp.50—81.Jean C.Oi,"Fiscal Reform and the Economic Foundations of Local State Corporatism in China",World Politics,Vol.45,No.1,1992,pp.99—126.对于这个解释也存在学术争论,请参见Hongbin Cai and Daniel Treisman,"Did Government Decentralization Cause China's Economic Miracle",World Politics,2006,Vol.58,No.4,pp.505—540.周黎安:《中国地方官员的晋升锦标赛模式研究》,《经济研究》2007年第7期,第6—50页。
⑥David R.Cameron,"The Expansion of the Puhlic Economy:A Comparative Analysis",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72,1978,pp.1243—1261.
⑦Junko Kato,Regressive Taxation and the Welfare State:Path Dependence and Policy Diffusion,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3.
⑧Andrea Louise Campbell and Kimberly J.Morgan,"Federalism and the Politics of Old-Age Care in Germany and the United States",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Vol.38,No.8,2005,pp.887—914.
⑨Jonathan Rodden,"Reviving Leviathan:Fiscal Federalism and the Growth of Government",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57,2003,pp.695—729.
⑩Pierre F.Landry,Decentralized Authoritarianism in China:The Communist Party's Control of local Elites in the Post-Mao Era,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8.
(11)景天魁、毕天云:《从小福利迈向大福利:中国特色福利制度的新阶段》,《理论前沿》2009年第11期,第5—9页。
(12)张秀兰、徐月宾、方黎明:《改革开放30年:在应急中建立的中国社会保障制度》,《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2期,第121页。
(13)Benno Teschke,"Theorizing the Westphalian System of States:International Relations from Absobutism to Capitalism",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Vol.8,No.1,2002,pp.5—48.
(14)Charles Tilly,Coercion,Capital,and European States,AD 990—1992.Cambridge,MA:Blackwell Publiahers,1992,p.182.
(15)Michael Mann,The Sources of Social Power I:A History of Power from the Beginning to A.D.1760,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6,pp.456,476,479.
(16)Robert H.Bates and Da-Hsiang Donald Lien."A Note on Taxation,Development,and 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Politics and Society,Vol.14,No.1,1985,pp.53—70.
(17)Thomas Ertman,Birth of the Leviathan:Building States and Regimes in Medieval and Early Modern Europ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7.
(18)刘瑜:《经济发展会带来民主化吗?》,《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1年第4期,第16—25页。
(19)Kellee S.Tsai,"Capitalists without a Class",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2005,Vol.38,No.9,pp.1130—58.
(20)Bruce J.Dickson,"Cooptation and Corporatism in China:The Logic of Party Adaptation",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Vol.115,No.4,2000,pp.517—540.
(21)Tianjian Shi,"Village Committee Elections in China:Institutionalist Tactics for Democracy",World Politics,Vol.51,No.3,1999,pp.385—412.
(22)Montinola Gabriella,Yingyi Qian,and Barry R.Weingast,"Federalism,Chinese style:The Political Basis for Economic Success in China",World Politics,Vol.48,No.1,1995,pp.50—81.
(23)Richard Snyder,"Does Lootable Wealth Breed Disorder? A Political Economy of Extraction Framework",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Vol.39,No.8,2006,pp.943—968.
(24)Youssef Cohen,Brian R.Brown,A.F.K.Organski,"The Paradoxical Nature of State Making:The Violent Creation of Order",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75,No.4,1981,pp.901—910.
(25)Hootan Shambayati,"The Rentier State,Interest Groups,and the Paradox of Autonomy:State and Business in Turkey and Iran",Comparative Politics,Vol.26,1994,pp.307—331.
(26)G.Okruhlik,"Rentier Wealth,Unruly Law,and the Rise of Opposition: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Oil States." Comparative Politics,Vol.31,No.3,1999,pp.295—316.
(27)Keliang,Zhu and Prosterman,Roy,"Securing Land Rights for Chinese Farmers:A Leap Forward for Stability and Growth",Cato Development Policy Analysis Series,No.3,October 15,2007,p.1.Available at SSRN:http://ssrn.com/abstract=1066812.
(28)Thomas P.Bernstein and Xiaobo Lü,Taxation without Representation in Contemporary Rural China,Cambridge and 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3.
标签:社会关系论文; 国家经济论文; 中国资源论文; 国内经济论文; 财政制度论文; 中国学者论文; 社会资本论文; 经济学论文; 社会资源论文; 社会问题论文; 财政学论文; 商业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