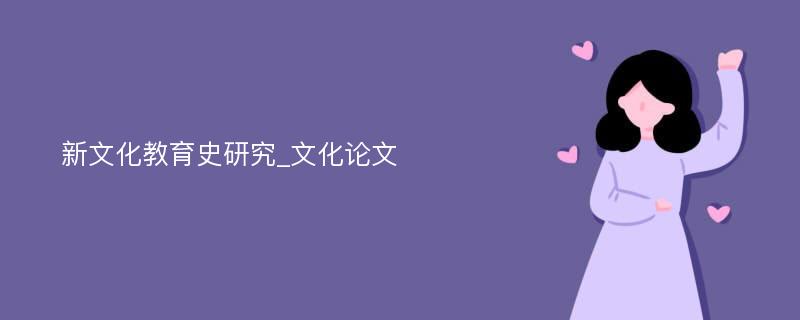
新文化史与教育史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化史论文,史研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5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413X(2016)04-0012-04 自古代希腊以来,西方就有着悠久的文化史研究传统。希罗多德的《历史》被视为一部文化史,关注希腊世界与其他文明的互动和交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出现了许多文化史的经典作品。20世纪中期以来,西方史学先是从传统史学转向社会科学化史学,后来又经历了从新社会史到新文化史的发展历程。新文化史的真正突破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初,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是新文化史发展的兴盛时期,形成了引人注目的新文化史运动,对各国历史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也对教育史研究有诸多重要启发。 一、新文化史运动 “文化”一词具有多重不同的含义。文学理论家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把文化称为“英语世界中最为复杂的两三个概念之一”[1](P61)。他试图通过研究各个历史时期该词的用法,来解释其多重交叉含义。到20世纪,文化在总体上用以表示象征体系。彼得·伯克(Peter Burke)认为,文化史这个名称也不是什么新发明,早在二百多年前的德国,就已经有在“文化史”(kulturgeschichte)名义下进行的研究[2](P6)。再往前追溯,文化史早在古代希腊就出现了,希罗多德的《历史》被视为一部文化史,其视野广阔,包罗万象,可以从中看到希腊世界与其他文明的互动和交流。但在希罗多德之后,史家似乎更注重当代史和政治军事史,如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在19世纪,民族史学兴起,兰克注重政府档案,历史研究的范围变得更窄了。 彼得·伯克将1800-1950年称为文化史的“经典”时期,著名的文化史作品包括瑞士历史学家雅各布·布克哈特(Jacob Burckhardt)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1860),荷兰历史学家约翰·赫伊津哈(Johan Huizinga)的《中世纪之秋》(1919)以及英国历史学家G.M.扬(G.M.Young)的《维多利亚时代的英格兰》(1936)。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1904)也被认为是一部文化史著作,其要点是为经济变化做出文化解释。诺贝特·埃利亚斯(Norbert Elias)的《文明的进程》(1939)实质上也是一本文化史。 新文化史的兴起与战后历史学的总体变化相关联,特别是与历史观念和史学观念的变化有密切联系。文化史得以重新发现的原因在于当代史学的困境,与后现代主义对历史学、历史写作的冲击及其后果有关,后现代主义其实是对现代性的一种反思。战后,西方不再是世界的主宰,并为自身存在的许多问题所困扰,“大写历史”走向衰落,人们对兰克的“如实直书”产生了怀疑,进而对“小写历史”产生了研究兴趣,历史认知的问题被提上议事日程。“其结果就是,原来视为天经地义的历史的规律性发展,不断为人所怀疑。而后现代主义的主要论题之一,就是质疑启蒙思想所揭橥的历史发展的规律或上面所说的历史的一线形的发展”[3](P27)。一些学者过去主张不变的理性,现在他们的兴趣日益转向价值观即特定群体的时代和特定地点所持有的价值观。 文化史被重新发现或说新文化史的真正的突破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初。在各门学科中,对文化、文化史以及文化研究的兴趣越来越明显。“1980年代至1990年代是新文化史迅速扩张发展的时期,涌现出一大批新的经典,一方面用文化研究的角度和方法刷新了传统政治史、思想史、社会史等领域,同时更开拓出史学研究的诸多新领域,构成了波澜壮阔的新文化史运动。”[4](P3)新的经典作品涵盖了多个领域,包括政治文化史、社会文化史、物质文化史、感性文化史、身体性态史和媒体与传播史等,其发展的结果,就是颠覆了盛行一时的社会史模式。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新文化史渐入颓势。 美国当代史家林·亨特(Lynn Hunt)是一位公认的新文化史的领军人物。她主编的《新文化史》(1989)和《超越文化的转向》(1997)成为人们了解新文化史的必读书目,前者明确打出“新文化史”的大旗,确定了历史学主流之“文化转向”(the cultural turn);后者则进入了每个学派发展到一定时期应有的自我批评的阶段。在林·亨特之后,新文化史作为一个学派不断更新,开始从重大的历史事件转到比较边缘的、以往为人所忽视的领域,研究更加微观的历史现象。“如果说对叙事的关注构成了过去20多年中历史书写的确定特征之一的话,那么,‘文化转向’(the culture turn)似乎是一个更宽广的运动,它横扫整个人文科学领域,并且囊括从意义建构到商品消费等各种形式的文化。因此,在新形式的理论与新类型的史学关系中,文化的概念居于核心地位。”[1](P61)在新文化史兴起之初,也有一些著名的新文化史著作考察的是重大的历史事件,如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家爱德华·汤普逊(E.P.Thompson)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就是一部对新文化史的兴起极具启发性的著作,他是将“文化”引入史学领域的先驱之一。 二、新文化史的研究路径 新文化史的研究主要有两个进路,一个是人类学,另一个是文化理论。在人类学和文学模式之间以及各自内部存在着很多差异,但两者也有共性,主要表现在都将语言看作隐喻,显示出对于权力关系的深刻关注,象征性行动如屠猫和暴动等被放进文本或语言的框架中被解读或解码。林·亨特主编的《新文化史》的第一部分检视了文化史诸种模式,第二部分则举出了一些具体例子以展示当时正在进行的新研究。她在该书的导论中回顾了新文化史兴起的历程,揭示了新文化史与文化理论和人类学的密切关系。林·亨特认为,文化史是一门诠释的科学,其中心任务在于破解含义,而非因果解释。 新文化史的兴起与先前的社会史研究朝着文化史的转向有着重要的联系。林·亨特认为,历史研究中的社会学转向受到两种支配性解释范式即马克思主义和年鉴学派的影响。但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在马克思主义和年鉴派史学解释模式中发生了研究重点的重大转移,两派史学家对文化史的兴趣日益浓厚,他们转向了人类学,试图寻找另一种把文化和社会联系起来的方法。马克思主义史学中的这种转向的突出表现是汤普森的《英国工人阶级的成长》。与此同时,该学派对语言也越来越有兴趣。年鉴学派第四代史学家罗杰·夏尔提埃(Roger Chartier)和雅克·瑞威尔(Jacques Revel)则深受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对社会史的基本预设批评的影响,转向考察文化的实践。福柯透过权力技术的多棱镜来研究文化,并策略性地将此多棱镜放置在话语之中,在文化史的理念方面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在林·亨特看来,人类学模式统领了以文化入手的研究进路。仪式、颠覆性嘉年华(carnivalesque inversions)和成长的仪式(rites of passage)在每个国家和几乎每个世纪都能找见。“盎格鲁-撒克逊和美国的文化史研究进路所受到的来自英国和英国训练的社会人类学家的影响绝不亚于、或甚至大于年鉴派风格的‘心态’史”[4](P10)。新文化史是从历史人类学中发展起来的,其中一些重要人物如娜塔莉·戴维斯(Natalie Z.Davis)和雅克·勒高夫(Jacques Le Goff)既属于历史人类学的领域,同时又参与了新文化史运动。在文化研究和历史研究中最引人注目的人类学家是克里斯福德·吉尔兹(Clifford Geetz),其论文集《文化的阐释》(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为众多学者所引用。他将破解含义视为文化人类学的中心任务,这种趋向被称作历史研究的人类学转向(anthropological turn),指的是历史研究转向人类学意义上的文化研究,以及采用人类学中人种志的厚描方法对这种文化的历史加以表现。“厚叙述”(thick description)是人类学研究的一个传统,而这个传统在20世纪70年代以来再度吸引了史家。在史家的研究从宏观转向微观之际,人类学提供的这种“厚叙述”叙述史的复兴成为历史学与人类学之间结合的桥梁。 新文化史在文化理论的进路方面受到后现代主义史学的影响。后现代主义史学从多个不同的视角看待历史研究。从诠释学的视角看,历史是文本;从文学批评的视角看,历史是话语、是叙事;从人类学视角看,历史是文化。所以,有学者将新文化史与社会文化史都置于后现代主义史学流派之中[5](P490)。在林·亨特主编的《新文化史》的第四章《文学、批评及历史想象:海登·怀特和多米尼克·拉卡普拉的文学挑战》("Literature,Criticism,and Historical Imagination:The Literary Challenge of Hayden White and Dominick LaCapra")中,罗伊德·克雷梅(Lloyd Kramer)梳理了这两位史学家与文学理论最密切的相关著作,清晰地揭示了文学进路如何使怀特和拉卡普拉得以拓展文化史的疆域。在林·亨特看来,在新文化史研究的文学进路方面,夏尔提埃也是一个重要的代表人物。他受到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的影响,从共同体向差异移动及重新定向,并更倾向于直接使用文学理论,强调描述过去的象征性行为的文献不是清白透明的文本,其作者有着各自的意图。因此,文化史家应该设计他们自己的解读策略。英国史学家西蒙·冈恩(Simon Gunn)在《历史学与文化理论》(History and Cultural Theory,2006)一书中更为全面和深刻地揭示了历史学与文化理论的密切关系。他认为:“文化理论对当代历史书写的影响,不仅被视为是宽泛的,而且,某些情况下,更是深远的。”[1](P201)在他看来,文化理论与历史学合为一体,其中的许多理论已经介入与马克思主义的对话当中,文化理论家在与社会和政治史学家保持联系的同时,显示出对于权力关系的深刻关注。 21世纪初,新文化史在得到公认的同时,也成为众矢之的。彼得·伯克认为:“新文化史并不是没有遇到挑战。支撑它的基础理论不仅经常遭到传统的经验主义者的批判或拒绝,也遭到爱德华·汤普森那样一些富有创新精神的历史学家的批判和拒绝。汤普森首次发表于1978年的那篇题为《理论的贫困》的文章,就对新文化史进行了批判。”[2](P86)21世纪伊始,有人宣告“后理论”时代的到来,暗示“宏大”理论家的传统的终结,也意味着与后现代主义相关的思考样式的能量已经耗尽。人们批评新文化史家对文化的强调削弱了历史与社会科学的联系,应在以文化转向为指导的同时,重新评估社会科学方法论的价值。还有人批评文化理论模糊了话语的起源或者核心,混淆了想象与真实的区别,给历史编纂带来了负面影响。 三、新文化史对教育史研究的意义 文化史在上一代人当中成了一座舞台,围绕着历史研究方法而展开了一些让人激动又具有启发意义的讨论。文化史学家不仅让历史更接近广大公众,也扩展了史学家的领域。在新文化史这把大伞底下进行的实践采用了各种各样的研究方法,在过去的三十多年里取得了令人瞩目的集体成就。教育史研究者能够从经典文化史作品和新文化史的研究成果中得到诸多启发。 首先,教育史研究者应该思考新文化史家提出的一些重要理论问题。文化理论对于历史学家来说仍然不可或缺,它允许历史学家跨越民族性、学术传统和学科归属的边界进行更加广泛和深刻的交流。文化史学家强调了复数形式“文化”的整体性,从而提供了一种弥补手段,克服了当代历史学科的碎片化状态。经验主义的历史学家或“实证主义”的历史学家中的许多人对符号学缺乏足够的敏感,还有许多人把历史档案当作一眼就可以看穿的东西,不再费心去关注或根本不关注其中的修辞。而文化史学家已证明了这种实证主义研究方法固有的弱点。相比之下,计量史学方法过于机械,对于多样性不够敏感,这是不言自明的。如果把内容分析法与传统的文学细读法结合起来,至少可以纠正这类偏向。例如,我们可以运用“话语分析”(discourse analysis)的方法研究教育史。话语分析是指对比单句更长的文本进行语言学分析的一种方法。它与已被它取代的内容分析法并不完全相同,更加关注日常会话、言语图示、文学载体和叙事研究。 其次,在注重教育史的经济和政治解释的同时也可以尝试文化解释。晚近以来,文化和人类学建立起密切的联系。以往,社会科学化的历史学研究更依赖于传统的经济学、社会学和政治科学,而新文化史更依赖于人类学、语言学和符号学。“事实表明,符号或象征人类学推动了人类学的文化转向,如果说皮尔斯、索绪尔以及巴尔特的符号学理论还只是这种转向的理论源头;那么,象征人类学理论则直接体现了当今文化人类学的主旨,同时也是后现代主义史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5](P466)。前几十年的历史学家喜欢将“社会”挂在嘴边,现在的历史学家更加喜欢使用诸如“印刷文化”、“宫廷文化”和“绝对专制主义文化”等词语。20世纪90年代出版的书籍,书名中经常会出现“美德文化”、“爱情文化”、“抗议文化”、“清教文化”和“礼仪文化”等。结果,每一样东西都有它自己的“文化”,包括食品、睡觉、情感、身体、旅行、记忆、姿态和考试等。在教育史研究中,我们可以借鉴这些方面的研究成果,以丰富和深化教育史研究。 再次,从经典文化史中汲取与教育史研究有关的养料。如前所述,雅各布·布克哈特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约翰·赫伊津哈的《中世纪之秋》、英国历史学家G.M.扬的《维多利亚时代的英格兰》和诺贝特·埃利亚斯的《文明的进程》都是值得我们研究的西方文化史的经典,他们的主要目标是描绘文化模式,而教育史家可以通过对“主题”、“象征”、“情感”和“形式”的研究去发现这些模式。约翰·赫伊津哈在《中世纪之秋》中讨论的骑士风度和生活理想以及象征主义在中世纪晚期的艺术和思想,有助于我们深化对中世纪骑士教育的研究。诺贝特·埃利亚斯的《文明的进程》集中研究了餐桌礼仪的历史,以便揭示西欧宫廷内自我控制或情绪控制的渐次发展过程。他有关15世纪至18世纪之间对自我控制的社会压力的研究以及他的“自我控制的文化”理念,也有助于我们加深对伊拉斯谟的名著《男孩子的礼仪教育》的理解。 最后,应研究新文化史对于各国教育史学发展的影响。比如,我们可以研究“戏剧类比”的文化观念对教育史学观念的影响。“人类学家提出的广义的文化概念过去有而且现在仍然有另一个吸引人之处,那就是它把曾经被平庸的历史学家丢弃给研究艺术和文学的专家们去进行的符号学研究与社会历史学家们正在探索的日常生活联系起来了。戏剧的力量,部分就在于它推动了这种联系的建立”[2](P46)。克里斯福·吉尔兹的“戏剧类比”把过去对“上层”文化的关注与日常生活中的新的兴趣相联系。从这个视角研究教育史会发现每一种文化教育都有自己一套独具特色的“保留剧本”或者保留剧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