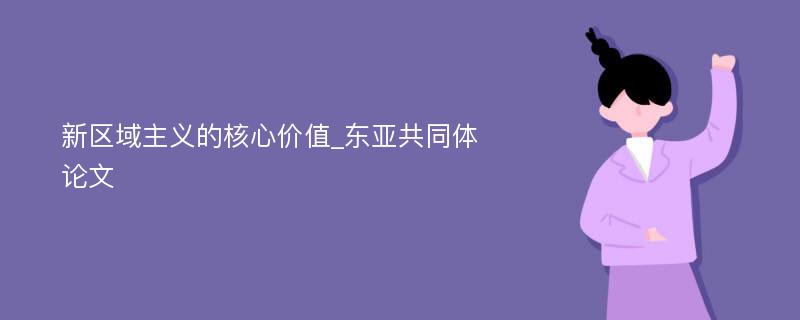
新地区主义的核心价值,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核心论文,主义论文,价值论文,地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新地区主义在世界上的兴起已是不争的事实,而从规范的角度思考新地区主义的国际研究文献仍捉襟见肘,很不完整,更不系统,其关键在于缺乏对新地区主义核心价值的确认和探讨。从新地区主义的内在逻辑上看,我们可以发现一个通常不加以正面表达、但却无处不在的观念和价值,那就是把“地区”放在了观察和思考世界政治的首要位置,这种观念和价值对新地区主义而言是核心的,概括起来就是四个字:“地区至上”(或“地区优先”、“地区第一”)。(注:在英文中其对应词应该是“primacy of
region”或者“put the region first”,当然,至今还没有见到哪位国际理论家在英文文献中这样用过它。)
一、提出“地区至上”价值的理论依据
为了简明而又连贯地解释“地区至上”这种新地区主义价值的合理性,首先让我们借用一下世界政治研究中的层次分析法(注:国际关系学者对层次分析法已耳熟能详,它起源于肯尼思·沃尔兹(Kenneth Waltz)1959年和戴维·辛格(David Singer)1961年的倡议,运用最成功且影响最大的则是肯尼思·沃尔兹。常用的层次分析法以三层次分析居多,也有四层次分析和五层次分析。国内学者对层次分析法的介绍,主要可参考秦亚青:《层次分析法与国际关系研究》,载《欧洲》,1998年第3期。)——它是迄今国际关系学中最为简明、最为中立也最方便交流的分析方法。
参考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广为运用的层次分析法,我们这里把国际研究的对象分成五个范围不断扩大、依次递进的层次:一是个体层次;二是地方层次;三是国家层次;四是地区层次;五是全球层次。每个层次中都有特定的行为体和内部结构,而五个层次又是相互联系而不是完全分隔的。对于研究这个世界的政治理论而言,这五个层次又相当于五种观察世界的视角,从不同的视角出发可以构建不同特色、不同性质的理论。比较争论中的各种国际关系理论,可以归为五个不同的层次:
全球(体系)层次——全球主义(体系)理论(现实主义和新现实主义理论、无政府社会理论、相互依赖论、帝国主义论、依附论、世界体系论以及各种全球主义理论等);
地区层次——地区主义理论(联邦主义理论、功能主义和新功能主义论、国际一体化理论、政府间主义和自由政府间主义理论等);
国家层次——国家主义理论(“民主和平论”、“历史终结论”、“文明冲突论”以及各种对外政策分析观等);
地方层次——地方主义(次国家主义)理论(“多层治理论”、各种次国家政府国际行为理论等);
个体层次——个人主义理论(人性政治论、各种认知理论、女性主义理论以及某些和平研究方法等)。
当然,更多的理论是跨层次的,毕竟层次本身不是理论,而是供人们进行理论思考的空间基础和出发点。另外,仅从空间范围来划分理论并不排除从其它视角出发构建的理论,如文化理论、历史理论等。不过,上面的五层次划分可以给新地区主义理论提供一个初步的支持,也是我们提出新地区主义的核心价值——“地区至上”的前提和基础。
有了这样五个层次的划分,我们就可以为新地区主义确定一个相对重要的位置,也就可以更进一步去探讨它的核心理念或价值。
二、“地区至上”的主要内容
“地区至上”是对新地区主义核心价值的高度概括,集中反映了新地区主义的实质内容,因而它决不是一个空洞的口号。从字面上理解,“地区至上”意味着把“地区”置于我们讨论新地区主义时的最高地位,具体地说就是:新地区主义应该把对地区利益的考虑放在首位,把解决地区性问题列为头等大事,把实现地区一体化、建设地区共同体的目标作为最高目标。这三个方面构成了“地区至上”价值的主要内容,现分述如下:
(一)地区利益至上
对新地区主义的倡导者来说,促进地区利益是其首要的任务。所谓地区利益,准确地说就是地区公共利益或地区共同利益(regional public goods)。地区利益有物质的方面,也有信念和意识的方面即“地区意识”,因为意识到地区利益的存在本身已经构成了地区利益的一部分。
近年来,全球治理的倡导者们提出了全球公共品供给的问题,也就是如何实现全球治理的问题。其依据是:传统上我们最看重的是国家利益,把主权国家意识放在最突出的位置,认为主权是绝对的、至高无上的和不可分割的。研究世界政治的学者一向把目光盯在“国家之间”(inter-state),专注于研究各国对外关系和相互关系。而在全球化加速发展的条件下,国家作为政治经济行为体的相对重要性已经下降,国家管理“国家之间”公共事务的能力也在相对下降,于是人们又呼吁把注意力更多地放在全球治理层面上,以推动全球公共利益为第一要务,但是全球利益的界定和实现在目前阶段存在着一个严重的困难问题,那就是缺少合法性。比较谨慎的学者们则复活了罗伯特·考克斯的“国家的国际化”(internationalizing of the state)这个概念——其中包含三项内容:一是存在形成国家间共识(interstate consensus)的过程,其发展是按照世界经济的需要而进行的,并有一个日益达成的共同意识形态框架;二是参与到这样一个共识形成过程是不均匀的、分层级的,其中美国、日本和德国等扮演主要角色;三是民族国家的反应是,改革国家内部结构,以最好地把“全球共识转化为民族的政策与实践”。(注:Robert W.Cox,Production,Power,and World Order,1987,p.254.Cited fromWil liam D.Coleman and Geoffrey R.D.Underhill,eds.,Regionalism and Global
Economic Integration,Europe,Asia and the Ameicas,Routledge,1998,p.6.“国家的国际化”概念的提出,抓住了非常关键的一点就是试图在民族国家管理失着之后、全球治理实现之前探索出一条居间的解决之道,这与新地区主义的初衷是不谋而合的。这里所说的“国际化”不同于现实主义所最为关注的“国家间”,它是从“国家间共识”形成的高度来看问题,超越了着眼于国家层次的一般分析,尽管它仍赋予国家以重要的角色地位,但实质上表达的是对“国家中心论”的批评。)
考克斯的意图也许是寻找超越国家之外的共同利益,但首先是从共同意识着眼,并且认识到了其中的不均衡问题,这更证明了全球利益的难以界定。由此看来,人们既已不可能只关注国家利益,但又无法清楚地界定全球利益,现阶段又缺乏促进全球利益得以实现的可靠手段,因此就有了寻找地区利益和认同的可能性。欧盟的发展表明,为了合作管理地区性经济社会事务而共投主权,并发展准联邦性的地区制度安排,可以有助于界定地区共同利益并实现一定程度的地区治理。东亚地区经济合作的发展也表明,超越国内治理困境的一条可行办法就是寻找地区共同利益,达成地区共识,并建立一些有效的地区合作框架。
地区利益绝大多数是客观存在的现实利益,比如对于东亚地区来说,发展经济一直是一项十分突出的地区利益,为发展经济而谋求长期稳定的安全环境也是整个地区的共同利益,伴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而产生的改善社会和生态环境的需要又成为新的地区共同利益;此外,在全球化过程中应付来自地区之外的经济政治挑战和压力也使地区内各种行为体的利益紧密关联起来,形成新的共同利益,比如在GATT和WTO的多边贸易谈判中所呈现的。只要有地区的划分存在,就必然有地区利益存在,因为地区从来都不是单纯依据地理界线来划分的,而是一开始就具有共同利益的内涵。甚至有学者干脆仅仅依据共同利益来划分地区,比如曼斯菲尔德和布朗森把相隔遥远的美国和以色列作为一个地区,其理由是美国与以色列之间建立有特惠贸易安排(PTA),因而它们的经济利益是连在一起的,也就出现了一个超越地理空间的“美—以自由贸易区”。同理,他们还把欧盟与非(洲)、加(勒比海地区)、太(平洋岛国和地区)之间基于特惠贸易协定(“洛美协定”)而形成的区域也称为经济意义上的“地区”。(注:See,Edward D.Mansfield and Helen V.Milner,“The New Wave of Regionalism,”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53,3,Summer 1999,pp.589—627.)
有了共同的利益才会有合作,地区合作也正是建立在地区共同利益的基础上。这一逻辑听起来极其简单,而事实上,承认地区共同利益并开展有效的地区合作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二战后的欧洲,虽有很多精英人物认识到欧洲联合以图复兴的必要性,但还是经历了漫长而艰辛的寻找和界定共同利益的过程。整个欧洲的联合最符合欧洲全体人民的利益,但在东西方走向对立和分裂的形势下,这成为不可能的事;西欧的联合显得更加可行,但马上结成联邦或邦联则同样不可能;于是人们便设想从较容易为各国接受的地方——经济领域着手开展合作,但全面的经济合作在短时间内又困难重重,因为首先战胜国与战败国的经济要求就差距甚远;于是,有人就从一个更小但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地方入手,即首先把法德等国的煤钢生产联合起来,建立了“欧洲煤钢共同体”这样一个有限产业的跨国生产经营机构(1951年),后来又成立了“欧洲经济共同体”和“原子能共同体”(1957年),而到1967年才合并成立了“欧洲共同体”,但仍然基本上是一个经济意义上的地区联合体。在此之后的半个世纪期间,从欧共体发展到欧盟,实现三大共同利益基础上的联合即经济联合、共同安全、法律和社会事务联合,这个过程也是一个逐步寻找共同利益并扩大共同利益范围的过程。更准确地说,这样的一个过程也就是一个寻求对地区利益的承认即寻求地区共识的过程。
因此,可以说,倡导和实践地区主义尤其是新地区主义,首先必须把地区利益放在首位,这是开展地区性合作的前提。当然,对地区利益的认识和界定是一个不断扩大和深化的过程。
(二)地区性问题优先
倡导新地区主义的一个主要动机是,世界上的问题已经大量地表现为地区性的了。出色的跨国公司有一种典型的思维方式或口号,即所谓“放眼全球、立足本地”,或者说“全球性思考、本地性行动”(Think globally,act locally)。提出这一口号的关键是认识到了地域差异的重要性(当然其中还包括民族性等其它带有本土性的问题在内),认识到了全球性的生产经营战略必须合于地区性的需要,必须以解决地区性问题为契机。如今全球范围内的政治经济合作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即如何适应各个地区的需要,怎样为解决地区性的问题提供优先方案。地区性问题中有一大部分是民族国家的问题(或者为民族国家所特别关心的问题),也包括一些地方性问题。对于新地区主义而言,解决某个地区或所有地区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乃是其优先议程。
下面我们从经济、安全、社会、环境和政治五个主要领域出发来具体分析一下地区性问题的内容,以说明新地区主义优先解决地区性问题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经济领域经济学家们早已注意到,当今世界经济的两个重要发展趋势,一个是全球化,一个是地区化。从问题的角度看,世界经济既要解决全球化带来的问题,又要解决地区化带来的问题,而且地区化问题的解决相对地具有优先性,不解决地区经济问题就很难解决全球经济问题,反之,地区经济问题的解决往往给全球经济问题的解决创造了条件。比如WTO,它所做的工作除了制定多边贸易规则之外主要就是解决大量与贸易有关的世界经济问题,特别是提供贸易谈判场所和解决成员国之间的贸易争端。但是WTO的这些工作开展得并不顺利,对于它所不能达成解决方案的问题往往是地区性经济组织或协议能够首先解决。WTO也承认地区性经济合作组织在推动贸易自由化方面具有一定的优越性,承认它们所推动的地区一体化进程与WTO所推动的多边一体化进程是“互补的,而不是相互替代”。(注:世界贸易组织秘书处编(张江波等译):《贸易走向未来:世界贸易组织(WTO)概要》,81页,法律出版社,1999。)同样,目前大多数地区性经济合作(包括东亚地区经济合作)进程中,在倡导优先解决地区性经济问题的同时,也承认解决全球性经济问题的重要性,基本上都认为两者并行不悖,主张地区主义的开放性和与WTO的一致性。欧盟的成功主要在于优先解决好了本地区的经济合作问题,实现了关税同盟和内部统一大市场,统一了货币,建立了高层次的经济协调和管理机制,它为全球其它地区性经济问题的解决提供了示范,而且它也注意开展与区外的经济联系,避免成为一个封闭的“欧洲堡垒”。在东亚和太平洋地区,最早由PECC提出了“开放的地区主义”概念,APEC成立后加以继承并发扬光大,特别是APEC曾经在推动GATT乌拉圭回合多边贸易谈判中起过先导作用,而且在后来的发展进程中(主要体现在历次APEC年会上),APEC总是在寻求找到WTO多边谈判僵局的突破口,比如最近的APEC曼谷会议,一个重要议题就是尽力推动WTO重启刚刚失败的“多哈发展议程”;东亚国家与欧盟之间定期举行的“亚欧会议”进一步证明了这种地区性经济组织对开放性的追求。因此,在面向全球的基础上,优先解决好地区性的经济合作问题,并注意与全球性经济合作组织相协调,这就是新地区主义在经济合作领域里的现实追求,也是其优先议程。
安全领域冷战结束之后,国际关系学者们提出了“综合安全”的概念,开始把目光投向世界共同面临的所谓“综合安全”问题——其中包括经济金融危机、难民问题、生态环境灾难、恐怖主义问题、毒品与走私问题等等。不少学者倾向于把这些问题跟传统国际安全问题一起,笼统地放在“全球化”主题之下。(注:王逸舟主编:《全球化时代的国际安全》,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不过,我们可以对此提出两点质疑:首先,是否应当划清楚安全与影响安全的因素之间的界线呢?其次,现实世界上的许多安全问题是否一定发生在“国家”(或“国际”)与“全球”这两个方便的分析层次上?对第一点而言,我们承认很难做到(不过至少我们可以对这种把几乎所有的世界事务都“安全化”的做法提出质疑),但对第二点我们却可以肯定地说“不”。因为综合考虑“全球的”和“国家的”安全问题仍是因袭传统的两层次或三层次分析法,并没有把今天已经日益重要的“地区的”安全问题这个层次考虑进来,因而尚有不够“综合”之处。我们应该看到,今天真正进入全球安全议程中的安全问题似乎只有核扩散问题,而其它安全问题的解决总是隶属于地区性努力的范畴。比如在所谓的“金融安全”问题上,虽然金融的全球化成为重要发展趋势,金融危机的影响也总是波及全球,但目前已出现的金融危机主要还是地区性的,受到最严重冲击的还是地区性金融市场,无论1994年底爆发的墨西哥金融危机还是1997年开始的东亚金融危机,它们在爆发点和影响的主要空间上还是地区性的,并没有酿成类似于20世纪30年代的全球性经济金融危机。欧洲金融市场的独立性从另一个侧面反证了金融的这种地区化而不仅是全球化的双重效应。其它所谓“新安全问题”如生态恶化、石油和水资源短缺、恐怖主义与难民潮等虽然都具有全球性质或影响,但它们基本上都是地区安全所主要关心的问题(当然,全球变暖除外,它具有天然的全球性质和影响,而且仅凭任何一个地区的努力都是不能解决的)。研究安全地区主义的两位外国学者曾预言:“在可见的将来,暴力冲突最有可能起于地区问题上,且被政治行为体从地区而不是全球的视角来考量。应付暴力冲突的努力跟实现秩序和安全的努力一起,将主要是在地区水平上安排和行动。”(注:David A.Lake and
Patrick M.Morgan,eds.,Regional Orders:Building Security in a New World,The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1997,p.5.)总之,军事安全领域问题的地区化是显而易见的,其解决方式也理应以地区性努力为优先。
社会领域关注宏观意义上的社会问题是国际关系学的新动向,甚至可以说,今天的国际关系研究有一种“社会化”的倾向,特别是以温特为代表的社会建构主义理论开辟了国际政治理论的“社会学转向”之路之后,这种社会化倾向更重了。一个突出的例子是,近年来开始受到中国学者注意的“哥本哈根学派”的安全研究中,把国家安全转换为社会安全加以研究,也直接得益于社会学家如安东尼·吉登斯的社会学思想,并把当代社会学中对“身份”或“认同”问题的关注融合进来。社会领域的问题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个是宏观方面的社会问题,主要包括国际政治社会学所研究的文化、民族和宗教认同问题;另一个是微观方面的问题,包括跨国资源利用问题、地区不发达问题、国际恐怖主义问题(不仅仅是军事安全领域的问题)、跨国难民问题、跨国毒品和走私问题、跨国公共卫生问题以及其它共同面临的社会问题等等,其中国际公共卫生问题在不久前的SARS危机中成了牵涉面相当广泛的地区性和全球性问题。宏观社会问题的解决与“共同体”建设是连在一起的,这里所说的“共同体”在国家层次上是指民族国家这个最现实的共同体,在全球范围层次上是指世界共同体这个最不现实的共同体,而地区层次上则是指像现实存在的欧盟和仍属于“想像的共同体”范畴的“东亚共同体”等。(注:另外,在个人层次上“共同体”是指民族、种族、宗教,甚至家族,而在地方层次上则是指像社区那样或较大范围的认同单位。)我们提出研究地区主义,一个主要的意图就是建设地区性的共同体,即着眼于地区层次和地区范围来构建新的认同,因此解决宏观层次的社会问题乃是新地区主义的题中之义。至于微观层次的社会问题,可以根据形势的发展分出轻重缓急,因而一向是开展地区合作的突破口,比如东北亚地区经济合作的各种构想和行动,特别是图们江地区的开放和开发解决的就是跨国资源利用等问题;中国与东南亚有关国家就湄公河流域的共同开发进行的国际合作解决的不仅有跨国资源利用问题,还有地区性的不发达问题;上海合作组织的最初倡议和后来的活动,主要建立在对国际恐怖主义问题的共同认识基础上,它的主要矛头也针对的是中亚地区近年来日益猖獗的国际恐怖主义、民族分裂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请注意这已不仅是微观方面的社会问题了,已经上升到了宏观层次,也因此使得上海合作组织的影响日益扩大,成为一个突出的地区合作组织);不久前的SARS危机诱发学者们开始思考建立地区性公共卫生预警与合作机制的问题,甚至以此为契机开始谈论起“社会地区主义”(注:在这方面最先提出讨论的是庞中英博士,见庞中英:《东亚需要“社会地区主义”》,载《东方早报》,2003年7月18日;《社会地区主义:东亚从SARS风暴中能学习到什么》,载《国际政治研究》季刊,2003年第3期。)的新概念来。总之,新地区主义的“新”就新在其对社会领域问题的关注,不仅关注宏观层次的社会问题,而且关注微观层次的社会问题,而且这两方面是相联系的。
环境领域环境问题除了全球气候变暖(温室效应、臭氧破坏等)之外基本都是带有地区性的问题,当然很多环境问题其严重程度足以引起世界性的危机,如水资源枯竭、荒漠化、森林砍伐、物种灭绝和人口爆炸等等,但现阶段它们毕竟还主要表现在地区性的环境灾难和环境危机上,其解决途径也主要仰赖于地区性的环境合作,如东北亚国家在沙尘暴问题上的合作等。对于我们所研究和倡导的新地区主义而言,另一个重要的方面是,解决地区性的环境问题总是与解决其它领域比如社会领域、经济领域和军事安全领域的问题紧密相关的,这在东亚地区表现很明显,比如开展东亚环境合作总是与地区性贫困问题的解决、与资源开发和利用、与安全领域的互信措施的建立等相联系。而上升到政治领域的环境问题在欧洲也已很突出,比如近年欧洲绿党在欧盟组织中活动的加强等。
政治领域谈到政治,往往与“政府”或“治理”有关。政治领域的问题当然不都具有地区意义,其范围是广泛的,但是,地区问题的政治性却是越来越突出,这也是我们提出加强对新地区主义的研究的根本理由(我们也承认,当我们谈论“地区主义”而不仅仅是谈论“地区化”时,已明显地带有使之政治化的倾向)。简单地说,目前所有由政府出面开展的任何形式的地区合作活动都是政治性的——东亚地区合作最初是从民间的经济合作开始的,但经过二三十年的发展,已经过渡到政府间合作的层次上,越来越带有地区政治性。地区合作的开始阶段往往需要避开某些政治问题,但合作的深入却往往需要以解决某些政治问题为前提,况且,合作活动本身在开始阶段又往往是“政治意义”大于经济意义或其它意义。当我们把政治看作是“治理”的时候,这些情况就更明显了。我们所倡导的“新地区主义”强调地区治理的重要性,在一定意义上也就是把所有地区性问题的解决当作地区性政治来对待。
(三)地区共同体目标至上
新地区主义核心价值的提出始于解决地区问题的紧迫需要,而归结于实现地区一体化、建立地区共同体的长远目标。任何“主义”都有其最高的目标,否则就称不上“主义”,新地区主义亦然。新地区主义在特定条件下必须走功能性的道路,但它终究不是功能主义,功能主义或新功能主义都无法正确概括其本质,这或许是20世纪70年代厄恩斯特·哈斯宣告功能主义失败的一个潜在根源。
把地区共同体作为新地区主义的至上目标,或许会引起不小的误解,因此需要解释一下,我们所说的地区共同体并不是一个静止的“乌托邦”,而是一个变动的目标,形象地说就像是一个“移动靶”(a moving target(注:这一比喻出自于美国一位经济学教授(Manoranjan Dutta)对APEC的描述,具体参见:Manoranjan Dutta,Economic
Regionalization in the Asia-Pacific:Challenges to Economic Cooperation,Edward Elgar Publishing Limited 1999,p.93.)),因而在很多时候我们使用“地区一体化”来表达这一目标。经济学中往往把经济的“一体化”分解成所谓的五种形式或五个阶段,即:关税同盟——自由贸易区——共同市场——货币联盟——经济货币同盟,(注:Peter Robson,The Economics of International Integration,4th ed.,Routledge 1998,pp.5—6.)它们实际上都是经济一体化的政策目标。这种划分在理论上是站得住脚的,而且对实践具有指导性的意义,比如欧盟基本上就是按照这个不断递进的目标路线发展的。研究东亚地区主义的学者一开始容易受到东亚地区合作起点低、步伐慢的迷惑,武断地认为东亚地区主义将不以“共同体”为目标,单纯地强调“化”而故意忽略“一体”,只重视合作的过程。重视过程当然是好事,强调“化”也没有错,但是没有一个长远的目标定位和发展方向(“一体”)却绝对不是好事。当年APEC年会上为了“共同体”(Community)一词的英文首字母大写不大写起过争论,最终以小写达成“共识”,中文文本里甚至讳言“共同体”而称“大家庭”(其实,过时了的“大家庭”一词的消极内涵远远大于更具现代气息的“共同体”的消极内涵),这种灵活处理的做法虽然有利于消除分歧,但在一定程度上却降低了APEC的政治价值(幸运的是,不管当时如何理解和翻译,在APEC历年的报告和宣言中,还是经常能找到community这个词,这为今后重新强调共同体建设埋下了伏笔)。后来APEC的发展表明它在吸取这种没有目标定位的教训,开始探索建立一个自由贸易区(《茂物宣言》是一个转折点),但仍未论及建立经济共同体的问题。当然,亚太作为一个地区的复杂性超出国际经济学理论的一般解释,上述对APEC的指责并不意味着否定它十多年所走过的道路,相反,APEC始终代表着新地区主义的核心精神,包括地区利益至上、地区性问题优先。另外,在东亚地区合作中,我们也看到类似的这种回避共同体目标提法的现象,包括将各国领导人的年度定期会晤界定为“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把东盟与中、日、韩三国的合作机制称为“10 + 3”会议等,其实“10 + 3”会议的目标应该明确,就是要建立一个东亚共同体,其它官方和非官方的协商机制与合作活动也应该明确以推动东亚共同体建设为目标。(注:国内最早提出“东亚共同体”概念的学者是张蕴岭教授,见张蕴岭:《关于推进东亚合作的若干战略构想》,载《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此处引自互联网:http://www.cass.net.cn/y-rwsk/y-rwsk-114.htm。最近他又在另一篇文章中强调了这一主张,见张蕴岭:《东亚合作与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设》,载《当代亚太》,2002年第1期。)当然,在实际的组织运作过程中,权宜之计是必要的,但理论界应该是清醒的,不应该怀疑甚至否定这一目标定位。
宽泛地说,地区共同体的目标其实并不等于经济学中所论述的地区经济一体化目标,它可以是像欧盟那样以建立一个经济、政治和社会完全整合为一体的联盟为目标,也可以是新地区主义的倡导者们所主张的以实现地区治理为目标。也许有人认为“地区治理”比“地区共同体”能更完整地表述出新地区主义的目标定位,但在我们的理解中,它们基本上是等值的概念,因而都可以作为对新地区主义至上目标的表述。(注:当然,我们还是不排除这样的认识,即认为“地区治理”与“地区共同体”在性质上有区别,前者强调地区内部诸行为体的行为有序程度,而后者强调地区内部诸行为体相互关系的紧密程度。)
地区共同体是新地区主义的天然抱负,讳言地区共同体的人只是不希望把这种抱负总挂在嘴边,我们也不希望。“多谈问题、少谈主义”在实践中往往是必要的,但不能丢掉“主义”,只谈“问题”。我们主张在东亚地区合作中深入践行新地区主义,把建立东亚共同体作为最高目标。我们承认,实现东亚一体化的道路是漫长的,东亚共同体的建立绝不可能一蹴而就,但是,确定东亚地区合作的最高目标仍然是必要的,否则就无所谓地区主义,更无所谓新地区主义。
以上对新地区主义的核心价值进行了概括,并从三个方面对“地区至上”的主要内容进行了说明和论证,希望引起理论研究者的兴趣和讨论。不过,最后还必须承认,新地区主义的“地区至上”价值也有其局限性,它并不是普遍价值,不是人们可以在任何场合、任何时代都可以遵奉的普遍真理;它也不是惟一价值,与它并存的还有民族主义的和全球主义的价值观,它们是交叉共存的。
标签:东亚共同体论文; 社会问题论文; 国家经济论文; 经济学论文; 东亚研究论文; 东亚文化论文; 至上主义论文; APEC会议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