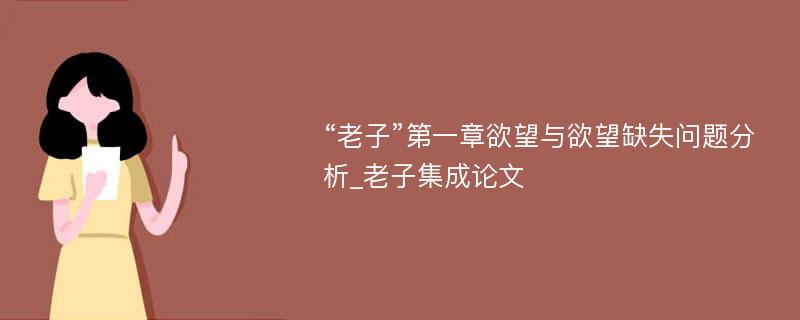
《老子》首章无欲、有欲问题辨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老子论文,无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老子》首章“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一句,通常有两种断句方法,即“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和“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其实汉唐时期的《老子》注疏,都是“无欲、有欲”断句,到了宋代,王安石、司马光、苏辙等人注解《老子》,则提出了“无、有”断句的新见,影响很大。由于马王堆帛书本此句作“恒无欲也,以观其妙;恒有欲也,以观其徼”,说明以“无欲、有欲”断句更加符合老子的原旨,这样,老学史上这个著名的句读问题似乎顺理成章地得以解决了。然而现实的情况却并非如此,到目前为止,很多老子研究者仍然认为应该从“无、有”断句,他们并不以帛书本的句读为然。看来,关于《老子》首章无欲、有欲的理解,并非仅仅与版本和断句相关,而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对此,本文试图结合老学史的发展以及经典诠释的特点来加以辨析。 一、无欲、有欲的两条诠释理路 关于《老子》首章“无欲”、“有欲”的解释,在汉唐时期的注疏中,《唐玄宗御制道德真经疏》较为全面,该疏说: 欲者性之动,谓逐境而生心也。言人常无欲,正性清静,反照道源,则观见妙本矣。若有欲,逐境生心,则性为欲乱。以欲观本,既失冲和,但见边徼矣。徼,边也。 又解云:欲者思存之谓,言欲有所思存而立教也。常无欲者,谓法清静,离于言说,无所思存,则见道之微妙也。常有欲者,谓从本起用,因言立教,应物遂通,化成天下,则见众之所归趋矣。徼,归也。①疏中提出了无欲、有欲的两种不同解释,意思相差很大,但都可以说通。这实际上代表了老学史上关于元欲、有欲诠释的两种不同路向,且两者都有所本。 无欲、有欲的第一种解释,“欲”训为“性之动”,即欲望,有欲乱性,这是一个负面意义的理解,与无欲对立,无欲有欲之间存在明显的褒贬之分。从现存的老学文献来看,这种解释当本于《老子河上公章句》。河上注说:“妙,要也。人常能无欲,则以观道之要妙。要谓一也。一出布名道,囋叙明是非也。徼,归也。常有欲之人,可以观世俗之所归趣也。两者谓有欲无欲也。同出者谓同于人心。异名者,所名曰异。名无欲者长存,名有欲者亡身。”河上注中的有欲即指欲望。值得注意的是河上注对“同谓之玄”的解释:“玄,天也。谓有欲之人与无欲之人,同受气于天。”“玄”一般解为深远玄妙,这样就为“此两者……同谓之玄”的解释带来了一个问题,也就是说,如果把两者解释为无欲有欲,那么无欲尚可谓之玄,有欲怎能称玄呢?因此河上注训玄为天,便避免了这个麻烦。而且,“玄”从字义上看是可以指天的,如《释名·释天》:“天,又谓之玄。”《楚辞·招魂》:“青骊结驷兮齐千乘,悬火延起兮玄颜烝。”王逸注:“玄,天也。”河上注的这一解释,显然是道家气禀说和汉代元气论在老学中的体现。老学史上将“有欲”做负面价值解释的例子很多,但大都能够自证其说。换言之,即使把有欲理解为欲望,也不会构成老子首章诠释的障碍。而其中的关键是对后面“此两者”的解释。如河上注把“两者”解为无欲、有欲,相应训“玄”为天,从而使前后语意贯通。事实上,“两者”所指为何,可以有多种看法,如成玄英认为是指“无欲有欲二观”,唐玄宗疏则说:“两者,谓可道、可名,无名、有名,无欲、有欲,各自其两,故云两者。”此外,“两者”还可以指始与母、妙与徼等等。由于对“两者”的理解具有开放性,故关于“同谓之玄”的诠释在前后语意的连贯上是不存在问题的。 无欲、有欲的第二种解释,即唐玄宗疏的“又解”,“欲”训为“思存”,这样,无欲与有欲也没有了褒贬的区别,两者都是道的体现,如果说无欲是道之体,那么有欲便是道之用。唐玄宗疏解“常有欲,以观其徼”为“从本起用,因言立教,应物遂通,化成天下,则见众之所归趋”,正是道在宇宙、社会、人生等各个层面的具体落实,是道之作用。此解的来源,从现存的老学文献看,应该是本于王弼《老子注》。王注云:“妙者,微之极也。万物始于微而后成,始于无而后生,故常无欲空虚,可以观其始物之妙。徼,归终也。凡有之为利,必以无为用。欲之所本,适道而后济,故常有欲,可以观其终物之徼也。”高明认为注中“欲之所本”之“欲”即思虑之意,指“思虑必须以无为本,然后才能适合于道,有所归止”②,高先生的解释是合理的。唐玄宗疏的“又解”,是在王弼注基础上的进一步引申。此后,沿着这一解释理路的注家也很多。如北宋陈景元注云:“夫虚无之道,寂然不动,则曰无欲。感孕万物,则曰有欲。无欲观妙,守虚无也。有欲观徼,谓存思也。尝谓真常即大道也。无欲有欲,即道之应用也。”(《老子集成》第二卷,第579页)思路与唐玄宗疏的“又解”是一致的,并且把无欲、有欲与《易传》所言“易无思也,无为也,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联系起来,使解释更加全面了。总之,老子无欲、有欲的这一诠释,并非指人的世俗欲望,而是从体道者(通常指圣人)的角度来说的。当体道者内心处于寂然不动、虚静无为的状态时,即“无欲”;及其内心意念发动,感受到外面事事物物的变化发展,并因循自然,随之作为,则为“有欲”。 二、无、有断句的新意与影响 由上所述,汉唐时期关于无欲、有欲的解释实际上并不存在什么障碍,不过,宋代王安石、司马光、苏辙等学者却别出心裁,提出了无、有断句的新解。王安石说: 道之本出于无,故常无所以自观其妙;道之用常归于有,故常有得以自观其徼。……盖不能常无也,无以观其妙;不能常有也,无以观其徼。能观其妙,又观其徼,则知乎有无者同出于玄矣。(《老子集成》第二卷,第559页) 万物既有,则彼无者宜若无所用矣。然圣人常存无不去,欲以穷神化之微妙也。无既可贵,则彼有者宜若无所用矣。然圣人常存有不去,欲以立万事之边际也。(《老子集成》第二卷,第540页)王安石与司马光都强调了道含有无以及有无相生,不可分离。相对来说,王注更加富于哲理的思辨。而且,在老学史上,王安石注早于司马光注。漆侠认为王安石《老子注》当是在嘉祐三年到六年(1058-1061)完成雕印的③,此说可从。王安石十分推崇《老子》,受其影响,他的儿子王雱、门人王无咎、陆佃、刘概等都注《老子》。至于司马光,思想比较正统,由于强烈反对王安石变法,他上疏请求外任,于熙宁四年(1071)判西京御史台,自此居洛阳十五年,不问政事。在此期间,他主持编撰了《资治通鉴》,其《道德真经论》一书,极有可能也完成于该时期。可见,对《老子》首章常无欲、常有欲的解释,王安石是第一个提出以无、有断句的研究者。比王安石、司马光稍晚,苏辙作《老子解》,也采取无、有断句,并解释说:“圣人体道以为天下用,入于众有而常无,将以观其妙也。体其至无而常有,将以观其徼也。”由于王安石、司马光、苏辙在当时都是大名鼎鼎的人物,具有很大的号召力和影响力,故他们对《老子》首章无欲、有欲句的新解,很快得以风行,并产生持续的影响,自宋元明清直至现当代,从者众多。 无、有断句的新解能够得到广泛的支持,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其一,认为更加符合老子思想的内在逻辑。首章标明道是有无的统一,并与后面“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的思想保持一贯。其二,解决了后人所谓有欲不能称作玄的问题。如俞樾说:“若以‘无欲’、‘有欲’连读,既‘有欲’矣,岂得谓之‘玄’乎?”而坚持无、有断句者认为,道含无、有,当然可以“同谓之玄”了。其三,能够更好地彰显出老子思想的哲理。《老子》文本仅仅五千言,但历代注疏层出不穷,既有对原义的疏解,更多是思想的探寻,将无、有作为哲学范畴凸显出来,无疑有助于阐明老子思想的精神特质。 无、有断句的新说尽管得以流行,但也不乏批评者。如朱熹说: 今读《老子》者亦多错。如《道德经》云“名非常名”,则下文“有名”、“无名”,皆是一义,今读者皆将“有”、“无”作句。又如“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只是说“无欲”、“有欲”,今读者乃以“无”、“有”为句,皆非老子之意。(《朱子语类》卷一二五)朱熹肯定了河上公、王弼以来的传统读法,认为自王安石以来兴起的从“有”、“无”断句不合老子之意。又如南宋道士董思靖作《道德经集解》,专门就常无欲、常有欲问题发表了自己的观点: 或问:常无欲常有欲者,前辈多以常无、常有为绝句,今亦不然,则所谓无欲故可,而谓之有欲可乎?曰:圣人之心何尝有欲,今所谓有欲,乃即其起处而言耳。当其静而无为之时,乃无欲也。及其应物而动,虽未尝离乎静,然在于事事物物,则已有边徼涯涘之可见,故对无欲而言有欲也。欲犹从心所欲不逾矩之欲耳。朱文公答沈庄仲之问,亦云。徼是边徼,如边界相似,是说那应接处。向来人皆作常无、常有点,不若只作常无欲、常有欲看。今若必欲以常无、常有为绝句,则是常无未免沦于断灭之顽空,而常有乃堕于执滞之常情,岂足以观妙道之体用哉。(《老子集成》第四卷,第354页)董思靖的看法是比较全面的,也注意到了朱熹的意见。他认为《老子》此句应该以无欲、有欲为读。这里的“欲”,并非指普通人的一般欲望,而应该从圣人体道的角度来理解,这也就是沿着关于无欲、有欲诠释的第二条理路进行解读。“无欲”为圣人内心寂然不动的状态;“有欲”则是圣人意念起动处,感受到外面事物之边徼涯涘。董思靖批评从无、有绝句,将沦于顽空执滞,不足以显示老子之道的玄妙,所以不如从无欲、有欲断句。 不过,从朱熹开始的这些批评意见尚不足以否定无、有为读的解释。如明代危大有说:“或曰:诸家皆以常无欲、常有欲句解之,今独取常无、常有句解者,何也?曰:诸家皆以常无欲、常有欲句解者,理非不通也,但与下文同谓之玄意不相属。若常有欲,岂可谓玄?又曰有欲者亡身,亡身为玄,可乎?又有以常有欲为运用工夫,此说非不妙,亦未免牵强耳。不若常无、常有句绝者平易而理长也。今故取之。”(《老子集成》第六卷,第33-34页)此后,从释德清到近现代的老学研究大家马叙伦、高亨等都力主无、有断句。纵使马王堆帛书《老子》出土后,维护此说的学者仍然很多,有代表性的学者如严灵峰、陈鼓应等。以无、有断句,帛书本无欲、有欲后面的也字怎么解释呢?陈鼓应先生采纳严灵峰的观点:“帛书虽属古本,‘也’字应不当有。”④认为帛书本中这两个关键的“也”字当是衍文。这种简单的处理,自然难以服众,所以廖名春便做了进一步的分析:“以‘无’、‘有’为读,最大的问题是帛书甲、乙本‘欲’后的两‘也’字。根据帛书甲、乙本,的确不能在‘无’、‘有’后断句。我们不能说是帛书的抄手抄错了,因为即使甲本抄错了,乙本也不会错。可见帛书甲、乙本‘欲’后的两‘也’字渊源有自,是其战国时期的祖本已经如此。”这一看法很有道理。但廖名春又认为应该把《老子》首章之常训为尚,并去掉帛书甲、乙本“欲”后的两个“也”字,文本前后的思想才能贯通。他说:“当帛书本与《老子》的内在逻辑发生矛盾时,我们应该优先考虑其内在的逻辑,要以能说清楚文本的思想为先。正确的态度应该是,既要极其重视帛书本,但又不能唯帛书本是从。因此,尽管帛书甲、乙本两句‘欲’后都有‘也’字,我们还是要以尚无、尚有为句,将此段读为:‘故尚无,欲以观其妙;尚有,欲以观其所曒。’”⑤在文本上承认帛书本“也”字的合理性,进行义理诠释时又要强行去掉这两个如此“麻烦”的“也”字,正反映出坚持无、有断句所遇到的困境。 三、《老子》诠释的原旨与发挥 如果没有帛书本的两个“也”字,主张无、有断句未尝不可,但坚持者总是试图否定无欲、有欲读法的合理性,则显然不妥。且不说帛书本从“恒无欲也”、“恒有欲也”断句确凿无疑,而自汉至唐历经千年的《老子》诠释史,都以无欲、有欲为读,这一事实本身就充分说明无欲、有欲应该是老子思想中固有的观念。然而直至现在,并不因为帛书本的出现,无欲、有欲断句就成为了定论,反对的声音还是很大,无、有断句仍然具有其影响力,如李若晖言:“即便承认当依古本旧注以‘无欲’、‘有欲’为读,也并不能等同于这就证明历来关于‘无欲’、‘有欲’的解释是正确的。答案正确并不能证明论证正确。不能就‘有欲’与道的关系提出令人信服的论证,仅仅以帛书本的‘也’字为据断定新说为误,只能激起更强烈的反弹。”⑥事实确如此,随着帛书本的出土,张舜徽、张松如、许抗生、尹振环、李零、高明、刘笑敢等认为无欲、有欲断句合理,严灵峰、任继愈、古棣、卢育三、孙以楷、陈鼓应、廖名春等则仍然坚持无、有为读的解释。那么,到底该如何看待《老子》无欲、有欲这一棘手的问题呢?也许我们应该换一种思路。 从老学史的角度看,自古至今对《老子》的注解无外乎两种类型,即追求原旨与注重发挥。从《老子》文本出发,准确理解和把握其中的含意,是《老子》研究的应有之义。不过,相对于追求《老子》的原义来说,重视个人的发挥在老学史上显得更加突出。朱熹曾说:“《庄》、《老》二书,解注者甚多,竟无一人说得他本义出,只据他臆说。某若拈出,便别,只是不欲得。”(《朱子语类》卷一二五)朱熹的这一论断尽管相当主观,但也说出了部分事实。在中国老学的发展过程中,确实存在一个非常突出的现象,即不同时代有不同时代的“老子”,也许很多学者为《老子》作注疏的初衷都力求其解符合老子的原义,但实际情况是注解者往往自觉或者不自觉地进行一些发挥,将自己本人的思想融贯其中,这种重视义理发挥的注解,在朱熹看来便全是“臆说”,这也是他认为历代老、庄之注,“竟无一人说得他本义出”的原因之所在。然而,重视义理疏解,正是老学独特价值之所在。 从思想史的角度看,疏解《老子》时加上个人的发挥具有必然性。中国思想史的一个特点是重视经学形式,如张岂之先生指出:“中国思想史重经学形式,许多思想家托圣人而立言,通过注解经书来阐述自己的思想,很少独立地发表自己的见解。”⑦儒家通过注解儒家的经典,道家通过注解道家的经典,借此陈述自己的学说,建立其思想理论体系,以满足不同时代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变化的需要。汤一介先生说:“注重历代对《老子》、《庄子》注释,是全面了解中国哲学发展的至关重要问题。”⑧汤先生强调的“至关重要”,便是看到了《老》《庄》注疏的思想史价值。据此,我们对老学的研究,要特别重视《老子》注者的思想创新和时代特色。以此来衡量《老子》无欲、有欲的问题,当然不能否定无欲、有欲的断句方式,而无、有为读,自宋代以来的解释则体现了对老子哲学的深入探寻以及对道家思想的不断开拓,其思想价值确实不可抹杀。 从诠释学的角度看,追求《老子》原旨与对《老子》进行思想上的发挥,两者的交错形成了诠释的内在张力。成中英先生曾指出:“诠释是就已有的文化与语言的意义系统作出具有新义新境的说明与理解,它是意义的推陈出新,是以人为中心,结合新的时空环境与主观感知展现出来的理解、认知与评价。”⑨成先生认为,从道的层面看,诠释不在于把握所有的真理或常道,而在于体现道的本体的活力与创造性,在于以有限提示无限,以有言提示无言,以已知提示未知,进而促进道的理解和体会。成先生从本体层面所进行的这些阐发,可以为《老子》研究提供有益的借鉴。如本文前面所指出,《老子》首章常无欲、常有欲句,无、有为解着眼于阐发老子思想的哲理,也即有助于更全面深刻地理解和体会老子之道。在这个问题上,西方现代诠释学理论也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些启发。如加达默尔强调:“一切诠释学条件中最首要的条件总是前理解,这种前理解来自于与同一事情相关联的存在。正是这种前理解规定了什么可以作为统一的意义被实现,并从而规定了对完全性的先把握的应用。”⑩根据加达默尔的观点,由于“前理解”造成了解释者和原作者之间的一种难以消除的差异,所以经典的解释总是不可避免地带有解释者的主观色彩,形成鲜明的时代印记,解释不可能和经典原意完全一致。因此,经典的诠释虽然首先应该具有准确性,但成功的诠释还必须兼具创新性。具体到《老子》的注解,既要以文本为根据,又要能够做到思想的推陈出新。 大致来说,上述三个方面的因素,使得马王堆帛书本《老子》没有能够完全解决《老子》首章“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的句读问题,也是当前一些老子研究者仍然坚持无、有断句的主要原因。但我们应该认识到,依帛书本无欲、有欲断句,更与《老子》的原貌接近,无、有为读,则不是《老子》的原旨,属于诠释者个人对老子思想的发挥。坚持无、有断句,不应否定无欲、有欲断句的合理性;认可无欲、有欲断句,亦需注意无、有断句在老学史上的思想创造性。 注释: ①熊铁基主编:《老子集成》第一卷,宗教文化出版社2011年,第451页。 ②高明:《帛书老子校注》,中华书局1996年,第226页。 ③漆侠:《宋学的发展与演变》,河北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320页。 ④陈鼓应:《老子注译及评介》,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61页。 ⑤廖名春:《〈老子〉首章新探》,《哲学研究》2011年第9期。 ⑥李若晖:《道之隐显(上)——〈老子〉第一章阐微》,《哲学门》第20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 ⑦张岂之:《中国思想史·序言》,西北大学出版社1993年。 ⑧汤一介:《论魏晋玄学到初唐重玄学》,《道家文化研究》第19辑,三联书店2002年。 ⑨成中英:《从真理与方法到本体与诠释》,见《本体与诠释》,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 ⑩加达默尔:《真理与方法》,洪汉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第37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