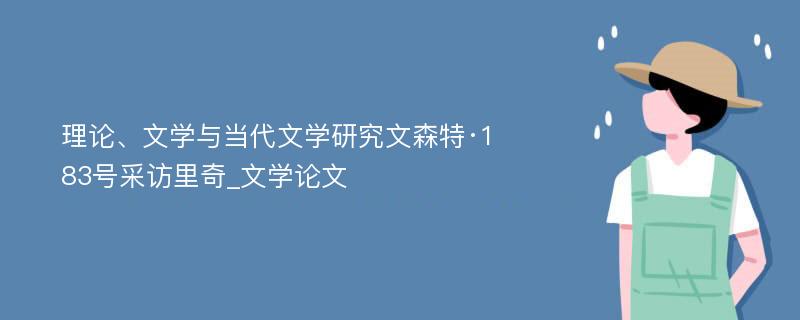
理论、文学及当今的文学研究——文森特#183;里奇访谈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学论文,里奇论文,当今论文,访谈录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马蒂·萨伏莱宁(以下简称“萨”):在美国,60和70年代是理论和理论话语形成并繁荣的年代,一些学者片面地强调理论著作而几乎放弃文学阅读。与此同时,欧洲大陆理论(Continental theory),尤其是法国的理论也涌入了美国。您觉得如今对理论的狂热是已经衰退趋于平静了呢?还是理论只在某些领域占有一席之地?或者我们能否从地域的角度来理解目前的状况,即某些著名的文学系迎合理论热而国内其他的文学系则或多或少走着他们从前的路子?
文森特·里奇(以下简称“里”):回想起来,我曾在20世纪70年代私下发誓再也不写关于文学的东西,而将注意力仅仅集中在理论上面。当时,欧洲大陆理论,尤其是法国和德国的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理论正大量涌入文学系。学者们致力于严肃的理论研究,这在当时是很平常的事。下一代或两代人,即80和90年代的人,他们的经历则完全不同。如今回顾起来,我们将美国70年代的现象称为“宏大理论”(grand theory)现象,而将之后的一段时期称为“后理论”(post-theory)时期。总的说来,理论的当代接受可以分为几个不同的阶段:不同年代的知识分子对于60年代以来的理论热反应不同。
就研究生层次上的理论研究来说,有些美国大学的课程设置和师资力量明显要高于其他学校。有些大学,诸如加利福尼亚大学厄湾分校、康奈尔大学、佛罗里达大学、杜克大学的博士生课程在理论方面有特别的专长。
当然,理论的传播极为广泛。如果你在当今的美国大学里听取10来门本科生或研究生课程的话,几乎每门课上你都会遇到某种理论。理论无处不在,只不过在有些大学里它被更加自觉地嵌入到课程计划中,并且得到了系统地学习。
我定期讲授理论课程,而在我讲授文学课程的时候,也会讲授理论,并且像近几十年来的教授们一样,我会着重突出理论。理论已经胜利了:文学话语和文化研究中处处渗透着理论。或许后理论的传播使之看似衰退了,但实际情况恰恰相反:理论远远没有衰退。
萨:在《30年代至80年代美国文学批评》(American Literary Criticism from the 1930s to the 1980s)一书中,您证实马克思主义在80年代美国学术界受到了重视,并指出在大多数情况下,它不再具有政治影响或实际的社会目标。然而,在文化研究或传媒研究领域,几乎所有理论或课程都被马克思主义理论化了,至少是带有某些蛛丝马迹或是受到了潜移默化的影响。简而言之,您怎么看待马克思主义在文学研究与文化理论界的这种“归化”(“naturalization”)?
里:马克思主义在美国的情形与在诸如芬兰等其他国家的情形不同。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末,马克思主义一直受到压制,在很大程度上这正是我在《美国文学批评》一书中以“美国马克思主义”一章作为当代美国批评史的开始,并以“文化研究”(代表了马克思主义在某种意义上的回归)一章作为结束的原因。美国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官方压制的一个结果就是使我们历经了长时期的左翼政治——包括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工团主义/工联主义(syndicalism/unionism)、共产主义,以及进步党人的主张(progressivism)——而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如今,我们一些主要的左翼知识分子,例如诺姆·乔姆斯基、贝尔·胡克斯(Bell Hooks)、爱德华·赛义德等,他们都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左翼分子。我们的左翼政治是一种松散的联盟,有些人是马克思主义者,而很多人则不是。20世纪90年代,随着新世界秩序(New World Order)和资本主义全球化的胜利,在很多观察者看来,马克思主义似乎已经结束了。然而,我们可以肯定地说,马克思主义还会回来。雅克·德里达在他的《马克思的幽灵》一书中就做了这样的论述。他指出由于资本主义剥削正在世界范围内持续加剧,一个新的工人共产国际正在形成。马克思主义还远未离我们而去。
在文学批评和文化研究领域,马克思主义理论提供了分析的关键元素。我指的是诸如意识形态(ideology)、霸权(hegemony)、经济基础/上层建筑(base/superstructure)、生产方式(modes of production)、商品化(commodification)等概念。这些都是当代批评和理论的重要工具,在许多非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中也是如此。在做后殖民批评和种族研究时,我们会用到霸权理论的常规观点,而很少想到这其实来源于马克思主义。近几十年来,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与归化十分广泛。
美国许多重要的文学批评家都自称是马克思主义者,如加亚特里·斯皮瓦克(Gayatri Spivak)和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年轻一代自称马克思主义者的批评家也正在出现。有些文学批评家属于马克思主义文学团体(Marxist Literary Group),简称MLG,这一团体在学术界拥有几百名成员,他们每年六月和十二月举行聚会。一方面,人们希望马克思主义不曾受过压制,希望过去曾有过某种健康的、广义上的左派政治政党,如果不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话。然而,马克思主义以多种形式(包括后马克思主义(post-Marxism))存活了下来,在大学中尤其如此。我可以说,在可预见的未来,马克思主义将继续生存下去。
萨:您怎么看待与文学研究相关的文化研究体制化问题?这是一种威胁还是一种激励?另外,当我们讨论文化研究的目标及作用时常常会碰到的一个问题是:如何理解这种语境下文化研究的跨学科性?这些主张在多大程度上得到了实现?
里:就文化研究而言,我有几种观察:首先,据我所知,在美国没有一家大学开设文化研究系。有一些相关的课程、协会和中心,但是没有实质意义上的文化研究系。(在英国,情况则完全不同。)美国的机构已经接纳了文化研究,但没有像人们想象或希望的那样以一种重要或永恒方式来接纳。这个问题值得注意的另外一面是:有许多拿到文化研究方向博士学位的毕业生找不到工作,因为在美国这样的工作并不多见。
如果你看看不同大学校园里的各种各样的文化研究形式,你就会发现它们通常是校园内发生的各种事情的晴雨表。例如,当我在普渡大学教书的时候,我刚刚提到过,在文学与哲学博士生课程设置中,我们没能使这一方向对文化研究开放。原因是哲学家们反对。因此,文学组的人提议在英文系设立一个半自治的(semiautonomous)理论与文化研究(theory and cultural studies)方向,简称TCS,在行政模式上自觉地与系里业已存在的语言学方向、创作及修辞与写作方向相对称。关于英文系内半自治方向的模式,我们早有先例。理论与文化研究方向便模仿这些模式,以使这一提议更好地满足系里其他教师的意见。当时系里五十位成员中,有相当一部分人仍然抵制将TCS作为单独的研究方向。
关于普渡大学的理论与文化研究课程是否具有跨学科性的问题,答案既是肯定的,又是否定的。那门课的所有教师都是英文或比较文学的博士,他们没有受过其他学科的训练。(我们曾尝试开设一门涉及哲学系、英文系及其它诸如政治科学、社会学、艺术史、传播学等科系的跨学科课程,但没能办到),在这个意义上说,答案是否定的。但是当我们看到文学系、各种研究中心、机构里研究者们所做的工作时,就会发现这门课确实是与其他学科的混合物,它结合了社会学、传媒研究、理论、哲学等等,从这个意义上看,答案又是肯定的。就我看来,文化研究是后现代学科(postmodern discipline)最精华的部分,是一个交叉的、混合的领域,一个创新的大熔炉。说到此,我们也应该记住,每一个学科都或多或少地参与到其他学科中,这使跨学科性既是一个起点,又是未来的一个理想终点。
萨:在您所主编的《诺顿理论与批评文选》中,起点似乎理所当然地从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开始,尽管在不同的年代里所选的章节不同。翻开目录,我感到您很谨慎地试图将中世纪包含进去,或者更广义地说,从古希腊古罗马时代之后直到16、17世纪,而这个时期经常会被很多人一带而过。您大概想要依照恩斯特·罗伯特·库丘斯(Ernst Robert Curtius)① 的精神试图强调拉丁或拉丁化文学传统,从而将其带入现代时期吧?
里:我小时候就经常听人说拉丁语。和许多生长在天主教传统中的同时代人一样,我也是在天主教学校学习的拉丁语(在各种天主教学校中,我总共度过了13年的时光)。一直到20世纪60年代后期,天主教会会众都是讲拉丁语的。但是再看看美国20世纪的教育史:30年代,我父亲上高中时所学的是希腊语和拉丁语;60年代,我在学校学的是拉丁语和法语;而到了90年代,当我两个儿子上学的时候,他们已经不学拉丁语了,而是学现代欧洲语言(德语和法语)。拉丁语的传统在进入20世纪的同时也接近了尾声。对此,我真是百感交集,既感伤怀旧,同时又对本国语言的胜利感到欢欣鼓舞。
除了语言的问题,中世纪还有许多引人注意的著作。当然,中世纪研究家们对此并不陌生,只是还没有将其作为代表,选入理论与批评文集中。这是以前文集编辑们的一个疏忽。
这里还有一个颇有争议的问题。在我这个年代里,对于“理论”的定义要比过去各个年代的定义宽泛得多。如果把40、50和60年代有代表性的文集放在一起,与后来的文集进行比较的话,你就会明白我的意思了。当我在界定“理论”的时候,我并不仅仅指诗学(poetics)和美学(aesthetics),而是包含了其他许多学科及其分支。这在一定程度上也说明了为什么中世纪是个引人注意的时期。也就是说,对我们当代人来说,“理论”的触角远远超出了诗学和美学的范围,而是伸向了修辞学(rhetorics)、语言哲学(philosophy of language)、评论传统(释经学)(exegesis)、语文学和阐释学(hermeneutics)的领域。正因为如此,我们不仅选择了托马斯·阿奎那和但丁的著作,而且选了奥古斯丁和摩西·麦蒙奈德斯(Moses Maimonides)② 的作品。后者为犹太经文注释提供了理论依据。理论还包括政治理论和教育学(pedagogy)。我所说的政治理论是指在社会中产生影响力的作品的一种职责,而不仅是《理想国》中的政治理论。如果人们看一下克里斯蒂娜·德·皮桑(Christine de Pizan)的作品,就会发现15世纪人们就已经在抱怨女性没有受教育、读书写字的权利,没有阅读文学作品的权利。我们选入了几个与此相关的理论文本,内容涉及地方语言的问题,提出了有关霸权语言和文学与少数民族语言和文学的问题。教育、教学法、语言、文化水平以及政治,这些都是文学与文化史上重要的部分,在文集中都应予以体现。
顺便提一下,《诺顿文选》是从乔治亚斯(Gorgias)开始的,而不是从柏拉图开始。诡辩家的论说观是值得重新思考的,而柏拉图则需要在理论家中重新定位。
萨:让我们来看看20世纪以及您所选的尼采、弗洛伊德、索绪尔等人的作品。这段时期在不同的文集里通常会有较大的不同。离当代越近,差别就越大。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代表黑人、第三世界或后殖民主义观点的声音,如佐拉·尼尔·赫斯顿(Zora Neale Hurston)、弗朗兹·范农(Frantz Fanon)、霍米·巴巴(Homi K.Bahabha),也可以看到法国理论家们的权威地位依然延续,如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雅克·德里达、米歇尔·福柯、埃莱娜·西苏(Hélène Cixious)。尽管法兰克福学派得到了很好的体现,但对德国作家们也许还是略有忽视。而欧洲的现象学阐释学(phenomenological-hermeneutic)传统在书中几乎没有体现,对此我略感吃惊。例如,虽然对弗雷德里克·施莱尔马赫(Friedrich Schleiermacher)、马丁·海德格尔有所涉及,但没有提到伽达默尔和保罗·利科(Paul Ricoeur)。对符号学也是如此,我们找不到埃柯的名字。您能对这些人的入选和落选做些解释吗?
里:我所认为的阐释学是广义上的阐释学,因此,在文集中阐释学的代表人物应该包括但丁、阿奎那、奥古斯丁等人,甚至也包括弗洛伊德。比如说,在弗氏的《梦的解析》一书中,就可以看到很重要的阐释理论。我们还选取了赫希(E.D.Hirsch)、麦蒙奈德斯、施莱尔马赫、汉斯·罗伯特·姚斯(Hans Robert Jauss)的著作。阐释学传统不仅仅局限于现象阐释学,还有一种“一般阐释学”(general Hermeneutics)。在一般阐释学那里,我们除了可以找到18世纪中叶出自德国并一直持续至今的现象阐释学传统,还可以找到释经学、法律阐释学以及文学阐释学。
至于伽达默尔和利科,我们几位编者确实研究了两者的文章,但对于到底选取哪一篇没能达成一致。如果人们看看这本文集阐释学所占的比重,从黑格尔、海德格尔、乔·布莱(Georges Poulet)、萨特、德·波伏瓦直到伊瑟尔(Wolfgang Iser),就知道我们选取了足够的代表现象学传统的作品。尽管利科不在所选之列,我们还有好几个其他的代表人物。当然,选择总是很艰难的,即使是这么大的文集,也不可能囊括所有作品。
关于阐释学还有另外一个现象:在美国,阐释学尤其是20世纪的阐释学是一个较小的流派,只在来自于天主教传统的人群中讲授与研究。如果生活在那种宗教传统之中,并研究文学理论,阐释学也许是最重要、最经久不衰、最有活力的一种思想源流。然而事实上,生活在这种传统之中的人又不得不研究像海德格尔这样的叛教者。比如约翰·卡普托(John Caputo)——维拉诺瓦大学(Villanova University)最主要的天主教哲学家和阐释学专家——他的书论述了海德格尔、福柯和德里达在重新释放活力的阐释学传统中对天主教成员和信奉者的作用。在更大的后现代解释理论背景下的阐释学工程中,我所说的研究叛教者和非天主教徒的意义,在他的书中可见一斑。(在我的《后现代主义——地方效应及全球流动》(Postmodernism:Local Effects,Global Flows)一书中,有一章关于“后阐释学”(Posthermeneutics)现象,专门论述约翰·卡普托。)
关于符号学传统以及你对埃柯未被列入文集表示惊讶一事,有几点需要说明。文集中有关结构主义及符号学的内容已经有很多,从索绪尔、罗曼·雅各布森、列维-斯特劳斯直到雅克·拉康、路易斯·阿尔都塞、罗兰·巴特、诺思洛普·弗莱、茨维坦,托多洛夫和海登·怀特。顺便提一下,奥古斯丁的符号理论也可算在内。关于这一问题还有一点我没说到,就是《诺顿理论与批评文集》是针对谁设计的问题。这本书的读者主要是文学专业的本科生。我阅读埃柯的经验是,他最好的理论一般不能被本科生所接受。而且如今他在美国的影响极小,科学符号学总的来说也是如此。
也许你是在问另外一个更大的问题:在21世纪初的美国学术界,文学符号学的地位怎样?我的看法是:符号学是文学与文化研究一个小分支。许多人正从事叙事学——符号学最主要的组成部分——的研究,他们有自己的组织,每年有自己的年会。但对于普通符号学来说,我的感觉是它主要在传媒和电影研究中传播。社会符号学已经成了文化研究的一个派别。人们可以在传媒和日常文化的章节选段中对符号学的进展有所了解。我指的是巴特、劳拉·马尔维(Laura Mulvey)和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在他们那里,文化代码的批评判断已经被普遍应用并惯例化了,不再活动在先锋派符号学的大旗之下。
萨:“政治正确”(Political correctness)的种种诉求因其多样性和异质性而很难实现,但是就我所看到的,您在这方面的策划是相当成功的:非裔美国文学批评,如芭芭拉·史密斯(Barbara Smith)、亨利·路易斯·盖茨(Henry Louis Gates Jr.)、贝尔·胡克斯;美国土著居民文学批评,如保拉·甘·艾伦(Paula Gunn Allen)、杰拉德·维茨诺(Gerald Vizenor);拉丁美洲视角,如格洛莉娅·安扎尔朵(Gloria Anzaldua);同性恋理论,如艾德里安娜·里奇(Adrienne Rich)、伊芙·科索夫斯基·塞奇威克(Eve Kosofsky Sedgwick)、朱迪斯·巴特勒。我还很高兴地找到了唐娜·哈拉维(Donna Haraway)的《赛博格宣言》(“A Manifesto for Cyborgs”)。您认为这个原则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您目前的编辑工作?
里:在美国这样的背景下,“政治正确”这个词语是右翼分子使用的蔑称,主要用来描述自由主义者和左翼分子的活动和价值的特点。我对这个词感到不舒服。不管怎样,问题是:现在你要将一些选段整理成一个像诺顿文集这样的课本,就目录这一部分,你该对不同的种族和族群、不同的性属和性别,以及不同社会阶级的代表作品表现出多大的兴趣呢?
批评和理论,尤其是20世纪60年代至今的理论,自从后现代诞生的那一刻起就受到来自种族与族群理论、性属与性别理论以及社会阶级理论越来越大的影响,这是我最初的反应。要试图描述当今的理论现状,就必须涉及“政治正确”,无论你愿意与否。这是首当其冲的事。但是一旦面对当代理论界有关种族与族群、性属与性别以及阶级的大批著作时,就产生了谁在历史上是这些领域的先驱的问题。有没有值得回顾的早期阶级、性属和种族与族群的理论?你会发现文集中20世纪以前的部分有与后来20世纪的选段产生共鸣的地方。例如,克里斯蒂娜·德·皮桑的部分,就有关于女性性属的问题。显然,这一问题在后来的19世纪和20世纪都再次出现。这就是在历史上所熟知的众多“政治正确”例子中的一个。
你问我对此事的看法?好哇!如今我们这些后现代派认为文学和理论不仅局限于冷战时期形式主义批评所认为的狭隘过时的经典,还应包括新出现的其他种族和性属的经典。现在,美国土著文学(包括其口头文学)和非裔美国文学(包括其口头文学)都被视为是扩大了的、多层面的文学传统的一部分。现代狭隘的把文学限定在18至20世纪中叶的纯文学定义在今天已经受到了各方面的质疑。对我来说,这是一种解放,而且我可以毫不迟疑地说,这是一件好事。
萨:斯图亚特·摩尔思罗普(Stuart Moulthrop)是你们几位批评家中最年轻的一位(生于1957年),而且负责文集结尾的一章。他那篇《你说你要一场革命:超文本及传媒法则》(“You Say You Want a Revolution:Hypertext and the Laws of Media”)的文章使读者体验到了文本的新形式和新空间,走近了数码产品和互联网。撇开文集不谈,您认为这是文学研究未来的走向吗?还有那些几乎一生都在教授纳撒尼尔·霍桑和弗吉尼亚·伍尔夫的文学教授们,或者那些以维多利亚时期小说为专长的教授们,他们会怎么样呢?
里:我在美国文学系的经验告诉我,当新事物到来时,我们不是抛弃原有的东西,而是把新事物添加进来。覆盖的原则是建立在增加而不是抛弃的基础上。在任何时刻,任何一个有代表性的英文系的教师群体,根据不同的年代划分方法,总可以分成四代或三代人。假设每年调离和新聘员工的更替比率为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教师队伍总是在不断的调离调入。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这些不同年代的人都在同时上课:一些人按照50年代“传统”的方法讲授维多利亚时期小说,而另外一些人则在按照21世纪的模式讲授超文本。而我的感受是:正在发表的“老一代”的研究,例如19世纪美国研究或者对于维多利亚时期小说的研究,已经受到了理论和批评的影响——如果在教学前沿不是如此,在研究和出版前沿肯定如此。一位老一代的教授可以用福柯的理论来分析狄更斯的小说。事实上,我并不认为快速的(理论)变化会使大批的老一代教授们无以容身。也许应该如此?而且发展不平衡的现象已经开始出现了。有些科系(我不具体指名了)在70年代对理论的潮流采取了坚决抵制并加以拒绝的态度。有些直到90年代才开始清醒,决定对课程大纲不设理论课和不聘用理论界教师的做法采取些措施。你可以根据一个系的教师和这个系所代表的及未代表的东西,包括标准时期、流派覆盖面和理论,来确定这个系的发展历史。每个系都有其独特的历史和轮廓。
你还问到文学研究的走向问题。我认为我们研究的文本经典和采用的批评方法还将继续扩大,并且将被分成不同的种类、范围和模式。文学的定义已经被大大地扩展了,而且将继续扩展。它不仅包含了经典文学,而且还包括少数民族文学和通俗文学(通俗爱情故事、哥特式恐怖小说、科幻小说、神秘小说、侦探小说及西部文学)。在这种背景下,可以想象,超文本小说很快就会被纳入文学范畴,更不用说其他将会出现的新形式。文学及经典的定义扩大是后现代时期的一大特点,但这并不意味着文学类别和形式的等级就被推翻了。在文学史家那里,史诗与悲剧的地位仍高于散文诗和小说。近几十年来,我们进入了一个极度扩展的时代,刚好与先前文学史将文学限定在18世纪至20世纪中叶的极度收缩相反。受到一些激烈的反对是预料之中的事。经典文本的范围越大,所使用的分析方法越多,我们就越有可能遭遇防守方的抵制(比如那些试图复原经典并限定批评方法的人)。但是一种“重新审视”将会持续下去。这尤其需要重温传统并赋予其新的内容。例如,用酷儿理论(queer theory)解读莎士比亚的作品就是一种重新评价莎氏并赋予其新的面貌的方法。要直接回答你关于文学研究走向的问题,我认为未来十年中,老的经典和老的文学类型等级将继续存在,但同时对它们予以“提高”和“重新审视”并赋予其新的内容的做法也将与之并存,将会有新的话语添加进来,同时也会有试图还原文学研究的努力,更进一步的扩展和分割将会继续。
有时我感到担心和疑惑的是,在美国的环境中那些半自治课程,例如修辞与写作、语言学、创作、电影研究及文化研究会有可能脱离原有的文学研究系或英文系。如果它们开始大规模朝自己的方向发展并建立自己的科系,这一方面是件好事,但另一方面,失去了现有的研究内容,文学研究系会感觉外部势力使它变得残缺和狭窄。为了适应这种新的现实,新的意识形态就会产生,结果可能是,文学研究又缩回到更为保守的模式中去。
萨:20世纪80年代,关于经典的辩论达到了顶峰。经典构成的问题成了“热点”,那种普遍通用的价值观和亘古不变的标准观受到了挑战。与此相应的,在阿兰·布鲁姆(Allan Bloom)的《走向封闭的美国精神》(The Closing of the American Mind,1987)和E.D.赫希的《文化修养》(Cultural Literacy,1987)中,两位作者分别用不同的方式表达了他们对西方文明的状况、尤其是对美国文化的担忧与焦虑。经典和经典构成在美国现今仍然是在讨论的问题吗?这一问题与文化差异和文化多元主义这个更大的问题有什么关系?
里:在美国,关于经典的战争已经“结束”——经典已经被改变并扩大了。可是这项工作还将持续到未来。值得注意的是,围绕着经典问题,我们还有其他许多需要为之奋斗的问题。正如你刚刚提到的,阿兰·布鲁姆和赫希在80年代末的著作很有影响,二者都极力地为“伟大的传统”辩护,声明我们应该研究伟大的作品,那才是最重要的事情。尽管两本书的核心内容都是保卫伟大的传统,它们又有着相当大的不同。例如,布鲁姆的书充满了对大众文化,尤其是摇滚乐和电视的敌意。而且布鲁姆还暗示说文化研究毫无用处。布鲁姆的书以一种丝毫不加掩饰的方式提出了高雅文化与低俗文化的问题,即安德里亚斯·海森(Andreas Huyssen)所说的“大分水岭”。我把布鲁姆的书看作是反后现代或前后现代的(anti-or pre-postmodern),因为它一方面企图保持伟大的传统,另一方面又排斥大众的、通俗的、中产阶级趣味的和“低俗”的文化。
而赫希的书主要表达了他对大学前的学生,包括小学和中学生,该得到什么样的教育的关注。文学理论家专注于大学前教育及教育方法,这已经不是第一例。I.A.理查兹在40年代就曾有过同样的经历。诺思洛普·弗莱曾为一系列的文学课大纲制订了一套教材。如今美国高中所讲授的是伟大传统和多元文化传统的一个混合体。如果你按照学校系统学习美国文学或英国文学,你两者都可以学到,而不是非此即彼。赫希继续指出,目前对通俗文化的介绍太多,而对文化传统的关注还不够。
如果考察一下二战后期美国移民运动的话(我们有一段很长的移民史,而且颇为复杂),这段时期有好几次大的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潮。大量的移民进入这个国家,每年大约接近一百万人。今天美国文化的多元意义比20世纪初我的祖先从爱尔兰和西西里移民来时要强烈得多。我不认为经典会在不久的将来得到净化,也不认为我们在20世纪末所参与的后现代多元文化的转向会被完全清除。我期待着经典会得到进一步的扩大和更细致的划分。极端民族主义者、民粹主义者、种族主义者以及反移民的“英语优先”语言运动都不会阻止变化的潮流,尽管新保守主义者们的反补偿法案(或译“平权法案”AntiAffirmative Action)的诉讼以有限的进展在各地获得了一些胜利。
萨:我们再来谈谈世纪之交美国文学现象。随着某些话题的流行、某些奖金的出现,以及学术领域或文学作品的分支变得热门,某些当代作家受到了极大的关注。对此您有何评论?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非裔美国女作家流行之后,又出现了对其他族裔文学的兴趣,如美国土著文学和亚裔美国文学。在很多场合,女性作家也开始在会议上发言了,如莱斯利·马门·西尔科(Leslie Marmon Silko)、路易斯·厄德里奇(Louise Erdrich)及汤亭亭。
里:我认为后现代全球化在美国文学这个层面上是一种文学“跨国化”行动,既有来自“内部”的,也有来自“外部”的。换句话说,如果你问我什么是美国文学,我的答案是,美国文学是由很多的文学组成的。有美国土著文学、亚裔美国文学,还有拉美裔美国文学等等。我们可以列出一个很长的单子。它们中的每一个又都包含了许多不同的文学传统,比如说亚裔美国文学之内又包括菲律宾裔美国文学、华裔美国文学、日裔美国文学、韩裔美国文学等将近24种不同的传统。这些类别的文学有时不仅是用英文创作,而且还用亚洲的语言。例如,有三万越南人就居住在俄克拉荷马州,他们是70年代越南战争之后来到俄克拉荷马市的。他们之中就有人用越南语写故事、写诗。我们把这又称之为什么呢?越裔美国文学。意大利美国文学、华裔美国文学和墨西哥美国文学也有同样的情况。哈佛大学最近刚出版了一本由的由马克·谢尔(Marc Shell)和沃纳·索勒斯(Werner Sollors)编写的文集:《多种语言美国文学文集》(The Multilingual Anthology of American Literature,2000)。书中收集了几十种以非英语为母语的语言创作的美国文学作品,是一本开拓性的著作。这就是我所说的美国文学来自“内部”的跨国化。
另外,还有来自“外部”的后现代全球化现象:英语文学(Anglophone literature)、黑色大西洋艺术(Black Atlantic Arts)、法语文学(Francophone literature)、中美洲(MesoAmerican)和美洲(Inter-American)文学。最后这一类,美洲国家之间的文学,包括加拿大、美国、中美洲以及作为一个统一地区联合体的南美洲本土文学。它们之间的共性多于它们恰好成为其中一部分的“国家”文学的共性。这就代表了来自“外部”的跨国化,如果我可以这样表达的话。因此,是的,在文学界,我确实看到了一些新事物,很显然,新的作家将会而且正在出现。
萨:接下来我们可以谈谈主流文学吗?如果说品钦研究最狂热的时期已经过去,还有没有其他作家可以向他的地位提出挑战?也许唐·德里罗(Don DeLillo)可以?保罗·奥斯特(Paul Auster)在圈内的地位如何?
里:你实际上是在问,谁是美国下一位伟大作家,下一位伟大的小说作者、小说家?对不对?当今很多出版的文学研究成果,至少是以专著形式出版的研究成果,都不是以单一的作家为研究对象的。导师们经常建议博士生不要专门写一位作家,因为这样的书卖不出去;这种方式太过时了;出版商对此不感兴趣。常见的是关于流派和运动的著作,如关于非裔美国女作家、亚裔美国小说家,或者是关于某个主题和话题的,如当代文学中性属受压制或被忽视的问题。
如果以不同的文学类型为着眼点,我们会得到完全不同的结果。以美国诗歌为例,直到20世纪中叶为止,美国诗歌主要集中在东北部主要城市和沿东海岸线的地带,尤以纽约为中心,可是现在已经遍布全国了。这是一场真正的爆发,也是后现代无序性在文科内体现的一个例子。与此同时还有通俗音乐产生所带来的现象。在过去,一个摇滚乐团要想出名就得有一家代理公司,找到一个主要的唱片商标,进行特点鲜明的俱乐部巡回表演等。但是现在人们只需要用较少的钱就能制作出自己的CD,安排自己的演出,从而在某一个地区成名,所有这些都不需要太费周折。通俗音乐的生产方式改变了,结果是各地到处都有乐队在制作自己的CD。诗歌也一样:有数不清的小型诗歌杂志和诗歌朗诵会。诗歌的生产方式发生了变化。比起过去,现在有更多的人写诗,出版诗集。就看看美国有多少创作培训班吧。我们还有很多当代诗歌选集也见证了这场诗歌热潮。注意,我还根本没有谈到关于诗歌的说唱及其他有活力的现象。同时,传统的那种由大商业出版社制作并发行的单一作者的诗集正在消失;这些东西不挣钱,而是赔钱。戏剧的情况就不一样。戏剧需要剧场和剧组演员。虽然现在地区性的和社区性的戏剧要比起过去,比如说中世纪繁荣得多,上演戏剧还是太昂贵了。假如我们不把电视(尤其是有线电视)和电影剧本算在内的话,当代戏剧没有像诗歌一样经历了无序的(激增)。小说自有其复杂的情况,这里我就不多说了。
你问谁是美国小说界下一位伟大的作家,也许我们应该首先考察一下小说界本身?对我来说,目前美国文学圈内最有意思的现象就是:诗歌的继续激增,戏剧繁荣的地域化和分散化,族裔文学的兴起,通俗文学的扩张,特别是后现代时期理论的发展,但是并没有多少关于谁是最主要的小说作者的讨论。你遗漏了托尼·莫里森和其他像索尔·贝娄这样的获诺贝尔奖的作家。但是我宁愿不去挑出一个能成为下一个伟大小说家的胜利者。作为对这一话题的最后评论,我只能说保罗·奥斯特在欧洲的声望似乎比在美国更高一些。也许欧洲会参与选择谁是下一个最主要的小说家。
萨:您能不能超出《诺顿文选》的框架对美国文学理论和文学研究的未来做一下预测?它的未来走向如何?正在出现的领域都有哪些?以劳伦斯·布尔(Lawrence Buell)的关于梭罗的书《环境想象》(The Environmental Imagination,1996)为例,您认为这种以生态批评的形式出现的对环境问题的关注是否正在增长?加里·斯奈德(Gary Snyder)也为这种方法提供了大量的资料。
里:请允许我做点预测:将来会有更多令人印象深刻的网络文学和超文本作品。文化研究也会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制度化。一些运动、方法、流派和团体将会继续生机勃勃地发展下去:其中最显著的将是酷儿理论、后殖民研究和新历史主义研究,以及美国土著文学研究、亚裔美国文学研究、拉美裔美国文学研究。
如果说到批评和理论发展的主要模式的话,20世纪30年代到60年代主要是新批评(文学形式主义);然后是70年代和80年代的后结构主义;80年代末到现在,文化研究是主要的研究模式。在这些模式之中,又有各种各样的选择和逆流。如果你问我下一个主要的模式、文化研究之后是什么,我没法回答;我看不到任何的迹象。我想文化研究还有很长的路可走。
虽说如此,但又必须指出,新的领域和新的研究分支正在形成和发展。身体研究和酷儿理论就是两个例子。还有科学研究和休闲研究。另外还有生态批评、视觉文化研究、全球化研究等等。这些都是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新领域(或亚领域),很快它们就会以“自治”的面貌出现。关于你特别问到的生态批评,我预感它不仅会成为一个半自治的亚领域,而且还会成为全球化理论与批评的重要分支。
一种新的纯文学主义(belletrism)(借用杰弗瑞·威廉(Jeffrey William)的术语)也会以几种形式得到发展。有好几位主要的批评家都明确无疑地从艰深的理论批评转向个人批评及自传记写作。亨利·路易斯·盖茨和简·汤普金斯(Jane Tompkins)就是其中两个主要的代表。这一新的文学至上主义还有另外一个方面,随着二战后美国生育高峰期出生的那些人慢慢衰老,逐渐退休,可以预计他们的文学研究观将会走上保守的阶段,重新返回到对传统经典文学的研究。几年前我们就看到弗兰克·伦特里夏(Frank Lentricchia)出现在《交际语》(Lingua Franca)杂志上,声明自己将不再从事理论研究,而是将重点放在阅读和讲授文学上。这暗示了在未来的岁月里可能出现的一种转向,对此我不会感到惊奇。
〔译者单位:郝桂莲,四川大学外国语学院;赵丽华,西华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注释:
①库丘斯(1886—1956),德国文学史家、法文教授。著有:《巴尔扎克》(1923)、《新欧洲的法国精神》(1925)、《詹姆斯·乔伊斯》(1929)、《欧洲文学与中世纪拉丁文》(1948)等。
②麦蒙奈德斯(1135—1204),犹太哲学家,生于西班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