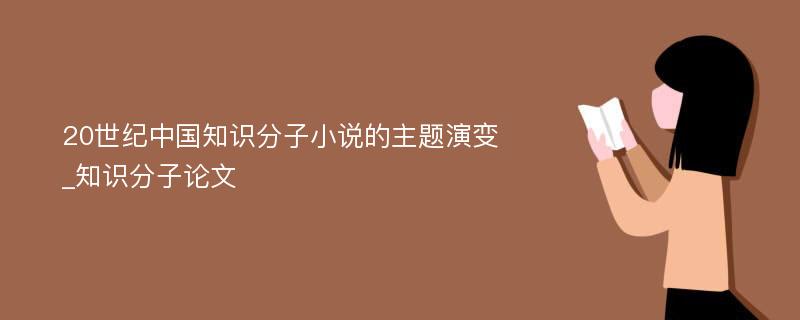
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题材小说的主题嬗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知识分子论文,中国论文,题材论文,世纪论文,主题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6924(2007)06—081—086
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在风云变幻中完成了从古代士大夫到现代知识分子的转型。历史的生动成就了文学的精彩。知识分子命运的不断变幻也促使知识分子题材小说的主题随之嬗变。
五四时期,在“民主”与“科学”的旗帜下,“启蒙”成为主流话语。知识分子题材小说着重凸显启蒙的象征——知识分子张扬个性,反叛传统,努力改造社会的人格精神;同时也深度关注知识分子背着历史的重负在时代洪流中因屡遭失败而困惑彷徨的现实处境。30年代,在“革命”的激情感召下,知识分子走向了社会革命。不少小说主要表现他们在革命历程中“幻灭”、“动摇”、“追求”的艰难而曲折的心路历程。抗战爆发直至建国前夕,知识分子题材小说把表现的重点放在了中国知识分子在民族独立和解放的历程中苦苦的人生挣扎和人格的复杂变化上。“十七年”及“文革”时期,知识分子逐渐失却自我身份与自由人格,成为被“改造”的群体,小说演绎的是他们在改造中丧失了独立思考的勇气,因恐惧而放弃了自我言说的欲望,最终成为忏悔者的悲剧。进入新时期,中国社会由政治社会向经济社会大转型,知识分子的思想地位与经济地位严重蜕变,他们“由时代的中心转到时代的边缘”[1]。小说着重揭示的是知识分子在经济大潮中生活的窘困、价值的失落以及走向世俗甚至在世俗中堕落的生存困境。若依时代的推演而论,大致可分为四个板块。
一、五四的“启蒙小说”:“狂人”的“呐喊”与“零余者”的“彷徨”
一部中国近代史,就是一部中华民族的灾难史。国家的孱弱与民族的衰败,使世纪之初的知识分子们以极大的热情接受了西方民主思想,鲜明的树立起民主和科学两面大旗,向封建主义的思想文化展开猛烈的进攻。他们主张解放思想,尊重科学,对文化传统进行重新评价,掀起了声势浩大的五四新文化运动。
五四新文化运动从本质上讲是反封建蒙昧主义的思想启蒙运动,文学上与之相应的是启蒙主义文学观。考察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题材小说,启蒙无疑是主流话语。作为启蒙的象征,知识分子的觉醒与觉悟,怀疑与反叛,奋起与失败,困惑与彷徨,孤独与苦闷,都是整个五四时代小说所要倾力表现的内容。因而,从文体精神上讲,五四时期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小说可以概括为“启蒙小说”。
五四时代,率先觉醒的知识分子以启蒙为主要目的,在思想界表现出反抗的勇气和战斗的姿态。鲁迅便将“立人”的希望首先寄托在高度敏锐的知识分子身上。他以自己深刻的笔触在《呐喊》、《彷徨》里为中国现代文学刻画出第一组觉醒的叛逆者形象。《狂人日记》里的“狂人”,《长明灯》里的“疯子”就是典型代表。狂人生活在一个充满杀机的空间里。他从“易子而食”、“食肉寝皮”的记忆联想开去,有了一个触目惊心的发现:“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吃人’!”由此开始,狂人便开始了强烈的反思和大胆的叛逆。面对因循数千年之久的传统思想,他尖锐地提出了“从来如此,便对么”的质疑,将怀疑和否定一切的五四时代精神呈现在人们面前。同时,狂人以空前的现代理性精神,以对民族命运忧愤深广的情怀,将彻底扫荡“人肉筵席”的使命寄托在年轻一代身上,发出了令人振聋发聩的呐喊——“救救孩子”!而“疯子”的形象则表明觉醒的知识分子已由思索的一代向着行动的一代过渡。因为要吹熄“吉光屯”那盏象征封建统治的“长明灯”,“疯子”遭到禁闭,但“疯子”高喊“我放火”!并且“在地上、在空中、在人身上迅速地搜查,仿佛要寻火种。”叛逆者的战叫,改革者的奋起,在几千年黑暗的历史隧道里无疑就是一粒“火种”,一粒启蒙的火种。
然而,也正如鲁迅所指出的,五四时代知识分子中“有醒着的,有睡着的,有昏着的,有躺着的,有玩着的,此外还多。”[2] (P210)历史也告诉我们,中国知识分子是一个非常特殊而重要的群体,他们既怀有“达则兼济天下”的伟大爱国情怀,同时,也有内在性格的复杂性和软弱性,群体的人格独立性较为欠缺,容易在动摇中成为孤独、彷徨、心理焦虑的“零余者”。当衰瘦、颓唐的吕纬甫现身于《在酒楼上》的时候,很难让人想象十年前他是一个热情的、充满理想的、“敏捷精悍”的“改革家”。冷酷的现实磨尽了他的锐气,使他变得行动迂缓、反应迟钝,对生活“敷敷衍衍、模模糊糊”,再也难以奋起。而《孤独者》里的魏连殳则更“像一匹受伤的狼,当深夜在旷野中嗥叫,惨伤里夹杂着愤怒和悲哀”。鲁迅是要借此谱就一曲曾经觉醒的知识分子面对强大无物之阵时的悲歌,也一如自己“彷徨期”的精神写照——“寂寞新文苑,平安旧战场;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
郁达夫笔下的一群知识分子也都曾极力张扬个性,热情追求自由与爱情。但人生的不济,落魄的现实处境,使他们不得不时时陷于“性的苦闷”和“生的苦闷”之中,最终成了“生则于世无补,死则于人无损”的“零余者”。《风铃》里的于质夫、《春风沉醉的晚上》里的“我”、《茑萝行》中的“我”,都是怀着“到社会去奋斗”的抱负从日本留学归国的,但从他们踏上中国领土的那一刻起,面对的就是失业。“失业”使他们走上穷途末路。同样,丁玲《莎菲女士的日记》中的莎菲,也是一位忍受着巨大心灵苦闷的叛逆者。
知识分子的这种现实处境,打上了鲜明的时代印记。五四时代,随着封建体制的解构,中国社会开始了各个层面的转型。社会的转型引起了中国社会经济结构的动荡,导致知识分子社会生存景况急剧恶变,他们甚至成了“有识无产阶级”(郁达夫语)和社会的“零余人”。“零余人”的现实处境,导致的是知识分子严重的心理不安和不满。他们内心焦虑,“一种在内心逐渐增加、无所不在的孤独感,及置身于充满敌意的世界的无助感”也便油然而生。[3] (P57-60)
二、左翼的“革命小说”:“十字街头”的徘徊与“围城”中的偷生
1930年3月,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标志着中国文学从“文学革命”转变到“革命文学”时代。这个时代显著的特征是五四所开启的有相对思想自由的氛围消失了,文学主潮随着整个社会的变革而变得空前的政治化;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在相当程度上决定着此后二三十年间文坛的走向,并且左翼文学为选择最理想的文学形态而积极推进着文学的“一体化”。因此,这是一个革命文学主导文学格局的时代。就小说创作而言,政治话语异常鲜明是其突出特点,可谓之“革命小说”。“革命小说”在表现知识分子题材时,毫无疑问地要以政治为内核。
如果说五四是思想革命、个性解放的时代,那么,30年代初期则进入了社会革命、社会解放的时代。知识分子的思考中心发生了重大转移:从对人的个人价值、人生意义的思考转向对社会性质、出路、发展趋向的探求。在探求中,知识分子对革命的狂热使他们迅速地“左倾化”和“革命化”。
现代知识分子的左倾化和革命化复杂而曲折。革命之初,他们为中国社会的变革所感动,对新兴的革命感到兴奋,为寻求民族振兴之路而苦苦求索;但他们投身于革命时仍有追求个人幸福的冲动,在急需行动和服从的年代仍耽于不切实际的幻想,这使他们往往感到彷徨、苦闷,因理想幻灭而产生立场的动摇。在革命的“十字街头”,在人生奋斗路上,他们徘徊着,挣扎着,心路历程艰难而曲折,充满了浓重的悲凉色彩。
茅盾的《蚀》三部曲,是第一部成功地反映现代知识分子心路历程和人生抉择的作品。作家以大革命前后某些小资产阶级知识青年的思想动态和生活经历为题材,描写了他们在幻灭、动摇、追求中寻求人生的苦难历程以及最终失败的结局,将苦难时代青年知识分子所经受的难以忍受的精神折磨,所经历的曲折、痛苦生动地展示在人们面前。《虹》也通过时代女性——梅行素从五四到“五卅”时代大波澜中的种种挣扎、反抗,写出了知识青年从单纯反抗封建婚姻对个人的压迫到投身群众斗争行列的曲折历程。叶绍钧的《倪焕之》,则以小学教员倪焕之在人生道路上摸索探求中的悲剧:追求——失败——再追求——再失败为主线,勾勒出自辛亥革命前后到五四运动、再到“五卅”运动和大革命失败十余年间知识分子的价值追求与人生困惑。同样,柔石的《二月》也表现出对知识分子苦闷彷徨的审视。作为知识分子,肖涧秋是有自己独立的信仰的。但痛苦的人生经历使他感到人间的孤独。这铸就了他悲哀、抑郁,而又略带孤傲的个性。他身处大革命时代,却游离于革命潮流之外,漂泊6年,对社会现实深感失望,却又看不清斗争的方向。他希望用单纯的人道主义和朴素的民主思想去改变现实,但每每事与愿违,思想性格渐趋颓唐消沉。芙蓉镇的是非似乎让他有所醒悟,他选择了离开。作者也似乎暗示主人公即将走向新路,但“二月”的寒意尚未彻底褪去,肖涧秋们的振作还有待时日。
在整个抗战及其后续的年代,知识分子则成了一个社会处境十分尴尬的群体。一方面,民族独立与解放的伟业迫切需要作为社会精英的知识分子担当重任;另一方面,历史的基因却使知识分子人性本质中脆弱、虚伪的一面在血与火的洗礼中暴露无遗。他们要么自视清高、高蹈孤傲,要么投机钻营、自私自利,要么消极处世、软弱无为,躲进“围城”,苟且偷生。时代与知识分子的要求和知识分子的实际人格状态发生了“错位”。于是,40年代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形象渐渐由觉醒者、启蒙者而成为了被讽刺的对象。
在钱钟书的《围城》里,一群现代知识分子变异扭曲的人格遭到了无情的揭露:李梅亭的满口仁义道德,满腹男盗女娼;韩学愈的内心龌龊与招摇撞骗;高松年的道貌岸然与老奸巨猾……构成的是一幅现代儒林的百丑图。而方鸿渐、高辛楣、苏文纨等刚刚留洋归来的学子们,尽管他们接受了西方文化的影响,但他们在现代中国显得是那样的“弱智”。于是,他们有的沉沦,有的堕落,有的一事无成,在人生与爱情以及传统文化秩序的围困中消磨着人生,完全是一群无用的“无毛两足动物”。师陀的《结婚》对胡去恶由最初的正直、诚实到后来的自私堕落、投机冒险进行了冷峻的嘲讽;李劼人的《天魔舞》、张恨水的《魍魉世界》对白知时、西门德由辛勤工作的教员、心理学教授,转而成为投机商、暴发户的人格操守变异满含不屑;张天翼的《华威先生》,更是以明快热辣、冷峭尖锐的笔调对虚伪而缺少人格的知识分子进行了无情的抨击。
鲁迅说:“我觉得文人的性质,是颇不好的,因为他智识思想都较为复杂,而且处在可以东倒西歪的地位,所以坚定的人是不多的。”[4] (P593)鲁迅的论述足以剖析40年代知识分子的灵魂。
三、“十七年”及“文革”的“改造小说”:灵魂的改造与身份的丧失
1949年,新中国的隆隆礼炮,振奋了知识分子的实用理性和政治激情。他们欣喜地呐喊:“我们再不是奴隶,再不是任凭命运摆布的可怜虫,我们再不用悲叹,再不用流泪,我们要用自己的双手来铸造我们的未来,一切失去的,我们都要夺回来!”[5] 理想的现实化与现实的理想化使知识分子迅速沉入精神的“乌托邦”。同时,《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关于高级知识分子待遇问题的意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使知识分子产生了一种被新的权力系统接纳的“归属感”。这个时期,费孝通先生曾称之为“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
然而,早春时刻,乍暖还寒。知识分子应该料想得到,新的时代,他们的介入必须以改造为前提。毛泽东在革命战争年代就曾说过:“拿未曾改造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相比较,就觉得知识分子不干净。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我们知识分子……得把自己的思想感情来个变化,来一番改造。”[6] (P851)为了努力建设一支“完全新型的无产阶级文艺大军”,50年代至60年代,中国共产党人一直进行着知识分子的改造。意识形态领域发生了一系列与知识分子命运息息相关的运动: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对梁漱溟反动思想的批判,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批判,对萧也牧创作倾向的批判,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对马寅初新人口论的批判……严厉的批判,使得许多知识分子开始迷失自我,精神信仰受到严峻的挑战。几乎是一夜之间,知识分子陡然感受到难以言传的身份焦虑。大多数作家面临一个重要的难题:自己的世界观、人生观怎样改造?郭沫若痛心疾首地想把自己以前所写的全部东西付之一炬,老舍诚惶诚恐地向上级交上了一份《我的改造》,而胡风等人则被打成了“反革命集团”,集团的主要人物阿垅抗争说:“可以被压碎,决不被压服!”结果,他真的就被压碎在监狱。
改造,是“十七年”及“文革”时期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关键词。知识分子题材小说所体现出来的共同基调也自然是“改造”以及以此为核心的话语。这类小说大体上可称之为“改造小说”。
审视“改造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形象,马上会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几乎很少有正面人物。《青春之歌》算是一个特例,但主人公也免不了是被教育、被改造的对象,须不断地想得到工农大众的认同。知识分子必须严格剔除其与生俱来的“小资产阶级”本性,灵魂的改造成为宿命。王蒙的《活动变人形》可以照见知识分子改造过程中的尴尬情状。倪吾诚,这个辛亥革命前三个月出生的地主的儿子,长大后出国留学,满脑的西方文明,“主张中国必须优化”;回国后又与传统文化“剪不断,理还乱”,后来又抱着对新生活的向往,对中国革命胜利后的陶醉,真诚地投身革命。当革命胜利后,他却被告知:他仍然必须为那个已经消灭了的阶级和逝去的旧时代背负罪责;他的唯一出路就是接受工农大众对他的改造。王蒙向我们深刻揭示的是类似于倪吾诚的老知识分子的全部痛苦:在一个需要激烈的社会革命才能拯救的国度里,他们从国外接受的知识、观念、理想和信仰都是无足轻重的;而当革命胜利后,他们所受的教育、所拥有的知识,反过来又成了他们的罪恶,成了新政权改造、批判乃至斗争的对象。
60年代,对知识分子的改造达到了极限。“文革”中,大字报取代了科学研究,反革命、黑帮、特务、牛棚、厕所、干校、改造,成了知识分子的代名词。知识分子在“我是谁”的惊惧中彻底迷失自我。如何找回自我?答案只有一个——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接受劳动改造。于是《创业史》中的农业技术员韩培生到蛤蟆滩指导农业生产,他也只是业务上的骨干,在思想上却落后于生宝妈和任欢喜这两个贫下中农。在与泥土的亲密接触中,在与最普通的农民的融合中,知识分子荡涤着令自己百思不得其解的反动、肮脏、卑下、丑恶的灵魂。在灵魂的改造中,知识分子的价值观念、情感方式完全认同于低位文化。几经“洗澡”,知识分子逐渐失却了独立思考的勇气,人格彻底坍塌,对自己身份的怀疑、焦虑异常沉重。尽管此前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的指导下,出现了《红豆》、《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等作品,使知识分子形象有了一些亮色,但不久,“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政治警示发出之后,文化环境越发冷峻,当代知识分子形象便被公然作为与无产阶级对立的一个阶层出现在60年代的文学创作中。
“文革”更是中国历史上知识分子的大劫难,极左路线对于知识分子的严重摧残至今仍令人咋舌。“四人帮”疯狂而无人道的蹂躏、践踏、侮辱和摧残,使知识分子饱受人生磨难,他们几乎完全丧失个性特征,而处于一种失语的状态。这是一个敏感的年代,当传统的“士农工商”排序而变为“工农兵学商”,而在“工农兵学商”顺序中列第四位的知识分子再一变而为“臭老九”的时候,知识分子题材小说创作更出现了从未有过的沉寂。以“潜在写作”出现的《九级浪》(毕汝协)、《逃亡》(佚名)、《第二次握手》(张扬)、《波动》(艾珊)等知识分子题材小说,相对于“红色主流文化”,虽以清醒的思索和看待现实问题的视点,做过找回知识分子身份与人文传统的挣扎,但在那个价值失落的疯狂年代,其声音的微弱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四、新时期的“人性小说”:反思中的人性寻找与欲望支配下的人格缺位
新时期的小说创作,知识分子题材占了很大比重。不少学者把它看作继20年代以后的第二个黄金时代。考察这个时期知识分子题材小说的创作,可以分为两大阶段。70年代末——80年代后期为第一个阶段,其主题表现为:在对历史的返观中审视知识分子的心灵伤痕,反思知识分子的精神忧患,在人性的自审、忏悔中重新确认知识分子的身份。80年代末期——90年代为第二个阶段,其主题表现为:知识分子在世俗欲望支配下的精神委顿与人性迷失,其身份认同与道德认同又一次陷入尴尬。因此,从文体本质上说可以把这些小说概括为知识分子的“人性小说”。
70年代末,伴随着思想领域“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和稍后不久新政治体制的建立,“抗战以来影响了中国文化建构四十年的战争文化规范被否定,中国真正进入了和平经济建设时代,思想解放路线和改革开放路线相辅相成地推动和保证了中国向现代化目标发展的历史进程。”[7] 以后的整整十年,一大批知识分子或从梦魇中醒来,或从被监禁、被流放的地方归来。第二次客观意义上的“解放”给所有的知识分子带来了生命中的第二个“春天”。
禁锢既以解除,知识分子作为“人”的地位和命运理所当然地引起文学家们的思考。于是,小说中出现了一批揭示知识分子心灵苦难和肉体折磨的“伤痕文学”与反思和批判自我主体意识的“反思文学”。其目的是争得知识分子做人的权利和恢复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张贤亮就以独特的审美视角描写出知识分子在特定历史阶段的苦难命运,尤其是他们在“灵与肉”的双重折磨下饱尝的炼狱之苦。反思文学则由开始的政治性批判、控诉转入深层次的哲学历史反思。出现了一大批倾注了哲学本义的忧患意识的优秀作品。《犯人李铜钟的故事》、《天云山传奇》、《布礼》、《蝴蝶》、《人到中年》、《灵与肉》、《人啊,人》等,这些作品的主题无疑都是人的发现、人性的寻找。正如王蒙的《活动变人形》所包蕴的哲思:生活改变了人的形,为了生存人不得不变形;而知识分子又不得不在精神失衡的状态下,忍受精神失败的苦楚和理性思考的孤独。人性扭曲的痛苦是刻骨铭心的。身份复位后,章永璘、汪苦舟、邵南孙、倪藻等,或从原罪的、或从道德的、或从责任的不同角度作出反思,在反思中寻找着精神的解脱和人性的超越。这个时候,知识分子身上所体现的人性内涵,几乎都具有这样一种特点:价值理性单向,情感追求执著。强烈的使命感使得知识分子自觉地去追求和塑造更高尚、更完美的人格。《人到中年》中的陆文婷医术高超,医德高尚,始终默默无闻地为社会奉献出自己的一切,在社会角色和家庭角色的冲突和双重压力之下,她心力交瘁,濒临崩溃。《春之声》中出洋归国的岳之峰由于出身问题曾经做过“没完没了的检讨”,但“平反”“解放”后依旧痴心不改地对祖国怀着深挚的热爱。他们的价值追求所体现的道德理性内容,皆与传统观念所要求的知识分子的人格品性相符合,总是与崇高、神圣、纯洁、执著、伟大等字眼联系在一起。知识分子在努力地寻找、恢复着自己的角色与地位。
然而,时至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商品大潮兴起。自由经济时代基于物质诉求的社会主题逐步引发了经济理念在社会各个层面上的深入渗透,社会形态开始实现真正的转换。这种转换,却使刚刚摆脱精神困境的知识分子又陷落到物质贫穷的窘迫之中。严航(方方《无处逃遁》)全力攻读留美博士,却无力很好地解决自己的生计问题,只得准许妻子出门干第二职业。他最终虽通过了留美考试,却由于没有经济担保而前功尽弃。高人云夫妇(方方《行云流水》)都是大学副教授,家里却显得格外寒酸,以致他不得不在理发店忍受一群女孩子的奚落,甚至还得忍受自己学生的嘲弄。高人云总“觉得他这一生还从来没有如此的尴尬和窝囊过。他想他是不是和这个时代生活的哪个齿轮错了位。”刘震云的《一地鸡毛》,池莉的《热也好冷也好活着就好》,杨绛的《洗澡》、阎真《沧浪之水》、张者的《桃李》,王家达的《所谓作家》等等,生存窘迫都无一例外地成为知识分子无法摆脱的情结。由于先天的不足,当社会价值体系又一次悄然发生变化,物质享受的诱惑主导社会认知的时候,知识分子的人格操守和启蒙理念便再次迅速动摇,甚至为追求所谓人生价值的物质体现而滑向世俗。“这一时期社会人文环境对知识分子人格姿态构成最大影响的是日渐兴盛的物质主义潮流。而这股潮流之所以会构成巨大的深刻的影响,就在于它几乎一夜之间让所有的人感到物质基础对于生存的重要性。物质财富的多寡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成为社会地位的象征,并进而直接成为人的价值评价标准。”“价值失落的深切痛苦,不仅来源于他们所尊奉的道德观念和人格姿态遭到社会现实的无情嘲讽,而且还来自于他们一向引为骄傲的文化优势在商业社会面前竟成为生存劣势。当习惯了处于社会中心的知识分子被波涛汹涌的商潮抛到社会的边缘,甚至在边缘也需有一番挣扎才得以有容身之地时,他们的内心深处无疑要经历一场激烈的灵魂风暴。”物化时代,欲望膨胀,消费人生,使不少知识分子由精英化、革命化、知识化迅速滑向了世俗化、低俗化。在这部分人身上,他们的先锋意识消失了,楷模形象消解了,精神坚守出现了总退却。知识分子身上“鼓手”与“代言人”的光环越来越淡,知识分子与权威意识形态之间“应答”的现实可能性越来越小,知识分子的身份自然发生了阵痛性的变化。一腔热血走革命道路的“改造者”不见了,痛苦追寻自我以求超越的“自省者”不见了,相反,一类主动放弃了精神信仰与道德自律、同时又暗自蓄势自我陶醉的“萎顿者”出现了。欲望凸显,道德迷失,知识分子陷入了人格缺位的身份陷阱里。[8]
由于知识分子崇高形象开始倒塌,作家们便纷纷把他们作为调侃、嘲笑、“开涮”的对象。王朔笔下的知识分子都是“无行”、“丑陋”、“愚蠢”的典型形象,甚至是“流氓”、“骗子”。他以“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来概括自己作品的主题。90年代崛起的女作家徐坤以讽刺家的尖刻与老辣,将高级知识分子形象揭露得体无完肤。她笔下的教授、诗人、小说家、记者、主持人等高层知识分子的种种神话被她一一消解了,露出了知识分子深处的丑恶、阴暗、怪诞、荒唐等丑行。贾平凹的《废都》更是将知识分子的堕落充分显示出来。庄之蝶从一个“不大缺钱的主儿”发展到逐步染指金钱,甚至成为和别人合伙谋取龚靖元的名人字画以牟取暴利的无耻之徒,而且,私生活也放纵糜烂。是人文心态的失落使庄之蝶们彻底走向了颓废和堕落,在转型期失去了原有的崇高与尊严,在世俗欲望的支配下失掉了知识分子本应具备的人格精神。
总之,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题材小说,其主题伴随着时代风云的变幻,总在不断的嬗变之中。在一百年的中国历史中,知识分子走过的是一条艰辛之路,他们有过太多的思索与抗争,也有过太多的苦闷与困惑,在反复与曲折之中坚韧地寻找着自己的方向,而当下时代又似乎迷失了自我。那个历史期待中的能够超越利益得失的个体,勇于担当历史和现实的道义职责、被赋予了独特价值职能的知识分子群体还能够出现吗?什么时候出现?中国的知识分子题材小说又将出现怎样的主题嬗变?随着社会的进步和时代的发展,笔者认为,结论应该是乐观的。
标签:知识分子论文; 文学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中国形象论文; 读书论文; 启蒙思想论文; 五四运动论文; 革命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