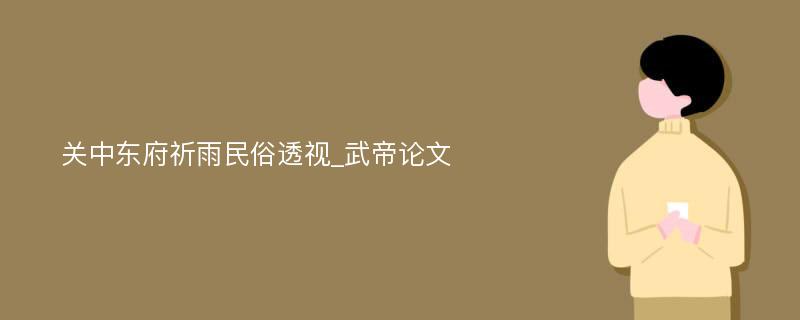
关中东府民间祈雨风俗透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东论文,风俗论文,透视论文,民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陕西省合阳县属关中东府,在省会西安东北180公里处。合阳是传统的农业县,但在建 国前的漫长岁月里,除了黄河边的洽(hé)川和金水、徐水河谷一小部分村庄的农田可 以灌溉外,塬区的庄稼几乎完全依赖于天雨,甚至许多村庄人畜用水都有困难,或六七 个人一班在深五六十丈的水井里去绞,或用笨重的木桶来回跑十多里下海参上塬去挑, 在县西南最缺水的地区流传着“秦城和家庄(方言读卓,zhuo),马尿光馍馍”,“ 宁给一个馍,不舍一碗水”的民谚。
合阳受东亚季风的影响,干湿季明显,冬季风期少雨,夏季风期多雨,年平均降水量5 50毫米,而且集中在夏季,夏季年平均260毫米,占年总量的47%;秋季为160毫米,占 年总量的28%。冬小麦是合阳的主要粮食作物,而在小麦越冬季节、春季返青季节和灌 浆季节往往缺雨,对产量带来极大影响。
干旱留给合阳人的记忆太惨痛、太深刻了。十年九旱,三年一小旱,五年一大旱,几 乎成了亘古不变的规律。由于旱引起的灾荒(合阳人俗称“遭年馑”)令合阳人谈“旱” 色变,不寒而栗。《合阳县志》记载:清顺治十四年(1657年)至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 年)的246年间大旱33次,平均7.9年一次;民国6年(1917年)至民国34年(1945年)的29年 间大旱7次,平均4.2年一次。其中尤为惨烈的是光绪三年(1877年)和民国18年(1929年) 两次。据《合阳县全志》(清乾隆本)记载,合阳乾隆年间的人口是61万,但经过光绪三 年大饥馑,人口锐减至不足13万!孟家庄光绪五年所续《党氏族谱》序中记载这次灾荒 时写道:“自元年至三年,天无雨降,地不滋生,连年荒旱,饥馑至极。春夏食槐叶有 几,秋冬食榆皮而榆皮无多。荒旱去已,疫气流行,渭河以北,同州府属,被灾尤重。 举数十年之生聚而死于岁者十之三,死于疫者十之三。盖十分生灵亡去六七。”号称合 阳财东村的灵泉村有一位叫党德荣的老秀才,以一名目击者的身份写成《记荒文》,记 录了被称为合阳“白菜心”的坊镇地区在光绪三年的社会状况:“鸡犬牲口尽被人食, 甚至人有死者,辄行抬取,即生亦诱至僻处,分食其肉,甚至有母食其子者。”党德荣 在光绪五年去世后,他的学生党桂一把这篇文章刻成石碑,以警世人。该碑现收藏于合 阳县博物馆。《合阳士女续志》载:“(光绪)四年七月后,合邑人死八成以上,计饿死 四成,疫死四成。”
新中国建国后,合阳人大搞水利建设,从大跃进时期在金水上游修筑白家河水库起, 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相继修建了定国水库、五八水库、红旗水库、百良水库以及一批 小水库;国家投资,群众投劳从1975年起兴建了大型黄河堤灌工程,解决了合阳7个镇4 4万亩土地的灌溉问题,“靠天吃饭”的局面有所改变,但在县西部和西北部仍有一大 部分土地依旧处于干旱的淫威之下。
在建国前漫长的岁月里,甚至在建国后合阳的西部地区,当干旱肆虐之时,无计可施 的人们只有仰仗人世弱者的烛光——神灵,一次又一次地用各种形式进行祈雨。
祈雨是远古时期人类对自然崇拜延续到今天的表现。人们对横行暴虐的自然灾害无可 奈何,便按照自己的思维方式,认为有某一方神灵在主宰着人世间的雨雪阴晴,于是乞 求这些神灵,以慈悲为怀,拯救天下黎民。
一、长长的司雨神谱
祈雨,清晰地凸现了民间神灵崇拜的多样性和实用性。凡是在老百姓的心目中认为能 够降雨的神灵,都在祈求的范围之内,形成了一列长长的司雨神谱。即使那些平日门庭 冷落、香火难以为继的神灵,比如猴王之类,天旱时也倍受拥戴,前来烧香膜拜的人络 绎不绝。
老百姓认为能够降雨的神灵有以下各位:
(一)韩山奕应侯。不知何种原因,合阳的老百姓对韩山奕应侯的态度特别热情。韩山 奕应侯是春秋时晋国赵文子的封号,赵文子就是从屠岸贾的追杀下侥幸逃出的那个孤儿 ,秦腔传统戏《八义图》(或名《狗咬赵盾》,建国后改名《赵氏孤儿》,京剧里亦有 《搜孤求孤》的剧目)讲述了这个故事。在合阳民间传说里,人们把两个相隔几百年的 人物拉扯到了一起,说赵文子是汉武帝的舅舅,甥舅二人都看中了渭北合阳境内一座风 景秀美的山,外甥机灵,用计占了山,而在黄龙山里为舅舅另找了一座山,名叫韩山。 这座山民国时期仍属合阳,新中国建国后才划归黄龙管辖。清乾隆三十四年本《合阳县 全志》记载:“韩山,在梁山西北,距今县城一百二十里。俗名救郎山(为藏赵氏孤处) ,有奕应侯赵文子祠。”清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钱万选所著《宰莘退食录》载:“又 一庙在梁山上,祈雨辄应,其神为晋赵文子,亦俗传也。”因为黄龙山植被好,所以降 水相应也多,合阳的降雨云多从黄龙山中涌出,天旱时群众“祈雨辄应”,人们认为这 都是韩山奕应侯的威力,随之对他的崇敬远在其他神灵之上。《合阳县全志》记载:合 阳县城西边有韩山奕应侯庙,系唐太和四年(830年)工部尚书谭石建,宋政和五年(1115 年)礼部侍郎王显重修。另外在合阳的一些大村庄,如县西南的路井镇、秦城村、县东 的阳村、东清村都有规模相当大的韩山奕应侯庙,俗称“救郎庙”。在民间把韩山奕侯 称为“救郎爷”,方言把音念转了,久而久之,成了“九老爷(ya)”。东清“救郎庙 ”目前主本建筑尚存,另有三通立于清代的碑石,记载重修、增补等与庙有关的事项。 在秦城村的“救郎庙”里,有一通元代至元六年(1340年)所刻的《韩山奕应侯祈雨感应 碑》,碑高1.67米,宽0.78米,厚0.34米,碑文记当年伏旱时秦城村民去梁山韩山奕应 侯赵文子祠求雨得泽一事,是迄今为止我们所见到的有关民间祈雨的最早的记载。在救 郎庙里,无一例外地都建有专为唱神戏的戏台(民间亦称戏楼)。
(二)武帝爷。传说汉武帝刘彻当年喜欢求仙问道,他看中了合阳境内的染山西峰,抢 在他舅舅赵文子的前头占了这座山,后来他的儿子在山上修了“汉武帝祠”,梁山西峰 便被称为武帝山,而本来是君王的汉武帝也被尊为“武帝爷”,进入了神的行列。这在 中国的帝王之中,大概是极其个别的例子。据民间传说,当年汉武帝从长安城骑马到渭 北,途经合阳的善寺村,人困马乏,吃了那里群众的“麦籽泡踅踅”(注:麦籽泡踅踅 间合阳民间饭食。麦籽是用麦仁煮成的汤;踅踅即煎饼。),元气恢复,后来该村改名 “井溢”,天旱祈雨时便去武帝山上。因为武帝山背后的放马沟据传是源头,加之武帝 爷吃了人的口软,不会让井溢村的人空手而返,所以天旱时井溢村的人便上武帝山祈雨 ,而且据说没有一次不灵验的。
(三)河伯。合阳县靠近黄河的洽川虽有瀵泉浇灌,旱涝保收,但塬坡地仍摆脱不了靠 天吃饭的局面。这里的人们除过敬龙王之外,还向河伯祈祷。清乾隆年间“洽川才子” 许秉简为村民撰写的《祷雨河伯文》中说道:“河自昆仑发源,九折入海,流经合上, 合民沾其润久矣!而伯之庙又近在蒲坂,去合不百里,一岸之隔,其沐泽宜更深耳。兹 者合旱,合民奉天子之命,吏祷雨于伯,诚以伯膺天子之显爵,享天子之明,兴云致雨 ,普润万物,能代天子膏泽兆民也,故于淫祀不之祷,而祷于伯。”
(四)大禹及禹母。大禹是传说中治水的英雄,在“三官”中居“水官”的地位。在合 阳,既有供奉许多包括大禹在内的“三官庙”,而且有许多专门供奉大禹的“禹王庙” ,最有名的是矗立于乳罗山西峰之颠的“禹王庙”,建于明万历壬辰(万历二十年,159 2年),距今已四百余年。庙为一砖箍窑洞,今仍完好,戏楼等附属建筑则不存。老百姓 认为,既然大禹能司雨解除干旱,那么母亲在儿子面前说句话也应该是算数的,所以禹 母庙也被列入雨神范围。在梁山二十四峰中有一座芙蓉山,俗称“尖山”,峰顶建有禹 母庙,所以该峰又称“禹母峰”。天旱不雨时,附近村庄的群众便到尖山顶上的禹母庙 去祈雨。
(五)四姑。在和家庄镇萧家城村西有一座“四姑庙”。萧家城也在乳罗山上,向西距 禹王庙约莫十里路。据民间传说,四姑是禹王的小女儿,聪明伶俐,最受钟爱,但有时 未免有点淘气。她父亲禹王特别关注合阳人,让她代为行雨叮咛她“三天一下,四天一 下”,她心慌之中听成“山西一下,四川一下”,结果老百姓还是来向禹王求。求四姑 表示以后再不敢粗心了。老百姓把四姑也作为司雨之神供奉,认为她从父亲那里要雨是 不成问题的。碰到天旱,附近村庄的人就趁三更半夜之时悄悄地把四姑神像偷走,供奉 起来祈雨,等下了雨再敲锣打鼓地送回来。原庙在解放战争中被国民党军队拆毁作了工 事,四姑像移放在一座土窑洞里,1994年村民集资盖了一座小庙安放四姑像。
(六)观音。老百姓特别喜欢观音菩萨,认为她可以管天地、管风雨、管家庭,甚至管 每一个男女老幼,具有全方位的功能。她右手持的柳枝,是生命与活力的象征,她左手 捧着净瓶,可以涌出滋润万物的甘露。她大慈大悲,以救苦救难为己任,只要她愿意, 肯定能使人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昔日在合阳大地上,大大小小的观音庙随处可见, 许多家里也供奉有观音菩萨。经建国后历次运动,现在合阳的观音庙已荡然无存了。
(七)龙王。昔日龙王庙遍布合阳城乡,与观音庙的数量不相伯仲。其中规模最大的是 县城东南十里的龙王庙,是一处占地十余亩的建筑群,气势恢宏,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被 拆毁。民间传说龙王爷座下有一个“海眼”,与东海相通,可以听见大海的涛声,故而 所在的地方名为“海龙镇”。每年农历四月初一的龙王庙会规模极大,驰名渭北。在老 百姓的心目中,行云布雨是龙王的本职工作,既然享受百姓的香火祭祀,就应全心全意 地为老百姓服务,使百姓赖以生存的土地免受干旱之苦,所以每到干旱时节,那些大大 小小的龙王庙便会热闹起来。
(八)猴王。合阳的一些村庄里建有“猴王庙”,供奉的神灵就是那个大闹天宫、搅得 玉皇大帝也不得安生的美猴王孙悟空。按照老百姓的思维方式,连玉皇大帝提起他也怯 惧三分,更何况那些龙王,到天上要个两三场雨那还不是小事一桩?再说他又是来自基 层,对群众的疾苦感同身受,富有同情心,因此天旱时便要诚恳地请猴王爷亲自出山, 上天去辛苦一趟了。
(九)土地。土地爷类似于农村的基层干部,长年累月生活在民间,始终和群众保持着 密切联系。再说,他的职责就是保佑庄稼丰收,让老百姓过上安居乐业的日子。虽说职 位低了点,但毕竟是神,是家庭的“中央主”,到上面说句要雨的话总比普通百姓的力 度要大,所以恳求他为民请命,上天要雨便是情理之中的事了。
(十)石狮子。狮子威雄壮,具有镇妖辟邪的功能,是老百姓的保护神。特别是村里庙 院前的那些大石狮子长期生活在神的周围,受环境薰染,免不了也要沾一些“神气”, 对于神灵的性情和办事规律也会略知一二,打通它们的思想,请它们在神灵面前帮着说 几句好话,或许不会是一件太难的事情。出于这一种思维方式,所以石狮子便被老百姓 作为一种辅助力量而让它在祈雨中发挥作用了。
二、五花八门的祈雨方式
按照老百姓思考问题的逻辑,雨水是由天上的一些神灵管理着,这些神灵可能也跟世 间的芸芸众生一样,有的喜欢听顺情入耳的好话,有的则需要用强硬的手段逼其允诺, 有的还得用软硬兼施的方法,所以便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祈雨方式,然而目的只有一个, 那就是下场好雨救救庄稼。根据笔者田野调查的情况,关中东府合阳县民间祈雨方式大 体可以分为感情投资、苦行感动、善行乞求和恶行逼迫四种。在一个村庄的祈雨过程中 ,可能并用两种方式。
(一)感情投资
路井镇是合阳的南大门,原名露井,据说某年因雨得瑞,故名。清同治年间,方圆近 十个村庄联合起来在镇上盖了一座规模很大的“救郎庙”。每年农历六月十三庙会时, 都要先一天专程上乳罗山把禹王请来一起看戏,热闹一番。请神时八个社的锣鼓队、芯 子杆、高跷、旱船等,加上全副执事、万人伞之类,抬上神楼,浩浩荡荡排成几里路的 长队,走到十余里外的山上,先在戏台上唱三折好戏,请出禹王神牌,恭恭敬敬地安放 在“救郎庙”神殿里,请两位神灵一起看戏,神前的香烛、供品极尽富丽堂皇。戏看完 ,庙会结束之日,仍然是原样隆重地把神送回山上。路井人的想法是,平日对神要虔诚 ,这叫感情投资,等到天旱要雨时再跟神套近乎,未免有些太势利了。当地群众说,每 年的六月十三庙会之前的初九日左右,大小总要下一场雨,这时候正是路井地区秋苗生 长需要雨水的时候,农谚云:“有钱难买五月旱,六月连阴吃饱饭”,他们认为禹王爷 理解人的心情,下一场雨让老百姓心里安稳,高高兴兴地过庙会。
(二)苦行感动
祈雨的人为了众人的利益,要勇于做出牺牲,用自己的苦行来换取神的怜悯,在黄河 岸边的一些村庄,那些壮小伙子用纳草圈的篾针从腮帮这边穿到那边,血流不止,却神 态自若;上武帝山祈雨的人一律赤着脚片,不管路上有破瓦片、圪针刺,踩上去眉头皱 都不皱;头上不准戴草帽遮荫,而是套个柳圈,听凭毒太阳晒。到神前轮流跪拜,每人 一炷香,香着完才能起来;有的还跪在炭渣上、铁索上,腿上鲜血淋漓。求到雨后,背 水的“水(方言读fù)僮”几十里地要一口气走到家,脚步不能停。而护水的人紧随其 后,还有那些沿途加入的自愿者,浩浩荡荡排成长队,一边行进一边念“祈雨歌”,尽 管是各念各的,但一刻也不停,而且感情真挚,声调悲怆,令听者动容。
笔者采录到的“祈雨歌”有以下几种。
水歌 甲
一瓣莲花一瓣开,我有真心拜佛来。
先拜南海观世音,再拜我佛武帝神。
身里难,难里身,救苦救难观世音。
然后换数序,从一念到十,再从头反复。在这首“水歌”里,人们把观世音菩萨和武 帝爷并列,其实武帝属于道教系统,但在老百姓眼里,他们都是管下雨的神,所以很自 然地把他们联在一起。
水歌 乙
一炷香,一礼拜,我问武帝爷爷要雨来。
二炷香,二礼拜,我问二郎爷爷要雨来。
三炷香,三礼拜,我问三官爷爷要雨来。
四炷香,四礼拜,我问四海龙王爷爷要雨来。
五炷香,五礼拜,我问五湖四海龙君爷爷要雨来。
六炷香,六礼拜,我问南斗六星爷爷要雨来。
七炷香,七礼拜,我问北斗七星爷爷要雨来。
八炷香,八礼拜,我问八仙爷爷要雨来。
九炷香,九礼拜,我问九天玄女娘娘要雨来。
十炷香,十礼拜,我问十殿闫君爷爷要雨来。
南无阿弥陀佛!
这首祈雨歌里的“礼拜”是方言“跪”的意思;“问”是向的意思,即从某某处要雨 。歌里涉及到佛家和道家的诸多神仙,反映了旱情紧急,群众见佛就烧香的急迫心情。
水歌 丙
香炉平,冒头高,搭金板,过金桥,
王母娘娘摘仙桃。
摘一山,望一山,没有弟子上青山。
青山有一支腊树,支腊树,开白花,
左手扳枝右手掐,一下掐了一百八。
摆到各神面前快救难,
就地风云起,青龙坐雨台,
早下通天雨,苦救万民安。
水歌 丁
丁丑年,遭天荒,麦薄收,秋未安,
一片黄地实可怜,百草都旱干。
井里无水池又干,无奈何,上青山,
武帝面前垒水坛,清风细雨下三天。
在晒猴王爷和土地爷(详见下文)时,那些年轻姑娘们也要脱掉鞋袜,挽起裤腿,戴着 柳条冠跪在打麦场上,陪着神一起晒,“祈雨歌”从她们的口中念出,更增加了几分悲 凉的感觉。
一盆莲花一盆开,我有真心拜佛来。
一拜南海观世音,二拜罗汉五百身。
我佛早下安心雨,普救万民。阿弥陀佛!
金香炉,银供桌,下雨就在今后晌(方言念shuo)。
秋薄收,麦未安,地里胡基堆如山。(胡基:大土块)
碌碡碾,土冒烟,娃娃饿的怪叫唤。
万民个个哭皇天。只盼南岸上来一朵云,遮了太阳阴了天。
清风细雨下三天……
(三)善行乞求
昔日一遇到天旱,各村神庙里前来跪拜烧香的人便络绎不绝,昼夜不断。尽管人们自 己可能要面临断炊的危险,但必须用上好的白面为神蒸献供的“神桃”。有的还请来巷 院的能人巧手精心地做成面花,以示虔诚。
旱塬上的村庄都有一个甚至多个涝池,用来蓄住雨水供洗涮和饮牲口,但天旱无雨时 ,只用不添,涝池便干了。这时便有那些热心公共事业的寡妇相约在夜深人静、星星出 全之时去打涝池。她们拿上扫炕用的细篾长帚,认真地在涝池底部扫些干土,再用箩面 的细萝子箩下去,一边箩还一边念“祈雨歌”或说些祈求神灵降雨的好话,至于为什么 是寡妇去而不是其他人去,这是因为他们认为寡妇属纯阴,阴气盛了,天便要下雨,当 寡妇是一件很痛苦的事,身份往往受到歧视,在生活中有许多意想不到困难,但在打涝 池祈雨时,寡妇的身份却成了她们荣耀的资本,她们感到自己为村人做了一件善事,也 想用自己的善行唤起神灵的同情,早些下雨。
狮子在民间被视为吉祥物和保护神,天旱缺雨时,姑娘小媳妇会悄悄相约,同样在夜 深人静之时端上一盆清水,每人拿一条干净手巾到村中庙院大门口去洗石狮子,一边细 心地擦拭一边念:
洗了狮子头,下得满街流;
洗了狮子腰,下得起了蛟;
洗了狮子尾,下得没处避。
在她们看来,“我们对神的护卫都这么虔诚,对您老人家的态度那就更不用说了”, 希望神灵能念及自己的一片善心,早些下雨。
(四)恶行逼迫
上文提到过的井溢村祈雨时与众不同,因为当年汉武帝吃了他们村的“麦籽泡踅踅” ,有了短处,所以在井溢村人的面前便不那么威风了。而井溢村人亦自恃有恩于武帝爷 ,要雨时便理直气壮得多。井溢村的祈雨队伍到了武帝山下的西牛庄,先进武帝庙撞钟 ,西牛庄的人便知道井溢村祈雨来了,马上烧茶备饭,招呼休息,然后一起上山。祈雨 的人先在武帝神像前轮流下跪,甚至跪在铁索或炭渣上,希望用自己的苦行感动武帝爷 。如果过了三天还没动静,便把献殿前盖在南天门上的大石板揭开(这石板平日是不准 动的),意思是“你从南天门里往下看一看,看地里旱成啥样子咧!”如果打开南天门还 没作用,便选出一名代表站在武帝像前怒眉横目地大声问三遍:“给雨不给?”其它的 人便抡起镢头打神台,挖山门,甚至把铁索搭到神像脖子上拉例神像,把神庙弄个一塌 糊涂,然后扬长而去。说也怪,往往这么一糟践,没几天便下雨了,非常灵验。
“晒猴王爷”也是一种恶行逼迫。天大旱时,把猴王从庙里抬出来,放到打麦场上, 面朝南晒太阳。按老百姓的想法,猴王晒得撑不住了,便会上天要雨。陪着猴王爷晒的 还有从各家各户偷来的土地爷,在猴王周围摆了一圈。
有些地方的祈雨就像今天的谈判一样,时而和言悦色,时而声色俱厉,拉拉打打,晓 以利害,最后达到下雨的目的。比如前面提到的那篇《祷雨河伯文》便是一例。开宗明 义讲了为何要向河伯祈雨的理由后,便质问道:“祷之一日不雨,二日不雨,三日又不 雨。合民卜兆,兆三日以内雨。明日雨不洒尘,无济于禾,伯之雨止是耶?”接下来又 以和缓口气问道:“抑将大雨,而参以是发其端耶?”给神一个台阶下,以免神太难堪 。但接着又要把这种假设落实:“果以是发端,祈今夜雨,今夜不雨,来朝雨。来朝不 雨,明日不雨,是终不雨也。民等起坛不敢复祷于伯矣!”这已经很有些威胁的味道了! 大约是生怕这样做引起神的不快,遂又换为激将法:“河伯果不能致雨耶?抑能致雨而 故屯其库不肯雨耶?不然,将冥然居于府,虽有祷不之闻耶!”紧接着加浓了火药味,步 步进逼:“夫不能致雨民等无可如何?若能致雨而故屯其库,是为不仁;冥居水府,虽 祷不闻,是为不灵。不仁不灵,而受天子之爵,享天子之祭,而不泽天子之民,与淫祀 何殊?”这一番劈头盖脑的质问之后,却又态度一转,为神许愿了:“河伯念之在此祷 矣,祷之而雨,牺牲以祭伯,歌舞而娱伯。”但如果仍不下雨,这一切可就都享受不上 了,“如其不雨则伯之神不灵,而民不复信任矣”,不下雨便得不到百姓的信任,还有 比这更可怕的事么?河伯权衡利弊,肯定会选择下雨这一条路。
三、祈雨的组织和顺序
昔日农村里议事都是在村中神庙、寺院一类的公共场所里,俗称“官地方”,实际上 是“公地方”,在方言里把“公”念转音了。村中的乡约头邀集各社乡约开会商议。社 是一种农村的基层组织,有按姓氏分的,有按地域分的。比如井溢西村分张社、习社、 任社、马社四社。议定各社应出人力和应摊钱财。一部分人上武帝山祈雨,一部分人在 家做后勤和接水的准备。上山祈雨的每社一人,再选一名眉清目秀、聪明伶俐、属龙的 青年人担任“水僮”,负责背水;还有一名帮差,负责联系、报讯和在神前帮忙看水。 因为当年汉武帝吃“麦籽泡踅踅”是在井溢东坡,所以该村是首社,他们可以单独去武 帝山祈雨,其他各社没有首社参加则弄不成。1995年天旱时井溢东坡就单独上山祈过一 次雨。
祈雨的人出发前先在村中的武帝庙烧香,叩三个头(农村人称为“半祭”)然后出发, 只能步行,不准坐车,以示虔诚。到山下西牛庄的武帝庙里撞钟,打扫庙院,叩三个头 ,吃罢饭,脱鞋上山。到山上的武帝祠里叩五个头(全祭),选一人说:“武帝爷,今年 又寻你老人家来了!”在供桌上的香炉旁用香板斜搭个桥,轮流目不转睛地盯着,如有 虫子爬上去,便表示神给水了。再抽签、打卦问何时到龙王眼去灌水,如果是上卦,则 表示马上可以灌水。到泉边点三炷香,叩三个头,在花瓷瓶里灌上水(只能灌到瓶颈处 ,不准溢出),再烧香叩头,放到泉旁的龙王神龛里,用蜡封住瓶口,小心翼翼地端上 山,向武帝爷汇报。然后再打卦问神何时可以出发下山。报讯的人此前早已回村报告神 给了水,村里马上筹备接水事宜。
四、得雨后的喜悦
上山祈雨的人护着水瓶一点也不敢大意,如果在路上有个闪失,便会前功尽弃。旧日 还有专门截水(群众称为“叼水”,即从手里夺去的意思)的,打听到谁家祈下了雨便在 背水人经过的僻静处设伏,常常为此打得血头烂面。群众还传说,神灵给了水,但有旱 魃一类的妖魔偏要破坏,比如在金水沟上游的念吉沟里,地形险要,有一座小桥,有一 年背水的走到那里,一阵黑风刮来,飞沙走石,把水瓶殛破了,落了个空欢喜。以后人 们格外小心,接水的人跑几十里专门等在念吉沟里,先放一孟三眼铳镇妖驱邪,然后护 着水往回走。接水队伍浩浩荡荡,举着旗,打着执事(也叫銮驾,即金瓜、钺斧、朝天 镫之类),庄严肃穆。
祈雨队伍每经过一个村,村里都在大路旁摆了香案和盛着清水的瓦罐,意思是让他们 也能沾一点光。队伍一过,便把瓦罐打破,让水沿淌在地下,意思是这水已带了神气, 可以滋润万物了。
水瓶供奉在村里的神前,村里人继续烧香上供,直到下了雨也不停止。下雨后便要隆 重地谢神,有的村甚至以整猪、整羊作为牺牲,至于平日敬神用的油轮、时鲜水果更不 在话下。
谢神的重要内容是唱谢雨戏。每座神庙里都有戏台,还有的是对台戏楼。村中按户或 按地庙收取唱戏费用,然后请来合阳特有的提线木偶戏或大戏,唱他几天,借娱神之机 让人也得到欢娱。此时蒸馍买菜,邀亲戚,请朋友,村中热闹非凡,一场好雨把人心头 的愁烦和郁闷扫荡净尽,万民同欢。戏剧创作家李新庆曾给我说过,临解放时他在坊镇 南街教小学,久旱之后下了一场好雨,他们当先生的也跟着群众一块儿高兴,几个人一 起仿小学启蒙的诗句凑了一首:“一下二三日,地湿四五寸。麦打六七石,八九十日戏 !”表达了人们的欢欣之情。不光看戏的人高兴,唱戏的人也高兴,因为风调雨顺,庄 稼丰收,请戏的人便多,他们的衣食也有了保证。在董家河小戏楼的后墙壁上留有民国 时期艺人唱谢雨戏时题的诗:“民国世事不论理,众位合润不一起。苍天降下清风雨, 料今年不得死。”(合润,合阳方言,指那些技艺高超又能配合默契的行家里手。)虽说 诗不怎么讲究,但那种“料今年不得死”的欢欣情绪却至今仍让人感受强烈。
井溢村唱谢雨戏之前,还有个“打旱复”的程序,即在开戏那天,由锣鼓队领头,捧 着瓶子再次上武帝山,一是请武帝爷下山看戏,山下西牛庄的村民自然也在邀请之列; 二是拿上水瓶直接再去龙王眼灌水,意即请武帝再给些雨,彻底解除旱象,是一种重复 祈雨的形式。
各村在接水和唱谢雨戏时都是竭尽全力,搞得热闹隆重,各种民间艺术形式争奇斗艳 ,得到了展示和提高的机会。黄河畔上的东雷村有一种特殊的民间艺术——上锣鼓,每 年春上祭三官庙、谢雨时都要表演一番,代代相传,久演不衰。洽川的莘里村有一种古 老的戏剧——跳戏,村里的龙王庙各社轮流主持祭祀,逢节和祈雨时演跳戏是必不可少 的内容,因之该村的跳戏十分出名。合阳东南的南吴仁村分为东西两社,村中的龙王庙 也是轮流祭祀,在交接时队伍里都要有“撂锣”这种民间艺术。应该说,昔日对司雨之 神的崇拜和祈雨是促进民间艺术发展和繁荣的重要因素之一,上锣鼓,跳戏和撂锣这几 种富有地方特色的民间艺术在改革开放后都引起了专家们的极大兴趣,走上了中央电视 台或陕西电视台的荧屏。
五、录以备忘
在下乡采风的过程中,笔者曾了解到不少祈雨灵验的事,尤其是井溢村的例子最多, 因为都是当事人讲的,令人不得不信,但笔者目前又无法对此做出科学的、合情合理的 解释,姑且抄录如下,或许可为研究者提供一些参考材料。
习永德(井溢村人,1997年为66岁,文盲,3岁时父母双亡,过继给堂叔):1962年村里 上武帝山祈雨时我是“水僮”,那是我第一次干这事。要下水后走在路上我听得瓶子响 了三声,有一滴水滴到我的脚面上。走到过了白家庄的南北路上,瓶子爆了,赶紧用馍 把漏出的水渗完,只担心把水遗了。越往南走太阳越红,心里不踏实。但回到庙里,解 开绳子,绽开裹着水瓶的伯叶,发现瓶子已成两半,水却还有大半瓶子,怪事!王村公 社(当时井溢村属王村公社)书记马一久打电话到村里,说王村是红日头,你们哪里祈下 雨了?我村的会计马万祥把电话耳机放到房檐口滴水下,说:“马书记你听!”因为下了 雨,所以“社教”时没寻村干部的事。后来我们这些祈雨的人都进了学习班,公社还派 人把武帝爷的像扳倒扔到沟里。从那以后直到前年,三十我年再没祈雨。
管章海(鹅泳村人,1997年在井溢村学校当教师,高中文化程度):1962年那次祈雨我 是目击者,当时是抱着反对封建迷信的眼光去看的。(当时管正在合阳中学上高一)听说 给了雨,但接雨的队伍到了王村,还是满天红日头。走互鹅泳村南,仍是红日头。队伍 进了庙,只见放三眼铳的往空中一打,空中的筛子底大一朵乌云,顷刻之间,乌云散开 。我一看要下雨赶紧往回跑,井溢到鹅泳不过三里路,路上回去也不过二十来分钟,但 我到家门口时便落下了雨点。
这场雨只下到鹅泳村,而且很小,根本不到南王。往南不过大天沟,就是从井溢坡到 西坡这十里烂井溢的地界上落了大雨,能种秋了。
当时祈雨,公社领导是反对的。那时正抓阶级斗争,祈雨确实是冒险行为。万一祈不 下呢?那问题可就大了。
赵德生(井溢东坡人,1996年时62岁,农民。):1995年秋旱,我联络几人到武帝山祈 雨在武帝祠献殿的墙壁上写下了两段话:“乙亥年,天大旱,井溢坡,上武山。硬要雨 ,把民安,不下雨,不下山。武帝神,听弟言,想当初,食我饭,今日里,用雨还,你 美名,世代传。”“名神名山名景,旱年旱月旱日。受饿受冷受苦,下雨下雨下雨。” 7月25日天降大雨,旱象解除。我们几个在山上待了三天,武帝袋子就把雨给了。我急 忙赶回村报讯。到村里已快半夜了,刚踏到门坡坡上便下起了雨。村里许多人觉睡实了 ,第二天早上起来才晓得下了雨。这雨就一阵儿,只下到我村的地界上,邻近二三里的 村子都没滴雨。过了几天才下了那场大雨,全县都下到了。
习永德:今年(1997年)祈雨时,我去迟了三四天。一问,说没什么情况。我说,大约 是你们给老人家没往开的说(指讲明白),老人家胡里颠东,还以为你们是开玩笑哩!现 在已快到白露,地干的种不成,赶紧要下雨哩!等到第七天,就给雨了。八月初八(公历 9月9日)夜里12点左右,飞来一只大花蝴蝶,给了大雨。农历八月十五开始唱谢雨戏, 早上由锣鼓队领着上山“打旱复”,请武帝爷和牛庄人下山看戏。当夜戏完后,十一点 多又下雨,十六日下了一天,天黑前雨停了,接着开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