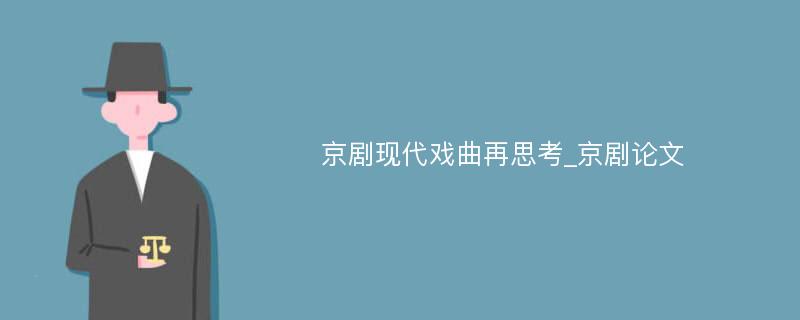
三思京剧现代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现代戏论文,京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京剧现代戏创作是戏曲界最具争议性的话题之一。2008年以来,我们又一次看到政府那只“看得见的手”对京剧现代戏创作的强力推动。如同此前京剧现代戏创作的三次高潮(20世纪50年代初、1958-59年、1964—“文革”)一样,这根敏感的神经太容易被触动,它的是非得失,也就不可避免地要成为众说纷纭的焦点。围绕京剧现代戏创作展开的探讨,不是孤立的经院式的理论命题,它涉及到对京剧的理解和对现代戏的理解,涉及到京剧的发展和前程,当然也涉及到国家的戏剧政策。它的复杂性超乎想象,实有细细分剖的必要。京剧现代戏创作包含多个不同层面的问题,至少有三个难点亟须细加辨析。这就是,京剧能否表现当下的现实生活内容,如果可以,那么京剧现代戏创作的成功可能性有多大,最后,就是如何评价京剧现代戏的代表——“样板戏”。
一、不要低估京剧的表现力
“京剧现代戏”更准确的称谓,是表现20世纪以来的生活题材的京剧新剧目。诚然,在实践中“现代戏”的指意并非如此单纯,20世纪50年代以来,“现代戏”这个词汇被附加了特殊的意识形态内涵,我曾经写有专文《现代戏的陷阱》,此处不赘。这里的讨论只涉艺术,暂且忽略“现代戏”一词的政治色彩。
戏曲(当然也包括京剧)从无题材古今的限制,元杂剧分十二科,并不用题材的年代为分类标准。“现代戏”或曰“现实题材”的京剧新作品创作受到特殊的关注,成为一个热门话题,只是晚近出现的特殊现象。表面上看,其因是19世纪后期以来东西方文化的碰撞,导致中国的社会形态以及中国人的生活方式、生活内容甚至情感表达方式都发生了重大转型,但是真正内在的原因,是20世纪50年代初以来,“表现现代生活”成为政府对京剧乃至于所有戏曲剧种提出的特殊且强烈的要求,只有在这一背景下,京剧是否应该和可以创作现代戏,才成为问题。
从20世纪50年代至今,一直流行一种观点,认为京剧是古典艺术,其表现手法,只适宜于表现传统社会的生活内容,而不适宜于表现当下的现代生活。如果用另一种说法表述这一观点,实际上是说以京剧所拥有的技术与表演手段,并没有能力表现近代社会转型以后的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内容。
京剧有没有能力表现现代生活,这既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是一个实践问题。作为一个理论问题,京剧能不能表现现代生活和应不应该表现现代生活的讨论始终扭结在一起,而有关它的讨论,至少已有近六十年历史。根据1950年底在北京全总招待所召开的全国戏曲工作会议演出座谈会的记录,阿甲在12月12日的座谈中就曾经指出,对京剧表演而言,主要需解决不能反映现代生活的问题,他明确反对周扬有关“京戏比地方戏精致一些,艺术性高一些,因此表现现实比较困难”的看法,认为“这在理论上说不过去”。
阿甲这里转述的周扬的观点在1949年以后的一段时间内非常有代表性,它就是著名的“分工论”的基础,强调不同的剧种在题材上应该各有所侧重,应该各有提倡,可以有“分工”;在肯定一些比较年轻的剧种如评剧、吕剧、沪剧等新创作的《小二黑结婚》、《小巧儿》、《李二嫂改嫁》、《罗汉钱》等现实题材剧目的成功的同时,认为像昆曲、京剧还包括秦腔和川剧等等这些诞生年代久远的、在表现手法上已经比较成熟、传统剧目的积淀比较深厚的剧种,与那些相对比较年轻的、因而尚未形成完整独特的表演程式的剧种,在表现题材上应该有所“分工”,简而言之,那些成熟的古老剧种应该仍然保持其以表现历史题材为主的传统特色,而那些新剧种既然没有多少值得去珍惜与保留的表演艺术传统积淀,就可以转而多去表现现代生活。
如同阿甲所言,这种观点的理论支撑非常牵强和脆弱,说那些年轻的小剧种在表现手法上还没有充分程式化,恰因为尚未成熟、没有多少所谓“传统包袱”,所以表现现代生活时没有“负担”,因而应该由这些剧种去表现现代生活;而那些更具历史积淀和在美学上更有优势的剧种,反而可以允许它们回避现实题材创作,不需要接触去创作与当下人们的生活与情感关系更为密切的生活内容,它的潜台词,似乎把表现现代生活当成戏曲艺术的灾难——仿佛努力表现现代生活,必然会对剧种造成致命的伤害,因此,让京剧表现现代生活的美学成本太高,至于评剧、沪剧和越剧之类,反正没有多少家底,即使它们因表现现代生活而受到伤害,也不值得痛惜。
指出“分工论”的提出后面包含的这些潜台词,并不是毫无根据的揣测,当戏曲表现现代生活不是出于戏剧家以及观众的欣赏需求,而成为政府向戏剧界分派的宣传任务时,躲避甚至拒绝现代戏,就成为戏剧艺术家们努力捍卫戏曲本体的特殊的策略。其实,时至今天,各种各样的“分工论”之所以仍有不少呼应者,主要不是由于“分工论”在理论上的说服力,更在于它是传统戏剧拒绝成为政治宣传工具、遏止政治对戏曲的肆意凌辱的有效借口。正是由于有戏剧发展的实际需求,这个确实“在理论上说不过去”的观点,才有其格外顽强的生命力。
如果回归到理论层面,冷静地讨论京剧表现现代生活的问题,就应该承认,“分工论”的提出固然有现实的背景,却缺少了更重要的符合戏剧艺术本身规律的理由。
当人们说京剧不能、或不适宜于表现现代生活时,主要的理由是说京剧表演包含大量的程式化手法,它们的指意和现代人的生活内容很不一样,京剧诞生于传统社会,它在起源与成熟的漫长历程中渐渐发展出来的那些舞台手段,用于表现古人的生活内容,表现历史故事和历史场景很合适,而用来表现今人的生活是不合适的;且这些手段迥异于当下环境里人们的举止言谈,在舞台上用这样的方式扮演现代人,会和人们的日常生活经验产生冲突。但人们似乎没有注意到另一方面,京剧、戏曲这种特殊的艺术样式,几乎它的所有表现手段,和人们在现实与历史中的实际生活之间,都刻意保持明显的距离,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说,这种艺术样式表现任何时代的生活,都是不合适的。假如拘泥于京剧以及所有戏曲剧种的舞台表演手法与它们所表现的生活内容之间是否具有相似性,当人们说京剧不易于表现今人生活时,同样可以说,京剧很难表现秦代、唐代或晋代人,以及别的什么朝代人们的生活。20世纪40年代的延安,有戏班子让抗日将领彭德怀身穿蟒袍背插靠旗,上台自报家门“我乃彭德怀是也”。它一直被当作反面教材备受嘲笑,但是嘲笑戏班如此扮演彭德怀的人未必是普通观众,不过几十年前,京剧《八大拿》演清代豪杰却不穿清代服装,被观众普遍接受了;清末田际云将《洪杨传》改编成《铁公鸡》,舞台上的人物虽着清装,表演功架以及武打却一仍其旧,刚刚见识了湘军的观众们并没有拒绝;相反是时装戏《潘烈士投海》里的主人公穿西服上场,被座客哄笑。在一般观众眼里,只要是他们已经接受、熟悉并喜爱的舞台表演手法,即使与其表现的人物事件有些外在形态上的差异,却未见得非要穷究不舍。
京剧的现代手法与现今人们的生活固然有很大的距离,但它与古人的生活,未见得距离就更小。耕、读、渔、樵,农耕时代这些生活内容需要在舞台上用戏曲的手法表演,同样需要克服很多表演上的障碍。戏曲表现古代社会的生活和表现现代社会生活都不容易,尤其是在需要表现超越日常生活的政治与战争等宏大题材时。《挑华车》表演古代战争场面,演员所运用的手法我们早就习以为常。然而,一个从未见识过这些已然呈现在戏曲舞台上的表达方式的人,会很难想象用京剧的舞台手段如何表现这样一场战争,尤其是如何去表现杀伐征战的场面。漫长的古代社会里任何年代的战争,都不是以京剧舞台上所呈现的那种方式进行的,它从来就不是两个将领穿着如此夸张的服饰同时出场,互报姓名,然后对打以分胜负。从先秦到汉唐直至宋元明清,两军之间的交战都和我们在戏曲舞台上看到的情形大相径庭,历史上实际的战争,那种血淋淋的场面,那种数以千计、数以万计的兵士们参与其间的大规模战争,与戏曲舞台上所看到的战争场面,差异之大简直无法形容。战争不是两个人的格斗,戏曲表演艺术家们创造性地将两支军队之间大规模的战争,借舞台上少数几个人物的格斗的形态呈现在观众面前,这就完成了从生活到戏曲的特殊的艺术转换,这种转换之所以必要,恰由于战争之无法在舞台上直接表现。
我们之所以不去质疑在舞台上表现古代战争的可能性,不是由于戏曲的表演手法与古代社会中实际发生的战争比较近似,而是由于千百年来,我们的戏曲表演艺术家找到了合适的方法,用以象征性地、表意性地表现古代的战争场面,并且为人们普遍接受了,观众们因此不再由于舞台上的战争和实际的战争之间存在很大的距离而觉得不习惯、不接受或者不理解。
有种观点认为现代社会已经变成机械时代或者信息时代,它不同于戏曲所表现的手工时代,身体的姿势与动作已经不再重要,戏曲丧失了它所擅长表现的农耕时代或者冷兵器时代主要依赖身体行为的生活对象,因而遭到时代的遗弃;更有人举例说,现代社会的象征与代表是宇宙飞船上的杨利伟,可是他的所作所为完全没有动作性,因而戏曲无法表现。如果要举杨利伟为例,那我们可以有另一种思考,坐在完全封闭的轿子里的女性,她的处境与行为岂不是也和杨利伟差不多?京剧《锁麟囊》“春秋亭”一场,就在舞台上让两位出阁的小姐各自坐在轿子里对唱,正因找到了特殊的舞台处理方式而成为经典。
传统戏曲甚至解决了骑马、划船这些比乘坐现代交通工具更不易表现的难题。以《秋江》为例,手里拿着桨的艄公固然有很强的动作性,但坐在船上的陈妙常却没有什么明显的动作性;要解读戏曲表现手段的奥秘,关键不仅在于艄公的表演,更在于陈妙常的表演,乘船追赶心上人的陈妙常找到了她特殊的舞台手段,充分运用多种表演手段将内心外化,把一个坐在江船上的姑娘演得令观众陶醉,她才是戏的主人公;骑马对舞台表演更是巨大的挑战,戏曲演员用象征性的马鞭以及类似骑马的形体动作代替骑马这种难以表现的行动,以避免将真马牵到舞台这种既不方便控制也不利于表演的尴尬局面,同样需要完成从日常行为到戏剧语言之间跨度极大的转换。戏曲舞台上以桨为船,以旗作车,只是转换的结果,而且这样的转换,用这种表演形式实现转换而不是用另一种转换形式,其中充满了艺术的偶然性。恰由于偶然,戏曲表演充满了张力,充满了变化的可能与发展空间。
笼统地说,原则地说,戏曲表演将日常生活转换为虚拟性的舞台身段,这一规律相对于古今中外千变万化的戏剧题材,似有难易之分,实为生熟之别。既然京剧可以表现坐在船上的陈妙常和坐在轿里的薛湘灵,有什么理由认定它无法表现宇宙飞船里的杨利伟?当然,我们不能简单地否认不同艺术形式有其最适宜的题材和人物类型,然而,简单化地用时代的差异去判断什么题材、什么人物适宜于用戏曲表现,同样缺乏理论支撑。无论是恢宏的战争场面还是庸常的日常生活,叱咤风云的英雄还是朴实无华的平民,是否适宜于用戏曲表现,关键不在于它们与戏曲通常习见的表演程式是否有距离或有多大距离,关键在于我们能不能找到合适的表达内容,为戏剧家想表达的对象找到精彩的舞台手段,跨越生活与艺术之间的巨大鸿沟,完成从生活到戏曲表演的创造性转换。
从这个角度说,京剧没有多少艺术的理由以拒绝和回避现代生活。记得张庚老晚年多次指出,京剧艺术的表现力还远远没有穷尽,我觉得这是讨论京剧现实题材剧目创作时最值得思考的精到表述。在这个意义上,说京剧无法表现现代生活,那是低估了京剧这样一门卓绝非凡的舞台表演艺术样式的可能性,低估了京剧的表现能力,低估了京剧表演手段的拓展空间。
其实近几十年来,戏曲艺术家不断在寻找各种各样的方法,努力尝试着现实题材的京剧新剧目创作,取得的成就不能完全无视。只是由于现实题材的戏曲剧目创作经常被用以为政策宣传的工具,更由于文化大革命时期那些被称为“样板戏”的现代戏曲作品沦为了政治斗争工具,才激起戏曲界内外对现代戏的强烈反弹。如果撇开政治的干扰,现代生活不应该是京剧题材领域的盲区,更不应该成为京剧舞台表现的不可逾越的障碍。继续深入挖掘和展现京剧表演艺术的表现力,现实题材的京剧创作,完全有可能出现优秀的传世佳作。
二、不要低估京剧现代戏的困难
用戏曲艺术的特殊手段表现生活内容存在种种可能性,在表演艺术家们寻找到某种特定的手法表现与之相对应的生活内容之前,我们永远都无法想象这些生活内容可以如何去表现。因此,轻言哪些生活内容不适宜于戏曲,不适宜于京剧,背后缺少的,恰恰是对表演艺术家们应有的尊重。
诚然,肯定京剧现实题材创作的可能性,只是问题的一方面。另一方面,出于非艺术的原因,轻率地不负责任地推动和鼓励京剧院团以及戏曲艺术家创作现实题材剧目,容易走入另一个误区,那就是,既低估了京剧表现现代生活的困难,也低估了京剧艺术家们在培育与发展京剧过程中所做的美学贡献。
京剧表现生活,但京剧并不是简单化地通过单纯模拟的途径表现生活。王国维称戏曲是“以歌舞演故事”,齐如山说国剧“有声皆歌,无动不舞”,虽然上述定义仍有许多可以深入讨论的空间,但是在戏曲拒绝用模拟生活的方式表演这一点上,他们都指出了戏曲最重要的美学原则。这是京剧表演的特点,又是京剧表演的难点。京剧表演形态与它所表现的生活内容之间的关系,应该在“似与不似”之间,然而,恰因这似与不似“之间”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抽象与具象之间分寸感的拿捏,就成为决定表现是否成功的关键。京剧的表演与生活有距离,但这种距离并非刻意地要以有异于日常生活为目标,而是为了通过写意的舞台处理,找到更传神、更凝练、更具韵味与魅力的身体手段,通过表面上“不似”的形体语言,实现对戏剧人物与行为更具表现力的艺术传递;即以旦角演员最常见的水袖论,观众认可与否的要义不在于袖之长短,而是一招一式中传递的戏剧内涵,尤其是通过技术上的不断完善和提升,使之足以完成叙事抒怀、表情达意等复杂的任务。因此,水袖固然非现实生活中所有,却因其足以表达观众期待演员通过表演可能表达的内容,并且更具欣赏价值而被普遍接受;戏曲表演虽然在表现上有异于实际生活,却能够让观众通过舞台表演清晰准确地感知戏剧内容,因而所有那些与实际生活有异的形式感很强的表演,都只能是“有意味的形式”,因而是观众可以具体、准确地感知其戏剧内容的形式,这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表演程式”。
京剧之难,就难在程式与它所表现的对象之间“似与不似”的恰如其分,因而它的发展与成熟,无论是水袖还是脸谱,都需经历较长的过程,需要积累,更需要在与接受者的互动过程中逐渐得到观众的充分认可。京剧舞台上高度程式化的表演,从最初的探索到最终为观众普遍接受的漫长过程,其中积淀的前辈艺术家的创造与艰辛,很容易被今人忽略。要撇开这些珍贵的积累另起炉灶,那我们得问问自己美学上的准备是否充分,理由是否充足。尤其是现实题材的创作,既然我们因拘泥于现实题材剧目的舞台呈现与现实生活之间的形似,拒绝水袖这类写意传神的表演程式,那么,今天的演员们怎样才能发展出更好的、至少同样好的表演手段,用以替代扮演古代女性的演员们只需用水袖不经意地传递给观众无限丰富意蕴的精湛技艺,并且在很短的时间里得到观众的认同?前辈艺术家发明了戴髯口时丰富的表演,不戴髯口,演员用什么填补这表演的空白?这就是现代戏要成为“戏”必须跨越的铁门槛,如果意识不到这一跨越的难度,就极易被现代戏创作的盲目乐观情绪所支配。
近年里江苏京剧院的《骆驼祥子》和天津京剧院的《华子良》都因其致力于用戏曲化的虚拟表演表现现实生活而受好评,但我们还得承认,《华子良》“下山”的精彩,是由于人物行动经过了高度戏曲化的处理,因化用大量传统技法为新剧目所用而博得好评,可惜精彩未能贯穿于整部作品;而《骆驼祥子》里的“洋车舞”要成为新的表演程式,还需超越拉洋车这种过于具体的戏剧行动,使类似的表演手法可以在更多场合通用。进一步说,京剧现代戏创作是否可能成功,不仅需要创造出像我们在《骆驼祥子》、《华子良》里所看到的那些具体的招式,更需要通过新剧目中大量的观众认可的新型戏剧人物的塑造,形成一系列新的戏曲程式与行当——“行当”的意义在于它通过某一类型的戏剧人物,将一些零散的舞台表演手段凝聚成相对完整的系统,由这一系统化的形体手段搬演戏剧人物。京剧艺术发展的历史就是行当生成与发展的历史,通过对戏剧人物的类型化处理,构成一系列为观众普遍接受的抽象与具象相结合的表现手法,包括手眼身法步在内的身段和造型,形成完整的表演语汇。没有新的行当就意味着现代戏表演方面的技术手段仍然是一盘散沙,没有舞台语言,没有表现语法,所以,它们在艺术上就必然是支离破碎的,难以形成一以贯之的表演美学。
这才是京剧现代戏创作的困难所在,京剧现代戏的创作并不是难在为内容不同的每部戏找到不同的新招式,而在于在表演上是否真有可能通过新的行当,建立有异于传统风格的新的美学。每个时代都会涌现出一些优秀的戏剧艺术家,几十年来京剧现代戏的创作已经有了一定的积累,但是这种积累还远远不敷使用,离系统化就更远;兼之在现代戏创作中,京剧艺术家们经常被要求按照一种很狭隘的戏剧观念,以各行各业的英雄模范为戏剧主人公,以行业而非人的情感、生活与命运为关注焦点,导致京剧在努力表现现当代戏剧人物及其行为的过程中缺乏足够的连贯性,舞台表演手段的探索无法经历相互间的借鉴与继承,以渐渐形成新的、系统的程式化表演手段以及新的行当,这些都严重影响了现代戏创作的发展进程。
如果说1958年政府大力推动现代戏创作,声称要“以现代剧目为纲”,“苦战三年”争取戏曲舞台上现代剧目的比例占到20%-50%,因而在全国掀起一个畸形的现代戏创作高潮,还可以归之于“大跃进”的疯狂,那么,假如忘却当年以政治运动的方式“大写现代戏”后戏曲界一片狼藉的教训,忽视用戏曲表现现实生活在表演上的诸多难题,当年“写得快,演得快,丢得快,观众忘得快”的情景就很容易再现。假如现代戏创作不能完全承继传统剧目的表演手法,无论是依托于传统戏曲身段的现代转化,还是重新摸索与创造新颖的舞台形体动作,都需要长时间的认真探索,才可能创造出一整套新的程式化表演手段;在此基础上,还需要经过大量的艺术实践,让观众逐渐接受并且充分认可这些既是“现代”的、又是京剧的手段。而实现这一目标,都需要智慧、灵感以及时间和耐心。
三、历史地认识京剧现代戏创作面临的挑战
除了具体表演手段的探索,京剧现代戏创作还在面临更大的挑战——创作的成败,要从京剧发展历史的维度予以评价。
京剧并不是凭空出世、从天而降的剧种,它从起源至今虽然不过150年左右历史,却继承了汉剧、秦腔、昆曲等历史悠久的剧种大量的传统剧目以及诸多表演手法,集花部、雅部之长于一身;而戏曲自宋元年代诞生以来接近千年的漫长时间里,尤其是从昆曲到皮黄,无数代戏曲表演艺人通过表演实践以及在演出市场中与观众的良性互动,逐渐积累了丰富多样并且为观众所充分认可了的表现手法,而大量的经典剧目就是凝聚着各种各样具有代表性的表现手法的结晶。这些经典以及被浓缩在经典剧目中的丰富的技术手段,是京剧艺术发展的重要依托,它使京剧这样一个诞生时间并不太长的剧种,一跃成为最足以代表中国戏剧所达到的艺术成就的剧种之一。京剧所拥有的丰富而精彩的表演手段,是千百年来无数艺人代代积累的精髓,京剧历史上留存至今的丰富的积累,集中在传统社会生活领域,因此历史题材剧目新创作可以借鉴的表现手段,必然远远多于现实题材新剧目创作。
历史地看,数十年来,至少是在中国社会因现代转型而发生重大变化以来,京剧有过许多表现当下故事、人物与生活内容的成功经验,这是我们今天讨论京剧现代戏创作不可回避的背景。完全否认京剧历史上在表现现代生活方面曾经取得过的成就,既不客观,也不理性。然而今天我们重新思考京剧现实题材新剧目创作时,还需要认真、客观且理性地看到,京剧表演历史题材、表现传统社会生活取得的成就,才代表了京剧之艺术水准;相比表现现实题材的剧目,表现历史题材的剧目要远远丰富得多,其艺术成就也要远远高得多。
因此,当代京剧艺术家在创作新剧目时,不同时代的题材选择就意味着不同的起点。题材的时代差异,意味着可资运用与借鉴的表现手段之间有着非常之大的差异。如果说对任何一位当代京剧艺术家,新剧目的创作都要面临一个重大考验,那就是他的创作——从剧目的整体水平到表演中的一招一式——将要被放置在京剧发展历程这个大背景下加以衡量。人们判断某个新作品是否成功,甚至衡量它“是”京剧或“不是”京剧时,所运用的标准不仅仅是技术的或概念的,而且还是美学的;不仅是静止的,更是动态的和历史的。同样,对一部现实题材京剧作品成功与否以及艺术价值的评价,不仅是对一部独立的艺术作品的个别的判断,这种判断不会完全脱离京剧的历史文化积淀,必然要将它放置于京剧历史发展的维度中衡量;也就是说,京剧在表演艺术上已经拥有如此之高的成就,使得任何新的京剧创作达到的艺术水准,都须“对得起”京剧这个称谓,这样的作品才配称之为“京剧”,这样的舞台表演,才被认为是“戏曲化”的,或“京剧化”的。
如此看来,近几十年里相当多现实题材京剧新剧目的创作,就其本身而言也许不无亮点,也未必都不受观众欢迎,却始终难免“不像京剧”之讥。当人们说这些新剧目不姓“京”,“不像京剧”时,除了指其在音乐与表演上疏离了京剧的传统与美学原则,更多场合是说它就其整体水平、或仅就表演艺术上达到的水平而言,与京剧已有的高度并不相称。当人们努力去演绎新的时代与生活时,忽然发现这样的演绎所达到的艺术高度离京剧传统距离甚远,困惑甚至反感也就因此而生。
京剧新剧目创作要得到观众普遍认可并不容易,而现实题材剧目要达到这样的高度,就尤为艰难。如果说对于当代京剧艺术家而言,戏曲美学规律已经为今人提供了表现任何时代的生活内容所普遍适用的原则,那么,一旦舞台表演进入许多具体而微的细节的表现时,有没有可资借鉴的传统,以及能够多大程度上借鉴传统,就决定了创作的难易之分,并且会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创作取得成功的概率。假如现实题材创作决定了艺术家们几乎只能从零开始,完全依赖自己一己之力寻找新的舞台表现手段,我们就很难对它有多少期待。
京剧诞生150年左右,任何时期都有新剧目不断涌现。优秀剧目的成功大多是天才的后人较好地继承并发展了前辈艺术家的创造性成果而获得,很多精彩的舞台表演手段,在昆曲、高腔、梆子时代就已经发展得相当成熟,而那些表现传统故事与人物的剧目尤其如此;然而,当京剧要表现一类新的题材以及新的故事与人物,要想让京剧去表现另类的题材,更由于误认为传统手法不足于或不适宜表现当下生活,艺术家只能在舞台上痛苦地探索尝试,要寻找到足够丰富的新的、具有同等表现力的舞台手段,谈何容易。这也就是此前数十年里大量不成功的现实题材新剧目被人们讥为“话剧加唱”的原因所在,尽管话剧在中国戏剧界一度很受推崇,戏曲甚至被认为应该向“先进”的话剧学习,而在多数场合,“话剧加唱”基本上是个贬义词,指的就是表演上未能充分和流畅地运用戏曲手法,缺乏戏曲应有的韵味的新剧目,其中又主要是指背离戏曲美学原则的现实题材新剧目。
用戏曲手段演绎现实题材、表现现实生活,将人物及其活动充分戏曲化并不容易,要让这样的创作与传统经典剧目显得旗鼓相当更有难度。千百年来留下来的那些经典剧目,已经有前辈艺术家创造积累的高度成熟的表演手段,它们具有很强的表现力和感染力,并且已然为观众所熟悉与认同,然而一部新创剧目的舞台表演水平很难在短时间里达到同样的高度,因此,新创剧目、尤其是现实题材新剧目要能和这个剧种的经典相提并论,其困难可想而知。就以最常见的京剧传统剧目《玉堂春》为例,多少年来无数演员在舞台上表演这出戏,千锤百炼才打磨出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格局。不仅如此,它的表演手法不是孤立的,因为与诸多相似与相关的剧目形成“互文”,已经成为整个京剧表演传统的有机组成部分,一招一式,每个场景和每个具体的戏剧动作,人物的内心世界和外在表现,就是京剧这座传统大厦中的一砖一瓦。编排一部新戏时,我们或许能从传统技法中汲取一些营养并将其转化为表现现代生活所用,在个别场景还能够找到某些新的卓绝手段,可是新创剧目很难有那么多机会,从头到尾充分调动剧种千百年来的积累,使表演在整体上达到与传统京剧相称的水平;至于现实题材创作,如果非要强调它与古代生活的差异,就更少现成的技术手段可资利用,而且,在利用传统手法时还需要时时注意要与其所欲表现的对象之间的对应关系。
观众对新剧目的评价必然涉及复杂的历史因素,因而,对现代戏创作面临的困难更应有充分估量。如果执意拒绝接受观众以及历史的褒贬,时间终究无情,自会给予种种罔顾艺术规律的鲁莽创作以相应的答案。
现实题材新剧目创作要想达到令人满意的结果,要走的路还很长,且很险。看不到困难所在,或者低估了京剧现代戏创作的困难程度,贸然地推动和鼓励剧团关注现代题材,甚至对这样的创作抱着不切实际的期许,只会遭遇挫折。
四、总结汲取“样板戏”的经验和教训
现实题材京剧创作不是新事物,近几十年来,政府曾经多次基于各种原因,鼓励和推动京剧现代戏创作。诸多经验与教训,值得严肃地总结与汲取。无论基于什么立场,想要认真讨论京剧现代戏,都不能回避数十年来的京剧现代戏创作的准确公正的评价,尤其是离不开“样板戏”。
无论我们今天如何看待“样板戏”在艺术上的得失,希望复制样板戏当年的辉煌,始终是现代戏创作中挥之不去的心结。从1964年的“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到1967年前后主要由京剧现代剧目组成的“八个样板戏”在表演艺术领域形成无可动摇的垄断地位,现实题材戏曲作品创作的影响达到了巅峰。改革开放以来,围绕着京剧样板戏的成败得失有各种观点。无论把这些剧目单纯看成江青“阴谋文艺”的产物,还是将它们完全说成是“广大革命文艺工作者”辛勤创作的丰硕成果,是江青“窃取”了广大京剧艺术家的成就,恐怕都与事实有悖。对样板戏准确且尊重历史的表述应该顾及到多个层面,其一,无论在哪个阶段,这些剧目始终笼罩在让艺术服从现实政治需求这一阴影下,它们既有很强的艺术性,又都不是纯粹的艺术品;其二,既要看到这些剧目创作过程中许多艺术家的集体创造,同时也应承认江青个人的突出作用,尤其是1964年以后,江青主导了这些剧目的创作与修改,并且在其中多方面地、充分体现了她个人的政治与美学旨趣;如果说一代京剧艺术家在让现代戏创作为政治服务的过程中确实在技术与舞台表现上精益求精,那么,用“呕心沥血”来描述江青的参与也不过分。
样板戏创作既是一个复杂的政治过程,同时也是一个复杂的艺术过程。它代表了延安时代以来现实题材戏曲剧目创作最高成就,同时又对后世的戏曲现代戏创作产生着巨大影响。客观地说,样板戏是京剧现代戏创作留下的最重要的成果,而直至今天样板戏的许多唱段仍为人们耳熟能详,也不能仅仅用怀旧来解释。现实地看,当下京剧舞台上流传最广的剧目就是两大类——传统戏和样板戏,也就是说,样板戏几十年来形成了某类剧目的代表或范本,它其实已经成为京剧新传统之一,是我们今天要面对的京剧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无法抹去也无从回避。样板戏的存在充分说明让普通观众接受京剧现代戏并非完全没有可能,当然,样板戏的历程同时也意味着想要简单化地推动京剧现代戏的创作未见得可行。
样板戏在努力解决用有异于京剧传统的手法表现现实题材的难题上,取得了不菲成就。如果有人要用京剧样板戏的存在和成就,证明京剧可以在新的美学原则基础上成功表现现代生活,在一定的意义上,至少是在艺术的意义上,不能说一点没有说服力。因为,至少是20世纪50-70年代开始接触京剧的两代观众,曾经不同程度地接受了京剧样板戏的艺术风格与表现手法,很少有人觉得样板戏是艺术的怪胎,对这些欣赏样板戏的观众而言,用京剧表现现实生活并没有多么难以接受。换言之,其实在样板戏泛滥的年代——无论我们多么痛恨令样板戏横行而压抑其他所有京剧传统剧目的极左政治霸权——以样板戏为代表的京剧现代戏已然是现实的且有影响力的存在。
样板戏与传统京剧的内容及风格确实有明显的距离,无视样板戏已然为两代人接受这一现实,只能说是艺术上的鸵鸟心态。但是,样板戏为什么能够在京剧舞台上立足,为什么这些有异于传统京剧的剧目能够存在并且为观众所接受?要解答这个问题,还不能仅仅从京剧表现现实生活的角度分析回应。
样板戏是一段京剧史的厚重积淀,这段历史,包含了从延安时代以来在京剧表现现实生活领域的漫长的探索。它的背景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特定的戏剧环境,这个时代占据主流地位的戏剧理论,对京剧用传统表现手法创作现实题材剧目的价值与可能,表示了坦诚尖锐的怀疑。特别指出这一点,是由于在此之前,以京剧界的梅兰芳为代表的无数曾经涉及现实题材剧目创作的戏曲演员,并没有真切地感受到有如此迫切的疏离传统的必要,更不觉得需要为这些被特地命名为“现代戏”的戏曲新剧目创造一整套全新的舞台表现手法。20世纪50年代以来戏曲理论界对传统手法表现现实题材的强烈质疑,形成一种持续不断的压力,艺术家们只能努力寻找新的与传统京剧迥然不同的舞台手段,于是才有从京剧《白毛女》开始的现代戏创作过程。京剧的舞台表演形态因此得到大幅度的拓展,迥异于传统戏的样板戏就是它最后的标志性结晶。在这一过程中,无论是在创作第一线的京剧艺术家们还是江青,确实在既充满信心、又小心翼翼地试图解决现实题材戏剧创作遇到的各种理论和实践难题,而江青的思考与尝试是这个过程中最重要的、并且是集其大成的部分。诚然,创作过程中始终面临诸多政治的干预,因为屈服于意识形态需求而违背艺术规律的现象也屡见不鲜,但是在整体上,无论是剧本、音乐、表演还是舞台美术等所有领域,创作者围绕如何化用京剧已有的艺术手段,力求完美传神地用京剧的方式传递艺术内涵,在艺术与政治的博弈中,尽可能地展现京剧的内在特色与优势,这就是样板戏能够取得一定艺术成就的根本原因。它们给京剧带来的改变,当然不是梅兰芳式的“移步不换形”,但是,至少做到了政治与艺术、新的美学追求与传统京剧之间尽可能的相互妥协,以及基于此之上的戏剧的完整性。
样板戏经历漫长的创作历程,才出现了这些足以传世的作品。其中一个值得记取的成功经验,就是京剧行话说的“讲究”,慢工出细活。样板戏是“讲究”的创作,“讲究”的艺术品,而无论是整体还是细节,从主要人物到群众演员,从表演、唱腔、伴奏、化妆到舞美等等,自始至终,每个环节都非常讲究。这种讲究的背后就是理想,有一个相对成熟的、固定的理想,为了这个理想去努力。在某种意义上说,样板戏是有理想的艺术,这里所谓理想包括两部分——政治理想和艺术理想。我们可以完全不认同样板戏的政治理想,这些高度意识形态化的政治观念导致了对人性的压抑甚至摧残,并且它是营造着虚伪的假大空的根源,可是样板戏创作中自始至终毕竟有一以贯之的政治理念;是非固然需要重新评价,至少它们是经历多年积累、有丰富的感性材料和历史内容的思想与理念,是一些经过深思熟虑的理想和人生信念,而这正是防止戏剧创作流于肤浅和表面化的重要力量。当然,艺术的理想同样重要,甚至更重要。样板戏的艺术理想内涵既丰富又复杂,其中也不无互相冲突自相矛盾之处。无论我们在整体上和各细节上是否认同和接受这些艺术观念,这些艺术观念同样也自始至终地贯穿在样板戏创作中。正因为样板戏是一种有理想的艺术,所以我们看到样板戏的整个创作过程,人们为实现这些理想费尽心血,不惜代价,如果今天从事京剧现代戏创作的人们能像当年样板戏的创作群体,为实现某种理想——无论这些理想是否正确——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段里,全身心投入创作,或许也有可能创作出新的、能经得起时间检验的作品;然而问题恰恰也就在这里,在一个创作人员普遍缺乏一直坚守的核心价值的艺术环境里,无论是现实题材还是古代题材,都难以取得令人满意的创作成果。
样板戏决不完美,政治与艺术的缺陷比比皆是,两者之间的矛盾与冲突,更是屡见不鲜。但是它的创作者努力在政治诉求和京剧规律之间寻找平衡点,即使有很多不尽如人意之处,这样的努力还是足以避免使作品成为空洞无物的赝品。更重要的是,一以贯之的政治与艺术理想帮助作品形成了自己一套相对完整的艺术语汇,甚至因人物的类型化而形成了某些新的行当——比如已经拥有许多形体与语言标识的女干部——和不少程式化的舞台手法。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此前数十年里支配了京剧现代戏创作的那套理念有足够的合理性,也不能因为样板戏的存在,就简单地以为今天的创作者仍然可以亦步亦趋地复制样板戏的模式。样板戏现象的重现需要太多前提,它旧日的辉煌很难成为现代戏创作的范本,为当下的现代戏创作导出一条走向成功的坦途。
除非我们大胆地沿用京剧历史上已然形成的基本表演手段,如果说在戏曲现代戏创作过程中,传统的戏曲舞台表演手法必须置换,那么,现实题材戏剧创作就需要努力去建构新的为业内外人士充分认同的一定之规,需要像历史上戏曲形成的漫长过程那样(至少像样板戏那样经历几十年的孕育创作期),由一代又一代艺人经过长期的摸索,形成新的相对完整的体系化的舞台表演程式,并且,进而还需要新的帮助新一代演员掌握这套表演程式的人才培养模式。如果这条道路既漫长又艰辛,那么,重回样板戏是否有可能?经历三十年改革开放,中国戏剧大约很难回到“文革”时代,尤其是当政治与艺术的压力不复存在,人们还有多少理由按照江青模式继续走样板戏的创作道路,就很值得怀疑。现在的戏剧环境已经与20世纪60年代完全不同,无论中国古代戏剧传统还是西方现代派与后现代戏剧都不再是禁忌,而恰恰在艺术表现的空间迅速扩大之后,京剧艺术家们不再需要刻意地去按照江青所规定的路径创作,艺术家拥有更多选择,却更容易左右摇摆,失去方向。多元的时代,更需要艺术家们有足够的耐心和更多相互交流的机会,珍惜一点一滴的艺术积累,为现代戏闯出一条新路。
这就是后样板戏时代京剧现代剧目创作的困难,今天的创作者,从剧作家、导演到演员,都必须正视这一困难。盲目地照搬样板戏模式既不可行,要想在短时间内做出接近于样板戏的创作成就更不可能。
我不想劝告当代京剧艺术家放弃创作现实题材的京剧新剧目的追求。我只想说,艺术层面的梳理与辨析对京剧现代戏创作是有益的,因此愿与读者同行分享我对京剧现代戏创作三方面的思考,名为“三思”,同时也意在敦请有关部门,在推动与鼓励京剧现代戏创作时,三思而后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