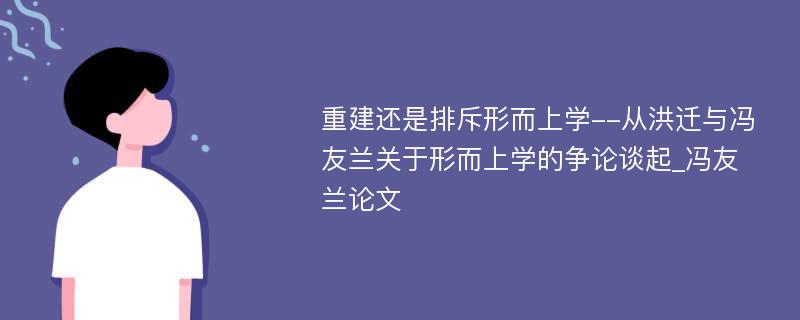
重建还是拒斥形而上学——从洪谦和冯友兰关于形而上学的论争谈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形而上学论文,谦和论文,冯友兰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08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353(2002)01-0050-05
20世纪30年代前后是维也纳学派的鼎盛时期。众所周知,维也纳学派的哲学家关注的一个主要问题就是要坚决而又无情地拒斥形而上学。其实在西方哲学中,反形而上学有着悠久的传统。维也纳学派只不过将之推向了一个极端。所以在当时的西方哲学界,拒斥形而上学成了一种不可逆转的哲学潮流。于是坚持形而上学的哲学家们感到大势已去,节节败退,以至于无处藏身。
但在中国哲学界,情形却截然不同。许多哲学家清楚地知道西方哲学家的反形而上学的立场,然而他们却偏偏要坚持形而上学的哲学立场。于是在30或40年代的中国哲学界却出现了与当时西方哲学界不同的潮流,即形而上学的哲学思潮左右着中国当时的哲学界。如在当时的中国哲学界有着重大影响的哲学家冯友兰、熊十力、金岳霖等人都建构了自己的形而上学哲学体系。这些哲学思想体系是中国现代哲学的主体。然而,需要指出的是,也有学者在积极努力地反对这种坚持形而上学的立场。洪谦就是这样的一位哲学家。他以冯友兰的“新理学”的形而上学思想体系作为靶子,对之作了坚决的批评。
洪谦和冯友兰在如何对待形而上学的问题上所发生的争论,按其性质说就是逻辑实证主义者和新实在论者之间的争论。这场争论虽然发生在1946年11月11日的中国哲学会昆明分会的第二次讨论会上,但是洪谦和冯友兰在关于形而上学的看法上是历来就有矛盾的。据张岱年在《回忆清华哲学系》一文中的叙述,洪谦和清华哲学系在哲学观上是有明显的分歧的。张岱年说:“在1936年的一次讨论会上,张岱年提出,有的哲学家注重建立‘统一的世界观’,有的哲学家则认为哲学的任务只是对于科学命题进行分析。当时金岳霖先生接着说:我现在就是要建立‘统一的世界观’。其后不久,他的《论道》写成了,这是以分析方法建立形而上学体系的重要著作。”冯友兰也在差不多的同时建立了自己的“新理学”的形而上学哲学体系。当时也在清华哲学系的洪谦的哲学观显然是不同于金岳霖和冯友兰的。在提及这一点时,张岱年这样说道:“洪谦于1936年曾到清华哲学系任教。洪谦在奥国受学于石里克,是维也纳派的成员,坚持维也纳派的关于哲学的观点。他注重运用分析方法,但反对任何建立本体论的企图。因此,洪谦不同意冯友兰的‘新理学’与金岳霖《论道》的学说,因此洪谦与清华哲学系的关系趋于淡化了。”[1]可见,洪谦与冯友兰及清华哲学系在哲学观上的争论是由来已久的。
在昆明讨论会上,洪谦发表了《论〈新理学〉的哲学方法》的演讲,对冯友兰的《新理学》的哲学思想方法提出了直接的尖锐的批评。在洪谦发言之后,冯友兰本人当即提出答辩,金岳霖及沈有鼎亦先后发言,设法替冯友兰解围。像这样针锋相对地就某一哲学问题进行直接的讨论应该说是很有意义的。遗憾的是,在讨论会上,冯友兰及金岳霖、沈有鼎的发言没有直接的记录,所以我们现在难于了解当时争论的具体情形了。但是洪谦的文章全文刊登在《哲学评论》第十卷第一期上。此文是针对冯友兰的《新理学在哲学中的地位及其方法》而写的。冯友兰关于自己的哲学在中国哲学史、世界哲学史上的地位曾经有过多次的论述,除了上述的文章之外,他在自己的专著《新理学》、《新知言》、《新原道》等书中都有极其详尽的论述。
在冯友兰看来,维也纳学派的哲学纲领就是要拒斥形而上学。而维也纳学派拒斥形而上学的主要手段便是关于命题的理论及其命题证实的理论。冯友兰认为,维也纳学派分命题为两类,一类是分析命题,一类是综合命题。命题只有这样的两类。一个命题不是分析命题就是综合命题。综合命题是关于经验事实的命题,它的意义存在于它的证实方法之中。这也就是说,一个综合命题必须有可证实性,然后才有意义。冯友兰指出,分析命题,我们在形式上就可以断定它是真的。分析命题的特点在于,如果我们否认这样的命题就必然会陷入自相矛盾之中。所以这样的命题是必然的真的。因此分析命题也可称之为必然命题。逻辑和数学中的命题就是这样的命题。在冯友兰的理解中,维也纳学派拒斥形而上学的主要理由是,他们以为形而上学中的命题都是综合命题,又都是没有可证实性的,所以形而上学中的命题也就是没有意义的命题。这样的形而上学中的命题类似于“砚台是道德”、“桌子是爱情”等的似是而非的命题,显然是毫无意义的。传统形而上学讨论的命题如“上帝存在”、“灵魂不灭”、“意志自由”等命题,无论你对之作肯定还是作否定,这些命题都是没有意义的。因此,冯友兰认为维也纳学派拒斥这样的形而上学是对的,是有根据的。
但是冯友兰紧接着指出,虽然维也纳学派能够推翻传统的形而上学,然而他们却不能拒斥他自己的形而上学。因为他自己的形而上学不在维也纳学派批判的范围之内。为什么呢?他认为,他是要“经过维也纳学派的经验主义而重建立形上学”。这一重建的具体途径就是利用逻辑分析的方法来对经验事实作所谓的形式的分析,“由分析实际底事物而知实际,由知实际而之真际”。他的形而上学的要义在于要从经验事实出发,进而从中演绎出没有任何经验事实的形而上学所需要的全部观念。由于对经验事实只作形式的分析,所以在冯友兰看来,真正的形而上学的命题必须是“一片空灵”的。可见,在冯友兰本人看来,他的形而上学的全部命题是毫无经验事实内容的,所以这样的命题是不容易为维也纳学派所取消。因为他认为,他的《新理学》中的形而上学与传统的形而上学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形而上学。这种不同表现在传统的形而上学是以“对于事实为积极的肯定”的综合命题为根据的,而他的形而上学是以“对于事实作形式的解释”的分析命题为根据的。维也纳学派能够取消传统的形而上学是因为这样的形而上学的命题是似是而非的命题,而他自己的命题则是空且灵的,所以是维也纳学派所不能推翻的。
然而洪谦并不这样认为。从冯友兰本人来看,维也纳学派所以推翻形而上学是因为传统形而上学的命题是对于经验事实作积极肯定的命题。但洪谦指出,从维也纳学派的哲学立场来看,问题就完全不一样了。他这样说道:“从维也纳学派立场而言,它的‘反形而上学’(Antimetaphysik)的主要点,并不是如冯友兰所言将形而上学从哲学上加以‘取消’,只想将形而上学在哲学中的活动范围加以指示,在哲学中的真正地位加以确定。换句话说,维也纳学派虽然否定形而上学之为一种关于实际的知识理论体系,但并不否认它在人生哲学方面的重要意义。所以某种形而上学之能被‘取消’或不能被‘取消’,与某种形而上学之以某种命题为根据,毫不相关。某个形而上学家视他的形而上学是否为一种关于实际的知识理体系,才是其唯一的标准了。”[2]这就是说,在洪谦看来,冯友兰对维也纳学派有关形而上学的理论是有误解的。第一,维也纳学派并没有拒斥或取消形而上学,只是划定了形而上学的活动的范围,把它从实际的知识体系领域中逐出,但是并没有彻底地取消形而上学在哲学中的地位和作用,也没有否认形而上学在人生哲学方面所能起的重要作用。第二,如果说维也纳学派取消形而上学的话,那么他们所运用的标准也并不如冯友兰所说的那样是以什么样的命题为根据,而是看形而上学是否是一种关于实际的知识理论体系。
我们已经知道维也纳学派是从知识理论的角度来评述形而上学的,认为形而上学不是一种关于实际的知识理论体系。洪谦实际也是从知识理论的角度来评论冯友兰的《新理学》的。他提出,冯友兰实质上确实是把形而上学视为一种关于实际的知识理论体系的。因为冯友兰本人这样说过,人类的知识可以分为四种:1.数学逻辑,2.形而上学,3.科学,4.历史。洪谦指出,冯友兰与传统的形而上学家不一样的地方在于,他没有强调在科学这样的关于实际的知识理论体系之外,还有所谓的超越实际的知识理论体系。但是他却认为,关于所谓实际的知识也可以分为两种,即“积极的实际知识”和“形式的实际知识”。他于是这样说道:“所谓实际的积极方面的知识,就是一些‘对于事实为积极的肯定’的综合知识。所谓实际的形式方面的知识,则是如冯先生所谓‘对于事实为形式的解释’的分析知识,就是冯先生所主张的形而上学知识了。”[2]洪谦认为,冯友兰关于知识的这两种分类是成问题的。
因为在维也纳学派看来,一个关于实际的命题在原则上必须对于事实有所叙述,有所传达。被叙述、被传达的事实对象就是这个命题有无意义的唯一根据。说一个命题是对事实有所叙述有所传达必须以这个命题有无证实方法为之标准。所谓的证实方法实质上是指,命题与其所反映的经验事实之间有无一一相应的关系。如果有这样的关系,那么这个命题就是真的,相应的它也就有了意义。否则,这个命题就是假的。当然维也纳学派所谓的证实方法并不是很严格的,所以它的证实方法有原则的和事实的两种。如果一个命题没有事实上证实的可能性,但是只要这个命题有原则上被证实的可能性,就可以说这个命题具有实际的意义。如果一个命题没有这样的原则上的可证实性,那么这样的命题就是在原则上无法加以肯定或否定的,所以也就没有实际的意义的了。洪谦指出,维也纳学派之所以能“取消”传统的形而上学,就是因为传统的形而上学的命题在原则上就没有可证实性,所以这些命题都是一种“似是而非的命题”了。
在洪谦看来,冯友兰的形而上学的命题也是没有实际意义的命题。但是与传统的形而上学的命题不一样,《新理学》中的命题的没有意义不是因为它们是“似是而非的命题”,而是因为它们是“重复叙述的命题”,所以这些命题才没有意义。“重复叙述的命题”所叙述所传达的对象,我们根本就无法从事实方面加以肯定或否定。同时它是否是真或假、是否有实际的意义,我们也无法从事实方面加以肯定或否定。可见,“冯先生的‘对于事实为形式的解释’的形而上学命题如‘山是山,水是水。山不是非山,水不是非水。山是山不是非山,必因有山之所以为山,水是水不是非水,必因有水之所以为水’,在原则上就是一些对于事实无所叙述无所传达的‘重复叙述的命题’,因为这样的命题对于事实所叙述所传达的对象,我们从事实方面亦不能有所肯定或否定,同时这样的命题亦不因其在事实方面不能有所肯定或否定而失去它的真性,而失去其原有的意义的。”[2]所谓“这样的命题不因其在事实方面不能有所肯定或否定而失去它的真性,而失去其原有的意义”是说,“重复叙述的命题”的真假并不决定于事实。洪谦接着指出,如果传统的形而上学命题是一些变相的“桌子是爱情”、“砚台是道德”之类的“似是而非的命题”的话,那么冯友兰的形而上学中的命题则是一些“今天是星期三就不是星期四”、“今天是晴天就不是雨天”一类的对于事实无所叙述无所传达的“重复叙述的命题”。洪谦把传统的形而上学的命题说成是没有根据的“胡说”,而冯友兰的形而上学的命题虽然没有“胡说”的成分,但是他的形而上学的命题对于事实也是没有叙述没有传达,所以这样的形而上学最终也不过是“一种‘空话’的理论系统了”。冯友兰把形而上学看作是他所理解的知识中的一种,但是经过洪谦这样的分析,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他的形而上学的命题也与传统的形而上学一样并不能构成关于实际的知识理论的系统。
冯友兰自认为,维也纳学派能够拒斥传统的形而上学,但是却不能推翻他的形而上学。因为他的形而上学是以维也纳学纳的经验主义为基础,而进一步超越了维也纳学派。但是洪谦却不这样看。他说,传统的形而上学,在维也纳学派看来,固然不能成为一种关于实际的知识理论体系,但是它们在人生哲学方面还是具有科学所不具有的深厚的意义和特殊的作用的,“我们从形而上学的体验中和形而上学的理想中确能得到内心中的满足和精神上的安慰,确能弥补生活上的空虚,扩张我们体验中的境界。”“我们从传统的形而上学命题如‘上帝存在’、‘灵魂不灭’、‘意志自由’中,可以得到在理想上的许多丰富的感觉,优美的境界,得到许多满足许多安慰。”[2]然而冯友兰的形而上学既不是关于实际的知识理论体系,同时它也不具有传统形而上学所具有的人生哲学方面所能发挥的作用,“两者俱无一厝”。所以他的结论是,如果维也纳学派真的要取消形而上学的话,“那么冯先生的形而上学之被‘取消’的可能性较之传统的形而上学为多”[2]。
我们可以相当清楚地看到,洪谦彻底地否定了冯友兰的形而上学思想体系。
现在的问题是,洪谦对冯友兰《新理学》的批判是否有道理。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如果站在维也纳学派哲学的立场上,那么毫无疑问,洪谦的这种批判是绝对正确的。因为事实上冯友兰的形而上学与传统的形而上学相比是大同小异,两者之间并没有实质上的区别。所以如果维也纳学派要取消形而上学的话,那么冯友兰的形而上学也难逃这样的厄运。这应该是显而易见的事实。因为冯友兰的形而上学同样不是对实际有所反映的知识理论体系,他的体系中的命题同样缺乏可证实性,不但事实上无证实性,就是在原则上也缺乏可证实性。冯友兰称自己的形而上学中的命题为“重复叙述的问题”,这样的命题也就是重言式命题。重言式命题的真假值显然不取决于其是否与外界的经验事实有一一相应的关系,所以这样的命题当然也就不可能对实际有所反映了。冯友兰的形而上学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他反复地宣称哲学始于分析经验事实,所谓分析经验事实就是对经验事实作形式的分析,而不是对之作积极的或有内容的分析。这样作的目的是要从特殊的经验事实过渡到一般性的东西。这当然是不可能的。而且命题分类理论本来是维也纳学派用来批判形而上学的,但是冯友兰却不加以改造就利用所谓的分析命题来构造自己的形而上学,这当然会带来种种困难。这个体系还有其它的一系列问题。总之,如果从哲学方法论的角度来看冯友兰的形而上学,那么我们不得不说他的这一哲学体系之中充满着很多的矛盾,难以成立。我们应该说洪谦对《新理学》方法论的批判是正确的。
冯友兰的《新理学》不是在一个严格的分析哲学的传统中形成的,而且他本人对于现代数理逻辑并没有作过深入的学习,更谈不上有什么研究了,所以在运用逻辑分析方法来建立自己的哲学体系之时难免会有不少错误。而洪谦在严格的分析哲学的传统中接受过专业的训练,并对现代科学有较深入的了解。在科学方法或逻辑分析方法方面,洪谦当然具有更厚实的知识基础和更全面的方法论的训练。
但是问题的另一方面却是,冯友兰和洪谦有着不同的哲学背景。洪谦可以说完全是在西洋哲学背景之下成长起来的哲学家,他的思维方式明显的是西方式的。而冯友兰则不同,他虽然也曾赴美国留学,也曾受过新实在论哲学思想和方法论的影响,但是他的哲学思想主要还是中国传统哲学的。中国传统的哲学思想虽然不重视逻辑的分析,但是却特别注重人生哲学中的人生境界理论。冯友兰完全继承了中国传统哲学的这一优良传统,他的哲学工作的路向就是要给传统哲学的人生境界奠定一个现代性的哲学理论或方法论的基础。在这样做的时候,他思考的重点毫无疑问的是传统的人生境界说,而从西方借鉴来的逻辑分析方法在他看来只不过是一种工具。可见,在他的哲学思想体系中,西方的逻辑分析方法是为中国传统的人生境界说服务的。
冯友兰从事于哲学研究的目的似乎并不纯粹是一种学术的事业,或者仅仅是为了求真。他在民族危机深重的年代创立自己的“新理学”哲学思想体系,目的是要“以志艰危,且鸣盛世”,他是要以自己的哲学思想体系为中华民族确立哲学思想的基础。可见,他是有着民族文化的担当。因此他同时在追求着真和善,或者说在真和善这两者之间,他更注重的是善,所以他认为,形而上学虽然不能增加人们实际的知识,但是它确可以提高人们的境界,他的《新理学》就是要帮助人们进入天地境界,成为圣人。显而易见,冯友兰的哲学思想研究并不仅仅是一种学术事业,而且也是一种民族文化的担当。我们这样说并不是说洪谦不关心国家的安危,而是说他是把哲学研究看作是一种纯学术的事业。而且我们也能很清楚地看到,洪谦的分析哲学指向的是真,真是最高的,是唯一的。他完全赞同维也纳学派的哲学的任务就是要说明科学命题的意义就是一个明证。
洪谦对冯友兰的批判固然是一个逻辑实在论者对一个新实在论者的批判,而更为根本的是,这一批判也是一个完全站在西方哲学立场的哲学家对一个中国哲学家的批判。这就涉及到维也纳学派与中国哲学对待形而上学的根本态度问题了。可以说,在这个很重要的哲学问题上,他们之间有着很大的分歧。在西方哲学史上早就有一个取消形而上学的传统,维也纳学派只不过将其推向极端而已。但是在中国哲学中确从来就没有这样的排除形而上学的传统,不但没有,而且还积极地维护形而上学。这是因为按照中国哲学家的看法,哲学从本质上说就是形而上学。应该说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有着某种共性,但不能否认它们之间还是有着很大区别的。西方文化的核心是宗教而不是哲学。与此不同,中国文化的核心却是哲学。西方人的终极关怀和终极托付是宗教,而中国人的安心立命之所却是哲学。准此,我们可以说,西方人具有宗教的本质,而中国人就其本质说是哲学的。把哲学看作是概念游戏是典型的西方人的说法,因此对于他们来说,哲学并不是绝对必须的,相反,对于中国人来说,特别是对于中国的知识分子来说,宗教倒并不是必须的,但哲学却是不可一日或缺的。这倒是应了黑格尔老人的一句名言,一个国家没有哲学,就像一座雄伟壮观的庙中没有神像一样,空空荡荡,徒有其表,因为它没有可信仰的东西、可尊敬的东西。哲学或形而上学就是中国人可信仰的东西,可尊敬的东西。对于形而上学的执着追求源于中国人的本性。冯友兰就是这样看的,他认为,人没有必要一定要具有宗教的性质,但每一个人却必须学习哲学,具有哲学的修养,他才有可能成为真正的人。因此哲学才是人的本质。而且他还进一步指出,在不远的将来,哲学一定会代替宗教。显然,这就是典型的中国哲学家的看法。其实有这样看法的不仅仅是冯友兰,熊十力也有同样的看法。
与他们不同,熊十力基本上是一个传统的中国哲学家。他维护形而上学或本体论的立场则更为积极。他的哲学思想体系就是本体论或形而上学。他说:“学问当分二途:曰科学,曰哲学。科学,根本是从实用出发,易言之,即从日常生活的经验里出发。……哲学自从科学发展以后,他底范围日益缩小。究极言之,只有本体论是哲学的范围,除此之外,几乎皆是科学的领域。……哲学思想本不可以有限界言,然而本体论究是阐明万化根源,是一切智智,与科学但为各部门的重视者不可同日而语。则谓哲学建本立极,只是本体论,要不为过。夫哲学所穷究的,即是本体。”[3]洪谦或维也纳学派的哲学家们认为,哲学不是一种知识体系或科学,而是一种活动,它的任务就是要说明或明确科学命题的意义。总之,哲学没有自己的独立性,没有自己独立的领地,而只不过是科学的附庸,只不过是科学范围之内的一种活动。而熊十力却不这么看,他指出人的智有性智和量智的区别。“性智者,即是真的自己底觉悟。”“量智是思量和推度,或明辩事物之理则,及于所行所历,简择得失等等作用故,故说明量智,亦名理智。此智,元是性智的发用,而卒别于性智,因为性智作用,依官能而发现,即官能假之以自用。”[3]他认为,性智是一切智中最上的智,它要高于量智。本体需要性智才得体认,而量智的运用形成的是知识。他于是这样说道:“哲学所以站得住者,只以本体论是科学所夺不去的。我们正以未得证体,才研究知识论。今乃立意不承有本体,而只在知识论上钻来钻去,终无结果,如何不是脱离哲学的立场?凡此种种妄见,如前哲所谓‘道在迩而求诸远,事在易而求诸难’。此其谬误,实由不务反识本心。易言之,即不了万物本源,与吾人真性,本非有二。遂至妄臆宇宙本体为离自心而外在,故乃凭量智以向外求索,及其求索不可得,犹复不已于求索,则且以意想而有所安立。学者各凭意想,聚讼不休,则又相戒勿谈本体,于是盘旋知识窠臼,而正智之途塞,人顾自迷其所以生之理。”[3]由于人们认识不到本体,所以才凭借量智向外逐物,在知识论上纠缠不休,所以才认识不清哲学的真正目的在于认识本体。
根据熊十力的这种看法,知识论的研究不是哲学内容,更不是哲学追求的目标。很显然,这样的看法与西方近代以来的哲学思潮是背道而驰的。从笛卡尔、洛克以后的西方哲学史的重点似乎一直是在知识论方面的研究,这就是所谓的“认识论的转向”。所以在西方哲学中,一个真正的哲学家如果不去研究知识论,不建立自己的知识理论的体系,就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可见,在西方哲学中,知识理论恰恰是哲学的中心内容。而形而上学在近代以来的历史中却逐渐地失去了原有的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在历史中渐渐地隐去。熊十力不可能不知道西方哲学的发展史,他的上述思想似乎就是批评西方哲学的这种发展趋势的。冯友兰和金岳霖都在西方学习哲学多年,对于西方哲学的发展更是了如指掌,但是他们似乎也没有为这种哲学发展的趋势所动,而仍然执着地坚持着形而上学的立场,花了极大的精力来创建自己的形而上学哲学体系。冯友兰认为,形而上学是“最哲学底哲学”。金岳霖也明确地指出“玄学是统摄全部哲学的”。他虽然在知识理论的研究方面花了极大的工夫和时间,但他对知识理论的看法却是,知识理论应该是以形而上学或本体论为基础的。
总之,上述的哲学家们都毫不犹豫地坚持形而上学才是哲学的核心内容的哲学立场。我们由此可以看到,中国现代哲学虽然受到西方哲学的很大的影响,但是中国现代哲学还是在走着自己的发展道路。我们上面所作比较的意图就是要显示中西哲学之间的区别。
[收稿日期]2001-10-18
标签:冯友兰论文; 形而上学论文; 哲学论文; 哲学研究论文; 命题的否定论文; 洪谦论文; 西方哲学家论文; 命题逻辑论文; 中国哲学史论文; 哲学史论文; 金岳霖论文; 维也纳论文; 理学论文; 新理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