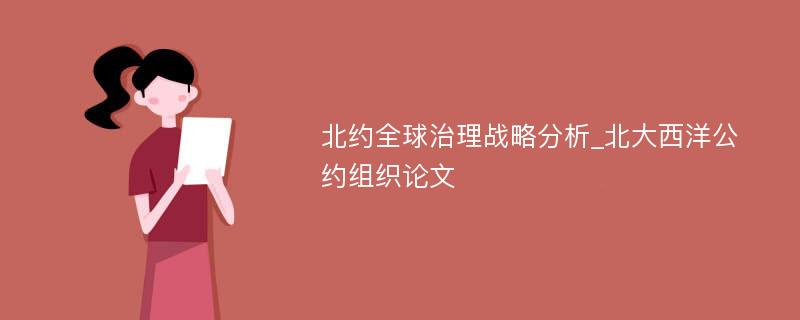
北约的全球治理战略论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北约论文,战略论文,全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北约既是当今世界的超级军事集团,也是唯一具有全球军事行动能力的军事组织,还是能通过扮演诸如“国际安全援助部队”等角色有效参与全球安全治理的联盟实体。冷战结束以来,北约开始从传统安全事务稳步向非传统安全事务拓展,在危机管理、冲突治理和安全重建等诸多安全治理问题上的表现尤为显著,从而在全球治理领域不断发挥重要作用。不过,北约全球治理战略总体上尚不够清晰,还需进一步调整和完善,才能在全球治理领域有更大的作为。 一、北约战略构想中的全球治理战略因素 受传统观点的影响,学界更多地关注北约在传统安全领域的表现,较少关注它在全球治理领域的作为。究其原因,一是把北约视为纯粹的传统安全联盟,因而与全球治理无涉;二是对是否存在所谓的“北约的全球治理战略”存在分歧;三是北约自身尚未明确制定和公布全球治理战略。不过,北约并非没有自己的全球治理战略,而是内嵌于各种联盟战略中。实际上,北约的全球治理战略散见在各政策文件——特别是联盟战略文件、秘书长和北约最高司令等重要政策讲话和声明中,显得零散而不系统。冷战结束至今,北约联盟战略几经调整,核心目标却始终不变——通过战略转型与全球拓展,巩固和改善美国与欧洲伙伴的联盟合作关系,维持并促进以美国和西欧国家为代表的冷战“胜利果实”,巩固并促进北约在欧洲乃至国际安全体系的主导地位①。为此,通过梳理冷战结束后北约数次调整的联盟战略,我们可勾勒出一个北约全球治理战略的基本轮廓。 1967年北约发布的《哈梅尔报告》强调“威慑”与“缓和”并重,使北约战略从大规模报复战略转向灵活反应战略,以期在冲突水平之间建立分界线,防止战略核杀戮的发生。1991年罗马峰会批准的新联盟战略保持了《哈梅尔报告》的前述要义②。为应对冷战结束初期的战略环境,该联盟战略还确定了北约的四项基本任务:(1)保持足够的军事实力以防止战争并进行有效防务;(2)提升处理影响成员国安全的各种危机的总体能力;(3)通过各种政治努力实现北约与其他国家的对话;(4)为欧洲安全积极探求各种合作方式。为确保这些任务的实现,新联盟战略把“集体防御”、“危机管理与预防冲突”、“对话与合作”确定为联盟在新时期的主要使命。其中,“对话”主要面向苏联与中东欧国家,旨在增强苏东国家安全事务的透明性和预测性,维护地区稳定;“合作”主要面向整个欧洲国家,旨在促进欧洲安全领域的各种双边和多边合作,防止危机发生或确保危机的有效处理。该联盟战略承认,北约通过政治渠道解决安全问题比以往变得更重要。不过,它仍有很强的冷战色彩,强调军事手段的重要性,认为保持适当的军事实力是维护联盟目标的核心。只有这样,北约推动的各项对话与合作才能有效发展并取得预期效果。 为更好地适应21世纪新的安全环境,北约在1999年华盛顿峰会上通过了新的联盟战略③。该战略再次确认了集体防务与跨大西洋联系的承诺,并首次提出要在北约框架下建设“欧洲安全与防务特性”(ESDI),以增强伙伴关系与美欧对话。它继承了1991年联盟战略关于北约基本安全任务的规定,并把它们概括为安全、协商、威慑与防务。此外,为进一步增强欧洲—大西洋地区的安全与稳定,该联盟战略还对“危机管理”和“伙伴关系”做了特别规定。在危机管理方面,北约根据《北大西洋条约》第7条的规定,可视具体情况并经协商一致的原则和程序,为有效预防冲突和积极参与危机管理——包括危机反应行动——做出贡献;在伙伴关系方面,北约着力推动欧洲—大西洋地区广泛的伙伴关系,促进合作与对话,以增强该地区的透明度、互信度,并提高联盟的联合行动能力。为积极有效地促进地区安全与地区合作,北约还决定把“欧洲大西洋伙伴关系委员会”与“和平伙伴关系”确定为主要的协作机制,以应对各种危机并建立良好的伙伴关系。这样,核生化武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恐怖主义、地区危机冲突等被确定为严重威胁欧洲和大西洋地区和平、安全与稳定的因素,成为北约在新时期重点防范和整治的对象。 “9·11”事件后,恐怖主义在美国和北约的安全关切权重骤升。小布什政府选择了以单边主义和军事力量作为主要的反恐战略手段。对此,北约总体也积极地支持并参与美国为首的联合反恐行动。不过,北约成员国在具体参与打击恐怖主义、军控与防扩散、消除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等安全治理领域存在分歧。美国保守主义者所渲染的“老欧洲”和“新欧洲”一事就是最显著的表现。 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世界变得更不稳定、更不可预测,北约也面临诸多新的风险。在2010年举行的里斯本峰会上,北约理事会批准了新的联盟战略——《积极参与和现代防务》④。里斯本联盟战略把“集体防务”、“危机管理”与“合作安全”作为联盟的三项核心任务,并强调要促进联盟进行改革,使之实现现代化转型。同时,该联盟战略还再度确认了集体防务的首要地位,并要求北约明确预防危机、冲突管理和冲突后稳定化的角色,对危机实施全方位管理。在构建国际伙伴关系方面,北约尤为重视与联合国、欧盟之间的合作关系,以共同应对弹道导弹扩散、核武器扩散、恐怖主义、网络安全、通信与交通线安全等各种安全治理问题。为此,新联盟战略要求联盟要在全球范围有更多的参与,在塑造北约领导的行动中扮演实质性角色。此外,该联盟战略还把某些重要的环境与资源问题纳入合作安全的范畴。比如,它把全球性人口变化与环境恶化等问题视为不稳定性因素,强调联盟要给予更多的重视⑤。 在此次峰会上,北约各国领导人对采取新的联盟战略和一系列使北约适应21世纪安全环境的政策充满信心。但是,关于北约在21世纪安全环境中的角色问题,各成员国却没有达成共识。这成为北约各国领导人在2012年5月芝加哥峰会上讨论的焦点。此外,北约各国领导人始终对集体防御与北约参与危机管理之间的平衡问题,以及北约应该准备做出反应的危机类型存在争论。尽管如此,各国仍开始认真考虑采取一系列措施使联盟更好地适应新的全球安全环境,更快地实现转型。因此,北约决定承担新的任务,以应对新兴安全挑战,其中包括网络威胁。北约也致力于精简联盟的官僚机构并简化和优化它的伙伴体系。所有这些措施,都旨在使北约有效应对超越经济挑战之外的各种安全挑战⑥。 通过考察1991年以来北约历次联盟战略的演变可以发现,北约在坚持“集体防务”这一传统安全首要使命的同时,逐步积极地拓展自身对非传统安全的防范与治理,并不断丰富非常规威胁的内涵,使之涵盖了从军控和防扩散,到危机管理、国际恐怖主义、网络攻击、环境恶化、能源交通线等全球治理的各个方面,“北约全球化”的态势日趋明显⑦。在安全治理领域,北约的治理区域也从欧洲—大西洋地区,向北约边界之外拓展。特别是,在危机与冲突管理方面,北约也完成了向全方位管理的转变,强调综合的方式、合作安全的模式。 历史地看,不同于冷战时期强调联盟的“防御性质”并严守战略构想信息,北约在冷战结束后积极地推向东扩并高调宣传战略构想,为自身的合法性与正当性正名。2010年里斯本峰会通过的联盟战略的蓝本——《2020年的北约:确保安全与动态参与》报告指出:“联盟要使北约国家的民众知道,他们的利益受到联盟提供的安全的保护;要使北约之外的国家的民众知道,北约国家及其伙伴每天都在为构建一个更加安全的世界而努力。”⑧不难看出,这些冠冕堂皇的词句背后,显现了北约领导人在新世纪全球安全事务突进的战略姿态。 二、北约全球治理战略的主要内容 通过不断地更新联盟战略并向全球化转型,积极发展各种伙伴关系融入地区与全球事务,最大限度地维护欧洲—大西洋地区乃至全球范围的安全秩序,以军事转型为契机推进以安全事务为核心的全球治理体系发展,构成了北约全球治理战略的核心内容。具体来说,就是以在一个更加不稳定、不可预测的世界中保持快速做出有效反应的能力,维护联盟及其成员的安全和重大利益为目标,确保联盟的团结、安全与稳定;利用冷战结束后缔造的各种伙伴关系与合作安全的成功经验,逐步拓展联盟的国际事务参与度,并以超强的军事实力在国际安全机制中谋求安全治理的领导权;以应对各种非常规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因素为契机,改革并优化联盟的军事能力结构,为国际社会提供紧缺而可靠的、全方位的危机与冲突管理服务,逐步提升北约的国际政治影响力⑨。 (一)以危机管理谋求全球安全治理领导权 战后欧洲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在很大程度上是美苏战略均势的结果,体现了欧洲力量平衡的重要性。冷战结束后,凭借政治团结、相互防务的承诺及强大的军事能力,北约成为欧洲—大西洋地区安全与稳定的重要基石。北约领导人认为,尽管针对北约成员国的直接军事侵略的风险有实质性下降,但在全球化背景下,不仅欧洲边缘地区的各种不稳定事件会影响北约地区的安全与稳定,而且发生在相对远离欧洲地区的各种危机和冲突事件,同样会波及北约的安全与稳定。为此,北约不能对边缘地区及边界外的不稳定事件无动于衷,需要对全球范围的危机与冲突进行有效管理。 这样,在必要的情况下,北约将实施防止危机、管理危机、稳定冲突后形势并支持重建的全方位危机管理。北约的危机管理理念强调:(1)冲突管理的最佳方式是在一开始就防止它们发生。为此,北约要持续地监督和分析国际环境,以预测危机的发生,并采取适当的积极措施以防它们演变成更大的冲突。(2)当预防冲突被证明不成功时,北约要准备并能随时处理发展中的敌对事态。对此,北约要快速运用并维持强大的军事打击力量。(3)即使在冲突结束之后,国际社会也需经常地提供持续性支持,为冲突后地区的持续稳定缔造条件。这种危机与冲突管理涵盖了预防冲突、冲突解决与稳定化三个维度,构成一个相对全面的危机管理体系。基于阿富汗问题与巴尔干危机的经验教训,北约将综合运用政治、军事和民事的方法和手段,使全方位危机管理体系更为有效。 (二)以非常规威胁谋求边界外安全与稳定 在可预见的未来,鉴于敌人跨越北约边界发动直接军事攻击的可能性较低,北约将主要应对各种非常规的安全威胁。2010年的联盟战略强调,未来十年北约国家最有可能面临非常规威胁,其中:弹道导弹攻击(不管有无核装置)、国际恐怖主义集团发动的打击、严重程度不一的网络攻击、对能源和海上供应线的破坏、全球气候变化的有害影响以及金融危机,都属于此类潜在的非常规威胁。该战略构想确信,全球化时代世界某一地区发生的事件对全世界的影响,已超出了过去时代的想象。一些在北约边缘或遥远地区引起的非常规威胁,都将影响北约本土的安全与稳定。因此,北约须调整专守领土的传统防务方式,对安全概念做新的界定,以新的安全治理模式应对边界外的各种非传统安全威胁⑩,同时增强在边界外实施军事行动和其他任务取得胜利的能力。 实际上,自建立以来北约所有的联盟战略都强调,联盟必须能够威慑并防御针对成员国的任何侵略威胁。2010年的联盟战略强调,北约要扩展条约第5条关于集体防务的规定,对那些在欧洲—大西洋地区内外发生的各种危险和威胁做出反应。其中,防区外的威胁和网络攻击尤为值得关切。这份联盟战略指出,即便是一个房主都对他或她邻居的安全存有利益,因此北约“自然地”也有理由关切它所在地区边缘的稳定情况。在保护维持“民主社会”的全球生命航线以及维护超出边界的地区安全与稳定方面,北约都有自己的利益所在。 虽然网络安全还只是一种早期发展,但其仍受到北约国家前所未有的重视(11)。由于包括北约国家在内的世界各国对网络信息体系有严重的依赖,这种依赖覆盖了从政治、军事、经济、生活等各个方面,而这一信息体系又有潜在的脆弱性。因此,北约强调各成员必须加快采取措施,以应对网络攻击的危险,保护联盟的通信和指挥体系,帮助盟国提高防止网络攻击并从攻击中恢复过来的能力,发展各种网络防务能力,并进行有效的侦测和可靠威慑。不同于北约面临的其他非常规威胁,由于占据明显的技术优势,因此北约自身在严重依赖网络技术的同时,为确保这种前瞻性安全,还将主动塑造北约占优的网络空间形势,从而把握网络安全的战略主动权(12)。 (三)以合作伙伴关系发展联盟的多边角色 北约领导人意识到,北约在21世纪将不可能单独行动。《2020年的北约:确保安全与动态参与》承认,北约是一个地区性而非全球性组织,受权力和资源的限制,因此“不指望”执行其他组织和国家能够成功处理的任务。相反,北约在日常国际事务中主要围绕各种伙伴关系展开。为此,北约必须厘清并深化与关键伙伴之间的关系,并在适当的地区建立新的伙伴关系。 为增强伙伴关系,北约准备与全球范围的任何国家或组织开展政治对话并进行切实合作,为“和平的国际关系”努力;在共同关心的全球问题上,它将向任何伙伴国敞开协商的大门;在有关北约领导的国际事务的战略和决定上,北约也将使参与行动的伙伴通过实质性的角色做出贡献;进一步发展既有的伙伴关系,并维护它们的特性。其中,北约尤为重视它与联合国、欧盟、俄罗斯之间的伙伴关系,强调欧洲大西洋伙伴关系委员会、和平伙伴关系在促进整个欧洲自由与和平的作用,深化并落实“地中海对话”和“伊斯坦布尔合作倡议”。 北约领导人认为,北约与联合国之间合作伙伴关系将继续对全球安全事务做出重大贡献。因此,北约将深化与联合国的对话和合作,切实履行2008年签署的《联合国—北约宣言》。而一个积极有效的欧盟,有助于整个欧洲—大西洋地区的安全,从而是北约独一无二且至关重要的伙伴。在促进国际和平与安全方面,北约与欧盟能够且应该互相补充和相互增强,双方将在互相公开、透明、补充和尊重独立性和组织完整的基础上,全面加强战略伙伴关系。为创建一个共同和平、稳定与安全的地区,北约与俄罗斯之间是具有战略意义的合作伙伴关系。由于确信北约与俄罗斯的安全相互交错,北约将致力于构建一个有建设性的伙伴关系,积极利用北约—俄罗斯理事会就共同关心的重大问题展开或保持对话,并争取一致行动。此外,北约的全球治理战略也对中东、亚太、南美洲、非洲等地区潜在合作伙伴进行了考虑,逐一分析上述地区的主要不稳定因素,以及北约能够介入其中的可能性与潜在合作伙伴。 (四)以综合合作安全提高北约的领导力 2010年的联盟战略确信,未来十年北约将受到新凸显的危险、复杂行动的多方面需求的挑战。全球政治环境不断增长的复杂性,将会导致一系列复杂的问题。为此,北约需要采取综合的方式应对这些新的复杂问题。其中,良好的伙伴关系能为北约创造解决影响自身安全的复杂问题的机会。在大多数情况下,北约领导人认为,他们应该首选一种综合军事和民事因素的解决办法。该联盟战略承认,北约虽然强大且活跃,但它并不必然地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其他的国际组织、政府和非政府实体在不同的领域也能大有作为,比如经济重建、政治调解、改善治理和加强公民社会。因此,北约将依据特定情况的实际需要展开国际协调,或实施特定的援助,或某些补充性角色方面扮演主要的组织者。 在导弹防御、军控和裁军、防扩散、反恐乃至反麻醉毒品、反盗版等领域,北约可与联合国、欧盟、俄罗斯、中国等国际组织或大国展开合作,以实现合作性安全。经联合国授权的、北约领导的国际安全援助部队,就齐集了医疗、卫生、工程、通信、教育等方面的国际合作。进一步地,通过向符合北约标准的所有欧洲国家敞开联盟的大门,或者帮助那些希望加入其中的国家符合北约标准,北约可以将那些不稳定因素实现“稳定化”。为此,北约专门成立了一个大约由170位民事专家组成的“综合方式援助团”(13),涵盖了从安全治理到经济发展、媒体、农业到环境等多个议题。这些举措的目的,在于使北约更好地把军事成功转化为长期的政治稳定,使北约更好地应对未来各种复杂的全球问题。 应当承认,北约的安全影响力依旧超群,是当前全球安全秩序不可忽视的一支力量。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北约在巩固传统安全领域治理的突出地位的同时,也开始积极地谋求全球非传统安全领域治理的发言权和代表权。 三、北约全球治理战略的基本特点 (一)以安全治理为核心 北约的全球治理战略受联盟的军事特性影响,具有强烈的安全治理色彩,并以此为核心形成了富有特色的安全治理理念与实践。一方面,北约现有的决策机制和行动能力主要以军事打击和制止冲突见长,旨在优先确保北约本土的安全与稳定;另一方面,北约又意识到自身资源和权力的限制,因而希望与其他国际组织、非军事组织和机构展开合作,共同面对各种非常规威胁,有效地实施全方位危机管理,采取政治、军事等综合手段对有可能影响北约安全与稳定的各种危机和冲突——不管是发生在北约边缘地区,还是发生在相对遥远的中东、中亚地区——进行有效的治理。 但是,北约在应对这些非常规威胁方面并非没有分歧。以能源安全为例,虽然北约内部高度关注能源问题与全球能源市场发生根本性转变有关,但由于政治考虑与实际操作,要界定北约在能源安全领域的角色较为困难。不少北约国家认为,使一个重要的经济问题“军事化”将会对能源市场产生扭曲影响,并违背北约关于降低政治和安全风险的角色定位。当然,放任不管显然更不明智。因此,北约必须认真考虑如何才能对牵涉许多政治与安全影响的经济问题的解决做出贡献。在2006年的里加峰会上,美国参议员理查德·鲁格提出了“威慑”角色。杰米·谢伊则提出了更为具体的三项建议。不过,这些建议仍充满浓厚的展现军事肌肉的气味(14)。 (二)超越联盟边界谋求利益 历史地看,北约有在域外冲突中进行联盟内合作的传统。朝鲜战争和第二次印度支那战争,就见证了北约内部的这种合作。这种合作不仅包括直接的军事参与,也包括有关的政治支持、物质支持和部署援助。北约在联盟防区外进行军事干预的举动,实际上突破了其“集体防御联盟”的定位(15)。为此,最新的联盟战略为北约积极在联盟边界之外做出有效反应做了明确规定。 虽然《北大西洋条约》第6条把联盟防区的边界界定为,终止于任何成员国的司法管辖权的岛屿,到北回归线范围内。并且,出于资源考虑(主要是军事援助计划基金的充足问题),以及美国不情愿支持欧洲殖民体系,因而北约对防区进行了严格的限制。但是,《条约》第4条又暗示,北约可在“任何成员领土完整、政治独立或安全受到威胁时”进行协商和采取可能的协调行动。这就意味着,“联盟成员可以干预其他成员的全球事务,或者使盟国参与缔约国的域外问题”。虽然威胁环境的变化消除了北约的主要敌人,但这不意味着联盟没有需要抵御的威胁。北约最强大的角色仍是发挥集体防御作用,为成员提供物理性安全。不过,在新时期的安全防御问题上,它面临着防御什么安全威胁这一核心问题。最新的联盟战略要求联盟把目光投向防区外的全球问题或者紧急事态。因此,北约把发生在盟约之外的军事威胁来源也考虑在内,包括中程弹道导弹威胁,以及反西方民族主义问题。在2012年的芝加哥峰会上,北约各国领导人对此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负责应对“新兴安全挑战事务”的北约副助理秘书长杰米·谢伊则把它归结为对“巧防御的巧计划和巧思考”,认为此举有助于北约为超出预期的世界做好准备。 (三)合作性安全与防范性合作并存 不过,受实际能力与资源的限制,北约在许多全球性问题上都无法单独行动。北约如果单干,它将只能解决其中的一部分问题。面对其他的问题,如果要使之得到解决,北约将只能跟其他组织进行合作(16)。为此,北约推行合作性安全的主要目的,在于依靠其他国际组织、国家和非军事机构的资源和力量,以最小的成本换取最大的收益。但是,它并不甘心扮演这样一种角色:一个协调政策者;特定援助提供者;或某些补充性活动的组织者。相反,北约更乐于牵头某些行动,而不是由别的国际组织或国家领导。因此,按照北约领导人的理解,所谓的“合作性安全”就是北约领导下的安全合作。进一步地,北约并不完全信任联盟之外的合作伙伴。在《2020年的北约:确保安全与动态参与》报告中,俄罗斯就被北约界定为一个被争取实质性合作的对象,同时由于难以预测俄罗斯对北约的未来政策,因此还要防止俄罗斯对它采取更具敌对性的政策。 此外,北约也曾考虑在平等、互信和互利原则的基础上,与非洲联盟、美洲国家组织、海湾合作委员会、上海合作组织和集体安全条约组织,以及中国、印度等国家建立更为正式的合作,把它们纳入北约全球治理战略的合作伙伴序列。但是,2010年发布的最终战略构想却把这些国际组织和国家排除在“伙伴关系”的范畴之外。可见,不仅北约所宣称的合作性安全有特定的内涵,而且这种合作还有特定的选择性。它既体现了北约对安全秩序主导权的维护与渴望,也反映了北约对其他国际行为体的信任限度乃至怀疑。总之,北约通过合作性安全寻求联盟外的国家和国际组织的帮助,需保持在一定的限度范围内,使之服务于北约威慑战略的可靠性及联盟转型的目标。 (四)推进联盟的全球化转型 一方面,北约自称属于地区性而非全球性组织,自知自身资源和力量有限,不指望单独承担其他国际组织和国家能够胜任的国际事务,而是寻求在其中扮演协调者、组织者与援助者的角色;另一方面,北约又力求对全球范围兴起的各种非常规威胁做出快速而有效的反应,要求对传统的领土安全概念做出新的规定,主动承担对全球和平与法治的承诺。联盟的多边角色转型趋向逐渐明朗。其中,欧盟是北约最信赖的合作伙伴。北约领导人认为,欧盟具备危机管理和其他事务方面提供关键民事服务的能力,还共享大部分联盟伙伴,可以且应该进行有效的整合。不过,欧盟在这方面的历史表现并不令人满意。正如奥尔布赖特所言,美国对待北约,“可能的话,就采取多边行动;必要的话,就采取单边行动”。在她看来,“美国是一个不可取代的国家,比其他国家看得更远。”相反,欧洲对北约则强调“欧洲世界大同主义”,力图扩大欧盟的影响力,不甘愿完全受美国领导的北约体系的束缚(17)。为克服相互间的分歧,继2010年里斯本峰会再次确认“欧洲安全与防务特性”之后,2012年芝加哥峰会又进一步提出了“巧防务倡议”,其目的在于通过增强北约的欧洲维度强化跨大西洋纽带,弥合美国与欧洲盟国之间的分歧,最大限度地调动欧洲盟国的积极性,使北约的全球行动能力得到有效保证。 四、北约全球治理战略的多重困境 综上可以看出,北约力图把自身的军事优势转向有利于西方国家的长期政治稳定,拓展自身在全球事务中的影响力。这种全球治理战略以鲜明的安全治理为核心,力求通过北约主导的伙伴关系与合作安全,构筑维护北约国家利益的全球安全秩序。然而,北约的全球治理实践并非总那么成功。在一定程度上,正是由于北约的介入与主导,许多全球问题被不恰当地军事化和政治化,从而使问题的解决变得复杂。实际上,北约的全球治理战略面临着许多制约和挑战。 (一)财政困境 经济问题的困扰会分散人们对安全需求的关注。自联盟成立以来,防务开支分担一直是北约成员争论不休的议题。虽然通过各种伙伴计划,北约从非成员国那里获得了大约40个国家的参与,北约领导的部队有近10%来自这些国家,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北约国家的防务开支压力,但北约大部分成员国都面临大幅度的预算限制,财政紧缩的压力迫使有关北约未来角色和使命的战略辩论,也仅能停留在辩论层面。特别是,美国依旧承担着联盟大部分的防务开支。依据重返亚太的“再平衡战略”,美国开始从欧洲撤离数千人的部队,以增强它在亚洲的安全角色。但许多欧洲成员国也在减少自身的防务开支,以应对经济危机。欧洲盟国面临着更大的防务压力。依据国际战略研究所的报告,2011年亚洲防务开支(包括澳大利亚)首次超过了欧洲防务开支。可以预见,依据北约国家的国内政治体系,成员国国内政治优先将会毫无疑问地超越联盟层面的需求,这将对北约的军事作为和政治行动构成结构性障碍。北约的全球治理战略将因此陷入内部供应不足的困境,更遑论向国际社会持续有效地提供安全治理等全球公共产品。 (二)意愿困境 北约已从成立之初的12国,扩大为28国。联盟的扩大虽带来了可观的潜在实力,但联盟的决策能力与决策效率、意愿的共识性却没能相应的深化。相反,在一定程度上,联盟的扩大增加了成员国在重大事务上达成一致的难度。因此,对北约的决策和指挥结构进行变革成为了历次峰会的重点议题。显然,意愿的不足除了受成员国国内经济财政问题的严重影响,还与联盟主导国美国的政治意愿密切相关。应该注意,作为安全治理的重要假设之一,不断变化但结构性中立的“意愿联盟”似乎正在取代稳定且敌对的传统联盟(18)。在新兴的全球安全治理模式中,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主要国家,都更愿意通过灵活的意愿联盟解决全球安全问题(19)。意愿联盟既能使政策变得灵活,还往往使防务开支变得经济。更重要的是,意愿联盟并非新的均势模式。它们只是对地区性或全球性安全治理做出的反应,会依据不同的议题和领域而变化。“9·11”事件之后,美国就曾多次绕开北约,组建美国主导的意愿联盟展开行动。可以认为,这种嵌入合作性安全的意愿联盟,在一定程度上对北约传统的常规联盟构成了潜在的挑战(20)。 (三)策略困境 财政的限制与意愿的不足,还潜藏着北约的欧洲支柱与北美支柱之间的策略分歧。北约作为一个多边主义组织,长期以来主要由美国单边主导。以法国和德国为代表的欧洲主要盟国,则对多边主义情有独钟(21)。几乎所有的西欧盟国,都希望发挥一定程度的欧洲特性。因此,要使欧洲成员国投入更多的防务开支和政治意愿,在全球治理问题上与美国在北约框架下展开合作,美国就不能不正视欧洲盟国的战略需求和策略需要。相应地,如果欧洲盟国想让美国倾向于多边主义,并促使华盛顿更加关注欧洲伙伴的意见,那么它们选择加入美国可能参与的多边论坛或协商机制,就比较符合自己的利益,它们也可借此获得更多的讨价权力(22)。 实际上,美欧关系会由于一些分歧而导致极大的危机(23)。严重的时候,这些分歧将会导致北约无法有效地参与全球治理。那样,北约的角色就会有被边缘化之虞。这种结果自然是美国及其欧洲盟国都不愿见的。实际上,欧洲国家在安全和防务问题上取得完全独立并不现实,成本过于高昂与欧洲决策精英们的主观愿望,无疑是两大显著因素。欧洲盟国可在某些问题上凭借有限的实力单独行动,对北约进行补充而非与美国分庭抗礼。这正是“欧洲安全与防务特性”的本意。只是,欧洲的安全特性到底特别在哪里?它的基本角色在北约框架下能够有多大的作为?它的最终目的是谋求欧洲的完全独立,还是始终服从北约体系?这些问题需要美国及其欧洲盟国进行认真的回答。这些问题的悬而未决,将深刻制约北约参与全球治理的效度。 (四)法理困境 实际上,冷战结束后北约历次发起和参与的国际事务,既饱受合法性困扰,也难以打造一个更加和平稳定的局面。如果说北约作为一个集体防御组织,依据《联合国宪章》关于单独或集体自卫权利的规定,可对北约防区的成员国实施正当的集体自卫权,那么,在北约把目光投向联盟边界之外,不断介入域外危机和冲突事件的情况下,它的法理就没有前者那么自然与正当(24)。在为北约干预域外的危机和冲突管理寻找法理依据时,北约领导人特别是欧洲盟国领导人更多地坚持联合国授权。实际上,冷战结束后联合国的权限已扩展到由冲突引起的治理领域,不过,这种扩展已引发国际社会关于“后冲突”治理及合法性的争论。有论者指出,《联合国宪章》本身对联合国的授权是有限的,联合国使用武力的合法性也是有限的。因此,联合国维护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必要性不能以牺牲成员国主权为代价(25)。 这样,在治理危机与合法性危机相互渗透的情况下,国际社会各种政府组织乃至草根组织,都试图通过弥补现有国际组织的不足,发出自己的声音(26)。北约则以其超强的军事实力和政治集合力,在安全治理领域“拔得头筹”。北约整体坚持,欧洲—大西洋地区的安全有赖于北约成员领土之外的安全,防区外的危机管理行动要在联合国授权下进行,北约在危机地区的重建过程中要超越纯粹的军事举措,在“后冲突”环境下实现更广泛的再稳定化和秩序重建(27)。不过,它难以通过指责联合国在国际冲突治理上的不力,而使自身获得合法的自我授权。特别是,既然连联合国本身都不能牺牲成员国的主权,那么北约作为地区性组织,自然也不能正当地侵犯别国的主权——哪怕有联合国授权做支撑。要使自身的治理实践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信服,北约除需调整自身如何恰当展露军事肌肉之外,还要在法理上切实地下一番功夫。然而,对长期恪守法理并纠缠规则而行事的北约国家特别是欧洲盟国来说,此举并非易事。 五、结语 诚然,北约并不像联合国、欧盟或其他全球治理主体那样,直到目前尚未制定出清晰的全球治理战略。除了前述困境,美国决策界和国际关系学界对“治理”和“全球治理”的有限讨论,使美国领导下的北约在全球治理领域更为困难。总的来看,北约的全球治理战略内嵌于其全球化联盟战略中,尚处于非系统状态。不过,为适应冷战后的新形势,特别是非传统安全威胁,北约在理念与实践上都致力于积极推进联盟的战略转型。可以说,向全球化转型的北约联盟战略包含全球治理战略的因素是不争的事实。由于安全治理契合冷战结束后北约向非传统安全合作拓展的战略需求,因而构成北约全球治理战略的核心。从本质上看,从北约全球战略到全球治理战略,再到安全治理,反映了北约政策制定者们力图使联盟更好地实现转型,确保联盟在新时期的生存和发展的新思路。只是,这种思路目前尚不够清晰,使北约全球治理战略的实践深受影响。 注释: ①1991年之前的北约战略文件,可参见Gregory W.Pedlow,eds.,NATO Strategy Documents 1949-1969,Brussels:NATO International Staff Central Archive,1997。 ②Timothy J.Birch,"After the Threat:NATO and European Defense in the Post-cold War Era," Ph.D.dissertation,University of Missouri-Columbia,1995,pp.118-119. ③"An Alliance for the 21st Century," Apr.24,1999,see http://www.nato.int/cps/en/natolive/official_texts_27440.htm?selectedLocale=en. ④"Active Engagement,Modem Defence," NATO Public Diplomacy Division,November 20,2010. ⑤该联盟战略认为,全球性的人口变化会加剧诸如贫穷、饥饿、非法移民、大范围流行病等问题的严重性。 ⑥Nicole Ameline,"Matching Capabilities to Ambitions:NATO towards 2020," November 2012,International Secretariat,NATO Parliamentary Assembly. ⑦张健:《北约新战略概念解析》,《现代国际关系》2010年第12期;许海云:《北约“亚洲政策”的表现及其影响》,《现代国际关系》2007年第2期。 ⑧"NATO 2020:Assured Security; Dynamic Engagement," NATO Public Diplomacy Division,May 10,2010. ⑨Graeme P.Herd and John Kriendler,Understanding NATO in the 21st Century:Alliance Strategies,Security and Global Governance,New York:Rutledge,2013. ⑩有关冷战结束后对国际恐怖主义、跨国犯罪、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等新型国际安全威胁的安全治理分析,可参见Commission on Global Governance,Our Global Neighborhood,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5,p.79; James N.Rosenau,"Governance,Order,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 in James N.Rosenau and Ernst-Otto Czempie edited,Governance without Government:Orde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2,p.3。 (11)有关北约对网络恐怖主义的高度重视,位于安卡拉的北约“反恐卓越防御中心”2008年编辑出版的一份研究报告可见一斑。See Centre of Excellence Defence Against Terrorism,ed.,Responses to Cyber Terrorism,Amsterdam:IOS Press,2008. (12)有关北约针对网络攻击的“网络安全治理”,可参见Herd and Kriendler,Understanding NATO in the 21st Century:Alliance Strategies,Security and Global Governance,New York:Rutledge,2013,pp.154-175. (13)这项举措构成了北约《综合方式行动计划》(A Comprehensive Approach Action Plan)的重要组成部分。 (14)这三项建议包括:(1)在北约内部建立一批监测与评估机制,包括援助盟国的第5条——比如在不启动第5条的情况下做出联合协商和反应战时;(2)海上监测;(3)可能的军事封锁行动。See Herd and Kriendler,Understanding NATO in the 21st Century:Alliance Strategies,Security and Global Governance,New York:Rutledge,2013,pp.191-213. (15)有关北约“无边界集体防御原则”,可参见许海云:《利比亚战争后的北约及其动态研究》,《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5期;关于北约在防区外进行集体行动的困境,可参见吴宇:《北约成员对美防区外战争的反应》,《国际政治科学》2013年第2期。 (16)Birch,"After the Threat:NATO and European Defense in the Post-cold War Era," Ph.D.dissertation,University of Missouri-Columbia,1995,p.103. (17)Christopher Coker,"Why NATO Should Return Home:The Case for a Twenty-First Century Alliance," The RUSI Journal,Vol.153,Issue 4,2008,pp.6-11. (18)安全治理的另外两项重要假设是:(1)地理和职能的专业化降低了国家间战争的威胁;(2)国家更倾向于与其他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一起解决各种国家或国际安全问题。参见Elke Krahmann,"American Hegemony or Global Governance? Competing Visions of International Security,"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Vol.7,No.4,2005。有关“意愿联盟”与其他联盟的区别,可参见Jeremy J.Ghez,"Alliances in the 21st Century:Implications for US-European Partnership," RAND,2011,pp.vii-viii、4-6。 (19)孙德刚:《论“准联盟”战略》,《世界经济与政治》2011年第2期。 (20)不过,也有分析家指出,在一系列安全议题上,北约始终保持大量正式和非正式的网络供成员协商和协调。特别是,北约已建立起自己的快速反应部队(RRC)负责域内事务。盟国的远征部队执行域外紧急事态的情况下,快速反应部队也可被派遣执行这些任务。按照伊丽莎白·舍尔伍德的说法,这种“影子联盟”构成了北约力量的一部分。Elizabeth Sherwood,Allies in Crisis:Meeting Global Challenges to Western Security,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90. (21)有关北约的多边主义与美国霸权争论的经典分析,可参见Steve Weber,"Shaping the Postwar Balance of Power:Multilateralism in NATO,"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46,No.3,1992; Steve Weber,Multilateralism in NATO:Shaping the Postwar Balance of Power,1945-1961,Californi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1。 (22)Sally McNamara,"The Bucharest Summit:Time to Revitalize the NATO Alliance," March 27,2008,No.2119. (23)Ivo Daalder and J.Goldgeier,"Global NATO," Foreign Affairs,September/October 2006,pp.105-113. (24)这里所以用“法理”一词,而不是用“合法性”,主要是出于北约面临的这种困境不仅仅是国际法意义上的合法性问题,而且还兼具政治秩序意义上的正当性与合理性的问题。 (25)Michael J.Matheso,"United Nations Governance of Post-conflict Societies,"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Vol.95,No.1,2001,pp.76-85. (26)Manuel Castells,"Global Governance and Global Politics," Political Science and Politics,January 2005,pp.9-16. (27)Ameline,"Matching Capabilities to Ambitions:NATO towards 2020," November 2012,International Secretariat,NATO Parliamentary Assembly,p.3.标签: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论文; 军事论文; 大西洋论文; 全球治理论文; 北约成员国论文; 美国军事论文; 冲突管理论文; 中国边界论文; 联盟标准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