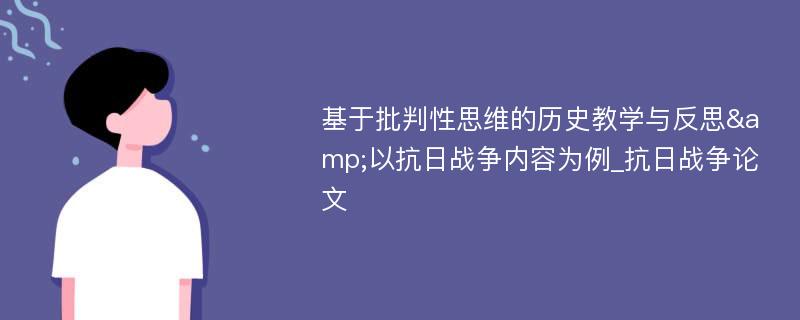
基于批判性思维的历史教学与反思——以抗日战争内容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抗日战争论文,批判性论文,为例论文,历史教学论文,思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历史批判性思维的最本质特征是追求真实、论从史出。茅海建先生说:“一直以来,中国近现代史学科发展的轨迹是主题先行,很早就有了许多重要的结论,但这些结论所依托的史实却是在匆忙中搭建,根基并不是很深……学术发展到今天,我们手中并不缺乏结论,相反的是,我们的思考却为各种各样相互对立抵牾的结论所累。”[1]而中学历史教科书所汇聚的,恰恰包含了根基不深、经不起查证的“史实”。中学历史教学若仍然沿用经不起查证的“史实”和结论,如何能承担起提高现代公民人文素养、培养创新型人才的责任呢?所以反思历史教学是十分必要的,下面笔者就抗战史教学谈一些认识与思考。
一、问题的呈现——抗战史教学反思的现实要求
首先,反思抗战史教学是贯彻课程标准的要求。课程标准要求通过教学培养高中学生从不同角度发现问题,“探究历史问题的能力和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论从史出,史论结合”,但由于种种原因,很多教师仍然沿用革命史观讲述新课程内容,简单的阶级分析法仍大行其道,掩盖了历史的复杂性。近几年有关抗战的影视剧风靡,《中国远征军》《滇西1944》《亮剑》几乎家喻户晓。影视作品和媒体传播的历史信息与历史课堂教学内容形成巨大反差,学生们关于抗战史的认知早已超出教科书的描述。如果不反思抗战史教学,历史教育如何培养学生“求真求实”的品质?
其次,反思抗战史教学是新课程高考的要求。陆静老师在《从高考抗日战争的试题反思教学》一文(《历史教学》2010年4期)中,从2008年以来全国卷和海南卷、广东卷中摘取大量实例,说明仅仅依据教材复习备考是不能应对高考的,并且认为:“高考对某段历史要求掌握到什么程度,这是第一位的问题。高考考试范围不一定以教材为准,高考的标准是什么,只有研究高考试题才能得出结论。第一位的问题不解决,中学教学永远处于滞后的、被动状态。”教材是高考命题与中学历史教学的聚焦点,但不是说教师只要教教材,学生只要背教材就行。教材总是滞后于学术,但中学历史课堂不能滞后。况且,高考历史科命题强调“不拘泥于教科书”,[2]历年高考试题也已证明,追求真相是高考命题的重要指导思想,故有高考命题专家这样说:高考命题的角度很多是用来批判教材的,近几年高考的材料题很多材料也是取自于各领域学术研究前沿的成果。我们认同在教科书的基础上建立新的知识体系,这个新的知识体系不能脱离教材,但要纠正、补充教材的缺陷。而用来纠正、补充教材缺陷的工具就是批判性思维,材料应来自不断更新重建中的“史实”和“结论”,来自学术研究的前沿,至少是比较前沿的成果。
新课程改革实施以来,一线教师的教学手段、模式、观念在悄然改变,但也不乏为了迎合教学组织形式的创新而丢弃了教学内涵的发掘和提升的情形。笔者以为,中学历史教学的批判性思维与历史学术领域的批判性思维的指向应该有所不同。学术层面所指向的,主要是史实和结论的重建;而中学历史教学除了要吸收新的学术研究成果,还应该更多地指向现行教材的结构编排、材料选择以及对课标要求的相关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全面呈现和多元思考。
二、问题的追溯——课标与相关教科书中的抗战史
新课程历史教科书对抗战史的叙述有所变化,主要表现在对日本侵华罪行的叙述逐渐增加,有关正面战场初期抗战内容比重加大,国共关系冲突渐渐淡化等方面。这些改进是相对客观的,但“一纲多本”的现状使不同版本教科书在客观性上有较大的差异。
课程标准将抗战史归入政治史模块之“列强侵略与中国人民的反抗斗争”,具体要求是:“列举侵华日军的罪行,简述中国军民抗日斗争的主要史实,理解全民族团结抗战的重要性,探讨抗日战争胜利在中国反抗外来侵略斗争中的历史地位。”值得注意的是,课程标准将抗战史作为一个单独的学习要点,是有别于近代其他的侵华史和抗争史内容的。但由于编写者对此的理解不同,故不同版本教科书对抗战史的编排、内容选择及表述也有差异。
首先,不同版本教科书对抗战史的编排及篇幅大小不同。岳麓版和人民版教科书目录中找不到“抗日战争”的字样,前者将其纳入“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发展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单元,在第21课《新民主主义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用第五个小目“国共合作抗日”来呈现,占了两个多版面;后者在相关单元之“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一目中呈现,其表述加上标点仅95个字符。其次,不同版本教科书对抗战史内容的选择也存在明显差异。如对滇缅战场的介绍,是人教版内容选择上的一大亮点;岳麓版增加了国民政府“以空间换时间”的抗战战略;人民版几乎没有抗战具体事件的表述。
诚然,各版本教科书客观性上不同程度的差异会给教学带来一定的挑战,但这不能成为历史教师放弃追求客观真实的理由。教师不应局限于教科书,而应立足于批判性思维,适度延展教学内容,对教科书所选择的素材进行二度开发,在求真求实的氛围中开启学生的智慧之门。
三、教学的反思——基于批判性思维的抗战史教学
抗战史历来是学术研究的重点,随着学术环境的开放、研究领域的拓展,有关抗战史的新内容、新提法、新观点也多了起来。虽然教科书不可能及时反映,但相关新成果对学生全面了解“中国军民抗日斗争的主要史实”,正确理解“全民族团结抗战的重要性”是极为有益的,中学历史教师应及时了解抗战史研究的学术动态,加强教学内涵的挖掘,以扭转“教教材”的传统做法。如针对高一年级学生,教师可以发掘本土教学资源以延展教学内容,激发学生学习热情。以湖南为例,相持阶段的抗战可用发生在1943年被史学界称为东方“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的常德会战,该会战规模之大、兵力之多、战线之长,仅次于台儿庄会战,国民党第74军57师师长余程万率部死守常德的战斗业绩,在抗战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并见证了国民党军队的抗战。还有著名的长沙会战、衡阳保卫战等。教师可通过向学生提供发生在本地的史事,引导学生阅读和理解材料,挖掘历史的价值和意义,让学生在领悟和思考后得出结论。
针对文科班学生,教师在把握高考试题趋向的同时,一方面围绕课标落实基础知识,一方面依据学术研究成果对教科书内容进行取舍、延展。根据抗战史教学实践,笔者认为,至少以下几个问题在教学中是不能回避的,应立足批判性思维有针对性地反思。
1.适当补充中缅战场问题,以弥补教材不足。从学术上看,我们可以把抗战中的中国战场分为敌后、正面、中缅国际三个战场,也可把中缅战场归入正面战场。中缅战场有很多值得介绍的人和事,如战场开拓卓有成效的美国人史迪威;血洒疆场的国民党高级将领戴安澜及十万中国远征军;战功卓著的孙立人和仁安羌大捷等等。教师可在史料的基础上说明,作为中华民族抗击日本法西斯的重要组成部分,二战期间中美英反法西斯国际合作的重要战场,中缅战场具有无可替代的地位,中国军队不仅打击侵华日军,还抗击了东南亚的日军,不仅独自承担着国内抗战的艰巨任务,还与国际力量共同作战。全面理性认识抗战的历史有利于培养青年学生正确的人生观、民族观、价值观。
2.关于持久战略的提出问题,应适时给予正确引导。岳麓版对“以空间换时间”做了简单阐述,但事实上,早在1937年夏,著名军事家蒋百里在《大公报》上发表《国防论》一文,提出了持久战思想;1938年,国民政府确立了“以空间换时间,积小胜为大胜”的战略方针。教学中,教师应基于事实,正确解读史实与《论持久战》的关系,强调虽不是毛泽东最早提出“持久战”思想,但《论持久战》在持久战略、人民战争、游击战术等方面,“异常清晰而符合实际的判断,回答了人们最关心而一时又看不清楚的问题,使人们对战争的发展过程和前途有了一个明白的了解,大大提高了持久抗战的信念。”[3]所以,《论持久战》是一篇足称伟大的著作。
3.关于相持阶段国民政府抗战问题,应该以史实分析为主。长期以来,关于抗战相持阶段的教学,教师习惯以皖南事变和豫湘桂战役为例来说明,即认定皖南事变是蒋介石的“蓄谋”,“皖南新四军不管走哪条路线,均避免不了蒋的袭击”,[4]并被作为国民政府“积极反共”的铁证;1944年国民政府组织的豫湘桂战役是一次“大溃败”,被作为国民政府“消极抗战”的典型。关于皖南事变,学术上存在较大争议,如中共党史研究专家杨奎松先生认为:蒋介石国民党并未有过一个明确的旨在处心积虑消灭皖南新四军军部的蓄谋。[5]建议教师们尽可能淡化处理。只有用客观的态度分析才能更好地揭示抗日战争时期蒋介石国民党对共产党态度的变化及其原因,让学生明白历史的复杂性。关于豫湘桂战役,历史学者温锐、苏盾等人从1944年正面战场的战略意图、战场得失以及它在客观上对中共领导的中国革命的影响入手,探讨了1944年的中国正面战场,认为正面战场事实上形成了“东守西攻”的战略态势,随着滇西战场的胜利,中国战场摆脱了遭受东西夹击的局面,为1945年东线战场反攻态势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从东西两线得失看,整个正面战场还是得大于失。[6]客观地看,抗战后期的国民党战场在牵制、打击日军,并最终打败日本侵略者的过程中是发挥了重大作用的。关于抗战后期正面战场的作用,教师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分析:挫败了日军的战略企图;有力支援、配合了盟军在太平洋战场的作战;支援、配合了敌后战场。一方面,西线的中印缅战场中国军队反攻不断发展,并在1944年底取得了缅北滇西战役的决定性胜利,打通了中印国际交通线,为战略反攻准备了有利的支援条件;另一方面,东线豫湘桂战役的作战牵制了大量日军,使日军无法抽出更多的兵力加强太平洋战场,也减轻了中国敌后战场的压力,对太平洋和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起了积极的作用。
4.关于战略反攻的时间质疑,教师可以呈现不同的说法并加以分析说明。长期以来,史学界多以全面战略反攻为标准来衡量中国抗战的战略反攻时间,回避或不谈国民党正面战场的战略反攻。近年来,随着研究的深入,有人对反攻标准进行商榷,对反攻阶段的起始提出看法。有学者认为,反攻始于1944年的滇西战场;有人认为始于1945年初;还有人认为从1945年春夏之交的老河口战役、湘西战役开始。教师可以根据自己对历史的认识与理解进行介绍,进而指出中国抗战的战略反攻问题,是国内外史学界长期争论的一个热点。这不仅事关战略反攻问题本身,而且涉及对中国抗战后期的形势、地位及作用等重大问题的认识和评价。
教学实践表明,立足于批判性思维,论从史出,才能启迪学生的智慧,这样的教学态度,无论是对贴近高考,还是对促进历史教育本质要求的实现,都具有积极意义。这就要求我们本着正确的史观,把握好课标的要求和方向,选择教学素材、设计教学问题,尽可能地对教学对象的“然及所以然”做最好的诠释:对那些滞后的史学观点,需要用新观点、新提法取代而不刻意回避;对陈旧而已被基于史实重建的新研究证明是不可靠的结论该说明的一定要说明;对现象背后那些需要加以分析的问题要适当引导。
笔者认为,如果说关注史学研究动态,启发学生历史思维,培养学生探索求真之心,是历史课堂教学在内涵方面的追求,那么高中历史新课程对中学历史教师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们不一定都是学者,但我们可以将成长为“学者型”的教师作为我们的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