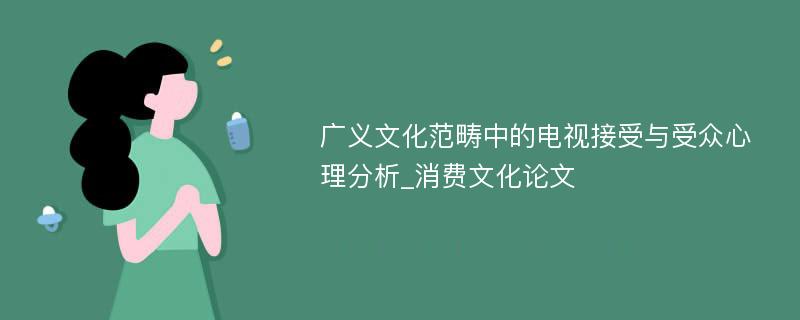
广义文化范畴中的电视接受及受众心理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广义论文,受众论文,范畴论文,心理分析论文,电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电视接受是一种全方位的精神活动
人,作为社会存在的主体,具有双重的“生产——消费”属性。作为电视接受的观众,也不可避免地受“生产——消费”的社会机制的制约。广义而论,人的这种“生产——消费”属性具有两大方面的内容,即物质产品的生产与消费和精神产品的生产与消费,电视接受在文化形态上,正是这两种生产与消费的统一体,但在观众心理的意义上,它更多地体现为精神生产与精神消费。就“精神”的内涵而言,这是一个无所不包的世界,正如电影主要表现为艺术的精神现象一样,小说、诗歌,更多地表现为文学的精神现象,而政治、经济等的观念形态,则表现为社会意识的分类的精神现象。那么,电视的“精神”生产与消费该如何理解呢?我们认为,电视的消费不是单一类型的精神消费,而是一种全方位的精神活动。
一般而论,电视文化的基本形态由电视文化的文艺形态、教育形态及商业形态构成,从这个意义出发,电视接受是否也可以理解为三种类型的文化接受呢?的确,这三种类型可以是电视观众接受形态的基本类型,但在整体上,电视接受并不是这三种类型的绝然对立,而是这三种形态以及其它形态的杂处形式。人们在新闻节目中感受政治、经济、文化等观念的冲击,在文艺节目中接受伦理、道德的熏陶和审美教育,在广告节目中领略现代经济、文化的新风采,在各种知识性节目中获得广义教育的知识,在与观众相关联的节目安排中,寻找人与人的沟通、理解等等。我们甚至还可以进入深层去寻找这种杂处形式,如在文艺节目中,人们既可以窥视现代服饰与服饰的演变,又可发现某一时代的社会心理、人情冷暖;既可以发现古代战争的隐秘,亦可看到现代政治的演变;既可以了解旧文化的发展,又可畅想未来世界的景象;既可以认识教育儿童的价值,亦可觉察老年人的“童心”世界;既可看到罪犯的猖狂,又可体验到英雄的伟大,……我们甚至可以无限制地写下来,因为生活有多丰富,文艺就有多丰富。在新闻及其它节目中,社会变化的丰富同样可以在电视接受中形成多重文化因素的复合,诸如政治心理的演变,阶级意识的渗透,伦理观念的净化等,都可以成为电视接受中的心理效应。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电视接受可以看作是一种全方位的精神活动——无论是接受的具体形态,还是深层意蕴,都统一在“全方位”的前提之下。但“全方位”并不与“不可知”相等同。在心理意义上,电视接受可分为三个层次:一是电视接受与人本心理的关系;二是电视接受心理的社会性变异;三是电视接受心理的审美升华。事实上,电视节目的制作与编排也必须以观众心理为出发点,也应按照人本心理——社会心理——审美升华的心理趋向加以考虑,否则将出现电视接受的非积极性效应。从电视观众的接受而言,这种层次的划分也将为顺应观众心理——重塑观众心理奠定理论基础。
二、电视接受心理与人本心理的关系
电视接受是一种实质性的精神消费,精神消费的核心是心理问题,从接受主体出发,这种心理表现为人本心理及其在变异过程中的寻求与满足。
所谓人本心理即存在于人的内心世界的主体。对于人而言,物质世界的对象是客观的物质存在,心理世界的内涵则是一种主观的精神状态,这种精神状态表现为人的内心的体验,这种体验又离不开人的生理存在。著名的心理学家,被称为“第三思潮”代表人物的马斯洛将人的需要分为五个层次,即生存需要、安全需要、归属需要、尊重需要和自我实现的需要。但这五种需要并不是单独孤立的存在,而是一种杂处的形态,表现为多重的动态复合。生存也是自我实现的一种形式。归属也不排除生存的成份。这样,这些需要仅仅表现为人的需要及其实现的一般过程,并不能显示出人本心理的具体内涵。所以,理论上又将弗洛伊德的学说视为人本心理的“恰当”的概括,但实际而论,性心理作为一种人本心理的确存在着,但它绝不代表一切,性心理是生存需要也是自我实现的需要,却不是存在着的人的唯一需要。我们认为,从人本心理角度讲,性爱心理、主宰意志、服从意识、尚武心理、慈善心理、娱心心理都是人本心理的具体表现形式,这些形式在人的心理中按照马斯洛所归纳的五个需要的层次发生运动,而在具体的特定的心理过程中,又常常以某一种具体形态如性爱心理的爱情显现,慈善心理的母爱意识显现而表现为“个体的体验”。
电视接受显然在最基本的意义上与上述各种人本心理有着密切的联系。当电视观众作为被动接受者时,接受主体并没有固定接受意向,但接受主体在五彩缤纷的世界中,就不可避免地出现选择与认同,排斥与超越等心理趋向,在这种趋向的流程中形成“历史”与“现实”与“未来”相交融的心理定势,于是,人本心理种种内涵的面影便在一种“消费”中成为一种“消费的基础”。以性爱心理为例,鲁迅曾说过“才子”从《红楼梦》中看到的是“缠绵”这样的话。事实上,这种心理体验并不仅仅存在于“才子”之中,凡具有正常的性心理的接受个体都会从中体验到这种性爱意识及其心理显现。当《红楼梦》拍成电视剧并在电视中广为传播时,作为人本心理之一的性心理,便在与艺术中的情爱现实的对应中形成心理碰撞,生成以性爱心理为基础的各种观念形态的爱情观(注:这是人本心理的社会性变异,我们将在下一个问题中论述。)。再以尚武心理为例,人,尤其是在男性儿童心理中,以父性为崇拜对象的心理外化为一种“权力意志”进而演化成一种破坏性心理积定,于是就有男性儿童经常性的“斗殴”事件的发生,这种事件的内涵便是人本心理的征服欲或称“尚武心理”。不用说这种心理与电视文艺中的武打类型的节目相对应,就是在一般新闻节目中,这种本能的心理也能找到对应关系。假如新闻中播出某某国与某某国正在开战,并以清晰的图像报道了战斗的情况,接受个体在接受过程中,除了对时势等内容的顺应或逆反的接受之外,还潜存着对战争的厌恶感——表现为人本心理中的慈善性,同时也潜存着对“征服欲”的认同感——表现为人的“尚武心理”,比如可能会出现“假如我是指挥官”这样的潜意识,也不能排斥“假如我是总统”这样的潜意识的出现,其中,人的荣誉,权力意志也表现为儿童期尚武心理的变异形态。显然,在电视接受中,从最基本的层面出发,人本心理与电视接受心理是一种同构关系,且由于人本心理与电视的传播接受都是动态的结构,人本心理与电视接受心理的关系可表述为动态的同构关系:任何一种人本心理都可能在潜存意识中突发性地与一种电视内容的接受现实形成对应,个体与群体,都无法超越这种关系。
三、电视接受心理的社会变异
电视接受是社会存在的人的行为,社会存在的人的主要特征便是人的社会属性,所以,电视接受主体的心理状态就必然受社会属性的制约,这种制约又表现为电视接受心理中的决定性因素,由于这种决定性因素导源于人本心理,又称为电视接受心理的社会变异。
西方心理学家弗洛伊德将人的性意识界定为人的原欲并在此意义上认定人的心理是性本能的显现,成为轰动世界的理论,但很快,连他的最有力的支持者荣格也另立炉灶,举起“集体潜意识”的旗帜,从而将人的本能看作是一种社会发展的产物。后来的科学家曾就这些问题加以研究。如雅克·莫诺在《偶然性和必然性——略论现代生物学的自学哲学》一书说:
万物都来源于经验,这并不等于都来源于每一新世界的每一个体所反复进行的当前的经验,而是来源于物种在其进化过程中的所有祖先积累起来的经验。只有那些被选择的和经过磨炼的无数次尝试——才能同其它器官在一起,使得中枢神经系统变成一个器官,使之适合于它自己的特殊功能。(注:厅·莫诺《偶然性和必然性》第114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
接着,这位1965年诺贝尔医学和生理学奖获得者又说:
每个活着的生物也是一种化石。在每一个生物体内,所有的结构,包括蛋白质的微观结构,都带有它祖先遗留下来的痕迹……同其他动物物种相比,人类更是依赖物质的和观念的双重进化的力量,人就是这种双重进行过程的继承人。(注:厅·莫诺《偶然性和必然性》第114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
显然,生物学家也认为人作为生物物种的进化,存在着先验形态。那么,作为物质与精神一体的存在着的电视观众,不也同人的存在一样,具有多重的社会性吗?!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明确说过,“人们是自己的观念思想等等的生产者,但这里所说的是现实的,从事活动的人们,他们受着自己的生产力的一定发展以及与这种发展相适应的交往(直到它的最遥远的形式)的制约。”(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0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交往,是人的需要,也是人的社会属性的外在形态,对于电视接受心理而言,这种精神生产与消费是人的交往的直接产物。仅以电视接受中的艺术接受为例,人们普遍认为艺术的起源是个体人为了将自己体验过的感情传达给别人,在自己心中重新唤起这种情感并以某种外在形式表现出来的心理历程,反之,艺术接受也不仅仅是一种感情的需要,因为接受主体的情感创造欲也是一种客观的潜在结构,正如我们在前一问题的分析中所表述的,这是一种同构关系,只是这种关系是以整个社会为背景而存在的,因此,电视接受心理就不可避免地具有社会性变异——人本心理的客观存在是一种无序的杂乱形式,人本心理的社会性变异,则表现为人的社会心理的有序结构,正如法律道德是人的存在的制约机制一样,这种社会性变异是一切精神活动的制约性存在机制,电视接受作为精神现象之一类,亦不能例外。
那么,电视接受心理的社会性变异有哪些基本形态呢?
首先是时代精神与历史意识。本世纪80年代初,在日本和中国均形成一股旋风的电视连续剧《阿信》及其所形成的接受心理,是值得引起注意的。在宏观背景上,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的文艺发展有很多积极的现象,其中,作为一种美学风范的“坚忍心理”,便是重要的时代精神,一方面,它表现为民族心理的重建;另一方面,它体现出对传统文化的顶礼膜拜,同时,它还与吸收外来文化的心态构成矛盾的统一。当《阿信》播放时,一时形成人人足不出户的景观,尤其是一代女性,更视其为“慰安的天国。”人们希望在电视接受中得到什么呢?这与其时日本国民的思维定势有关。通观全剧,人们看到的是阿信的一生与近代日本历史的侧面,从明治、大正、昭和三个历史时期的世态和人际关系中,从阿信由一个贫家女而成为拥有众多超级市场的老板娘的历程中,一种接受关系在内质上表露为对日本人战败到经济繁荣的社会心理的认可与梳理、反思与前瞻。同辈人在阿信身上寻找逝去的年代,晚辈人在阿信身上寻找一个民族的历史。显然,一种时代精神与一种历史意识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与此同时,人本心理的面影也寓于其中。在阿信的情感生活中,可以发现人本心理的性爱意识;在她为人帮工的苦难生活中,隐蔽着接受者的主宰意识与服从意识的矛盾,以及慈善意识所展示的同情心,进而与社会属性的阶级观念联系在一起。这些具体的接受内容在总体上又与时代精神及历史意识相对应而存在。所以说,电视接受中的人本心理只能是一种“集体无意识”的存在形态,只有与社会属性构成一体时才有意义。
其次,是道德与文化意识。道德是人的自我规范,往往表现为“历史与现实的统一”。道德又是一种具体的精神文化现象,与文化意识相关联。如电视接受心理中的性爱心理,已超出了一般的性的规范,成为一种文化形态。接受主体可能会对电视中的情爱现实予以性心理的一般认同,但更多是的性爱心理的道德化认可。以电视连续剧《红楼梦》为例,对于最主要的两个女人,人们的道德评价往往是多种多样的。人们认为薛宝钗知书达理、有品有貌,在经济上也不依赖别人,在她身上最完整地体现了两种规范,一是作为女人的贤妻良女,一是封建时代的传统道德,也正由此,才使得她终于陷入被遗弃的境地;同样,人们认为林黛玉缺少一种封建淑女应该具有的道德条律,加上她天资聪颖,多情善感,使她在一种不适宜的环境中显得有点“超越”,而正是这种“超越”与薛宝钗的“固守”形成两种道德观念的撞击。进而,人们得出结论,认为黛玉是爱情,宝钗是婚姻。由此,不难看出所谓人本心理的情爱观念是与性爱意识的社会化分不开的。
电视接受心理社会性变异的其它类型包括神话意识、宗教意识、政治意识、阶级意识等等。以神话意识为例,电视连续剧《济公》之所以在接受群体中成为普遍欢迎的对象,就在于济公形象满足了一种扶正除邪的社会心理,而这种“匡扶正义”的意识自古以来已经成为一种社会的崇拜意识,并且已经“神话化”了。其中,也难以回避“慈善心理”的潜在的影响。
总之,社会的精神现象已随着人类的历史发展逐渐形成了有序的结构形态,作为精神现象之一的电视接受,尽管以人本心理为基础,但起决定作用的仍是社会精神的心理体现。
四、电视接受心理的审美升华
电视接受是社会、节目制作、节目形态与观众的具体接受行为的一体化的凝聚物。从接受理论的角度看,通过影像传播形态问津观众的电视,只有在接受过程中才能完成传播的形式,而作为接受主体的观众又是具体的人,整体的人,甚至是抽象的人。而在人的需要中,审美愉悦又是一种普遍存在却又是最高境界的情致——通过心理活动达到的特定阶段。在现实中,并不缺少美,但在“第二自然”的艺术世界及与此相关的文化传播中,都存在着“更美”的形态。由于人本心理的无序,由于社会心理的有序,审美心理便表现为一种“整合”,即在杂乱的人本心理的基础上,通过社会审美规范化、借助艺术如电视及传播的情感形式,通过审美境界,使接受主体形成心理境界的“审美愉悦”。马克思曾说过:“动物只依照它所属的物种的尺度和需要来造型,但人类能够依照任何物种的尺度来生产,并且能够到处都把内在尺度用到对象上去,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造型。”(注: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96页。)电视节目的制作也体现着这一精神,表现为对对象的主体渗透——主体的意志、主体的情感、主体的道德、主体的美学理想。而作为在一定的前提下完成的电视接受形态,也同样体现自身的美学理想等以达到满足主体审美需要的目的。电视接受心理正是在这双向的碰撞中形成审美的创造意识,即“按照美的规律来造型。”当我们以电视接受中的艺术接受为主要描述对象时,便会发现以人本心理为基础,以社会属性为制约的这种接受关系在更高层次上是一种审美关系。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没有电视的艺术创造,电视接受必然失去对象之物;二是电视的生产和电视艺术品的审美性质规范着电视接受必须具有审美的形式;三是电视艺术生产出能够消费它的“消费主体”。诚如马克思所说:“艺术对象——任何其他生产物也一样——创造着有艺术情感和审美能力的群众。”(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第155页。)因之,电视观众也具有主体的情感和审美能力。换句话说电视观众的心理状态是一种审美感知和审美理解。这种理解贯穿在整个电视接受过程之中。因为电视观众总是让自己的感知、想象和情感循着对象的指引和规范,自由地和谐地活动起来,而在最终获得审美愉悦中,蕴含着对于对象所具有的社会理性内容的理解和认识的,电视文艺节目的接受如此,其它节目也不例外,因为“第一自然”与“第二自然”的和谐一致是靠一种“审美力”来实现的。试举一例。女作* 王小鹰喜得“千金”,为普遍流行的杂志《家庭》写了篇“主妇手记”,题为《活杀鱼》,文中叙述了她为了女儿吃鱼,去市场买了活鱼回来,在杀鱼时,如何不忍心,后来竟产生了“毛骨悚然”的心理感觉。这时,“丈夫探进头来问:‘怎么回事?’我望望我两只沾满鱼血的手,轻轻说‘我简直象个凶恶的刽子手!’丈夫笑了,说‘你看过《动物世界》的电视节目吗?狮子无比残忍地噬杀了梅花鹿,当它叼着鹿肉去喂它的小狮子时,你又觉得它的慈爱,世界本身就是这样的。赶紧煮鱼吧,棒棒等急了。’”(注:王小鹰《活杀鱼》,载《家庭》1990年第5期。)这是一篇生活实录,无意中透露出一种电视接受的心态。首先,妻子对杀活鱼之不忍心,是人本心理中的“慈善心理”,但又必须杀鱼,则是一种社会规范——人的生存需要,进而这种生活需要又被一种道德意识所同化——“世界本身就是这样的。”问题在于,这“点睛”之笔的内涵是什么呢?从结局看,鱼总是要杀的,但所举电视节目中的“狮子与梅花鹿”的事实为例,实际上是一种“自然的人化”与“人化的自然”的统一的心态的解剖:世界的本来面目就是美与丑共存,离开其中的一方,另一方也就不存在了。显然,这是一种审美判断,而思路的引发又是电视中“凶恶的狮子”与“慈善的狮子”的统一,由此窥见字里行间隐着一句:人,难道不也是如此吗?我们再也无法否认这种道德意识是以审美情感为依附的,人本心理、社会心理和审美心理是三位一体的,这种心理的变化与组合可称之为“审美升华”。在电视文艺接受中,它表现为审美情境的产生,在电视其它形式的接受中,它表现为道德心理的认同与超越——一种审美感的伴随性感知。
五、求真、求知、求美的辩证统一
在前文中,我们将电视的文化类型分为三个最基本的形态,即艺术类型、教育类型和商业类型。这些类型在实质上并不与电视节目形成固定的对应,却又具有一定的对应性,同时我们又认定电视接受心理的基本走向是“人本心理——社会心理——审美心理。”当我们仔细分析电视节目的构成时,便会发现电视接受心理在具体的接受过程中并不具体地体现为人本心理、社会心理抑或审美心理的单一显现,原因在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在社会意识的大系统中,人的意向是一个复杂的子系统,作为电视接受者来说,其主体意向也必然是这个复杂体的显现。假如一定要寻出人的意向心理,恐怕又有不同层次的划分。如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伦理观等属于高级的意向心理,而兴趣、动机、偏好以及同环境制约的态度等则属一般的意向心理,这两个方面又共同构成一种需要心理。在电视接受过程中,这种需要心理表现为多种形态,诸如我们曾经分析的道德心理、政治意识、文化心理以及时代精神与历史意识等都是诸形态的具体内容,照此分析,社会的复杂性在内容上的类型是无法穷尽的,因此,我们认为电视观众的接受心理在理论上并不以以上的种种类型加以总体概括,而应在一种社会存在的既非宏观的又非微观的认识中总结电视接受心理的统一形态,我们将这种统一的心理形态界定为“求真、求知、求美的辩证统一。”这是电视观众接受心理意向的“中观”概括。
何以为“真”,何以为“求真”?生活本身既是一种真。作为“第二自然”的电视形态,在接受的过程中,亦体现为对象化的物态真实。真是一种客观存在;是一种再造的真实;是一种“求真”观念;是“求真”的动态化过程——表现为电视观众接受主体的“善”的选择。“真”与“求真”是一种存在的两个方面。对于观众心理而言,在绝对意义上,真与求真,是一对不变的美学范畴,而与真相联系的“善”的内容,则是变化的,真与善是不可分离的。善的具体内容即如上分析的道德、政治、阶级、文化等因素及其观念的形态。
在电视接受心理中,这种求真心理表现为电视观众在心理上将真实的存在(现实与历史)视为参照系,吸收、评价、舍弃电视接受内容的精神过程。在电视文艺节目中,以曾在电视转播的电影《天云山传奇》为例,接受主体寻求的是一种对复杂历史与现实的重新评价: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在蜕变的过程中不断走向心理的自我完善,这正是民族心理“真”的表现,艺术的再现将这种真提高到更真的境地,电视(电影)接受主体心理中的“民族心理的真实观”在一种艺术接受中形成“真与善”的统一。在电视的非文艺形态的接受中,这种统一及其心理过程也表现出同样的“结构”。对世界政治事件的报道,观众世界观中的“真”的标准影响着观众对政治报道的选择与认同,当然,政治报道本身也体现出“真与善”的观念形态,所以,电视观众的“求真”与电视内容之“真”是一种同构形态。
同样,“求知”是电视接受心理的另一种中观形态。人,既要生存,就不能不进行知识的传授与学习。在这种现实的规范下,“求知”的电视接受心理外化为“电视的教育形态”,这种形态又有广义与狭义之分,我们是在二者统一的意义上认定这一“求知”的前提的。在人类发展中,知识作为一种文化形态,是人类得以持续不断发展文明的累积的形式。进入电视时代之后,知识的传播与接受扩大了范围,加强了深度,提高了速度。在专门的电视教育节目及接受过程中,“求知”成为直接的功利目的,在非专门的电视教育节目中,这种“求知”成为“需要”与“给予”的统一体,“需要”是人的生存本能,自我实现的人本心理的社会化形态,“给予”则是一种“选本文化”属性,电视观众的“求知”心理便在这种对应性结构中完成其运动形态。以儿童为例,社会的环境与儿童希望满足“为什么”的心理共同形成未成年人的教育形态,在电视传播中,专门的儿童教育节目按不同年龄层次设置传播内容,形成正规教育的补充形式,但儿童在电视中捕捉的更多的是非专业性教育节目的传播内容,诸如动画影片等。在正常的具有积极意义的社会秩序中,一切与儿童有关的非专业教育节目的内容,一般都在社会伦理的最基本点上伸展想象,如友谊、同情心、正义感、功善惩恶等,这些内容标志着儿童求知心理在满足过程中接受着既定的文化,由此引伸,随着年龄的增长,这种接受心理便成为一种心理定势,在继续不断的求知过程中,一般表现出积极的文化教育成果。同理,在成人的接受心理中,求知在深层内涵上与前述儿童的景况是一致的,只是更为复杂一些(注:参见拙作《一种文化机制:广义影视教育的形态及其构架》,载《北京电影学院学报》1990年第1期)。
求真与求知心理是人普遍存在的心理现象,在电视接受中,只不过表现得更为直接且以情感中介为载体。由于电视中存在着大量的文艺、亚文艺形态,由于电视中的非文艺性节目如新闻的影视形态的逼真性的制约,电视观众的接受心理便不自觉地遵守一般文艺接受的规范。文艺节目,亚文艺节目的情感属性自不待言,以影像为主要传播形式的电视新闻给人以亲切感,更能诱引一种情感的认同,在有些特别新闻节目中,时有催情的画面,音乐的陪衬,从而使电视观众的心理在一种情感接受中完成求真与求知的目的。这种求真与求知的目的在接受主体这里并不常常表现为“直接索取”,而表现为不经意的潜移默化形态,进而“真”与“知”的满足往往伴随着的是接受主体的身心愉悦——建立在情感形式与情感内容相统一的“满足”形态基础之上的一种境界,正如前文所述,这是审美境界,所以,在总体上,求真、求知与求美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这种“联系”所构成的统一形态,便是电视观众接受心理在人本心理、社会属性与审美境界一体化的意义上生成的综合效应。
至于影响到求真、求知、求美等形成的深一层次的心理因素,我们认为主要表现为“参与”和“选择”。
六、参与、选择及受众心理的自然完善
影响到接受者求真、求知、求美心理的主要形态是“参与”。人,作为电视接受主体,与通常意义上人的存在并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电视接受主体是个体的存在又是社会群体的存在,个人与社会、个体与群体,共同构成相互依存的关系。个体除了生理、生存的需要之外,还有自我实现、审美等等需要,而群体除了群体的生存需要之外,也有价值需要、经验的需要等。二者的统一构成社会的信息性传播、审美性的情感联结等。于是像尊重自我与尊重别人,保持个人心理平衡与平衡社会心理,个体的成就感与社会的发展目标等就共同形成主体人的社会存在与社会需要。在电视接受心理中,接受主体的参与意识便在这个意义上生成。中央电视台1986年的一次调查证明,电视观众首先是渴望获得各种信息,其次就是消遣娱乐。假如再深入地看这个问题,便会发现,获得信息的深层意蕴便是“参与”。比如政治信息的获取,便表现为公民的潜在的参政意识。西方各国的选举如全国大选等均借助电视完成信息传播与信息接受,选民的参政即参与的意识是极为鲜明的,决定这种参与意识的是公民(在这里具体化为电视受众)的存在观念:经济的、文化的、社会的或政治的观念。而这些观念又与观众的主体需要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妇女对主张妇女解放的竞选者予以青睐,老人对关心社会老龄化的竞选者予以认可。因此,需要与参与构成了一体。就娱乐而言,它也是人的消费需要的一种主要形态,从接受心理角度讲,主体的需要在这里要寻觅的具体内容是情感的参与与身心的愉悦。
显然,电视受众在屏幕前潜存着一种“参与”的心理,这种参与心理在与接受内容形成一致时,便构成“需要”与“需要的满足”。接下来的问题便是,主体的参与是否有选择性?
参与是一种选择,在受众的接受心理中表现为主体存在的复杂性。需要进一步说明的问题是,这种选择表现为多种存在形态与真实观念的有机统一。
首先,在宏观上这种选择是确定性与非确定性的统一。所谓确定性是指电视接受主体的世界观、生存意识等精神现象对个体与群体而言,都是既存的“真理性”形态,基本观念形态一经形成就会规范着主体的选择;而非确定性主要是指个体选择的随意性结构——不同的心境,不同的需要,不同的需要对象,变化的社会环境,动态的人际关系等是构成个体接受选择的因素。由于确定性与非确定性是主体接受过程中同时出现的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所以,二者在制约选择心理的同时表现为“对立的统一”。
其次,选择的多种存在形态具有民族差异、社区差异、阶级差异、性格差异等特征。1987,美国广播公司拍摄完成了一部描述前苏联占领美国之后社会状况的电视连续剧《亚美利加》。该片尚未上映即遭到两种意见的攻击,左派影评家认为这是对前苏联的污蔑,右派则抱怨说,电视剧将俄国人描写得太富有同情心了。试播之后,立即遭到前苏联的反对。其中,接受心理的选择性便表现为对立的阶级、民族及至意识形态的制约。选择,在这里表现为对政治的认同。再如80年代初期,在中国大陆各地电视台,不断播映了台湾、香港的一批电视剧,其中,《射雕英雄传》、《霍元甲》、《上海滩》、《十三妹》等在内容上明显存在着虚构甚至荒诞性,同时,还存在着游离于情节之外的“爱国主义金粉”,尽管如此,这些电视节目在当时依然大受欢迎,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从群体的选择性出发,我们发现接受主体的选择性在这里隐藏着一种民族崇拜心理,所谓一民族对一民族的心理认同在这里得到最佳体现。当然,正义、真诚与不太协调的爱国主题在接受心理上也是形成对应性选择的基础,但民族崇拜心理却是更深层的主体的选择倾向。
电视接受的参与心理所表现的选择性还表现为对表面的固定节目的选择,如对新闻节目的选择,对文艺节目的选择,对体育及其它节目的选择等。这种选择在参与的意义上更多地表现为个体或个性色彩。我们认为,这一问题在理论上的表述应是“参与是自我完善的机制”。
电视受众的参与心理是接受主体的自我完善的命题,更多的体现为个体性,而个体性则主要表现为个体存在的创造性和自主意识,在人格完善的意义上,我们称其为“自我完善”。显然,我们从人的存在的角度为这一问题寻找最基本的理论支架。
亚里斯多德曾把人定义为“社会动物”,事实上,这是不全面的。社会性,比如人的社会分工甚至还不如某些动物如蜜蜂和蚂蚁更明确,但是,人的社会决不仅仅是一种“分工”的社会,在人的社会里,我们看到另一种仅仅专属于人的社会性——语言、神话、艺术、政治、科学等高级的社会形式或社会的构成条件,这是人的社会意识的产物。换句话说,人只在在与上述各因素相关的社会生活发生关系时,才能发现人自己,进而言之,人才能在个体的意义上找到“个体性”或“自我完善”的契机。电视接受,正是人的这种社会活动之一类,所以,一种参与感便不可避免的体现为“自我完善”。稍稍再作深层的剖析,便会发现这个论题仍然缺少点什么——“自我完善”在上述的分析中实质上还是指人的群体,而不单单是指个体,作为补充,我们以如下的事实为例:自古以来,人们就发现蜜蜂在筑巢时,就像一个出色的几何学家那样达到了最高的准确性和精确性,这样的活动需要一种非常复杂的协调和协作系统,但是在这类动物的所有行为中,我们看不到任何个体的差别,而仅仅是单一的“物种”的尺度,相对于此,人的任何正常的个体选择都体现出“自由”以及发挥自由的能动性,人不仅建筑自己的“巢穴”,而且还建筑千姿百态的不同风格的“巢穴”。所以,人在整体和个体两方面都追寻着“自我完善”。电视接受作为人的社会化行为的中介,就无法避免参与心理的“自我完善”。假如以对电视中体育节目的偏好为例,我们可以找到多种既复杂又简单的个性和自我完善心理:对比赛节目十分热衷,通过电视弥补不能直接观看的损失;充满“热量”的个体借体育比赛的竞争排遣“能量”;弱者对强者的崇拜;打斗心理的别一种满足形式……这类一般形态的概括虽不能说是对“自我完善”心理的极为恰当的解释,但在个性心理的意义上足以证明“自我完善”意识的存在。在电视接受的其它类型的接受中,这种体现为“自我完善”的参与心理的例证俯拾皆是,但对每一种特定心理的个性显现,又极难做到绝对的准确,因为心理在这里的存在形态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动态多变的,况且,人本心理、社会心理、审美意识等方面的具体性因素又直接影响到参与心理,所以,“自我完善”又是一种“运动”的形态结构“自身”,我们称之为“自我完善的机制”。这种机制的构成,是人的存在因素的多重组合,而不能仅以某一方面的内容加以概括,因此,“自我完善”在电视接受中又具有普遍性。
电视接受行为中的参与意识,是接受主体的需要,是一种随机选择,是接受主体心理的自我完善的机制。
总而言之,在广义文化范畴中,电视观赏行为及受众心理,涉及人本心理、社会属性、审美境界等三大方面。在具体的接受行为中,对作为主体的受众而言,其求真、求知、求美的辩证需求心理,又以参与、选择及自我完善等心理因素为基础,共同构成了广义的电视时代电视人的电视文化心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