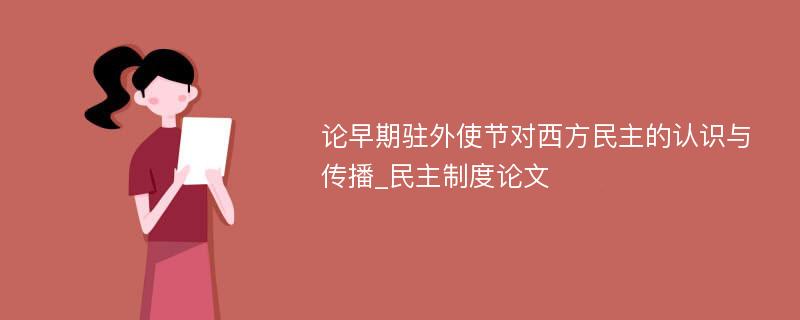
论早期驻外使节对西方民主政体的认识与传播,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使节论文,政体论文,民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54.3文章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667(2000)06—0066—07
互派常驻使节本是近代国与国交往中的正常现象。但是,1876年以前(尤其是鸦片战争前),清政府在处理中外关系时却坚持奉行所谓天朝体制,使中国成为一个世界,而不是世界的一部分;中外之间不存在对等性的外交关系。这种传统的外交体制是中国中心主义观念的产物,是封建社会内部尊卑等级观念在外交事务上的应用,它与建立在近代国际观念基础上的互派常驻使节制度格格不入。19世纪中叶后,清王朝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发生了急剧变化。在西方列强的炮火一次次无情地打击下,昔日天朝上国传统的朝贡制度已日趋瓦解,清政府不得不重新选择一种新的外交制度。历经艰难曲折,伴随着屈辱和痛苦,到19世纪70年代中叶,中外关系终于揭开了崭新的篇章:1877年1月, 清廷第一个驻外使馆在英国伦敦创设,郭嵩焘成为中国第一位驻外公使。从此,使节步出国门,联翩驻外,中国趔趔趄趄地走进国际大家庭中。
1895年以前,近代使节制度处于初步建立阶段,派出的使节数量较少,任职时间较长;驻外公使大多数为思想比较开明的洋务专家,对西方世界的了解比当时大部分官僚士大夫要多一些,但几乎无人受过正规的外语和国际法训练,仍然深受儒家学说的浸润;且驻外使节一般并非实官,只是一个临时差事。这些与甲午战后近代使节制度纵深发展阶段大不相同。这些早期驻外使节包括出使英、法、俄、德等欧洲国家的郭嵩焘、曾纪泽、刘瑞芬、薛福成、崇厚、洪钧、许景澄、龚照瑗、刘锡鸿、李凤苞,出使日本的何如璋、黎庶昌、徐承祖、李经方、汪凤藻、张斯桂(副使),出使美国、西班牙(当时称日斯巴尼亚,晚清文献中称其为“日国”)、秘鲁的陈兰彬、郑藻如、张荫桓、崔国因、杨儒、容闳(副使),共22人(署理公使及未成行者除外),出驻12个国家 [1](pp.3028~3038)。
作为较早走向世界的一批官僚士大夫,早期驻外使节这一群体的活动远远超越外交范畴,在晚清社会变革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本文试就早期使节对近代西方民主政体的认识和传播进行论述,彰显其功绩,凸现其特色,并可从中窥见近代中国政治民主化进程之艰难。
一
19世纪70年代中期至90年代中期,中国的政治体制依然是承袭了几千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而在西方,随着资本主义的形成与各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成功,以主权在民、天赋人权观念为主要理论基石,法制化、权力制衡为明显特征的资产阶级民主政体已经普遍建立起来了。
驻外使节亲历西土后,对西方国家的认识并未停留在其富强文明的表象上,他们对西方国家的体察已由感性认识阶段上升到理性思考阶段:在赞叹西方国家民富国强的同时,开始认真探索西方富强之本源究竟何在,这就开始涉及到西方的政治体制等更深层次的西方文明。
驻外使节这样综述世界政体大略:“地球万国内治之法不外三端,有君主之国,有民主之国,有君民共主之国。凡称皇帝者,皆有君主之全权于其国也,中国而外,有俄、德、奥、土、日本五国;巴西前亦称皇帝,而今改为民主矣。美洲各国及欧洲之瑞士与法国,皆民主之国也,其政权全在议院,而伯理玺天德(president,即总统)无权焉。 欧洲之英、荷、义、比、西、葡、丹、瑞典诸国,君民共主之国也,其政权亦在议院,大约民权十之七八,君权十之二三。”[2](p.586)
他们认识到,在西方民主政体的国家中——无论是“民主之国”还是“君民共主之国”,议院都享有崇高的地位,是国家政权的中枢,作用重大。正因如此,他们对作为西方民主政体重要标志的议会给予了特别的关注。
使节们时常被邀请或主动去参加议院旁听,与一些议员也时有往来,因此对于议院议事情形、章程有了一定的了解。1878年至1881年在职的首任驻美西秘公使陈兰彬对美国议院作了如下记载:“(美国)事权统归议院。上议院每邦二人,共计76人,下议院每邦多少视其大小,现计294员,皆由各邦民间公举,赴京办事。凡有举措,须询谋佥同, 间有异议, 则用其签名之多者,伯理玺天德特总其成而已。”[4](第十六册,第十二帙,陈兰彬:《使美纪略》)1886年至1889年任驻美西秘公使的张荫桓统计1886年美国各州及属地的土地面积、人口情况及各州推举议员的人数,总计“上议院议绅共84员,下议院议绅334员”[5](卷一,光绪十二年五月初五日记),并总结道:“总统之权,实则议院主之。总统奉行,无能准驳也。”[5](卷六, 光绪十四年四月初一日记)第四任驻美西秘公使崔国因对议院更为关注,总论西方各国议院章程:“欧墨洲各国均设议院而章程不同,美之议绅均由民举,不分上下也;英之下议绅由民举,而上议绅则由世爵,然权归于下议院,则政仍民主之也。欧洲除法国、瑞典、瑞士外,政皆君主,而仍视议绅之从违,则民权仍重。”[6](pp.996~997)对于美国议院情况,崔国因了解更多,他在日记中详细列举了参众两院议员年俸,美国各省总督(州长)年俸及各州举众议员人数等[6](p.65),可见关注程度之深。
使节们也注意到与议会相关联的政党制度、三权分立制度。
首任驻英法公使郭嵩焘谈到两党制度,谓专制政体“随声附和,并为一谈,则弊滋多。故二百年前即设为朝党、野党,使各以所见相持争胜,而因剂之以平”[3](p.389)。1890年至1894年任驻英法意比四国公使的薛福成对英法两国政党制度的记载比较详细:“英国有公、保两党。公党退,则保党之魁起为宰相;保党退,则公党之魁起为宰相。两党互为进退,而国政张弛之道以成。然其人性格稍静,其议论亦较持平,所以两党攻讦倾轧之风,尚不甚炽,而任事者亦稍能久于其位。”“法国左中右三党,而三党之中,所分小党甚多,又有君党、民党之别。其人皆负气好争,往往嚣然不靖。凡宰相所行之政,议院中是之者少,非之者多,则宰相必自告退,宰相退,而其所举之各部大臣莫不告退,由伯理玺天德另举一人为宰相,其被举者必先自审其党友之中可为各部尚书者若干人,若尚阙而不备,则必力辞不敢居位,而伯理玺天德又别举焉。”[2](pp.603~604)
黎庶昌将西方政党制与中国朋党之祸进行对比:“西洋朋党最甚,无论何国,其各部大臣及议院绅士,皆显然判为两党,相习成风,进则俱进,退则俱退而与国事无伤,与中国党祸绝异。”[7](p.426)
美国是三权分立制度最典型的国家,驻美公使张荫桓描述美国“政治分三门,一曰行法司,总统是也;一曰立法司,国会是也;一曰定法司,律政院是也”,并对这三个部门的构成、职能作了详细的介绍[5] (卷二,光绪十二年十一月二十日记)。崔国因这样记载:“美国开国之律,由华盛顿订定,政归三处,立例者,议院;行例者,总统;守例者,察院。议院有立例之权,则大事为议院主之,总统不过奉行耳。盖议绅总统皆由民举,而总统仅二人,不及议绅之数百人者,但能公而不能私,为民而不为己也,故事之创也,必由议院决之。”[6](pp.891~892)
我们可以看到,使节对议院、政党、君主、总统之间的制约关系的描述是大体准确的,表明使节对西方民主政体的概貌有了大概的了解,但他们把德、日等国归为与中国一样的“君主之国”,认为“民主之国”中总统无权,及其对议院权力的过分夸大,表明其对西方政体的内涵尚知之不详,察之不深。
在当时的西方社会,资产阶级民主政体主要有君主立宪制和共和制两大类。君主立宪制分议会制和二元制两种。议会制君主立宪制以英国为典型,君主不握有实权,行动受议会约束,政府只对议会负责。而二元制君主立宪制,是君主握有比较多的实权,其行动基本上不受议会约束,君主可以任命内阁成员,政府只对君主负责。1871~1918年的德意志帝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日本,就是二元制君主立宪制的国家。共和制则分议会制和总统制两种。议会制共和政体中,由选举产生的国家元首具有“虚位元首”的性质,本身没有独立的行动权力,政府对议会负责。而在总统制下,国家最高行政权掌握在由全国直接或间接选举产生的总统手中,政府对总统负责,总统的行政权受议会立法的制约,但并不受议会领导或对议会直接负责。美国是总统制共和政体的典型。
二
对于西方民主政体,驻外使节没有仅局限于简单的事实介绍,而是观照中国的政治状况,表示出或隐或显的赞美之情。
郭嵩焘对西方政治体制讨论极多。早在出使英国前,他就发现“西洋立国有本有末,其本在朝廷政教,其末在商贾,造船制器相辅以益其强,又末中之一节耳”[8](p.345),主张取法西方“强兵富国之术,尚学兴艺之方,与其所以通民情而立国本者”[8](p.348)。出使以后,加强了对西方政体的了解,类似内容的文字更多,如“西洋立国自有本末,诚得其道,则相辅以致富强,由此而保国千年可也;不得其道,其祸亦反是”[3](p.137)。他多次致函李鸿章,赞美西方风俗政教之美:“此间政教风俗,气象日新,推求其立国本末,其始君民争政,交相屠戮,大乱数十百年,至若尔日而后定,初非有至德善教累积之久也。百余年来,其官民相与讲求国政,白其君行之,蒸蒸日臻于上理,至今君主以贤明称,人心风俗,进而益善。”[9](p.188)郭嵩焘光绪三年十一月十八(1877年12月22日)在日记中,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更深入的探究,他追溯了英国从“君权”到“民权”的政治制度发展史,最后得出一段意味深长的结论:“推原其立国本末,所以持久而国势益张者,则在巴力门(即parliament)议政院有维持国是之义,设立买阿尔(mayor,市长)治民,有顺从民愿之情。二者相持, 是以君与民交相维系,迭盛迭衰,而立国千年终以不敝,人才学问相承以起,而皆有以自效,此其立国之本也。而巴力门君民争政,互相残杀,数百年久而后定,买阿尔独相安无事,亦可知为君者之欲易逞而难戢,而小民之情难拂而易安也。中国秦汉以来两千余年适得其反,能辨此者鲜矣。”[3] (p.373)这里,对西方民主政体的赞美,对中国专制体制的不满, 已经呼之欲出了。认识到西方国家立国有本有末后,郭嵩焘对洋务派仅从学习西方兵事和器械上用工夫、舍本逐末的作法提出批评。对李鸿章、沈葆桢、丁日昌三位洋务大员,郭嵩焘原来是很推崇的,称赞李鸿章办洋务“能见其大”,沈葆桢“能尽其实”,丁日昌“能致其精”,但对西国立国本末认识深切以后,他对三人也进行批评说:“合肥伯相及沈幼丹、丁禹生诸公专意考求富强之术,于本源处尚无讨论,是治末而忘其本,穷委而昧其源也;纵令所求之艺术能与洋人并驾齐驱,犹末也,况其相去尚不可以道里计乎!”[3](p.855)郭嵩焘在给李鸿章的信中强调:“要之,国家大计,必先立其本,其见为富强之效者,末也。本者何?纪纲法度、人心风俗是也。无其本而言富强,只益其损耗而已。”[9](p.240)郭嵩焘这种本末论的文字不胜枚举。总而言之,就是认为中国的变革仅从兵事、器械上考究是不够的,更应该注重政治制度、人心风俗等本源之处,而西方的各种创制多有可供参考之处,议院制度尤其值得借鉴。
1879年至1886年任驻英法俄公使的曾纪泽对西方议会制度也表示由衷的欣赏。他发现,“自法国改为民主之邦,国之事权皆归于上下议院”,总统“位虽尊崇,权反不如两院”[10](p.361)。在伦敦, 他致函丁日昌,对西方“政教之有绪,富强之有本”, 表示“艳羡之极”[10](p.171)。以顽固守旧著称的首任驻德公使刘锡鸿,在1877 年到英国各地访问并去议院听了几次演讲后,这样写道:“凡开会堂,官绅士庶各出所见,以议时政,辩论之久,常自昼达夜,自夜达旦,务适于理、当于事而后已。官政乖错,则舍之以从绅民。故其处事,恒力据上游,不稍假人以践踏。而举办一切,莫不上下同心,以善成之。盖合众论以择其长,斯美无不备;顺众志以行其令,斯力无不殚也。”[19](p.62)他不得不承认“合众论”、“顺众志”的议会民主制确有优越性。
虽然“民主之国”与“君民共主之国”都以议院为国家中枢,但使节们多对“君民共主”的君主立宪制表示好感。薛福成的观点颇具代表性。他评说君主制与民主制的利弊:“民主之国,其用人行政,可以集思广益,曲顺舆情,为君者不能以一人肆于民上,而纵其无等之欲;即其将相诸大臣,亦皆今日为官,明日即可为民,不敢有恃势陵人之意。此合于孟子‘民为贵’之说。政之所以公而溥也。然其弊在朋党角立,互相争胜,甚且各挟私见而不问国事之损益,其君若相或存五日京兆之心,不肯担荷重责,则权不一而志不齐矣。君主之国,主权甚重,操纵伸缩,择利而行,其柄在上,莫有能旁挠者。苟得贤圣之主,其功德岂有涯哉。然其弊在上重下轻,或役民如牛马,俾无安乐自得之趣,如俄国之政俗是也。而况舆情不通,公论不伸,一人之精神,不能贯通于通国,则诸务有堕怀于冥冥之中者矣。”既然民主、君主皆有利亦皆有弊,薛福成合乎逻辑地得出最后的结论:“夫君民共主,无君主、民主偏重之弊,最为斟酌得中。”[2](pp.605~606)
需要指出的是,对于西方民主政体,驻外使节多仅在日记、信函中进行议论,或隐或显地透露出赞美向往之情,但是多数人引而未发,未敢明确提出政体改革的主张。对西方民主政体多有研究的郭嵩焘,最多也只是向洋务首领李鸿章提出自己的主张,未以奏折的形式正式向皇帝进言。这是由特定的政治氛围和使节自身的地位造成的。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顽固守旧者大有人在,思想钳制严重,谈洋务已大受抨击,政治体制改革更是十分敏感的话题,属于大经大法的范畴,地位较高、颇具影响力的驻外使节不敢轻易触及这一时忌。首任公使郭嵩焘仅因在《使西纪程》中讲到西洋也有两千年文明、不能以夷狄视之等内容,就遭到书被毁版、人被罢官弃置的下场,而谈论政体问题显然更犯忌讳,使节们怎敢轻易置喙?为明哲保身起见,只得采取曲折隐晦的方式表达自己的主张,而不能象郑观应、王韬等在野知识分子那样撰文著述,明确表达自己的政治见解。这是驻外使节的一大遗憾。
值得一提的是,驻美西秘公使崔国因明确地向朝廷提出了开设议院的政治主张。崔国因是安徽太平人,字惠人,1871年中进士,1889年自翰林院侍读赏二品顶戴充出使美西秘大臣,1893年任满回国。早在1883年,崔国因就上奏折提出储才、兴利、练兵等十项自强之道,其中第九项就是“设议院”。他说:“议院之设,分为上下。其上议院由王公大臣议之,所以率作兴事,慎宪省成,知其大者远者也;下议院由各省民间公举之人议之,所以通幽达隐,补弊救偏,兴利除害,知其小者近者也”,在列强环伺的时局下,要让全国百姓心甘情愿地为国分忧效力,议院之设势在必行。崔国因主张议院更人换代,应以三年为期,使上议院无权重之弊,而下议院新举自民间,于民事知之甚悉,以免议院之设流于形式,真正达到沟通上下之情的目的。崔国因特别强调,开设议院是各项自强之道中最根本、最关键的一条,“议院设而后人才辈出,增饷增兵之制可以次第举行也”,“设议院者,所以因势利导,而为自强之关键也”[11](pp.22~23, 《奏为国体不立后患方深请鉴前车速筹布置恭折》)。这份奏折“理所应当”地遭致留中未发的命运。崔国因任驻外使节后,经过实地考察,对议院制度更加推崇,再次向朝廷提出开议院的请求,认为“泰西富强之政,不胜枚举,随时随事行之,但得其利而无其弊者,其枢纽全恃乎议院”[11](p.69,《条陈辛丑三月呈请大学士掌院代奏未行,为谨拟新政备资采择恭折》)。崔国因是近代中国向朝廷明确提出开设议院要求的第一人。
然而,驻外使节介绍西方议院制度,主张中国效法,主要是从议院可以通上下之情的角度立论的。郭嵩焘、曾纪泽、薛福成、李凤苞、崔国因等人无不如此。郭嵩焘多次谈到通民气民情为变革之先务,他将设议院视为通民情、去隔阂的最佳方式。曾纪泽对西方议院主政令“众心齐一”赞羡不已。薛福成表达得更清楚:“议院者,所以通君民之情也。凡议政事,以协民心为本,大约下议院之权,与上议院相维制;上下议院之权,与君权、相权相维制。”[2](p.603)李凤苞更是把“设上下议院”以“通民气”列为西国制治之要五大端之首,他说:“民居甚散,分位悬殊,通之匪易,乃由乡举里选,以设上下议院,遇事倡言无忌,凡纤悉不便于民者,必本至诚以设法妥帖之。又设卿大夫、里正等官以安闾阎。以审狱讼,用民治民,自无纷扰……俾一夫无不得所,则君公之分愈尊,而上下之情愈通矣。”[12](卷一○三,李凤苞:《巴黎答友人书》)崔国因向朝廷提出设议院,也是强调议院可以沟通上下之情。他说:“三代以上,君民之气相通,民好好之,民恶恶之,惟其通也;三代以下,上下之情日格,官不亲民,民不爱官,惟其隔也”[11] (p.69),而三代之所以上下之情相通,是因为“三代立政, 无议院之名,确有议院之实”,而“《虞书》载‘稽于众,舍己从人’,《大舜》‘乐取于人以为善’,《洪范》言‘谋及庶人’,《周礼》‘外朝询众庶’,凡此,皆议院之明征”[11](p.70)。
综上所述,我们会发现,驻外使节要仿效西方国家而在中国设立的议院,并不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三权分立中的立法机构,而是供皇帝咨询的“通下情”的机构;并不是君权的对立物,而是君权的维持和补充。在他们看来,尊君与重民并不相悖,尊君必须重民,重民是为了尊君,议院和君权可以相容。他们的思想理论基础,是中国传统民本思想而非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在他们的思想武库中,多见“民贵君轻”、“谋及庶人”等民本思想的阐述,而难觅天赋人权、社会契约论等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影踪。实际上,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与“主权在民”的西方民主理论差距极大,二者是不同质的政治范畴,不可同日而语。但使节多为科举正途出身,长久以来儒学的浸润已深入骨髓,受此知识背景和认知框架的制约,早期使节在认识和传播西方政体时,自觉或不自觉地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的一些概念和判断来阐释西方政体,这无疑大大影响了早期使节对西方民主政体本质的认识。这也是时代的局限。
甲午战争以前,先进的中国人对西方民主制度的认识尚处于起步阶段,以君主立宪制为参照、提出改革中国传统君主专制制度的构想者对西方民主的认识也大都停留在制度层面上,有的甚至在倡导君主立宪制的同时,激烈地否定自由、平等观念,维护三纲五常的封建礼教。与驻外使节同时代的郑观应、王韬、马建忠等被称为早期维新派的有识之士,在谈论议院时,也以通民情为言。在1875年基本写成的《易言》一书中,郑观应介绍了西方各国均在都城设有上下议政院,“凡有国事,先令下院议定,详达之上院,上院议定,奏闻国主”,“故泰西政事,举国咸知,所以通上下之情,其措施之善也”,提出“上效三代之遗风,下仿泰西之良法”[13](p.103), 比较明确地表达了仿效西法设立议院的主张。稍后,王韬也提出了类似主张。到19世纪80年代,特别是中法战争后,持这种言论的人更多了。郑观应在1893年刊行的《盛世危言》中响亮地呼喊出“欲张国势,莫要于得民心;欲得民心,莫要于通下情;欲通下情,莫要于设议院”的主张[13](p.314)。 马建忠谓:“重议院之权而民情可达。”[14](卷二,《巴黎答友人书》)陈炽强调议院可使“民气日舒,君威亦日振”[15](p.246, 陈炽:《庸书·议院》)。郑观应、王韬等人也将西方君主立宪制说成是“君民共主”,也以为这种制度“犹有中国三代以上之遗意焉”[16](p.26,《重民》下)。
由此可见,早期维新派对西方政体的认识水平与驻外使节不相上下。早期驻外使节中的薛福成,就被公认为是早期维新派的代表人物之一。虽然使节主观上倡导的是“君民共主”而不是“民主”,但已经包含有相当大的“民主”成分,实际上提出了变革中国传统君主专制制度的任务。在洋务运动“中体西用”的大背景下,这种对“中体”的侵犯,表明其思想中已涌动着突破洋务藩篱的潜流,为随后蔚然兴起的维新思潮开了先路。这是时代精神的表现,其进步性是不言而喻的。
三
虽然有这样那样的制约和遗憾,早期驻外使节对西方民主政体的认识对国内官僚士大夫阶层仍有着独特的影响力。
早期驻外使节品秩较高,薪俸优厚,经历独特,在当时是一个颇受官僚士大夫瞩目的群体。这个群体中,个人素质有高有低,但其对西方民主政体的体认却基本能达成共识——即棉美西方民主政体,希望中国有所仿效。这种群体性的共同认识对国内人士的震撼力是可以想见的。
使节的影响力主要通过以下两个途径实现的。
一是著述流传。总理衙门规定,出使各国大臣“应随时咨送日记一片,内称凡有关系交涉事件,及各国风土人情,该使臣皆当详细记载,随时咨报”[2](p.406)。早期使节多受过严格的传统教育,文化素养深厚,长于文字,他们亲历西方后,留下了大量的日记、奏折、信函、书牍等文稿,记述内容的深度和容量较之以前出洋者的记录普遍有所增加,反映了对外部世界认识的发展和深化。使节的出国载记为近代出国著述的代表作,得到士大夫阶层的普遍重视,影响至为深远。郭嵩焘的《使西纪程》、曾纪泽的《使西日记》、薛福成的《庸庵海外文编》及《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崔国因的《出使美日秘国日记》等,都是颇具影响力的载记。上述日记加上刘锡鸿的《英轺私记》、陈兰彬的《使美纪略》、李凤苞的《使德日记》等均被梁启超作为了解西方的佳作选入《西学书目表》。
二是通过对洋务大员的影响。早期驻外使节多与洋务大员颇有渊源:郭嵩焘与李鸿章为同科进士、至交好友,与沈葆桢、丁日昌等关系也不错,又是曾国藩、左宗棠的儿女亲家;曾纪泽是曾国藩的长子,与李鸿章等大员关系非同一般;薛福成为曾国藩、李鸿章幕府中上佐之才,李鸿章对他几乎言听计从;许景澄与张之洞关系密切,张之洞是许景澄的“座师”[17](p.1016);陈兰彬曾入曾国藩幕府;黎庶昌为“曾门四弟子”之一;郑藻如、陈兰彬、龚照瑗、刘瑞芬都在李鸿章创办的江南制造总局中任过总办或会办;张荫桓出使美西秘前,特地“到津晤李傅相,筹商一切”[5](卷一,光绪十一年十月廿四日记);崔国因、 龚照瑗与李鸿章为姻亲[18](p.168.p.170)。使节出洋, 多经由洋务大员推荐,驻外期间,与国内洋务大员多有联系,互通声气,洋务人员的思想程度不同地受到驻外使节的影响,进而影响到整个官僚士大夫阶层甚至更广泛的领域,这是传教士与在野知识分子都无法相比的。
此外,早期使节对西方民主政体的认识和传播,在近代中国政治思想史上具有更直接的启蒙意义。使节出洋之前,近代中国人对西方政治制度的了解,主要来自三种人的著述:一种人是传教士;一种人是国内的有识之士,如林则徐、魏源、徐继畲等;另一种人是走出国门的中国人,如斌椿、张德彝、孙家谷、志刚等。传教士著译书籍、在报刊上发表文章,比较客观地传播了议会制度、民主思想等内容,虽对中国思想界有一定的启蒙作用,但他们对中国传统的专制制度无深刻地了解,不能将西方的民主与中国的专制联系起来,显得缺乏针对性。林则徐等人编译的书籍如《四洲志》、《海国图志》、《瀛寰志略》等,因多来自翻译,而且其本人未步出国门,对西方政体无亲身体察,故有内容疏略、文字艰涩、甚至辞不达意等不足。斌椿等人虽有机会亲历西土,但囿于识见和身份,其对西方政体的记述有走马观花之弊,缺乏深度,流于简单。与这三类人相比,早期使节亲历西洋,对西方政体进行了近距离观察,有感性认识;其特殊身份和见识又是斌椿等人无法相比的,故使节对西方民主政体的描述无论就准确性还是系统性而言,都更胜一筹。驻外使节熟悉中国政情,在介绍西方政体的过程中,自觉地进行中西对比,比起传教士的宣传更真切可信,更富有针对性,因此具有更直接的启蒙意义。
早期驻外使节之所以能对西方民主政体的认识和传播作出贡献,完全得益于他们独特的身份及走向世界、实地考察西方社会的经历。“百闻不如一见”是一个既浅显又深刻的道理。走向世界与更新思想之间存在着必然的联系。走出国门,是使节思想产生飞跃的外在条件。使节对西方民主政体的认识和传播,就是这种飞跃的主要表现。在近代国际性开放的大趋势下,中国要变革求新,就不能不走向世界以汲取养分,这是时代潮流推动下的必然趋势,也是早期使节赋予人们的一个有益的启迪。
标签:民主制度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君主制度论文; 议会改革论文; 历史论文; 李鸿章论文; 郭嵩焘论文; 薛福成论文; 陈兰彬论文; 洋务运动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