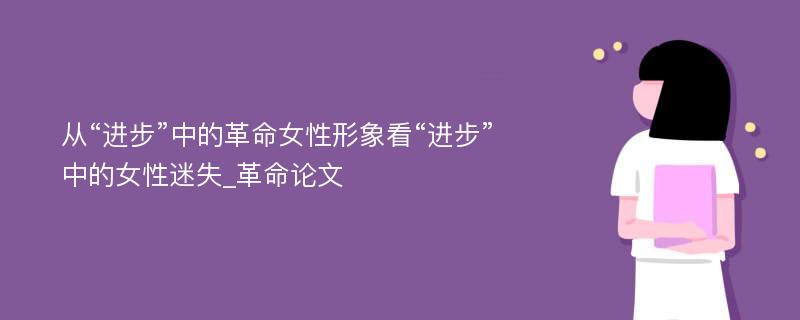
被“进步”迷失的女性——从随笔中的革命女性形象谈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女性论文,随笔论文,形象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240(2003)04-0113-04
革命女性是现当代中国史上一个很值得注意的历史现象,分析这一历史现象既是剖析现当代中国史的重要切口,又有利于加深我们对“女性解放”这一课题的认识。然而目前关于革命女性的学术研究性文章并不多见。
笔者拟以近年来公开发表的几篇随笔中的革命女性形象为例,来分析革命女性的特点、产生这些特点的社会因素,并试图对革命女性的评价问题谈一点自己的看法。限于篇幅,本文所探讨的革命女性主要是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中,无限信仰“革命”、狂热追求政治“进步”的各阶层妇女。
一、随笔中的革命女性形象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对整个国家和社会进行了全面、彻底的整顿,妇女也获得了“半边天”的美誉,普遍地走出家庭,投入社会。她们兴奋地以为自己得到了解放,拥有了前所未有的追求“进步”的机会,于是她们中的很多人竭尽所能地为政治“进步”而努力,而狂迷。胡平的《不再是秦兵马俑的脸》、舵儿的《自杀研究》、李南央的《我有这样一个母亲》中的“母亲”可以说都是这类被“进步”迷失的革命女性的缩影,刘乃元的《遭遇革命大学》也从侧面对革命女性形象进行了勾划。
在胡平的《不再是秦兵马俑的脸》中,很早就失去父母、只读完初中的“母亲”以为,嫁给身为大学教授的“父亲”“就等于上了一份温暖的保险箱”[1],然而“父亲”出乎意料地于1958年春反右派运动已近尾声时被打成了“右派分子”。向往“党温暖的怀抱”[2]的“母亲”接受不了“父亲”被中国共产党唾弃的现实,急急地抛家离子,要与丈夫划清界限,并提出离婚。她以为这样便可以获得“组织”的信任,得到政治“进步”的认可,早一天被“党温暖的怀抱”所接纳。不料,母亲尚在接受“组织”考验时,就因长途跋涉中暑而死。
和胡平文中的“母亲”相比,舵儿《自杀研究》中的“母亲”更具悲剧色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从小要强、年轻时在海外侨界小有名气的“母亲”虽然婚姻和事业都不如意,但却“越来越‘革命’了起来,发誓要彻底洗尽身上的‘资产阶级淤泥腐水’”,而且“脑子里什么都不想了,只有一个心思,就是‘入党’”,“除此之外,她不知道人生还有别的什么价值。丈夫不必说了,需要的话,家庭、子女、亲友乃至她的生命,什么她都可以在所不惜地献给党。”[2]文革中,母亲被逮捕关押,受尽折磨,但她处处不忘追求“进步”,不仅向牢友宣传毛泽东革命路线的伟大,讲述旧社会的黑暗,而且为了不给党和国家添麻烦,生了病拒绝吃药。六年的狱中生活结束后,“母亲”对政治“进步”的追求更加狂热,坚信只有四人帮才是真正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文革结束不久,“家里系里,大大小小的矛盾、冲突、精神折磨,世界沧桑巨变,偶像的倒台”等等,“使母亲这样绝对刚强的人也终于精神崩溃”[2],以至自杀而死。
如果说胡平和舵儿文中的“母亲”还只是一般地醉心于“革命”的女性的话,那么李南央等下的“母亲”则算是彻头彻尾的革命女性了。“母亲”从十六、七岁起就投身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学生运动,后来又奔赴延安,经历过延安整风的磨炼。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母亲作为南下干部“任接收长沙自来水公司的军代表,后调北京任石景山发电厂的副厂长。再以后就一直在航空工业部工作。”[3]有着曾学习于延安马列学院这一自觉“比人高出一头的资本”[3]的母亲,坚信“亲不亲,阶级分”,大义灭亲,为了表示自己坚定的革命立场而以子虚乌有的罪名状告亲兄弟;不许成分不好的婆婆进家门;丈夫因为所谓的右倾思想被隔离审查后,她立刻站出来毫不留情地揭发丈夫的“反动”言行;文革中领着孩子对着毛泽东像早请示、晚汇报;指斥女儿日记中提到的“母爱”是资产阶级情调;文革结束后,“她就像埋在地窖里的陈年老酒,年代越久,‘革命’的味道越‘醇厚’”[3]……曾经年轻、漂亮又有才华的“母亲”到老年众叛亲离,心中充满的只有刻骨的恨和极度的不平衡。
刘乃元《遭遇革命大学》中负责女生工作的女干部“老潘”虽然年龄只有三十几岁,但“不停地吸烟,牙齿黄得可怕,看来没有刷牙的习惯”[4],头发蓬乱,腰间常系一根草绳……
三位“母亲”家庭出身不同,人生经历各异,但建国后的表现却出奇地相似:她们都是母亲,都深深地爱着孩子,充满着对正常生活的向往,但是她们把过上美好生活的希望寄托在对政治“进步”的追求上。这本无可厚非,可惜的是她们已经完全被所谓的“进步”、革命所迷失,不敢也不再独立思考,不顾一切地只求靠近中国共产党的怀抱、不被抛弃,正常的人情味在她们眼里只不过是资产阶级情调而已,只有革命是至高的,立场是最重要的。“老潘”则是以一种被认为是“世界上最难看的动物之一种”的仪表来表示自己的革命坚定性。
用我们今天的眼光来看,这四位革命女性最明显的特征不是性别,而是进步性、革命性。而“所谓革命,就是高度政治化,‘政治是统帅、是灵魂’,与政治上的正确性相比,其它一切都不重要。”[5]
这几位在当时看来具有一定文化水平的女性为什么会如此不顾一切地迷恋革命与“进步”呢?应该说这是有一定的社会因素的。
二、革命女性极端革命性特点形成的社会因素
1.革命女性的极端革命性是“五·四”以来女性“走出家庭”的意识在建国后的畸形发展。
“五·四”以来,中国女性追求自我解放的意识迅速地萌醒,“走出家庭”投入社会成为女性展示独立姿态的一种普遍方式。二十世纪上半叶,无数的女性从传统家庭中走了出来,她们或是为了摆脱封建婚姻,或是为了展示独立自尊的心性,或是……她们的经历是曲折的,但是她们勇敢的、叛逆的行为让传统的、没有走出家庭的女性钦羡不已。作为正常人,哪一个女性不愿挺直腰杆、自由自主地在人生走一遭?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运用政权的力量使广大妇女普遍地走出家庭,习惯了低眉顺眼的广大女性获得了“半边天”的美誉。史无前例的扬眉吐气之感极大地激发了女性走出家庭、投入社会的热情。自然,她们也对使她们“翻身做主人”的中国共产党充满了感激之情和由感激而生出的无限信任:她们诚挚地愿意跟中国共产党走,中国共产党指向哪里她们都愿意回报以热烈的响应。
一般的女性尚且如此,比较要强的女性更是有强烈的走出家庭、紧跟中国共产党的意识。然而什么是走出家庭呢,她们大多没有清醒的认识,只是把所有的希望寄托于中国共产党。对于刚刚建立起新政权的中国共产党来说,建设国家、医治多年的战争创伤是当务之急,于是它把妇女解放置于国家建设和社会革命的大目标之下,号召妇女积极投入到国家建设的大潮中,在政治上和经济上、思想上都服从建设和革命的大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中国共产党对整个国家和社会进行全面整顿,妇女作为社会的分子被动员起来加入其中。比如在“三反”“五反”运动、三大改造运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乃至文化大革命运动中都有广大的女性参与,不仅有青壮年妇女,而且有中老年妇女,她们大多直接站在运动的第一线。以农业合作化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为例,农村的成年妇女除了实在不能从事劳动者之外,几乎无一例外地加入其中,按照体力的不同从事不同的劳动。城市妇女在历次运动中也被要求完全投入。在当时的氛围中,女性只有积极投入社会运动才被认为能跟上时代的步伐。否则会被认为落伍、保守。不甘心落后的女性自然会面临两难境地:一方面要和男性承担同样的政治和生产任务,一面又必须照顾好多子女的家庭。传统贤妻良母的角色再加上进步的新女性的现代角色使得她们不堪重负,只好把重心放在家庭和社会两者之一上。在当时,一些心性要强的城市女性大多数选择了社会,因为这表明自己不同于以往围着锅台转的传统女性,表明自己是新时代的新女性。
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在全国人民的心目中很有威望。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能接近中国共产党是无尚光荣的,加入中国共产党自然更是求之不得的。入党是一个人事业成功的重要指标之一,和党的言论高度一致是时代的要求。新女性们唯恐自己落后于时代,自然就把政治“进步”看作生命中至高无上的目标,竭尽所能地要投入党的怀抱,家庭、人情等都必须服从于政治这一最高目标。
2.革命女性的极端革命性是各种宣传媒体不断催化的结果,是当时整个国家和社会高度政治化的缩影。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电影、报刊、喇叭等宣传媒体所塑造和宣扬的正面女性形象非常突出革命性。以当时的文艺作品为例,无论是女英雄、革命母亲、知识女性还是新农村妇女都有极强的革命性,形象非常高大。比如歌剧《洪湖赤卫队》中的韩英面对敌人的威胁高唱:“为革命,砍头只当风吹帽,为革命,洒尽热血心欢畅!”[6];李英儒《野火春风斗古城》中的杨晓东母亲为了革命在敌人的威逼面前以死抗争;电影《青春之歌》中的林道静在丈夫和革命之中毅然选择了革命的滚滚洪流;电影《李双双》里塑造的李双双本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传统农村女性,17岁就出嫁,成天忙于生儿育女和其它家务琐事,然而随着农村合作化运动的发展,爽快、勤劳的李双双大胆地走出家庭,响应中国共产党和国家的号召,投入集体劳动中,成长为一个热爱集体、敢于同旧习惯作斗争的新女性,为农业和农村的发展而努力。……相对于这些“进步”的、革命的形象,看重个人和小家庭的生活被视为落后和令人唾弃的行为。
党的重要喉舌《人民日报》建国后在树立革命女性形象、宣传“进步”意识方面也起了很大作用。它所塑造的“进步”女性典型形象不论是哪一个历史阶段的,都无一例外地坚决响应党的号召:中国共产党需要我们做什么,我们就义无反顾地去做什么。比如抗美援朝期间国家掀起增产节约运动,就有细纱工人模范郝建秀小组;学习苏联“老大哥”时期有苏联经验指导下的模范调度员孙孝菊[7];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有一批投身于国家建设的女典型[8];反右派运动中有热爱新社会、斗争意识强的优秀共青团员田蒂[9]和“革命妈妈施小妹”[10];大跃进时期更是树立了一大批跃进的女典型[11]……
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大量地进行革命宣传和阶级教育,各种媒体充斥着浓厚的政治化气氛,普遍标榜“把一切献给党”、站稳阶级立场、提高阶级觉悟之类的观念,而且大加渲染。比如在50年代社会的阶级气氛相对缓和时期,《人民日报》就经常出现与《为党贡献自己的一切力量》[12]、《永远作毛主席的一个忠实战士》[13]、《不许丈夫走资本主义道路》[14]、《站稳立场,划清界限》[15]相类似的文章标题,涉及到相关内容的文章之多也是可以想象的。60年代和70年代此类的宣传更是铺天盖地,随处可见。
各种媒体的反复宣扬,使女性普遍认同这样一种价值观:女性只有投身于革命的洪流中才是时髦的、进步的。这样一种价值观本无可厚非,但是当时各种媒体几乎是反反复复地如此宣传,甚至不仅是提倡,而且把这样一种价值观提到是否爱党爱国家爱人民的高度,而把与此种价值观不同的其它价值观贬低到反党反人民的层次。过分的渲染极易激起人们的极端行为。在中国,城市女性总是比农村妇女有更多的条件和机会追求时代性,她们往往也更容易激进。于是,有机会表现“进步”的女性无不抓紧一切时机狂热地追求“进步”,渴望革命。她们的热情估计不会次于21世纪初的城市中上层女性对“减肥”之类的时髦的追赶。广大的农村女性和城市下层女性为生计所迫,也为文化水平所限,革命和“进步”在他们的生活里只能是奢侈品,可望而不可及。因此,一些城市中上层女性自然成了女性追求“进步”的先锋。
3.极端革命性是女性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近三十年紧张的政治气氛中形成的自我保护的方法,是对恐惧的一种本能反应。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近三十年中,大大小小的运动连续不断,涉及到社会的各个层面。在极左思想的影响下,一次次的运动对人们思想的钳制越来越严厉,不仅党外人士人人自危,连党内人士也不得不谨小慎微。在运动中,一个人一旦成为运动对象,不仅自己要经受群众斗争的疾风暴雨,而且会牵连到亲属,从而遭受物质和精神的双重折磨。在这种紧张的政治气氛中,恐惧是难免的。面对恐惧,人们会本能地寻求自我保护。历次政治斗争的经验使得很多人懂得紧靠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保持高度一致才是相对安全的。因此,党外人士急切地想要加入中国共产党,仿佛入了党就进了政治保险箱;党内人士极力地紧追中国共产党的步伐,唯恐有所闪失而失去党的信任。
更何况,一个人的政治条件无论对自己的正常生活、提升,还是对家人及子女的“前途”都是至关重要的,大到提职、小到孩子的升学都必须过“政审”关,而政审的内容主要是家庭出身、父母亲属乃至自己的政治身份、政治表现等。出身不由己,政治条件却是可以通过自己的表现来换取的。既然如此,谁不愿意表现得革命一些、“进步”一些,以为自己或亲人(至少是孩子)的前途尽自己所能呢?
在社会上处于强势的男性如此,相对处于弱势的女性寻求自我保护的欲望自然更加强烈。她们的过分忧虑乃至恐惧使得她们在入党、革命等方面极易表现出极端化的倾向。
总之,正如男性是社会造就的一样,女性也是一定的社会环境造就的。革命女性是特定时代的产物,作为一种即将成为历史的现象,我们对待她们的理性态度是理解和反思,而不是一味地嘲讽和蔑视。
收稿日期:2003-05-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