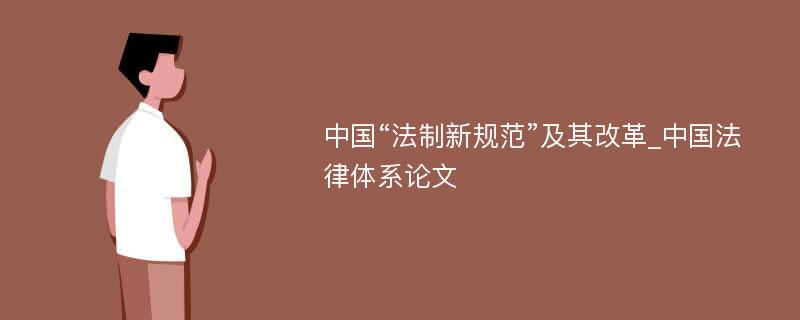
中国“法制新常态”及其改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常态论文,中国论文,法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2014年10月,中国共产党十八届四中全会在北京召开,首次将法治建设列为执政党的最高代议机构——中共中央委员会——的专门议事主题,并在会后发布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下文简称《依法治国重大决定》)。至此,至少在意识形态层面,法治中国建设成了朝野的共识。在理论上,现代社会中的法治建设的重要性自不待言。①在当下中国的具体语境而言,建设法治中国,可以让全体中国人对国家的未来更有安全感,中国公民之间彼此可以更加信赖,华夏儿女对民族自我可以更加认同。简言之,法治兴,则中国兴。② 但是,即便法治中国建设的重要性似是一个常识,关于法治的朝野共识形成也历经了挫折。1997年的中共十五大和2013年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可谓是中国法治建设的两个重要分水岭。中共十五大提出了“依法治国”,在意识形态层面初步认可了法治在中国政治生活中的地位。但是,即便如此,在此后的十多年,法治建设还是经历了“走两步、退一步”的历程。③其中的曲折,不仅有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争议搁置,也有操作路径中的试错失误。2013年,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是一个新的分水岭。该会之后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下文简称《全面深化改革重大决定》)指出,当下改革重点任务之一是建设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三位一体”的法治中国。2014年10月,《依法治国重大决定》进一步对法治中国建设的问题与任务做了全面阐释,并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体系”,视之为国家治理体系的核心要素,至少在意识形态层面对法治进行了正名。至此,关于是否需要法治已经不再是主要问题。毋宁,如何推进法治的路径问题更加明显地凸显出来。 在本文中,笔者试图对当下制约法治中国建设的制度因素作一个简单的梳理,指出中国走向法治的困境,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下一步推进法治的思路与可能路径。第一部分将简要梳理中国法治建设目前所面临的问题和取得的成就,并说明问题和成就背后的共同制度根源。接着,笔者会在文章的第二部分把目前中国法律体系运作的状态归纳为“法制新常态”及其带来的改革僵局,并在第三部分探讨如何在“法制新常态”的困局中深化法治中国建设的思路与路径。最后是简要的结论。 二、中国法治问题的两面性及其制度根源 人们对于中国当前法治建设进程中的诸多问题已经有了广泛认识,这些问题不仅仅为学者和专家所熟悉,也为执政党的高层所认可。在《依法治国重大决定》中,中共中央对目前法治建设所面临的问题进行了全面的描述:“有的法律法规未能全面反映客观规律和人民意愿,针对性、可操作性不强,立法工作中部门化倾向、争权诿责现象较为突出;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现象比较严重,执法体制权责脱节、多头执法、选择性执法现象仍然存在,执法司法不规范、不严格、不透明、不文明现象较为突出,群众对执法司法不公和腐败问题反映强烈;部分社会成员尊法信法守法用法、依法维权意识不强,一些国家工作人员特别是领导干部依法办事观念不强、能力不足,知法犯法、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现象依然存在。这些问题,违背社会主义法治原则,损害人民群众利益,妨碍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必须下大气力加以解决。”这些问题涉及执政、立法、行政、司法与守法五个领域。应该说,该决定对问题的描述是非常深刻的,也是非常坦诚的。 然而,即便学者、专家和决策者对当下法治建设的问题有全面的了解,还是在有意无意间忽视了这些问题的两面性。一方面,毫无疑问,《依法治国重大决定》所罗列的上述现象的确是问题,也是值得在未来的改革中一一解决的。不过,这些问题的形成与存在还有另一方面,即在一定程度上,它们是目前中国法律体系的必然组成部分,它们与中国法治建设所取得的重大成就是“一块硬币的两面”。 自1978年至今,尽管中国的法律体系还存在诸多问题,但是法律改革所取得的成就毋庸置疑。在2011年年初,当时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做了一个专题报告,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④中国政府随后发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白皮书提到:“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的立法工作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截至2011年8月底,中国已制定现行宪法和有效法律共240部、行政法规706部、地方性法规8600多部,涵盖社会关系各个方面的法律部门已经齐全,各个法律部门中基本的、主要的法律已经制定,相应的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比较完备,法律体系内部总体做到科学和谐统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⑤不仅仅在立法层面,在颇令社会各界质疑的司法运作方面,其成就也相当突出。⑥至今,虽然不能说中国已经成为法治(rule of law)国家,但是相比三十多年前,已经向法治社会大大地迈进了一步,初步实现了从法律虚无盛行的社会到法制(rule by law)社会的伟大转型。 那么,为什么说《依法治国重大决定》所罗列的问题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白皮书所列举的成绩是一块硬币的两面?在笔者看来,上述问题和成就根源于相同的制度根源,是1978年以来中国实行的“圈自留地式改革”的必然产物。这种改革逻辑的核心是,尽可能明确个人、组织与机构的权利(力)与义务(责任)边界,通过市场竞争或者准市场竞争的机制来实现优胜劣汰,通过利益激励来让个人、组织和机构做事情——激励他们做对个人与社会有积极意义的事情。 在经济领域,上述改革逻辑的实施和绩效是有目共睹的:从早先的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乡镇企业、大中城市(未尽的)国企改革和蓬勃发展的民营企业,遵循的都是这个逻辑。在有了私有产权或者准私有产权之后,人们通过努力工作来获得属于自己的回报。用在20世纪80年代一句流行的话说,“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中国经济目前取得的成就说明,中国的改革是个伟大的转型。⑦ 在政治领域,改革也遵循了同样的逻辑。在“块块”上,改革之前,中国政治体制的一个根本性问题是,地方政府不受“财政硬约束”。⑧在这种体制之下,地方政府干好干坏一个样:干好了上缴中央政府,干坏了则由中央政府提供财政转移支付来补贴。而20世纪80年代的中央分权改革及“财政硬约束”的实施,其目的是让地方政府及其官员一方面拥有更多在经济事务中的主动决策权,在另一方面让他们对自己的决策承担更多的责任,并且通过组织人事来奖优罚劣。这就是政治体制内部的“锦标赛模式”。⑨在“条条”上,情况有所异同。不同点是,作为“条条”的行政机关所提供的公共产品天然具有独特性,而作为“块块”的地方政府所提供的公共产品则具有雷同性。因此,“条”与“条”之间不好开展充分竞争,而“块”与“块”之间可以开展锦标赛。但是,即便如此,对于“条条”上的干部任免,执政党高层仍然是遵循“有为才有位”的逻辑:对于干得好的部委负责人给予升迁奖励,干得不好的则靠边站。在一定程度上,以部委为代表的“条条”机构之间也有一定的“锦标赛”。 自1978年以来,中国的法律发展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上述以利益激励与竞争为核心的改革逻辑。⑩执政党高层设定了追求经济发展的执政目标,并通过其掌控的人事任免权对那些能够推动经济发展的官员给予政治奖励;为了获得这种政治奖励,“条条”和“块块”的主要决策者同样通过人事任免权的杠杆,激励自己管辖权限范围内各级官员,通过各种手段来直接或者间接达到上述目标。其中,推动各项工作的“法制化”是达成上述目标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上述改革逻辑的作用之下,首先出现的是“立法”的爆炸式发展。无论是地方政府还是中央部委以及在两者指挥之下的地方厅局委办等机构,纷纷通过立法或者制订规范性文件的方式来刺激本管辖领域内的经济活动。这种爆炸式的“立法”不是来自中央政府——或者更确切地说“党中央、国务院”——的具体授意,而是在上述“锦标赛体制”指挥棒之下的政府官员自觉活动。其次,在行政领域,由于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转型,行政机关在新陈代谢的同时,一边扩张自身的行政权力,一边在被动中约束自己。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众多行政机构潮起潮落,几经兴衰。但是,无论是哪个机构以什么样的名头来执法,都具有两个共同特点:(1)每个权力机构一旦产生和存在,便在上述激励机制的作用之下,倾向不断地明确、巩固甚至膨胀自身的权力;(2)中国市场与社会的伟大转型,在一定程度上需要这些权力机构不断地采取各种方式去干预市场和社会生活。前者是权力行使的供给,后者是权力行使的需求。在这两者结合之下,以明确行政权力为核心的部门立法与以规范部门内权力运作的规范性文件也大量地喷发。当然,行政机关在扩张权力的同时,也遭到了“兄弟部门”的局部抵制以及不胜其烦的社会和市场主体的反抗。在上述多重利益主体的多重博弈之下,行政机关在权力扩张的同时,也在被动地规范自身权力的运作。经过三十多年的如此发展,如今,中国公民举目张望,随处可见名目众多又相对规范化的行政权力对社会与经济生活的干预。最后,在司法领域,在“市场经济就是法治经济”以及“为经济建设保驾护航”的意识形态保护之下,司法部门(检察院和法院系统)抓住了历史的机遇,也在快速扩张自身的同时尽可能专业化,以凸显司法工作与其他党政工作的差异性。在这个指导方针之下,司法系统自身进行了系统升级,尽管目前还面临很多问题,但还是取得了非常突出的成就。(11) 当然,就像市场会失灵一样,上述以明确权力为前提,通过市场或者准市场机制来激发人们做事热情的改革逻辑,同样会产生一系列的问题。这些问题的核心是,公权力毕竟是公权力,不能被圈为“自留地”。一旦公权力被视为“自留地”之后,难免会出现两个消极的结果:其一,公权力机构利用手中的权力去为个人或者部门谋取私利;其二,在需要承担责任之时,畏缩不前。在政治领域,上述“块块”之间进行的锦标赛,其显著负面后果之一是严重的地方保护主义,(12)而上述“条条”之间进行的竞争,其显著的负面后果之一是公权力执行的“碎片化”。(13) 在法律领域,公权力私用的负面后果也是非常明显的,其核心问题是导致法律制度的“自利性”,并在立法、执法和司法过程中都有显著体现。在立法和规范性文件制定领域,权力机构习惯性地以“立法者”的身份来界定自身的权力,并且在政治、经济与社会生活中经常性出现过度规范化的问题。在执法领域,行政机关不仅努力通过立法通道来获取授权、权力自设和权力攫取,还经常性地选择性执法——对自己有利的执法则时时出现在第一线,对于自己不利的执法则畏缩不前、推卸责任。在司法领域,整个司法体系在专业化的同时越来越明哲保身——尤其是,在会得罪其他权力部门的案件上,经常性地拒绝受理案件或者糊涂司法;并且,在微观的司法过程中,司法人员越来越机械地适用法律规则,尽可能规避额外的解释法律工作。同时,由于公权力机构在法律制定、执行与司法过程中的自利性与选择性,使理性的中国公民在遵守法律过程中也明显地采用了实用的工具主义立场——对自己有利的场合便会搬出法律武器,对自己不利的场合对法律也是不闻不问。(14) 简言之,1978年以来以利益激励与竞争为核心的改革逻辑是当代中国法律变革的制度根源,并造就了当前中国法律体系运行的两面性:权利(力)的私化,促成了法律体系的快速成长;权利(力)的私化,也促成了法律体系的内在不和谐。 三、“法制新常态”及其面向 上述1978年以来的改革逻辑不仅造就了中国目前法律体系运作的两面性,而且事实上把中国的法治建设带入一种新的改革僵局。也就是说,包括执政党中央在内的各个方面都意识到了问题所在,并试图改善这种状态但是又无法轻易改变它。为了给这种中国法律体系运作的现状取一个“响亮”的名头,笔者在此处借用一个时髦的词语“新常态”,把它命名为中国的“法制新常态”——不过,对于这个命名,笔者保持开放态度,一旦找到更合适的词汇,便立时替代它,以免东施效颦之弊。 “新常态”(new normal)是2014年的中国媒体用得非常频繁的一个词汇。在当代的学术语境中,它最初由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PIMCO)在内部研究报告中提出,并由时任该公司首席执行官的穆罕默德·埃尔·埃里安(Mohamed A.El-Erian)在2010年的一次演讲中公开倡导。埃尔·埃里安及其研究团队用“新常态”来描绘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经济所面临的状态,指的是发达国家在金融危机之前经济领域发生了一系列结构性变化,量变导致质变,使金融危机之后的经济结构同之前完全不一样,并因结构性的改变而不可能轻易回到过去的一种状态。(15)中国的媒体与经济学者在该词流行之初便已经关注到了它。(16)更值得关注的是,在2014年5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河南考察时首次公开用了“新常态”这个词来描绘中国当前经济发展所处的状态,并在之后的不同场合也用过这个词。此后,“新常态”被中国的媒体和经济学者频频用来归纳中国的经济新状态。(17) 尽管“新常态”说的是当今世界经济领域的发展动态,但笔者认为,该词也能比较形象地描绘中国当前法律体系运行——同之前相比的——一种新状态。它能帮助我们理解由于上述改革逻辑所造成的当前中国法律体系的一些面相。 首先,诚如上文所述,当前的中国法律体系成绩与问题共存,因此显然不是一种理想的法治状态,也明显不是之前的法律虚无社会,而最接近我们常说的“法制”社会。美国法理学者塔玛纳哈(Brian Z.Tamanaha)把法治分为“形式法治”和“实质法治”。其中,形式法治强调法律的形式合理性,有三种形式,包括以法治国、形式合法性和民主+合法性。实质法治强调法律的价值合理性,也有三种形式,包括个人权利、尊严和/或公正和社会福利。(18)套用塔玛纳哈的理论框架,目前中国法律体系勉强能够达到以法治国和形式合法性的“形式法治”,是我们所说的法制国家状态。 其次,在宏观层面,中国目前法律体系的形成与变化受国家、市场和社会等因素互动所形成的结构性制约。(19)在当下的中国法治建设语境中,国家、市场和社会都是相对独立的力量,国家既不能包含市场与社会,反之亦然。同时,经过多年的改革发展,法律体系也相对成形,尽管不具有同前三者相匹配的能量,但也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国家、市场、社会与法律体系这四种力量中,两两之间存在利害关系,因此相互之间存在直接的互动,并彼此影响。其中,任何两个力量的互动又间接受制于它们同其他力量的互动。特别地,法律体系同国家、市场和社会的任何一方直接互动,都受制于它同另外两个力量的互动以及后三者之间的互动。由于上述直接和间接的互动关系,使国家对于法律体系的干预受制于它对市场转型和社会现代化的态度,因此会形成“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效应。这就是我们称其为“结构性”制约的根本原因。在结构性制约中,法律体系主体的互动交往是多次重复的,相关的利益博弈是比较充分的。 最后,从理论上看,中国的“法制新常态”是一种制度非均衡,处于不稳定的发展状态,但在实际中,主要的利益相关方又无意或者无力改变这种制度非均衡,因而陷入一种改革僵局。根据制度经济学者的定义,“所谓制度均衡就是人们对既定制度安排和制度结构的一种满足状态或者满意状态,因为无意也无力改变现行制度”;同时,“制度非均衡就是人们对现存制度的一种不满意或不满足,意欲改变而又尚未改变的状态”。(20) 如同前述,中国目前法律体系存在诸多问题,显然不是一种理想的制度均衡。这意味着,在中国,关于法治的制度需求与现存的制度供给并不一致。从长远来看,法治给中国社会带来的整体制度福利一定比现在的法制社会更好。执政党中央也看到了这一点,因此才有了从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国”到十八届四中全会升级到“全面深化依法治国”的整体改革蓝图。 然而,问题在于,尽管存在一幅改革蓝图,看起来可以大体上满足中国公民对法治的制度需求,但是法治建设的具体制度供给却不是由执政党中央直接落实的,而是由下面的公权力机构来“操盘”的。也就是说,在当前的法治建设中,执政党中央是制度供给的“总发包方”,而其领导下的公权力机构属于制度供给的代理人。并且,从中央到地方,还存在多层次的代理人。尽管“总发包方”的初始想法比较接近中国公民对法治中国的诉求,但是当“总发包方”把制度建设的工作委托给代理人时,一定存在代理成本,并且代理层次越多,代理成本越高。且不论,法治建设的目标是直接或者间接改造现存法律体系中对各类、各级代理人有利的自利性制度。作为执政党中央委托进行法治建设的各级公权力机构,一定会想方设法在法治建设的“施工”过程塞进各种私活,以最大限度地保留自己的利益。 同时,在理论上,作为法治的最大受益者与制度需求者,中国公民应当对法治的制度供给实施影响。只有这样,制度的供给才可能接近制度的需求,并最终实现一个良性的法治均衡。然而,在中国当前的政治现实中,除了维权人士(尤其是其中的“技术死磕派”律师)能够在局部领域施加影响外,(21)大部分的公民(包括体制外的法律职业者)能够影响制度供给的场合微乎其微,更勿论主导制度的供给。(22) 由此可见,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似乎让我们看到一道曙光:法治中国的制度“总发包方”(即执政党中央)和制度的需求者(中国公民)在法治中国建设问题上达成了共识,因此理论上可以促成“法制新常态”这个制度非均衡滑向法治的制度均衡。然而,在实践中,真正的制度供给者是管事的公权力机构,而他们又可能在走向法治的过程中失去很多利益,因而未必有动机并采取有效的举措来促成法治的制度均衡的形成。在这个意义上,作为理论上制度非均衡的“法制新常态”在事实上是一种改革僵局的状态。以十八届三中全会启动的司法改革为例,改革的蓝图是非常令人鼓舞的,但是经过中央政法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上海市高级人民检察院—试点单位层层“发包”之后,试点方案的具体举措大大地萎缩了,并且至今,很多事实上有利于司法公正和效率的举措未必能够推行下去。 综上,不出意外,即便存在《依法治国重大决定》这样一个“高大上”的改革蓝图,如果执政党中央不改变推进的策略,那么最后落地的改革举措一定离目前的“法制新常态”不远。究其原因,目前的状态已经是在过去的法律制度改造中,各种利益相关者相互充分博弈的结果,并且受到宏观环境的结构性制约。在没有新的变量和能量的冲击之下,目前的“法制新常态”将会持续很长时间。 四、走向法治:如何破局 如果笔者在前面讲述的道理成立的话,那么中国目前的“法制新常态”既是1978年以来中国法律制度改造的伟大成就,也将是未来走向法治的泥潭。若非有强大的力量去改变这个状态,恐怕这个状态要存续很长时间,其中的问题也将成为顽疾。那么,若是真的要实现法治中国,如何破局? 答案看来只有一个,下猛药去破解目前的改革僵局,尽快实现一个良性的“法治均衡”!药方有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系统认识“法制新常态”中的制度自利性,有针对性地进行能够体现公共利益的改制;另一个部分是尽可能由代表公共利益的机构去落实改革举措,并对阻拦者进行惩罚。 首先是在法治建设的规划上,应当由能够代表公共利益的机构来进行设计。在本轮改革中,尽管“顶层设计”未必完全符合公共利益的标准,但也大体上扮演了这个角色。除了个别领域,应该说,2013年的《全面深化改革重大决定》和r2014年的《依法治国重大决定》基本上是朝正确方向上去的。不过,在设计层面,下一步值得继续做的工作是,还要系统梳理、分析在“法制新常态”之下,立法、执法和司法部门的哪些举措是明显具有自利性的,并予以针对性的改革设计。目前官方文件对问题的描述尽管比较全面,但并没有对问题根源进行太多的分析,尤其是没有对改革的利益相关者的立场和态度进行分析。(23)在下一步就具体法治问题进行改革设计时,应当予以改善。 其次,更为关键的问题是,给定目前的改革蓝图不大改动,在了解具体法律制度所存在的自利性以后,如何推进下一步的改革?如前所述,目前的安排是,由顶层来设计,但还是由同改革相关的公权力机构来落实改革方案;其结果必然是,涉及其切身利益的改革举措势必被打折扣,而对公共利益有利的改革举措势必遭到各种权力机构的“围剿”而大打折扣甚至夭折。针对这个问题,笔者认为,可行的举措有两个方面。 一种可能性是,由执政党中央直接负责具体改革措施的落实,以减少乃至完全避免由于层层委托所形成的代理成本和政策偏差。事实上,如何降低中央政策在落实中的偏差及解决地方治理中的“土皇帝”现象,一直是中国这样的大国治理所必须解决的难题。在古代中国,“巡按”或者“钦差大臣”制度是用来解决此类问题的药方之一。(24)只不过,巡按或者钦差大臣适用于解决个案问题、特殊问题、阶段性问题,而不适合常态化问题的解决。在新中国时期,“巡视制度”是中国古代巡按或者钦差大臣制度的现代翻版。(25)在本轮反腐中,巡视制度也较好地完成了对个案性、特殊性和阶段性问题的解决,但是巡视中的问题如何解决,该项工作是否以及能否制度化,也有待实践证明。(26)在走向法治的改革中,可以借鉴钦差大臣和巡视制度的优点,探索一种由执政党中央委派专员一线监督改革方案实施的路径,以减免改革的代理成本,并实际上推动改革方案落地。 另一种可能性是,寻找改革一线中能够代表公共利益的机构或者个人来设计和/或者监督改革举措的落实。在目前的政治体制中,比较可行的方案是激活人大系统,由人大组织或者代表个人来负责改革方案的设计和/或者监督方案的实施。相比较上述中央委派“钦差大臣”的改革路径,激活人大的改革路径的缺点和优点都比较明显。其缺点是,在目前的政治体制之下,人大缺乏必要的人、财、物和权来实现改革的设计和监督,绝大部分的人大代表对法治事业比较陌生,以及无论是人大组织还是代表个人,都不会有太强烈的动机去从事这项公益性事业。因此,在目前的体制之下,激活人大的改革路径的成本较高。相反,在目前中央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之下,中央委派专员比较容易实现现场监督并调配必要的资源来落实改革举措。当然,激活人大的改革路径也有明显优势,那就是,一旦在试点成功以后,由人大组织与人大代表来实现公共利益改革的路径比较容易制度化。在《依法治国重大决定》中,执政党中央也似乎有了强化人大职能的想法,但是其配套落实举措有待观察。(27) 当然,在目前,上述两种新的可能路径是否可行以及如何操作,只是停留在理论层面探讨。具体的方法,还有待进一步设计以及今后实践的检验。为了检验其效果,可以考虑在局部地区进行试点。在未来的三到五年,如果提到的三种改革路径——即执政党中央委托代理人改革、中央委派专员设计/监督改革、激活人大设计/监督改革——能够分别试点,那将可以通过“百花争鸣、百花齐放”来择优推广。否则,诚如本文所言,如果依旧遵循中央顶层设计、层层委托下级公权力机构落实改革举措的做法,很可能掉进“法制新常态”的泥潭里难以自拔。空说无凭,司法改革的“上海方案”就是一块很好的试金石,让我们拭目以待。 注释: ①参见於兴中:《法治东西》,法律出版社2014年版;季卫东:《通往法治的道路》,法律出版社2014年版;Brian Z.Tamanaha,On the Rule of Law:History,Politics,Theor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4。 ②参见江平:《法治兴,则中国兴——“法治中国”丛书总序》,载季卫东:《通往法治的道路——社会的多元化与权威体系》,法律出版社2014年版。 ③当然,更为消极的看法则是,在十八大之前,中国的法治建设经历了“大倒退”。比如,江平先生在2010年年初评论道“从我们国家现在的情况来看,我是觉得中国的法治处在一个大倒退的时期,或者说我们的法治建设、司法改革、政治改革都处在一个大倒退的时期。”张思之等:《江平与法治天下——〈律师文摘〉2009年年会精选》,载《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10年第3期(总第17期),第88页。 ④吴邦国:《在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座谈会上的讲话》,载《人民日报》2011年1月27日第002版。 ⑤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 ⑥参见最高人民法院:《人民法院工作年度报告(2011年)》,2012年3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的司法改革》,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⑦参见[美]罗纳德·哈里·科斯、王宁:《变革中国:市场经济的中国之路》,中信出版社2013年版。 ⑧参见[匈牙利]雅诺什·科尔奈:《社会主义体制》,张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版。 ⑨周黎安:《中国地方官员的晋升竞标赛模式研究》,载《经济研究》2007年第7期;周飞舟:《锦标赛体制》,载《社会学研究》2009年第3期。 ⑩参见程金华:《国家、法治与“中间变革”——一个中央与地方关系的视角》,载《交大法学》2013年第4期。 (11)参见夏锦文:《当代中国的司法改革:成就、问题与出路——以人民法院为中心的分析》,载《中国法学》2010年第1期;公丕祥:《当代中国的司法改革》,法律出版社2012年版;最高人民法院:《人民法院工作年度报告(2011年)》,2012年3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的司法改革》,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12)参见沈立人、戴园晨:《我国“诸侯经济”的形成及其弊端和根源》,载《经济研究》1990年第3期;银温泉、才婉茹:《我国地方市场分割的成因和治理》,载《经济研究》2001年第6期;李善同等:《中国国内地方保护问题的调查与分析》,载《经济研究》2004年第11期;冯兴元:《地方政府竞争:理论范式、分析框架与实证研究》,译林出版社2010年版,第四章。 (13)Kenneth G.Lieberthal & David M.Lampton(eds.),Bureaucracy,Politics,and Decision Making in Post-Mao Chin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2,pp.1-31. (14)参见Xingzhong Yu,"Legal Pragmatism in the PRC," Journal of Chinese Law,Vol.3,No.1,1989,pp.29-51;程金华:《中国行政纠纷解决的制度选择——以公民需求为视角》,载《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6期。 (15)Mohamed El-Erian,"Navigating the New Normal in Industrial Countries," Per Jacobsson Foundation Lecture,October 10,2010. (16)比如参见[美]比尔·格罗斯,《“新常态”的真正含义》,载《上海证券报》2010年7月12日第S04版;徐以升:《中国经济“新常态”》,载《第一财经日报》2012年3月12日第A07版。 (17)比如参见陆娅楠、刘志强:《新常态,新应对》,载《人民日报》2014年8月18日第017版;李稻葵:《中国经济的四种“新常态”》,载《北京日报》2014年9月29日第025版。 (18)Brian Z.Tamanaha,On the Rule of Law:History,Politics,Theor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4,p.91. (19)关于中国法律发展的“结构性制约”,参见程金华、李学尧:《法律变迁的结构性制约——国家、市场与社会互动中的中国律师职业》,载《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7期。 (20)张曙光:《论制度均衡和制度变革》,载《经济研究》1992年第6期,第31页。 (21)关于维权人士和“技术死磕派”律师对法治建设的潜在影响,参见季卫东:《论中国的法治方式——社会多元化与权威体系的重构》,载《交大法学》2013年第4期。 (22)在选举国家,“我们人民”很显然具有对法律制度供给的最终话语权,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公民通过投票来改变宪法。参见[美]布鲁斯·阿克曼:《我们人民:奠基》,汪庆华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我们人民:转型》,田雷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23)关于中国法律改革的利益相关者,参见程金华:《中国司法改革的利益相关者》,载《北大法律评论》总第15卷第2辑(即出)。 (24)参见刘太祥:《试论秦汉行政巡视制度》,载《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5期(总第37卷第5期);王世华:《略论明代御史巡按制度》,载《历史研究》1990年第6期;高春平:《试论明代的巡按制度》,载《山西大学学报》1990年第1期;董倩:《巡按御史与明代地方政治》,载《青海社会科学》2000年第1期;张晶晶:《清代钦差大臣存在原因探析》,载《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3期(总第42卷第3期)。 (25)参见郑传坤、黄清吉:《健全党内监督与完善巡视制度》,载《政治学研究》2009年第5期。 (26)焦建国:《巡视制度与防止“钱穆制度陷阱”》,载《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04年第2期。 (27)《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到:“健全有立法权的人大主导立法工作的体制机制,发挥人大及其常委会在立法工作中的主导作用。建立由全国人大相关专门委员会、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组织有关部门参与起草综合性、全局性、基础性等重要法律草案制度。增加有法治实践经验的专职常委比例。……明确立法权力边界,从体制机制和工作程序上有效防止部门利益和地方保护主义法律化。对部门间争议较大的重要立法事项,由决策机关引入第三方评估,充分听取各方意见,协调决定,不能久拖不决。”标签:中国法律体系论文; 法律论文; 法治中国论文; 公权力论文; 法治政府论文; 立法原则论文; 社会改革论文; 全面依法治国论文; 市场均衡论文; 社会问题论文; 时政论文; 中央机构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