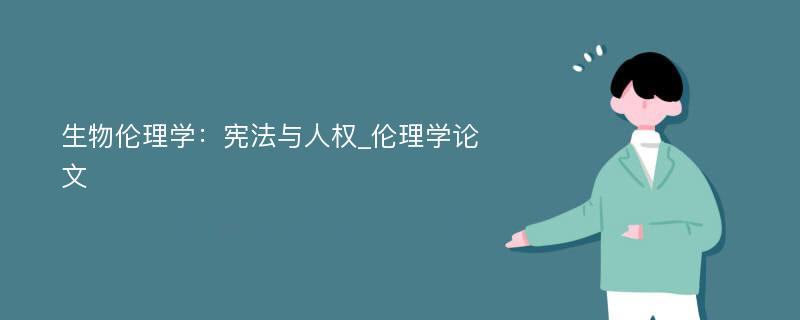
生物伦理学:宪制与人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伦理学论文,人权论文,生物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导论
25年前,有谁曾想到一位美国生物学家的一部著作间接使用的一个新词“生物伦理学”竟会如此风行,而变成本世纪末的哲学和法学思考的支柱之—? 其实,是在1970年,生物学家和癌病专家范·伦塞勒·波特发表了他的《生物伦理学——生存的科学》一书。
以生存概念为参照,亦即以人类的某种可能的目的观为参照,这从一开始就赋予了生物伦理学在当初和今天的重要作用。但它究竟是什么?由“生物学”(生命科学)与“埃托斯”(éthos——行为、品德)两词组合而成的生物伦理学,通常被定义为面对生物学和遗传学突飞猛进造成的种种情况,用来“指导人类行动”的全部行为法则〔1〕。
生物伦理学的涵义不能等同于单独就生物学和人类遗传学所说的涵义或者一般所说的生命科学中的研究加上由之衍生的应用之和。生物伦理学法与生存法有时被当作同义词来使用,以唤起今日社会对于保持自然平衡——维持人类生活的条件的义务和责任。这就是生物伦理学的生态学的和宇宙进化论的意义〔2〕。
如果就保护人权而言,那么这里应该采纳的乃是涵盖人的生存法的生物医学伦理学的最常用的严格定义。
1.生物伦理学的滥觞
离开了对进步质疑的普遍运动,就不能理解对生命科学的伦理学思考的奇特命运。
科学技术社会一方面引起了对于技术——万欲之的——的空前迷恋,另一方面却又导致了对于其自身的争议。不过,这种争议并非是进步的副作用的唯一事实。相反,在工业化国家里,出现了对于“为消费而消费”社会和被看做不平等与非人道化因素的物质进步的批判。
然而,从社会和人类的观点来看,科学技术的进步今天往往被视为中性因素 它既可以带来好处,也可以导致恶果。用科学哲学家乔治·坎吉尔海姆的话来说,科学“乃是无目的性之真理”。它并不提供如何正视科学发现所包含的潜能的社会行为教育。而进步见诸于我们日常生活的每一时刻。
意识到这样的状况,使人感到立法之作为社会选择的表述,对于重新赋予进步以意义,倡导有益地利用科学,禁止可能给人带来危害的应用是完全必要的。
这就是生物伦理学法的使命。事实上,生物学和遗传学在赋予人以改造其自身空间的不平等权力的同时,也就把某些新的责任压在了人的肩上。这些新的责任,以新的方式提出了历史的意义问题。
保罗·瓦莱里宣称:“我们,我们这些文明人,我们现在知道自己是垂死的”。可以将这一说法搬用到生物伦理学领域里,改头换面说:“我们人类现在知道,我们可能因为自己的所作所为而消亡。”
在德国哲学家汉斯·乔纳斯看来,生物伦理学乃是对于新的生物技术工具所构成的“新威胁”的回答。在他的著作《责任的律则》中,乔纳斯甚至鼓吹完全放弃对于生物技术工具的应用。他写道:“最终挣脱了锁链的普罗米修斯,科学赋予了他前所未有的力量,而经济及其无节制的推进要求一种伦理学,通过完全自觉自愿的制约,来阻止人类变成自己的恶运制造者的权力。“〔3〕
生物伦理学虽然不想退回到诸如此类的基本上是灾难论的科学观和人生观,但它不能不流露出对于限制新权力——科学权力和经济权力的关注。事关人类未来,“不允许胡作非为”。
1947年8月19日纽伦堡法庭的判决对此作了重要说明。因为通过这个条文,生物医学伦理学意义上的生物伦理学具有了历史的合法性。事实上,医生和研究人员积极参与了对纳粹集中营里的囚徒和拘留者犯下的暴行,这些暴行的揭露产生了巨大冲击。对这些被无耻地当作实验品扭曲和宰割的男人和女人的“试验”,构成了纽伦堡法庭正式判决的对象。纽伦堡法庭特别强调了个人的独立性,其中包括对人进行的一切研究必须事先征得个人自愿的严格要求。“在接受某种实验之前,应向接受实验者本人说明有关看法,接受实验者必须被告知实验的性质、期限和目的,所使用的方法和手段,可以合理地预见的所有不适和风险,以及参与这种试验对于其健康或人身可能会引发的后果。”
事先被告知的自愿原则后来在许多国际集会上得到再次确认,例如在1947年制定了《纽伦堡法典》的世界医学协会后来又发表了其他宣言——1964年6月的赫尔辛基宣言和1975年的东京宣言。同样,这一原则见诸于世界卫生组织和医学科学组织国际理事会联合发表的《马尼拉宣言》(1988年)。它最终越来越频繁地被纳入各国的立法,以及现行的或正在制定的各种不同的国际文书。
以纽伦堡法庭的判决为参照,对于这个问题有着根本的意义。它明确地肯定了从其起源以来生物伦理学与人权之间固有的密切联系,法学家一般将国际法中保护个人的滥觞追溯到对纳粹组织及其头目的审判〔4〕。
如果它们的出生证是合在一起的,而且思路的来源也是共同的,那么我们能否依然有效地坚持说“人权”的保护目标没有充分考虑到生物伦理学的关注目标?
2.生物伦理学的特殊性
综观世界各国,所有的社会无不围绕因各国的国情和文化而异的两条基本原则进行组织。
其一是等级制原则。它给自由留下很小的余地,虽然可能保障某种特定的安全。其二是尊重个人权利和自由的民主原则。它以普选权和自由选举为基础,赋予当选的多数以制定法律的责任以及对社会的全体成员行使这些法律的责任。但在对于外部影响特别敏感的——通过前所未有的多种传播手段的途径——我们的多元化现代社会的背景下,以政治民主为基础的多数行为在某些方面有所不足。这种不足越来越强烈地要求建立中介监督程序,而且要求建立新的自由反思和讨论的机构和场合。
生物伦理学的探索与这些监督程序是不无关系的。它之所以获得越来越大的成功,盖因为它适应了现实社会的需要。各种伦理学委员会作为我们时代的另一个突出现象,恰恰提供了这种相互促进的公开争论场所。〔5〕
它们的章程和作用可谓五花八门〔6〕。最初的一些委员会创立于60年代,旨在由各国同仁联合肩负起挑选论文发表于英美的学术刊物,因此其目的是保证公开发表的研究成果的学术质量。后来,在医务机构成立了若干伦理学委员会,旨在应医生的要求解决需要作出敏感的有时是痛苦的决定的病人护理问题。另一类的委员会是为了监督人体医学实验计划,并在必要时追踪其过程而设立的。最后,出现了“一般性的”委员会,它们是集反思、讨论和荐举于一身的机构。这种类型的第一个委员会——法国全国委员会(生命科学和健康伦理学全国咨询委员会——CCNE)创建于1983年,它所遵循的是多学科、多文化和诸权分立的模式,行使着咨询的职能。它的使命首先是超越政治的、哲学的或宗教的纷争,作出独立的论断。〔7〕
这类委员会的工作只能受到政治家的欢迎,而且最终决定也取决于政治家。这是因为,就生物医学这样一个正在发展之中并涉及个人生活的最隐私的方面和人类前途本身的领域而言,有待确立的规范实际上是不确定的。
就关心人类的前途而言,其具体表现乃是建立国际层次上的各种委员会。其范围可能是区域性的,如:欧盟的生物技术伦理学顾问组(GCEB),该组织附属于欧洲委员会〔8〕;或者是世界性的,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国际生物伦理学委员会(CIB),它是联合国唯一的系统伦理学委员会〔9〕。
不管它们如何多样,对于这些伦理学委员会的分析可以得出一个普遍的看法:这些委员会起初只是讨论的“论坛”,今天成为辅助决策的机构。
伦理学委员会通过它们的分析以及它们提出的问题和主张的导向,帮助立法者“承担不确定性”。这正是法国国民议会议长菲利普·塞甘在1995年9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生物伦理学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开幕词中所着重指出的。他说:“立法者面对技术或道德方面的不确定性的责任,乃是作出选择,但不能保证前途不违背其意愿。”毫无疑问,生物伦理学的重要贡献就在于它可以充当政治选择的承担者,但并不强求推行某些终极的绝对真理。
事实上,生物伦理学是价值观的一个表达。从生物伦理学的观点来看,颁布生物伦理学法规中比较明确的规范则是旨在实现必然是暂时的某种平衡。作为一种哲学实践,生物伦理学成为对于人类进化的意义的种种探索的组成部分。而生物伦理学法规在某种意义上则是作为某种文明计划的再建因素之一出现的,这样的文明计划的实施乃是科学技术时代不可或缺的。这说明在各国立法表面的多样性(见第一部分)背后,可以发现若干共同的指导原则,而生物伦理学法规的国际化使之更为有效(见第二部分)。
一,各国立法的多样性
1.影响生物伦理学法规的诸社会文化因素
除了在1992年5月17日通过“全民公决”来补充宪法的瑞士之外,所有的国家都满足于采用一般法。首先进行生物伦理学方面立法的乃是西欧国家。但现在整个欧洲和所有其他大陆都加入了这一行列。例如,最近的一部法规是1995年在巴西通过的。各国立法之间的差异主要反映了各自的传统;此外,国家的政局也起着某种作用。
因此,各国所涉及的主题各不相同。有时,生物伦理学法规致力于规定通过人工受孕技术“制造生命”的新的方式〔10〕。
有时,医学对于结束生命的干预,通过实在法来寻求合法化。例如,荷兰1994年的一项法令规定,在某些条件下撤销医生因实施安乐死而招致的刑事惩罚。
在研究欠发达和生物医学的实践尚不很普遍的其他一些国家,生物伦理学法规主要针对人体的使用,特别是器官的提取和移植。
此外,法规的强制程度也是因国而异的。实际上,这是同国家对于个人及社会角色的作用联系在一起的。例如,在美国除了同器官移植有关的问题之外,中央政府并不立法,表明国家对于社会生活的干预很弱。同样的自由传统影响着1990年英国关于人体受孕和胚胎学的法律,而诸如德国和法国等国家采用了强制性较大的立法手段,明确限制人在生殖方面的选择自由(1990年德国关于保护胎儿的法律,1994年7月的法国生物伦理学法规)。
确实,在日本虽然国家发挥着主导作用,但我们看到不存在生物伦理学法规。究其原因,乃是社会共识使得确立强制性的规范无疑成为多余〔11〕。
每一项立法归根结蒂反映了每个国家所固有的传统〔12〕。盎格鲁—萨克逊传统国家的法规把重点放在个人——患者或研究对象的独立性上,强调保障个人对治疗或实验的意愿的表达。
在另一些国家,尤其是天主教影响的国家(法国,拉丁美洲国家),维护人——依据上帝的面貌造就的创造物——的尊严,成为复兴同家庭和社会生活相关的伦理学规范的当然理由。在德国,出于同历史相关的原因(特别是纳粹主义),生物伦理学规定了众多禁条。亚洲或非洲的人生观——人是大自然和谐的组成部分和整个群体不可分割的存在——也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按照一般法则,个人应服从于群体的命令。例如,安乐死在中国并不先验地受到谴责,因为它可以满足病人希望减轻他认为压在社会头上的负担的愿望〔13〕。
2.生物伦理学法规的内容
这种文化背景的差异明显地体现在法规之中。
在有关人的生命发端问题上,这一点尤为突出。事实上,这是显示最鲜明的价值冲突的环节。建立一个家庭,要不要孩子,这样的选择难道不是自由的最根本的东西?
某些立法——英国出于文化的原因,西班牙则出于同佛朗哥主义之后的政治环境相关的原因——赋予个人自由或夫妻自由以首要地位。人工受孕技术之所以要有法律规定,首先是为了能够对这样的技术进行监督和评估。但是,在女子和男子中都广泛接受这种技术。本着同样的精神,对人的胚胎的研究在怀孕14天之前不受限制,技术方面的限制除外。
在其他一些国家(德国,若干斯堪的纳维亚国家),观点不是那样自由。对胚胎的研究在那里是禁止的。接受人工受孕限制很严,主要是为了保护将出生的婴儿的利益。一般说,只有已婚夫妇才能接受人工受孕;同时,某些技术有时被排除出使用之列,以避免贮存多余的胚胎(德国禁止捐赠卵子和胚胎)。
1994年法国关于生物伦理学的法规保持了中庸的解决方案。禁止对胚胎的研究,但不禁止“本着医学的目的,而且不会给胚胎带来损害”的考察。
在最近时期之前尚不是立法对象的产前诊断,现在成为某些法规的主题。例如,1994年法国和挪威的法律明确规定,只有十分严肃的医学指征才能成为使用遗传学诊断的正当理由〔14〕。
在其他一些国家,产前检查偏离了其治疗的目的。众所周知,在中国和印度,它主要被用来识别将产婴儿的性别,而且一般造成怀女性胎儿的妇女中止妊娠。1994年的印度立法虽然禁止这种做法,但很可能在短期或中期内它还不足以战胜作为这种做法原因的自古以来的重男轻女偏见。不过,这个法规所代表的官方立场是值得欢迎的,它证明了一种至少是负责的政治勇气。
尚处于初期试验阶段的植入前诊断,由于它是以挑选胚胎为前提的,因而再一次更加激进地提出了优生学问题。这说明为什么对之进行干预的一些法规或是加以禁止(1990年德国的法规,1992年奥地利的法规),或者规定只有在例外情况下才能进行(1994年法国和挪威的法规)。
法国的新的刑法一般指控“实施企图组织人身选择的优生操作活动”(《新刑法》第511-1条)。
由于遗传学工程除了认识个人遗传性状之外,还提供了改变基因组的崭新的可能,所以这些条文远非是多余的。这就是主要是通过关于基因疗法特别是可以在生殖细胞上操作的基因疗法的争论,使我们看到了对科学的能力的看法再次产生歧义的原因。力图赋予科学以帮助“改善人种”之使命,这种勃勃雄心产生了新的诱惑,我们能否永远不受其侵袭?
米雷叶,德尔马斯-马蒂曾援引了本世纪初的法国生理学家夏尔·里歇的骇人听闻的言论〔15〕,其用意是在优生学的陈词滥调突然死灰复燃的时刻,呼吁人们提高警惕〔16〕。里歇在1913年写道:“强迫一个聋哑人、一个白痴或一个佝偻病人活下去,这不啻是一种野蛮行为”。“世上的低劣的生物不值得任何尊重,也不值得任何同情。坚决消灭它们乃是造福于它们,因为它们永远不能摆脱悲惨的生存。”遗憾的是,这种论调并非只是纸上谈兵。它成为推行优生论政策的理论基础,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导致美国和欧洲强迫许多精神病人绝育,甚至加以灭绝,而这发生在纳粹德国大规模实施灭绝政策之前。
社会优生论同样是玩弄词藻的各种基因疗法的冒险游戏,据说人们试图利用基因疗法来“改善”个人的非病理性状〔17〕。至于将植物和动物身上使用的超前发育技术搬用于人的生殖疗法,它本身是否可行?难道不应该像大多数欧洲国家立法所做的那样,用法律来公开禁止吗?
预测性的遗传学测试的扩散所产生的潜在影响,同样也提出了最令人忧虑的问题之一。今天已有可能认识个人的遗传型所包含的某些危险因子,从而给予了个人从预防的角度,通过改变生活方式和接受医务监测来调整其行为的能力。然而,与此同时,这种健康的预测手段也存在着引起新的社会排斥和歧视形式的风险。
在招工和保险范围内的这些歧视性做法的危险,越来越清楚地显现出来。正如媒体所披露的,伦理学委员会的见解和立法辨论在这方面表达了正当的不安〔18〕。但有利于预测医学——获得了重要的经济和财政利益——发展的潮流,很有可能在保健费用成为越来越不堪忍受的重担的这个时代占据上风。
生命终止问题本身也在争论之中。日益加速的人口增长和日益普遍的经济不稳定的世界环境,显然颇为适合这样的争论。我们可以透过关于安乐死的讨论了解这一点。同样,“大脑死亡”的概念虽然在许多地方还遇到宗教的禁忌(在亚洲和伊斯兰世界),但在医学的压力下越来越被人们所接受。在突尼斯,1991年以来生效的法律不顾宗教的有关规定,容许提取死去的捐献者身上的器官。在以色列,虽然有着种种哲学的和宗教的避讳,但大脑死亡的概念终于被接受。在日本,一项关于器官移植的法律草案已于1994年提交给国会,而按照这个国家的传统,原则上只有在完成丧葬仪式之后死亡才能得以确认。
这些立法上的演进表明科学与社会之间关系的不断变化,科学日益成为改变思想和习俗的一个矢量。
二,生物伦理学法的共同基础
1.生物伦理学的指导原则
对各种生物伦学法规的比较研究,以及对既有的各种伦理学委员会的见解的分析实际上说明了当代伦理学思想的统一性〔19〕,尽管它们的规定和建议有相左之处。诚然,生物医学的研究和实践的法律框架构筑方式乃是每个国家思想状态、经济和技术发展水平及社会结构的作用结果。
然而,我们惊奇地发现,在世界各地,生物伦理学问题的提出基本上都是为了保护人身(包括其个人的和社会的全部构成因素)权利。
生物伦理学赋予个人以首要地位,同时关心整个人类的命运。用让·贝尔纳教授的话来说,维护“人的意义”实际上是赋予生物伦理学的主要使命,以免生物技术把人贬低为它的单纯的生物学基质。
伦理学的使命恰恰是促进个人权利。而个人权利是多方面的,这是因为个人以各种各样的面目出现:根据《普遍人权宣言》的表述,个人是“具有意识和理性的”个体;但个人也是人类——在生命科学赋予“人类家庭”的意义上——的组成部分;最后,个人作为女人或男人处于赋予他们以权利和义务的社会群体之中。而在任何情况下,其共同的参照系乃是具有内在价值的人。
在建立在种族基础上的各种特殊论、语言、历史和文化成为诸多分离乃至冲突因素的时代,生物伦理学试图建立各种文化之间的桥梁。它旨在使各种不同文化能够就人面对科学进步的地位和前景开始不可缺少的对话,因为要驾驭科学,就必须有各民族之间的最起码的团结。
在法律和政治上确认个人的权利乃是生物伦理学的核心。赋予个人以高于生物学和遗传学进步的首要地位,这是通过尊重个人尊严的原则来体现的。1945年6月26日的《联合国宪章》前言提到了这个原则,宣布尊重“人类家庭的一切成员所固有的同样的尊严”的1948年12月10日的《普遍人权宣言)重新确认了这个原则。在生物伦理学的框架内,它首先意味着人的首要权利乃是被承认为人,人作为主体不得被科学当作物来对待。逻辑的必然结论是,人的尊严意味着以超越单纯宽容范围的方式尊重具有文化和遗传的独特性与认同性的他人。尊严在法中确立了这样的观念,即他人既应被注意,又应被尊重,因为他是不同的,他又是自我的一部分。“每个人即是大家”,让—保尔·萨特的这句名言概括了不同于其他一切法律原则的尊严原则的法学和哲学内涵。
首先,这个原则划出了缔造文明者与处于野蛮状态者之间的区分。这从《普通人权宣言》的本文中清楚显示出来。该宣言的前言表达了对于“叛变人道意识的野蛮行动”的谴责。其目的在于通过把尊严当作文明的基本原则,为人们提供一道防止诸如奴隶制或奴役(第4条)、酷刑、刑罚或不人道的和可耻的虐待(第5条)等野蛮暴行出现或长存的防御墙。
尊严要求禁止像对纳粹集中营的关押者或在日本的战俘所作的实验那样的不人道行为。所以,它今天应禁止遗传学认识的进步可能助长其滋生的歧视和排斥。
尊严原则具有不同于个人的其他法规的第二个特点:它有着某种绝对性。这也就是说,它同其他原则特别是确立各种自由的原则相反,不能在任何意义上受到限制。
按照一般规律,自由在其行使中会遇到体现具有集体性的生活的制约的两类限制。一方面,正如1989年的《人权和公民权利宣言》第四条所陈述:“自由即是能够做不损害他人的一切”。另一方面,正如宪法法院的判例所说明的,自由“既非普通的,亦非绝对的”,必须同具有宪制价值的其他原则和法则相协调。
仅以引自生物医学的情况为例,自由地进行研究工作必须同被用于作为医学实验对象的个人的健康保护和安全的法规相协调。在这方面,今天平衡是通过同监督对人的医学研究相关的规定来实现的。
我们无意介入是否存在“超宪制性”——在此名义下,一些原则应处于各种法的等级分类的顶端——的争论,更不想问有时赋予个人尊严原则以“自然法”这样的界定是否合适,只是想着重指出,个人尊严原则作为生物伦理学法的基础,明显地扩大了作为法主体的个人概念本身。它在个人作为个体或某个群体成员得到认同之前,就使他具有一种内在价值。〔20〕
1994年7月27日法国制宪议会的决议——一个宪法法院在今天就生物伦理学所作的唯一决议,在这方面是颇能说明问题的。〔21〕虽然1958年的法国宪法与欧洲其他国家的宪法不同,没有提及个人尊严原则,1789年的《人权宣言》更没有确立这个原则,但制宪议会却能从1946年宪法前言的导论的最基本的概念中引出这个尊严原则。其中的一句话实际上表达了法国公然表明同“试图奴役和剥夺个人尊严的一切制度”彻底决裂的意志。制宪议会陈述道:“从这些词语中可以得出结论说,维护个人尊严,反对一切形式的奴役和侮辱,乃是一个具有宪制价值的原则。”这样的演绎推理可以赋予尊严概念以完整的历史意义。这个原则之所以实际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才被国内和国际法所接受,乃因为我们意识到人可能成为毁灭其自身的工具。因而,生物伦理学所提出的保护逻辑恰恰是为了阻止人对人加以损害。
那么能否真的认为个人尊严原则与个人权利和自由之间存在某种冲突?当然不存在,其原因是尊严高于权利和自由。确实,尊严原则在已经遭到歪曲,譬如说被用来作为书报检查的借口。更为可悲的是它充当了为国家优生论辩护的论据,这种优生论见诸于实践是在本世纪初,当时它还没有成为纳粹主义的学说。后来它成为了纳粹主义学说的一个基本要素,“一些人的生活不值得过下去”。
但对于尊严原则的歪曲丝毫无损于它。今天它成为把生命科学的活动纳入法制轨道所不可或缺的原则。
仅以法国立法的例子来说,尊严原则阐释了对个人自由支配其身体所作的限制。这些限制主要是为了确认人的身体的组成因素和产物——器官、组织、细胞或基因的非承袭性。此外,它说明了对自由进行研究活动作出限制,特别是禁止对人的胚胎进行研究的理由。
法学教授贝特朗·马蒂厄指出:“享有尊严的权利乃是一系列正式法定的保证的母体,而对这些保证进行保护乃是确保尊重该原则本身所必须的”。根据法国1994年关于生物伦理学的法规,这些保证是:“个人的优先地位,从其生命开始之日尊重人,人的身体的不可侵犯性、完整性和非承袭性,〔22〕以及人类的完整性”。
作为新的特殊法平行的来源和具有绝对意义的普遍原则,人的尊严乃是至高无尚的“不可违背的”法律。同样,它实际上不能成为限制的对象,适用于一切环境,无论是战时抑或在“威胁国家生活的例外的公众危险”的情况下(1996年《联合国关于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第4条,《欧洲保护人权公约》第15条)。此外,它自身不能成为任何限定或细分的对象。
生物伦理学有可能作为各种制约的源头,但它同样也是开放自由的新空间的机会。根据康德的看法,个人自由乃是“属于符合人性的每一个人的唯一原始权利”。作为生物伦理学的另一个指导原则,个人自由实际上是个人尊严的组成部分。无论是在国家层次抑或国际层次上,生物伦理学都肯定了个人自由的两个基本保证。其一是个人的明确的自愿。这就是说,个人必须同意治疗、实验、捐献器官、组织和细胞、以及个人医学资料转用于研究目的。
第二个保证关系到尊重私生活的法规,这见诸于许多宪法条文和判例。这一保证之所以得到认可,是因为考虑到遗传学数据尤其是信息论的数据的贮存和流通的大量增长,以及保护其机密性的困难。此外,遗传学的数据不仅对于个人本身,而且对于其家庭包含着信息内容。因此,作出公断是必要的,因为前者和后者的利益有可能产生分歧。最后,个人的遗传学信息具有对于第三者的特定的社会经济功用,第三者间接或直接地参与了承担保健的责任(社会安全部门,保险公司,雇主……)禁止这些角色占有这些医学信息的时代不是到来了吗?〔23〕
何况,个人尊严导致承认作为集体价值的人类所固有的权利。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在195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举办的《种族与历史》讲座中指出,无差别地包容了各种族和一切形式的人类文化的这个概念姗姗来迟。〔24〕人类在几千年的时间里停留在部落圈子里或村落的界限内,而人们与他们的身边的环境、动物和大自然共生。
人类放眼全球,同情和愿意减轻他人痛苦,这种情感在晚近的19世纪促使人道主义激情的产生,于是这种活动觅求有一个自己的体制框架。
但是,需经过纳粹主义及其疯狂理论和邪恶的种族大屠杀的劫难之后,才在法律中明确地引进拥有自己的固有权利的人道概念。1945年的纽伦堡法庭的章程第一次确认了“反人道罪”,这种罪恶被宣布为具有不受时效约束的性质,实际上将人道视为独立的主体〔25〕。
普遍的人道以拥有保持“完整性”权利的“人类”的名义(根据1994年7月29日法国生物伦理学法的用语),要求强化其法律保护制度。然而,人类的完整性并非意味着人的遗传型的不可侵犯性。这一原则见诸于欧洲遗传学工程理事会评议大会1992年通过的建议等欧洲国家的文件,后来没有再次得到肯定。何况,由于人的基因组天然地是不断变异的东西,所以上述原则的实际意义不大。相反,人类的完整性要求对建立在遗传学基础上的优生学活动进行谴责。
此外,这个完整性概念提出了“人的生物多样性”的可能具有的法律意义,反映了人与人之间差异的丰富多彩。因此,哲学家阿兰·芬基尔克劳特指出:“杂交不复是人类的一种冒险的神奇可能;他是人的定义本身”。〔26〕
2.生物伦理学国际法的高涨
生物伦理学不仅仅是国家层次上的社会立法的对象。它同样也在国际层次上激发了巨大的立法热忱。近20年来,除了《人权宣言》相关的基础文件之外,制定了多个纯粹通告性质的宣言。这些宣言或是在学术会议和科学大会之际,或是在各种学术联合会——不论是否非政府组织性质的——的活动范围内公诸于世。其中,1990年医学科学组织国际理事会(CIOMS)发表的犬山宣言规定了研究者必须遵守的伦理标准,呼吁必须恰当地利用遗传学知识。
政府间的国际组织也转向生物伦理学领域。其中,欧洲的各种组织(欧盟和欧洲议会)尤为投入。同样,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内部,国际生物伦理学委员会对以宣言形式发表的一个普遍文件进行了预先的研究。
由于其活动领域、职责和运作方式各自有别,这些不同组织的步调各不相同。例如,欧盟的经济目的性导致欧洲委员会对于舆论面对生物技术发展的怀疑反映尤为敏锐。这个委员会还关注生物技术的应用对于1992年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明确提到的(第3F条)欧洲公民基本权利的影响。因此,继这个条约之后,欧盟在1992年建立了一个同各个伦理学委员会的准则相应的“生物技术伦理学顾问小组”(GCEB)。顾问小组由9个不同国籍的9名成员组成,是多学科的和多元化的,享有独立的地位。它根据不同情况,审议欧洲委员会提交的或者其本职应关注的问题,提出某些看法。借这样的机会,它可以对有待研究或现行的欧洲立法作出判断。通过这样的方式,它对1989年6月14日关于输血安全的指令,对关于同生物技术相关的许可证指令的提案,对关于标明遗传学工程衍生食品标签条例的提案,以及对健康欧洲前景下的基因治疗条例的提案,发表了自己的见解。这些十分具体的意见反映了生物伦理学的指导原则:维护个人尊严;尊重患者的明确的自由意愿;保护个人遗传学数据的机密性,等等。
欧洲议会采用了一种不同的做法。它依据1950年的《欧洲保护人权和基本自由公约》,着手起草一部生物伦理学公约-宪章。1994年初公布的这个公约-宪章草案最终没有被欧洲议会议员大会通过。有两类条款特别引起争议:授权各国在某些条件下准许对胚胎进行研究的条款;使人隐约看到有可将不能表达自己的明确自愿意向的“易受损害的”人员用于实验的条款。
至于其余条款,公约草案表达了国际上对于生物伦理学的基本原则的共识,实际上是建立在尊重个人尊严和保护其权利与自由这两大支柱基础上的。〔27〕
在另一个层次上,早在70年代就开始介入生物伦理学领域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已经制定了一个《关于保护人的基因组的国际文书》,并按照该组织成员国大会使用的程式,列入1993年11月15日的决议案中。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举措的独特性同它从属于联合国系统的地位相一致,联合国要求将普遍化和多元化结合起来。同时,这种独特性还在于该组织秘书长费德里科·马约尔预定的程序。国际生物伦理学委员会(CIB)作为一个研讨机构创建于1992年,包括了来自40个不同国家和代表各个不同学科的50名委员,费德里科·马约尔希望它在教科文组织内部成为一个世界一切文化间交流的独立场所。
正是在国际生物伦理学委员会内部进行了关于未来的《保护人的基因组宣言》的最初几次研讨。
这个研讨阶段成为一种广泛的跨文化对话的机会。事实上,宣言的本文不仅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本部由国际生物伦理学委员会召开的历次年会上进行讨论和接受公开批评。它还由该委员会在全世界散发,向学术机构、大学和各地存在的伦理学委员会正式征求意见和收集反映。对后来寄送到国际生物伦理学委员会的评论进行综合,形成了一个具有头等重要意义的文件,因为它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示了各种文化和各个民族对于生物伦理学的反映的整体面貌。特别是它使人们能够排除那种认为不可能建立生物伦理学的普遍基础的想法。因此,生物伦理学是符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目的,特别是1946年它的成立《宪章》的前言所宣布的“个人尊严、平等和尊重的民主理想”。
《保护人的基因组宣言》不是各国的宪法或立法在世界范围的增扩,因为它在把人的基因组归入人类共同遗产的同时,预示着一种新的思想〔28〕。
人类共同遗产的思想首见于19世纪末,而在本世纪60年代又有了新的创意。它来源于人们在某些历史阶段或强或弱的一种意识:他们注定要生活在一起,从而注定要携手合作来维护其共同的利益。人类共同遗产的概念首先被应用于国际管理被认为是不可或缺的某些物质财富。这些财富包括某些海底、大气外层空间或者还有某些天体,它们不从属于各国的领土主权。但这个概念很快被应用于构成世界遗产的文化财富,虽然它们仍然服从于领土管辖国的立法。保护作为各种文明和文化见证的这些财富,主要是1972年11月16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的事业。
今天,将人的基因组纳入人类共同遗产的组成行列,符合多个目的:首先这表明人的遗传型既不代表其人格,也不代表其个性,所以面对科学在治疗目的之外所提供的利用和改变人的基因的种种可能手段,必须加以保护。此外,这种基因型代表着比字面所指的东西本身多得多的涵义。保罗·奥斯特在他的长篇小说《孤独的创意》中写道,每一个人在其基因中承载着“以往的全部人类的遗产”。
这说明为什么作为其全部数据集合体的人的基因组,乃是应该能为人类所知并为其服务的全部基础知识。
根据联合国《人权宣言》的精神,同样应该认为生物伦理学的指导原则本身也是人类共同体的文化遗产的一部分〔29〕。
事实上,生物伦理学的主体不是人的基因组,不是简单的DNA分子;正如哲学家和生物学家亨利·阿特兰着重指出的,DNA分子本身不代表生命〔29〕。生物伦理学的基本主体乃是有着多面形态的个人。
国际生物伦理学委员会准备的宣言想要强调的正是拒斥任何还原论。人不能被混同于他们的单独一个遗传基。人种纯粹的神话不应让位于基因纯粹的神话。
在国家层次上和今天在国际层次上出现的生物伦理学规范的多层次化,不是偶然现象的结果。它体现了面对极权意识形态的失败和意识到经济主义所固有的局限之后的寻求定位的尝试。从这一意义上说,生物伦理学的反思成为一种酵素,给予不得不重新觅求科学权力与人的尊严之间必不可少的平衡的我们的社会以新的动力。
注释:
〔1〕让-皮埃尔·尚热:《思考生物伦理学——一场哲学争论》(Penser labioétique,undébat philosophique),载于费德里科·马约尔编:《自由交往》(Amicorum Liber),第2卷,布鲁塞尔,布鲁伊朗出版社,1995年。
〔2〕皮埃尔-安德烈·塔古叶夫:《生物伦理学的空间》(L’espace de laBioéthique),见《生物伦理学论集》(Discours sur la Bioéthique),载于《政治词语和言语》(Mots/Les langages du politique》,政治科学出版社,第44期,1995年9月。
〔3〕汉斯·乔纳斯:《责任的律则——技术文明伦理学》(Le PrincepeResponsabilité。Une éthique pour la civilisation technologique),巴黎,雄鹿出版社,1990年。
〔4〕伊芙·马迪奥:《个人的国际保护》(La protection internationale de lapersonne),载于《作为法主体的个人》(Personne Humainsujetdu Droit),普瓦蒂埃大学法律和社会科学系出版物,法国大学出版社,1994年。
〔5〕见乔治·库图克季扬领导下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生物伦理学小组所进行的调查,载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讯》(Le Courrier de I'UNESCO),1994年11月,第11期。
〔6〕克莱尔·安布罗塞利:《伦理学委员会》,见《我知道什么?》丛书,巴黎,法国大学出版社,1990年。索尼亚·勒布里斯:《欧洲议会对伦理学委员会的研究》(Etude pour le Conseil de I’E urope sur les Comités d'éthique),欧洲议会出版物,1994年。
〔7〕见前引让-皮埃尔·尚热著作。
〔8〕介绍生物技术伦理学顾问组(GCEB)的小册子,可向秘书长办公室索取(地址:Isabelle Arnal,Commission Européerme,200,rue de la Loi,1040,Bruxelles)。
〔9〕国际生物伦理学委员会(CIB)历届会议文件,可向秘书长办公室索取(地址:Georges Kutudkijian,Direction de I’Unité de bioéthique de I’UNESCO,I,rue Miollis,75015 Paris)。
〔10〕让-路易·鲍多因和卡特琳娜·拉布鲁塞-里乌:《生产人——谁之权?》(Produire I’Homme,de quel droit?),巴黎,法国大学出版社,1987年。
〔11〕□口洋·和克里斯蒂安·索特主编:《日本的国家和个人》(L’Etat et I’individu au Japon),巴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1990年。
〔12〕诺埃勒·勒努瓦:《生物伦理学与公共卫生政策》(Bioéthique etpolitiquesde Santé publique),载于玛丽亚娜·贝托-武伦塞主编:《欧洲保健》(La Santéen Europe),巴黎,法国文献出版社,1994年。
〔13〕见中国社会科学院生物伦理学计划主任邱仁宗1995年9月提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生物伦理学委员会的报告:《多文化环境下遗传学筛选和试验的伦理学问题》(Ethical lssuesin Genetic screening and Testing in a multicutural context),载于《文件集》第2卷。
〔14〕诺埃勒·勒努瓦:《产前诊断的法律和伦理学问题:法国和其他各国的现行法律和实践)(Aspects juriduques et éthiques du diagnostic prénatal:le droitet les pratiques en vigueur en France et dans divers autres pays),见瑞士比较法研究所出版物。《“人的遗传分析与维护人格”国际讨论会文件》,洛桑,1994年4月。戴维·夏皮罗:《遗传学试验与筛选》(Genetic Testing and Screening),提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伦理学委员会的报告,见《文件集》,1995年。
〔15〕米雷叶·德尔马斯-马蒂:《反人道罪——人权与人的不可还原性》(Le crimecontre I’humanité,les Droits de I’hommeet I’irréductible humain),载于《刑事学评论》(Revue de Science Criminelle),第3期,1994年7-9月:
〔16〕让-保罗·托马斯:《钟形曲线与优生论的水恒复归》(La courbe en clocheou I’éternel retour de I’eugénisme),载于《两个世界评论》(La Revue des Deux Mondes)第2期,1995年。
〔17〕哈罗德·埃德加:《基因疗法》(La Thérapie génique),提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生物伦理学委员会的报告(《文件集》,1995年);皮埃尔,列恩:《基因疗法》(La Thérapie génique),生物技术伦理学顾问组报告,1994年。
〔18〕见1995年10月30日,第46期,生命科学和保健科学伦理学全国咨询委员会关于《遗传学与医学:从预测到预防》(Génétique et mèdecine:de la prédiction à la prévention)的意见。
〔19〕雅克琳娜·罗斯:《现代伦理学思想》(La Penséeéthique contemporaine),《我知道什么?》丛书,巴黎,法国大学出版社,1994。年。
〔20〕诺埃勒·勒努瓦:《世界各国与生物伦理学法规》(Les Etats et le droitdela bioéthique),载于《卫生与社会法评论》(Revue de Droit Sanitaire etSocial),第2期,1995年4—6月。
〔21〕贝特朗·马蒂厄:《面临科学挑战的审慎的宪法法官)(Un juge constitutionnelréservé face aux defis de la science),载于《法国行政法评论》(RevueFrancaise de Droit Administratif),第1018期,1994年。同一作者的专栏文章:《确认人权的宪制保护问题上的原动力原则》(Pour une reconnaissance de principesmatriciels en matière de protection constitutionnelle desdroits de I'homme),发表于《达洛兹评论》(Revue Dalloz)第27期,1995年。
〔22〕并见对制宪议会的决议的评论,载于路易·法沃雷和洛瓦·菲利普:《制宪议会的重大决议)(Les grandes décisions du Conseil constitutionnel),达洛兹出版社,第8版,1995年,第847页。
〔23〕人的躯体的非承袭性和非贸易性原则深深地扎根于法国法律传统,尤其是1952年的第一个血液采集法以后。在其他各国,这一原则并未得到普遍确认。例如,夜美国,1988年的约翰·莫尔案件中加利福尼亚高等法院作出判决之后,关于是否有可能制定个人躯体组成因素及其产物的遗产法的争论一直很活跃。申诉人要求研究人员因利用其包含稀有性状、具有重大科学价值的细胞而给予报酬的起诉被驳回。但法院作出驳回判决的原因是同利用有价值的细胞的准确条件联系在一起的,而并非是因为不存在人体组成因素及其产物没有承袭性的普遍原则。
〔24〕医学数据的保密性问题极为复杂,而且随着经济的或社会的、国家的或私人的机构越来越对承担某些人可能出现的健康风险持保留态度,这个问题变得愈益棘手。尊重私生活的权利被用来同这种有害于团结的倾向进行斗争。例如,在1994年10月5日的判决中,欧共体法院认为,欧洲人权公约第8条所确认的私生活的权利涵盖了个人不透露关于其健康状况的权利。在这种情况下,一个明知自己已感染上了爱滋病毒的待业人员拒绝了作HIV检查的要求。但是,欧洲法院又认为,雇主可以有权根据招聘医学检查的结果来决定是否最终录用某一雇员,如果其合法的利益必须这样做。见《大法官会商文件)(Actesdu colloque des Intellectuels Juifs),巴黎,阿尔班·米歇尔出版社,1995年。
〔25〕阿兰·芬基尔克劳特:《我们时代的重担》(Le fardeau de notre temps),载于《人道观——大法官会商文件》(L'ldée d'Humanité,Actes du Colloque desIntellectuels Juifs),巴黎,阿尔班·米歇尔出版社,1995年。
〔26〕见前引米雷叶·德尔马斯-马蒂著作。
〔27〕公约草案全文见于《永恒的词典或曰生物伦理学和生物技术》(Dictionnairepermanent,ou bioérhique ètbiotechnologies),法律出版社。
〔28〕穆罕默德·贝贾维:《作为人类共同遗产的人的基因组或曰遗传学——从恐惧到希望》(Le génome humain comme Patrimoine commun de I'Humanité,ou lagénétique,de la peur à I’espérance),载于费德里科·马约尔主编:《自由交流》,第2卷,布鲁塞尔,市鲁伊朗出版社,1995年。并见赫克托·格罗斯·埃斯皮埃尔:《人类共同遗产——人的基因组》(Le génome humain,Patrimoine commun de I'humanité),即将出版。应该指出的是人类的共同遗产,根据制宪议会1994年7月27日的决议,在法国的法中不具备宪法基础。
〔29〕我们从中可以重又看到类似于欧洲议会章程前言中的观点,正是这样的观点促使该章程宣布1949年文本的签字国热爱”作为其人民的共同遗产的精神价值和道德价值”。
〔30〕亨利·阿朗和卡特琳娜·布凯:《生命问题——在知识与舆论之间》(Questions de Vie.Entre le savoir et I'opinion),巴黎,瑟伊出版社,1994年。
标签:伦理学论文; 生物伦理学论文; 生物科学论文; 生物医学论文; 立法原则论文; 人权论文; 生物技术论文; 法律论文; 科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