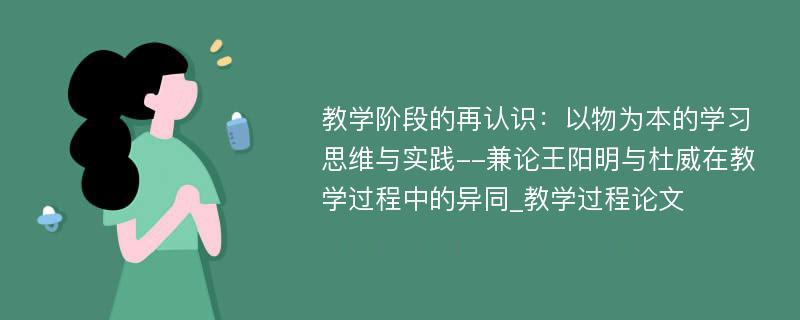
教学阶段再认识:以事为本的学问思辨行——兼论王阳明与杜威教学过程思想的异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再认论文,思辨论文,异同论文,为本论文,教学过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642;G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1610(2015)02-0065-08 “学、问、思、辨、行”作为教学过程的五个阶段,一经《中庸》提出,便显示出自身的顽强生命力:从古代知名书院的院训,如朱熹的《白鹿洞书院揭示》,到现代名校的校训,如孙中山先生的广东大学(现中山大学)校训,再到当代中国学校校园文化对“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的强调,都表明了这一点。现在的问题是学问思辨行教学阶段思想虽在实践中生生不息,但其思想的丰富内涵,尤其是时代内涵却很少被揭示出来,从而致使人们难以更加深入地把握其内涵。鉴于此,笔者试图将阳明心学的学问思辨行教学过程思想诠释出来,以期激发学界对中国传统教学阶段思想的兴趣,从而更好地发掘其丰富内涵。 在阳明看来,“学、问、思、辨、行”是一种知行合一,五者统一于“事”,是学习做事的五个阶段或方面[1]134: 以求能其事而言谓之学,以求解其惑而言谓之问,以求通其说而言谓之思,以求精其察而言谓之辨,以求履其实而言谓之行。盖析其功而言则有五,合其事而言则一而已。 这里的“行”是指做事,而“学”即是“学怎样做”,“问”即是“问怎样做”,“思”即是“思怎样做”,“辨”则是“辨怎样做”,四者都是围绕“将事做成”服务的,从而将教学的五个阶段统整为学习做事的有机过程,进而形成了以事为本的学问思辨行教学阶段思想。这种思想既与杜威的教学阶段思想十分相似,又与之有别。 一、博学以求能其事 在阳明看来,教学过程的首要阶段是“博学”,它明显地不同于杜威(John Dewey)的教学过程思想。在杜威看来,教学过程的第一阶段即是让学生有一个真实的经验情境:让学生有个感兴趣的活动,并在活动中自然感受到困惑,这种直接经验的关键要素是兴趣、活动与困惑。[2]165然而,在阳明看来,学习做事的第一步并非是让学生直接置身于对事情的直接经验中,而是“博学”,即调动学生的积极性,让学生就“所学之事”广泛地搜集信息,既包括通过读书向前人学习,又包括自己的身体力行和反省内观。 (一)“学”的首要含义是“主动求学” “学”的首要含义是学生“主动求能事”,[1]134即学生主动地要求“学做事”。在阳明看来,真正的教学起始于学生的“诚意”,即“志立于学习做事”,表现为对学习做事的主动要求。阳明基于自己12岁时“做圣人”的体悟,认为学习的起点在立志,认为人的学问之所以无所长进,主要原因在志不立:“立志如同种树植根,志之不立,犹如种树不种其根,虽徒事培拥灌溉,则劳苦无成”[3]。 最终致使“志不强者智不达”;而一旦志立,便会“持志养气”,从而具有可以聚精会神学习的“精气神”,拥有克服学习困难的坚强意志,进而会产生“以志养智”的效果:虽然自身的智慧起初可能并不强大,但只要志立于学习,自身的智慧就会日益强大。 很明显,在激发学生学习动机方面,阳明采取了与杜威不同的方式。杜威采取兴趣视角,认为“兴趣是从事各种活动的动力”,[2]143力图从学生兴趣出发选择要学习的内容,或者说学习内容本身内在地符合学生的兴趣,在教学的初始阶段主要采取活动本身的趣味性来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与动机。阳明则主张目标理论,认为学习是通达人生目的的途径,调动学习动机的最好办法在于确立为学的终极价值目标——人生的伟大理想(在阳明看来是做圣人),因为学习不仅为即时的兴趣所激发,更为人的终极价值理想所激励:即时的兴趣需要被更为远大的人生理想所统领,才不会迷失方向;学习不仅为兴趣所激励,更为道德责任所鞭策,“立志”所确立的人生责任感使学习成了一种道德责任,这种道德责任使学生在学习路上走得更远,虽然一路上亦须有兴趣陪伴。 (二)博学即广泛涉猎多方面事务 从学习内容角度看,“博学”即学习多方面的事务,像孔子一样“每事问”,从而使“万物之理皆备于我”,进而为实现“万物一体”的人格理想奠基。在阳明看来[1]207: 人者,天地之心。天地万物本吾一体者也。生民之困苦荼毒,孰非疾痛之切于吾身者乎?……视人犹己,视国犹家,而以天地万物为一体,求天下无冶,不可得矣。 宇宙万事万物是一个息息相通的有机系统,其中的每部分都与自己有着直接的联系,都是与自己息息相关的一部分,作为天地之心的人,其意识不仅是他个人的自我意识,更是宇宙境界的自我意识,因而使得自我有责任和义务去关心宇宙万物的繁衍生息,就像有义务关心自己的家庭成员一样。[4]而要使天地万物繁衍生息、自我实现,则必须按照万物各自的内在之理来善待它们、治理它们,而不能凭借自己的私欲任意处置它们。 (三)博学即多渠道收集信息 从学习方式角度看,“博学”即从多种途径广泛地获取信息,主要包括三方面:其一,“遍读圣贤书”。阳明认为圣贤书是求“天理”。一旦得到天理,便可“得道弃书”,就像“得鱼忘筌”。[5]然而,并非所有的书籍都有“天理”,因此需要师生慎选圣贤书,将那些能够将“天理”更全面、更深刻地表现出来的书籍当作教材。不但如此,在学习过程中,还应依据“天理”本身的标准来审视圣贤书,汲取其合理成分,修正其不合理成分。正是在这种意义上,阳明认为自己的见解不必尽合于圣贤,相反,圣贤的箴言圣训却必须放在“天理”面前,接受“天理”的检验。[6]266 其二,“事上磨炼”。阳明认为,“天理”不是与人的生活无关的抽象的观念,而是生活境域中的“活理”,获得这种“活理”的最直接途径自然是将自身投入到事情本身中,亲身体之、验之、磨之、炼之。[7]318从这种意义上讲,“‘博学于文’为随事学存天理”[1]130,即在做事中体验事中的“天理”,“如言学孝,则必服劳奉养,躬行孝道,然后谓之学”,[1]134这种功夫正像“医经折肱,方能察人病理”[1]279。正如杜威的“自然在经验中”:事物本身虽然就存在那里,但事物本身却不会自动地在人面前显现自身,而只能被人的经验所打开。“事物的内在本质乃是作为事物被直接体验到的性质,在经验中显现出来的”[8]。 其三,“用心观看”。阳明虽然并不否认事物之“理”的存在,但对事物之“理”的获得却必须反观自己的内心——意识内容。事物的“理”不像具体事物可以为肉眼所把握,就像阳明自己用“肉眼”盯着竹子并不能将竹子的“理”看穿一样。[1]312事物的“理”必须通过人的“心眼”——意识——才能被人看到,才能为人所把握,因为事物的“理”虽然本有,却处于不为人所见的“寂然”状态,就像“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心同归于寂”一样;而人的意识出场则将处于寂然状态的事物之“理”照亮,使其在人面前显现自身为自身,就像“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一样。[1]286也如胡塞尔用意识对事物进行现象学还原从而使事物本身在人面前显现自身为自身。总之,阳明将“学”作为学习做事的第一阶段,认为“博学之”要求学生不仅通过读书,更是通过自己的躬身实践和现象学意识来更多地获取做事信息,从而自己学做事打下广博的基础。 二、审问以求解其惑 在“问”的阶段,阳明与杜威既相似又不同:杜威将之分解成让学生感受到困惑、将困惑转化成引导探究不断进行下去的问题、形成解决问题的假设三个阶段,认为第二阶段的主要任务是引导学生将感受到的困惑进行理智化,从而将其表征为一个将要被解决的问题,进而卓有成效地将困惑转化为明确的探究过程。[9]49-50 (一)“问”的首要含义是“主动问” 阳明认为,推动教学不断进行下去的是师生之间的“问—答”结构,在这种结构中,问的主体是学生,而不是教师,学生能否主动提出问题是教学能否继续进行下去的关键,《传习录》作为阳明教学实践的总结更好地体现了这一思想。在阳明的教学实践中,学生成了提问的主体,学生基于自己的学习情况主动提出疑问,教师则借助学生的提问而有针对性思考与回答问题,从而展开教学。其中,教师的职责主要在于使学生意识到自身的无知,并督促学生自己主动提出问题,正如阳明在教学中所说:“诸公近见时,少疑问。何也?人不用力,莫不自以为己知。”[1]67不但如此,教师要有能力识别学生所提问题的价值,进而引导学生主动提出有价值的问题,正如阳明与萧惠之间的教学问答[1]124: 惠请问二氏之妙。先生曰,“向汝说圣人之学简易广大。汝却不问我悟的。只问我悔的”。惠惭谢。请问圣人之学。先生曰,“汝今只是了人事问。待汝辨个真要求为圣人的心来与汝说”。惠再三请。先生曰,“已与汝一句道尽。汝尚自不会”。 总之,对于课堂提问,杜威着重强调问题须由学生自己提出,而不是教师所为;问题须从学生自身经验中产生,而不能是与之无关。[2]143阳明则在二者基础上更强调要让学生主动提出有价值的问题,而不是虚假的问题。 (二)审问即批判圣贤书 “审问”的对象首先是圣贤书,学习者要敢于挑战圣贤书,提出创造性问题,并给出创造性回答,这一点与朱熹截然不同:朱熹对待圣贤书的态度是去私意,尽可能多地再现“圣贤本来观点”[10]: 读书须是虚心,方得圣贤说一字是一字。自家只平着心去秤停他,都使不得一毫杜撰。学者看文字,不必自立说,只记前贤与诸家说便了。 王阳明则批判朱熹对待圣贤书的态度,认为圣贤书不是“是非”的终极判断标准和依据,相反,圣贤书本身的真理性仍需检验,检验的标准便是圣贤书所意欲再现的“天理”。因此,学习者不能以圣贤之是非为是非,而应依据事物自身的“道理”提出自己的创造性见解,而不必尽合于先贤先儒之说。[5]这便是“审问之”的第一层含义:对所学的圣贤书详尽设置疑问,其目的不是为了一味地否认圣贤书而是为了考证圣贤书[1]199,其言虽出于孔子,不敢以为是也……其言虽出于庸常,不敢以为非也,而况出于孔子乎? 更是为了提出自己的创造性观点,《五经臆说》便是证明。阳明依据自己心得体会对《五经》做出了创造性诠释,而非像朱熹那样对《五经》进行复古式阅读。 (三)审问即自我批判 “审问”的对象不仅是外在的圣贤书,更是自己。学习者必须在批判圣贤书的同时,展开自我批判,从而能够正确认识自己,深刻意识到自己的长处与不足,意识到自己在学习过程中所遇到的真正问题,然后针对性地向别人学习——“见贤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针对人性的弱点,要努力做到:“初学用功,却须扫除荡涤,勿使留积,则适然来遇,始不为累,自然顺而应之”[1]328。 在“学者有四失”中,要尤为注意不要使自己浅尝辄止,自以为自己学的很多,懂得如何为学做事了。为此,必须展开自我批判。实际上,格物不是去格外物,而是格心,要努力使自己的内心光明,从而使万物之“理”在自己心中更好地显现出来[1]66: 心犹镜也。圣人心如明镜。常人心如昏镜。近世格物之说,如以镜照物,照上用功。不知镜尚昏在,何能照?先生之格物,如磨镜而使之明。磨上用功。明了后亦未尝废照。 一旦获得真理,则坚定不移地按照真理的指示去做,从而在匡正事物的同时,使事物的“真理”永存在自己心中。 (四)审问即提出真问题,形成真见解 所谓真问题就是,直面要学习的“事物本身”,亲自将自己置身于“事物本身”之中,“习”之,“磨”之,以便对“事物本身”形成原初体验,并对自己在体验“事物本身”的过程中所遇到的疑惑进行提问。[7]9这样的问题便是在经验事物本身中自然产生的问题,它既与事物本身密切相关,又与学习者对事物本身的把握息息相连。学习者的提问须是自己在学习做事的过程自然产生的真问题,正像杜威所说学生所要探究的问题须从对事物的探究活动过程中自然产生。[2]19不但如此,学习者还要依据自己所提问题对事物展开进一步的观察,以提出解决问题的尝试性设想,正像阳明的学生经常带着问题与对问题的尝试性回答来请教一样。 三、慎思以求通其说 慎思即贯通。阳明认为“审思”的根本含义是融会贯通——“求通其说而言谓之思”[1]134,即将各种学说融会贯通,将学说与事物融会贯通,将个别的事与普遍的理贯通,从而形成对所学之事的完整认识。 (一)慎思即贯通各种学说 各种学说是人们解释事物的方式,而人们解释事物的方式来源于人们经验事物的方式,同一个事物则在不同的经验方式之中呈现自身不同的样子,进而使得人们对同一事物采取了不同的解释方式,形成了不同的学说,正如在天泉证道中王畿与钱德洪所做的那样面对同一事物——阳明四句教:“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1]312。钱王二人采取了不同的诠释方式,形成了相互对立的诠释理论。王畿将其解释为“四无说”:“心无恶无善,意无恶无善,知无恶无善,物无恶无善”[1]312,而钱德洪则将其解释为“四有说”:“至善无恶者心,有善有恶者意,知善知恶者良知,为善去恶者格物”。[1]312贯通各种学说的必要性在于将各种学说融会贯通,从而使人对事物本身的理解更加全面,这不仅是因为各种学说都以不同方式从不同视角深刻揭示了事物的不同方面,而且是因为各种学说在深刻揭示事物的同时亦显示了自身视角的局限性,显示了解释事物的片面性。正如阳明在肯定钱王二人诠释方式合理性的同时指出两种方式存在的局限性。自己的四句教既不是片面地主张四无,也不是片面地主张四有,而是同时容纳调和四无与四有的有机综合体。[6]186总之,善学者须学会将古今中外的各种学说融会贯通起来,从中汲取精华,形成对所学之事的完整认识,正如孔子所言:吾虽空空如也,但只要“叩其两端而竭”,便能获得对事物的完整理解。 (二)慎思即贯通学说与事物 要贯通各种学说,就不能仅仅只在各种学说中“打转转”,因为仅依靠各种学说而形成的对事物的融会贯通性认识,并不能保证对事物认识的真理性。对各种学说精华与糟粕的认定,并不取决于作者本人的权威性,亦不取决于学说内部的融洽及来自其他学说的支持,而是取决于学说与事物本身的一致性。一种学说的真理性取决于对事物本身的正确反映程度。学习者之所以学习各种学说,主要是因为各种学说记载了事物之理,进而使得人们可依据对学说的理解使事物之理在自己面前呈现出来从而达到对事物之理的正确理解,正像阳明所说:各种道德学说只不过是人心中良知的记录簿而已[1]349。 六经者,吾心之记籍也,而六经之实则具于吾心;犹之产业库藏之实积,种种色色,具存于其家。其记籍者,特名状数目而已。 另一方面学习者在依据各种学说寻求事物之理的同时,必须依据事物之理来拷问各种学说的正确性,正是在这种意义上,王阳明认为:“其言虽出于孔子,不敢以为是……其言虽出于庸常,不敢以为非”[1]199。应依据人心中良知来拷问《六经》的真实性[11]349。 世之学者,不知求《六经》之实于吾心,而徒考索于影响之间,牵制于文义之末,硁硁然以为是《六经》矣。 因此,善学者须在“以文求实”的同时做到“以实训文”,即在依靠各种学说把握事物之理的同时,依据事物本身的实际情况来辨别各种学说自身的真伪性,从而将没能反映或没能正确反映事物之理的各种虚假学说剔除出去,将正确反映事物之理的学说铭记在心中。理解经典即是在经典与事物本身之间融会贯通,在经典与事物本身之间来来回回地跑着,直到学习者能够完全地把握经典所言及的事物本身,并依据事物本身来拷问经典以辨明其中的精华与糟粕,正如阳明所认为的那样学习者应在通过“六经注我”来把握道德良知的同时,亦通过“我注六经”来利用人的道德良知本身去辨别《六经》所述的真伪性。 (三)慎思即贯通个别的事与普遍的理 在朱熹看来,贯通主要是指从对具体事物的认识过渡到对理的认识的过程,这一质的飞越是靠对具体事物的日积月累地格致来实现的。阳明则通过自己连续数日的格竹子实践证明朱熹即物穷理的方法行不通,进而认为有形之物的理在事物中总是处于隐而不显的寂然状态,人无法直接从具体事物中找到其“理”,换句话说,事物之中的理只是寂然状态的“本有”而非显现状态的“实有”,因此这种理在“实有”意义上并不存在。如何让学生获得具体事物的“理”便成了阳明思想的中心问题。为此,阳明先生提出“心即理”的说法,认为具体事物的“理”只能通过人的意识才能从寂然状态转化为显现状态,从“本有”转化为“实有”,从而为人所把握。换句说法,人只有通过自己的主动意识,而不是朱熹所谓的格物,才能将具体事物与其“理”贯通起来。从人的意识可以将寂然状态的“本有之理”转化为显现状态的“实有之理”角度而言,从显现状态的“实有之理”只能存在于人的意识之中角度而言,“心即是理”,“心外无理”,于本心之外逐物求理,终将无功而返。因此,要想得到事物的理,务必内求于心,发明本心,使本心光明,从而使事物之理在自己心中更好地显现出来,因为人心如同一面镜子,学习者应把心镜磨明再去拿它照物,而不应该在心镜不明的情况下去照物:心镜不明则物来不能照,难使事物之理在心中显现;心镜磨明了再去照亦不废照,[1]66就像磨刀不废砍柴的道理一样。鉴于此,学习者要想贯通个别的事与普遍的理,必须将自己心中的现象学意识发扬光大。 总之,慎思的主要任务在于围绕所学之事,通过各种学说之间、学说与事物之间、个别的事与普遍的理之间的贯通活动,将博学得来的各种信息融会贯通,将审问产生的各种疑点与解决疑点的办法融会贯通,从而将所学之事的各方面有机统一起来,将所学之事的各阶段有机统一起来,并最终获得对所学之事的完整认识。这种做法既与杜威教学过程的推理阶段十分相似,又与之差别很大。杜威虽然将推理视为“形成彼此之间意义相互涵摄的理念”[9]51所做的努力,认为推理可使解决问题的假设更连贯,从而与更大范围的事实相一致。[12]但杜威很少论及将所学之事的各种学说——历史经验——贯通起来,将各种学说与所学之事贯通起来,因为杜威的问题解决过程很少论及对人类历史经验的借助问题;另外,杜威亦很少论及如何将所学之事的个体经验提升到普遍的人类经验的问题,因而较少阐述个别的事与普遍的理之间的贯通问题。而这些恰恰是阳明所重视的。 四、明辨以求精其察 学习者不仅要获得对所学之事的整体性认识,还应将这种整体性认识具体化、精细化,并在具体化过程中通过精细考察来修正整体性认识,从而使之更精确。为此,教学必须进入“明辨”阶段。这里,“明辨”的根本含义是精细考察——“以求精其察而言谓之辨”[1]134,主要包括“省察”、“体察”和“公共辩论”三方面。 (一)明辨即省察己见 精察的首要含义是“省察”,[1]248主要是指反省自查,即反观自己的意识世界,在自己的意识世界中对通过博学、审问、慎思而获得的关于事物的整体性认识进行仔细观察与详细推敲,其主要任务是通过逻辑推理和现象学想象来详细论证自己的观点。一方面通过逻辑推理来进行,其主要任务是以概念、范畴为基本工具,合乎逻辑地对自己所得出的关于事物的整体性认识进行系统化的理性演绎,并在这种逻辑演绎中继续探索、修正、完善与丰富自己的整体性认识,正如柏拉图在《理想国》中通过逻辑推演来详细展开论述自己的“理念论”,亦如黑格尔在自己的历史哲学中通过从纯粹的概念辩证地推出现实。这种方法常常被称为哲学思辨或反思。另一方面通过现象学想象来进行,其主要任务在于通过无拘无束的自由联想将验证自己观点的例子进行尽可能的变形,从而将自己关于事物的看法置于该事物的尽可能多的变形之中,接受这些变形的检验,并依据自己观点与事物诸多变形体之间的一致性来判断自己观点的合理性,来修正与发展自己关于该事物的看法。在这里,检验自己的观点的不是事物的现实世界而是事物的可能世界,即事物所有的可能样子,虽然它在原则上是一个可以被我们经验到的世界。[13]这就使得经过现象学想象检验的观点具有更广范围的适用性。正是在这种意义上讲,王阳明认为判断是非得失的标准不是外在的事实世界,而是自己心中的意识世界:“众皆以为是,苟求之心而未合焉,未敢以为是也;众皆以为非,苟求之心而有契焉,未敢以为非也”[14]。这种方法有时被称为思想实验,一种与真的实验相对应借助人的想象与逻辑推理在人的思维中进行的实验,这种方法已成为一种不可替代的科学研究方法,为检验思想观点的合理性提供了新的论据。[15] (二)明辨即体察己见 “体察”主要是指实地考察,即亲自进入事物或事件的发生现场进行考察,考察者在这里并不是事件发生的当事人,而是事件发生的旁观者。阳明认为,通过博学、审问、慎思而获得的观点不仅需要思想实验的验证,而且需要实地考察与核查。仅仅停留于思想实验,而不将自己心中的观点放在实际的事物面前接受实际事物的进一步检验,最终会使自己的想法趋于不切实际的“虚无”;反过来,如果能坚持将自己的观点放到实践面前随事随物体察自己观点与实际事物的一致性,就会使自己变得日益明智,就算是“昏暗之士”也能使自己“由愚变明”。[1]137现代科学亦证明由思想实验得出的观点有时并不可靠,如牛顿用以证明绝对时空的双球思想实验、爱因斯的反量子力学思想实验并没有达到有效验证自己思想的目的。[16]因此,通过实地观察或内省而得出的结论,其真理性仍然需要接受新的实际观测事实的进一步检验,并在接受客观事实的不断检验中舍弃自身的虚假成分,增添真理成分,从而使自己对事物的认识愈来愈符合事物本身。 (三)明辨即公共审查己见 所谓公共审查,即将这种认识放在众人面前做进一步的检验,因为自己的思想由自己检验,可能会产生刚愎自用现象,从而会使自己的结论有所偏颇,就像胡塞尔在“本质还原”之后要做“先验还原”一样。要对进行本质还原的经验主体进行先验还原,从而使现象学还原的主体由经验主体提升至先验主体,一种从人类角度而非个体角度进行的现象学还原。[17]为使学生自己得出的见解跳出自我的限制,走出唯我论的泥潭,阳明不但要求学生在心中省察自己的观点,从实地观察随事随物体察自己的观点,而且要求学生将自己的观点与师友分享,让自己与师友通过辩论来明辨自己的观点的是非得失,这一点较好地体现在阳明的教学实践中,如在“天泉证道”教学过程中阳明让王畿与钱德洪二生就各自心中的见解在师生之间与生生之间展开辩论,从而使王畿意识到自己“四无说”的适用范围及其精华糟粕所在,使钱德洪意识到自己“四有说”的是非得失,从而为各自学说的进一步发展指明方向。[1]137 由此可见,阳明要求学生在将自己通过博学、审问、慎思而学到的思想观点付诸实践之前先行评估其思想观点的合理性,评估的方式主是“省察”、“体察”和“公共辩论”三者相结合。这一点既与杜威的“推理”教学阶段十分相似又与之不同:其一,目的相同,都是让学生在将自身的观点或假设付诸行动之前,进行再一次的评估与检验,从而使自己的观点或假设变得更加完善。其二,在手段方面,相异之处多于相同之处。杜威认为评估主要是在理智范围内通过推理而实现,这一点类似阳明所说的“省察”,而阳明则主张“省察”、“体察”和“公共辩论”三者相结合。杜威强调评估诉诸学生的亲身体验,王阳明则强调评估要诉诸学生亲身体验与公共经验并举。 五、笃行以求履其实 对于学做事而言,学问思辨行是一个完整的教学过程,“笃行”作为学习做事的最后一个阶段:“辨既明矣,思既慎矣,问即审矣,学既能矣,又从而不息其功焉,斯之谓笃行”[1]134。主要是指将通过学问思辨得来的“知识”坚持不懈地付诸实践的过程,包括学以致用、行以验知和行以充知三层内涵。 (一)笃行即学以致用,将己知化为行动 “笃行”作为思想的实现,主要包括三方面含义:一是“行是知之成”。知识天然地包括行动,知的过程直到“知”获得了自己的工夫——行——才算真正的完成。在整个致知过程中[11]306,其最终目的导向了“做这件事”,“践行”在此意义上成了学问思辨得以不断进行的目的因,因而亦成了“学做事”教学过程的最终环节,学问思辨只是为了“践行”而做的前期准备,只是整个“践行”过程的起始环节,“践行”则是“学问思辨”的完成。[18] 二是“行是知的价值实现”。知识通过践行知识的实践才能实现自身的价值,为此,教师应引导学生以其所学去改造世界。将学到的“自然知识”应用于自然世界的改造,将学到的“道德知识”应用于社会世界的改造,从而使世界中的“事事物物”得以匡正,同时使自己内在的道德德性得以养成。这便是阳明所强调的“致良知”。 三是“知易行难”。相对而言,认识事物的道理比较容易,而要按照事物的道理去治理事物却比较难,其内在原因便是人性的弱点,它阻碍着人去学以致用,正像阳明所说:“良知自知,原是容易的;只是不能致那良知,便是‘知之匪艰,行之惟艰’”[1]313。正因为如此,教师应引导学生努力克服自身的弱点,积极创造条件将自己所学运用于实践,正像王阳明时刻不忘教世人去“致良知”一样。[1]25 (二)笃行即行以验知,用实践检验己知 知之后之所以有个“行”紧随其后,因为先知的知是不是“正确反映事物之理”的真知,有待于相应实践的检验。所谓真知,便是可以真切笃实的知,“知而不能真切笃实,便是妄想”[11]306。一种知识是可以真切笃实的真知,还是不能真切笃实的妄想,需要相应的践行来检验。从这个角度讲,“践行”的含义,不再是“思想的实现”,而是“检验知识能否真切笃实的手段和标准”。作为检验知识的手段与标准,“践行”是和理想状态的知天然一体的,因为真知必定包含着真切笃实的含义,那就是“行”。之所以说“知”又说“行”,是因为有种人成天只知道冥思苦想而不肯着实躬行,必须教这种人以“笃行”,必须对这种人说个“行”,方才可以使其获得真知。对于深谙知行本体的人来说,说“知”则“行”已经在其中了。[1]21-22所以,教师应引导学生通过亲自做来“体察”自己的主张或假设,这一点和杜威“用行动检验假设”的含义是相通的,学生通过自身的实践活动(包括实验)来检验自己的主张或假设,失败的主张或假设被修改或抛弃,成功的则被用来指导今后的实践,并继续接受未来实践的考验。[12]71值得一提的是,教师要特别注意失败结果的教育价值,让学生善于从失败中总结教训,从失败中学到与成功经验不同却又同等重要的经验。[19]99 (三)笃行即行以充知,以实践深化己知 “笃行”作为思想的扩充,主要包括两层含义:一是行使知“由空到实”,由名言意义的知走向经验意义的知,从而贯通名言与经验。学生由学问思辨所得的知识在其本质上属于名言意义的知识,是一种概念性知识,而不是经验意义的知识,因而还是空的。就像从未吃过“甜东西”的人,通过书本、教师与他人的言说而获得的对“甜”的理解,只是代表他对甜味概念的掌握,所掌握的只是“甜”的名言意义,而不是“甜”的经验意义。从有无实际经验的角度讲,他掌握的“甜”字意义因没有获得自己体验的支持而只是停留在概念上的掌握,因而只是空的,正像康德(Immanuel Kant)所说概念没有经验的支持只是空的一样。[20]一旦他亲自去尝甜东西,他对“甜”字意义的概念性理解就获得了经验的印证与支持,因而获得对“甜”的名言意义与经验意义的双重理解,并将“甜”的概念与经验贯通成一体,这就是“体念有得”。正是在这种意义上,阳明强调知后必须有“行”,强调让学生通过“行”而获得对事物之理的理解,因为对事物的理解不仅是概念的掌握,更是体验之“知”,正像只有亲身经历过痛感的人才真正知道什么叫痛,只有亲身遭受过寒冷的人才真正知道什么叫寒。[1]20 二是行使心中的知“发扬光大”,由弱小变得强大,由不稳变得牢固。由学问思辨所得来的知识在学生心中并不稳定,亦不强大,通过对知识的践行才能使心中的知识变得更加强大,从而更加坚实地巩固在心中,就像孟子所讲的恻隐之心在人心中刚开始并不强大,只有通过不断地将“恻隐之心”付诸于体外的“恻隐之行”才能使“恻隐之心”在自己心中发扬光大,从而使“恻隐之心”牢固在自己心中。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教师应当教学生念念不忘“学以致用”,就像人在道德修养上时刻不忘“致良知”一样。“致良知”是实实落落地依据自己心中的良知做事,从而将心中的良知发扬光大,使良知能够牢固在心中[1]319;“学以致用”则是坚持不懈地将自己所学到的事物之理(包括道德伦理)运用于实践,从而使事物之理在自己心中变得更加强大,更加牢固。 由此可见,学问思辨行教学过程的“行动”环节比杜威“用行动检验假设”的教学阶段具有更多的内涵。阳明的“笃行”,蕴含着杜威所说的“行以验知”,更蕴含着让“知”在转变成“行”的过程中实现“知”的社会价值,扩充“知”的内涵使“知”在心中变得更加强大等方面的意义。 综上所述,阳明与杜威都将教学看成是学习做事的过程。第一,杜威主张直接以将学生置身于令人困惑的情境中开启教学,而阳明则主张先让学生就所学做的事通过阅读书籍、亲自考察等途径广泛地搜集信息。第二,在“问”的阶段,阳明将学生收集与处理做事信息所产生的困惑、对困惑的问题表达以及试图解决问题的主动尝试——主张与见解——融合在“审问”阶段;杜威则将之分解成让学生感受到困惑、将困惑转化成可以探究的问题、形成解决问题的假设三个阶段。第三,在“思”的阶段,阳明注重让学生围绕“事”,通过慎思使各种学说相互贯通,使学说与事物相互贯通,使个别的事与普遍的理相互贯通,从而形成对所学之事的完整认识;杜威则甚少论及这个问题,只在“推理”教学阶段,以“蜻蜓点水”的方式提及让学生通过“推理”使假设更加连贯的问题。第四,在“辨”的阶段,阳明注重让学生对自己通过博学、审问、慎思而得出的思想观点,通过“省察”、“体察”和“公共辩论”三者相结合的方式对其进行合理性评估;杜威则主张评估主要在理智范围内通过推理来进行,类似于阳明所说的“省察”。第五,在“行”的阶段,阳明认为“行”具有实现知识的价值、检验知识与扩充知识三方面的作用,杜威则强调知识的检验。第六,在整个学做事的过程中,阳明注重人类历史经验与个体亲身体验的互动,因而多了个“博学”环节,而杜威则更注重学生个体的直接经验。第七,阳明认为学问思辨行是围绕“学做事”的一件事而不是五件事,只不过这五个方面既各有各的功能,又相互渗透,从而组成有机的“知行合一”过程[1]319;杜威则认为教学过程是反省思维的五个阶段,所反映的是反省思维的不可缺少的特质,这五个特质并非必然地按照固定的顺序一个接一个地出现,而更可能是相互涵摄的。[19]99二者在这一点上是相通的。第八,阳明教学阶段思想像断了线的珠子散落在其著作的各个角落,隐而不现,杜威教学阶段思想则如同整齐摆放在商店柜台之中的项链,博人眼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