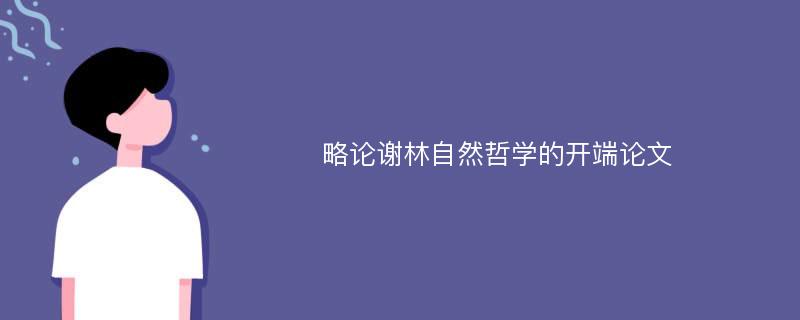
略论谢林自然哲学的开端
庄振华
[陕西师范大学,西安 710119]
摘 要: 谢林在承认自我意识的关键性作用的基础上,跨出康德与费希特所坚守的自我意识视角之外,将原初同一性界定为观念东西与实在东西之间(而非表象与对象之间)的同一性,在此基础上建立他的自然哲学。这就既继承了近代哲学在自我意识方面的遗产,又在德国观念论语境下复兴了传统的秩序观。对于倾向于忽略人类思维对于形式的反思能力的当前时代而言,这种古典类型的秩序观未必能直接为当下的问题提供答案,却具有重要的参照价值。
关键词: 谢林;自然哲学;自我意识;人工智能
德语思想界早在中世纪后期,从埃克哈特(Meister Eckhart)开始,就奠定了十分不同于拉丁语思想的一种内在性构想,这种构想不满足于仅仅在从感性事物到上帝逐步上升的那种层级宇宙观中看待事物,而是坚持认为感性的个体事物本身中就体现出绝对者的力量。它将新柏拉图主义教导的绝对者与各层级事物之间“坚守—产生—返回”(mone-proodos-epistrophe)的模式凝结为个体事物内部的存在结构。到了近代,如果说这种思想在康德之前(斯宾诺莎、莱布尼茨)还保持了浓重的独断色彩,那么自从康德系统演绎自我意识的枢纽性作用(1) 从笛卡尔开始到康德之前,许多思想家发现了这种作用,但那主要是在意识内部对这种作用的一种体验,很难说达到了康德的先验演绎中这种系统的证明。 之后,它便开始在人可以亲历亲证,可以由理性合乎逻辑地一环环连续构造的平台上,以更为坚实的步伐重新“开张”了。费希特的知识学、谢林的自然哲学和黑格尔的精神学说在这场运动中都扮演了十分精彩的角色。
在亨利希及其弟子们(“海德堡学派”)的影响之下,德国古典哲学研究界在最近半个世纪以来形成了一个比较普遍的共识,那就是认为德国古典哲学诸家之间并没有什么“从康德到黑格尔”的简单线性进展,而是形成了一种既具备家族相似性,又呈现离散状态的“星座”(Konstellation)。而本文关注的是,在这场运动中,如果像亨利希所说的那样,费希特的“原初洞见”是自我意识的一种前反思的自我意识,那么谢林使这场运动别开生面的利器——自然哲学——究竟肇端于何处?这一开端使得谢林自然哲学获得了何种特质?最后,如果这个开端具有重要价值,它在当前时代是否还应当和能够起作用?
一
站在康德的立场回顾近代的一些思想,我们会发现,自从笛卡尔坚定地以自我意识为立足点之后,意识内部的深奥结构再一次向西方人敞开了自身。在西方思想史上,如果说这个结构上一次开始展示自身是在前期基督教哲学中,其标志是以奥古斯丁为典型的教父们发现了下面这一点,即人类意志只有在人内心深处,而不是在任何外物那里,才与上帝意志发生最密切的交流,因而这个结构在当时是因应信徒与上帝交流和回返到上帝怀抱中这一需求而形成的;那么笛卡尔以降的近代思想家再次挖掘自我意识的深层结构,则是为了探明,站在自我意识内部来看,被理解的世界是如何建立起来的。既然是从自我意识内部看问题,那么看到的自然只能是理性所构造出来的世界图景了——这里不是已经埋下了“哥白尼式革命”的种子吗?如果单从这个方面来看,贝克莱的主观观念论和休谟的怀疑论其实并无任何荒谬之处,它们只是笛卡尔奠定的那个思路的深入推展罢了。后来德国思想发现,这一思路的要害是:与人打交道的其实不是事物本身,而是人所理解的事物,因而人实质上是在与自己的理解方式打交道。上述三人所不同者在于,笛卡尔对通过自我意识构造起来的这种事物图景的客观实在性基本持信任态度,(2) 至于他先前的怀疑,只是为了最终重建这种信任而进行的预备步骤。 而贝克莱与休谟则持否定或怀疑的态度。
众所周知,在休谟怀疑论和卢梭教育观的震撼下,康德在承接上述思路的同时,也要力保自我意识构造的那个世界图景的客观实在性。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讲明自我意识通达客观实在性的那个关键原点何在。康德给出的答案是能进行原始综合统一的统觉。统觉固然是主体的一种能力,但它不同于一般的心理活动,它是一种具有先验性质的能力,这种能力才是康德呼吁的“哥白尼式革命”的关键,因为它才能使我们通达主观表象与客观事物所共有的形式规定性,而后者才是康德所呼吁的“假定对象必须依照我们的知识”(3) 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15页。 的真正根据。换句话说,客体之所以符合于主体,绝不是由于主体可以对客体予取予求,而是由于主体在有意识地采取任何行动“改造”客体之前,就已经具有了和客体相同的形式规定性,这种形式规定性如宿命一般,是人类不得不置身其中的一种架构,它甚至是人类思考灵魂不朽、意志自由、上帝存在这些更高远问题的基本前提。一方面,主体只能接触到具有这种规定性的客体,因而贝克莱和休谟对于人类表象能力的局限的洞察是很深刻的;然而另一方面,客体也只能依照这种规定性而在这个世界上显现,这意味着主体所见的世界图景并非什么主观幻象,而是具有某种客观实在性的——尽管这种客观实在性并不足以使人直接通达事物本身(自在之物)。
本例中,中国法官所说的最后“陈述”是一个具有文化特性的词,译员为了消除被告的理解障碍,在口译时增加了必要的信息:“如果你对判决有任何要求和希望,你可以向法庭提出要求和希望。”在许多情况下,当译员一时难以找到对应词时,可以直接通过解释来调解。比如,翻译一个地名时,译员可以在保留原来的发音时,解释说“这是一个地方的名称”。这样的调解策略有利于保证各方沟通的流畅而不影响庭审的节奏。
费希特进一步探究了表象与客体之间的这种原初同一性的发生机理,极富洞见地提出,前反思的自我意识本身就是一种集生产与产物、行动与事态于一身的结构,它能有效防止反思的无穷倒退。(4) Cf. D. Henrich, Fichtes urspr üngliche Einsicht ,Vittorio Klostermann , Frankfurt am Main 1967. 这里无须详细复述他的这一思想。引起笔者注意的是,费希特一生提出的多个版本的知识学,从一方面来看固然表现出他越来越寻求突破自我意识,将他所洞察到的原初同一性推展至存在本身那里的宏愿,但另一方面,这也未尝不可视作自我意识立场的强大张力的表现。这种张力甚至大到了规定与束缚那种立场的批判者(后期费希特)的批判方式的地步。我们看到,当费希特在后期意图突破自我意识而进入存在本身之中时,他大体上是将早期知识学中“本原行动”的架构挪用到了绝对知识、绝对存在、纯粹之光等终极要素上罢了,比如他在1801年的《知识学的阐述》中就说,绝对知识既不是知识或主体性,也不是存在或客体性,而是使得一切行为与事件都能被设定的那种知识本身。(5) J. G. Fichte, Darstellung der Wissenschaftslehre, in: Ders., Sämmtliche Werke, Zweiter Band, Verlag von Veit und Comp, Berlin 1845, S. 13, 14, 54. 费希特毕竟不是谢林,这里不大可能发展出谢林式的自然哲学。
由上可知,覆盖决策系统(U,A∪D)的规则蕴含关系保持的一致集B就是一个满足RSθ,η(A,D)中规则在剔除A\B后置信度保持不变的条件属性子集。又由性质1知,RSθ,η(A,D)中规则在剔除A\B后覆盖值仍不低于η,因此,通过该约简,可以提取置信度不小于阈值θ且覆盖值不低于η的紧凑规则。由于规则蕴含关系保持的一致集或约简能够保持RSθ,η(A,D)中规则置信度不变,因此又可称其为规则置信度保持的一致集或约简。
而谢林则更强调前一方面。他在学生年代便已在柏拉图研究方面颇有造诣,就在相当程度上恢复了存在本身的问题,或者说至少是在近代语境下努力恢复存在本身的问题。康德留下的遗产固然可贵,但谢林援引斯宾诺莎与莱布尼茨的思想,证明人不一定只能局限在自我意识内部看问题。他看到,近代早期只有斯宾诺莎与莱布尼茨的体系才是从主体的本性(7) 谢林此时试图从他那个意义上的原初同一性出发规定主体概念,但严格来说他此时对自我意识的态度还比较模糊,不如几年后那么清晰。他在《先验观念论体系》中明确说道,自我意识不是一切存在的绝对原理,而只是一切知识的绝对原理,一切知识都以其为出发点。参见谢林:《先验唯心论体系》,梁志学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第23页。 中推导出客体的客观性的,(8) F. W. J. v. Schelling, Ideen zu einer Philosophie der Natur , in Der., Sämmtliche Werke, Erste Abtheilung, Zweiter Band, J. G. Gotta’scher Verlag, Stuttgart und Augsburg 1857, S.35.本文中该文献以下采用夹注,仅标注文献页码。 而这个本性并非单纯的主观思维,而是观念东西与实在东西的同一性。(S.35 f.)可惜斯宾诺莎并未进入到这本性的深处,而是立即迷失到我们之外的一种无限者理念中去了;(S.36)相比之下,莱布尼茨则突出了自我的本性这个要点,从而改进了斯宾诺莎的体系。(S.37)表面看来,好像谢林这里说的同一性就是康德和费希特从自我意识角度看到的那种同一性,然而无论从谢林对观念东西、实在东西极有古风的规定,还是从斯宾诺莎、莱布尼茨学说的唯理论性质,以及从历史上二人学说被德国古典哲学吸收的实际情形来看,都会发现谢林从二人那里继承的东西与自我意识哲学大异其趣。其实这种做法绝非谢林一时兴起而为之,而是他一以贯之的选择。亨利希与弗兰克便注意到,谢林最初是受到他在蒂宾根的老师启发,从康德那里直接发展出自己思想的,他在接触费希特知识学之前就踏上了另一条不同于自我意识的进路。(9) Siehe D. Henrich, Grundlegung aus dem Ich .Untersuchungen zur Vorgeschichte des Idealismus . Tübingen-Jena (1790-1794),Zweiter Band, Suhrkamp Verlag, Frankfurt am Main 2004, S. 1551-1699; M. Frank, “Reduplikative Identität”. Der Schl üssel zu Schellings reifer Philosophie , frommann-holzboog Verlag, Stuttgart 2018, S. 67.
二
4.3.1 有机井管理房 将管控器保护柜通过¢12膨胀螺栓锚固在管理房内墙面,输电线采用25 m2的铜芯线,将电线接入直径为75 mm的pvc管内进行保护。
那么以自我意识为基点的这一系思想的限度何在?自我意识这个基点形成它看问题的视角,而如果局限于这个视角看问题,西方传统的形式观中的一些要素就会被“过滤”掉。古代的“形式-质料”学说主张形式自身对质料有一种塑造成形与指引方向的作用,这种作用同时也被视作形式在质料中实现自身或质料从潜在状态趋赴其本质状态的运动过程。中世纪思想开始以人格主体的视角看问题,只不过这个主体不是理性之人,而是以上帝为终极目标的信仰之人——当然,上帝在某种意义上是终极主体,但人不可能具备上帝的眼光。此时上帝及其带起的信仰引领着人的生活方向,人如同古代时一样,只是整个生活秩序中的一份子,而不具有赋形的或引领的地位。近代意识哲学则不同,它的主体是理性之人。这样的人虽然貌似在探求一个不完全以其自身为转移的同一性之点(康德和费希特),貌似服从于一种高于其自身的崇高秩序(如康德的理念架构,费希特的绝对知识、绝对存在与纯粹之光),但却忽视了一点,即无论同一性之点还是崇高秩序,都依然是他站在自我意识的视角看到的,它们都以自我意识为预设前提(认知根据),而非相反。更准确地说,在存在的意义上,自我意识固然以更高的秩序为“悬设”,但在认识的意义上,自我意识始终是优先于更高秩序的。而这后一方面却是上述思路更强调的。(6) 在康德和费希特这里,该思路虽然意识到了前一方面,而且努力以实践哲学的形式(这是他们认为唯一合法的阐述形式)阐明它,但依然没有脱离自我意识这个基点。实践哲学在他们这里很可能只是以创造性行动之名反过来巩固了意识哲学的框架。从谢林《先验观念论体系》一书的结构和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精神”章中对道德世界观的批判来看,他们二人明确意识到了这个限度。
这种同一性的性质毕竟不同了。谢林对费希特相当不满,因为他认为费希特哲学仅仅是从主观意识方面在讲同一性,(S.72)他甚至判定,整个现代思想都是观念性的,因为它的支配性的精神是往主体内部走的精神。(S.72)在他自己看来,绝对观念东西不是个别人的什么想法,而是绝对思维(absolutes Denken)。(S.61)他又称之为绝对知识(absolutes Wissen),并说在这绝对知识中“主观东西(das Subjektive)和客观东西(Objektive)并非作为对立的东西结合起来,而是整个主观东西就是整个客观东西,反之亦然”。(S.61)这是相当深刻的一个思想。这里的主观东西和客观东西不能仅仅从上述自我意识哲学所说的表象与对象的意义上理解,因为谢林惯常的做法是将处于同一性关系中的“主体与客体”拿来和“形式与质料”对举,(S.62)他已经不仅仅从“我如何思维”和“事物如何对我显现”的角度考虑问题,而是一开始就通过自我意识这个枢纽进至“事物本身的形式与质料如何相互规定”的问题了。换句话说,谢林承认并接受从笛卡尔到费希特为止的一众思想家们对于自我意识的关键地位的揭示,他同样认为自我意识是世间极其高贵的东西,如果没有自我意识,人之异于禽兽者几希,根本不会像康德这样探究出原初同一性,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原初同一性只是自我意识所见的那样,不意味着自我意识可以独占原初同一性。谢林的立场借用康德的术语来说就是,自我意识虽然是原初同一性的认知根据(Erkenntnisgrund / ratio cognoscendi),原初同一性却是自我意识的存在根据(Seinsgrund / ratio essendi)。后一方面是决定性的,如果不预设原初同一性,那么自我意识作为认知根据的地位也不保了。不仅如此,谢林此话更丰富的含义在于,在原初同一性中主观东西与客观东西不是偶然、外在地被人发现了一些相同点或类似之处,而是整个地规定了对方的存在或认识,没有一方就根本不可能有另一方。比如谢林就莱布尼茨的个体性概念说过,“雅可比 证明,他(指莱布尼茨——笔者按)的整个体系都出自个体性 概念,又回归到那里。只有在个体性概念中,其他所有哲学所分离开的东西,即我们本性中的肯定性东西和否定性东西、能动的东西和受动的东西才原初地合为一体。”(S.37)德国思想关于个体性的这笔可贵的遗产,不绝如缕地流传下来了,谢林显然明确意识到了这一点,并主动接受和发扬了它。在他看来,每一个具体的事物都有肯定的、能动的和否定的、受动的这两个方面,没有前一个方面,后一个方面是无规定而散漫无归的,更不可能被认识;没有后一个方面,前一个方面是无法显现,也无所依归的。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万物都是两个对立本原的争执的产物。(11) B.-O. Küppers, Natur als Organismus .Schellings fr ühe Naturphilosophie und ihre Bedeutung f ür die moderne Biologie ,Vittorio Klostermann , Frankfurt am Main 1992, S. 56. 这便涉及原初同一性的动态发生性特征,谢林正是用这种特征说明万物的生成的。(12) 费希特知识学也描述了他眼中的原初同一性的动态构造过程,目前还不能断定谢林的这方面思想得自于费希特,因为他很可能在深入接触知识学之前就有了这一思想。 在他看来,绝对者是一种永恒的认识行动(Erkenn-tnißakt),是一种生产(Produciren)。(S.62)他将上述意义上的主体和本质当作这生产的生产者,将实在东西、客体,尤其是它们的形式,当作这生产的产物。(S.62)而本质与形式之间并非往而不返的关系,不仅本质可以化为形式,形式也可以被收回本质之中。——我们看到,谢林后来所说的根据与实存者、肯定哲学与否定哲学之间的关系模式在此已隐约可见。
此次黄麦岭集团党委开展“主题党日+”活动,对党员干部们是一次震撼心灵、激励前行的教育。全体人员表示,今后工作和生活中,要牢记《准则》、《条例》,慎独慎微,守住“底线”,不越“红线”,时刻警钟长鸣,处处自重、自律、自醒。要以革命先辈为榜样,学习他们艰苦朴素、甘于奉献、廉洁自律的精神品格,矢志不渝地践行入党誓言,要学思践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忘历史、不忘信仰、不忘奋斗、不忘前进,兴学习、强思想、激情干事业,为推进企业转型升级,提质增效,全面高质量发展而努力奋斗。
我们可以将这种原初同一性视作谢林自然哲学的开端。何以如此?这不仅仅是因为谢林极其强调这种同一性的肇始作用,比如谢林说过,“迈向哲学的第一步,以及没有它人们永远都无法进入哲学的那个条件,就是这样的洞见:绝对观念东西也是绝对实在东西,而且在绝对观念东西之外一般说来就只有感性的和有条件的实在性,而绝没有绝对的和无条件的实在性”。(S.58)这更是因为它才真正使谢林获得了一个不同于康德、费希特的基点,从这个基点来看,不仅自然哲学,他的整个哲学的布局都呈现出全新的样貌。简单来说,在谢林看来,自然哲学不是在先验观念论(如康德)的架构内部的一个领域,(13) 其实谢林也从不承认自然哲学是后来黑格尔的绝对观念论的一个部分。 比如康德那里与实践哲学相对而言的理论哲学,(14) 或者黑格尔那里与精神哲学相对而言的自然哲学。 而是与先验观念论并驾齐驱的另一个领域。谢林说,先验哲学与自然哲学“这两门科学必然是两种永远对立的科学,二者决然不能变成一个东西”,(15) 谢林:《先验唯心论体系》,第3页。 谢林终生坚持先验观念论之外的某个独立领域的存在,尽管“自然哲学”作为一个名号在他的中后期思想中似乎隐没了,但催生了自然哲学的那个开端,却一直在起作用。
不难看出,谢林自然哲学在内部层次和具体概念方面的这种特色,在根本上也是由他的自然哲学的开端决定的。正如前文所说,谢林虽然承认自我意识这一通道的可贵,但并不局限在自我意识的视角内,而是从观念东西与实在东西的原初同一性出发,以绝对者由本质化生形式、从形式复归本质的运动来解释万物的存在,这就必然会预设类似于斯宾诺莎实体结构的某种“大全一体”的宏大结构。因为我们能设想的世界上任何现实的观念东西、实在东西以及双方的规定方式(比如植物的本质生成其形式的方式,以及我们在该形式的规定下理解植物质料的方式),都必定是有局限的,而规定这种局限之为局限的,乃是作为整体的绝对者,以及——在间接的意义上——其他比该种观念东西、实在东西层级更高或更低的观念东西、实在东西。在这个意义上,谢林认为万物内在地是一个本质,万物之间的差异都只是非本质的、量上的差异。(S.65)比如关于自然界各个层级的运动,他便如此规定:重力是量上的运动,化学运动是质上的运动,机械运动是关系上的运动;与它们对应的三门科学分别是静力学、化学和机械力学。(S.28)又比如他的重力概念,明显就是绝对者的本质由天体凝聚成形开始,一直到最具内省特征的人脑形成为止的那整个运动过程中的一个环节,要规定这样一个环节,就必须在两重本原(观念性、肯定性、形式性本原与实在性、否定性、质料性本原,实即前文中所谓的观念东西与实在东西)相互作用的关系模式下进行探讨,而重力概念恰恰满足了这样的要求。
在这种体系格局之下,谢林自然哲学内部的层次和概念也呈现出鲜明的特色。值得注意的是,自然界与观念性世界各自在其内部又包含三个层次的统一性,谢林称之为三个潜能阶次(Potenzen)。比如谢林在《一种自然哲学的理念》中对自然哲学要探讨的三个潜能阶次的规定便是:普遍世界构造;普遍机械论(即共相化为殊相,或者由光向物体的运动);有机论。因此自然哲学的最高对象便是有理性的有机物,或者说人脑。而在具体概念的规定上,谢林的做法也颇不同于我们对这些概念的一般印象。比如重力、时间、空间等概念就是如此。我们知道,重力对于物质是至关重要的规定,它甚至比笛卡尔那里的广延更根本,因为广延更多的是一个空间规定和延展规定,而纯粹的延展(排斥力)实际上是不存在的。换句话说,单纯只有广延而没有凝聚性的物质是不存在的,只有重力才能同时将这两种规定性包含在内,即既包含了物质的排斥力,又包含了物质的吸引力。换句话说,只有重力才能保证物质既是它那种形式而不是别的形式,又能保证它在那里存在而不归于消散。这个意思用谢林的术语来说就是,重力是对空间的否定(negirt)(16) 这里实际上有“扬弃”的含义,而不是指对空间的绝对否定或消灭。 和对时间的设定(setzt)。(17) F. W. J. v. Schelling, Von der Weltseele, in Ders.:S ämmtliche Werke ,erste Abteilung , zweiter Band, J. G. Cotta’scher Verlag, Stuttgart und Augsburg 1857, S. 364.如果单纯只设定空间而不扬弃空间,那么我们最多只能保证物质的各个部分各自是那些部分,而不能保证它们构成同一个整体——物质。只有设定了时间,或者说只有每一个部分能一直保持为那个部分,一直与其余各个部分保持同样的相对关系,它们才能维持它们的整体——物质。那么反过来说,时间是什么?时间不是现成化的钟表刻度,而是存在的方式。从实在的一面来说,时间就意味着物质此刻是物质,下一刻还同样是那个物质,即便它发生变化,成了另一个物质,我们也能确定地指出它是由某A物质通过某种原因的作用而变为某B物质的;从观念的这一面来说,在我们这个世界上,时间是使得我们可以确定地将某种物质表象为某种形式(比如桌子、石头、灯光等等)的根据,如果没有时间,我们对任何物质的哪怕一刹那的表象也是不可能的。
而要进一步深入了解这两种哲学的关系,我们还得回到本质与形式的关系问题上。首先,谢林认为绝对者既可以体现为“本质化为形式”的运动,也可以体现为“形式回到本质”的运动。在绝对者中,当本质现身为形式时,便有了具备具体形式的客观事物,此时绝对者的主体性便化为具体事物的客体性;当形式收回到本质之中时,事物的形式来源于绝对者的主体性的情形便被把握到了,此时具体事物的客体性便被理解为绝对者的主体性。(S.63)这两种情形又分别可被视作无限化为有限和有限化为无限的运动,二者都是统一而完整的结构,谢林称之为统一性(Einheit)。在他看来这样的统一性一共有三种:除了上述两种之外,还有将这两种统一性统一起来的统一性。(S.65)谢林又将统一性称作绝对性(Absolutheit),并认为这三种模式在其相应的运动(本质化为形式、形式化为本质的运动,以及上述两种运动合为一体的运动)中都不会失去各自的绝对性。(S.64)三种统一性中的前两种分别对应于自然界(或称实在世界)和观念性世界(或称观念世界),(S.66)这两种世界又各自含有绝对者的体现:在实在世界中,绝对者隐藏于有限者中;在观念世界中,绝对者蜕去有限者的外壳,作为观念东西、认识行动而出现,此时事物的实在性方面被抛下,只剩下观念性方面被人把握。(S. 67)与上述架构相应,哲学体系便包含了两个方面,自然哲学探究的是第一个方面,即无限化为有限、本质化为形式的实在世界方面;(S. 66)很明显,先验哲学的任务便是探究第二个方面,即有限化为无限、形式化为本质的观念世界方面。
为了解谢林早期哲学体系的整个架构,我们再具体看看自然哲学与先验哲学(即先验观念论)的关系。为此首先要弄明白谢林关于相对的观念论与绝对的观念论的区分。所谓绝对的观念论,是指我们从理念的角度、绝对的认识行动的角度来看,由自然哲学与先验哲学构成的整个哲学都带有观念论的特征,这意味着这两种哲学都不过是绝对的认识行动(绝对者)的行动方式,只不过两种哲学的行动方向不同罢了;而那时人们通常说的先验哲学,即康德和费希特的哲学,只是与自然哲学相对而言的“相对的观念论”,(S.67)比如谢林就说过知识学只是相对的观念论。(S.68)
这一点表现在对体系原点的规定上便是,谢林将关注的焦点从康德、费希特那里主体(或表象、知识)与客体(或对象、存在)之间的原初同一性,转向了观念东西(或形式、肯定性东西、能动性东西)与实在东西(或质料、否定性东西、受动性东西)之间的原初同一性。他所说的观念东西(das Ideale / Ideelle)并非人在自我意识角度得到的主观表象,而更类似于古代意义上的形式概念;与此相应,实在东西(das Reale)也并非被表象的对象,而是由形式赋形的质料性东西。与康德和费希特那里类似,人必须通过自己的理性才能真正把握到这种同一性,“通过理性自然才破天荒第一次完全回复到自身,从而表明自然同我们之内认作是理智的东西本来就是同一的”,(10) 谢林:《先验唯心论体系》,第8页。 因此关于外部世界的一切表象必然出自我自身,(S.33-34)但这当然不是在自我意识哲学的意义上说的。
三
不可否认的是,德国古典哲学在近代语境下重新恢复西方核心秩序观的这场运动,基本上发轫于谢林对于原初同一性的独特规定。这场运动后来的主角是谢林与黑格尔两个人,只不过二人的侧重点有所不同:谢林将更多的精力放在对绝对者使世界发生并返回自身的设想上,力倡世界本身的形式结构,他不断尝试改进上述设想,最后达到的是肯定哲学这一惊人的思想成果;而黑格尔的思想结构甫一定型,便极少变更,他将重点放在了这一结构内部的所有范畴的思辨与构造上。——关于二人之间如何争论的问题,当然是一桩有趣的公案,然而相比于他们共同的思想史任务而言,这个问题是第二位的。
在这种情况下,谢林的工作就显得尤为可贵。谢林实际上是在德国观念论的语境下,重新恢复了西方文化中一个深厚的传统:由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及新柏拉图主义塑造而成的那种有着严格方向规定的动态秩序观。谢林使这个传统在德国观念论中重放异彩,并以其为主轴,整合了历史上许多思想遗产:(1)如果没有康德的先验哲学,谢林通过自我意识抵达原初同一性的这个思路是不可想象的;(2)如果没有斯宾诺莎和莱布尼茨的遗产,谢林超迈自我意识视角之外去重新定位原初同一性的做法恐怕很难成功;(3)如果没有基督教三位一体学说,(18) 谢林认为三位一体是一种比基督教更根本、也更古老的结构,参见先刚:《从“超神性”到“上帝”——略论谢林世界时代哲学时期的“神学”》,发表于《哲学门》2018年第2辑。本文暂且撇开二者孰先孰后的问题,将这一框架称作“基督教三位一体学说”。 谢林关于人格性上帝创世又吸引造物回归自身的思想图景,包括关于本质与形式这双重本原的学说,便无从说起;(4)如果没有古代秩序观,谢林关于形式与质料、观念东西与实在东西的相互关系,以及关于世界各层级之间产生与回返的关系模式的设定,更是无源之水。——然而谢林就是谢林,尽管有这些思想遗产在前,如果没有谢林的独创性思想努力,自然哲学和他的整个体系都是不可能的。
正如前文所说,近代理性虽然热情地向世界求索,却陷入了一个怪圈:人类以为自己在寻求世界本身的真理,殊不知在人类这种一往无前的求索态度面前,世界只会呈现出人想得到的那副面貌,换句话说,世界并未敞开其自身,近代理性从来只能在世界上得到它所能理解的,甚至可以说由它投射到世界上去的东西。康德首次挑明了这个局面,功莫大焉。但更深的问题在于,康德与费希特即便探知到原初同一性的极端重要性,只要他们拘囿于自我意识的立场之内,他们所见到的就只能是“表象 / 自我的设定行动”与“对象 / 自我设定而成的事态”之间的同一性,最多只能像后期费希特那样,在自我意识的基点上作出一种跨出的姿态,实际上却仍然以自我意识的行动模式去类比更根本的绝对者。这样一来,虽然康德与费希特都不同程度地意识到世界的目的论结构,对上帝、绝对之光念念不忘,他们的视角最终还是限制了他们对问题的看法和阐述。
这场运动对后世的影响不可谓不大,然而时代毕竟不同了,他们关于形式与质料、观念东西与实在东西之关系的核心思想,往往由于后世对于体系、绝对者乃至一切自身有效的秩序(而不是作为主体“必要的虚构”的秩序)的嫌恶,而遭到了忽视。后世学者更重视的是他们思想中可为其所用的一面,比如谢林自由学说中的质料主义因素,以及黑格尔关于承认、劳动、社会的一些说法,而将他们关于绝对者、精神、国家的论说弃之不顾。殊不知后一方面恰恰是他们学说的落脚点和归宿,是他们自己最看重的东西。
今后,只要在住宅小区内有固定场所,为小区居民或村民提供自行车维修、小家电维修、缝纫修补、管道疏通和卫生保洁等服务的,就可不办理营业执照,只要向所属居委会或村委会备案即可。
幸好我在街上。幸好?是啊,嘈杂的大街,不会引起怀疑。男人不在家,女人去逛街再自然不过。最初有几次,小涵在电话里就这样顺带着问他,你在哪里?为什么这么安静?他记得当时自己说,在会议室外的走廊里,老林在发言。还有一次,他让小涵的电话足足响了很久,一直等到他跑到饭店门外的大街上才接,小涵说,你忙什么呢不接电话?他说,会议要求手机静音,这会正忙着送领导呢。小涵其实也没什么要紧事,多是告诉他晚上临时有饭局晚些回去。
本文无意于就学术论学术,仅仅停留在学者们对谢林或黑格尔学说的研究范围内,讨论他们的研究孰是孰非。笔者关注的是一个不那么“学术”的问题:当今时代是否已失去了古典意义上的形式感,以及通过理解各种层次的形式的局限而不断提升人性的能力?
我们不妨以近年来风头正健的人工智能为例,略作讨论。在目前阶段,学界关心的是通过神经网络研究和深度学习研究(19) 这类研究和下文中说到的计算机语言的发展,其本身可能并无对错好坏之别,本文无意于妄加臧否。我们这里讨论的是将二者作为人工智能研究的手段时,是否有必要反思它们的界限的问题。 探讨人工智能会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会改变人类正常生活的问题,而科技公司关心的则是如何在可操控的范围内将人工智能的效用发挥到极致。这两个群体关注的仿佛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实际上是同一个问题:我们是否能在有利于人类的前提下,让机器做到人所能做的一切事情,甚至做到人所不能为的更多事情。按照这个思路,人工智能研究有着广阔的发展空间和极其美好的前景,因为计算机语言所能做的事情,远不只是用程序做几道计算题那么简单,它可能远超普通人的想象之外,因为基本上可以通过算法语言表达出来的、有技术执行路线的一切人类活动,包括人的一些极其微妙和细腻的反应,人工智能都是可以做到的,那只是个时间早晚的问题。
然而我们只要洞察计算机算法的本质,就会发现上述种种做法只不过是在结果的层面、技术的层面处理问题,都有意无意回避了计算机算法与人类思维的根本区别。人工智能通过将算法形诸于实际参与人类生活的独立行动者(机器人、信息集散与交换装置等),看似便利了人,实际上是在抹杀人类思维最可贵的东西。原因在于,计算机语言,无论是否基于图灵机层次上,都一定是通过算法来执行的。“便利”一定是在特定算法的前提下而言的,它实际上是该算法用以自我美化和自我强化的手段。比如我们如果只以是否合乎几何学上的整齐划一,是否具有所谓的“工业美学”来衡量一个村落的规划与建设,我们建造出来的村落可能对于建筑师、交通、物流、消费而言都是“便利”的,给人一种“生活方便了”的感觉,然而村落却很难入画了,它也失去了自然村落与居民之间那种生生不息的亲密氛围,用海德格尔的话来说,它便成了“无根的”(bodenlos)纯工具。但人类思维区别于人工智能的根本,在于人能反思各种形式(20) 算法是计算机化、人工智能化的形式。但笔者所说的“形式”并不仅限于算法这类可以由人设计和改变的形式,它还包括许多未被人意识到的形式,比如我能在这里坐下、呼吸、思考,这就预设了我身体的平衡与重力所共有、我的鼻腔细胞活动与空气所共有、我的思考活动与思维对象所共有的种种形式。算法或许可以扩展到后一类形式上,但那一定是思维对原初形式进行的反思,而不是原初形式本身。德国观念论早在费希特那里就展示过这种反思与本原行动的区别。 的局限,并突破这些局限,进行攀升。(21) 彻底唯物主义者——如《直觉泵》的作者丹尼特(D. C. Dennett)——往往主张将思维活动还原成人脑的活动,在他们看来,问题的关键不过就是计算机活动如何不断趋近于对人脑活动的原样重现,并在此基础上实现自主学习和自我改进而已。这种观点一上来就没有看到人类思维的上述根本特质。 相比之下,人工智能只能在给定的形式的基础上进行运作,包括深度学习时也是这样,因为即便这种学习也要遵循学习的算法这种既定的形式。人工智能科技如果不意识到自身的这个界限,无限制发展,人本身终将成为它急欲消除的最大障碍,因为人的种种反思、迟疑,人对意义的种种探索,包括许多“无意义”行为,必将被计算机语言视作有害无益的冗余。这样一来,事情很有可能发生戏剧性翻转:起初人们认为,人工智能的问题总不过是如何以其便利人类生活的而已,到最后人本身却成了妨碍人工智能发展的最后一个累赘,人本身成了最后一个不便利的东西。
由此可见,人工智能的本质是意图通过操控自我意识所认定的同一性形式(比如便利、可视化等标准),在给人造成“便利”的虚幻感觉的同时,达到生活的全盘算法化;而如果跨出自我意识之外,正视事物本身的原初同一性起点,那才是希望之所在。谢林哲学不仅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跨出自我意识之外而触及作为事情本身之开端的原初同一性的先例,还系统展示了世界不同面向、不同层次的各种形式,是一种真正尊重事情本身,也真正尊重人性的思想。虽然很难说这一思想能为当下生活中的问题提供什么直接的答案,但它至少告诉我们:生活可以是别样的,并非只有越来越深的算法化这一途而已。
A preliminary study of the beginning of Schelling ’s philosophy of nature
ZHUANG Zhen-hua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Xi’an 710119, China)
Abstract : While acknowledging the important function of self-consciousness, Schelling has transcended the perspective of self-consciousness, which is held firmly by Kant and Fichte. He defines the original identity as the identity between the ideal and the real, rather than that between representation and objects, and constructs his philosophy of nature on this basis. Therefore Schelling has both inherited the legacy of self-consciousness from early modern philosophy and revived the traditional theory of order in the context of German Idealism. For contemporary times, which is apt to ignore the capacity of the human thinking to reflect on forms, perhaps this type of classical theory of order could not provide ready-made answers to contemporary questions directly, but it has much value of reference.
Keywords : Schelling; philosophy of nature; self-consciousnes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中图分类号: B516. 3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7511( 2019) 05-0022-08
收稿日期: 2019-03-08
基金项目: 陕西省社科基金年度项目(项目号:2017C003)、陕西师范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项目号:16SZTZ01)、2016年陕西师范大学“优秀青年学术骨干资助计划”项目。
作者简介: 庄振华,陕西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责任编辑/张瑞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