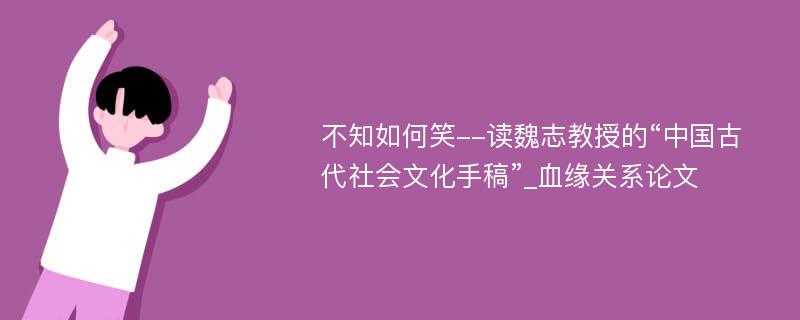
会心不觉拈花笑——读斯维至教授《中国古代社会文化论稿》,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古代论文,社会文化论文,教授论文,斯维论文,拈花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先秦史号称难治。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斯维至教授自20世纪40年代至今,孜孜不倦,皓首穷经,献身于先秦史研究。年前,笔者率新招收的先秦史研究生前往拜望。斯先生回答了学生的问题之后,问到学生的年龄。问罢若有所思,叹道:“为什么要研究先秦史呢?在西安,搞隋唐史不是满好吗……先秦史,我搞了一辈子,不能说没有什么成就,有一点点,算是开了个头。可如今80多岁了,头发白了,牙齿掉了,精神也不行了……”随着一声长叹,我们都沉默了。我脑中浮现新近读过的斯维至先生著《中国古代社会文化论稿》(台湾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997年出版),那是斯先生一生心血的结晶。其所反映的先生研究方向和方法的变化,则可以说是半个多世纪中国先秦史研究的一个缩影。
先生浙江诸暨人,1916年生,早年因家贫失学,以王冕、高尔基为榜样,刻苦自励;在那钟灵毓秀的名山胜水间,饱受优秀文化薰陶。时逢日本侵华铁蹄南下,先生辗转流亡成都,当过中学教师,又在四川省图书馆谋得一职。遂从四川大学蒙文通、徐中舒等先生研读先秦文献、古文字学,旁听文化人类学、民族学、考古学等。至1947年开始,陆续发表《两周金文所见职官考》、《关于殷周土地所有制问题》(《历史研究》1956年第4期,《论稿》未收)、《论庶人》、《说德》等论文数十篇。如台北杜正胜先生在《论稿·序》中所说,斯维至先生是“1949年以前养成的学者”。斯先生在40年代所发《两周金文所见职官考》、《殷代风之神话》等文,用金文、甲骨文材料探索殷周时代文化特色,有在古史研究领域大展宏图的气势。其成果多年来颇得海内外学人赞许、征引。与此同时,在中国史学界兴起一股新的史学思潮,这就是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前的人类史,大体分为按时间演进的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三阶段。其代表作是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郭氏此书影响甚大。斯维至先生在抗日战争初期读到此书后,开始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这是社会动荡中知识分子寻求思想指导的迫切需要,也是当时关心时代变革、国家命运和社稷民生的知识分子的普遍选择。
1954年郭沫若先生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新版的《引言》中这样说道:“掌握正确的科学的历史观点非常必要,这是先决问题。”观念成为第一性的,史实成为第二性的。这预伏了中国先秦史研究的不幸。
在50年代,斯先生也不能不将所谓“五阶段论”作为自己治史的指导思想,并希望为解答中国古史的分期问题(即上古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形态的更替问题)贡献力量。1956年,斯先生在《历史研究》上发表了《关于殷周土地所有制问题》一文。此文代表了他在经过50年代初期的“批判自己、改造自己”的政治学习之后对殷周社会的新的研究。此文未收入《论稿》,这里有必要简单说几句。
《关于殷周土地所有制问题》展示了斯先生深厚的学术功底和严谨的治学态度。但象当时所有讨论这一问题的文章一样,此文在方法上“以论带史”:以对一种社会进步规则的信仰作为研究历史的“先决”条件,这就注定了这样的劳动很难有重要的意义。斯先生此文一方面承认殷周是奴隶社会,一方面又认为平民不是奴隶,而当时的主要生产者又是公社成员——平民。这应该如何解说呢?斯先生不能说明白,只好留待下一步思考。今天回过头来看,斯先生留下这一疑点,正反映了他治学的严谨和史家的耿直。须知,直到90年代,才有很多先秦史专家倾向于认为殷周不是“奴隶社会”。
此后近20年,与整个先秦史学界一样,斯先生在学术上几乎陷入停滞状态。这主要因为有不断的政治运动的干扰,同时也是由于“分期问题”在理论上步入了误区。70年代末,斯先生发表了《论庶人》等几篇文章。这可以说是对50年代遗留问题的回答。《论庶人》论证庶人实为平民,改变了1956年认为被征服部族的人民是奴隶的看法,同时也批评了郭沫若将春秋时期的平民反抗贵族的斗争作为“奴隶起义”的错误。此文在80年代初曾被评为优秀论文并得到奖励。但先生自己,实际上已不很看重此事。他已经发现,用“两大对抗阶级”的观点来看待早期华夏国家,(尽管中间加了一个“平民阶级”)是不妥当的。在80年代全国性的“文化热”兴起之先,在“文革”尚未结束的70年代中期,斯先生已经开始重新以极大热情关注考古学和民族学研究。当他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和全力论证中国历史“五阶段”的苦闷中脱身,来到临潼姜寨遗址参加发掘,来到凉山彝族和版纳傣族村寨进行访问的时候,当他从地下二三米深的探方内挖出彩陶、石器或骨架的时候,当他从彝族“家支”组织中看到西周宗法制度的影子、从傣族份地制看到西周“井田”的遗迹的时候,那种难以言状的轻松愉快,是我们这一代史学工作者难以领会的。与《论庶人》一文相先后,斯先生发表《说室》、《释宗族》(《思想战线》1978年第一期,未收入《论稿》),说明商周时期社会基层组织是父家长家族,“室”为一夫一妻的小家庭。一方面,先生讲商周建国,“作为阶级压迫工具”,另一方面先生又强调,“国家就是父家长家族的扩大”。由此可见,先生对商周社会的看法,“奴隶制度”观念在淡化,血缘关系观念在强化。
笔者认为,以血缘关系为核心的社会,血缘亲疏是决定因素,由此形成权利不同的多等级的阶梯;以阶级关系为核心的社会,主要以人们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职业关系、产品分配上的关系以及地域户籍关系等作为人际关系的依据。应当说,以血缘关系为核心的社会与“奴隶社会”具有绝然不同的思想观念和文化特色。如果不注意区分,只会把问题复杂化。
论证这一时期是“奴隶社会”的困难,还体现在对于“国”“野”关系的理解。在《中国古代国家的形成》中斯先生说到:“我们认为,国与野的划分,就是我国古代国家第一次阶级的划分。”“但是无论国人或野人,仍是以血缘关系来划分的,而不是以财产多寡来划分的。这标志着我国古代国家形成中的特点。”“野人、庶人,并不是奴隶。因为一般来说,他们仍旧有家属子女,还保留着公社,因而有一份私田和工具等等。”既是“阶级关系”,而野人、庶人又不是奴隶,那么,这时是不是奴隶社会?斯先生未能冒然断言。依我们今日看来,既然以血缘关系来划分,就不是两大对立阶级意义上的阶级关系,就不应以“奴隶社会”来硬套。纵观先生书,《论庶人》中“庶人不是奴隶”似是斯先生论证商周社会形态问题的中心。然而,就在笔者准备撰写书评的时候,1999年3月3日下午,斯先生来电话,郑重地告诉笔者,他认为,《说德》一文可以概括全书的主旨,是贯穿全书的红线。在电话上,先生说:“《说德》发表之后,此问题仍时常萦绕于脑际。读书愈多,愈信‘德性’之说为不易。”“孔子说:‘中庸之为德,其至矣乎!民鲜久矣!’,到战国时,法家、道家都离开了‘德’,儒家思孟学派则追求这种‘至德’的境界。”以上是先生电话叮咛的原话,笔者照录。《说德》是斯先生向他40年代开始的先秦文化研究的回归,是先生如实地把商周社会看作以血缘关系(既先生文中的“德”)为核心的社会的标志。
《说德》发表于《人文杂志》1982年第2期。此文抓住了以血缘关系为核心的那个社会最本质的东西。先生认为,“德”为生、为性。《左传》隐公八年“天子建德,因生以赐姓,祚之土而命之氏”,此可证“德”与生育不可分,“德性”即由血缘关系所决定的族姓特点。《左传》僖公二十四年又有“太上以德扰民,其次生生以相及也”一语。太上,斯先生认为指五帝时代,以德扰民即以血缘关系为纽带建成氏族社会。先生发明德之本义为性,以此读《论语》,颇多新解。如解“乡愿,德之贼也”,说乡愿扭曲了人的本性;解“凤兮凤兮,何德之衰”,认为德与图腾联系在一起,实在是李玄伯“德为图腾的性质”的最好的证明。先生此文还揭示了“德”——“道”——“理”三概念演化的过程,从而贯通了上下3000年的中国哲学主流的最高概念,发前人所未发;其中深意,值得我辈后学探讨若干年了。
在1995年发表的《中国古代国家的形成》一文中,斯先生有这样一段精彩的论述:
我们认为,等级和阶级是两个不同的历史概念,即古代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以前)重视等级而很少使用阶级。在我国,阶级一词可能是由西方传入的。等级是因血缘关系来决定一个人的社会地位及其权利的,因此它是世袭的的、身份性的,而阶级是根据一个人占有生产资料的多少或有无来决定的。
这段话,是斯先生对中国古代社会认识的升华,标志着他向文化史研究的回归。当然这种回归不可能一步到位。比如该文中他引用《左传》昭公七年芋尹无宇所说“人有十等”一条时,先生说:“因为古代只有等级概念而无阶级概念的缘故,很难说清。假如我们一定要把它们‘换算’成阶级的话,那么,我们勉强可以把我国古代社会划分为三大阶级,即一个贵族阶级,包括天子、诸侯、卿大夫和士;二是平民阶级,包括庶人和工商;三是奴隶阶级,包括皂、舆、隶、仆、台等。”其实,斯先生多年来论庶人、释奴隶、研国野,“一定要把他们‘换算’成阶级”,都是很“勉强”的。相反,当他一旦抓住血缘关系这根“红线”,让先秦史研究回归于文化研究,斯先生立即才思泉涌,左右逢源。这些“才思”不仅给后学以丰富的启迪,亦令先生自己振奋,重新立起雄心壮志而不知老之将至!1987年,斯先生在给《中外历史》杂志当年第2期写的一篇自我简介中,情不自禁题诗一首:
皓首穷经岁月长,云蒸霞蔚书斋香。会心不觉拈花笑,正是青山照夕阳。
拈花微笑,典出佛教传说:世尊在灵山会,拈花示众,唯迦叶领会,破颜微笑。此乃禅宗所谓以心传心之根据。(见丁福保《佛学大辞典》,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688页)笔者认为,先生此处之“会心,应是与其半世纪前的老师蒙文通、徐中舒等神会。笔者比斯先生小近30岁,是60年代毕业的大学生,但也亲历“文革”前后史学思潮的变幻,也经历从“经世致用”的史学研究到民族文化底蕴的探求这一过程;当拜读斯先生《论稿》,从中看到老一辈学者探寻真理的艰难历程,看到先生踏实的步履时,尤其是在读到《说德》等处的勇敢的笔触时,不由自主地,随时发出会心的微笑。
如今先生年过八旬,然而仍在敏捷地思维,探索不止。想到在“文革”之类运动干扰下,我们曾困惑多年;在商品经济大潮冲击下,我们又几度傍徨;年轻的史学工作者,似应当从斯先生身上得到某种启示。我们深感我们民族优秀文化的承传,有赖于一代又一代史学工作者前仆后继的努力。笔者以此文示诸研究生,年轻人亦深以为然,似有所悟。由此可谓三代学人皆为之会心而笑了。
标签:血缘关系论文; 文化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先秦文化论文; 古代社会论文; 先秦历史论文; 读书论文; 社会阶级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