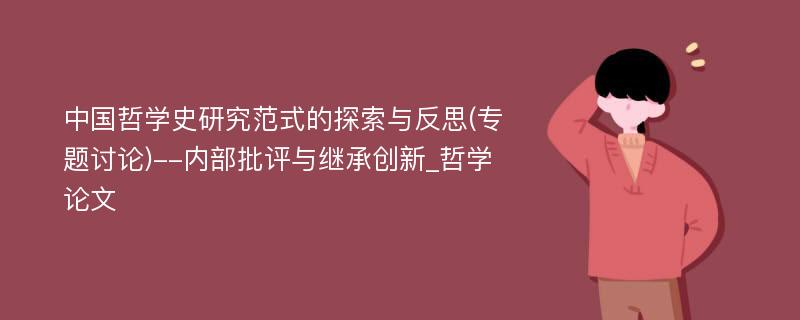
中国哲学史研究范式的探究与省思(专题讨论)——内在式批判与继承性创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专题讨论论文,范式论文,中国论文,史研究论文,哲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主持人:郭齐勇
[主持人语]目前,我们对于中国传统哲学自身的特性以及治中国哲学史的范式和方法,仍处在摸索之中。我们应当有一种自觉的自识,即努力发掘中华民族原创性的智慧与古已有之的治学方法,同时借鉴国外的治学方法,加以创造性转化,目的则是创造性地发展中国的哲学史研究。我所主张的方法论是一种“谦虚”的方法论。所谓“谦虚”是一种“同情的”、“客观的”理解,是“以继承为前提的创新”和“弱势或软性的诠释”。徐洪兴主张研究中国哲学首先是取法要正,即对中国哲学正视和正说,从正面来研究我们先人的思想,而不是带上各种各样的“眼镜”。潘德荣提出中国哲学史研究中的“经典诠释学”方法,这是对理论的出发点及其整个发展历程的反思,这一反思是在一个新的、更为广阔的视野中进行的,因而包含着某一理论原本所不具有的新因素。陈少明提倡中国哲学史著述中的反思性方式,即在叙述古代哲人的思想成果的同时,把哲学思考的方式也带给读者。上述观点是这组专题讨论的主要内容,作为一种抛砖引玉的初衷,希望关于中国哲学史研究范式和方法的讨论,能够像陈少明所言,当有人以西方哲学为范本在知识形态上批评中国哲学不够哲学时,有志于当代中国哲学事业的同道对此应当有自觉的反省,即通过我们的积极探索,使中国哲学史的著述不再仅仅是一个展示古代思想遗产的成果,更应是全力推动现代哲学发展的思想力量。
[中图分类号]B01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7071(2009)02-0036-10
在中国哲学研究中,凡涉及中国哲学史的方法论,必然离不开“理解”与“批判”、“继承”与“原创”、“传统”与“现实”等关系问题。笔者所要强调的是:所谓“批判”,应是在全面深入理解基础上所作的内在性的批评,而不是毫不相干的外在批评;所谓“原创”和“创新”,不应是一味追求标新立异或剑走偏锋,而是在真正全面继承的基础上所作的开拓,是扬弃(既保留又克服);弘扬传统并不意味着脱离现实,而是调动并创造性地转化传统文化资源,以其中的某些因素介入、参与、批判、提升现实,促使传统与现代的互动。
一、全面深入理解基础上的内在性批判。有的所谓“新批判主义者”自命颇高,所论却每每隔靴搔痒,偏失过当。因为批判应是内在的,不是随意性的、外在的、不相干的,更不是无知或偏见。
刘述先十分强调内在的探讨与内在的体验,他认为必须有深刻的、同情的了解才能做好哲学思想史研究,而同情的了解要靠相应的才具。他说:“不只鉴往以知来是人类学习的一个最大的泉源,而且客观地了解别人的历史以及自己的历史,才能训练我们自己培养成一种现实主义的态度,不把自己的行为建筑在主观的空想、情感的反映与错误的估计之上,这样当然会产生比较好的效果。……要了解一家哲学,我们必须要了解这一家哲学产生的时代和文化的背景是什么,所感受到的问题是什么,所提出的解决问题的方向是什么,独特的哲学心灵尤其需要独特的处理,庸俗的眼光未必能够了解崇高的哲学的境界。狄尔泰说,只有一个诗人的心灵才能够了解诗。同样,只有一个哲学的心灵才能够了解哲学观念的意义。而我们在评价以前,首先必须有深刻的同情的了解,而后再加以批评,这才可能是比较深刻的批评。”“缺乏同情的了解是研究传统中国哲学的一大限制,而时代气氛不同,尤其使我们难于领略过去时代的问题。……故此研究思想史贵在作深入的内在的探讨,外在的论议是其余事。从这一个观点看,胡适与冯友兰的哲学史都不能够算是深刻,因为它们不能作足够的内在的深刻的讨论的缘故。大抵在中国哲学史上,以佛学与理学最不容易处理,以其牵涉到内在的体验的缘故。如果缺乏体验,根本就看不出这些东西的意义。入乎其内,而后才能出乎其外,这是研究一家哲学的不二法门。要了解一个哲学所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着手的方法是什么,所根据的经验基础是什么,这样才能看出这一哲学的优点与缺点所在。”[1](P221-223、224-225)刘述先认为,由此我们才能理解古人的陈述与陈述背后的洞识,显发古人思想中所潜在的逻辑性,使其具备与内容相适应的理论结构。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批评精神和思维训练,如何解决批判精神的缺乏的问题?韦政通认为:“必须培养合理的怀疑态度和同情的了解及客观研究的能力,还要具备中国哲学以外的广泛知识。有了合理的怀疑态度,才能发现问题;有了同情的了解的能力及客观研究的成果,才能提供批判的基础;具备广泛的知识,不仅可以发现中国哲学内涵的限制,同时也有助于发现原有哲学的新的意义。”[1](P28)可见,要真正做到内在性批判是非常不易的,没有同情的了解的能力以及客观研究的成果,就失去了批判的基础或资格。那些以西方的框架或自以为是西方的、实际是自己的某些想当然,以及用简单粗暴的方式来宰制、肢解或强加给中国哲学一些东西,那种没有经过耐心细致的缜密功夫从中国哲学家或思想系统的内在理路出发作出梳理,却先在既定地把中国哲学思想(特别是儒学)执定为粗糙、落后和保守,这种所谓的批判与中国思想文化是不相干的。韦政通曾提出了一个难题,即如何既有概念明晰的严谨理论又能保存生命体验,不丧失传统哲学的精神?他说,实际情况是,愈有思辨能力的人,离体验愈远,在这个连人格都被市场化的时代,如何唤起中国学者的道德实践的愿望?缺乏这种愿望又如何去体验传统的内圣之道?他认为,批判精神及能力、思想训练等,应当是徐复观所说的思辨与体验的兼资互进。当然,关于思辨与体验的互济,在徐复观之前,熊十力论说最详。其实,我们需要的批评精神和思维训练,应当基于孔子所说的“四毋”:“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2](《子罕》)“先读懂,再批评”或“先理解,再批评”,应当是最起码的要求。
二、全面真正继承基础上的创新或原创。我们讲创造性诠释,不应理解为强势的诠释。我把诠释分为两种,一种叫强势的(硬性的)诠释;另一种叫弱势的(软性的)诠释。我主张弱势的(软性的)诠释。因为哲学家、哲学史家或诠释者个体,都是有限性的动物。面对无限的自然、社会和人,面对纷繁复杂的历史人物、事件与思想世界,作为现代解读者的个人在一定阶段凭其经验与理性所理解的内容,因时空环境的变化,极有可能完全或部分地不相应。我们不一定比古人更有智慧。有些事比前人看得清楚,有些事不一定比前人看得更清楚。我们今天所理解的自以为清楚的东西,过一段时间,当我们的知识、经验、才干、体验更丰富一些后再去理解,又会得出不一样的结论。因此,我们不能把话说绝。我们特别要从一百多年来过分抬高了的达尔文主义、黑格尔主义的思想中超脱出来。单维的进化论、进步观助长了现代人的盲目自大,以为历史上的哲学家与哲学思想(特别是中国的)都不如我或我们,可以由我或我们去任意评说、宰割。黑格尔不容忍哲学体系之间的悲剧式的斗争、不可调和的对立和相互易位,因为他是一个绝对的逻辑主义者,他所恪守的原则是哲学体系的历史连贯性必须服从于辩证逻辑范畴的连续性。按照这一原则,后来的哲学必定高于先前的哲学,这当然是违背中西哲学史史实的。要之,在黑格尔那里,绝对精神及与之相应的哲学是最高的、无人企及的。几十年来,哲学史工作者习惯于给古人找时代与思想的局限性,这当然不错,问题是为什么要找,如何去找,在什么基础上找,够不够资格找,却一定要想清楚。在找的时候,是不是也要自省自己的局限性,例如所论对象的材料与相关的材料读了没有?读懂了没有?读完了没有?设身处地地了解了没有?
我所主张的方法论是一种“谦虚”的方法论。所谓“谦虚”,或前面所提到的“同情的”、“客观的”理解,以及“以继承为前提的创新”、“弱势或软性的诠释”等,这不仅是态度,而且是方法。徐复观说:“我所说的‘谦虚’,主要是对材料而言。先让材料自己讲话,在材料之前,牺牲自己的任何成见。我越到晚年,越感到治思想史的人的第一责任便是服从材料。‘自信’是在深入到材料去以后,对任何与材料不符,但被人视为权威的说法,都敢站起来替材料讲话。对任何权威的说法,都敢清查他的底细,穷根究尾,弄一个水落石出。这是面对知识的堂堂正正的人生态度。”[1](P169)
哲学思想的创新或原创不是空中楼阁、信口开河,不是不要理论与历史的基础,故没有深刻理解哲学经典的人,对哲学经典没有下过工夫的人,不可能有真正的哲学创造。哲学思想的创新或原创当然不能脱离时代,可能恰好是缘于时代的、现实的问题的启发、提问或挑战才应运而生的,但真正能从哲学理论上回应这些问题并作出理论建树的,一定是有其深厚理论与历史修养的人,而且是谦虚的人,不说大话,不自以为是权威,不搞文字游戏。在一定意义上说,创新离不开深入地理解传统,离不开真正的继承传统。原创不是踢开传统,原创恰恰源自传统。
三、强调读经典,主张弘扬传统文化精神并不意味着没有现实感、不关注现实或脱离现实,而恰好包含着批判现实,批判现代性的负面与偏弊,批判时俗流弊,批判“五四”以来相沿成习的某些误解。传统儒、释、道等思想的转化,主要是通过生活化的渠道来浸润。我们不要求所有的学者都具有强烈的现实关怀和忧患意识,在个人生活上、人格养成上、生命体验上身体力行,与所学、所研究、所提倡、所主张相一致或契合,但要求中国哲学特别是儒学学者,在言行一致、经世致用方面力求做得更好一些。近些年,我在组织有关“亲亲相容隐”的讨论中,是有强烈的现实关怀渗透其间的,讨论所针对的就是缺乏起码的思维训练的、胡子眉毛一把抓的、不讲分析的、对中国文化的教条主义的、强词夺理的方式,所针对的是现行刑法制度某些条文的改革,反思“文化大革命”,捍卫人权、亲情权、隐私权。这看起来似乎是在“发思古之幽情”,其实恰好是传统与现代的互动,是一个更具有现代性的论域。近些年来,我提倡的国学教育、让“四书”的内容更多地进入中小学课堂等,也是针对现行教育的一些弊端,针对知性教育的片面膨胀、道德教育的空疏不实的。
最后,我们再回到“思维训练”、“思想力”的养成问题上来。姚鼐把中国学问分为义理、考据、词章三大部分,其实这三者是统一的,当然,义理统率考据、词章,是考据、词章的灵魂。没有义理的考据是盲目的,没有考据的义理是空虚的;没有义理的词章玩物丧志,没有词章的义理行之不远。徐复观说:“某人的思想固然要通过考证(包括训诂、校勘等)而始能确定;但考证中的判断,也常要凭思想的把握而始能确定。……前后相关的文句,是有思想的脉络在里面的。这即说明考证与义理在研究历程中的不可分割性。就研究的人来讲,做考证工作,搜集材料,要靠思想去导引;鉴别材料,解释材料,组织材料,都是工作者的思想在操作。而‘思想力’的培养,必须通过了解古人的、他人的思想,而始能得到锻炼、拓展、提升的机会。所以思想力的培养,是教学与治学上的基本要求。岂有不求了解古人的、他人的思想而能培养自己的思想力?岂有没有思想力的人能做考据工作?”[1](P170)他主张通过了解古人的、他人的思想来锻炼、提升、培养“思想力”,尤其要学会把握古人思想的内在脉络,这才是批判的基础。
我们都需要以他者的视域来观照自身,也只有以他者的视域,在文明的比较之中,才能看清自己的缺弱和优长。当然,用庄子的说法,在以物观之、以俗观之、以差观之、以功观之、以趋观之的基础上,还要上升到以道观之的意境。
梁启超的“新民说”提出之时,中国积贫积弱,欧风美雨,坚船利炮,列强宰割,中国社会解体,中国文化处于危机之中。开发民智的启蒙无疑具有伟大意义。但随之而来,全盘西化成为主潮,似乎中国百事不如人。“文化决定论”成为思维定势,中国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成了替罪羊,中国“国民性”完全成了负面的东西。清末民初以来,对自家文明传统的非理性的践踏、毁辱成为主要思想潮流。一百多年过去了,对此需要重新检讨。中国崛起,文化自觉显得更为重要。
现在的思维训练、现代人思想力的培养,尤应注意以下几个方面:学会思考或反思当下的问题,学会思考或反思流俗,反思启蒙,反思习以为常,反思思维定势,反思一百多年来时髦人士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反思成见,反思科技文明,反思商业化,反思现代性,反思全球化,反思文化工业或大众文化或媚俗的文化与官场文化,反思功利时代,反思金钱与权力的拜物教,反思人类中心主义,反思今天的评价体系,反思富而后不教、富而不好礼,反思对根源性、对神圣性、对敬畏之心、对终极价值与安身立命之道的解构或消解,反思对列祖列宗创造并传承下来的文明遗产和中华文化精神不抱敬意的态度,重建崇高,重建信念与信仰。我们尤其要反思教条主义地肢解传统的方式,反思全盘西化,当然更要捍卫宪法赋予各色人等说话的民主权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