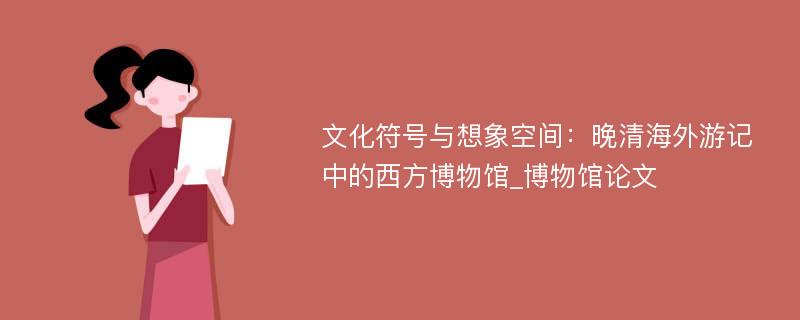
文化符号与想象空间:晚清域外游记中的西方博物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域外论文,晚清论文,博物馆论文,符号论文,游记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18X(2012)03-0109-05
较之一般的“游”而言,晚清时期的“域外之游”已失去了古典时代的优游姿态,行旅主体乘槎远行,将自我嵌入迥异于原来文化秩序的陌生空间,在地理、文化的越界过程中,开始追寻西方强盛的秘密。这一变化与书写主体有关,也与变局的时代境遇有关,晚清的域外游者,多为随洋翻译、自由知识分子及出洋使臣,如同为翻译的林鍼、罗森,同为政治逃亡者的王韬、康有为、梁启超,同为使臣的斌椿、志刚、郭嵩焘、曾纪泽、张德彝、薛福成等。他们留下了大量的域外游记,据清人王锡祺《小方壶斋舆地丛钞》所录,晚清时期约有90卷、几百万字的域外游记文本行世;内外交困下,这些游记书写重在探其利弊、考政求学,从古典式的山水吟咏转向经世致用式的社会记录,其中所呈现的西方经验或可成为我们触摸中国近代主流知识分子文化心理嬗变的重要文本。
将晚清域外游记作为我们研究晚清知识分子文化心理裂变的重要文本,其原因可以从费正清的论述中找到答案:“总的来说,外国入侵的历史是令人不愉快和蒙受耻辱的历史。此外,直接了解这种情况的只是统治阶级、文人和官吏中的少数人物,至于平民,特别是与外国人共事的人,则不习惯于把他们的看法和经历记录下来留给后世。所以我们在考察中国人对西方的看法时,不得不主要依靠上流社会学者们的著作;这些人受过中国经典学说的彻底熏陶,因而最不可能背离对待外国人的传统态度。”[1](P141)的确,从创作主体而言,晚清涌现的出使游记创作主体多是政治家、外交家、翻译官,他们处于知识阶层的精英范畴,受过中国传统经典的彻底熏陶,具有中国传统的文化身份,这种文化身份就如斯图亚特·霍尔所指出的是“一种共有的文化”,“提供了变幻的历史经验之下稳定不变和具有连续性的意义框架”。[2](P209-211)由于出使游记的创作主体社会身份一致、文化心理结构类似、创作背景相同等因素,我们能“在一个更坚实的基础上研究集体心态,可以使我们把握传统思想和行为方式的转变,以及新的心态的出现”[3](P92)。这使得域外游记堪称研究晚清历史的重要文本资料。
阅读这批浩如烟海的域外游记资料,读者不难发现,初见沧海之阔的晚清游者对西方博物馆有着浓郁的兴趣,几乎每位游者都会在游记中浓墨重彩地记录博物馆这一具有现代意义的文化符码。据《走向世界丛书》收录的《漫游随录》所录,王韬曾7次游历英法两地的博物馆,并在游记的23、24、28、38等章节中,以专章的方式对博物馆进行精雕细琢的描述;李圭的《环游地球新录》共4卷,其中第1卷用了约八章的文字对美国的博物总院以及机器、绘画、耕种等专馆进行了分门别类的介绍;郭嵩焘在《伦敦与巴黎日记》中,竟有24处以细致的工笔写到了西方博物馆;薛福成自称“余自香港以至伦敦,所观博物院不下二十余处”[4]。可见,对于晚清域外游者而言,博物馆似乎是不可不去之地、不可不写之所。
如此,我们不禁要追问:在变局之中产生的晚清域外游记,为何要反复书写西方博物馆?在书写中,作为游者的主体发现了什么?凸显了什么?西方博物馆是如何作为一个承载了多重文化意味的想象空间而被形成的?最终,有关博物馆的认知对晚清知识分子的文化心理图式带来了怎样的冲击?
一、西方博物馆:现代世界的认识空间
晚清士人笔下的西方博物馆是现代工业文明语境下颇具现代象征性的展览机构,大约17世纪晚期,它最先诞生于工业文明率先兴起的英国,其雏形是对英国自身历史器物的搜集与展示;1753年大英博物馆建立,成为全世界第一个向公众开放的大型博物馆。此后,西方不少国家纷纷仿效英国在本地开设博物馆,并以此作为肯定自身现代文明的重要表征。关于博物馆在西方的兴起,有诸多解释,从寻求自身正当性这一解释视角而言,西方为了争取他者对于西方的内在认同,建立西方秩序的正当性,需要一套具有说服力的修辞手段,博物馆不啻为一个堪当重任的有效工具,它有关地理、历史、文化的展示饱含政治能量,不仅折射了建立者的内在欲望,也有效地建立了一套有关现代世界的认知模式。
博物馆中有关历史、文化的开放式展览无疑对徘徊于西方文明外的晚清人产生了强烈触动,几乎每位出游者初次发现博物馆这一新质事物时,都持正面认同之意。1866年,张德彝陪同大臣斌椿首次出使西方,在谈及西方博物馆时,他不乏震惊地将其冠之为“炫奇会”[5],王韬则将之首译为“博物馆”这一溢美性称呼,并在《漫游随录·出游小志》中盛赞英国博物馆“无美不具,无奇不备,博采广收,分室收贮”[6];黄遵宪《日本杂事诗》(广注)也为博物馆做了褒扬性定义:“博物馆,凡可以陈列之物,无不罗而致之者。广见闻,增智慧,甚于是乎赖。”[7]这一具有强大诱惑力的西方场所被晚清游者反复论及,不仅在于它“无美不具,无奇不备”的直观冲击力,也与博物馆之博而带来的多元化现实世界有关。
当晚清游者乍然进入“殊方异物,珍奇瑰玮之观,无不毕至”[8](P479)的西方博物馆,其场域中具有条理性与安排性的历史的、地理的事物纷至沓来,带来的是关于世界多元化的冲击力量,是迥异于天朝帝国凝滞心性的世界认知模式。郭嵩焘游巴黎博物馆,见其中古钱、图画、钞书等藏品数量浩繁、“远及各国”,游肯辛顿博物馆,见其中有仿制的世界各地房屋,相形之下中国自视甚高的传统建筑却不免相形见绌:
其前数院,凡各国所建之坊,若石幢,若门楼,若亭,若石楼,奇丽宏壮者,皆仿为之。……巨壁张画一幅,极四大部洲最高房屋罗绘其中,以礼拜堂为最,伦敦已有高至五十丈者。南京琉璃报恩塔,其高得半而已。[9](P186-187)
在博物院,郭嵩焘见到了世界各地的建筑仿造物,它们“奇丽宏壮”显然不逊色于中土,其中伦敦的礼拜堂比南京的报恩塔高一倍以上,在建筑文明多元化的展示中,中国不过是其中并不出色的一名。博物馆之博让初次走向世界的晚清人莫不有“井底之蛙”的慨叹,薛福成说:“所观博物院不下二十余处,常有《诗经》所咏、《尔雅》所释、《山经》所志鸟兽草木之名,为近在中国所未见,及至外洋始见之者。”[4](P100)这种外在的观看刺激作用于郭嵩焘、薛福成等人的心理结构,使得其认知模式发生了相当转变,薛福成曾指出晚清正经历由“华夷隔绝之天下,一变为中外联属之天下”[10](P555)的变局。
这种遭遇西方博物馆而恍然对近代世界格局产生重新认知的心理转折,也同样发生在口岸知识分子王韬的身上。王韬见到大英博物馆丰富的藏书典籍,不禁为之折服,此博物馆以浩瀚的藏书彰显了毫不逊色于中华典籍文化传统的文明深度,被引以为傲的中国经典不过夹杂在别国的浩茫书海中,成为各国文明的一部分:
院中藏书最富,所有五大洲舆古今历代书籍,不下五十二万部。……各国皆按架分列,不紊分毫。[6](P101-102)
西方博物馆不仅收藏了浩繁的中国典籍而且包揽了五大洲的古今历代书籍,在重楼叠嶂的藏书室中,中国典藏不过成为按架分列的其中之一,这对惯于陶醉在“中国天下”幻觉中的晚清人而言,不能不是迷梦觉醒的开始。对于晚清之前的中国而言,基于中华文化共同体之上的天下意识作为集体性共识源远流长,古典中国对具有神圣性的中华文明充满信心,借此认定中国位居中央、为天下文明的中心,然而,在博物馆中所遭遇的现实境遇,让王韬等晚清知识分子得以打破文化迷梦,从世界的角度来重新认识中华文化在世界中的位置,乃至王韬发出这样的感叹:“盖其国以礼义为教,而不专恃甲兵;以仁信为基,而不先尚诈力;以教化德泽为本,而不徒讲富强。欧洲诸邦皆能如是,固足以持久而不敝也。”[6](P127)在与西方文化的亲密接触中,王韬具体而微地感受到西方文化毫不逊色于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
对于这批初次走向世界的国人而言,世界之大正以平铺的方式向他们席卷而来,他者的文明力量正以毫不逊色甚至优越的形态在对比中展开。博物馆之博首先击碎了晚清游者的天下意识,展示了一个平行的广大世界,这是一种扩散的空间开拓,博物馆中关于世界各地的器物陈列、建筑展览,形成了一个可以直观理解和传递现代世界意识的“认识空间”,有效打破了郭嵩焘等晚清士人的先在视界与所谓的天下构想,让他们在集中而对比强烈的纷繁事物中,被动接受了这个比中国天下要广大得多的世界,用罗伯逊的话来说就是,博物馆改变了中国的“世界意象”,西方博物馆构建的世界多样性加深了晚清人关于他者与自我的再度认识,从而发现独特的“这一个”中华文明不过是普遍文明中的“一个”。
二、西方博物馆:“西方”与“东方”的形塑空间
博物馆的功能在于向人们提供知识,博物馆因此常被笼统地说成是一个“知识场所”,然而,重要的不只是博物馆提供了知识,更重要的是博物馆提供的是什么样的知识。博物馆作为西方塑造自我的一个工具,在昭示世界之大的同时,也成为一个构建中国他者与西方自我的重要文化场域。其中,博物馆对西方历史及西方当代器物的连续性展示,从线性的时间层面构建了一个持续发展的西方文明形象,这成为西方向世界确立自我形象、构建其优越性地位的重要场所。
康有为从博物馆的精心编排中看到了西方进化发展的顺序:“今偏观各国博物院皆于十二三世纪后乃有精巧之物,可以观欧人进化之序。”[11](P357)王韬参观法国博物馆,见识了西方的兵器发展历程:
古时战斗之际,亦尚甲胄,其器械亦惟刀、矛、弓、矢,自火器兴而皆废矣。……阅其所陈战具,亦可悉古今沿革之源流,而行兵强弱之殊矣。[6](P91-92)
其中,王韬所谓“可悉古今沿革之源流”,说明西方博物馆从时间序列上一步步展示了西方军事文明的发生与发展,从古时粗陋的弓箭到现代的枪炮军火,法国军事进化轨迹一览无余。张德彝游不列颠博物馆,发现其中不仅有古物陈列,更有创新之物后续之。[12](P361)我们发现,在晚清游者的博物馆书写中,这一直线向前发展的西方形象在进入晚清视野时,是长驱直入,不加抵抗的,它成为理所当然的认识西方的有效媒介,成为从历史通向现代西方的一道叙事脉络,即西方是以前进的步伐从古代走向当下的,这不仅是西方博物馆自身的叙事方式,也是晚清游者观之于目、印之于笔的叙事手法。
当西方的文明遗留物与现代科技的展示成为叙事主体,它们被分门别类地书写,以时间序列的方式具体而微地建构了西方的过去与现在,在关于西方过去的文明博物的展示中,一个拥有文明并逐渐进步的西方在一个透明的一览无余的视野中形成了连贯一致的形象,勾勒了一条不同于停滞的东方的西方道路,这是一条不断进步、由古到今、由古物到创造的道路,是现代社会如何进化的最好的标本,它暗示的是当时西方正在进行一种普遍的文化继承与文化更新的过程,这一过程与只拥有古物的凝滞的东方文明是截然不同的。
在叙写西方进化的同时,博物馆也以展览古董与旧物的方式塑造了一个停滞的、愚昧的中国形象。在西方博物馆中,中国游者发现其中的展览品很大一部分是西方从中国所获取的战利品,它们多为从两次鸦片战争中掳掠而来,有相当收藏价值的宫廷古董,康有为游法国欹规味博物馆,看到大量的皇帝玉玺、乾隆御笔流落在此:“中国内府图器珍物在此无数,而玉玺甚多,则庚子之祸也。”[13](P214)游乾那花利博物院又见中国积年积世之精华流落法国展览室,其中有“御书印心石屋墨宝六幅,金纸《印心石屋图》三幅,亦刻龙。斋戒龙牌一。封妃嫔宝牒一。其他晶石漆瓶盘、人物无数”[13](P220)。这些价值连城的中国器物所闪烁的精致光辉,不仅不能带来自我印证的文化自豪,因是失败后被掠夺的战利品,反而成为无处不在的提醒,让目睹者一再回忆曾经辉煌的历史和失落的现在。面对这些拥挤在西方博物馆中源自中国的煌煌宝物,康有为凄凉回首,慨然国族陵夷,他随文附《巴黎睹圆明园春山玉玺思旧游感赋》一诗,哀婉地抒发了今非昔比的末世之感与变革情怀:
忆昔霓旌幸苑时,畴人南汤来侍值;寿山春日饶物华,辇路繁华好颜色;罗刹远遣图理琛,荷兰贡入量天尺。当时威廉始入英,人民不及五十亿;欧土文明未开化,惟我威灵照八极。百年之间新世变,汽船铁轨通重译;惜哉闭关守长夜,竟尔绝海召强敌……岂意京邑两邱墟,玉玺落此无人识。[13](P218)
康有为在博物馆睹旧物而生悲,他在感赋中追忆了往昔的辉煌,昔日的皇室内部繁华似春,外部则有俄罗斯、荷兰等国谦卑入贡,其时的英国还人烟寥落、处于未开化的蛮夷状态,然而“百年之间新世变”,西方在快速进入现代工业文明的同时,中国仍然“闭关守长夜”,不思变法求新,以致屡败于强敌,让曾经尊贵一时的玉玺流落异域。康有为的这番感慨自然与博物馆的中国陈列品所带来的心灵震撼分不开。这些迁流他国的故国宝物被西方放置在某种层级结构里面,以一种伤感的、断裂性的面目呈现,在它们的背后是中国成为西方文明麾下失败者的现实境遇,是曾经辉煌的东方文明被西方文明所控制、所容纳的结局,这就难免康有为在面对它们时要赋哀诗来抒发黍离之悲。
在展览西方作为胜利者取得的中国战利品同时,中国的鸦片、小脚妇人鞋也成为西方博物馆中惯常的中国标签,它们以愚昧、停滞的状态在展览台上接受晚清游者的注视。载泽游美国博物馆,发现南粤的粗劣物品与华商的被弃之物成为代言中国的具体物象:
内有一室列中国物,大半华商赛会时所遗。陈列无次,且多粤中窳劣之物,徒贻讪笑于外,深为愧疚。[14](P593)
这是西方形塑下的中国形象,它们通过博物馆陈列的方式,以镜像的形式投射于中国游者,中国被西方以一种轻慢乃至荒诞的姿态所拼凑,它带给游者的不再是一种展示力量与世界多样性的符号,而是西方叙事中有关破败、愚昧的中国想象,这是被西方所严格规定的“中国”。显然,西方博物馆的类似“中国展览”在某种层面上是西方从“东方主义”的意识出发,对中国物品进行的有意设置,萨义德曾指出,在19世纪的西方想象视野中,“东方则是遥远暧昧的、被征服的国度……被认为象征遥远和异国情调”[15](P80、P101),正是源于西方将“东方”建构为异质的、低下的具有异国情调的“他者化”的思维模式,西方博物馆中的中国陈列才会呈现出上述破败与荒诞的形态,我们可以说这是一种有选择的中国展览,属于西方建构产物,旨在为东西建立一个明显的分野,从而突出西方文化的优越性。
对于中国观者而言,西方这种刻意撷取的扭曲的中国叙事无疑是一种赤裸裸的民族伤害,它让书写者“愧疚”、“颜赤汗流”,也激起了“愤懑”的民族情绪。19世纪中后叶,中国屡屡败北于西方的事实,被具体化为破败物品的展示,对比同一博物馆中西方先进器物文明的展览,它更能在一种强烈对照下唤起国人的民族自尊心。康有为参观德国博物馆,因中国物品与黑人相并列而愤怒不已,借此抒发他的变法大志:
亦置在黑人之列焉,筑一亭,置一枷人首,海关道旗仗在焉。辱吾国体极矣。……而轻贱我同于非洲之黑人,假我国而见分灭,岂可言哉?志士不可不愤兴哉
康有为一贯持有严重的种族观念,他认为当时的黑人社会文明落后,与白人、黄人等文明世界的种族相去甚远,而这么一类让康有为深恶痛绝的种族却在西方的博物馆中与中国同置一列,康有为自认为是奇耻大辱,所谓仁人志士应当奋发图强以雪耻的意思自然不言自明。
三、西方博物馆:启迪民智的变革利器
虽然西方的博物馆多以不平等的序列展示西方与东方,由此引发晚清游者内心的痛楚与民族情绪,但是博物馆向普遍公众开放的运作模式与广开民智的教化功用,一直被痛思图强的晚清游者心向往之。具有启迪功用的博物馆在寻求奋起的晚清知识精英笔下,不啻为启蒙民智、感发人心的变革利器。
张德彝参观大不列颠博物馆,置身于纷至沓来的知识序列中,感慨博物馆是扩张庶民见识的重要知识场所:“盖人限于方域,阻于时代,足迹不能遍历五洲,见闻不能追及千古。虽读书知有是物,究未得一睹形象,故遇之于目而仍不知为何名者,往往皆然。今博采旁搜,综括万汇,悉备一庐,每于礼拜一、三、五等日开门,纵令士庶往观,所以佐读书之不逮而广其识也。”[12](P361)显然,在张德彝眼里,西方博物馆中超越时空的物品陈列,不仅能在直观的层面形象地为观者展示五洲之阔、千古之大,而且,令庶民往观的开放模式,能够从见识层面扩大民众的知识面,普及书本之外的知识信息,博物馆不仅具有怡情的情感功用,更具有“广其识”的现实功能。
康有为自变法失败后,汗漫海外,游遍欧洲,曾数十次参观各国博物馆,博物馆保存古物、传递知识的功能与他的政治理想产生了强烈共鸣。游意大利博物馆时,他从“以无用为有用”的哲学高度肯定了博物馆在保存古物、感发民众心志方面的重要意义:
考之各国风俗,皆有保全古物会。……凡一国之古物,大之土木,小之什器,皆有司存。部录之,监视之,以时示人而启闭之。郡邑皆有博物院,小物可移者,则移而陈之院中。巨石丰屋不可移者则守护之,过坏者则扶持之,畏风雨之剥蚀者则屋盖之,洁扫而慎保之。其地皆有影像与船记以发明之。有游观者,则引视指告其原委,莫不详尽周悉焉,而薄收其费。
夫天下固有以无用为有用者矣。……凡小人徒见其浅,而君子能虑其远。古物虽无用也,而令人发思古之幽情,兴不朽之大志,观感鼓动,有莫知其然而然者。[13](P118-119)
博物馆自19世纪以来已成为西方普泛性的公共场所,也是西方文明发展的重要标志,康有为游览欧洲各国,发现其中均设有博物馆保存古物,这一场所的建立与操作模式无疑给曾有此宏旨的他以强烈触动。游罗马博物馆,他“一面观之,一面私惭,甚憾吾国人之不能保存古物”[13](P118-119)。在上述引文中,康有为以详细的笔致介绍西方博物馆保存古物的方式,这类直观的带有考察意味的书写方式自然有呼吁借鉴之意。康有为在意大利游记与法兰西游记中数十次详尽写到博物馆,追慕之意溢于言表,这恐怕与他游历欧洲前便抱有的政治理想有关,于1885年脱稿的《大同书》中,康有为对博物馆的建立进行了浪漫构想,主张在理想社会“太平世”里,从上至下的行政区域都建立不同层级的博物馆,以供民众参观与扩增见闻;维新变法时期,康有为又孜孜将成立博物馆作为变革要务之一上报于光绪帝。变法维新要解决的国计民生问题可谓琳琅满目,康有为坚决将看似无关变法宏旨的博物馆作为要务呈报,其根本原因或许在于他在引文末所指出的博物馆能“令人发思古之幽情,兴不朽之大志,观感鼓动”,具有相当的开民智的教化功能。康有为借博物馆来启迪民智的夙愿终于在1905年得以实现,1905年,实业家张謇建成南通博物馆,并向普通公众开放,自此,中国拥有了第一家自建的博物馆。
通过对晚清域外游者笔下的博物馆进行分析,我们发现,晚清域外游记中的西方博物馆并非一个地理意义上的游览场所,它正成为一个具有包孕性的文化符号,它以具体的方式构建了西方文明的自我形象,并形塑了西方视野下的东方形象。西方博物馆以集中、有序列的文明展览打破了晚清人凝滞的西方想象,改造了晚清士人的内在心理结构,并于潜移默化中带来了一个让晚清人自惭形秽、意欲思变的新的现实世界。
标签:博物馆论文; 文化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世界历史论文; 华夏文明论文; 游记论文; 晚清论文; 西方世界论文; 康有为论文; 王韬论文; 郭嵩焘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