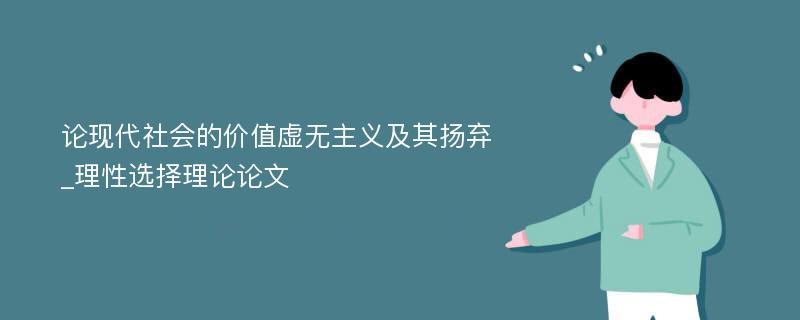
论现代社会的价值虚无主义及其扬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虚无主义论文,现代社会论文,价值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01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5)04-0062-06 价值虚无主义是现代社会最深刻的精神危机,其核心内涵在于传统社会神性立法权的剥夺与主体立法的失效。主体的强大使其不愿匍匐于神性立法的权威之下,将客观恒定的自在价值还原为主体的意志,然而主体的立法不仅使价值自身成为主观化、相对化的存在,更使其实质性内涵为外在性形式所僭越,从而引发了精神价值与意义世界的萎缩,变得空洞抽象、了无生趣。扬弃价值虚无主义成为一个重大的时代命题呈现在我们的面前。自由主义将责任伦理和社会正义的构建作为价值和意义的现实载体,却未能解决个人无家可归的根本问题;社群主义立足于社群共同体的构建,将美德传统或多元化的宗教视为超验神性在经验世界的支点,却未能解决价值诸神的冲突;马克思主义则确立了辩证的生命原则,在历史的维度中寻求价值的确定性,为祛除价值虚无主义提供了一个新的维度。 一、“形式”的僭越:价值虚无主义的核心内涵及其表现 历史上似乎并没有哪一个时代像当前这样对人自身都显得如此的困惑不解,整个社会陷入茫然与迷惑之中,由神性立法权所规定的客观价值秩序,这个曾经赋予了人们以人生意义的目的论神圣实体出现了坍塌和瓦解。从整体性中抽身而出,被连根拔起的社会主体获得了以自身理性立法来规约价值秩序的权利,然而这种价值的主体化并未使其获得真正的效能,反而导致了价值判定的主观化、相对化与形式化,陷入价值虚无主义的境地。也就是说,现代社会之价值虚无主义的核心内涵正是在于神性立法权的剥夺与主体立法的失效,使现代人想要寻求某种确定、牢固的价值基础与意义根基不再可得,而形式合理性之于实质合理性的僭越更引发了精神价值与意义世界的萎缩。人类失去了与世界、共同体在精神意义上的关联,也失去了自身实质性的内在本质,沦为一种空洞化、符号化的存在。 首先,传统社会神性立法权的剥夺所导致的意义根基的瓦解是价值虚无主义的核心内涵,它表明人类在冲破神性强制的同时也割断了与自身相连的精神血脉,从而失魂落魄、无家可归。个体的价值性与意义感只有在整体、持续的关联性中才可获得,个体惟其在所栖息世界的背景坐标中寻求到自我的“身位”之时,才能感受到生命的充盈与存在的价值。传统社会正是以目的论的理念、灵魂、人格等神性概念为前提,预设了其客体性与不朽性,整个世界都被理解为只为彰显神性理念而存在的神圣客体,是诸神的至上戒律、生命的神圣节律、上帝的至真至善的最好证明,包括个人在内的任何事物都成为神圣价值链条中的特定环节。他们的存在不再是任意的,而是体现了一种内在的根据和目的,个体便在分享神圣的永定之光、从整体性的规约和反思中获取自身的价值和意义。正如查尔斯·泰勒所言:“人们过去常常把自己看成一个较大秩序的一部分。在某种情况下,这是一个宇宙秩序,一个‘伟大的存在之链’,人类在自己的位置上与天使、天体和我们的世人同侪共舞。宇宙中的这种等级秩序曾反映在人类社会的等级结构中。人们过去总是被锢锁在给定的地方,一个正好属于他们的、几乎无法想象可以偏离的角色和处所。”①因此,个体必须从这种等级秩序之中、价值秩序之内寻求自己特定的角色,履行自身独特的功能,从而获取先在整体性所赋予的德性、现实自我的价值与人生的意义。这种价值供给形态与意义输出方式直接根源于传统社会同质性、未分化的等级性社会结构,因而需要统一的绝对价值,即涂尔干所言之“集体意识”来塑造社会成员一致的价值情感与价值信念,实现共同体的整合。 传统社会呈现出神性强制与意义充盈的深刻悖论,因为个体必须存在于先验的、稳定的社会等级秩序之中,只能在“神圣”的价值秩序内寻求自己的位置、身份与意义。诚然,这的确使个体能够与更为广阔的世界和共同体建立内在的精神关联,通过理性的沉思便可克服自我行为的任意性,获得生命的圆融和人生的意义,呈现自身客观而稳定的自在价值,然而对于个体而言,这种价值和意义的获取方式不仅具有很大的强制性,更抹杀了其独特的个性与生命的自由,沦为神圣共同体与神性价值的工具。因此,破茧而出的自由主体对神圣整体性的分化与瓦解便具有当然的合法性,从而推动着传统社会向现代文明迈进。人类自由的深化使最高神性价值的废黜不可避免,然而,“温馨的强制”与“残酷的自由”的极端跨越,使个体刚刚逃离了强制,又陷入了无根的漂泊,不再受到传统等级秩序权威和神圣目的论发号施令的人类意志却饱尝着理性化角色的分割之苦,从而使自身支离破碎。原子化的自我俨然成为承载角色外衣的衣架,不再具有客观实在性和稳定连续性,他可以扮演任何角色,也可以从任何情景或特性中抽身而出,碎片化的生存使人们失去了稳定的存在和行为的目的,不再拥有精神的归宿与意义的皈依。社会的整合越来越诉诸外在于一致信仰的法律契约,共同情操与文化纽带日益式微和涣散,人们失去了彼此之间深层的精神价值基础,这样建立起来的“一致性”只是依靠于博弈关系所取得的权利和义务的暂时性利益平衡。现代社会建立在泥沙般松软的价值地基之上,无任何束缚和限制的人类意志使社会价值秩序注定成为多元相对主义的“诸神之争”,时代的价值命运将是无休止的争吵和诸神的冲突,将是价值与世界观之间一场永恒的战争。诚如马克斯·韦伯所言:“这里有不同的神在无休止的相互争斗,那些古老的神,魔力已逝,于是以非人格力量的形式,又从坟墓中站了起来,既对我们的生活施威,同时他们之间也再度陷入了无休止的争斗之中”。②植根传统社会的绝对价值将过去引入现在与未来,它使人们的内心形成稳定的家园感和方向感,是凝聚民族的良知与神圣感的强大力量,更成为链接社会共同体深层的文化纽带与维系民族共同体内在的文化生命,割断了与它的血脉,陷入相对主义的泥沼,必然导致深刻的精神价值危机,一种因缺乏稳定的质性价值而生存空洞、无家可归的危机。 其次,现代社会主体立法的失效所表征之形式合理性对实质合理性的僭越是价值虚无主义的另一内涵,它表明主体赖以强大的力量却抽干了自身价值的质性内涵,从而抽象空洞、了无生趣。主体意志以理性的自律祛除神性巫魅的同时也祛除了不可实证的质性价值,导致价值丧失了自身的内涵,成为一种只能量化的、形式化的东西,从而宣告了主体立法的失效,一言以蔽之,就是形式合理性对于实质合理性的僭越,引发精神价值与意义世界的萎缩。理性的自决、功利的趋向和领域的分离合乎逻辑地使形式合理性不仅成为支撑经济活动、法律契约、官僚制度运行效率的理念基础、构成方式和组织系统,亦成为社会分化时代之相对主义多元价值得以沟通的外在客观标准与建制基础。合理性是韦伯用以把握社会行动性质的概念,行动与目的相一致即为合理性,否则即为非合理性,根据特定目的、超验目的或终极目的的划分,便可分为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形式合理性就是以价值中立为原则,通过精确计算、量化设计寻求达到特定目标最有效的方式、程序与手段,从而形成一系列组织流程、规章制度和规范建制,以实现功利效用的最大化,具有逻辑的形式化、程序的标准化、度量的可计算性、运行的可操作性等重要特征。当形式合理性以超越当下功利,寻求人类终极目的之实质合理性来规约自身时,尚具有明显的合法性,它最大限度地排除了人为因素的干扰,并由此获得了极大的效率,然而一旦其脱离了实质合理性的轨道,成为物化结构的自律存在,整个社会便犹如一个巨大的“铁笼”,无情地吞噬着一切超验价值。 形式合理性对于实质合理性的僭越,使价值自身成为只有空洞形式而无实质内涵的存在,表现在技术理性与交换价值两个层面,且彼此之间存在着相互促进的密切关联,交换价值是功利至上之现代社会的“终极价值”,技术理性是获取这种价值的内在动力,这样便在二者的互动推动中遮蔽了超验价值存在的独立性。技术理性无疑是形式合理性现实的表现形式与重要载体,它以现代技术为手段,以数理逻辑为基础,通过精密的计算昭示出客观对象的数量关系和运行规则,从而以最大的效率实现特定而功利的目的。平心而论,技术理性面对没有生命的僵死之物具有精准的分析力与巨大的效率,但当其面对极富灵性的人类自身时,却遮蔽了生命的体悟、思维的反思和圆融的智慧,人类诸多弥足珍贵的超验价值遭到了窒息。人们能感受到的只是机器的日夜轰鸣、制度的自动运转与被裹挟的无奈,从而“专家没有灵魂,纵欲者没有心肝”③,只能成为其中的一个零件而难以自拔。世界不再是冥想与爱的对象,它只是工作和计算的客体,不再富有诗性的审美力与灵性的生命力;人类不再是完整和丰富的生命体,他只是活着与认知的存在物,不再具有对苍穹的觉解力和生死的领悟力。而交换价值是资本逻辑的根本原则,是形式合理性在经济领域的表现形态,它一方面对社会财富的增长与生产力的提高提供了强大的合理化动力机制,却在另一方面吞噬着人类更为深远的精神力量,摧毁和虚无了内在于生命自身的超验价值原则。人格、尊严、自由等超验价值本应凭借生命自身就足以确证其独立的地位,资本逻辑的统治却使任何价值都必须在交换价值的天平上加以度量才能确证自身。由此生命的超验价值便失去了自在的意义和独立的地位,必须以交换价值为中介,否则便或者在现实中化为虚无,或者明码实价的换算与出售,从而丧失了应有的规范性。“‘抽象’的交换价值本来只是标识诸种感性活动与结果之间的同一性以确立交换的标准,如今却反客为主,致使感性事物沦为客体,自身却成为主体,人与物的关系从此颠倒,不再是人支配与使用物,反而是物奴役和控制人”④。正是由于交换价值的本末倒置,使生命的个性、灵性与神性都被抽象的魔法变得忽略不计,丰富而全面的生命内涵显得贫乏而粗陋,只有当对象以“物”的形态为我们所占有和使用的时候,才被视为是有价值的,高贵的生命价值、审美的精神价值、超越的终极价值便只是一个“无”。更为严重的是,交换价值的“终极性”与精神价值的式微使“物”拥有了操纵一切、颠倒黑白的、扭曲人性的魔力,使卑贱者因货币而高贵,孱弱者因货币而勇猛,邪恶者因货币而受到尊重。技术理性和交换价值所导致的精神价值秩序的颠覆和乱象便足以说明形式合理性在塑造社会生活的道德与价值规范上的苍白无力,从而宣告了主体理性立法的失效和破产。 二、“偏好”的抉择:价值虚无主义的伦理表征及其危害 主体理性立法的失效在伦理构建的维度中表现为规范形式对于德性实质的僭越,从某种意义上讲,也可视为是形式合理性对伦理世界的渗透和扩张。伦理仅仅成为外在的规则,失去了内在的德性作为支撑,“规则无人”成为价值虚无主义在伦理层面的重要表征,也是价值主体化的必然逻辑。现代社会已不存在一个对所有人都有效的至善或至上美德,也不存在一个完备而客观的价值序列,诸多价值的重要性都是由其所处之特定环境所决定的,换言之,价值已经成为主体根据特定环境设定的解释系统和评价体系,一定的评价体系对应着相应被设定的价值序列,即便最高价值也必定先存在于这个设定体系之中,才能获得自身的“价位”。由此,价值成为主体意志之偏好的抉择,最高价值也只是在主体意志设定的价值体系之中的最高价值,如此一来,社会价值秩序必须通过一种可以沟通不同价值序列的方式来维系其有序性,这就必然导致形式对于实质的僭越。 首先,传统目的论价值基础的瓦解使价值自身成为主体设定、解释、估价的结果,这必将导致价值的形式化与任意化,从而致使主体伦理立法的失效。诚如汉斯·约纳斯所言:“目的论从自然原因的体系中排除出去了,而自然本身是无目的的,它不再为可能的人类目的提供支持。一个没有存在物之内在等级体系的宇宙,正如哥白尼的宇宙那样,使得价值失去了本体论的支持,自我对于意义与价值的追求不得不完全地依靠自己。意义不再是发现的,而是被‘赋予’的了。价值不再被视为客观实在,而是被设想为评价产物。作为意志的功能,目的完全是我自己的创造物。意志取代了洞察,行为的暂时性驱逐了‘自在之善’的永恒性。”⑤这就意味着,传统目的论所支撑之客观统一的、非个体的价值坐标已轰然倒塌,先前个体以神圣之目的规约自身,规则内在于德性践行的伦理构建不复存在,现代伦理由此实现了价值的主体化,从而将伦理行为奠基在主体意志的理性自律的基础之上。这种主体实践理性之立法,即以个体良知与主体意志为支点的质性伦理构建,与其说是成功的,毋宁说是试验性的,只是对量化伦理的偶然性进行的一种颠覆性尝试。它是价值主体化以后,以主体目的论取代传统目的论的“替代品”,试图以“你应该”的强制性“绝对命令”建立对理性个体普遍必然的伦理有效性。但价值的主体化使“善”的客观价值被归结为主体的“向善”能力,价值自身被转化为主体的欲求,德性从此失去了特定而自在的价值品质,它的存在取决于人们的力量和行为所获得的品质与产生的效果。于是,抽象的道德自律主体与单纯理性限度的宗教相互支撑所产生的道德律令因缺乏客观而稳定的价值质料,实际上只剩下碎片化、纯形式化的规范原则,便难免在具体的伦理处境中遭受“谁之正义,何种合理性”的两难抉择,最终只能服从个体的主观偏好。现代伦理如此脆弱的主体化价值根基必将导致它自身所批判的价值评定与道德人格内在结构的经验量化,从而陷入更多数量的人们之功利秩序的价值关怀,而不再是离神性至善更近的价值充盈。价值主体化所引发的现代质性伦理构建的失效,加深了功利主义量化伦理在现代社会的大行其道。不同视角、不同立场的主体价值之间如果存在着相互关联性和可沟通性,那一定是数量的价值关联和刻度计量,财富、目的、人格、理想等都能在形式合理性之数量度量的基础上得以权衡和达成谅解。 其次,形式规则对于实质德性的僭越也表现为以量化的方式“度量”价值的功利主义伦理对超验价值的颠覆与对少数人正当权利的漠视。价值主体化以后,现代伦理学无论以何种方式意图重建具有普遍性的质性伦理,都以其无可避免的主观任意性而宣告失效,主体理性立法的最终结果似乎只能是以形式合理性为基础之功利主义伦理的大行其道,从而更加表征了这种立法的失败。功利主义伦理的失败并不意味着其完全失去了社会生活的规约力,而是由于它仅存在量化的维度,缺乏质性的支撑,因而具有自身根本无法克服的内在悖论。功利主义是市场原则向伦理世界渗透和侵入的必然产物,由于理性化对神性的祛魅,功利主义伦理理所当然地将自然人性设定为“趋乐避苦”,能增进快乐的就是善,否则就是恶,苦乐的功利原则由此成为至上的道德准则。这样,道德本身就失去了其目的性价值,沦为获得快乐的工具性存在,行为的价值便不再是德性的良善动机,而是行为的苦乐效果,也就是说,最大限度的、最高效率的获取快乐是唯一值得追求的目的,其它一切都是手段。显然,这种伦理构建是以量化标准和效率原则作为其内在基础,最终指向“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的终极目标。由于功利主义将快乐视为可以量化的存在,而在市场社会凡是可以量化的就必定可以通过货币去获取,因此,无论功利主义伦理以何种精巧的方式加以解释,始终无法取消包括人的自由、人格和尊严在内的一切超验价值都可以用金钱去衡量与购买的结论,从而在事实上造成了对超验价值的颠覆。与此同时,以量化的方式来度量“正义”同样会造成严重的社会后果,即对少数人的正当权利乃至生命的漠视,因为以效用最大化的方式来考量有关政策正当与否,必然会得出只要以大多数人的幸福为依据,任何事情都将是好事的结论,如果大多数人认为牺牲某个人的生命可以增进他们的福利,也将是合理的,这必然引发大多数人对少数人的奴役,而且是建立在“正当合法性”基础之上的奴役。 再次,形式规则对于实质德性的僭越还表现为公共生活奠基于形式合理性的“价值中立”。将道德信念归之于私人领域的自我选择,为公共生活中的道德冷漠与放弃道德责任的行为打开方便之门,这成为现代伦理设计的硬伤。现代社会由于诸多领域的相互分离,使私人领域与公共生活出现了相应的边界,公共生活的有序性直接来自于以形式合理性为基础的公共权力、官僚体系以及各种制度规则的规约,从而通过人们之间利益的调节来维系公共生活秩序的有条不紊,如此一来,为维护制度规则“价值无涉”的公正性与高效性,便将生命的目的与人生的意义等终极价值作为私人性的价值情感排除在公共生活之外,将它们交付于私人领域个体的自我抉择。与此同时,价值主体化本身也意味着其正当性基础直接来自于个体的理性良知,选择何种价值信念与生命目的成为完全由个人自我负责的事情,不存在任何权威对于个体道德与人生意义垄断与解读的合法性,亦不存在任何力量干涉个体价值抉择与决断的合法性,个体自身就是道德抉择与价值信念唯一的合法性权威。无可否认,这种公共生活与私人领域边界的划分的确有利于个人自由的保障和维护,然而公共权力与官僚体系自身由于秉承“价值中立”与“价值无涉”的效率原则,因而缺乏内在的道德评价机制与道德责任共负原则,呈现为道德价值的“真空”状态。也就是说,一旦以形式合理性为基础的官僚体系自身出现了共同的非道德性之恶,便会同时失去应有的规约和控制,从而通过理性化、价值中立的操作程序,共同从事“高效率”的恶行,而从属于形式合理化系统的非道德个体还会以“价值无涉”为由,实现自我的道德催眠与自身的恶行纵容。正如舍勒所言:“在近代个人主义及其紧密地依附于它的专制国家、民族主义和自由竞争经济的发展过程中,排开基督教精神的近代伦理以及与伦理相应的哲学伦理学,在感觉、欲求以至理论上,都已丢失了责任共负这一崇高原则,而且是在其理性根子上逐渐丢失了这一原则;我认为,这是近代伦理道德的一个根本缺陷。”⑥正是由于这个根本缺陷,现代性大屠杀、自然环境污染等公共性非道德事件才会如此“合乎逻辑”地发生和上演。 三、“确定”的寻求:现代社会价值虚无主义扬弃路径的探索 既然价值虚无主义是社会转型所导致的绝对价值向相对价值,客观价值向主观价值发生位移,从而致使价值自身缺乏确定性的支撑,成为一种任意性的东西,那么扬弃价值虚无主义的根本路径便在于如何在价值多元化已不可逆转的时代中寻求一定的价值确定性,在绝对与相对、客观与主观之间保持应有的张力,在这个已经祛魅的世界中为价值和意义寻求自身的一席之地。 自由主义将个人自由、价值分化、理性化祛魅视为现时代不可回避的价值处境和文化命运,既然已无神性创造之价值秩序可以遵从,既然已无先知所赋予之人生意义可以践行,价值和意义的选择与坚守便只能来自于个体自身,责任伦理与社会正义的构建便成为扬弃价值虚无主义当然的现实载体。自由与责任内在地联系在一起,所谓责任伦理就是个人义无反顾地为其自由行动承担后果,它肯定了生活价值的此岸性,即人生的价值与意义就是个人自由创造、自我选择、自我担当的产物,以“天职”的使命感去应对自己的工作和事业,提升自我的精神境界和自由人格。这就意味着人们不应将工作和事业仅视为一种谋生的手段,更要使之成为人生价值和意义的现实载体,勇敢地承担自我抉择的后果和理应履行的责任,“然后他遵照责任伦理采取行动,在一定的时候,他说:‘这就是我的立场,我只能如此’。这才是真正符合人性的、令人感动的表现”⑦。自由主义一方面将个人自由视为多元化社会存在的前提,另一方面又着力构建规范个人自由之正义的社会制度,自由抉择、担负责任的个体只有在正义的社会环境之中才是可能的,它范导着公平良善的社会秩序,是个体之善孕育的基本条件。社会正义的制度构建并不以完备的哲学、宗教、道德学说为基础,而是以多元化的深刻分歧为前提,以公共理性支撑的“重叠共识”为基础,构建个体之间公平合作的基本制度框架,力图让每一个具有独立人格的自由主体都有权利平等地追寻自我设定的生命目的与人生意义。由此,自由主义论证了一种在现代社会承载人生价值与意义的载体:责任伦理与正义制度,然而它以承认原子化个人存在之合理性为前提,无法解决个人无家可归的根本问题,同时它关注的只是伦理的制度化安排,而非人自身,“规则无人”的问题并未得到解决。 社群主义对于自由主义的方案提出了质疑,因为“无负荷的自我”根本不可能存在,价值和意义的基础也并非个体之良知,而是社群的共善与美德,于是,社群主义立足于社群共同体的构建,将美德之传统与多元之宗教视为超验神性在经验世界的支点。如何复归美德的内在性,治疗无家可归的时代病症,社群主义寻找到了承载生活、美德之完整性和人格同一性的社群共同体,在一定程度上为扬弃价值虚无主义建立了新的背景坐标。个体在社群共同体的共善中获得了和他人之间的精神联系,在整体性共同目的之价值坐标中成为“叙事的自我”,拥有了人生意义追寻的历史统一性,无论个体的道德信念和道德行为发生怎样的变化,其内在的精神人格在共善的感召之下,始终存在于自我的同一性之中。社群主义并不仅仅将孤苦无依的个体放置于当下社群的共善之中来承载价值的确定性,更试图将这种确定性安顿于历史性的“传统”深处。麦金太尔这样写道:“我发现自己是一个历史的一部分,并且一般而言,无论我是否喜欢它,无论我是否承认它,我都是传统的承载者之一。”⑧践行美德就是要继承相关的传统。社群主义将扬弃价值虚无主义的路径锁定在回归传统和重建社群共同体,只是当传统已经支离破碎,这种回归与重建何以可能。值得重视的是,多元化宗教社群的建构为超越价值虚无主义提供了另一种可能,它试图将多元化的神性资源引入此岸,为经验世界寻求超验的支点,为多元化的价值渴求群体提供可选择的超验空间,以宗教的神性力量赋予个体实质性的价值内涵。问题在于,多元化社群共同体之间并不存在较为确定的可沟通性,诸神之争的价值混乱依然在所难免。 马克思主义则确立了辩证的生命原则,以内在化的主体神性在对象性活动中形成“绝对”与“相对”的张力,并在历史的维度中寻求着价值的确定性,为祛除价值虚无主义提供了一个新的维度。在马克思的理论向度中,价值并不是一种主观任意性的东西,它遵从着辩证的生命原则,因而必然存在着自身的确定性,只是这种确定性并非僵死之绝对的神性,而是自由自觉的对象性活动中生命灵动之生成的神性。这就意味着,在客体的主体化与主体的客体化的相互交织之间,主体的合目的性必然受到客体合规律性的制约,从而避免了价值的主观任意性。主体必须在客体规律性允许的范围内来寻求生命所需要的确定性、稳定性与秩序性,为自身的生存寻求稳固的阿基米德支点。借助于这一支点,人们便可在变幻莫测的世界中获得生存的价值根基与精神家园,受其规约,亦可从中获取心灵的归宿和生命的意义。然而,辩证的生命原则同时也意味着一种突破僵死确定性的非确定性,它是生命自由创造的冲动力与未完成性的必然后果,从而不断否定现在、超越当下、迈向未来,使人类的价值构建在确定性与非确定性之间,形成永不停歇的创造性超越和提升。因此,马克思理论语境中的价值确定性既非僵死之绝对价值,亦非无确定性的相对价值,而是在绝对与相对、主体与客体、确定性与非确定性之间寻求建立在实践活动之上的生成性张力,在客观的历史语境中去呈现和生成价值的确定性。历史本身就是实践活动的延伸和展开,实践活动之于客观规律性的遵从,使价值原则不可能脱离历史的客观条件而自存,它只能存在于客观的历史条件之中,价值原则因而不可能是主观任意的,它是人们按照自身的物质生产力与相应的社会关系所建构的。因此,对价值虚无主义的审视、批判和扬弃就不能仅局限于生命价值本身,而应当深刻昭示形成特定价值状况的物质土壤与社会关系,从而以新型的生活方式与社会共同体的构建来根除这一严重的时代顽疾。这种新型的生活方式与社会共同体就植根于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的否定性因素,它将以确定的必然性承载人类的自由个性与生命价值。 价值虚无主义是现代社会最深刻的精神危机,它以物质性价值的短视堂而皇之地亵渎人类弥足珍贵的超验价值,窒息人类更为深远的精神力量,扬弃价值虚无主义已经成为一个重大的时代命题呈现在我们的面前。尽管自由主义、社群主义与马克思主义都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精密的诊脉与路径的寻求,然而并未在真正的意义上解决这一重大的时代问题,价值虚无主义依然在拷打着人类脆弱的灵魂,也在激励着人类整体的智慧,使其能够在自身的生存困境中破茧而出。 注释: ①[加]查尔斯·泰勒:《黑格尔》,张国清、朱进东译,译林出版社2002年版,第3页。 ②⑦[德]马克斯·韦伯:《学术与政治》,冯克利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40、116页。 ③[德]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于晓、陈维纲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143页。 ④刘宇等:《论马克思超越政治解放的市民社会批判》,《三峡大学学报》2011年第6期。 ⑤[德]汉斯·约纳斯等:《灵知主义与现代性》,刘小枫编选,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8页。 ⑥[德]舍勒:《舍勒选集》(下),刘小枫选编,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828页。 ⑧[美]麦金太尔:《追寻美德》,宋继杰译,译林出版社2003年版,第28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