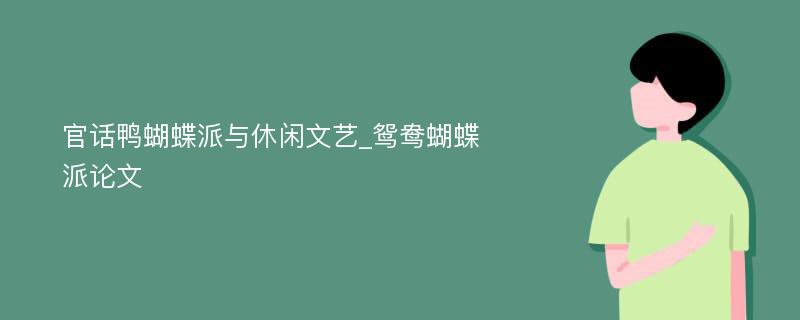
鸳鸯蝴蝶派与消闲文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鸳鸯蝴蝶派论文,文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五四文学革命运动的巨大影响,促使新文艺的蓬勃发展;但这并不意味着旧文艺会自行消亡。只要旧的社会基础还存在,只要具有旧情趣的读者群尚未消失,旧文艺总会延续下来,而且在某些时候,生命力还相当旺盛。五四以后,鸳鸯蝴蝶派文艺的长期存在,还占据着相当大的书籍市场,并且时不时地引起轰动效应,就说明了这个问题。
鸳鸯蝴蝶派代表着一种文艺倾向,反映了我国现代文学的一个方面。忽略了这个方面,就不能全面地考察现代文艺思潮;不研究这种倾向,更无法理解在鸳蝴派消声匿迹几十年以后,还会有同类作品的出现和泛滥。对鸳鸯蝴蝶派的考察,不仅是一种历史的回顾,也许还有助于对现实文艺的透视。
一、一场新旧文艺的斗争
鸳鸯蝴蝶派的作品属于通俗文艺,在正统文人看来,它虽然不登大雅之堂,但小市民阶层却趋之若鹜。民国初年,鸳蝴派的代表作《玉梨魂》居然发行了几十万册,可见读者之众。作品骈四俪六,情意绵绵,不但打动了小市民男女的心,而且引得状元小姐非要下嫁给作者徐忱亚不可。这段风流佳话,也可见鸳蝴派作品影响之大。
正因为鸳蝴派作品在当时影响很大,而这种影响又并非积极向上的,却是宣扬“发乎情,止乎礼”之类的封建思想,或吃喝嫖赌之类的行乐观念,这当然要受到新文化战士们的讨伐。可以说,从文学革命一开始,新文学家们就将鸳鸯蝴蝶派作为一个重要的批判对象。如鲁讯的《有无相通》、《名字》,钱玄同的《“黑幕”书》,周作人的《论“黑幕”》、《再论“黑幕”》等。教育部通俗教育研究会还发了一个《劝告小说家勿再编写黑幕一类小说的函稿》。周作人、钱玄同则在他们的文章中点出了鸳鸯蝴蝶派的名字。周作人1918年4月在北京大学小说研究会演讲《日本近三十年小说之发达》,就提到“《玉梨魂》派的鸳鸯蝴蝶体”;次年2月发表的《中国小说里的男女问题》里,又论及:“近时流行的《玉梨魂》,虽文章很是肉麻,为鸳鸯蝴蝶派小说的祖师。”钱玄同的《“黑幕”书》发表于1919年1月,其中特别指出:“其实与‘黑幕’同类之书籍正复不少,如《艳情尺牍》、《香闺韵语》及‘鸳鸯蝴蝶派小说’等等,皆是。”
接过《新青年》派的战斗旗帜,与鸳鸯蝴蝶派严阵相待,斗争最力的,是后起的文学研究会。周作人起草、鲁迅参加过意见的《文学研究会宣言》中说:“将文艺当作高兴时的游戏或失意时的消遣的时候,现在已经过去了”,就是针对鸳鸯蝴蝶派而发的。1920年初,文学研究会骨干沈雁冰接编《小说月报》,夺了鸳鸯蝴蝶派的重要地盘,将它变作发展新文艺的基地,双方的斗争渐趋白热化。关于这场斗争,郑振铎在《新文学大系·文学论争集》的《导言》中曾作过这样的评述:“鸳鸯蝴蝶派的大本营是在上海。他们对于文学的态度,完全是抱着游戏的态度的。……他们对于人生也便是抱着这样的游戏态度的。他们对于国家大事乃至小小的琐故,全是以冷嘲的态度出之。他们没有一点的热情,没有一点的同情心。只是迎合着当时社会的一时的下流嗜好,在喋喋的闲谈着,在装小丑,说笑话,在写着大量的黑幕小说,以及鸳鸯蝴蝶派的小说来维持他们的‘花天酒地’的颓废的生活。几有不知‘人间何世’的样子。……但当《小说月报》初改革的时间,他们却也感觉到自己的危机的到临,曾夺其酒色淘空了的精神,作最后的挣扎。他们在他们势力所及的一个圈子里,对《小说月报》下总攻击令。冷嘲热骂,延长到好几个月还未已。可惜这一类的文字,现在也搜集不到,不能将他们重刊于此。《文学旬刊》对于他们也曾以全力对付过。几乎大部分的文字都是针对了他们而发的。却都是以严正的理论来对付不大上流的诬蔑的话。”沈雁冰晚年在他的回忆录里忆及此事时说道:“我偶然地被选为打开缺口的人,又偶然地被选为进行全部革新的人,然而因此同顽固派结成不解的深仇。这顽固派就是当时以小型刊物《礼拜六》为代表的所谓鸳鸯蝴蝶派文人;鸳鸯蝴蝶派是封建思想和买办意识的混血儿,在当时的小市民阶层中有相当影响。”[①]沈雁冰和郑振铎都是当事人,是当时与鸳蝴派战斗的健将,从他们的文章中可以想见当时双方激烈斗争的情景。鸳鸯蝴蝶派的小报小刊,早已烟消云灭,他们的骂人文章现在是更难找了。但从现在还能看到的袁寒云的《小说迷的一封信》、胡寄尘的《文丐之自豪》等文中,其无赖相还跃然可见。文学研究会方面的文章,如叶圣陶的《侮辱人们的人》、郑振铎的《思想的反流》、沈雁冰的《反动?》,都是义正辞严的。特别是沈雁冰的长篇论文《自然主义与中国现代小说》,更具有理论的深度。
文学研究会对鸳鸯蝴蝶派的斗争,取得了新文学家们的广泛支持。创造社虽与文学研究会有门户之见,时以笔墨相讥,但对他们批判鸳鸯蝴蝶派之举还是赞成的。郭沫若发表了《致郑西谛先生信》,除纠正郑文中一个医学上的常识性错误以外,表示支持其基本论点。成仿吾在《歧路》中也提出对鸳鸯蝴蝶派的批判。巴金在《致〈文学旬刊〉编者信》里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后来,瞿秋白、钱杏村等人也都写有批判文章。
文坛老将鲁迅一直关心着这场斗争。他在《所谓“国学”》、《儿歌的“反动”》、《“一是之学说”》等杂文中将鸳鸯蝴蝶派与复古派的“国学”联系起来看;又在学术著作《中国小说史略》和《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中发掘了鸳鸯蝴蝶派的历史根源。直到30年代,他还在学术演讲《上海文艺之一瞥》中从社会史、思想史、文艺史等角度,对鸳鸯蝴蝶派作了全面的剖析。在《伪自由书·后记》里,鲁迅又记载了因《申报》《自由谈》副刊编辑易人而引起的风波,——这次《自由谈》编辑易人,情况有点与当年《小说月报》编者换班相似,也是新文学家换下了鸳蝴派文人。可见鲁迅对于鸳鸯蝴蝶派所代表的文艺倾向的重视。
虽然鸳鸯蝴蝶派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仍旧拥有相当大的势力,但在文化界的舆论上,渐处劣势,这使他们内里不免有点心虚。他们有些愿意向上的作家,很想听听新文学家对于自己作品的意见,如张恨水;有人知道鲁迅对他的某种工作做过肯定,表示感激万分,如周瘦鹃。但也产生了一种逃避的心态:竭力撇清自己与鸳鸯蝴蝶派的关系,否认自己是该派作家。特别是到了解放以后,鸳鸯蝴蝶派成为一个不光彩的头衔的时候。比如,包天笑在1960年发表的《我与鸳鸯蝴蝶派》中说:“据说,近今有许多评论中国文学史实的书上,都目我为鸳鸯蝴蝶派,有的且以我为该派的主流,谈起鸳鸯蝴蝶派,我名总是首列。我于这些刊物,都未曾寓目,均承朋友们告知,且为之不平者。我说,我已硬戴定这顶鸳鸯蝴蝶派的帽子,复何容辞,行将就木之年,‘身后是非谁管得’,付之苦笑而已。”他否认自己是鸳鸯蝴蝶派的理由是:他从未向《礼拜六》投过稿,而且也不认识徐忱亚其人。但《礼拜六》杂志的主编周瘦鹃却另有解释。他在《花前新语》中说:“我是编辑过《礼拜六》的,并经常创作小说和散文,也经常翻译西方名家的短篇小说,在《礼拜六》上发表的。所以我年轻时和《礼拜六》有血肉不可分的关系,是个十十足足、不折不扣的《礼拜六》派。”“至于鸳鸯蝴蝶派和写四六句的骈俪文章的,那是以《玉梨魂》出名的徐忱亚一派,《礼拜六》派倒是写不来的。当然,在二百期《礼拜六》中,未始捉不出几对鸳鸯几只蝴蝶来,但还不至于满天乱飞,遍地皆是吧?”平襟亚则出来解释,说“鸳鸯蝴蝶派”的命名,是出于饭局上的玩笑,纯属偶然。他在《“鸳鸯蝴蝶派”命名的故事》中记叙道:1920年的某一天,他们在小有天酒店叙餐,刘半农在隔壁闻声过来闯席,朱鸳雏道“他们如今‘的、了、吗、呢’,改行了,与我们道不同不相为谋了。我们还是鸳鸯蝴蝶下去吧。”杨了公因此提议飞觞行令,各人背颂旧诗一句,要含有鸳鸯蝴蝶等字。于是议及“鸳鸯蝴蝶”之入诗问题,而刘半农就即兴将《玉梨魂》列入“鸳鸯蝴蝶小说”,后来传了开来,遂有“鸳鸯蝴蝶派”之称。其实,如前文所引,早在1918、1919年,周作人和钱玄同就以此名来批判他们了。另外,范烟桥、郑逸梅则既讳言鸳鸯蝴蝶派,也不说是《礼拜六》派,却定名为“民国旧派小说”、“民国旧派文艺”。这个命名自然也不错。既然鸳鸯蝴蝶派作品属于旧文学范围,当然可称为“旧派文艺”。但其实,三者是一回事。说“鸳鸯蝴蝶派”,是就其主要特征而言;说“《礼拜六》派”,是以他们的主要刊物来指称全体;倘就其性质而言,自然可以称为“民国旧派小说”或“民国旧派文艺”。
但我们毕竟不能光在名称上兜圈子,还应该进行具体的剖析才行。
二、消闲的艺术观
鸳鸯蝴蝶派的作家们不承认自己是该派成员,主要的理由是该派并没有一个固定的组织,彼此间也并不全都认识,而且,他们所写的也并非全是鸳鸯蝴蝶。这些,可说都是实情。
的确,鸳鸯蝴蝶派并非一个有组织的文学团体。该派的作家虽亦有青社、星社之设,但都是聚餐会之类的松散团伙,意在联络感情,并无一定的宗旨。青社人数不多,星社虽发展到105人之众,但也未能囊括全体。鸳鸯蝴蝶派活动的时间跨度长,从清末民初起始,直到解放初消逝,可说是与民国相始终,前后包含几代作家;而且,地域范围广,作者分南派北派,分布在各个地方,他们之间有些时相过从,有些却并不认识。
但是,有组织的文学团体不一定能形成文学流派,文学流派不一定是有组织的文学团体。文学派流是由共同的艺术倾向形成的。
那么,鸳鸯蝴蝶派的艺术倾向是什么呢?
曰:消闲的艺术观。
鸳鸯蝴蝶派的作品很多,总数超过同时期的新文学作品。而且编有许多报刊,据郑逸梅在《民国旧派文艺期刊丛话》中所作的不完全统计,杂志有114种,小报有45种,还有4家大报的附刊。林林总总,百川归一,大抵而言,志在消闲。
有些报刊,单从名字上就可看出它的倾向。如:《游戏杂志》、《香艳小品》、《香艳杂志》、《眉语》、《好白相》、《白相朋友》、《情杂志》、《销魂语》、《消闲钟》、《消闲月刊》、《滑稽画报》、《游戏新报》、《游戏世界》、《快活》、《笑杂志》、《笑报》、《爱丝》、《荒唐世界》、《快活林》等。
有些报刊,在《发刊词》或《宣言》上大肆宣扬游戏人生,及时行乐的思想,把阅读作为买笑之用。其中说得最详尽的要算《〈礼拜六〉出版赘言》:“或问子为小说周刊。何以不名礼拜一礼拜二礼拜三礼拜四礼拜五。而必名礼拜六也。余曰。礼拜一礼拜二礼拜三礼拜四礼拜五。人皆从事于职业。惟礼拜六与礼拜日。乃得休暇而读小说也。然则何以不名礼拜日。而必名礼拜六也。余曰。礼拜日多停业交易。故以礼拜六下午发行之。使人先睹为快也。或又曰。礼拜六下午之乐事多矣。人岂不欲往戏园顾曲。往酒楼觅醉。往平康买笑。而宁寂寞寡欢。踽踽然来购读汝之小说耶。余曰。不然。买笑耗金钱。觅醉碍卫生。顾曲苦喧嚣。不若读小说之省俭而安乐也。且买笑觅醉顾曲。其为乐转瞬即逝。不能继续以至明日也。读小说则以小银元一枚。换得新奇小说数十篇。游倦归斋。挑灯展卷。或与良友抵掌评论。或伴爱妻并肩互读。意兴稍阑。则以其余留于明日读之。晴曦照窗。花香入坐。一编在手。万虑都忘。劳瘁一周。安闲此日。不亦快哉。”说了一大篇,无非是说他们的杂志与买笑觅醉顾曲有同等价值,且有优于它们之处。其创作的目的性很明确:消闲,寻欢。
我们当然不能说文艺没有消闲作用。古人所谓“娱心”,令人所谓“审美享受”,实际上也都是一种消闲作用。但消闲也有不同的情调,因而产生不同的后果。鲁迅在论及小品文的战斗作用时,说:“但自然,它也能给人愉快和休息,然而这并不是‘小摆设’,更不是抚慰和麻痹,它给人的愉快和休息是休养,是劳作和战斗之前的准备。”[②]而鸳鸯蝴蝶派作品给予读者的恰恰是精神上的抚慰和麻痹。他们自己所说的平康买笑、酒楼觅醉,非抚慰与麻痹而何?更有甚者,在广告语中还说:“宁可不娶小老嬷,不可不看《礼拜六》”,那是更趋下流了。
在实际作品中,这种麻痹性的东西比比皆是。
鸳鸯蝴蝶派的作品虽然并非全写鸳鸯蝴蝶,但“哀情”“言情”小说是它的重头戏,“卅六鸳鸯同命鸟,一双蝴蝶可怜虫”是其基调,故以“鸳鸯蝴蝶”名派,是恰当的。该派作家并非没有感到中国封建婚姻制度的缺陷,但却不引导读者去抗争,而是要人屈从,或者玩弄感情。徐忱亚的《玉梨魂》写一乡村小学教师,借住在亲戚家,兼教他家孙儿读书,这家儿媳是个美丽的寡妇,于是两人诗书往来,相亲相爱起来,但是,发乎情,止乎礼,以悲剧告终。这本“哀情小说”,在思想上是引导读者服从于封建礼教的规范的。该派还有许多才子佳人小说写的是嫖客与妓女的故事。娼妓的存在,是当时社会的一种畸形的产物,作家应该予以揭露。但鸳蝴派的此类著作,却把嫖客当作才子,把妓女当作佳人,写两者相亲相爱,则是抱着一种欣赏的态度来看待娼妓制度了。后来又有写两者相互欺诈的,那简直成了嫖学教科书。此外还有许多写良家女子与才子相爱的作品,也不过是花前月下,相悦相恋,但有情人每每不能终成眷属,那是才子多难,红颜薄命,正体现出“同命鸟”、“可怜虫”的基调,可以赢得读者的不少眼泪,此外别无什么积极作用。
与言情小说同时出现,而且同为鸳蝴派作品之大宗的,是社会小说。李涵秋的《广陵潮》是这类小说的开创之作。这部作品以扬州为背景,还反映了一定的社会内容,但因为深受晚清谴责小说的影响,一味追求“奇闻”、“怪现状”,情节过份夸张,已经不能准确地反映现实,再加上向言情小说靠拢,把主人公写成多情种子,卿卿我我,虽然增加了对小市民的吸引力,但更加冲淡了作品的社会内容。继起的社会小说,每每减少了社会内容,而增加了鸳鸯蝴蝶的成份,特别是以上海为背景的,如《上海春秋》、《新上海繁华梦》、《如此上海》、《上海风月》等,更加离不开妓院和妓女,情趣每趋低下。此类小说之坠入“黑幕书”,是必然的。黑幕小说专写吃喝嫖赌,欺蒙拐骗,名为“描写龌龊社会,揭发奸恶人心”,但没有批判,只加展览,而且写得“至详至确”,实际上则起了教唆作恶的作用。
武侠小说的起来略迟,但很快就成为书籍市场的热点,它是鸳鸯蝴蝶派作品的另一出重头戏。第一部走红的武侠小说是1923年开始发表的《江湖奇侠传》。作者平江不肖生——向恺然,是以写黑幕小说《留东外史》闻名的,何以忽然写起武侠小说来呢?此无它,市场行情使然也。鸳鸯蝴蝶派作家一向是以迎合读者口味,追求市场效益为务,从来不思以进步的思想和高尚的情操来提高读者的精神境界和改造他们的欣赏趣味,所以读者喜好什么,市场需要什么,他们就写什么。世界书局老板沈知方以精明的商人眼光,看出言情小说走俏多时,已经开始疲软,书籍市场需要有新的热点,于是他要平江不肖生改变路子,专写武侠小说。果然,《江湖奇侠传》一炮打响,不但本身畅销,而且还引起一股武侠热。特别是1928年明星影片公司将《江湖奇侠传》的部份回目改编成电影《火烧红莲寺》,在社会上造成更大的轰动,而且促使武侠热潮更加高涨。在《江湖奇侠传》和《火绕红莲寺》的刺激下,武侠小说和武侠影片蜂涌而起。就小说而言,南派有顾道明的《荒江女侠》、赵焕亭的《奇侠精忠传》等,北派有还珠楼主——李寿民的《蜀山剑侠传》、白羽的《十二金钱镖》等,总数有几百种之多,而且有些畅销书是一续再续,续个没完。然而,这些武侠小说给予读者的是什么呢?除了紧张的情节刺激以外,就是驾云御风,灵魂出窍,身剑合一,神化无方之类荒诞不经的东西。
此外,如历史小说喜讲宫闱秘事,滑稽小说善于插科打诨,消闲的目的是达到了,但留下的远非积极的影响。更有一种集锦小说,一人一段,还有叫板式的,即在前一段故事结束时,将别一作者的名字嵌入,叫出这位作者来接续,那简直是文字游戏了。
当然,鸳鸯蝴蝶派的队伍很庞杂,各人的情况有所不同,而且在漫长在日子里,变化也真不少,我们不能一概而论。其中有些作品还是有一定的暴露性的,比如,张恨水的《啼笑因缘》、秦瘦鸥的《秋海棠》,虽然全书仍是一个情字缠绵到底,总体并未超出鸳蝴派的框框,但对军阀恶势力的暴露性还较强。这些作品在写作技巧上也自有它的长处,不可一笔抹煞。鸳蝴派的作家往往是多面手,不但创作,而且翻译,有些译品还有相当的积极意义,如周瘦鹃早期曾译过一部《欧美名家短篇小说丛刊》,得到教育部的奖状,当时鲁迅任教育部通俗教育研究会小说股主任,曾给予此书以很好的评语:“用心颇为恳挚,不仅志在娱悦俗人之耳目,是为近来译事之光。……当此淫佚文字充塞坊肆时,得此一书,俾读者知哀情惨情外,尚有更纯洁之作,则固亦昏夜之微光,鸡群之鸣鹤矣。”就文学品种而言,我以为侦探小说的引进,有较大的积极意义。无论是翻译《福尔摩斯探案》,或是创作的《霍桑探索》之类,虽亦意在娱悦读者,不脱其消闲之宗旨,但其中渗透着法制观念和逻辑思维,于培养读者的现代意识是有好处的。而且,有许多鸳鸯蝴蝶派作家还是随着时代而前进的,或者说,为了能适应时代的变化而改变自己。比如,鸳蝴派作家原来是用文言写作的,有的还用骈俪文体,五四以后,他们很快就改用白话。你说他是在形式上向新文学投降也好,说它是迎合市场需要也好,总之,他是在变化。当抗日救亡运动兴起时,他们很多人都参与了文字上的救亡工作,写了很多救亡作品。由于能跟随时代前进,他们有些人的思想也提高较快,如张恨水在抗战时期写的《八十一梦》和战后写的《五子登科》,其暴露性都比以前的作品强。
由于鸳鸯蝴蝶派在当时有着很大的势力,占有很多刊物,因此,与他们有着这样或那样的关系的人很多,我们不能把他们都说成是鸳蝴派。比如,叶圣陶和张天翼,老舍和戴望舒等人,早期都在鸳蝴派的刊物上发表过作品,鲁迅的第一篇小说《怀旧》也是发表在鸳蝴派掌握的《小说月报》上,但他们的格调显然不同于鸳蝴派。有些原来是鸳蝴派作家,与他们有同样的情调,但后来却发生了很大的转变,成为新文学作家。最典型的例子是刘半农。他早期不但在鸳鸯蝴蝶派的刊物上写文章,而且的确有那种“红袖添香夜读书”的思想,应该说,是有鸳蝴派的情调。但当新文学运动起来,他一旦觉醒,就毅然转向,积极投入运动,为新文学开辟道路。所以鲁迅称赞他“跳出鸳蝴派,骂倒王敬轩,为一个‘文学革命’阵中的战斗者。”[③]
三、畸形社会的畸形文艺
一定的文艺是一定的时代条件和社会环境的产物,鸳鸯蝴蝶派文艺当然也不能例外。
钱玄同在《新青年》上论及“黑幕书”与“鸳鸯蝴蝶派的小说”时说:“此种书籍盛行之原因,其初由于洪宪皇帝不许腐败官僚以外之人谈政,以致一班‘学干禄’的读书人无门可进,乃做几篇旧式的小说,卖几个钱,聊以消遣;后来做做,成了习惯,愈做愈多。别人见其有利可图,于是或剪《小时报》、《探海灯》之类,或抄旧书,或随意胡诌,专拣那秽亵的事情来描写,以博志行薄弱之青年之一盼。适值政府厉行复古政策,社会上又排斥有用之科学,而会得做几句骈文,用几个典故的人,无论哪一方面都很欢迎,所以一切腐臭淫猥的旧诗旧赋旧小说复见盛行;研究的人于用此来敷衍政府社会之余暇,亦摹仿其笔墨,做些小说笔记之类。此所以贻毒于青年之书日见其多也。”[④]这就是说,在钱玄同看来,鸳鸯蝴蝶派的兴起和旺盛,是由于袁世凯实行专制主义和复古政策的结果。
从表面上看来,鸳鸯蝴蝶派的出现与袁政府毫无关系。因为鸳鸯蝴蝶的飞舞、嫖客妓女的调情,是并不关涉现实政治的。但这却正是袁政府专制主义和复古政策的产物。回顾历史,在大凡政治较为清明、庶民可以议政的朝代,或者中央权力式微,控制不了局面时,那些以天下为己任的知识分子总是关心社会、关心政治的,既见之于议论,也见之于文字,有时还见之于行动;而遇上专制时代,政府箝制舆论,实行文化统制政策,知识分子便只好钻入故纸堆去考古,或者专谈风花雪月,赏玩妓女风情,往往堕入淫猥,愈陷愈深。复古,是专制统治所需要的;狎妓,亦为他们所放心,虽然有时难免要装模作样加以查禁。淫猥文化之屡禁不绝,鸳蝴派之生命悠长,即此之故也。当晚清时代民族民主革命运动高涨时,鸳鸯蝴蝶的文字是不大有市场的。据阿英在《晚清小说史》里分析:“两性私生活描写的小说,在此时期不为社会所重,甚至出版商人,也不肯印行。杂志《新小说》、《绣像小说》,所刊载作品,几无不与社会有关。”但民国以后,袁世凯专权,民主革命受到挫折,文化界的情况大变。革命文化团体南社的诗人,就很有几个写起了鸳鸯蝴蝶体的小说来了。据范烟桥在《民国旧派小说史略》里说,《民权报》、《民权素》那时成为鸳鸯蝴蝶派的大本营,“辛亥革命以后,民党的文人,多数成为它们的撰述者。”这是革命失败以后,意志消沉的表现,鸳鸯蝴蝶派之兴起,正当其时也。
五四以后,鸳蝴派受到新文化运动的猛烈冲击,自然有所影响。正如鲁迅所说:“到了……《眉语》出现的时候,是这鸳鸯蝴蝶式文学的极盛时期。后来《眉语》虽遭禁止,势力却并不消退,直待《新青年》盛行起来,这才受了打击。这时有伊孛生的剧本的绍介和胡适之先生的《终身大事》的别一形式的出现,虽然并不是故意的,然而鸳鸯蝴蝶派作为命根的那婚姻问题,却也因此而诺拉(Nora)似的跑掉了。”[⑤]但是,形势一变,鸳蝴派仍会卷土重来。五四运动退潮以后,由小说《江湖奇侠传》所引起的武侠热,和大革命失败以后,由影片《火烧红莲寺》所引起的更大的武侠热,便是明证。特别是第二次武侠热的兴起,正是蒋介石取得了政权,实行新的专制主义的时候。对于革命文艺运动,蒋政权是坚决实行围剿政策的,但对于武侠热,却不但可以允许,而且还加以纵容。因为武侠热对他们不但无害,而且有益。至少,它可以用荒诞不经的神魔斗争把人们的注意力从当前的政治斗争中引开。如果你的生活太痛苦,受了什么冤屈,或对世事有所不平,那就等待专事打抱不平的飞天大侠来复仇,或者盼望主持正义的清官来拯救,自己不必起来斗争,也万万不可起来斗争。
作为复古势力的一种,鸳鸯蝴蝶派是有它的自觉性的。
当时复古派正以“国学”与新文化相对抗,有些鸳蝴派作家就想挤进“国学家”的队伍中去。鲁迅在《所谓“国学”》一文中揭露道:“现在暴发的‘国学家’之所谓‘国学’是什么?一是商人遗老们翻印了几十部旧书赚钱,二是洋场上的文豪又做了几篇鸳鸯蝴蝶体小说出版。”“洋场上的往古所谓文豪,‘卿卿我我’‘鸳鸯蝴蝶’诚然做过一小堆,可是自有洋场以来,从没有人称这些文章(?)为国学,他们自己也并不以‘国学家’自命的。现在不知何以,忽而奇想天开,也学了盐贩茶商,要凭空挨进‘国学家’队里去了。然而事实很可惨,他们之所谓国学,是‘拆白之事各处皆有而以上海一隅为最甚(中略)余于课余之暇不惜浪费笔墨编纂事实作一篇小说以饷阅者想亦阅者所乐闻也’”。这算什么“国学”呢?适足给“国学”丢人。所以鲁迅说:“‘国学’乃如此而已乎?”
鸳鸯蝴蝶派小说虽然算不上“国学”,但也总是旧文化的一种,——是旧的通俗文化的延续。它之所以能得到发展,也是一种需要,是某种国民心态的反映。正如鲁迅所说:“凡当中国自身烂着的时候,倘有什么新的进来,旧的便照例有一种异样的挣扎。”“上海之有新的《小说月报》,而又有旧的(?)《快活》之类以至《小说世界》,虽然细微,也是同样的事。现在的新文艺是外来的新兴的潮流,本不是古国的一般人们所能轻易了解的,尤其是在这特别的中国。许多人渴望着‘旧文化小说’(这是上海报上说出来的名词)的出现,正不足为奇;‘旧文化小说’家之大显神通,也不足为怪。”[⑥]
中国旧小说自有它的优秀传统,但是,鸳鸯蝴蝶派并没有吸取其精华部份加以发展,反而把它引入歧途。比如,古之人情小说,曾出过《红楼梦》这样伟大的作品,到晚清,则堕入狭邪小说,鸳鸯蝴蝶派的言情小说,不是继承《红楼梦》的优秀传统,却承狭邪小说之遗绪,推波逐浪,愈走愈远;讽刺小说,我们曾有过《儒林外史》这样的杰作,但到得晚清,就走了样,变成“辞气浮露,笔无藏锋,甚且过甚其辞,以合时人嗜好”的谴责小说,它与讽刺小说貌似而神异,鸳鸯蝴蝶派又把它发展成社会小说,以至黑幕小说,则更加等而下之了;武侠小说,则是把侠义小说、公案小说、神魔小说融于一炉,而发展了荒诞性和奴性思想,以适应时势和小市民读者的需要。
总之,作为旧文化的一个组成部份而言,鸳鸯蝴蝶派不是发展了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而是发展了它的糟粕部份。这样的艺术流派,而能延续那么长的时间,实在并不是什么好事。
注释:
①《革新〈小说月报〉的前后》,《我走过的道路》第15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②《南腔北调集·小品文的危机》,《鲁迅全集》第4卷第577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③《花边文学·趋时和复古》,《鲁迅全集》第5卷第535页。
④《“黑幕”书》,1919年1月9日《新青年》6卷1号。
⑤《二心集·上海文艺之一瞥》,《鲁迅全集》第4卷第294—295页。
⑥《集外集拾遗补编·关于〈小说世界〉》,《鲁迅全集》第8卷第111—112页。
标签:鸳鸯蝴蝶派论文; 鲁迅全集论文; 鲁迅的作品论文; 蝴蝶论文; 文艺论文; 小说论文; 江湖奇侠传论文; 文学论文; 小说月报论文; 鲁迅论文; 玉梨魂论文; 新青年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