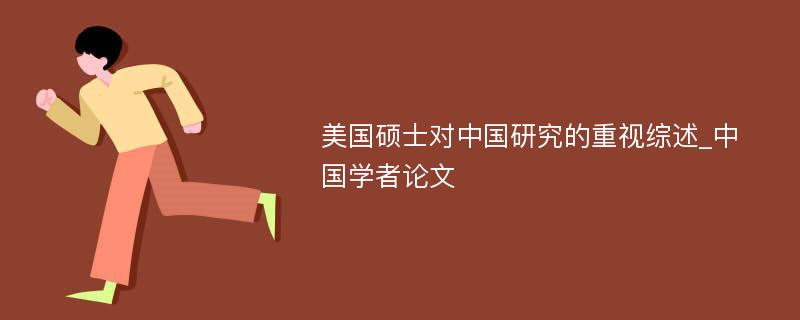
美国大师重视中国学的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美国论文,国学论文,重视论文,大师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我们在展开对海外中国学研究的时候,应该注意这些国家的中国学家对自己走过的学术道路的回顾和探讨,这些反思和总结有利于我们对研究对象国中国学发展史的深入认识和了解。
对中国学研究的总结从未间断
还是20世纪20年代的时候,美国学者中就有这样的回溯探讨。耶鲁大学赖德烈曾经一连写了3篇文章,总结前几十年的美国中国研究,分别是1918年的《美国学术与中国历史》、1921年的《过去七年的中国史研究》以及1930年的《过去九年的中国史研究》。这段时期是美国的中国研究向学院派汉学转型的时期,出现了一些重要汉学家和汉学著作,所以他对这段时期的研究走向十分重视。他的文章不仅注意中国国内的研究情况,也观察国际汉学的新动向,并由此探析美国汉学研究的新成果。他认为德裔汉学家夏德、劳费等学者对美国汉学的贡献是巨大的,相当程度上影响了美国汉学的发展;他也为美国本土汉学家柔克义、贾德的出现自豪,认为他们的贡献是卓越的。同时,他认为1928年燕京学社的成立和美国促进中国研究委员会的创建是美国中国学发展史上的大事,之后的研究成果“会有显著的成长”、“几乎没有国家能像中国这样通过文化影响人类的很大部分,也几乎没有国家在这么多的世纪里统治了地球上如此众多的人民和如此富饶的一片土地”。
20世纪50—60年代是美国中国学发展的又一重要关头。麦卡锡主义的困扰导致中国学地位的失落引起美国朝野的关注。1958年国防教育法案的颁布刺激中国研究重兴高潮,由此也引起对这波高潮的再总结和再思考。哥伦比亚大学林德贝克的《理解中国:对美国学术资源的评估》是这次反思论著中最有分量的一项。这是应福特基金会的要求撰写的一个关于中国学研究的调查报告。他对整个这段时期的美国中国学的状况作了梳理和分析,包括资金的投入、所引起的语言训练与设备的变化、教学研究队伍的发展、研究项目和学科建设、研究环境的改变等多个方面。福特基金会对中国学的资助是全球性的,所以还涉及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中东和其他西方国家中国学研究的考察,为此林德贝克还跑了世界多个国家和地区。这份以数据、分析、识见见长的总结一出现就受到关注。费正清、鲍大可等美国重要中国学家都非常赞赏这本书的资料和分析,认为是一项有眼光、有长远价值的研究,对了解这段时期美国中国学有重要参考价值,是对美国乃至世界中国学研究的贡献。
从费正清的“冲击—反应”论到柯文的“中国中心观”是一个相当大的历史观和方法论的演变过程。柯文的《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是关于这一转变的重要总结和反思著作。这本书既回顾了“冲击—反应”论兴起后在美国中国学史上的影响及其代表作的情况,也总结探索了批判、修正“冲击—反应”论的过程。作者特别注意到何炳棣等华人学者对这一历史观念演变所起的作用,也注意到孔飞力、魏斐德等学者在他们的著作中对修正费正清观念所作的努力,并将整个演变称为是中国中心观念形成和发展的过程。柯文认为“中国中心观”强调从中国而不是从西方着手的探讨,主张历史学与人类学等诸多学科的结合,开展区域和地方史的研究,强调把中国社会“纵向”分为不同阶层探讨,推动下层社会史的研究。这一著作是战后美国第二代中国学家研究群体及其理念崛起的标志之一,是对这一阶段中国学研究方法论的创新探讨。柯文的这本著作是美国中国学发展史上有里程碑意义的作品。
总结和反思涉及诸多学科
美国学者对中国学研究的总结和反思也涉及诸多学科,基本上各个研究领域都会有这样的研究作品。在中国近代史研究方面,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刘广京的《三十年来美国研究中国近代史的趋势》被认为是重要的中国学反思作品。作者有自己的关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学术体系和理论框架。他认为美国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经历过费正清“西潮冲击论”、列文森“历史遗产论”、芮玛丽“传统障碍论”等几个具体的理论模式,尔后又出现“内在动力论”、“民族觉醒论”以修正费正清的“西潮冲击论”。他认为史华慈、张仲礼、何炳棣、萧公权、魏斐德、孔飞力等学者的著作和研究理念,都是对“西潮冲击论”的修正。所谓“民族觉醒论”,是对当时中国国情下自觉自愿新趋向的研究,与历史遗产的内在动力论有很大区别。他认为孔飞力的太平天国研究就有“民族觉醒论”的特点。不过他又指出,光讨论“民族觉醒论”是不够的,周锡瑞的辛亥革命研究成果表明,事实上“中心问题又转移到经济史和社会史的关联处了”。刘广京对美国中国近代史研究过程中这些模式和理念演变的梳理非常细腻,是了解20世纪50—80年代美国中国近代史研究走向的重要文献。
中国妇女史、性别史研究是美国中国学研究的新领域,也是后现代主义思潮和新文化史研究兴起以后的新探索。美国学者在这方面的反思和分析文章也相当多。费侠莉《明清时代的性别、医学和身体——中国研究中女性主义历史写作的历程》、王政《国外学者对中国妇女和社会性别研究的现状》、姚平《中国古代史中的宗教与妇女研究》、程为坤《西方学术界的中国妇女与性别研究》等,都对美国以及西方国家的中国妇女史、性别史研究的发展作了总结和回顾。他们注意这一研究兴起的社会背景和学术背景的探讨,关注与世界女性主义学术的关联。撰著者充分肯定女性史学者对中国妇女社会研究的丰硕成果,肯定他们对历史上妇女主体性和能动性的揭示,认为女性成为边缘化人群部分地是由长期以来男性中心的历史制造出来的神话。学者们还强调批判“传统—近代”模式的重要性,女性史、性别史研究的发展正是有针对性地阐明了中国历史传统的丰富性和多样性。他们还深入探讨了这样一些很具体的问题:在性与性别问题上,中国儒家、道家的解释与弗洛伊德等西方学者的解读完全不是一回事。
“新清史”可谓当下美国中国历史研究的热点。我们也看到关于这一研究的学术梳理、探讨和反思文章,例如欧立德的《满文档案与新清史》、柯娇艳的《新清史研究的历史与理论》。两位学者都对美国清史和“新清史”研究作了十分具体的回顾和梳理。欧立德的文章主要就“新清史”的学术背景进行探讨。他说有些学者对多半出于“区域研究”模式学者的“西方中心”偏见感到不满,认为后现代主义对补正中国史这个历史研究中理论相对较贫乏的领域很有用。而另外一群学者则质疑,是否只有西方的中国史家将其文化偏见带入研究当中,而一些深植于中国学界中的诠释典范也需要拿出来重新检验。柯娇艳的文章则分“概述”、“旧清史”、“新清史”、“两派分列:‘满族中心观’与‘清史研究’”几个大部分,对从“旧清史”到“新清史”的演变作了全面探讨,认为将满族作为研究的主体能将清史置于世界史范围考察,她质疑迈克尔·弗朗兹关于清代国家兴起产生于对汉族政治体制文化适应中的观点。而在这个问题上,海内外学者几乎都能肯定“新清史”的研究特点和成绩,但也有学者特别强调,民族和国家认同是同等重要的。
虽然各家各派所总结的侧重点不同,但没有疑问的是,各领域研究的反思文章对中国学研究的总体发展有重要的基础建设意义。
着眼于经验和大问题的思考
在美国的中国学研究总结和反思的文章中,也有相当重视经验和规律问题探讨的。这些文章往往不只是中国学研究情况的梳理,更关注寻找有重大启示的答案。
美国当代中国问题研究学者何汉理曾有一篇题为《美国当代中国学的演变与展望》的文章,发表于1993年。主要对1949年以来当代中国研究的情况进行总结,基本以20世纪50—60年代为第一阶段、70年代为第二阶段、80年代为第三阶段,然后对90年代以后的趋势进行展望。作者认为1949年以来几个阶段中国学发展,基本都受中国国情演变的影响,呈波浪式发展态势。因此在未来的发展中,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如何改善自己的知识结构、形成宽广的知识视野和方法,以及争取各学科紧密结合和跨学科研究等诸多问题都提了出来。何汉理认为,能积极参与大众教育和政策讨论这样的活动,是这支队伍已经形成的传统。但要适应对中国这样有着诸多变化的国家的研究,专家应该得到更客观、综合、准确的知识,“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应该在90年代付出更大的精力和资源去接触超出他们小圈子之外的更广泛的读者与听众”。此前,傅高义曾认为美国当代中国研究的最大失败是不能预测“文化大革命”,何汉理显然是从另一视角的反省。他强调当代中国研究深入的希望在于研究者更出色的行为和作风。
裴宜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国的中国学研究:50年》也是一篇这样的重要文章,试图对50年来美国的当代中国研究作总结。她认为美国一些资深学者利用中国改革开放的大好机会充分地占有了资料,写出了很好的作品。她特别强调新资料对于中国学研究的意义。她还探讨了如何作好跨时段、跨时空研究当代中国学的问题。在她看来,费正清关于1949年以后一切今非昔比的观点是不当的,将1949年前后截然分离的做法是不合适的。她认为历史无法分割,1949年以前的影响今天无处不在,人民对地方历史和语言也不断萌发新的兴趣,这都需要专家适时进行新的跨时空比较研究。这种研究要说明现在与过去的区别,展开不同地区的比较分析,“这就要求我们脱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初期通常使用的观察方式”。作为当代中国问题研究专家,她比何汉理更强调历史方法和历史意识。她告诫她的美国同行:严肃认识历史和深入了解现实情况将更为有益。
柯文的《变动中的中国历史研究的视角》是他世纪之交的新文章,是对他个人和美国中国历史研究的一次新反思。这篇文章是他“中国中心观”以后的一次新探讨。其中的一个重要观点,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越来越怀疑过于夸大中国与西方文化差别的问题。他认为“冲击—反应”论实际上强调中国社会和文化的特殊性质,文化的“内在本质”静止不动;“中国中心观”强调了对过去更重弹性和变迁的看法,但对历史过程“高度的敏感”使“文化作为一种解释性的因素退居幕后”。他认为过分强调文化差异颇不妥当,难以理解文化所经历的变异,“也可能会忽略了某文化群体的思想和行为往往反映了跨文化的、人类与生俱来的特性”。他强调在探讨文化差异时,“必须注意人类社会有许多共通的方面”,这样才能对一个国家有全面、细致、眼光更广阔的认识。他认为要注意突破西方和中国历史学家以不同理由、不同方式为中国和中国历史设定界限的做法,要把中国历史从神秘烟幕和狭隘眼光所造成的框框里拯救释放出来,使生活在中国境内的历史经验,“对西方人民显得更容易理解、更有意义甚至更重要”。
在美国,往往是那些有重要学术成就的学者,更关注并亲自参与这类学科研究的回顾、总结和反思工作。他们的亲自领衔正说明这类研究的重要性和价值。所以我们对海外中国学的研究,要十分重视这一类的学术总结和反思。不仅能使我们从这些探讨中了解到更多学术发展史的详情,更在于能从这样的总结中把握一些重大理论关切与方法走向,包括及时发现一些重要理论谬误并适时展开反批评。如同我们重视《史通》、《文史通义》一样,这一涉及学术史问题的探讨越来越显得重要了。
